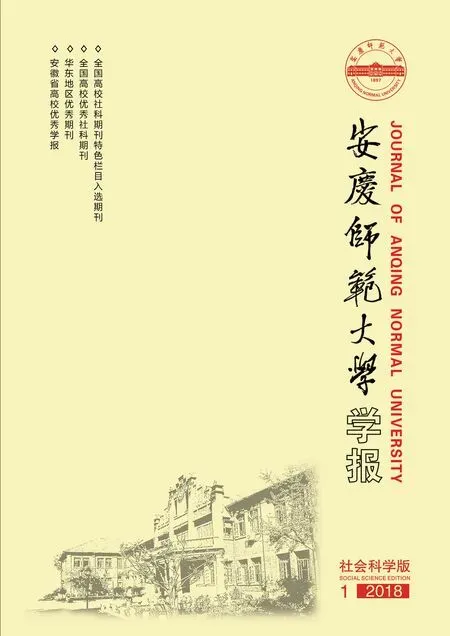浅勘“凤鹤之争”
欧璐媛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530004)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凌鹤与姚苏凤因《路柳墙花》引发的“凤鹤之争”(或“凤鹤之啄”),是紧接着“软硬之争”将左翼人士与论敌的影评斗争推进到白热化的标杆性事件。这折射出中国电影在“以变革与创新为标志”[1]的发展阶段的“第一个黄金时期”[2]重重力量角逐和文化冲突。然而学者们对于“凤鹤之争”并未过多关注,虽然丁亚平以其对电影史的敏锐嗅觉发现了作为“电影史与文学史交叉点上”[3]的“凤鹤之战”,但只在《中国电影历史图志1896—2015》一书中略谈二者的主要争论脉络而没有延展至对整个事件较为系统的评议。唯张华在《姚苏凤与1930年代中国影坛》中详细地梳理了“凤鹤之争”的经过,基于史料的翔实把握而有着较为客观的评述。但她不是以时间节点而是以主要论争文章的内容作为行文线索,侧重站在姚苏凤的角度上反观论战的主要分歧点,作论争内涵之辨析,却忽视了“凤鹤之争”作为一个独立性事件的阶段性发展及优劣处之意义阐释。基于上述学者对于“凤鹤之争”的多重节奏、面向、隐情、因由诸问题尚未详细廓清,至今尚付之阙如,本文尝试逐一进行问题清理。
一、“凤鹤之争”的多阶段与多面向发展
“凤鹤之争”关联的话语场域,线索错杂,不能简单地“一目了然”。根据这场“笔战”的报刊原文,笔者认为按时间发展,分阶段细加审视,似有必要。
第一阶段为开端与发展,由二者直接交锋而起,影评人纷至助澜。1934年9月15日,姚苏凤编剧的《路柳墙花》上映。随即《申报·电影专刊》和《大晚报·火炬》分别刊发了凌鹤的两篇影评:《评〈路柳墙花〉》与《〈路柳墙花〉小言》(化名为吟秋而写)。两篇影评站在影片社会价值的高度上对《路柳墙花》进行严厉的批判,驳斥其迎合落后小市民观众的“生意眼”。凌鹤认为编剧没有看到现象之下隐藏的本质,因此无法有力的暴露出社会之黑暗面,反而在一些场景之中歪曲了主题,没有为观众指示出正确的出路。凌鹤锋利的矛头开始便直指姚苏凤。
这引起了姚苏凤的强烈不满,立即在其主编的《晨报·每日电影》上进行反击,发表了《〈路柳墙花〉编剧者言》与《站在一个剧作者的立场上,揭开凌鹤的影评的内容:从今天起,我们来开始影评的“清洁运动”了!》等文章。基于凌鹤的影评,姚苏凤有针对性地进行“清理”。这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姚苏凤认为凌鹤的两篇影评的标准不一。在《申报》上以实名而写的影评颇有讨好制片者之嫌,而在《大晚报》上以化名“吟秋”所写的影评却“暗地里”“不负责地放袖箭向剧作者袭击”[4]。其二,“申诉”凌鹤基于不同的标准对待同期上映的《路柳墙花》与《黄金时代》。两片都曾受到电检会的阻碍而删改,而凌鹤却独对《黄金时代》宽容。他深感不解,认为凌鹤此举动机不单纯,指责凌鹤企图杀害了中国电影,要开展影评的“清洁运动”。姚苏凤以强势的姿态拉开二者“论战”序幕。凌鹤也并未沉默,第一时间针对姚苏凤的质疑与指责,作《谁杀害了中国电影》一文,后又作《敬答影评人及戏作者、每日电影编辑、明星公司宣传部长姚苏凤先生》,正式摆开迎战之姿。一时,影评人纷纷发表评论,加入“论战”。
由凌鹤的影评为起始点延至姚苏凤回击以及其他影评人出场,“凤鹤之争”呈多方鼎力之势。但张华将“凤鹤之争”定性为“姚苏凤、石凌鹤及其各自代表的《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在相关电影活动的交往中不断产生摩擦的必然结果”[5]202-203,由此将二者论战之开端述及1933年两刊之间围绕《恋爱与骨肉》以及《古国艳乘》的论争。张华在此问题上忽视了二者及二者所在刊物后面复杂的话语环境,若单纯以二者思想倾向为限,则考察二者影评文章,两位主将当时都无法脱身“意识论”大流。若以刊物的价值取向为限,虽二者同为编辑,但姚苏凤受国民党CC派潘公展的钳制、石凌鹤受《申报》“老报刊”保守观念的制约等因素都无法忽视,那么刊物之争是否可以完全以二者观点定性?若不然,那么二者的论争又何以以刊物之争而来呢?因此,笔者认为将“凤鹤之争”开端定于二者直接之交锋更有利于问题的明晰阐释。
第二阶段为高潮与落幕,“战况”围绕《影迷周报》刊出的文章而涨落。《影迷周报》第一卷第二期出刊,为“影评和剧作之战”专号,收录之前的各方面评论文字。编者韩平野认为此次“凤鹤之争”将比“软硬之争”成为“更有意义的一次论争”[6],积极呼吁读者、影评人投稿,颇有将“凤鹤之争”推向高潮之势。除开凌鹤与姚苏凤两位主要论战人物的影评文章之外,《影迷周报》按照出场顺序将另外九人的影评依次刊发,分别为:毛羽的《路柳墙花》、严郁尊的《路柳墙花》、萍萍的《路柳墙花》、李明明的《关于“路柳墙花”》、芜青的《评〈路柳墙花〉》、鲁思的《路柳墙花观后散记》、老藤的《敬祝尖众眼福无量》、舒湮的《路柳墙花》以及叔常的《“站在剧作者的立场”慰姚苏凤先生》。至此,“凤鹤之争”一时甚嚣尘上,其内涵也呈现出多面向发展的趋势。
一方面,在针对影片本身的批评中,这些影评人多集中在《路柳墙花》所指示的出路问题上,认为结局“实在不太巧妙”[7],“他只是站在那都市的河埠上伤感的喟叹着,目击着这‘来者自来,去者自去’的愚昧之群”[8],这便造成“想要剖白社会的深层,无论如何力量是不够的,努力的结果还不是复写出社会的浮面”[9],“回到农村去”的出路,在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的左翼影评人看来,不仅仅是编剧者对于当时社会情势有着模糊不清的认识,也深层次展现出小资产阶级迷茫失措的姿态。这势必会在“化大众”的过程中加入有害的“毒素”。除此之外,虽有影评人从暴露的力度、趣味低级、生意眼等方面进行评价,但他们的基本立场也都无法逃离意识形态批评之窠臼。影评人的不断加入,对《路柳墙花》形成了围剿之势。
另一方面,稍后的《影迷周报》第三、第四期陆续刊登各方评论,内容已经从对影片本身的批判转为对二者论战的总评。有论者认为二者论战“一定能够给予一些关于中国目前之电影地趋从及指示”,故“反对调解苏凤与凌鹤之争”[10]但也有人指出这是“一幕活剧,一幕不能再丑的丑态的暴露”,二者的论战已经从对内容的争论而转变为“疯狂的谩骂,甚至于无理由的引人私事乱说一泡”,“暴露了自己的‘不可教’与‘浅薄’,不单只是会阻碍到影评的进行”[11]。姚苏凤的《站在一个剧作者的立场上,揭开凌鹤的影评的内容:从今天起,我们来开始影评的“清洁运动”了!》一文,将二者恩怨从《一枝花》的影评述及《残春》,将凌鹤对于《路柳墙花》的两篇影评视为“敌意”,并且攻击凌鹤为“小丑式的政客”、“跑街”,指出他妄图控制影评界的野心,因此要将他从影评界清洗出去。
姚的内容、措辞已经超出了《路柳墙花》而言其他,将论战带离轨道,以至于大多数影评人对论战的意义产生怀疑。作为姚《每电》的同事,舒湮“于10月4日以《每电》编者的名义刊出《结束苏凤、凌鹤间的笔战》,要求双方就此停战,不便事态扩大。‘关于今后影评的如何改善与如何执行影评的‘清洁运动’,应该共同从长计议’”[12],以此表示对姚苏凤提出“清洁运动”动机的不满。甚至于高呼“论争”的《影迷周报》在第四期时也总结道:“凌鹤苏凤二君关于这一次论战的最要的真义,是放弃了的。”[13]《影迷周报》的总结性文章仿佛也将二者的直接论战宣告结束,凌鹤与姚苏凤再没有因为《路柳墙花》而在报刊上有文章之交集。二者也因陷入互揭私德的泥沼之中而没有得出论战的实质性结论。论战开始至落幕不足月余,如狂风骤雨,突袭各大报刊,又快速的归于平静。暂时的雨过之后看似平静,实则暗涌翻腾。
第三阶段乃为“凤鹤之争”余绪,二者借《循环》之辩再起事端。10月25日,凌鹤评苏联影片《循环》,“我又谨向观众们推荐这一名作”[14]。紧接着,26日《每日电影》刊出了“契夫”所写的《希都琳与〈循环〉》,文中指出苏联电影的问题,并且在“每日谈座”栏目中,将沈西苓看《循环》时打瞌睡为例引证《循环》不是名作,讥讽凌鹤“‘强作解人’地向观众‘推荐’为‘名作’”[15],又向凌鹤开火。31日,凌鹤作《〈循环〉评补——并答〈每日电影〉诸君子》一文,给以正面的回应:“很可笑的,因为我推荐了一下《循环》,便使《每日电影》某君子(大概又是姚苏凤先生吧?因为我始终是他的敌人。可惜的是每日谈座近来不见一连署名了)满不高兴,在‘党同伐异’的条件之下,认为我的批评又‘阻碍’了他的‘清洁运动前途’。”[16]“再后便有姚苏凤的‘质问’两点,再后又有凌鹤的四六骈文一则,在他们之间,似乎仍在小接触,可是到底不过是大战之后的余波而已。”[17]文中提及的质问、四六骈文等史料笔者实难收集,便也无法据此直判二者是否仍有蠢蠢欲动之势。
但刘日新在《影迷周报》第一卷第九期的《新的展开》中,认为,围绕《循环》而引起的“小接触”是沉寂下去了的“凤鹤之争”的“余绪”,并引出姚苏凤友人的话:“这一次论战他承认是惨败了的,静待时机反攻可也。”[17]考察刘日新文章的刊出时间以及《影迷周报》对“凤鹤之争”的关注度,刘日新的解释较为可信。此外,舒湮也曾回忆道:“凌鹤对此度量宽容,第一次主动为《每电》写稿,表示和解,苏凤犹悻悻然,不欲敛手。”[12]舒湮为姚《每电》同事,又与左翼十分亲近,他对事件的说法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两者皆言姚苏凤不欲收手,则考察《循环》的苏联背景及左翼人士的关注度,确是他“反攻”之机。张华顺延至此,也认为《每日电影》“对苏联影片的论争发生在‘凤鹤之争’的余绪之中。”[5]167二者论战无果而终,紧接着,苏联影片《循环》上映,借之二者文章再见诸报端,又起一番辩论之势。笔者认同上述观点,《循环》实乃《路柳墙花》引申出之外延事件,应归属“凤鹤之争”。
“凤鹤之争”中,姚苏凤多方涉足影场、影评、报刊等,深谙中国20世纪30年代影坛,为何对于凌鹤批判《路柳墙花》如此“盛怒”?而身为影评人的凌鹤又为何被姚苏凤扣以多种帽子而大加指责呢?这应当关涉各自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及无法忽视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即“软硬之争”。
二、寓于“软硬之争”话语之下的“凤鹤之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多方势力在不断争夺着电影话语权。以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教育电影”与左翼进步电影各据一隅。无法忽视的是,刘呐鸥等“软性论者”也以其纯艺术的旗号与左翼公开叫板,形成了围绕电影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争鸣。“软硬之争”正酣,“凤鹤之争”的登场是电影理论不断碰撞从而具体表现到一部电影上的必然结果,成为寓于“软硬之争”话语之下的具体事件。因此我们必须厘清二者在内涵中的关联性,考虑到“软硬之争”涉及的领域十分繁杂,本文仅将从二者紧密关联的三个方面进行辨析。
其一是形式与内容之辩。软性论者从一开始就针对左翼影评而举起他们的理论大旗,以自我的“软性”定义左翼的“硬性”,这也就无法摆脱二者互相对垒的局面。“软”“硬”双方,各自站在“形式”与“内容”的角度上进行割裂的机械论争辩。“形式至上”、“内容偏重主义”等词汇一时成为笔战双方的高频词。江兼霞与鲁思的文章最能为双方观点之代表,为了拔高自我而打压对方,这就导向双双落入二元论的藩篱。软性言论自有其不够严谨性,但这也使左翼影评的机械化弊端受到关注。
《每日电影》作为“软硬之争”的主战场之一,姚苏凤的主编位置使他主动或被动的接触两方言论。又因他电影编剧的另一身份,双方的争论思想在他身上所引起的变化必定是复杂的。他在主编《每日电影》期间,与左翼影评人深交,大谈“意识”,“面对血与火的外部环境,他们受到显而易见的刺激、激发、考量而具有活力;整个时代、社会把他们带离片场,带离艺术、娱乐之类的问题,转到有意义得多的时代关怀、社会改变、民族存亡的问题”[18],这是知识分子忧心天下的责任感之体现。但是,随着“软硬之争”不断推进,左翼影评的弊端不断显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姚苏凤对于“给眼睛吃的冰淇淋,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等追求纯粹艺术享受的倾向有着极大的共鸣,这就不禁动摇他继续追随左翼话语的步伐。
《路柳墙花》上映后,围绕其影片内容,影评人蜂拥而至,以凌鹤的两篇批评为代表,将其内容驳斥得一无是处,认为该片“除了跳舞,床上调情,诱奸开旅馆,租小房子等等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19]?由此得出了“这里没有高度的艺术成就,而有高度的商业成就”[19]等结论。在已经注意到左翼影评之机械化弊端的基础上,开始有了艺术探索自觉的姚苏凤必将给予猛烈回击。他在《编剧者言》中就表示“既然要暴露都会丑恶面,当然得写都会里所特有的许多丑恶的事实……你们可以看见我屡次用‘洋钱钞票’的特写来强调这些事实与经济的关系,还可以看到几张同样的叠用的‘东家好’的字幕”[20],力图和谐形式与内容,在电影中着力用镜头的特写与情境的氛围融合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倾向。“为了剧的效果起见,我编剧时所特殊注意用力构造的一点便是我使它做成一个‘悲喜剧’。(自然,这是我的大胆的尝试,不敢自夸其手法之胜利。)”[20]诚然,“凤鹤之争”中,凌鹤囿于左翼影评,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内化为自觉意识,在否定其内容的基础上将姚苏凤在技术上的尝试一票否决,甚至绝口不谈,恰恰没有逃离软性论者指责的“内容偏重主义”。作为一位在电影形式上有着自觉探索的导演与编剧,姚苏凤自然无法认同偏重内容的左翼电影模式。
二是艺术性和倾向性之争。穆时英曾在《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一文中谈及:“正确地,忠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就不能有倾向性,有倾向性,就不能是反映客观现实的。”(穆时英《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21])他把倾向性与艺术性置于二元对立的绝对之中,认为电影中二者不可兼得,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艺术性作为电影的独一性。作为电影反映现实观点的拥护者,尘无随即针对穆时英的观点进行了反击,“反映客观社会的真实的,那么他必须倾向于进化。所以他的倾向性越大,必然是越能够反映客观的真实的作品,相反的,蒙蔽真实的作品,他们倾向越大,必然是更不真实的作品,倾向性和真实,他不像穆时英先生那样理解的。”(王尘无《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22])尘无试图辩证看待倾向性,倾向性可分好坏,进化的倾向必然会最大程度地对现实进行剖白,然而蒙蔽真实的倾向只会用虚假的现实弱化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如鲁思认为的二者不应割裂开进行评论,左翼影评人并没有将艺术性与倾向性对立起来,只是将倾向性摆在首位,艺术性为其次。
从姚苏凤的《剧作者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构思这部剧的脉络走向。他力图将各自支离破碎的情节在戏剧冲突中关联起来,其偶然性的设置也是在人物的复杂关系中得出的必然结果,并没有过多的强拉巧凑之处。凌鹤虽然认为《路柳墙花》因其情节上的偶然性设置弱化了暴露现实的力量,“她们母女姑嫂之在上海受了一番欺骗与凌辱。不过是偶然的遭遇……剧作者绝对没有本质的说明,那是经济恐慌或事业问题的严重”[23],否定了电影中阻碍暴露现实的艺术化因素,认为偶然的设置是剧作者的讨巧行为,只会将观众蒙蔽在虚假的现实之中。但凌鹤并没有否定其艺术性,承认“对于一个故事的结构,他利用许多偶然的曲折而编制成功……比较《残春》的纯淫靡生活之描写,确见积极一些”[23]。在意识的进化倾向上,他肯定了姚苏凤偶然性设置的成功之处。虽然只是“一些”,但也可以辨析出凌鹤并没有完全将倾向性与艺术性二者割裂。这是左翼影评人较之于软性论者的可取之处。
其三是电影的基准问题之论。在这一问题上,软性论者站在电影本体的角度上提出了“影片制造,电影批评,必须先从它的艺术的成就、技术问题入手,内容是其次的”[24]的观点。左翼则站在社会价值的角度上将意识形态作为影评的基准。双方各自坚持的出发点不同,则很难达成共识。
张真在《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中指出:“一些批评者们以苏联为样板,急于把都市的芸芸众生转变为无产阶级普罗大众,把电影转化为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工具和文化武器。因此,他们并未清晰、明确地为这些目标服务的电影实践视作政治上的倒退或者是彻底的反动。”[25]电影需要指出一个进步的方向以教化民众,这是左翼思维的典型,因此“并未清晰、明确地为这些目标服务”的影片无法逃脱被批评的局面。凌鹤评《路柳墙花》时,便在文末指出:“其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进工厂去的呢?”[23]姚苏凤早在1933年《评〈清白〉》中就已十分超前而准确的回答了凌鹤的质问:“在今年,电影界有一个趋时的风气,便是不顾勉强与否地喜欢在影片里插进一些‘工厂’的场面或字幕中插进几句‘思想先进’的话——我不是说这种场面与这种字幕不需要,但我总觉得‘与其生硬勉强,不如没有’。”[26]张华引证了大量的回忆录、影评文字、报刊文章来说明姚苏凤与左翼影评人结盟转而亲近“软性论者”是由于他有着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又难以摆脱固有的小资产阶级文人习性。这两方面思想不断碰撞,争夺着姚苏凤随着社会时局、人生阅历的改变而改变的社会活动的主导思想。姚苏凤本着对电影技术的尊重,不愿勉强加入会破坏电影整体结构的因素。即使他已经敏感地认识到,左翼影评背后是有着明确的任务的,他们企图通过影评活动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恰如孟君所说的“斗争的胜负只揭示出话语权的归宿,并不能证明理想的虚无”[27],姚苏凤在争论中不断流露出的观点,是其返回自身,对追求电影艺术化观念的皈依。《路柳墙花》可以看做是他亲近“软性论”而拒绝左翼话语的一次创作实践,断然不会为了“趋时”而“勉强”加入这些场面。他抛开了大时代中意识的限制,离开了共语的范畴,关注电影本身,发出了一位独立电影人的声音,彰显了自己执念的电影理想。
因此,当以凌鹤为首的左翼影评人以“意识论”对《路柳墙花》大加讨伐时,姚苏凤一改往日谦逊的知识分子风度予以反击,将凌鹤冠以“小丑式的政客”名号欲以揭露他影评的“不正当作用”。之后,由姚苏凤电影观念的变化、《每日电影》在“凤鹤之争”后的转向可知,“凤鹤之争”已经不单纯为两位主人公之间的辩论,而是在空前政治化的三十年代上升为寓于“软硬之争”之中的电影界话语权的争夺。
三、“意识论”模式之下影评内涵的扩大与缺失
“凤鹤之争”之后,仍不断有影评人对此次争论进行总评。唐纳及前文提到的刘日新两者力图扭转“凤鹤之争”无谓的谩骂而转入问题本身,呼吁“我们只允许有理论上的斗争,而不应该有意气之争”[28],以此达到“凤鹤之争”应该达到的理论层次,即“广泛的讨论电影批评,如何走上健全之路,如何建立电影批评的权威”[17]。但囿于当时的话语环境,他们所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流于浮面。
从“凤鹤之争”的相关影评文章来看,影评人都站在社会价值的高度上来对《路柳墙花》进行评价。若不首先讨论凌鹤指责“剧作者或导演在社会教育的意义上,他们应当是无可容恕的罪人”[19]一言,就在态度较为平和的舒湮笔下,《路柳墙花》也只是“一种力量微弱的婉讽而已”[8]。左翼影评的“唯意识”理论,已经直接成为评判剧作者进步与否的标杆。这背后隐藏的是判断一位剧作者对于无产阶级政治话语的认同度。因此,笔者试图站在历史的大视野下,窥其在“意识论”影评模式之下的弊端。
首先,政治话语的扩大化。在与“软性论”者的辩论中,左翼影评人已经从电影艺术的本体问题跳跃而到政治话语之上,这无形中就使论战的内容与意义扩大化。
凌鹤回忆说反动派“除军事上对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外,对上海左翼文化也妄图进行‘围剿’。而革命文艺界则进行针对性的反‘围剿’,如我们组织力量对于反动的‘软性电影论’进行反击并取得胜利。”(凌鹤《30年代左翼戏剧运动及其它》[29]72)由此观之,左翼影人与“软性论”者的辩论已经达到与军事“反围剿”的同等高度之上。李少白也指出,蓝衣社特务捣毁艺华影片公司不仅是针对左翼文化运动和新兴电影运动的,而且直接配合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实行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可见,1930年代对“软性论”的批判,是在左翼势力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性活动之一。“凤鹤之争”之后,左翼影评人对《每日电影》采取中立的态度,洪深、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随即退出,孤立姚苏凤之后的《青春线》一片,无一人评论。左翼影评人与亲近“软性论”的姚苏凤的划清界限,是将“意识论”的影评模式下的政治话语扩大化的鲜明表现。但是,“凤鹤之争”是由双方的独特生命体验内化为各自坚守的信念而外现于电影观念的分歧。在对“软硬之争”愈来愈趋于弹性评价的当下,对于活跃在公共领域之中的电影人的观念的构成,我们需要作辩证解析,不应简单地将二者置于政治对立面来考察其中缘由。
“凤鹤之争”的结束,标志着《每日电影》这一“左翼阵地”的丢失。从1934年起,左翼在影坛上的势力不断收缩,这不仅有来自南京国民政府“清党”的血腥压力,更多的是左翼人士在面对不同声音时统一采取了敌对的姿态。虽然为了防止暴露身份,左翼有意识的收敛锋芒,但是艺华的被捣毁、鲁思的被迫西走等事件都无疑提醒了左翼人士一腔热忱后面需要平衡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活跃的左翼人士趋从情感的偏向,全局观念没有得到有效的坚守。政治话语的扩大化,致使艺术争论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造成了左翼整体的利益受到重创。
其次是对于视听语言讨论的缺失。在前文提到的九人的影评之中,只有芜青、鲁思、舒湮三人对画面有稍许的评价,芜青谈及“荐头店把五个女人分送到五家人家去,随后描写五家人家的‘东家好’这中间画面和画面的接续得简洁自然,情调的调和,都该是值得赞扬的……其他像五个女人初来上海时的繁嚣场面,描写三宝学习跳舞,用留声机片来预示时间的过去……”[30]的场面是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但是点评只能够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浮泛而谈,无法触及理论得出深层次的指导性结果。其余影评人几乎都从意识角度分析影片的内容,大谈“回到农村去”这一字幕是在有意地歪曲主题。这在姚苏凤的《〈路柳墙花〉编剧者言》中曾提到:“诸位批评家……一致以为我提出了‘回到农村去’的口号而认为是‘歪曲’的,其实,我不懂得这几位批评家为什么没有看见随着阿毛娘这句‘我们还是回到农村去吧’说话的字幕而出现在银幕上的,正是‘更多的农村妇女由而船上跑到都市里来’的那个很重要的画面。”[20]影评人对字幕的单独分析,造成了字幕与画面的脱节,违背了电影本体评判标准。因此,作为一位正在电影路上探索的艺术家而言,姚苏凤实难接受这种忽略电影本体艺术的影评体系。这也似乎可以解释他为何斥责凌鹤杀害中国电影了。
艺术上的争鸣染上政治色彩,那么左翼影人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就需要兼顾无产阶级对电影的接受能力。尘无在《中国电影之路》中谈及“要尽量的把电影大众化。这里所谓的大众化,并不限于票价方面,最至要的,还是影片的内容和形式方面……从前的中国电影,除了极少数以外,所有的影片中的人物和生活状况,思维方式,绝对不是大众所能够知道……所以电影的内容,非尽量的引用大众的真生活和拿大众每天接触的人物做主角不可。至于形式上,也应该非常明快的展开,多动作,少对白,千万不要运用一切倒叙回忆等只有知识分子,或则看惯电影的人,才懂得的手法。就是暗示,也应该拿大家们每人看得懂为限。象征的手法,是不必要的。”(王尘无《中国电影之路》[31])考察到当下中国民众对电影的认知力,左翼人士为了达到电影大众化的目的,只能从内容这一主要方面着手,因此对意识论的绝对推崇导致了左翼影人对电影本体艺术探索的无法兼顾。田汉在建国后也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工作中,左翼人士“对作品的‘目的意识’注意较多,对艺术上的精雕细琢注意较少。”(田汉《对党领导电影工作的一些体会》[29]128)由此观之,在与软性论者的辩论中,左翼人士对自己的不足也是有着清晰的把握的。
“视听语言是研究电影艺术的基础知识,无论是一个电影创作的初学者还是一个电影理论的爱好者……都必须认识和了解电影的基本元素及组成规律。”[32]在当代影视学者的认知下,视听语言的把握实乃平常,可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现场,影评人对于视听语言的探索则处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之中。1931年明星公司摄制《歌女红牡丹》,标志着中国进入有声电影时代。可是“1932年至1934年间,有声片创作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无声片制作仍居主导地位。三年间各公司共制作了约二百六十五部影片,其中有声片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三十”[33]。依托于视觉与听觉的电影艺术在中国实处于起步阶段,影评人即使有着极大的艺术自觉,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理论,也难以突破缺乏实践探索的囹圄之境。20世纪30年代影评人对于视听语言的把握处于弱势,更勿论在影评中涉及视听语言的讨论,这也为原因之一。
“凤鹤之争”的本质还是“软硬之争”,“争”的是电影是否一定要僵化地体现出先进话语而忽略电影本体艺术的探索。在不断发酵后,论争由艺术领域上升到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争夺,这便决定了双方在各自坚持的立场上,愈来愈疏远。“凤鹤之争”成为镶嵌在“软硬之争”中的一部分,二者交锋所迸发出的理论之多样性与独特性,必将其推向了更为广阔的讨论领域。
[参 考 文 献]
[1]郦苏元.30年代中国电影运动名称刍议[J].当代电影,2004(1).
[2]罗艺军.电影批评的黄金时代[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1).
[3]丁亚平.中国电影历史图志(1896-2015):上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200.
[4]姚苏凤.站在一个剧作者的立场上,揭开凌鹤的影评的内容:从今天起,我们来开始影评的“清洁运动”了[N].影迷周报,1934-10-03.
[5]张华.姚苏凤与1930年代中国影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韩平野.影评与剧作之战[N].影迷周报,1934-10-03.
[7]毛羽.路柳墙花[N].影迷周报,1934-10-03.
[8]舒湮.路柳墙花[N].影迷周报,1934-10-03.
[9]严郁尊.路柳墙花[N].影迷周报,1934-10-03.
[10]梅熹.反对调解苏凤与凌鹤之争[N].影迷周报,1934-10-17.
[11]方葛.关于影评剧作之战——站在‘影迷’的立场论‘凤鹤’之争[N].影迷周报,1934-10-17.
[12]舒湮.电影的“轮回”——纪念左翼电影运动60周年[J].新文学史料,1994(1).
[13]影评与剧作之战结论[N].影迷周报,1934-10-17.
[14]凌鹤.评《循环》[N].申报·电影专刊,1934-10-25.
[15]每日座谈[N].晨报·每日电影,1934-10-26.
[16]凌鹤.《循环》评补——并答《每日电影》诸君子[N].民报·影谭,1934-10-31.
[17]刘日新.新的展开[N].影迷周报,1934-11-21.
[18]丁亚平.电影怎样将这世界给予表达——中国电影与蔡楚生[J].当代电影,2004(4).
[19]凌鹤.《路柳墙花》小言[N].影迷周报,1934-10-03.
[20]姚苏凤.《路柳墙花》编剧者言[N].影迷周报,1934-10-03.
[21]严家炎,李今.穆时英全集:第3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171.
[22]广播电影电视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180.
[23]凌鹤.《路柳墙花》[N].影迷周报,1934-10-03.
[24]江兼霞.关于影评人[N].现代演剧,1934-12-20.
[25]张真.荧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320.
[26]姚苏凤.评《清白》[N].晨报·每日电影,1933-06-03.
[27]孟君.话语权·电影本体:关于批评的批评——“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论争的启示[J].当代电影,2005(2).
[28]唐纳.从苏凤先生的抗议说到影评的清洁运动与消毒运动——一个旁观者不知进退的话[N].青青电影,1934-11-10.
[29]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史料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30]芜青.评《路柳墙花》[N].影迷周报,1934-10-03.
[31]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42.
[32]陆绍阳.视听语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33]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