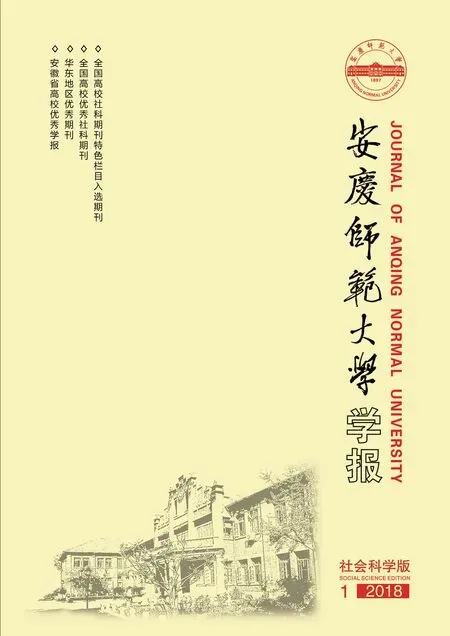论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发展
金仁义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与社会学院,安徽 安庆246011)
门阀士族与中古文化的关系向受学界重视。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曾说,“作为这种学问与现实社会的媒介体,即中国士大夫,在六朝也就是贵族。”[1]中国学者论述更为充分。上个世纪40年代陈寅恪即曾说过:“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2]钱穆撰著《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予以专论,基本结论是:“要以见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3]两位前辈的观点多为后来者阐发,已成学界共识。但他们所论,实乃强调中古文化与士族家学的关系,聚焦的是门阀士族与中古私学,至于士族与当时包括史学在内的官学发展之联系,并不在重点之列。
众所周知,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并行共进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我国传统史学独特的发展道路。南朝以降,随着士族渐趋衰落与皇权复振,皇权重新确立了对文化事业的主导地位,官方史学机构建设得到加强,官修史学成就也较东晋“国之大籍,成于私家”[4]大为更进,学界较多关注。牛润珍和胡宝国拓展周一良南北史学异同的考察,将视野延伸到南北官方史学比较上来,尤具启发意义。牛润珍曾言,“从史学的主流看,南朝北朝均以官方史学为主流……史学几乎被官方垄断。”[5]胡宝国也说,“东晋十六国以来,南北史书都是既有官修也有私撰。但就总体而言,南方私撰较多,北方则以官修为主。”“南朝以后,南方地区官修超过私撰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6]193这些成果给我们进一步认识南朝官方史学打下了基础。
既然南朝官方史学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而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之发展又莫不与门阀士族密切关联,那么具体到南朝官方史学究竟怎样?南朝是否已达到“史学几乎被官方垄断”程度?南朝官方史学如何定位?这些都需细致考察门阀士族在官方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后方能回答。
一、门阀士族与南朝时期史官体系
南朝著作省历宋、齐、梁、陈并有所发展,成为南朝最重要也最具制度化的史职机构。南朝时期,还一度出现刘宋元嘉年间由士族东海何承天主立的“史学”馆,以及宋齐之际总明观中“史科”等史学教育机构。但“史学”馆与总明观存在时间都不长,任职者多有失载,就整个南朝史学发展来说,影响显然不能与著作机构相比拟。比较起来,南朝著作机构对官方史学意义更为明显,任职人员史籍见载也较为翔实,为我们对其进行群体考察提供了可能。
南朝时期,著作郎多为皇帝或太子身边信臣兼领,著作佐郎也多为释褐或起家之选,是南朝官吏入仕的起点,因此著作官流动性很大。任职人员频繁进出,使南朝著作官形成一个相对庞大的群体(牛润珍和张承宗都对南朝著作官作过梳理,下文统计本以正史,在两位前辈成果基础上有所补充)。揆诸史志,刘宋时期见载著作郎有褚湛之、江智渊、何承天、何求、江恁、徐聿之、刘秉、徐爰、江敩、徐孝嗣、刘绘、许珪、孔灵运、王逡之,著作佐郎有顾练、殷朗、谢绍、褚寂之、江湛、褚渊、江恁、何承天、江敩、萧惠基、沈统、顾愿、王秀之、萧映、王奂、王莹、袁顗;萧齐时期著作郎有王逡之、周顒、王肃、萧业、沈约、顾暠之、傅昭等,著作佐郎有萧洽、张率、王瞻、王长玄、萧秀、萧藻、萧介、萧眎素、王僧祐等;萧梁时期著作郎有傅昭、任昉、王僧孺、裴子野、刘杳、许懋、陆云公、贺季、刘臧、刘刍、褚球、虞荔、杜之伟,著作佐郎有刘孝绰、谢绥、陆襄、刘谅、萧特、到仲举、到荩、徐悱、刘遵、萧几、柳仲礼、柳敬礼、徐敬成、陈昙朗、萧引、柳䛒、蔡允恭、姚察;陈朝著作机构任职人员著作郎有杜之伟、许亨、虞荔、徐陵、顾野王、陆琼、姚察,著作佐郎有姚察、陆从典、江溢,撰史学士有顾野王、许善心、傅縡,撰史著士有张正见、阮卓。统上所见,南朝四个王朝著作机构中见任著作郎共38人,著作佐郎47人,撰史学士3人,撰史著士2人,除出重复,计有82人出任著作史职。这个数字,显然不可能是南朝著作史官的全部。两晋南朝时期,著作省常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著作郎与著作佐郎的比例为1:8,统计所见著作郎与佐郎比例与此差距明显。不过,就考察南朝门阀士族与史职机构的关系来说,其结论应该与史实不会有太大出入。
南朝时期,门第郡望观念非常盛行,史籍可见这82人中,除极少数具体郡望不明,如顾练和顾暠之望出吴郡吴县抑或吴郡盐城,殷朗是否出自陈郡长平殷氏,均不可详考,其余绝大多数可以梳理清晰。寻绎诸史,可考郡望大体如下:琅邪临沂王逡之、王秀之、王奂、王莹、王肃、王瞻、王长玄、王僧佑;陈郡阳夏谢绍、谢绥;河南阳翟褚湛之、褚寂之、褚渊、褚球;济阳考城江智渊、江湛、江恁、江敩、江溢;东海郯人何承天;南琅邪开阳徐爰;南兰陵兰陵萧惠基、萧洽、萧介、萧视素、萧引、萧业、萧特、萧秀、萧藻、萧几;吴兴武康沈统、沈约;吴郡吴人顾愿、顾野王;陈郡阳夏袁顗;东海郯人徐聿之、徐孝嗣、徐悱、徐陵;彭城刘秉、刘绘、刘孝绰、刘谅、刘遵、刘刍;庐江潜人何求;会稽山阴孔灵运;高阳新城许珪、许懋、许亨、许善心;汝南安成周颙;北地灵州傅昭、傅縡;吴郡吴人张率;乐安博昌任昉;东海郯人王僧孺;河东闻喜裴子野;平原平原刘杳;会稽山阴贺季;沛国沛人刘臧;吴郡吴人陆云公、陆襄、陆琼、陆从典;会稽余姚虞荔;吴郡钱塘杜之伟;彭城武原到仲举、到荩;河东解县柳仲礼、柳敬礼、柳䛒;安陆徐敬成;吴兴长城陈昙朗;济阳考城蔡允恭;吴兴武康姚察;清河东武城张正见;陈留尉氏阮卓。上列79人分属35支郡望。其中,若琅邪临沂王氏、陈郡阳夏谢氏、河南阳翟褚氏、济阳考城江氏、东海郯人何氏、东海郯人王氏、南兰陵兰陵萧氏、陈郡阳夏袁氏、东海郯人徐氏、河东闻喜裴氏、高阳新城许氏、吴兴武康沈氏、吴郡吴人顾氏、庐江潜人何氏、彭城刘氏、平原平原刘氏、汝南安成周氏、北地灵州傅氏、吴郡吴人张氏、吴郡吴人陆氏、会稽余姚虞氏(王伊同《五朝门第》附表题为“会稽山阴虞氏”)、会稽山阴贺氏、会稽山阴孔氏、彭城武原到氏、河东解县柳氏、济阳考城蔡氏、陈留尉氏阮氏、清河东武城张氏等28姓计72人,均被王伊同收录在《五朝门第》“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中,显示南朝著作机构中门阀士族子弟比例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这和毛汉光考察两晋南北朝各政权所得结论基本一致[7],说明南朝时期,门阀士族仍然保持相当的活力,依旧是各王朝政权支柱。
如众所知,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对史官制度建设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东晋史官设置始于琅邪王导奏请,后来谯国桓温又对著作机构进行了改革。南朝时期著作机构的变化,如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设立撰史学士,是否与门阀士族倡议与推动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就南朝著作机构乃至所有史职机构而言,门阀士族的影响与印记,是无法回避的。唐时柳芳曾论江左士族:“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8]他所说的王、谢、袁、萧、张、顾、陆等侨吴士族,有不少子弟司职著作机构。史书说著作佐郎刘宋时“并名家年少”[9]1704、梁陈时为士族起家之选[10]741,洵非虚语。南朝还有些士族累世任职著作,如阳翟褚湛之、褚寂之、褚渊、褚球,济阳江湛、江恁、江敩、江溢,高阳许珪、许懋、许亨、许善心等。不可否认,南朝著作史官有名实不副的,如柳仲礼、柳敬礼兄弟与陈昙朗均以武功见长,但更多著作史官并非如此。柳氏兄弟与陈昙朗都是侯景乱梁前后进入著作机构。梁末选官非任是普遍现象,并不限于著作机构,但这种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陈书·徐陵传》载:“天康元年,迁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失其所,于是提举纲维,综核名实。”[11]332有陈著作史官遴选又恢复正常。姚察综论梁陈选官体制,说“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12]258。梁陈时得以跻身仕途仍有赖于文史才学。学界多注意南朝后期士族种种衰落迹象,然当时著作机构仍然充斥士族子弟,门阀士族凭借文化素养,依旧成为著作官员绝对主力,说明门阀士族的这种衰落是相对的、有限的。
南朝著作机构的存在,为南朝官方国史和起居注等修撰,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就此而言,门阀士族广泛参与著作机构,成为南朝著作史官主力军,对官方史学乃至南朝整体史学发展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二、门阀士族与南朝官修史学活动
论者对南朝官修史学成就的认识,往往立足于官修国史与集注起居。但国史修撰与集注起居并非南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全部,南朝帝王也会根据需要组织一些相关史学撰述,敕令个别朝臣撰述专史,并取得了相应的撰述成就。
南朝官方历来注重国史修撰并有所成,较有规模地组织国史修撰是在宋齐时期。宋文帝使何承天草创国史,又诏裴松之续修。宋孝武帝孝建年间先诏山谦之续修,又诏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修。大明五年,孝武帝又使著作郎徐爰主持,并敕令丘巨源襄助,一度掀起宋史断限讨论热潮。至萧齐建元二年,齐高帝以檀超与江淹掌史职,琅邪王俭与陈郡袁彖等参与了国史条例讨论[13]891。此后,南朝官方组织国史修撰,不再有较大规模的活动,但亦未曾间断。齐沈约“建元四年未终,被敕撰国史”[9]2466,谢超宗“世祖即位,使掌国史”[13]636,江淹“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12]250。梁国史多由著作郎掌知,如傅昭掌著作“撰国史”[12]570,周舍“国史诏诰”等“皆兼掌之”[12]376,裴子野“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12]443,杜之伟为著作郎“掌国史”[11]455。陈时,顾野王领大著作“掌国史”[11]399,陆琼“又领大著作,掌国史”[11]397,另,周弘直以秘书监“掌国史”[11]310、庾持“迁秘书监,知国史事”[11]458。刘宋时期以山谦之辅佐何承天、丘巨源辅佐徐爰修撰国史现象,萧梁时也可以看到,如傅昭掌国史时,“引显为佐”[12]570;周舍掌国史,刘杳佐其修史[12]716;裴子野掌国史,周兴嗣“佐撰国史”[12]698;杜之伟掌国史,表用姚察为佐,使之“仍撰史”[11]348。《梁书》还载任孝恭“外祖丘它,与高祖有旧,高祖闻其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12]726。西省为中书省别称,萧梁时期著作郎多兼任中书通事舍人、中书侍郎等中书省属官,如周舍、裴子野等,所以他们修史具体办公场所不在秘书省而在中书省。从增设助手到提供修撰场所,国史修撰组织程度明显提升。南朝各政权还留意前朝国史整理与修撰。如宋文帝令谢灵运撰《晋书》[9]1772,齐武帝敕沈约撰《宋书》,又敕令琅邪王智深撰《宋纪》[13]896-897,陈时杜之伟“仍敕撰梁史”[11]455、许亨“领大著作,知梁史事”[11]459、顾野王领大著作“知梁史事”[11]399-340,姚察于太建间“知撰梁史事”,后主初又“知撰史如故”[11]349。南朝国史撰修历代均有所成。宋时,谢灵运成《晋书》三十六卷,何承天成志十五篇及武帝功臣纪传,苏宝生撰元嘉名臣传,徐爰成《宋书》六十五卷。齐时,沈约成《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江淹成《齐史》十三卷,王智深成《宋纪》三十卷,另刘陟成《齐纪》十卷;梁时谢昊成《梁书》一百卷;陈大著作多有所成,许亨成《梁史》五十八卷,顾野王成《陈书》二卷,陆琼成《陈书》四十二卷,姚察撰《梁书帝纪》七卷,傅縡成《陈书》三卷。此外,尚有梁武帝令吴均撰成并躬制赞序的《通史》四百八十卷。
南朝集注起居的记史体制,构成南朝官方史学活动又一重要内容,成就显著。从史籍来看,刘宋时集注起居者不限于著作郎。如前废帝刘子业曾“启参承起居,书迹不谨,上诘让之”[9]147,吴喜受沈演之令写起居注[9]2114,裴子野也说:“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乡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诏撰《元嘉起居注》。”[14]子野曾祖即裴松之,时非著作官。萧齐著作郎专掌起居注,建元元年崔祖思启陈政事,提及“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13]520。次年,王逡之“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13]902。又稍后周颙“兼著作,撰起居注”[13]732。至齐明帝建武年间,琅邪王思远又以侍中“掌优策及起居注”[13]766,说明萧齐与修起居也不限于著作郎。梁时起居注亦由著作郎掌撰,王僧孺领著作“撰《中表簿》及《起居注》”[12]470,裴子野“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12]443,其撰史助手周兴嗣也撰有《起居注》[12]698。陈时所载稀见,史志仅一条,云:“初,世祖敕师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为十卷。”[11]232南朝官方集注起居注系列相对完整。据《隋志》,南朝有宋永初、景平、元嘉、孝建、大明、景和、泰始、泰豫、元徽、昇明,齐有建元、永明、隆昌、延兴、建武、中兴,梁有大同,陈有永定、天嘉、天康、光大、太建、至德等年间佚名起居注。除萧梁缺失较多,其他脱漏者仅宋前废帝永光,齐明帝永泰、东昏侯永元,陈后主祯明等年间起居注。后来章宗源又补出佚名《宋起居注》、《梁天监起居注》、《梁起居注》及《陈起居注》四十一卷[15]4976-4977。由《隋志》胪列来看,起居注一般按帝王年号分割而成,盖是官方将随时所成起居注汇聚整合,再以年号为单位重新分割,这样新成起居注便出现成于众手而不便署名的局面,故《隋志》与章宗源所补起居注不详撰名,正反证了这些起居注官修属性。众所周知,史官“汉魏已还,密为记注”[16],恰是“长期的‘密为记注’使大部分起居注的作者姓名不能流传于世”[17],从而使《隋志》见载南朝起居注多录佚名。
南朝时期,秘书省监、丞也屡屡整理秘阁图书,撰著簿录。南朝帝王还随时举办一些特设之局,如齐梁礼局、梁时谱局,组织人员进行撰述。南朝秘书监、丞多遵东晋李充旧法作《四部目录》。宋时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秘书丞王俭造《元徽四部目录》;齐时秘书丞王亮、监谢朏造《四部书目》;梁秘书监任昉、殷钧撰《四部目录》;陈天嘉间又重新审定,制成新编。[10]907礼局始于齐永明初年。《南齐书》载:“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13]117-118王俭曾令伏曼容与司马宪、陆澄共撰丧服仪,既而又准备与伏曼容共定礼乐,会薨事止。[12]663此后,何胤、徐孝嗣、蔡仲熊及何佟之相继掌事。梁时,复以明山宾掌吉礼、严植之掌凶礼、贺玚掌宾礼、陆琏掌军礼、司马褧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佟之亡后,以镇北咨议参军伏暅代之。后又以暅代严植之掌凶礼。暅寻迁官,以《五经》博士缪昭掌凶礼”,又使沈约、张充与徐勉同参厥务,徐勉总知其事,“末又使中书侍郎周舍、庾于陵二人复豫参知。”[12]381梁时礼局既有分掌,又有总知其事,与唐初史馆修史形迹相近,撰述也颇有成效。《隋志》史部“仪注”类载录明山宾《梁吉礼仪注》十卷、贺玚《梁宾礼仪注》九卷,又言及亡书有梁明山宾《吉仪注》、严植之《凶仪注》、陆琏《军仪注》、司马褧《嘉仪注》等[10]969-970。梁天监年间沈约上书校勘户籍,是梁加强谱牒修撰和控制之始。史云:“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18]11462杜佑《通典》又云:“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严。”[19]王僧孺在谱局成《百家谱》三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梁武帝设置谱局,令官方取得了谱系撰述新成就。诚如周一良所说:“盖梁时政府开始设机构掌握氏族谱牒,谱学由私家学世代传授而变为国家过问了。”[20]
南朝帝王常常随事敕令官员撰史,如宋文帝使兰陵萧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9]2013,又使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9]1701,宋明帝使丘灵鞠著《大驾南讨纪论》[13]890,又“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9]1290,宋后废帝敕琅邪王圭之“使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并成五十卷[13]903,齐武帝“敕仪曹令史陈淑、王景之、朱玄真、陈义民撰江左以来仪典”[13]772,梁武帝敕吴郡张率“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12]475,敕会稽贺琛撰《梁官》[12]679,敕裴子野撰《方国使图》、《众僧传》[12]443-444,又敕陆云公撰《嘉瑞记》[11]397,等等。这些应敕之作,在组织和参与程度上,官方介入不比前列国史、起居注、仪注及谱牒等深入,但亦可列为南朝官方组织的史学成就。
通过上述官方组织修史活动及其成就梳理,南朝官方史学作家群体大体情况业已明朗。其中郡望清晰可见者,举其大概,与修国史有东海何承天、河东裴松之、吴兴丘灵鞠、高平檀超、济阳江淹、吴兴沈约、陈郡谢超宗、北地傅昭、沛国刘显、汝南周舍、平原刘杳、河东裴子野、高阳许亨、汝南周弘直、颍川庾持、吴郡陆琼、吴郡顾野王、北地傅、陈郡谢灵运、琅邪王智深等,集注起居有河东裴松之、琅邪王逡之、琅邪王思远、汝南周颙、东海王僧孺、河东裴子野、沛国刘师知,其他史学撰述者有陈郡谢灵运、琅邪王俭、琅邪王亮、陈郡谢朏、陈郡殷钧、平原刘孝标、彭城刘遵、平昌伏曼容、庐江何胤、东海徐孝嗣、吴郡陆涵、济阳蔡仲熊、庐江何佟之、会稽贺玚、吴郡陆琏、汝南周舍、平昌伏暅、吴郡张充、东海徐勉、吴兴沈约、颍川庾于陵、东海王僧孺、兰陵萧思话、河东裴松之、会稽虞通之、吴兴丘灵鞠、琅邪王珪之、河东裴子野、吴郡张率、会稽贺琛、东海何思澄、平原刘杳、吴郡顾协、吴郡陆云公等。上述诸人,均为王伊同《五朝门第》“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载录,其未见者仅山谦之、苏宝生、南琅邪徐爰、兰陵丘巨源、乐安任昉、陈郡周兴嗣、刘陟、谢昊、刘子业、吴兴临安吴喜、吴兴故鄣吴均、河内司马宪、平原明山宾、建平严植之、河内司马褧、陈淑、王景之、朱玄真、陈义民等诸人。这其中,又有郡望不可详考的,或郡望尚可斟酌的,如刘子业为太子,又如任昉,史称与裴子野为从中表[12]441,由南朝盛行士族身份内婚制可知,门第郡望当与裴子野相近。综此可见,门阀士族是南朝官方史学的主要作家群体。
门阀士族是南朝官方各类史学活动主要参与者,成为官方修史的绝对主力。南朝不少官方史学活动还是由士族发起和推动的,如王俭之奏论国史条例,伏曼容之表定礼乐,沈约之奏定谱局,等等。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门阀士族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撰述的发展。
三、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地位
历史发展往往受多种因素制约而成。南朝重建皇权政治后,延续了魏晋传统,设置著作机构,组织了相关史学活动,并取得了一些史学成就。但南朝又长期内外矛盾交织,政局动荡频仍,官方学术活动也整体随之起落。元嘉四学与总明观旋立旋废,说明南朝官方对加强史学教育的兴趣是有限的。除国史修撰和集注起居等保持一定规模外,南朝官方其他史学活动并无长期规划,官方组织力度不大,参与程度也不深。因此,在看到南朝官方史学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其中存在的局限性。南朝官方史学地位,尚须进一步考察方能定断。
南朝时期,官修以国史撰著最为重要。金毓黻对魏晋迄唐初所修国史有个总体评述,即“官修之史,十才一二,私修之史,十居八九”[21]95。具体到南朝,他又说:“南北朝诸史之已亡者,多属私修。”[21]91即便是传世的沈约奉敕而成《宋书》,金毓黻也反复强调其私撰色彩,说其“虽受命时君,而奋笔一室,不假众手,亦与私撰无殊”[21]92,又说“名为敕修,实出一人之手,亦私史之比也”[21]95。日本池田温也持此说,他将魏晋南北朝所成正史分成两种,“一种是史家私人修撰的,如《三国志》、《宋书》。”[22]此《宋书》即指沈约《宋书》。南朝官成国史以沈约《宋书》质量最佳,然言宋史者却以裴子野私修《宋略》为上[23]353。就南朝国史成书数量而言,邱敏的考察更为细致,其结论也是私撰多于官修[24]。起居注本为官方专掌,但南朝亦出现私修且部帙庞大。史称徐勉“尝以起居注烦杂,乃加删撰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卷”[12]387。徐勉以个人名义对前期官修起居注进行重整,不是南朝特例。《隋志》著录有宋北徐州主簿刘道会撰《晋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章宗源考其乃是合两晋起居为一书[15]4975,亦属此类。对于刘道会与徐勉重整前期起居注,乔治忠视为不在官方记史体制之内的私修之作[25]。南朝风行地理书和杂传撰述,二者在当时史学撰述格局中颇有分量,但南朝官修杂传与地理书成就有限。又“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6]237,可南朝史学批评成就最突出者,莫过于范晔《后汉书》史论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因此,总体来看,南朝史学私撰依然胜于官修。诚如胡宝国所揭,南朝以后,南方地区官修只是“超过私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非已然超过私撰。
南朝官方组织史学活动虽然增多,但并无明显掌控史学的意图,这在前史撰述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宋文帝敕令谢灵运撰《晋书》,私撰则有臧荣绪《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等;齐武帝敕令沈约撰《宋书》、王智深撰《宋纪》,私撰则有刘祥《宋书》、裴子野《宋略》;梁时,萧子显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12]511,胡宝国释为“萧子显的《南齐书》也得到皇帝的认可”[6]205,未明说官修或私撰,赵吕甫释“启”为“开始”之意[26],则萧子显《南齐书》为私成清晰可见。梁还有吴均私成《齐春秋》。刘知几称:“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23]355可见,梁武帝虽拒绝赐阅官藏档案,但仍许吴均私自搜访,其无意垄断前朝国史修撰态度十分清楚。陈时,著作郎虽掌知梁史,但亦有庐江何之元私成《梁典》。即就当朝国史来说,南朝官方也并未垄断,如何点在齐私撰《齐书》以剌讥褚渊、王俭[13]938,许亨梁时勒修《梁书》[27]2804。南朝盛行的谱学也是如此,虽然梁代加强了谱牒官修,但谱牒私修仍广为流行。
从修史制度的规范化来说,南朝也还有不少发展空间。国史与起居注居然由非史任者兼掌。南朝史职引入不少名家,但所获成就不无遗憾。如裴子野史才出众,领著作然又兼掌中书诏诰,官事繁多,虽得周兴嗣辅佐而国史竟无所成。裴子野直至卸任中书并著作后方重提史笔,“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12]444又如顾野王,自陈太建六年起担任大著作,十三年卒,期间先后兼任太子率更令、东宫通事舍人、黄门侍郎、光禄卿等多职,结果造成他“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11]400。裴子野、顾野王等名家虽为史臣却兼职太多,因王役无暇而撰史难成,反映南朝撰史制度仍有待成熟。对前朝国史进行整理,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官方自觉意识,也是后来官修惯例。但南朝帝王这一意识并不强烈,史职机构长期并无修撰前史职守,直至陈才见有大著作掌梁史。
至此可见,南朝官方史学成就显然不可高估,官方史学是否堪称史学主流,似有重新斟酌之必要。
南朝官方史学并不胜于私修,原因仍与门阀士族有关。作为官修主要群体的门阀士族,其撰史热情并不限于官方组织的史学活动。苏绍兴分析南朝史学,说:“今统计南朝史籍著述,泰半为士族所作,盖彼等藏书较富,见闻又多,资料蒐集充实,而又有闲暇从事著述,开史家著史之风气焉。”[28]是以更多的士族,或者曾与役官修的士族会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私修之中,私修成果更多,推动私家史学潮流汹涌前进。门阀士族撰史动力,本源自极强的自觉意识。如两晋国史残缺,不断激发南朝士族史学旨趣。沈约“少时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18]1413,至齐梁兰陵萧子云仍“以晋代竟无全书,弱冠便留心撰著”[12]513。南朝门阀士族怀抱这种史学自觉,多积极私撰,或是聚私撰与官修于一身。尤其是后者,在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中,往往发挥出积极作用。乔治忠有言:“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最重要原因就是具备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29]门阀士族私撰之外参加官修,官修之余进行私撰,通过自身的史学撰述,完成了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还如沈约,少有著史之意,宋时撰《晋书》;齐时,沈约进入史职,先后与修国史和起居注,又受敕撰修《宋书》;梁时,沈约不为史臣,犹撰有《高祖纪》十四卷。沈约以私撰《晋书》锤炼史才,为《宋书》撰修提供了质量保证。反之,也有因得官修之便,引发新撰或是完善旧作。如河东裴子野,因私撰《宋略》展现史才,被举荐为著作郎,掌国史与起居注,其间受命撰《方国使图》,离开史职后,裴子野又利用遍阅官收档案之利着手修撰《齐梁春秋》。再如高阳许亨,梁时曾私撰《齐书》,成五十卷,又撰《梁书》阙而未就,至梁室交丧,“所撰之书,一时亡散”;陈永定中,许亨任职大著作,掌梁史,便“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27]2804。官修与私撰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多种类型、多种渠道的,但这些影响和作用最终落实,还须由史家主体来完成。南朝门阀士族,往往兼与官修和私撰的史学活动。他们在从事史学撰述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彼此融汇,存优汰劣,取长补短,促进官修与私撰的共同发展,甚至模糊了官修与私撰的界限。质言之,南朝门阀士族正是通过自身的史学实践,完成了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共同发展。
至此,我们以门阀士族为中心,对南朝门阀士族与官方史学关系进行较为细致梳理,大体可对前述问题作出回答。其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关系,与士族同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整体关系基本一致,佐证了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前辈的论断。门阀士族既是南朝官方史职机构的主力军,也是南朝官方史学撰述主要作家群体。南朝官方史学撰述,尤其是其中质量上乘者,多出自士族之手。其二,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政治环境仍相对宽松,统治者对私家修史并未有太多干预,距离官方彻底控制和垄断史学仍有较长路程。南朝后期吴均《齐春秋》的成书命运可谓典型:一方面,吴均可在梁武帝默许下私撰《齐春秋》;另一方面,虽因实录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而遭敕付省焚毁,但《齐春秋》实际上仍得以流传,唐修《隋书》著录其书即是明证。其三,相较东晋,南朝官方史学有着明显进步,取得了不俗成就,但仍逊色于私家史学,在南朝史学整体中的地位不可放大。凡上种种,均与士族史学情怀密切关联。南朝官方史学建设与发展,有赖于门阀士族的参与和推进。士族史志又多由内在自发而生,而非局促于官方驱动。这既促使史学风气突破官方意识而盛行,也导致私撰胜于官修。士族还在官修与私撰互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史学在两条路线上都得以发展的动力所在。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史学对门阀士族也有着一定的反向作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史学社会功能。如众所知,门阀士族走过东晋的鼎盛,至南朝时期开始趋于衰落。但刘宋以降,起家著作和梁陈以文史取士的制度化,南朝官方对谱学的重视和推进,都为士族仕途打开方便之门;出色的史学成就,也使士族得到更多赞许和肯定,有利于士族门阀地位的巩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进程。
[参 考 文 献]
[1]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M].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80.
[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1.
[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北京:三联书店,2009:207.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96.
[5]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45.
[6]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86.
[8]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677-5678.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2]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3]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4]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3944.
[15]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
[16]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681.
[17]陈一梅.汉魏六朝起居注考略[J].中国史研究,1996(4).
[18]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61.
[20]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82.
[2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2]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19.
[23]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4]邱敏.六朝史学[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145.
[25]乔治忠,刘文英.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J].史学史研究,2010(2).
[26]赵吕甫.《史通》新校注[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731.
[27]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8]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14.
[29]乔治忠,杨永康.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J].学术月刊,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