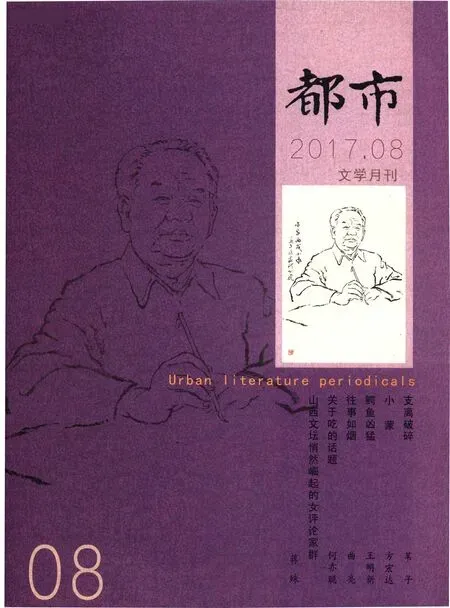关于吃的话题(五题)
何亦聪
关于吃的话题(五题)
何亦聪
豫北的早点
在这样一个饮食高度同质化、遍地是连锁餐饮店的时代,大约只有早点,最能见出一个地域的真精神了,可惜的是,即便是这一点点残存的真精神,也正处在飞速消退的过程中。梁实秋到台湾之后,四处寻找老北平的豆汁儿不可得,而如今即使是在北京,能喝得惯豆汁儿的人也已为数极少。早晨七八点钟站在城市街头,匆匆走过的多是手里拿着肯德基、麦当劳早点的上班族,可见不独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饮食,强求不得。我自幼生长在豫北、鲁西一带,于此一地区的民风、饮食最是熟悉,这里过去是黄泛区,民风强悍,饮食粗粝豪放,盛菜盛饭多用大盘大碗,寻常百姓皆极嗜葱蒜,凡吃烙饼、面条、饺子等,都会另摆一盘葱段或一碗蒜瓣在旁,致有无蒜不欢者——传言有个聊城女孩嫁到了苏州,竟因嗜蒜而与丈夫闹到分居,这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实我于“家乡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离开这么多年,念兹在兹的,想来也只有故乡的早点了。
豫北早点,若说有什么外地所难以吃到的特殊花样的话,当首推安阳的“扁粉菜”。“扁粉菜”名字怪异,顾名思义,“扁粉”就是扁粉条的意思,“菜”主要是豆腐、猪血和青菜。这几样东西放进一口大锅里,以高汤熬煮,出锅时浇上浓厚的辣椒油,就是所谓“扁粉菜”了。扁粉菜我只在安阳、鹤壁、邯郸、濮阳四个地方见到过,邯郸以北,如邢台、石家庄,没有此味,鹤壁以南,如新乡、郑州,也极少见早点摊上售卖。如此美味,何以竟不能普及各地呢?大约是口味偏重的缘故——华北人吃早点,总归以豆浆油条、清粥小菜为正宗,对于重庆人的一大早就吃麻辣小面、武汉人的顿顿早点不离热干面,是一向视作旁门左道的。吃扁粉菜必加辣椒油,如果加得少了,就嫌不够味儿,这有点类似麻辣烫,若不麻不辣,清汤烫菜,谁还乐意吃呢?扁粉菜因所用食材皆甚廉价,所以其定价亦较低,十五年前,在安阳吃一碗扁粉菜,只要一块钱。扁粉菜的标准搭配是油饼,或者称千层饼、手抓饼更加准确,很多人吃扁粉菜,是冲着可以不限次数添加的高汤而去的,毕竟,自家做饭大都懒得费工夫去熬煮这种猪骨高汤。
胡辣汤是较有名气的一种早点了,西安也有所谓的“肉丸胡辣汤”,从“胡辣”二字来说,似较河南的“逍遥镇牛肉胡辣汤”更名副其实,大约河南人在麻和辣两种滋味的接受度上总是偏保守些。有人说牛肉胡辣汤产生于北宋徽宗年间,也有说法认为其制法源出于少林寺的“醒酒汤”和武当山的“消食茶”,但二者皆难确考,从口味上判断,胡辣汤似乎更近于回民饮食。据说真正讲究的牛肉胡辣汤除了要用牛肉汤做底之外,还要加三十余味药材,并掺以面筋、腐皮、木耳、黄豆、黄花菜等物——这听起来仿佛是噱头,民间凡宣传某种特色美食,每每强调其用料之繁复,动辄数十种,其实是有违饮馔之道的,袁枚《随园食单》中尝有云:“味太浓重者,只宜独用,不可搭配”,这才是知味之言。胡辣汤不能算豫北特有的一种早点,烹制此味最负盛名的“逍遥镇”是在周口,“北舞渡胡辣汤”则是在漯河,但豫北各城市的早点摊上,大都有胡辣汤售卖。牛肉胡辣汤在豫北又名“红胡辣汤”,以其颜色绛红之故,同时可以和“白胡辣汤”相区别,至于“牛肉”二字,大可不必较真,以现下的物价,若指望在两块钱一碗的胡辣汤里品尝牛肉滋味,未免太痴。“红胡辣汤”口味咸重,早晨就着油条喝下两碗,一上午恐怕没有一暖瓶的开水解不了渴,所以豫北人多喜“两掺”,亦即将豆腐脑与胡辣汤掺在一起,以胡辣汤代替豆腐脑的卤汤,其口味相比北京的传统豆腐脑、苏州、四川的豆花,别具一格。
白胡辣汤是另外一种物事,这种胡辣汤大概只在豫东北的濮阳市可以喝到,在当地又称“传统胡辣汤”,相形之下,牛肉胡辣汤反而是一种新兴的、外来的吃食。白胡辣汤口味清淡,多用面筋(这种面筋与通常所见的那种海绵状面筋不同,呈不规则的带状,致密而有韧性)、菠菜、花生、粉条、海带等,“胡辣”的来源大概是胡椒粉,但其用量亦甚微,故胡辣之味并不明显,濮阳曾有阵子流行炸烧饼——即将刚出炉的芝麻烧饼入锅油炸,炸至两面金黄取出,洒辣椒粉、孜然粉,食客中有口味偏重的,往往在饼上放大量辣椒粉,乃至堆积如小丘,然后平端入内,再将饼上的辣椒粉倾入胡辣汤中,此亦一种吃法。白胡辣汤的源起不可考,但我觉得它与豫东北、鲁西南一带乡下人常喝的“粉汤”十分接近,所谓“粉汤”者,除了要勾芡、适度加入胡椒粉外,也要加菠菜、粉条等物,当地民风粗朴,乡民在家中设席,酒是自酿的桶装烈酒,菜肴如清拌黄瓜、芥末粉皮、炖鸡炖肉等皆用大盆盛放,酒足饭饱之后,定要一人来一大碗粉汤,才能收束得住这一场海吃海喝。所以,白胡辣汤与红胡辣汤名称虽相近,实则差异极大,一为清真口味,一为豫东北乡下家常口味;烹制方法也是一繁复,一简单。
豆沫是安阳、邯郸一带的特色早点,安阳曾是殷都,因而当地人都说豆沫的来源与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有关——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豆沫的主料是小米,另加黄豆、花生,皆磨成粉浆,并放入豆腐、菠菜、海带、花椒、精盐、芝麻等。与牛肉胡辣汤相比,豆沫的口感似更温醇稠密些,佐料味没有那么足,刺激性也没有那么强,有一股豆米清香,灰沉沉一碗端上来,上面浇几滴麻油,更是香气扑鼻,再就着不花钱的腌萝卜丝吃两根油条,算是种不错的享受。我有个居住在浚县的朋友,极嗜豆沫,尤嗜鼓楼往西的那家豆沫,当年读高中之时,从早自习下课到上午第一节上课之间,仅有五十分钟的时间,他也必定要骑自行车来回奔驰半个小时,以五分钟一碗的速度连罄两碗豆沫外加三根油条,鼓腹而归,若非如此,就总觉得仿佛缺了点什么。后来这位朋友到了别的城市读书、工作,便再难喝到地道的豆沫了,现在很多超市里有所谓的“豆沫粉”出售,可买回家按口味添加食材自行烹制,但据他说,满不是那个味儿。
丸子汤是到处都有的,但早晨就喝丸子汤,大概主要还是华北一带人的风习。北京早点里面有一种“豆面丸子汤”,所谓“豆面丸子”,是用豆面、萝卜丝、粉条等混合油炸而成,是素丸子;太原早点里则有一种“南肖墙丸子汤”,南肖墙是个地名,这种丸子介于荤素之间,主要由猪五花肉和土豆粉等掺和油炸而成。豫北一带只有濮阳的某些县区喜欢以素丸子汤为早点,从丸子本身来说,与北京、徐州的“豆面丸子”没有什么差异,都是以绿豆面、萝卜丝等为主料,再混合花椒面、葱姜等佐料——从这个角度讲,“豆面丸子汤”似乎应该算是“运河菜”之一种,凡淮河以北、京杭大运河沿岸地区,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河南省最东北角的台前县(属于濮阳市),地处豫鲁交界,旧时一直属于山东,四十余年前划归河南,其饮食、方言、文化兼有豫鲁两省特色,当地有种酸辣丸子汤,极勾人馋涎,丸子不必说,就是普通的豆面丸子,那碗微褐色的汤却着实有意思——它既不是以骨汤、鸡汤做底子,也没有用辣油、红油等,厨师不过是在十余种调料里随意掂配,拿滚水一冲,捏一撮香菜撒在上面,再浇几滴麻油,就自然成了一碗鲜麻酸辣的好汤。
烩馍给人的印象似乎接近西安的羊肉泡馍,洛阳有所谓“羊肉烩馍”者,从口味、用料等方面说,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羊肉泡馍,唯一的区别大概只在于馍是否要手掰,以及馍块的大小等;开封则有“牛肉烩馍”,亦属清真风味;杨朔有篇散文写他经过临汾,在小客店歇息时要了一碗烩馍,“这是种含有十足的西北风味的饭食”,可见也是牛羊肉烩馍一类。相对而言,豫北一带的烩馍则是另外一种吃食,既不用羊肉,馍本身也只是普通的发面馒头,而不是质地坚硬的锅盔。因此,如何让馒头本身在汤汁里不致泡发、松散,是门学问,对此,豫北烩馍的诀窍有二:其一,烩馍所用的馒头,本身较寻常馒头要更致密些,绝不是那种看起来饱满,双手一捏便缩成一小团的海绵般的馒头,鲁西一带有种远近闻名的“高桩馒头”(不同于临沂的高庄馒头),最为合用;其二,烩馍在加汤之前,要先切块与豆芽、蒜薹、酥肉等一同翻炒,经过翻炒之后的馍块,虽浸入汤汁,短时间内也不致泡散。就形态和烹制方法来说,豫北烩馍更像是一种加了汤的炒馒头块,豫北人嗜食馒头,这样一碗热腾腾的烩馍下肚,既有馒头,又有菜和汤,更兼香气馥郁,实在是平头百姓适口充肠的佳品。
呱嗒,名称甚怪,有些地方称之为牛舌头,以其形状长圆,毕肖牛舌之故。呱嗒本是鲁西一带的特色吃食,源起于济南、聊城等地,但豫北地区,尤其是临近山东的濮东诸县,也多有流布。无论是口味、制法还是用料上,呱嗒都与肉合颇为相近,所不同者,一是形状(肉合多作正圆形),二是厚薄(肉合较呱嗒更厚一些),三是馅料(呱嗒属于清真食品,故用料多以牛肉、粉条为主)。因形制长而薄,所以呱嗒的口感十分酥脆,豫北一带人的吃法,是喜欢用一个刚出炉不久的芝麻烧饼,从中弯折,将呱嗒夹着中间,就着一碗胡辣汤囫囵食之,其间趣味,似乎约略近于老北京的“烧饼夹油鬼”,不过呱嗒是有肉馅的,所以更复杂些。据说有个徐州人跟随当地的旅行团去北京,走马灯似的转了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回程坐的是夜车,经过濮阳时已是早晨六点,他下车吃早点,竟连吃三个烧饼夹呱嗒,喝下两大碗胡辣汤,结果一回到徐州就撑得进了医院——这虽是个不幸的例子,却也足可见得“烧饼夹呱嗒”确是美味,令人一尝之下便难以作罢,非吃得肚皮滚圆不可。
水煎包,是锅贴之一种,在古时应算作“扁食”。《清稗类钞》中记“扁食”云:“北方俗语,凡饵之属,水饺、锅贴之属,统称为扁食,盖始于明时也。”有说法认为水煎包的出现可追溯至秦末汉初时代,甚至与汉高祖刘邦有关,这当然不可信,“始于明时”大概还是确凿的。豫北一带的水煎包可以理解为一种素馅的锅贴,如在濮阳、安阳等地,只要早点吃水煎包,那就必是韭菜素馅无疑,想吃肉馅的,大可选择呱嗒、肉合、羊肉包子等。至于其他地方的水煎包,如菏泽、开封、西安等,则大抵有荤素之分,素的就是韭菜馅,荤的还可分牛肉、羊肉、猪肉馅。逯耀东描写他在西安逛夜市的经历云:“好不容易在夜市的尽头,找到一家牛肉丸子汤的摊子,于是坐下来,要了碗丸子汤,两只水煎包,在旁边的摊子要了一碟钱钱肉,钱钱肉就是驴鞭,还要了烤羊肉串,一大杯冰生啤酒,独自啜饮起来,小桌小凳颇有情味。”此种情形,颇引人向往,数年前我在开封的夜市也曾就着生啤酒吃大串烤羊肉和水煎包,只是单就豫北而言,水煎包仅仅是早点,晚上是无论如何吃不到的。
除却上述的种种吃食外,豫北早点还有豆腐脑(有荤汤、素汤、浆式、两掺之分)、羊肉汤、烙饼、炸布袋、炸糖糕等物,此处不再一一叙述。华北人的早点,不似江南、闽粤一带人那般讲究,像广州人喝早茶、苏州人吃头汤面那样的盛况,在此地当然不会有,味分南北,食有精粗,自古而然,倒也不必刻意标榜一地域之特色。如果说在豫北吃早点有什么讲究的话,大概是在搭配上——羊肉汤扁粉菜与手抓饼、油条布袋与胡辣汤、烧饼呱嗒肉合与素汤豆腐脑、水煎包羊肉包与糊糊粥……这些都是相对固定且经由多少代人积淀下来的经典搭配,饕客不可不知,如果拿呱嗒、包子、肉合与扁粉菜同食,则不免太咸重油腻,如果就着糊糊粥吃烧饼、手抓饼,又不免太寡淡无趣。凡事总要讲究互补,饮食之道,亦是如此。
米粉与米线
以前在北师大读书时,颇厌学校食堂的拥挤,幸喜食堂旁边有一家小小的桂林米粉店,虽然也是食客常满,但好在不必踩着饭点去。我总是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的时候,离开图书馆,踱步到那家小店,若是在冬天,彼时正值太阳落山,一路穿过校园,头上是盘旋的群鸦和光秃秃的树枝,道上是懒洋洋的行人,店里空荡荡,索一碗酸豆角米粉,加上浓郁的辣酱,吃得满头冒汗,十分饱足。说起来,那家米粉店的口味也只平平,但事关记忆,与过去的时光搅拌在一起,也就格外地让人惦念。
米粉一物,在北方原不多见,但在南方大概只是寻常吃食,到处都有,前面所说的桂林米粉,不过是其中一种罢了,其他如绵竹米粉、兴化米粉、会昌米粉、长沙米粉或潮汕米粉,也都各具特色。然而要吃到正宗的桂林米粉,大概也十分不易。桂林米粉的妙处,一在卤水,二在主料和配料,据说上好的卤水需用牛筒骨熬汤,另加二三十味调料制成,配料包含酸豆角、黄豆、酸笋、辣椒等物,主料中更有一味“锅烧”,亦即小火油炸而成的猪颈肉,香而不腻,风味绝佳。北京寻常的桂林米粉店里,卤水、主料、配料均极寒酸,米粉也往往非当日所制,至于老饕们所艳称的马肉米粉,更是难得能遇到。梁羽生《广陵剑》中曾写葛南威、陈石星在桂林吃当地的马肉米粉,描摹细致,煞是动人:
只见那盛米粉的碗只有茶杯大小,碗中的米粉也与他们习见的米粉不同。(一般米粉是扁平的长条,桂林米粉则是圆形的长条。)云瑚笑道:“原来是一口可以吃掉一碗的,怪不得食量大的人可以吃三四十碗了。”杜素素说道:“这米粉也很秀气。”吃了一口,只觉马肉甘香,米粉韧滑,汤水鲜甜。果然十分可口。她本来是捏着鼻子的,此时也吃得眉开眼笑了。
吃马肉米粉的规矩,客人不叫停止,伙计就得川流不息的送来,陈石星要了一壶三花酒,和葛南威对饮。不多一会,他们桌子上的空碗,已是叠得像小山一样。
如此川流不息地送,川流不息地吃,最后几个人总共是吃下去九十八碗——对于吃桂林马肉米粉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我曾听一个长期在桂林工作的朋友说,他们八个同事相约去吃马肉米粉,创下一顿吃掉二百八十七碗的记录。究竟马肉米粉好吃在哪里呢?中国各地以马肉入馔者很少,不独因为马与人类的情谊及其运载功能,也因马肉本身味酸而质柴,若烹调不当,更是容易肉质发硬,黑河嫩江一带气候苦寒,至今仍有吃马肉干的习惯,我曾尝过一次,说不上出色。而桂林马肉米粉中的马肉之所以好吃,大概是由于其特殊的腌制方法,这种腌制方法使得马肉本身的酸味被压制,甚至还微带甜意,当然,也只有选用上好的马肉,才能保证口感。据当地老饕讲,真正懂得吃马肉米粉的,首重在汤——必须是用马骨长时间熬制出来的清汤,其次,马下水更胜于马肉。虽说现在各地饮食文化趋于融合,一线大城市几乎无物不有,无味不具,但出了桂林,要吃到马肉米粉,还是很不容易,我只在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小馆子里吃到过一次。如此美味,不得普及,不知是何缘故。
潮汕一带有所谓粿条者,也是米粉之一种,此种食物在闽粤、台湾、南洋极为普遍,其地位有如面条之于华北、西北。我有一个朋友,常年居住在马尼拉,对当地食物没有什么喜好,日常饮馔不过两样,一是啤酒,二是粿条。啤酒是当地的红马啤酒,这是种烈性啤酒,据他讲口感颇为刺激,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杀口”,粿条则是出自福建手艺(在菲律宾生活的福建人极多),以番茄汁或咖喱汁炒食之,另加福建鱼丸数枚,就这样,一瓶啤酒,一盘炒粿条,便是一顿饭,日日如此,也不觉厌烦。潮州的牛肉粿条最是有名,懂行的食客一定会选择吃生灼牛肉,取其入口的质感,但此种吃法对于食材的要求必高,寻常牛肉,怕是不行。据说泰国潮汕人极多,其当地所烹制的牛肉粿条与潮州差异极小,蔡澜曾提到过一种艇仔粿条,似乎不错,只是卫生状况堪忧。
虽然近年来随着南北饮食风气的融合与人口的流动,米粉、米线已是到处可见,但总的说来,北方人对此两种食物的感情不免还是浅一些。周作人谈论南北点心,以为其最大差异是在北方人吃点心为的是充饥,南方人则视点心为闲食,绝不指望其能果腹,这大概说得是实情,因为许多北方人不喜米粉、米线的一个关键理由即是“吃不饱”。如今北京流行的“云南过桥米线”,多数只能算是“半过桥”,端上来的,是一只滚烫的砂锅,食客所需的种种主料、辅料,都是提前煮进锅里,按价格可选一荤几素、两荤几素等,米线亦是按份填加,每份皆事先煮好,售价三块钱,分量不大。数年前北师大北门附近有家云南米线——也是“半过桥”,但是其好处在于汤、米线、主料都十分考究,特别是米线,仍用的是“酸浆米线”的老法子制作,比之寻常米线店里所用的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干浆米线”,口感更有弹性,更兼有一股清香之气。曾有位来自山东的同学,到这家店用餐,一口气竟连加十一份米线,传为笑谈,然而后来向他询及此事,他只憨厚地笑一笑说:“米线不顶饥。”
制作“酸浆米线”一则程序复杂,二则,需用特殊的“桂朝米”,这种米粘性甚足,用来煮饭口感不佳,制作米线却最是合宜。之所以称之为“酸浆”,大概是因为在制作这种米线之前要先将大米发酵处理,入口略有酸味,其保质期也不超过五天。如今寻常米线店里所用的米线大都是干浆米线,要吃到酸浆米线已是十分不易,这或许也是近年来米线口味倒退的一个主要原因。至于有人以为米线本身无甚差异,重要的是在那一碗鸡汤以及主料的新鲜度、刀工等,这恐怕就是外行之见了。
除却专门的云南馆子外,华北各地常见的米线店大约只有两类:一类是前面所说的“半过桥”砂锅米线,此类米线大都冠以“云南过桥米线”之名,然而主厨师傅却未必是云南人,可能来自河南、安徽,也可能来自浙江、福建。据说有个昆明人到北京开出租车,中午歇班必以米线一碗充饥,然而吃遍了北京街头的“云南过桥米线”,竟未有一次吃到真正“过桥”的米线,于是愤而抛弃开出租车的事业,回乡苦学技艺,一年后返京开了家过桥米线馆子,虽定价稍高,但在制作细节上一丝不苟,米线是自制的酸浆米线,汤是用整只老母鸡加宣威火腿煨的鸡汤,且是用鹅油封面,香气清醇——须知绝大多数号称正宗的过桥米线皆是用鸡油封面,因为鹅油的成本高出甚多。如此精工细作,数年过去,竟得发达。另一类在北方常见的米线,可称为“快餐式米线”,这类米线大都不是由专门的米线店出售,而是与凉皮、米皮、土豆粉、担担面、牛筋面、夹肉饼、麻辣烫等小吃同店售卖,所用米线是批量生产的、易于储存的细如挂面的干浆米线,其风味也大同小异,只是我在云南并未见过此种米线,近年各地都兴起“融合菜”,大概这种快餐式米线也是融合之后的产物吧。
的确,过桥米线是昆明菜的代表作。直到现在,言米线而必曰“过桥”,仿佛不“过桥”就不能算作正宗米线,也差不多成了众多食客的一个潜在的心理定势。其实,过去云南许多地方地瘠民穷,等闲人吃不起过桥米线,平头百姓常常吃的,是小锅米线。小锅者,指的是米线不宜大锅煮食,一锅只出一碗,才能保证口味,汪曾祺以为吃小锅米线是昆明人的讲究,实则不然,小锅米线源出玉溪,玉溪当地有一个“米线节”,节日期间家家户户均以小锅米线宴客,现在俨然已发展成大型的美食文化节,有所谓“一套八小碗”的说法,指的是八种小锅米线,汪曾祺曾提到的焖鸡米线(实即焖肉米线)、爨肉米线,皆在其列。在北方要吃到品类繁多的小锅米线并不容易,以前我在北京读书时,常去文慧园附近一家大理人开的小馆子,这家店自制的米酒、乳扇、饵块,以及砂锅鱼、烤罗非鱼,都很不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售价八块钱一碗的凉鸡米线,酸辣鲜香,鸡肉肥嫩,米线有筋骨,盛暑时节,食欲不振,以这样的一碗米线作为午餐,实在比凉皮、米皮、凉粉等物更能提起胃口来。
开封十余年前有一家米线馆子,专做正宗的过桥米线,从米线、鸡汤到主料食材,都甚是讲究,腰片、鸡片、里脊肉片、乌鱼片、鱿鱼片,片得飞薄,整整齐齐在一个大圆盘子里码作一圈,也正为如此讲究,价格便始终居高不下,当时开封夜市上一碗砂锅面仅售三块钱,而这家馆子里一碗最便宜的过桥米线也要二十几块。开封人吃东西,颇有点两极分化的意思:要么是图实惠吃夜市地摊,开封夜市天下闻名,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要么是到大酒店里吃宴席,环境好,也体面,尤其是宴请比较重要的客人,更是非如此不可。米线一物,在开封人眼里近于小吃,以吃宴席的代价去吃小吃,自然是很没有“性价比”的,这家米线馆子开业三年,门可罗雀,本来已料定要关门歇业,可是老板脑子灵光,颇晓得变通之道,竟将米线馆子改为火锅店:原有的熬制鸡汤、骨汤的技术直接用于制作火锅汤底,腰片、鸡片等变为涮品,至于米线,则俨然成了该火锅店独一无二的特色,凡到该店用餐的饕客,饱餐了牛羊鸡肉、鱼片腰片肚片、蔬菜菌类豆腐之后,必点一盘自制的酸浆米线,仿佛没这盘米线,这餐饭就不得圆满。自改为火锅店后,乘着那几年饮食行业里面火锅崛起的东风,该店每日食客盈门,只在近几年才被新兴的连锁火锅店挤了下去,但老板早已赚足资本,到大洋洲某岛国安度余生去了,这也算是米线行业里的一个异数吧。
在山东喝啤酒
十几年前初到烟台的时候,颇为当地喝啤酒的风气感到讶异,街边的大排档坐满了吃海鲜、吃烧烤的男男女女,人人操着一口掺杂了东北味儿的胶辽官话,桌上皆摆着十升一大扎或五升一小扎黄澄澄透着凉意的散装啤酒。烟台民风豪迈,三四个当地男子围坐一桌,一扎啤酒往往顷刻而尽,一顿饭下来,人均十升亦是常有的事,此种情形,在鲁西一带并不多见。更奇的是,烟台各高校的食堂里也常年供应散装啤酒,且取价甚廉,一厂啤酒(即烟台啤酒一厂出品的啤酒)一元两角钱一杯,二厂啤酒则只售八角钱一杯,其容量约莫在五百毫升上下,比之喝可乐、雪碧还要便宜,因之许多学生在食堂就餐时每每佐以啤酒一杯。前些年烟台某大学校门口马路对面曾开有一家自助餐厅,以售卖铁板烤肉为主,每位收费二十元,食材粗糙,口味平平,好就好在有不限量的烟台啤酒提供,后来开了月余即以内部装修为名挂牌歇业,重新开业时已经改头换面成了面包甜品店,有好事者询其情由,告曰店里仅啤酒一项便收不抵支,然而若不开放啤酒供应,却又无法吸引食客,只好关门了事。
何以胶东人特嗜啤酒?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容易解答。人们或以为是青岛啤酒的畅销带动起了胶东半岛喝啤酒的风气,其实整个山东省,多数地区皆有其本地的啤酒厂和啤酒品牌,如济南的趵突泉啤酒、泰安的泰山啤酒、临沂的银麦啤酒、威海的威海卫啤酒等皆是,虽然近年雪花啤酒勃兴,到处可见“勇闯天涯”的影子,但就山东一省而言,本地啤酒仍占优势,这并不是什么地方保护主义的心理所致,而是与啤酒自身的特性有关——你只有在距离出产地较近的地方,才有可能喝到鲜度最高的原浆啤酒和散装鲜啤酒。
原浆啤酒和鲜啤酒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熟啤。原浆者,指的是未经任何杀菌处理的发酵啤酒原液,倒入杯中,其色浑浊,酒液似也略有粘滞感,泡沫细腻如奶油,入口醇厚,香气馥郁,这种啤酒营养最为丰富,称之为“液体面包”并不为过。原浆啤酒的局限在于其保质期短,以出厂时间计,通常只有七天的保质期,所以要喝到这种啤酒,最好是在酒厂附近区域,近年物流运输越来越发达,也有网购原浆啤酒者,如青岛原浆啤酒一升装的,要卖到五十到八十块钱,价格昂贵且不说,重要的是,长途颠簸,亦不免有损于原浆啤酒本身的口感。山东另有一种“泰山原浆”,如今行销各地,颇受欢迎,甚至被有些人推为“国产最佳啤酒”,但必须注意的是,泰山原浆分多种,保质期为七天的,口感最佳,是真正的原浆啤酒,至于保质期长达半年的,可想而知,也是经过了某种杀菌处理,勉强只能算作“自然浑浊型”啤酒罢了。胶东男人多有嗜饮原浆啤酒者,视它种啤酒如泔水,这大概是因为习惯了原浆啤酒浓郁、醇厚的口味。我在烟台时曾识得一壮汉,每次去吃大排档,必先点三个烤馒头,三十串烤五花肉,三升原浆,一个烤馒头劈作两爿,将十串五花肉夹在中间,就着大杯的啤酒且吃且饮,不出十分钟,便全部下肚,但这还只是一餐饭的开场,美其名曰“垫垫底儿”。后来我离开山东到了江苏,便再难看到如此畅快的吃喝。
有人以为鲜啤酒与生啤酒是两种物事,这大概是混淆了普通生啤与纯生啤酒的区别。普通生啤即鲜啤酒,它与原浆啤酒一样,未经杀菌处理,保质期只有七天,人们所艳称的青岛随处可见的那种塑料袋装散啤酒,便是此类,而各地饭馆中均可见到的瓶装“纯生啤酒”,虽未经杀菌,却已通过严格的过滤程序而达到了杀菌的效果,因此保质期可长达半年,但是,从口感上讲,瓶装的纯生啤酒显然不及散装的普通生啤。山东人既嗜啤酒,各地又都有啤酒厂存在,要喝到刚出厂的鲜啤酒,并不是什么难事。吾友王某,以长途客运为业,每天周转于濮阳、济南两城之间。某日傍晚自济南归,携得趵突泉鲜啤一桶,约莫十五升上下,于是呼朋引类,在一家驴肉馆小聚。因是刚出厂的缘故,啤酒接满一杯,尤带寒气,喝一口下去,果然鲜爽,惜乎啤酒只有一桶,喝酒的人却有八个,大盆的炖驴肉刚端上来,桶里就已空空如也了,无奈之下,只好再索瓶装啤酒一打,结果喝得索然无味。后来王某放弃客运事业,改做桶装鲜啤代销,竟得发达,而促使他萌生改行之念的,就是当年那一桶由济南带回来的啤酒。
据唐鲁孙说,英国诗人威廉傅汉日常以熟啤酒代替茶或咖啡,生啤酒却绝不沾唇,可见也有嗜熟啤酒胜于生啤酒之人。但是,我读了这一掌故,颇疑心是其所喝啤酒较为优质的缘故,尤其是英国所产的某些艾尔啤酒,确实浓郁醇厚,回味悠长,比之鲜啤酒并不逊色。至于我们国内惯常所能喝到的工业拉格,如雪花勇闯、普青之流,或入口酸涩,或清淡寡味,以之代替茶或咖啡,那就未免荒唐了。自离开山东以后,要喝到散装的鲜啤酒,已是十分难得,郑州一到夏天满街都是烧烤、扎啤,但是其所谓扎啤者,往往是加了碳酸气甚至掺了冰水的熟啤酒,刚入口甚是清爽,喝完却无回味,若掺的是生水,有时喝了还要闹肚子。太原人极嗜汾酒,爱喝啤酒的却不多,这从山西本土啤酒品牌的弱势即可看出——山西有一种杏花村啤酒,也是汾酒酒厂所出,但此种啤酒即使在太原的大型超市里都难得见到,随处可见的仍是雪花、青岛。太原城北有一家日料馆子,某日我与朋友路过,信步踱入,见有散装的朝日生啤提供,就着芥末章鱼、炸猪排等,每人连饮四大杯,鼓腹而出,才约略找回了当年在山东喝啤酒的感觉。
朝日啤酒在山东的销量不佳,这大概是由于当地啤酒品牌较为强势的缘故,唐鲁孙曾述及抗战时期日本借助侵华之机开展商业攻势,将株式会社出品的太阳牌啤酒推广得连偏远村庄的小卖铺里都绝不断货,却总不及双合盛的五星啤酒口感好。所谓太阳牌啤酒,可以算作朝日啤酒的前身,1916至1945这近三十年时间里,日本人曾经营青岛啤酒厂,所以民国时期市面上常见的太阳牌啤酒,多是青岛啤酒厂所生产,其口味据说也与青岛啤酒颇为相近。而双合盛的五星牌啤酒,现在似乎已与青岛啤酒合资,虽然仍在生产,市面上却难得见到,我曾通过网络渠道购得一箱,味道并不出奇,不知是不是品质发生了退化。当年双合盛啤酒厂所用啤酒花产自捷克,负责生产的技师尧西夫·格拉也是捷克人,推想其口味,应是与捷克产的淡色皮尔森啤酒相近,苦味度和麦芽香味均甚浓郁。
近年精酿啤酒崛起,各大城市均可见到打着精酿啤酒招牌的餐吧或酒吧,比较讲究的饭馆里也都有自酿的啤酒出售,价位大都不低,一升啤酒要卖到五十至八十块钱,品质却是良莠不齐,尤其是酿造过程不易掌控的艾尔啤酒,更是如此。我曾在济南某精酿酒吧品尝过其自酿的IPA啤酒,入口沉滞,回味竟有些发酸,着实不敢恭维。另有一些精酿酒吧,在基本的质量把控上都不能过关,其所酿啤酒,稍饮几杯,便口干头痛,这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总的说来,我以为,在国内的大环境下,选择啤酒仍当以大厂出品的原浆、鲜啤为上,如若想要领略更多的口味,也可选择各种进口的瓶装啤酒,小作坊生产的精酿啤酒在技术上尚不成熟,仍须假以时日。
喝啤酒必须冰镇,因为啤酒有其特定的适宜温度,过此则味道酸涩,不堪入口。这本是常识,然而无论是在山东、河南、山西,还是在北京、上海、江苏,都有大把大把要喝“常温啤酒”的人,许多饭馆为省电费,也往往只在盛暑时节才提供冰镇啤酒,甚至某次我在太原某面馆见一中年男人索雪花纯生两瓶,因是寒冬腊月,竟要求服务生“热一热”,真不知加热后的啤酒是何种风味。其实若不习冷饮,大可改喝白酒、黄酒、红酒或米酒,啤酒而不冰镇,有如煲汤不放盐,实在了无意趣。相对而言,胶东人对冰镇啤酒的接受度、适应程度,都要高一些,这大概与他们习惯喝刚刚出厂、温度很低的散装鲜啤有关,只是凡事有度,纵情豪饮总是不好。十年前我在烟台时,常与朋友去一家肘子砂锅店聚饮,该店老板是本地人,生得膀大腰圆,性情十分豪爽,凡有来店喝酒的客人,必手擎足有五百毫升的一大杯生啤至其桌前,稍一碰杯,便一饮而尽以示敬意,每每我们一顿饭下来,眼见他已喝掉二三十杯啤酒,仍面不改色,只肚腹鼓起而已,凭了这一手本事,他的饭馆常常座无虚席。去年我因事去烟台,又找寻那家砂锅店,只见店面依旧,老板却已换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问之,才知当年的老板便是其父,五年前已因肝疾卒,年才四十,思之令人忽忽不乐。
鲁西的“大锅台”
过去鲁西一带人不怎么吃火锅,“铜锅子”或许还可偶尔见到,其他如广式、川式火锅等,皆市面上所无,至于时下流行的潮汕牛肉火锅、重庆九宫格火锅、丽江斑鱼火锅之类,更是闻所未闻。冬日苦寒,无论是朋友聚饮,还是家人小酌,当然是守着一口热乎乎的锅子吃饭更有氛围,对此,鲁西人的解决方法,就是所谓的“大锅台”。
大锅台,顾名思义,其首要特点是在大锅和灶台二者上。大锅是一口黑黝黝的铁锅,直径可达一米,灶台中空,用以放置大锅,讲究些的,下面还可添加柴火,以免锅内的食物冷却,需注意的是,一定要用木柴,若用木炭、煤炭或固体燃料之类,就了无意趣了。说白了,大锅台就是大炖菜,这并非鲁西所特有的饮食特色,东北有,苏北也有,唯东北大锅台特重鱼鲜,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东北野生大鱼坊”之类,即由此而来,苏北大锅台则以“徐州地锅鸡”最是名声在外。相对而言,鲁西的大锅台是较默默无闻的,其风味、特色亦近于鲁菜,厚重、量足,并不以精致、细腻见长,曾有一个上海朋友到阳谷县谈生意,当地接待之人为显诚意,特地请他到一家大锅台吃饭,要了一锅炖大雁,另有一盆红焖肘子、一盘红烧黄河鲤鱼、一盘剔骨肉、一盘烧鸡,外加凉菜四味,大鱼大肉,琳琅满目,再配以高度数的景阳冈白酒,那位上海朋友却自始至终没有动几下筷子,可见不同地域自有其不同的饮食习惯,强求不得,在上海人看来,这种表面浮了一层油的大锅炖菜,恐怕连基本的食品卫生都是无法保证的。
吃大锅台要到乡下才有意思,一则,城里本就少有这类饭馆子(近年似乎稍有变化);再则,吃大锅台多少还带着那么点野意,若是在装修一新、器用现代、侍者环伺的雅间,拿捏着夹几筷子,反倒失了趣味。我有次随朋友去莘县,劳碌一天,到下午五点时分已是腹鸣如鼓,商量着晚餐要找家大锅台吃炖羊肉就馒头,结果寻遍整个县城未见一家,嗒然而返,不料却在离县城不过七八里许的一处小镇上接连见到十几家,每一家都是灯火辉煌、食客满座,于是任择其一入内,索五斤鲜羊肉现炖,纵情大啖之余,才恍然明白原来县城里的人要吃大锅台都会驱车至此。
鲁西大锅台既不像东北那样以野生鱼类为主,也不像徐州那样以炖鸡为主,其原因大概是在于:鲁西一带水产较少,鱼类无非鲤鱼、鲢鱼、草鱼、鲫鱼、鲶鱼等几种,这些鱼或者鱼刺太多,或者肉质不似东北鱼类那般紧致有韧性,又或者体型太小,皆不适合大锅久炖;至于炖鸡,鲁西人酷嗜此味,因此到处有专门的炖鸡店,倒也不必求之于大锅台。故而鲁西大锅台的菜品向来是以羊肉和排骨为主,如果想吃点新鲜花样,还有兔肉、鹅肉、大雁肉可选择,只是兔肉容易有股子草腥气,非四川麻辣口味不能遮掩之;鹅肉似以腊鹅、烧鹅为佳,炖鹅并非上品;大雁肉虽是出自养殖场,但价格也颇昂贵,寻常的朋友小聚,是很少点炖大雁这道菜的。
炖排骨并没有什么出奇,唯有“大炖羊肉”,才算得上是鲁西大锅台的招牌菜。究竟“炖羊肉”的前面何以要加上一个“大”字,存在多种解释,有人认为这是“大锅”或者“大火”的意思,因为鲁西的大炖羊肉要置于大锅之中用大火炖煮;也有人认为是“大料”或者“大块羊肉”的意思,因为鲁西人烹制“大炖羊肉”要放白芷、桂皮、良姜等多种佐料,羊肉也需切作较大的肉块。不过“大炖羊肉”并非鲁西地域的特有吃食,其他地方也有,如山西民歌有句云:“大炖羊肉满锅油,不如娘家下喝稀粥”;陕北民歌有句云:“大炖羊肉短不了葱,山曲不酸不好听”;内蒙古民歌则有句云:“大炖羊肉锅扣锅,实心实意你和我”。由此可见,至少在晋北、陕北、内蒙中部一带,大炖羊肉也是平头百姓的寻常吃食——以山西为例,越往晋北走,则吃羊肉的风气越盛,这大概是与其地气之寒冷有关。唐鲁孙谈论山西饮食,念念不忘大同的“犒劳”,亦即今日山西菜中的“栲栳栳”,这是一种以燕麦面为主要原料的吃食,“把面卷成实心春卷形,放在蒸笼里蒸,拿出来放在碗里掰碎,浇上浓厚的羊肉汤来吃”,之所以要这样吃,既是因为大同一带气候寒冷,面食以燕麦为主,也因为羊肉与燕麦面的搭配最能使人耐得饥寒。
鲁西的大炖羊肉论斤出售,十年前,每斤羊肉约二十元,现在则是五十元左右,这里指的是炖煮之前在肉床上现割下来的鲜羊肉,炖煮之后自然还会缩水。讲究一些的大锅台馆子会有种种炒菜,以鲁菜为主,如熘肝尖、爆三样、炒合菜、糖醋里脊等,寻常大锅台则除了炖羊肉等主菜之外只备现成菜,如卤豆皮、煮花生、糟鱼、盐水黄瓜、拌粉皮等。由于多数大锅台馆子都是自行杀羊、剥羊,所以如果时机凑巧的话,还可吃到新鲜的麻辣炖羊血,这道菜味道鲜麻香辣,口感又嫩滑酥爽,用作开胃菜是最合适不过,只是馆子里每日杀羊所得的羊血数量有限,刚刚出锅的麻辣炖羊血,往往一售即罄,能不能吃到,就只得看时机之是否凑巧了。
从口味上说,鲁西的大炖羊肉与白煮羊肉(如新疆的白水羊肉或苏州的藏书羊肉)绝异,羊肉经过掺有多种香料的浓郁汤汁炖煮之后,其特殊的膻气已几乎被遮掩无余,这对于不喜羊肉膻气的山东本地食客而言,简直是福音,毕竟羊肉的那种细嫩质感非猪肉和牛肉所能比拟;但对于专喜羊膻气的西北食客而言,就是场灾难——没有了膻气的羊肉,怎么还算得上是羊肉?有个甘肃的朋友到鲁西来做客,接风宴就是吃大炖羊肉,结果直到席终,他也不相信吃到嘴里的是羊肉,主人甚是尴尬,不料次日早晨去当地早点摊上吃羊肉包子喝胡辣汤——是那种特意在馅里剁进了羊油的包子,一口咬下去,油汤四溢,膻气扑鼻,他欣喜道这才是真的羊肉啊。大炖羊肉并非纯粹的炖肉,除了羊肉之外,通常还要放白菜和粉条,白菜最好用菜心,或干脆用娃娃菜,粉条则以红薯粉为佳。鲁西乡民若是盖房子需犒劳工人,也通常会弄一锅大炖羊肉,再蒸上百十个馒头,羊肉与白菜、粉条之间的比例把握,是考验主人豪爽程度的关键所在,若是遇上了吝啬的主人,没准吃一大碗也只能拣出两三片羊肉。
据说鲁西的“大炖羊肉”与单县羊肉汤之间颇有渊源,此说不无道理。单县羊肉汤有“红汤羊肉”之称,其宗旨亦不在保留原味,并且在烹制过程中也需加入多种香料。那么鲁西的大锅台馆子里究竟有没有“白汤羊肉”呢?至少在我的个人经验里,是未曾遇到过,仅有的一次特例,是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从一个以饲羊为业的亲戚那里弄到一只洗剥干净的整羊羔,遂邀得几位朋友,提着羊羔和啤酒去了一家相熟的大锅台馆子,请厨子帮忙加工。厨子打开袋子,将羊羔横置在案板上,双目放光道:“这是不满三个月的小尾羊!”遂建议我们不必用大炖的老法子处之,这等鲜嫩的羔羊肉,宜白煮,羊肉稍煮即熟,蘸椒盐吃,羊汤则可加芫荽、小葱等,如此吃肉喝汤,才是正道,否则便是暴殄天物。我们听后自是连连点头。羊肉煮熟后,果然鲜嫩异常,羊汤呈乳白色,上面飘了几粒绛红的枸杞,以及碧绿的芫荽、小葱,看着便十分诱人。一只整羊羔,熬煮成一大锅羊肉、羊汤端上来,再随意掂配上几盘凉菜,我们六个人,竟一鼓而荡尽,其中有位朋友连喝了九碗羊汤,出店门时已是腹胀难忍,走起路来竟是摇摇晃晃,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酣畅淋漓的一次吃大锅台经历。只是这样的白煮羊肉,一则于食材本身要求甚高,二则在鲁西地区也并不盛行,也不过是偶一为之罢了。
谈谈“急就章之菜”
郑板桥家书中有句话:“天寒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泡炒米是一种便于急就的吃食,在扬州、镇江、泰州一带颇为常见,有人以为这种炒米类似爆米花,是放入一个密闭容器内高温高压制成的,其实不然,对此,汪曾祺的《炒米和焦屑》一文中曾有细致解释,这里不必赘言。大概每个地域都有其特定的便于急就的吃食,袁枚的《随园食单》虽满纸俗气,但有一节却说得颇为隽妙:“若斗然客至,急需便餐;做客在外,行船落店;此何能取东海之水,救南池之焚乎?必须预备一种急就章之菜:如炒鸡片、炒肉丝、炒虾米、豆腐及糟鱼、茶腿之类,反能因速而见巧者,不可不知。”此处所谓“急就章之菜”,不难理解,指的是匆忙间能够拿得出的、对周边条件要求不高的菜品,由袁枚的文意推断,还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速成菜,另一种是现成菜。这里只说速成菜。
最常见的速成菜自然是简易的炒菜,如炒豆芽、炒肉丝、炒豆腐之类,这些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时下流行的一些速食品,如香肠、培根、方便面、速食汤等,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这里要谈的,是一些更具乡土性、地域性的吃食。
蒸菜在河南、山东是比较专门的一个名词——这里的“菜”专指菜叶,且大都是平常不吃的,如红薯叶、莴笋叶、芹菜叶、南瓜叶及种种野菜。曾有朋友到河南游玩,听当地人念叨蒸菜,以为是湖南的那种“小碗蒸菜”,及至吃到口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两种东西。河南的蒸菜算不上是什么地方特色,说穿了,这是一种“穷人菜”,诸如前面提到的红薯叶、南瓜叶等物,原是弃而不用的东西,仍然捡回来想法子吃掉,不是因为馋,是因为饿——过去哪怕有白菜、黄瓜、冬瓜、豆角之类蔬菜可吃,谁会去吃那些菜叶子呢?但是,穷时候养成的习惯延续下来,也就有了“蒸菜”这种吃食。蒸菜的做法,是将拣择好、洗净的菜叶用玉米面(也有用白面的)搅拌,再掺以盐、香油等佐料,上锅蒸熟。出锅或拌以蒜泥,或加点辣椒油。蒸菜因蒸好后便于存储,想吃时随时取出稍事加工即可,既可算是速成菜,也可说是现成菜,它不是什么美味,但若选材得宜、烹制得法,还是颇能勾人馋涎的。以我有限的经验来看,最宜于用来制作蒸菜的,是一种北方常见的野菜,学名叫作麦瓶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面条菜或扫帚菜。面条菜在华北的麦子地里随处可见,常常会被耕种者当作杂草给除掉,这种野菜只在幼嫩时可吃,稍老便苦涩不堪,豫北、鲁西一带的小饭馆里多有现成的蒸面条菜售卖,但不见得都能做得可口,如菏泽、济宁等地的蒸面条菜喜欢放大量蒜泥,那种滋味,南方人恐怕不敢领教,倒是濮阳有些地方舍蒜泥不用,反将蒸好的菜再入锅加猪油、辣子稍微翻炒一下,吃起来香气馥郁却又毫不油腻。
东北的乱炖,在冀南、豫北叫作熬菜,所用食材有些差别,就各自所承担的角色而言,也大不相同。乱炖在东北是主菜,故而花样甚多,有所谓“八大炖”之说,熬菜在冀南、豫北却不过是一种“应急菜”,只在人多口杂、仓促间无所措手或者图省事的情况下才吃,所以多半仅以大白菜、粉条、豆腐、猪肉片、丸子为主要食材,没什么变化。濮阳乡间凡有盖房子之类的事宜,请工人来干活,除每日照例的“日薪”外,在烟酒伙食方面,也有个统一的标准,酒通常是简装的牛栏山二锅头或沱牌大曲,烟在过去是“喜梅”、“芒果”或者“琥珀”,现在则是“红旗渠”、“帝豪”或者“将军”,至于伙食,多半是熬菜、馒头。有一次我在范县小住,所住房屋后面的住户恰好在施工,约有五六个工人,户主每日中午、晚上各管一顿饭,午饭熬菜馒头,晚饭再以中午吃剩下的熬菜作卤拌面条,虽只五六个人吃饭,但熬菜足足有一大锅(约莫三尺直径),上面飘着一层五花肉片,下面是层叠的白菜、豆腐、粉条,到吃饭时,工人们各自端着大海碗围到锅前,每人一碗熬菜,三五个馒头,又或者用铁皮桶提来一桶煮好的面条,也盛在海碗里稀里呼噜地吃,吃完用面汤涮涮碗,几口喝下肚去,如此景象,虽然粗朴,却让人记忆深刻。现在河南、河北、山东的饭馆里,多有熬菜或大炖菜出售,取价甚廉,但往往有拿隔夜剩菜回锅杂烩者,口味既不甚佳,卫生状况亦是堪忧,说到底,应急菜仍以不失应急本意为妙,若专门跑到馆子里去吃,反而无趣。
华北一带的蒸碗与湖南、广东的蒸菜都不同。就本来宗旨而言,华北的蒸碗,湖南的蒸菜(比如最有名的浏阳蒸菜),均属应急菜,其性质颇近于宫廷里所谓的“温火膳”——为了仓促间能够端得出来,一应主要食材均是经过提前加工,烹制之时,只需稍加佐料上锅蒸热即可。广东蒸菜则是着眼于养生,因为以“蒸”的方法烹调,最宜于保持食物自身的营养成分不致流失。如今湖南蒸菜已然蔚为大观,我曾在北京的一家浏阳蒸菜馆子就餐,见其蒸菜品类竟有五六十种之多,有的菜还要经过三蒸之后,方能上桌,这显然已远超出“急就章”的范围,倒是河南、山东的蒸碗,还能保留一些本来面目。蒸碗在华北虽是应急菜,等闲却也并不容易吃到口,要到春节前后,或家有红白事之时,才会列入食谱,饭馆子里也有售卖蒸碗的,如郑州的烩面馆子,除主食烩面之外,所售菜肴无非两种:一种是凉拌菜,如拌菠菜、拌黄瓜、拌粉皮、拌耳丝、拌牛肉之类;另一种则是蒸碗,有黄焖鸡、带鱼、扣肉、豆腐、丸子等。这是颇经济的一种做法,一则烩面馆子客流量大,近于流水席,每天所有凉菜、热菜一次性做好,售罄即止,多数时间只需几个做面的师傅忙活即可;再则,相较于寻常的“温火膳”,蒸碗更易保留食物原本的质感,如蒸碗中的鸡、鱼、酥肉等物,皆是经过油炸处理,其表面仿如形成了一个保护层,久蒸之下,亦不致松散或软腻。
蒸碗算不得什么珍馐美味,也很难说是哪个地方的特色,举凡河南、山东、河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等诸省,地方上都有以八大碗、九大碗或十大碗为名的饭馆,彼此间大同小异。车辐曾提到过川菜中的“肉八碗”,诸如红烧肉、姜汁鸡、烩酥肉、粉蒸肉、夹沙肉、蒸肘子等,且不说吃,只听名字就觉得肥腻不堪,然而蒸碗大抵宜肉不宜菜,试想如果将白菜、菠菜、萝卜、西兰花等物浇了浓汁上锅久蒸,那口感、味道多半不会好到哪里去,而即使是蒸豆腐,也需先将豆腐油炸才行,所用豆腐,亦以致密、坚实的北豆腐为佳,使用石膏液做成型剂的南豆腐是不合适的。
熬茄子在鲁西一带属于地道的平民吃食,其地位大概只比蒸野菜稍微高些,原因也很简单,在当地菜市场上,茄子、萝卜、白菜是售价最廉的三种蔬菜,相对而言,茄子又比萝卜、白菜更能顶饥下饭,所以尤为平头百姓所钟爱。汪曾祺有篇小说《晚饭后的故事》,写战争时期物价飞涨,戏子们生活不易,“有人唱了一天戏,开的份儿只够买两个茄子,一家几口,就只好吃这两个熬茄子。”可见茄子在哪里都是廉价菜。熬茄子到处都有,但做法不一,吉林有所谓“鲇鱼熬茄子”,当地谚语云:“鲇鱼熬茄子,撑死老爷子”,鲇鱼本身多油,熬茄子又需放大量油,过去平民伙食少油水,得此一味,吃到“撑死”,大概也是可以想象的;河北有土豆熬茄子,以土豆和茄子搭配,大概也是取其“顶饥”;梁实秋曾写过北方常见的熬茄子,“煮得相当烂,蘸醋蒜吃”,这在豫北叫作“蒜泥茄子”。鲁西的熬茄子是另一种物食,在定位上似乎介于主食、菜肴、羹汤之间,茄子要先切块,蘸上用面粉、椒盐、鸡蛋加水搅拌成的糊糊,下油锅煎得两面金黄,再加大量的水熬煮,出锅时浇香油,放切好的香菜末。因为茄子常常是事先煎好的,熬煮之前稍一过油即可,所以也可算是一道可用于应急的速成菜。按照“荤菜素做,素菜荤做”的道理,煎茄子所用的油自以猪油为宜,其味道远比用花生油、豆油来得香浓,阳谷县曾有个饭馆售卖熬茄子,三块钱一大碗,另加两个当地特产的大馒头,无论怎样的大肚汉,吃下去这些都该感到十分饱足了,只是这家饭馆煎茄子是用羊油,嗜之者以为无上妙品,不能接受羊膻味的,则闻之掩鼻。
鸡蛋茶里当然没有茶。过去华北乡民生活寒窘,仓促间需要招待远客,差一点的,是端一碗红糖水,好一点的,就是冲一碗鸡蛋茶,也有些地方,比如郑板桥曾做过官的河南范县(现隶属于濮阳市,与山东交界),当地习俗,是以红糖水荷包蛋待客——如果还嫌不够隆重的话,那就放两个荷包蛋。我幼时随伯父下乡,尝过一次这种糖水荷包蛋,那味道着实不敢恭维,但套用汪曾祺的话,这在旧时已算是“惯宝宝”才能常常吃到的东西,持以待客,厚意可感。鸡蛋茶其实就是开水冲鸡蛋,冲之前鸡蛋要打碎搅匀,之后还要滴几滴芝麻香油,糖、盐、酱油、味精等佐料一概不用,这样不甜不咸的一碗汤水端上来,喝到嘴里自然没什么滋味,不过是取其营养、方便罢了。阳谷县有家偏僻的早点摊,只经营鸡蛋茶、包子两种早点,包子是普通的牛肉粉条馅包子,那碗鸡蛋茶却是用整鸡熬煮出来的鸡汤沏就,上面除香油外又放了些许虾米皮,数年前我在阳谷小住时,距此早点摊很近,每日早餐以一碗鸡蛋茶、两个包子果腹,吃得心满意足。近年有注重养生者,在鸡蛋茶上弄出了许多花样,如阿胶鸡蛋茶、蜂蜜鸡蛋茶、杏仁鸡蛋茶、莲子鸡蛋茶等,这些新花样到底有没有养生的作用且不说,就其制作过程而言,显然已经失了“急就章”的本意了。
实习编辑 闫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