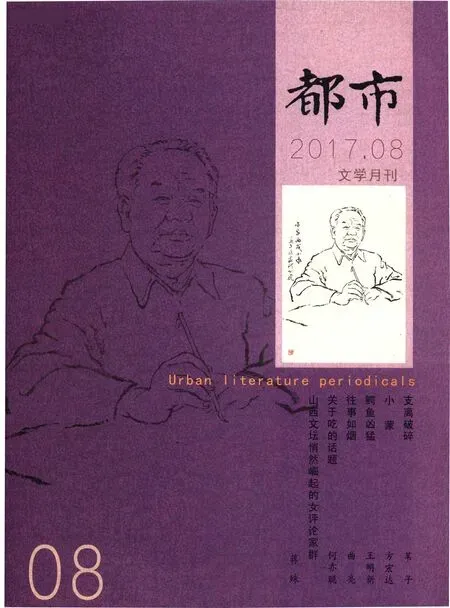往事如烟
曲 亮
往事如烟
曲 亮
题记:世界是早已安排好的,但一切不可预知。
宁小宁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像一支微风中的羽毛,不由自主地飘着,直到从窄窄的小巷子里拐出来走上一条黝黑的马路,他才感觉脚步变得结实起来,早上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眯缝着眼睛,用手摸了摸前额,凉冰冰的,好像自己刚从死亡中解脱出来。
他要去的地方是县城一条狭长的胡同,连宁小宁都不知道他是第几次不由自主地走到这里,这并不是一个怎么好的地方,它在小城的一个角落,靠近绛水河。就连阳光也不怎么光顾这里,巷子里到处阴暗潮湿,墙角和青石板的夹缝里长满了青苔,阴沟里的流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有只死鼠正躺在那里。一只灰褐色拴马石上布满了黑色的斑迹,像一个个恐怖骇人的虫子,拴马石的下面也长满了青苔。
这里的一切仿佛都是旧的,就连时光也是,那么散漫,慵懒。任何生命的迹象在这里都变得缓慢起来,呼吸,眨眼,心跳,血管里的血液缓缓地冲刷着血管壁,像奔跑到平原的洪水一样恣意流淌。
一切更像是一个偶然,一个垂暮老人的叙述让宁小宁无数次来到这里,他像着了魔一样来这里寻找,多少年了,他已经记不清,他有些累了,寻找和探知的欲望像一个巨大的引擎一样推动着他。最后一次,他又一次对自己说。他从没想或许这只是那位老人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
宁小宁一闭上眼就能记起老人的脸,慈祥安逸。那布满皱纹的脸总是微笑着,让他觉得自己是躺在美丽的夕阳下,就要经历一次幸福的死亡或是重生。他经常在梦里梦见那位老人,他总想问她,直到发现自己在梦里是一个哑巴,尽管他知道这只是一个梦,老人已经去世了,老人走的那天飘着大雪,有人说是百年不遇,因为村里唯一的那口甜水井被雪封了井口。临死前老人的嘴巴仍闭得紧紧的,好像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任何留恋又像欲言又止,可一些细节仍显示出一些端倪,比如,老人走的那天恰好是她九十九岁生日。之前她就说过,她是绝对不会活过一百岁的。
在梦里宁小宁想从老人嘴里得到答案,哪怕谜底极其简单幼稚,可老人从不说话,宁小宁知道她肯定不是哑巴,因为一切都是她安排的,老人笑着从一棵低矮的树上抓下一把树叶放进嘴里,她嘴里渗出的汁液让宁小宁感觉老人根本是一只牛马,老人突然愤怒的脸让宁小宁感到恐惧起来,那是一张充满世界上各种神情的脸,惊恐,暴怒和无可奈何……。
也许这根本不是什么梦境,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真实地发生过,他想知道答案,所以当他硬着头皮嚼着老人塞进他嘴里的树叶时,预想树叶的苦涩气味使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树叶是甜的,甜得像葡萄一样,他嘴巴里强烈的味道告诉他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当他睁开眼时才发现自己站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到处是绿色的葡萄,老人恶狠狠地说:“饿死人的葡萄。”其实老人根本没说话,可宁小宁却听得见那个声音,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默默进行着。
宁小宁没想到一个邂逅的老人会带给自己如此的痛苦,也可以说是快乐。猜谜般的快乐,就如对自己命运的揣测,充满希望和气馁。那是一个叫埠曲的村子,河流顺着村子拐了一个大弯,像一个母亲把孩子搂在怀里。
多么慈祥的老人,当时她正坐在夕阳下的一块铺垫上悠闲地织着鱼网,那个铺垫是用秋蒲晾干的叶子编成,旁边燃了几只拇指般粗细的秋蒲棒儿,那袅袅的烟雾围着门口的石鼓久久不肯散去。风吹动柳树枝条发出“莎莎”的响动。老人的牙齿异常锋利,咬断一根网线显得轻而易举,也许她是抽烟的,他这样想。他见过许多像老人这样的抽旱烟的女人。她们无一例外的牙齿都特别得好。
宁小宁走累了,他把自己写好的稿子放进包里,他的帆布包曾装过无数稿子,大多数是杂志社的退稿。后来稿子寄出去,干脆就不再退,那些稿子像战争中的亲人一样杳无音讯。他坐在老人旁边的一盘石磨上面,石磨有一铺炕大小,后来老人告诉他,那个东西叫碾。碾边缘的沟槽如同人脸上的皱纹。也许这是一个村庄的胎盘,宁小宁经常会有这样怪异的想法。碾中间的部分异常光滑,而且有一个陷下去的完美的弧形,那里显然少了一些石头,老人说,那些石头是被村里人吃掉了。村里许多老人的两条手臂磕在一起发出石头般清脆的响声。
老人自顾的叙述让宁小宁不敢确定她是否在和自己说话,她的叙述很平稳,声音像收音机一样富有岁月的年代感,声音配合着织网的节奏,像是演练了无数次,也许有无数的人听过。那感觉像一只小舟在水行驶,划出缓缓柔和的波纹。
埠曲一个古老的村子,老人稳坐的街口是通向寺院唯一的道路。这盘碾上应该坐过许多像宁小宁这样的探寻者,老人说“寺败了,龙走啦!”宁小宁听说过关于这座寺院的很多传说,他想从老人这里知道更多的关于寺院或是村子的历史,曾经有画家试图用画笔描绘当年的村子,可老人的怒骂让他们败兴而归。
老人像祖母那样摸摸他们的小脚趾,然后摇摇头说:“滚吧!外乡人!这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小村最后的秘密就掌握在老人手里。传说七路寺佛塔的地宫里面有无数的金银财宝。
老人的冷漠让宁小宁无所适从,夕阳好像总是那么高,老人的叙述显然已经很久了,因为她织的网已经抻出了很长。老人的故事吸引了宁小宁:那一口终年流水不竭的小井,单手撂倒骡子的莽汉,飞檐走壁的神偷,甚至是和小叔子私奔的女人。老人讲得很有兴致,她不断地擦去嘴角流下的涎水。仿佛又美美地活了一回。
最后老人说自己曾经也到过城里,是去贩卖旧衣服,她忽然抬起头盯着宁小宁,老人的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里,她的嘴唇瘪着,口腔里仅剩的几颗牙齿像忠诚的卫兵一样迟迟不肯离去。
老人说,其实那些衣服原来都是死人穿过的。是那些闯关东死在半路上的人,同伴抛弃了他们的遗体,所以有人就像强盗一样抢劫了他们。他们毫无怨言。
老人的手伸过来时宁小宁甚至都没有发觉,她用手摸摸宁小宁的小脚拇指,然后“呵呵”地笑出了声。她开始跟宁小宁讲故事。
宁小宁起身要离开了,或许他早就该离开,天已经黑了,老人手里飞快地织着网,梭子穿过细线后系紧的声音像勒死生灵时发出的喊叫一样瘆人,老人冲着宁小宁喊道:“孩子,耍累了就回家吧。七路寺不留香客!”宁小宁突然感觉自己和这个老人或者这个村子有着某种关系,可是一切都无从知晓。
宁小宁非常渴望把自己心里的故事讲给老人听,他甚至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老人能解开自己心里的结。可在老人很前,宁小宁就是开不了口,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遏制住了他的喉咙,他有些急了,抓耳挠腮,甚至开始流泪,老人抚摸着他的脑袋说“孩子,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只是时候未到,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事情就会像刀刃上的乱绳子那样迎刃而解。”
后来老人不在了,宁小宁再坐到那个碾台上的时候忽然感觉一阵冰冷,此前老人在的时候这盘碾始终像一盘炕那样温暖。宁小宁坐在冰冷的碾台上,回忆着老人的面容,干瘪的嘴唇,下陷的眼窝,骨瘦如柴的身体和一对如风干梨子一样的乳房,他试着在这冰冷的碾台上跟老人说话,他失败了,他的屁股像针扎一样疼。
难道真像老人所说,这世上所有的事情,原本都是一个梦?人死了究竟是梦的开始还是结束?他记得老人去世的挽联上写着:大梦一场。老人去世时很安详,面部的表情和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宁小宁总觉得老人会告诉自己点什么?老人要说的话会是什么呢?
之前老人提起过的那个售卖旧衣服的集市就在小城的一角,卖得不仅仅是旧衣服,旧家具,旧书报,古董,佛珠,花鸟鱼虫,什么东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卖。久而久之那里就被称为“破烂市”。好像一切都是旧的,卖东西的大多都是老人,他们衰老得很慢,时间仿佛在他们脸上停留住了,总之,这里的一切,都像过去的时光,或者说,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过去的影子或如烟似雾一样的往事。
往事其实很折磨人,只是这个过程比较缓慢,就是这个缓慢的过程才使那段往事变得狰狞恐怖,宁小宁每天都活在那段往事里,根本抽不出身来,有人甚至觉得宁小宁得了什么奇怪的病,要不然他怎么会瘦得像一具木乃伊,再后来,有人怀疑宁小宁吸毒。
每天一点一滴的改变让宁小宁没有觉得自己变得有些面目狰狞,只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单薄的身体有些承载不了自己的生命。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段往事,有时候他甚至觉得那根本就是他自编自导的一个故事,可他实在无法从这个故事中分身出来,那个女孩的身影在他心里总挥之不去,如影随形,他在梦里随时可以看见那个女孩脸上的绒毛,她温暖的笑容,她轻柔的话语,每当她转身离去,总会让他撕心裂肺地大哭一场。
当年他是班长,她是班团支部书记,她粉笔字写得好,他经常让她帮忙办班里的板报,板报上经常有宁小宁写的诗,经过她的手写出来,别样的美,宁小宁和她不怎么说话,他一看她,她就笑,低着头,脸红红的。宁小宁的一个眼神她就会明白,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时常让宁小宁陶醉,难道这就是爱情?这个想法让宁小宁吓了一跳,再看她的时候,宁小宁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可他心里是窃喜的,这种喜悦跟谁也不能分享,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把她从心里拿出来,想一想,然后再把她小心地放进心里。
就在宁小宁发表诗歌的第二天,他在操场上遇见了她,她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看一本书,那是快毕业的季节,同学之间正流行写分别赠言之类,宁小宁也给别人写了,可他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怎么好,要是自己的诗歌每次都由她来誊写该有多好?
其实这是送给她一个礼物的最好机会,快毕业了,同学们之间都在互相赠送礼物,宁小宁准备把自己发表诗歌的那本刊物送给她,扉页上写些什么字呢?他没想好,反正他不会写那些我喜欢你之类庸俗的话。
那天下午,宁小宁在那本诗集的扉页上写了两句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宁小宁觉得她一定会明白他的意思,可万一她不明白呢?为了更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又在这两句诗的后面画了一颗心,画完他就后悔了,那颗心画得实在太丑,简直看不出来像一颗心,更像一个梨子或是苹果,可是没办法,宁小宁就这样把那本诗集在下午放学的时候送给了她,宁小宁想,她一定会明白他的意思。
宁小宁在心里开始了种种设想,比如他们一起读高中,然后是大学,最后结婚生子,她躺在自己怀里,两个人一起看宁小宁写的小说。或是两个人拉着手走进电影院,一起看由宁小宁小说改编的电影。总之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要等她来,把这一切美好都说给她听。
第二天,她没来上学,有同学说,她不小心崴了脚,正在医院治疗,宁小宁不放心,可是没有办法,那一天,他心神不宁,第三天,她的父亲来搬她的书桌,班上的人这才知道,她死了。
后来关于她的死传出了N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说,那天放学回家,她拿了家里的衣服去河边洗,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个深潭,那是一个做黄金用过的废弃的池子,她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甚至都来不及挣扎就沉了下去,要不是因为散落在岸边的衣服,家里人要找到她只能等到她尸体浮上来的时候。
可是回家的路根本用不着路过那个大池子,何况那里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和秋蒲,她去那里干什么?难道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小解?还是其他?宁小宁想,这一切会不会是和自己有关呢?会不会是因为那本诗集呢?
这个想法让宁小宁激动起来。如同一个安静的水潭被抛进一颗巨大的石子。宁小宁知道她的继父对她管得很严,是不是她害怕被她的继父发现所以才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看那本诗集?还是真的和宁小宁没有一点关系?宁小宁心里不敢肯定,在这个尴尬的时间里,宁小宁和一起死亡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记得她曾经说过,她的志向是当一名医生,而且是妇产科医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疼爱她的小姨就死于难产。她想离开家,去到很远的地方上大学,她继父老打她。
宁小宁觉得自己也死了,他无法从她的死亡里走出来,他有时候也想,也许她的死只是一个偶然,这一切真的和自己无关,可是这需要证明,一个切切实实的证据,可他至今没有找到,也许老人给了自己指点,只是自己一时没有悟到。
这就是老人讲述的那个集市,果然有许多贩卖旧衣服的人,极少有人买,卖衣服的大多是一些老妪,她们都悠闲地抽着烟,这一切显得很不真实,甚至比梦里的都假,难道她们每天只是为了在这里等待一些根本不会到来的顾客?宁小宁在集市上走着,警觉得像一只兔子,他感到了许多异样的目光,卖旧衣的老者,花圈店的老板,他们互相交换着眼神。
宁小宁觉得自己像一个身陷重围的侠客,只等那搏杀的一刻,也许这只是一个梦,一个偶然的事件会让他醒来,重新坐进教室里,翻开她还回来的那本诗集,看看上面写得是什么?
整条集市的街道被光和影分开,宁小宁一脚踩着阳光,一脚走在暗影里,如同一半身子在地狱,而另一半尚在人间,他走到了旧书摊跟前,慢慢地蹲下,他走累,浓重的阴影把他包围起来。
书摊的主人同样是个老者,他正在听收音机,天线竖得老高,听到有人来他慌忙地从兜里摸出只有一条腿儿的眼镜挂在耳朵上,像遇到熟人那样冲宁小宁打招呼:“你来啦!”他的声音不大。并不像招揽顾客的生意人那样充满假惺惺热情的腔调。那种感觉就像你来拿寄存在这里的东西一样,他期望你赶紧拿走,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宁小宁“哗啦哗啦”地翻着书,他感觉到他正盯着他,尽管他已从茶色的镜片中看到他那如枯井般空空的眼眶,他再抬头看见镜片里自己消瘦得像病人一样的脸。“年轻人,好好找找,也许有你要的东西”。老者像是冲着空气喊。
“你怎么知道我是年轻人?”宁小宁本能地说出这句听上去不太礼貌的话。。
“是你的脚步声告诉我的。”老者回答。
薄云遮了太阳,光线像是透过磨砂玻璃洒了下来,像一支支箭一样射向地面。宁小宁从兜里摸出一个硬币丢给老者,他们之间的距离的确有点远,老者不去捡钱,好像知道宁小宁在试探他究竟是不是瞎子,他伸手从背后拿出一只鸟笼,煞有介事地向里面的鸟儿吹着口哨,茶色镜片上有两只鸟在打架。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瞎子,其实瞎子的眼睛在心里,比有眼睛的人看得都清楚。宁小宁这样想着,直走到大路,宁小宁才打开那本书,其实之前他根本没在意,他很久没有读过书了,他对书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忽然他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那些书本,他曾经那样地爱着它们,或许自己不应该那样做,至少书本没有像生活那样欺骗他。
他像掀开女人衣服一样翻开了书,书纸已经泛黄,也许是被水淹过,扉页上的签名有些模糊,但还看得清,或许只有宁小宁看得清,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宁小宁。那不应该算作是字,看上去更像是一条歪歪扭扭的曲线。那是他用左手写下的。
十二年前的阳光也是病怏怏的,就连校园里的那棵柳树也长满了虫子,而且一个个像空降兵那样肆无忌惮的拉着丝线降落到地面上来。
是因为一支烟,或者说是因为一个叫梅的女孩,她对宁小宁说:“来,你吸一口看看。”宁小宁用深陷下去眼窝里疲惫的眼睛望着梅,梅很坚决,口气无法让人推脱,她说:“你再不吸它就要灭了。”好像这根本不是在吸烟,而是救命,救一支香烟的命,宁小宁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那支烟,手像花朵一样绽开着,烟到唇边的那一刻他的手抖了,梅像一个阴谋者一样坏坏地笑。
宁小宁深吸了一口,马上有一只粘腻的手抓住了他的喉管,他的样子仿佛马上就要窒息,梅惊惧地望着宁小宁,她扶住了他的肩膀不让他倒下去,另一只手在他的后背上急促地抚着,宁小宁感到自己的脑袋被梅呼出的热气包围着,梅的手像是直接抚到自己的皮肤上,汗毛倒伏的快意使宁小宁差点喊了出来。此时,教师里空无一人。
那个满脸横肉的老师掌掴宁小宁的声音吓坏了所有人,梅以及告密者胡丽。胡丽没想到自己的告密会使宁小宁承受如此大的痛苦,作为一个偷窥者她更多的只是嫉妒,当她看到宁小宁嘴角躺着血冲她微笑时她怕极了,恐惧使她向梅投去乞求的目光。她感到自己身体里的东西被宁小宁一点点挖去,宁小宁的目光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宁小宁每天深重的呼吸让胡丽每天胆战心惊,可他每天还是那样长长地喘着气,像个严重的哮喘病人。这深深的呼吸让宁小宁感到快意,或是放纵,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位漂亮的女老师身上脂粉的香气和微微的她的皮肤散发出的汗味。宁小宁觉得自己是世界里的王。他不屑一切的神气让这位女老师有些恼怒,她拍着宁小宁的桌子说:“宁小宁你到底要干什么?”宁小宁很平静地说:“我只是想借一本字典查查我到底得了什么病。”说完他从燕子的书桌里拿出了那本字典,红色的厚重的字典。
也许是秋天了,不然怎么会多了两泓秋水。
宁小宁是下晚自习后被叫到办公室的。得到消息时他正在座位上发呆,刚刚他趁没人的间隙在黑板的一角写下了一个奇怪的符号—YX。他毕竟和这些乡下的同学不一样,那种不同是彻底的,从皮肤到骨髓。
那位漂亮的女老师旁边坐了另外一个女人,她更像女人而不像老师,巨大的乳房让她几乎弯不下腰去,只是探着身子用一根铁钩子在通红的炉子里乱搅(办公室刚刚粉刷了墙壁),火光让宁小宁感到一阵灼热,宁小宁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叛徒,他望着漂亮老师水汪汪的眼睛,直到看见自己从里面顺着一泓秋水流淌出来,宁小宁说:“我抽烟了!”
此前胡丽每天承受着告密者的恐惧,直到她把那封信交给宁小宁。宁小宁很轻松地揉碎了那封信,随手便把它扔进煤堆里。胡丽怒视的眼睛让宁小宁感到好笑,他不屑地盯着她,直到她的目光软了下来,她的脸夸张地扭曲着,她用手捂着肚子乞求般地望着宁小宁说:“我来月经了!”宁小宁像一起肇事案的旁观者一样走开了。
这件事情以后的一个月,宁小宁把诗集送给了她,在宁小宁接受耳光的时候,没人注意她趴在桌子上哭了,所有人都被那两记响亮的耳光吓住了,如果没有她的哭声,时间仿佛也会停住。
一切似乎都要结束了,就在那个夏天,宁小宁在诗里写道:分手的夏天离开的注定要离开留下来的注定要留下来……小宁写完这首诗,自己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宁小宁拿着那本书,那本发表了自己诗歌的那本书,它好像一个老人一样,面目全非,但是在那个旧书摊上,宁小宁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相通,宁小宁没有迫不及待地打开那本书,尽管那里面有他需要的答案。
他把书放在桌子上,然后去洗了洗脸,接着上了趟洗手间,刮了刮胡子然后刷了刷牙,他想这样多少可以恢复他当年的一点样子,他坐到书桌跟前,他点燃了一根烟,他也惊奇自己竟然如此的冷静,他吸了一口烟,然后打开那本书。
就在自己歪歪扭扭的那两句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凭明送客楚山孤”下面,写着两行娟秀的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的旁边还有两颗心,一颗丑陋的心和一颗美丽的心,上面的红色印迹有些褪色,没错的,那些是她的字,宁小宁心里一下子空了,太久了,他等待这本书等了太久,而一旦等来了这本书,心忽然空了,他不知道这是不是答案,或者说是最后的答案?
要走了,收拾行李,还有在互相的留言簿上写上祝福的话,她的书桌是她的继父来搬走的,宁小宁从那个矮小的男人脸上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婷的消息,也没有看出他的任何异样。
这个答案太模糊了,他仿佛看到她在那个水塘边蹲下,她好像是在洗手,她将自己调皮的辫子塞进衣领里,也许是旁边的一丛秋蒲里的鸟儿吸引了她,那是一群白色的极其美丽的鸟。
她想挥手吓唬它们,直到她在水塘里挣扎她仍没后悔自己的行为,池塘里的淤泥很快堵塞了她的鼻孔,盖住她的眼睛,她甚至没来得及喊叫,至少不远处的人没有听到她的求救,也许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起的是宁小宁的那本书,也许她什么都没想,只想活下去,哪怕是命运已给她安排好的痛苦的生活。
宁小宁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撕心裂肺的痛,他甚至开始恨她,为什么那么早的死去,他看见那首诗的旁边,有人写了两个醒目的红字:傻逼。他不知道这个写字的人是不是在骂自己,但不可否认,那两个字写得很漂亮。
数年之后,宁小宁从吴一海的口里得到了真相,当年是她的继父强奸了她,她走到水塘边也许是自杀,后来她的继父再一次酒醉后道出了实情,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来他在一次车祸中惨死了,尸首都没收拾完整。
吴一海也是宁小宁的同学,从警官学校毕业后当了警察,他在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讲述了这一切,宁小宁发现吴一海的脑袋比过去大了许多,脸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正方形,样子很像扑克牌里的老K。
责任编辑 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