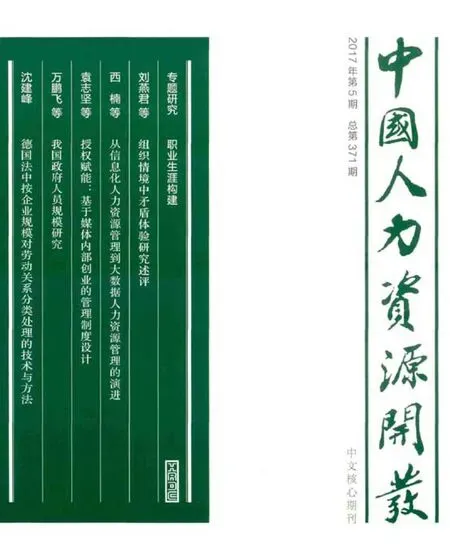德国法中按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分类处理的技术与方法
● 沈建峰
劳动关系
德国法中按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分类处理的技术与方法
● 沈建峰
德国劳动法中,对中小企业的特殊处理是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育也是为了适应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处理采取了临界值条款这一立法技术。各个规则或规则群适用的临界值主要通过工厂中的劳动者人数来确定,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以企业、雇主为计算单位的情况,另外一些特殊人群在计算时也有一些特殊规则。临界值的具体确定是一个理性计算、数字偏好以及利益博弈共同完成的过程。德国劳动法中目前有160多个临界值条款。解雇保护法适用的临界值是上述立法技术运用的一个重要领域。解雇保护法适用范围的临界值经历了5人到10人的变化过程,影响其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解决失业问题。工厂组织法中的临界值非常庞杂,但相对稳定。其临界值的设置体现了企业规模和参与管理强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德国的上述立法技术和方法在多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劳动关系 分类处理 解雇 参与管理
在我国《劳动合同法》修改的讨论中,一个日益被接受的观点是劳动合同法没有区分大企业和小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适用同样的劳动法律规则,因此完善《劳动合同法》的方向之一就是根据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进行分类处理(谢增毅,2017)。尽管有此共识,但为何要对中小企业进行分类处理,是要减少劳动者保护吗?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分类处理,按照统一的标准把企业分为大中小型?这些立法的目的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从目前来看却鲜有讨论,而这些问题才是把理念变成规则的根本性问题。在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和经验自然值得关注。德国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对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进行类型化处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一套方法和思路。梳理该思路、方法、制度和实践过程,吸取其中有益经验,对完善中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必将有积极的作用。
一、按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分类处理的目标与正当性基础
按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进行分类处理主要涉及对中小企业进行特殊规则设置(Lena Koller, Claus Schnabel, 2007)。该特殊规则设置的目标并不是要减轻对劳动者的保护,德国理论界认为有一些不可降低的劳动者保护,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只有在不可减低的保护之上,才可以根据企业规模进行特别处理。(Junker, 2004)按这种理念,与其说是按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分类处理是在减轻小企业劳动者的保护,不如说是根据大小企业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劳动者保护安排。
根据学者们的讨论,这种对中小企业进行特别处理的正当性主要涉及到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和就业方面的理由:中小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应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占了所有企业数量的99%,同时他们雇佣了超过50%的需要交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中小企业在德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WD6-3000-090/16)其二,社会政治方面的理由。对中小企业在劳动法上进行特殊处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原因。在德国的传统中,中小企业代表了社会中产阶级的力量,德国学者认为它构成了街镇共同体的支柱和市民社会的支撑者。(Junker, 2004)其三,劳动法上的特殊原因和理由。主要涉及到如下方面:1.成本因素。中小企业没有能力雇佣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法律专家,经常也没有能力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对较小的企业来说,在运用复杂的、部分还是不清晰的,没有专业法律人士的咨询就难以把握的解雇法会产生很大的困难。在这个领域,解雇期限引起的雇佣成本提高,补偿金的支付以及诉讼和继续雇佣的成本会影响企业的雇佣意愿。”(BT-Drucksache 13/4612)根据2002年德国的调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能够负担起劳动法律专业人士的企业数量也会增加。在中小企业领域,存在大量只能依赖于不健全的劳动法律咨询机构的企业。” (Junker, 2004)2.风险因素。对中小企业来说,每个员工行为都是企业经营的风险和利益来源,“在劳动力比较少的企业,经营的结果比大企业更加取决于每一个员工:更加依赖于每个员工的给付能力,个人的过错或者给付瑕疵在营业额比较小的企业会直接体现在经营结果上,在人数比较小的企业,企业损失也难以转嫁。” (Junker, 2004) 3.人身关系因素。在中小企业中,企业往往通过投资人自己管理,在企业主和劳动者之间并不存在专门的管理层,这种密切的人身关系也导致其劳动关系处理不同于大企业。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小企业内部管理和解除的规则都应当不同于大企业。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上述差异,明显的表现在解雇问题上。根据德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中小企业的离职率相对比较高。“在5人以下小企业,劳动者的离职率高达19%,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离职率开始下降。在500人以上企业,离职率只有9%,不到小企业的一半。”(Junker,2004)这是因为对大企业来说,可以通过内部调整实现内部灵活性,减少通过合同解除实现的外部灵活性,而对于小企业来说,只能通过人员增减来解决生产波动问题。小企业中劳动者主动离职比大企业更加普遍,因为小企业中劳动者上升空间比较小,容易导致劳动者主动离职。上述原因一方面说明了对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进行特别处理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中小企业劳动关系进行特别处理的规则指向和限度。
二、按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分类处理的法律技术——临界值条款
(一)企业规模在法律条文上的体现——临界值
尽管按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分类处理在观念上是为了适应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协调的特殊需要,但“德国劳动法和德国社会法都没有使用中小企业这个概念,相关规则(的适用范围)更多都是通过临界值来限定的。” (WD6-3000-090/16)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笼统或统一的中小企业概念,而只存在具体立法中通过临界值确定的特定规则适用的企业范围。在相关劳动立法中,这种根据企业规模确定法律适用范围,进而确定不同劳动者保护水平的规则就是所谓的临界值条款(Schwellenwert),它是指“规定特定个别法律效果或者较大的规则群的适用取决于符合确定涉及工厂或企业规模的数字的条款。它可以是单个的临界值(例如《非全日制和有期限雇佣合同法》第8条第7款),也可以是工厂组织法或参与决定法中广为使用的所谓的临界值列表。” (Junker, 2004)
(二)临界值的确定
1.确定临界值的指标
在确定临界值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以什么为参数或为指标。对此,一般的中小企业界定中都采取多元指标。2003年欧盟委员会确立了中小企业的新定义,根据该定义,确定企业规模时要考虑企业的雇员数、销售额以及资产负债表合计等,根据该新界定,中小企业的认定标准如表 1(http://www.ifm-bonn.org/definitionen/kmudefinition-der-eu-kommission/):
在德国具有较大影响的波恩中产研究所(IFM)基本上也按照上述标准对中小企业进行界定,只是仅考虑销售额,不考虑资产负债表这个指标。(http://www.ifmbonn.org/definitionen/kmu-definition-des-ifm-bonn/)
在劳动法领域如何来确定临界值,有学者认为应采取多元的标准。例如拉姆(Ramm)教授认为,“对劳动法的规则来说,仅仅以劳动者人数为指标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必须考虑经济上的给付能力这个指标。”(Junker, 2004)但立法和理论的主流意见却仅仅只考虑劳动者人数这个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上述欧盟的新定义允许在确定企业规模类型时只要不涉及竞争法就可以只考虑唯一的指标——例如员工人数,另一方面,德国理论和实践界认为“使用员工数量之外的其他指标或者该指标与员工数量一起,都不能实现调整的精准性,反而会影响法律的安定性。”(Junker, 2004) 。

表1 欧盟委员会中小企业认定标准
2.临界值的计算单位
在确定临界值时,第二个需要考虑的是计算单位,即以什么为计算劳动者人数的单位?在德国劳动法的框架下,至少存在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工厂(Betrieb)、企业(Unternehmen)和雇主(Arbeitsgeber)。工厂和企业是必须严格区分的概念。在内涵上,“工厂可理解为企业主(Unternehmer)通过它运用物质和非物质手段,投入人的劳动力直接追求生产技术目的推进的组织体。与此相反,企业则是企业主追求较远经济或非经济目的的组织体。工厂可服务于一个企业,这样工厂和企业所说明的就是同一经营组织体的不同侧面;但是一个企业也可以由多个在组织上互相紧密结合的工厂组成。” (瓦尔特曼、沈建峰,2014)与工厂和企业不同,“雇主是劳动关系中可以要求另一方也即劳动者为给付,并有义务向该方支付约定报酬的合同当事人。” (瓦尔特曼、沈建峰,2014)雇主和企业的关系是,雇主可以是法人、人合公司、民事合伙以及自然人,“一个自然人可以有多个企业,而法人按照权利承担者统一的原则只能有一个企业。” (Junker, 2004)对法人来说,企业、法人、雇主是一致的,但对自然人来说却不是这样。
在传统德国劳动法中,一般认为劳动法是要保护生产组织体中的劳动者,劳动法并不干预雇主的经营决策权,所以劳动法的核心概念是“工厂”,“许多非常有意义的规则都以工厂概念为连接点”。(Preis, 2009)劳动法上的临界值也往往以工厂为计算单位。但在现代法中,企业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立法和裁判实践中,也出现用企业概念替代工厂的概念的现象。(Junker, 2004)在临界值的计算问题上,有学者提出有的临界值是为了解决雇主的经济负担,所以应当以追求经济目的的企业为单位。在上述思路的影响下,在立法实践中临界值的计算单位上也出现工厂、企业或者雇主三个概念并存的局面。工厂是最小的计算单位,企业和雇主是基本统一的单位,从逻辑上说,相关法条以工厂为单位计算时,该法条的适用范围最大。
3.特殊劳动者群体的计算规则
临界值计算时的第三个特殊问题是一些特殊劳动者群体的临界值计算。主要涉及到非全日用工劳动者、学徒、孕妇、派遣工等在计算临界值时是否要考虑在内。这些劳动者群体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特殊状态,在计算劳动者时完全将他们作为正常劳动者看待,一方面对雇主来说并不合理;另一方面,会对雇主雇佣这些劳动者产生障碍。但是由于不同的劳动法规则群的规范目的不一,也很难统一规定如何对待这些特殊劳动者。以非全日用工为例,“在个别劳动法,按照非全日制劳动者工作时间的比例规定临界值当今依然不是一般情况,有些条文是按人头算的;而在集体劳动法中,不论非全日制劳动者工作时间有多短,一直以来都是按人头计算其数量的。” (Junker, 2004)在具体规则中,特殊人群是否计算入临界值,立法者的考虑包括特定人群的就业促进、企业的负担等各种因素。
4.确定临界值的方法
在以人数为指标确定劳动法规则的临界值时,最核心的问题是明确临界值数值如何确定。这首先是计算和评估的结果。以《德国解雇保护法》上临界值设置为例,解雇保护法适用工厂范围的临界值一再调整,每一次调整往往都会有一系列数据支撑。1996年和2000年,有草案两次希望将该临界值从5提到10人,其理由都在于“小企业往往涉及到设立阶段的企业,应鼓励它多雇佣,而不应受到事实上或心理上妨碍雇佣的条款的限制。在新设立企业,平均的雇员数是5.3人,在设立后的7年,平均的雇员数则增长到11.8人,基于这个理由似乎应将临界值提升到10人。”(BT-Drucks.,14/4103; BT-Drucks.,13/4612.)其次,数字偏好。学者们认为,“5这个数字具有形成体系的功能:因为一只手有5个指头,5这个数字一直都是对整个制度来说计算体系的基础;它是5体制的基础,在该基础上建立起了最重要的比较高的数值:10、20、50、100、500、1000和2000.”。(Junker, 2003)再次,利益博弈。可能影响临界值形成的第三个因素是相关利益群体代言人的利益博弈。例如1951年的《德国解雇保护法》,一开始两审草案中关于解雇保护法适用企业规模的临界值都是3人,但是“经济委员会希望将临界值设定为10个劳动者,(劳动者的)全国组织和政府希望设置为3名劳动者,最终以妥协的方式设置为了5人。” (Junker, 2004)。
在上述因素中,计算和估算是理性的方式,其他两个因素都具有一定的非理性色彩。这其实是由市场本身决定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因素错综复杂,各种原因和诉求相互影响,很难通过数据或者计算来进行精确分析。即使是上述计算和评估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初略的分析,根本没法回答为何是10人而不是6人?5人和10人分别对经济的影响如何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数值确定是一种试错、惯性、评估、利益对抗等因素综合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从96年到2000年,《解雇保护法》适用范围的临界值就先后从5到10(1996),又到5(1998),2000年又有立法草案要求提到10,2003年该数值做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调整后调整为了10人。
(三)德国劳动法中主要的临界值条款
劳动法中的临界值并不是一揽子体系设计的结果,而是在一个个立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方面,由于影响临界值形成的因素复杂,另一方面,也是精确调整,精细化立法的体现,根据德国学者的统计,在德国劳动法中有160个左右这样的临界值。(Lena Koller, Claus Schnabel,2007; Junker,2004)但也有学者不无批评的指出,它是“一片疯长的热带雨林” (Junker, 2004),这样大量、并且随着社会政策的变化,又在不断调整——上述160个数值中,“大约有一半在1993年后都进行过至少1次调整”——的临界值带来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管理成本等的增加。在此背景下,也不断有学者提出对其进行梳理,使它更加透明和简化。根据学者们的统计,最重要的临界值及其适用的范围等问题如表2所示(Lena Koller,Claus Schnabel,2007; Junker,2004; Junker,2003)。

表2 劳动法中的主要临界值及其适用规则
三、临界值的具体运用之一:解雇保护法
决定《解雇保护法》适用范围的临界值条款是德国劳动法中最活跃,变动最频繁的临界值条款之一。临界值条款的社会政策功能及其调整技术在此可见一斑。
1.历史沿革
在德国、奥地利等国,解雇保护制度首先出现在《工厂组织法》中,解雇保护中的临界值规则也发端于此。德国1920年的《工厂组织法》第84条规定劳动者在解雇提出后5天内可以向劳工或者雇员委员会提出请求,由于建立劳工或雇员委员会的前提是工厂中有20个劳动者,这就等于只有20个以上劳动者的工厂才存在解雇保护的问题。1951年《解雇保护法(草案)》第21条第1款第2句规定,“第一节(一般解雇保护)的内容不适用于一般情况下雇佣3名或更少劳动者的工厂或办公室,计算上述人数时不包括学徒。”在立法过程中,曾有人提出将该临界值提高到10人,反对意见则认为,“将人数提高到10人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难以容忍的。联合经济区(联邦德国尚未建立——作者注)的一项调查表明,受雇于雇员少于10人的工厂的劳动者或者雇员有3955000人,也就说36%的劳动者。受雇于少于5人的工厂的劳动者或雇员2307000人。您可以看到接受第二读动议后,将有多大份额的劳动者被排除在法律适用外。”(BT,159.Sitzung,10.Juni,1951)最终在一番妥协后该数值被确定为了5人。该临界值在1969年,1985年的《解雇保护法》修改中都没有调整。但1996年该数值被提高到了10人。其立法理由是:“目前的临界值特别是在手工业工厂中导致了雇佣障碍,而手工业工厂构成了小企业的大部分。尽管平均雇佣数在手工业工厂中从《解雇保护法》1951年生效时的3.5人,提高到了1995年11人。该发展趋势却是因相对较少的、建筑清洁和食品生产领域的大企业所引起。大部分的手工业工厂雇佣人数目前还是少于5人。将临界值增加到10人,依然保留了小工厂的特点,在小工厂中,工厂主和他的员工之间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为了工厂和平和工厂功能发挥应使必要的解除容易些。”(BTDrucks., 13/4612)此次修改之后,德国解雇保护法陷入了临界值之争,在1998年先后有不同党派提出修改临界值的法律议案,FDP党团和一些议员提出的法律草案认为应将该临界值提高到20人,其立法理由是“根据德国工商业大会今年(指1998年——作者注)8月公布的一项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推动力——劳动力市场上重要法律变动的就业效果’的研究,过去解雇保护法的修改产生了积极的就业效果。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废除10人以下工厂的法定解雇保护极大促进了这些企业雇佣新人的积极性。但也能够确定的是,将人员范围置于到10人以外,依然导致了明显的担心。一项实证研究证明,将临界值提到20人将产生就业促进的效果。”(BT-Drucks.,14/44)但SPD党团和90绿党联盟提出的草案则要求将10人临界值再次降低到5人,其理由是“1996年的《雇佣保护法》变动影响了社会和平和社会伙伴关系,而此二者是(经济增长)动力和成绩的框架条件。另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目的也没到达到。……。将临界值增加到10人导致两百万劳动者失去了一般解雇保护,相对于由此导致的就业减少,创造的新岗位根本不值一提。” (BT-Drucks.,14/45)并且该草案用一系列数据论证了上述结论。最后,SPD党团和90绿党联盟提出的方案得到接受,1998年上述临界值再次被降至5人。2000年,又有议员提出将上述临界值增加到10人的法律草案,理由和1998年要求上调的理由基本相同(BT-Drucks.,14/4103)。但是该方案并没有被通过。2003年联邦政府推出《劳动力市场改革法(草案)》,对解雇保护法中一般解雇适用的临界值进行修改,其目标在于“为了促进小企业中的就业,将解雇保护法适用的临界值进行灵活化设计”,(BTDrucks.,15/1509)在此过程中,不同党派先后提出了不同修改的建议,经过一系列咨询、讨论之后,最后通过的法律将临界值提到了10人,但对于2003年1月1日前已经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则依然适用5人的标准。
2.1996年以来导致《解雇保护法》中一般解雇适用范围临界值调整的根本原因
如上所述,临界值制度的一般功能在于服务于小企业中劳动关系的特殊状况。德国《解雇保护法》中一般解雇保护制度临界值的基本功能也是如此。5人的临界值在德国适用了45年(1951-1996),但是96年以后却进入频繁的调整期。从5人到10人,又到5人,再次回到10人,其间还不断出现将其提到20人的呼声。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工厂规模的扩大,直至2002年,5人以下的小工厂为1450000家,占工厂总数的68.4%。(Junker, 2004)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一,在中小工厂大量存在的背景下,劳工政策从对大企业关注转移到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关于劳动世界的政策问题的讨论,在70年代依然专注于大或者超大的企业,……,但是从80年代开始,对中小企业的兴趣日益增加。” (Junker, 2004)其二,解决失业问题。一般认为解雇保护制度会阻碍雇主雇佣劳动者的冲动,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说,企业内部调岗等可能性小,企业用工的内部灵活性差,在解雇保护比较严格的情况下,外部灵活性将会不足,企业会对扩大雇佣心存疑虑,中小企业宁可安排加班,而不愿意招用新员工。进入上世纪90年代,德国备受失业问题困扰,1996年,“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达到4百万,这是难以接受的。” (BT-Drucks.,13/4612)在此背景下,减小中小企业中的解雇保护,激发中小企业的雇佣冲动,对解决失业问题具有重要价值。1996年以后《解雇保护法》一般解雇保护适用临界值调整的首要目标之一就在于扩大就业。1996年将临界值从5调到10人时,立法理由提出,“如果目前每一个5到9人的工厂都愿意再雇佣一个人,则可能产生50万的新就业岗位。” (BT-Drucks.,13/4612)1998年将临界值从10降到5时,立法理由则是这种放松对减少失业的作用微乎其微。(BT-Drucks.,14/45)
3.现行临界值规则的基本内容
2003年《解雇保护法》修改后,第23条的临界值条款再未变动过。现行《解雇保护法》一般解雇保护规则适用范围的临界值条款主要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其一,涉及解雇保护的小工厂临界值条款主要适用于一般解雇保护,也就是《解雇保护法》第1节的内容,《解雇保护法》其他部分的内容以及《民法典》第138条权利滥用、第242条违反善良风俗等条款对解雇权行使的限制不受影响,另外,《一般平等保护法》关于解雇权的限制也不受影响。其二,计算临界值的单位是工厂(Betrieb)或者公法上的管理处(Verwaltungen desRechts)。在实践中,虽然联邦宪法法院虽然认为“对该小工厂条款做符合宪法的解释,也就是以企业为计算单位”,(BVerfG 27.1.1998,BVerfGE 97,169.)但联邦劳动法院在个案中并未完全遵循该立场,依然以工厂为计算单位。(Stahlhack,Preis,Vossen, 2015)其三,临界值计算的时间节点是“通常情况下”,也就是不是解除的时点,而是“正常情况下雇员的数量,在确定正常情况下雇员的数量时,要顾及过去和将来的人员需求。” (Stahlhack, Preis, Vossen, 2015)其四,临界值的数值原则上为10人,但是对2003年12月31日前入职的老员工,该工厂在2004年1月1日开始已雇佣超过5人未达10人的,其临界值依然按5人计算,可以适用《解雇保护法》一般解雇保护的规则。其五,对非全日制用工按照用工时间按比例进行折算。对每周通常工作时间不超过20小时的非全日制劳动者按0.5人算,对周工时不超过30小时的非全日制劳动者按0.75人算。此前,曾还有一个折算比例,周工时不少过10小时的,按0.25人折算,但是在1998年的法律修改中,该折算规则被删除了。
四、临界值的具体运用之二:《工厂组织法》
德国有发达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参与决定在劳动法中服务于实现社会政策上的基本关切:支配权限和领导权限应在相关人的参与下行使。” (瓦尔特曼、沈建峰,2014)劳动者参与管理发生在企业(Unternehmen)层面和工厂(Betrieb)层面。比较传统,而且最重要的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发生在工厂层面并由《工厂组织法》调整。
(一)决定参与管理制度临界值的因素
从工厂层面参与管理的制度定位出发,工厂规模在根本上决定了何时能够参与管理,参与管理的模式和内容。这是因为,其一,工厂委员会参与管理的目的原则上并不是限制和干预雇主的经营决策权,而仅是限制雇主用工自主权的滥用。而建立劳动关系后的用工自主权原则上只在大企业存在,并且企业规模越大,雇主方力量越强大,企业内部人员流动的恣意空间就越大,通过参与管理对其权力进行限制的需求就越大。这就导致企业内部参与管理的权限和工厂规模有比例关系。其二,工厂规模越大,参与决定的事务就越复杂,参与决定机构就越需要庞大和复杂。其三,建立参与决定的机构和制度都需要花成本,按照德国《工厂组织法》的规定,工厂委员会的经费由雇主承担,参与管理机构的成本必须和企业规模匹配,同时小企业根本无法承担参与管理机构运营的成本,参与管理机构的规模等必然与企业规模具有比例关系。其四,企业或工厂规模越大,对社会经济影响就越大,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相关经济信息等的公开就变得必要,参与管理的必要性也就随企业规模扩大而提到了。在上述种种因素影响下,德国工厂层面参与决定的临界值也表现出非常多样化和复杂的样态。
(二)设立工厂委员会的临界值
与《解雇保护法》一般解雇保护适用范围临界值一直争论不休,调整不断不同的是,设立工厂委员会的临界值一直未变,1949年《工厂组织法草案》第8条就规定“一般情况下雇佣固定的有选举权劳动者最少5人的工厂,如果上述5人中有三人有被选举权则可以设立工厂委员会。”(BT,Drucks.,01/3585)至于为何是5人,立法理由指出,“应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工厂最小规模的问题是一个经长期且深入讨论的问题。手工业和农业界的人认为应该是10名有选举权长期劳动者,但是委员会的多数意见认为在所有一般雇佣超过5名具有选举权的劳动者,其中有3名具有被选举权时,就应成立工厂委员会。” (BT,Drucks.,01/3585)总体上说,5人这个数量具有一定的专断的色彩,而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直到今天,《工厂组织法》中可设立工厂委员会的工厂人数也是5人。在此过程中,唯一的变化是1972年的法律改革为了规则的统一,将农业和森林企业10名雇员以上可以设立工厂委员会的规则给删除了。另外,德国工会联合会在1998年曾建议将该数值降为3人,(Junker, 2004),基民盟党团曾建议将该数值增加为20人(BT-Drucks,14/5753),自由民主党(FDP)党团曾建议将其增加为50人(BT-Drucks,14/5754),但这些都没有为立法所接受。该数值相对比较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德国法中,工厂委员会的设置并不具有强制性,由劳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同时在小工厂中,劳动者可以和雇主直接交流和协商,劳动者甚至不愿意在自己和雇主之间插入一个利益代言者。从实际情况看,200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雇员人数5-20人的工厂,只有4%建立了工厂委员会,在21-100人的工厂,只有28%建立了工厂委员会。” (BT-Drucks.,14/5741)而另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5-49人的工厂中,只有7%建立了工厂委员会。(Junker, 2004)在中小工厂对工厂委员会的需求不旺盛的背景下,提高还是降低法定临界值,并不是一个引起很大利益冲突的问题。工厂委员会本质上是一种适合于大企业中劳资双方合作和沟通的机制。
1.工厂委员会构成的临界值
工厂委员会构成的临界值从1920年的《工厂委员会法》开始采取的就是临界值列表的方式,1952年《工厂组织法》继续采纳了该方式,在此后40年间该临界值列表的数值基本没有变化。直到2001年《工厂组织法》改革中,该列表中100人以上的工厂里,工厂委员会构成人数比例被做了进一步下调。其立法理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工厂委员会的职责大大的增加。这种职责的扩张特别源于新技术引入和使用所引发的复杂问题以及现代生产和劳动方式、培训、就业安全以及劳动和环境保护。通过降低劳动者的临界值应使工厂委员会有能力更好的完成其职责。” (BTDrucks,14/5741)此后10多年间该数值未变,如表3所示。
2.工厂委员会权限的临界值
《工厂组织法》上的第三类临界值主要涉及根据劳动者人数的多少设置不同特殊的机构或者赋予相关机构特殊的权利。比较重要的临界值及其规则如下(Junker, 2003;Wolfgang Hromadka,Frank Maschmann,2010):如表4所示。
3.工厂委员会临界值计算的几个特殊规则
(1)派遣工的计算
根据2001年《工厂组织法》修改前原第7条的规定以及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意见,只有与工厂的雇主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才具有组成工厂委员会时的选举权,并且才可以计入计算雇佣人数临界值时的人员范围。但2001年《工厂组织法》改革过程中增加了第7条第2句,根据该句,在工厂中用工超过3个月的派遣工也享有组成工厂委员会时的选举权。其立法理由在于,在现代工厂中,多样化的用工方式导致工厂中的劳动者不一定与雇主具有劳动关系,但这些劳动者也处于用工单位的指示权之下,所以有保护的必要性。(BT-Drucks,14/5741)此外,让这些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享有选举权,也可以对雇主使用他人雇员产生相对的作用力。(BT-Drucks,14/5741)派遣工享有选举权是否就意味着在计算临界值时应将其计算在内?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应只计算具有劳动关系的人,但是2013年联邦劳动法院放弃了该长期以来它也采纳的观点,认为“在临界案件中应更多以规范的目的为导向。从赋予小企业特权的目的出发,派遣工也应当被计入《工厂组织法》第1条第1款第1句(计算临界值的规则——作者注)的框架内。” (瓦尔特曼、沈建峰,2014; Fitting 2014)。
(2)非全日制劳动者的计算
在其他法律中,非全日劳动者在计算临界值时往往被特
殊处理,但德国的主流理论和实践认为,“在工厂组织法中,非全日劳动者也是工厂中的劳动者。……,各个非全日劳动的时间长度和状态以及是否存在社会保险义务(对此)都不重要。”(Fitting 2014; Preis, 2010)在计算临界值人数时,非全日制劳动者被按人头计算,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非全日制劳动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针对非全日制劳动者的人事措施,工厂委员会也有参与管理权。在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对非全日制劳动者也应像在解雇保护法中一样,按比例计算。另外,根据欧洲委员会2003年5月6日《关于小微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界定的建议》第5条第2句也规定,在计算劳动者人数时,“非全年工作或者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以及季节工按照其在每年的工作时间份额计算。”在工厂组织法上,将非全日制用工和全日制用工一样看待,对使用非全日制劳动者的企业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同时也会导致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不愿使用非全日制劳动者。但如下原因导致主流理论和实践采取了将非全日制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同样看待的立场:其一,禁止非全日制用工歧视的压力。根据欧盟相关指令以及《非全日制以及有期限劳动合同法》第4条第1款,非全日制劳动者不得因非全日制劳动而享受比具有可比性的全日制劳动者糟糕的待遇,除非该区别对待可以通过实质上的理由被合理化。在参与管理的问题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将非全日制劳动者排除在外或者作出不同于全日制劳动者的处理。其二,禁止妇女歧视的压力,“非全日制劳动一如既往的主要由妇女来承担。在2012年,妇女中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占到了45%,男性只占到了9%。”(瓦尔特曼、沈建峰,2014; Waltermann,2010)在此现状下,将非全日用工排除在参与管理的制度外,或者做不利处理,会发生对女性的间接歧视。而2001年的《工厂组织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女性在工厂组织等中的地位。(BT-Drucks.14/5741)其三,就业市场的新形势。在德国,由于各种原因,非全日雇佣经历了极大繁荣,其中1991年,非全日制劳动者占到全体劳动者的14.1%;2012年,该数值达到25.7%。(瓦尔特曼、沈建峰,2014)将非全日用工排除在参与管理的制度外,或者做不利处理将会使大量劳动者参与管理的可能性受到损害,同时参与管理制度本身的存在也会因此受到挑战。

表3 工厂委员会组成的临界值

表4 工厂委员会权限的临界值
(3)家庭劳动者
严格意义上,家庭劳动者并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瓦尔特曼、沈建峰,2014)但在德国却存在着将其纳入《工厂组织法》适用范围的传统。从1920年的《工厂委员会法》第11条将一定条件下的家庭经营者视为劳动者,当时的学者认为,“家庭劳动者在经济上几乎与劳工处于同等地位,立法通过大量特别规定将其作为劳动者对待。”(Walter Kaskel,1925)在此基础上,该法第3规定使用20人以上家庭经营者的企业应为其建立专门的工厂委员会。1952年的《工厂组织法》第5条和1972年《工厂组织法》第6条第1款则直接将家庭劳动者也纳入了该法的劳动者范畴,规定“主要为本工厂工作的家庭劳动者也视为本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此后的法律修改未对该规定作出实质性调整。
五、代结论:德国制度对中国劳动法律修改的启示
在我国劳动法律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除了具体技术方面的做法外,德国根据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进行分类处理的思路在如下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1.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制度应当进行精细化立法
劳动关系协调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在国家通过立法对这种利益分配进行管制和干预的过程中,应当进行精细化立法,以满足在多样化的企业和劳动者形态之间进行合理利益分配的需要。对劳动关系进行分类处理实际上也是一个基本国际趋势。“许多国家根据企业规模进行区分,以减少小企业和新企业的负担。许多国家都存在家庭劳动、培训关系以及商事代表的特殊规则。法国法区分了30多种劳动合同。英国则区分employee和worker,employee享有解雇保护、补偿金和报酬继续支付等;而Worker则只享有部分适用于employee的规则。”(Rebhahn, 2009)
2.并不存在一刀切的适用于中小企业的劳动法规则
按企业规模对劳动关系进行分类处理的过程中,应承认并不存在一刀切的大企业、中小企业,如果这样那又是一种新形式的僵化;而只存在根据特定规则或者规则群的目的进行政策考虑和利益考量之后确定的规则适用对象。也就是仅存在针对特定规则的规范意义上的中小企业。从德国的实践来看,在确定各个规则适用的中小企业临界值,其主要标准是劳动者人数,计算单位是生产单位。这主要是出于规则简洁明确以及历史传统等需要。
3.影响相关规则临界值选择的有理性计算、传统、相互妥协等各种因素
在决定相关规则的临界值时,首先的是理性计算这一因素。所有的临界值设置都首先建立在调查、统计和计算的技术上。但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影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利益分配因素的多元性,决定了临界值计算不可能完全是理性的结果,而是受到传统、就业形势、力量对抗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防止非理性因素的主导,在此过程中必须保证立法过程的民主性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要在充分讨论、妥协的基础上进行规则设计。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和试错也可能再所难免。从我国的情况看,在立法技术上,也可以考虑先授权特定地区进行一定的试点和尝试。
4.对中小企业进行特殊处理的目的是回应其劳动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而不是降低劳动者保护
对中小企业进行特殊处理的根本目的,是要根据其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例如劳动关系内部灵活性较弱、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双方人身信赖色彩浓、劳资力量悬殊小等,对其进行特殊调整,实现符合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状况的劳资利益均衡,而不是要降低劳动者保护,涉及劳动者尊严、生命、健康等的生产安全、最低工资等基本事项,即使在中小企业中也不能减损。
1. 谢增毅:《我国劳动关系法律调整模式的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123-143页。
2. 瓦尔特曼,沈建峰译:《德国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3.Lena Koller und Claus Schnabel, Schwellenwerte im Arbeitsrecht:Höhere Transparenz und Effizienz durch Vereinheitlichung, in:Perspektiv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2007,8(3):S242-255.
4. Junker, Arbeitsrecht zwischen Markt und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Herausfoerdungen, Verlag C.H.Beck, 2004.
5.Vereinfachungen und Ausnahmerregelungen im deutschen Arbeits und Sozialrecht für kleine und mittlere Unternehemen,WD6-3000-090/16.
6.BT-Drucks., 13/4612
7. http://www.ifm-bonn.org/definitionen/kmu-definition-der-eu-kommission/.
8.http://www.ifm-bonn.org/definitionen/kmu-definition-des-ifm-bonn/
9.Preis,Individualarbeitsrecht,3.Au fl age, Verlag Dr. Otto Schmidt,2009.
10. Drucks., 14/4103
11. Junker, Schwellenwerte in arbeitsrechtlichen Gesetzen, in: NZA,2003, S1057-1078.
12. BT,159.Sitzung,10.Juni,1951.
13. BT-Drucks., 13/4612.
14.BT-Drucks.,14/44.
15.BT-Drucks.,14/45.
16. BT-Drucks., 15/1509
17. BT-Drucks., 13/4612.
18. BVerfG 27.1.1998,BVerfGE 97,169.
19.Stahlhack/Preis/ Vossen: Kündigung und Kündigungsschutz im Arbeitsverhältnis, C.H.Beck. 2015.
20. BT,Drucks.,01/3585,S22.
21. BT-Drucks,,14/5753.
22.BT-Drucks,,14/5754.
23.BT-Drucks.,14/5741.
24.Fitting,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 Verlag Franz Vahlen, 2014,S78.
25.Preis, Arbeitsrecht,Kollektivarbeitsrecht, 2.Auflag, Verlag Dr. Otto Schmidt,2009.
26. Walter Kaskel,Arbeitsrecht,Springe-Verlag,1925.
27.Rebhahn: Der Arbeitnehmerbegriff in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 RdA 2009,S.129-192.
28. Wolfgang Hromadka, Frank Maschmann, Arbeitsrecht, Band 2,Kollektivarbeitsrecht, Arbeitsstreitigkeiten, Springer,2010.
■ 责编 / 孟泉 Tel: 010-88383907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Classific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Enterprise Size in German Law
Shen Jianfeng
(Law School, China Institute of Labour Rel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o adapt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labor relation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German labor law has developed many special regulations. Those special regulations use the legislative technique of critical value. The critical value of many regulations is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workers in the factory. However, there is some situation,in which company or employers are the unit of accoun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ritical value is a process of rational calculation, digital preference and interest game. There are more than 160 critical values in the German labor law. The critical value of dismissal protection law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legislative techniques. The critical value of the dismissal protection law has gone through 5 to 10 people. The critical value of the Factory organization law is very complex, but relatively stable. The setting of the critical value reflects the scal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size and the intensity of participation in management. We can learn from Germany’s legislative techniques and methods.
Labour Relations; Solution by Types; Dismissal; Participation Management
沈建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shenjianfengl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