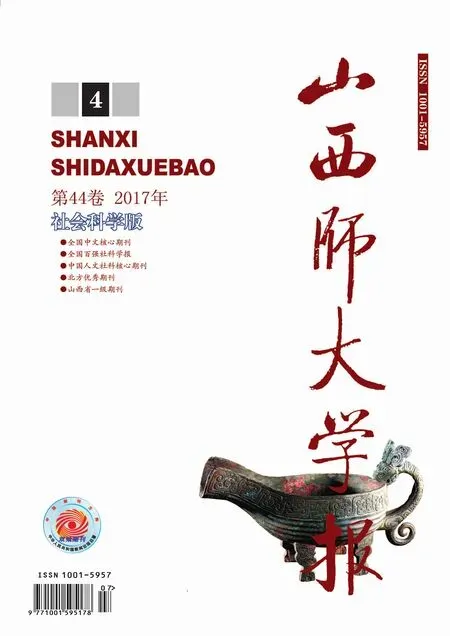宋代新《春秋》学的文化诠释
孙旭红,王 艺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如所周知,经学至西汉甫立,尽管今文经学使得儒学思想的经世功能得以发挥,但东汉以后古文经学的持久影响以及魏晋以来释道二教的盛行,经学研究重章句训诂之学,经典内涵隐而不彰,进而使得儒家经典维系人心、挽救世风的功能不断衰退。宋儒接续中唐啖助学派开启的“新《春秋》学”,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儒学,并形成了新的儒学形态——“宋学”。即以《春秋》学为例,他们于经典的阐发中所建构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儒学),更包含着一种对终极之“道”的信仰(儒道),一种如何处理政治实践的技术方法(儒术)。[1]21
一、知识形态的转型:章句训诂之学至义理之学
自西汉经学成为学者的“禄利之路”不过百余年,学界就出现了“一经说至百万余言”的繁琐现象。而经学内部又拘囿于家法、师法,学者仅据古注以释经,不敢稍有发挥。唐初虽然完成了经义的统一工作,但形成了所谓的“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说”[2]94。这种学风至中唐啖助学派得以扭转,啖助、赵匡、陆淳对先前《春秋》学之“固陋”深为不满,主张会通三传、直探经旨。因此,其开启的“新《春秋》学”研究引发了疑经变古的经学思潮,具体表现便是对以往经学权威的怀疑以及解经方法的反省。
但是,疑经变古思潮在北宋庆历前依然影响甚微,据《郡斋读书志》卷四《七经小传》条载:“元祐史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3]143但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由经及传已经不拘成法,议经、疑经已蔚为当时潮流。这其中孙复、刘敞等人首开风气,如孙复论曰:“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既往,六经之旨郁而不章也久矣。”[4]寄范天章书二刘敞自撰的《七经小传》:“稍尚新奇矣”,并始开宋儒“改经之例”[5]215。难怪清儒论曰:“北宋以来,出新义解《春秋》者,自孙复与敞始。”[5]215孙复、刘敞之后,王安石、苏辙、程颐等人接其绪而发扬之,且愈益昭著。尤其是王安石之《三经义》刊行后,士人更“视汉儒之学如土埂”[6]1094。其时治经学者,开始普遍怀疑经义的合理性以及先儒所公认的经师著作,对经文的脱简、错简、讹字等进行了全面的检视。这股疑经变古思潮改变了柔靡浮夸的文风,松绑了传统经学思维对人们的桎梏,宋儒开始逐渐摆脱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吸收佛、道两教思想的重要内容,从经书的要旨、义理来理解经典涵义,并逐步建构了经学的新内涵。另一方面则扬弃旧有解经方法,弃饾饤训诂而以阐释义理代之,直接从经学本身来创发义理之学,一弃一取,成就了宋代的新经学。
新经学首先表现为宋儒对《春秋》三传的批评。两宋间将三传分开来独立研究的屈指可数,宋儒接续啖助学派余绪,在疑经的基础上疑传。如孙觉云:“作传者即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释者又妄为之说。”[7]自序如此谬误相传才造成《春秋》经旨愈加晦暗不明。欧阳修认为,一经之指,三传之解却各不相同,是非正误难免引发学者的疑惑,因此,他坚持疑传从经的基本准则:“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8]131—132刘敞则认为,三传“以其善恶相反,其褒贬相戾”[9]序,因此,其解经权衡三家传注,不信传有而经无之记载,学者只有“信《春秋》,则外物不能惑矣”。[9]卷一王应麟则指出“三传皆有得于《经》而有失焉”[6]784—785,这个观点应当说是宋儒对待三传的共识,因此他们对三传优劣各有毁誉,但亦有极端如赵鹏飞者,甚至认为三传非解经之传。不但如此,连三传注疏名家也遭到了宋儒的怀疑和批判。董仲舒、何休、杜预、范宁、孔颖达以至于中唐啖助师徒都未能幸免。孙复在景祐二年(1035年)给范仲淹的一封长信中对六经之旨淆乱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孔子之后,汉魏以下,“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而学者莫得其门而入”。[4]寄范天章书二显然,先人眼中经学的权威注解,只能使得六经之旨益乱而使得后之学者无所适从。王晳则认为孔子之后的弟子皆未得圣人之意,即便“以贾谊之才,仲舒之文,向、歆之学,厥犹溺于师说,不能会通,况于余哉”[10]卷五。于是宋儒讲经尽脱汉、唐传疏,盖由怀疑经义,以六经所载失实,继而删改经文、辨别伪经,充分显现了宋人敢于变古,勤于辨伪的怀疑精神。
其次是对《春秋》经解方法的更新。对于唐大历年间兴起的啖助学派的治经之法,《新唐书》“儒学传”赞曰:“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啖助、赵匡、陆淳正是在“自用名学”观念的指导下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在宋儒看来,“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11]3640因此,“圣人之意可求也,求在义而已矣”[9]卷二。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宋人治《春秋》“各自为传,或不取传注,专以经解经;或以传为案,以经为断;或以传有乖谬,则弃而信经。”[11]序如欧阳修在孙复墓志铭中盛赞其“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刘敞《春秋》学以义理阐发而著称,如《春秋意林》,四库馆臣就认为“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得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6]338。这种“自用名学”的解经风尚以“直究本经”自许,最终瓦解了章句笺注的繁琐拘谨,其大胆作风远超啖助学派及其他同时期的《春秋》学者。
两宋间的疑经惑传思潮,使得宋儒不但疑经、疑传,进而改经、舍传,使得儒家经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宋儒怀疑的动机,是在彻底否定汉儒对经传经解的贡献。力图使圣人之道的传承成为义不容辞、时不我待的时代担当。换言之,他们只是对“湮没”已久的经义的抉发,而不是对经典本身价值的质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义理之学逐步取代汉唐训诂之学。朱熹曾提及宋初诸儒对于义理之学形成的开创之功:“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此先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12]2089此等评价公允与否暂置勿论,但朱子充分肯定孙复、刘敞、欧阳修在超越先前注疏并自出议论以阐发“理义大本”中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
二、“道”的寻绎:经典诠释与道统传承
《春秋》学在唐宋之际重新崛起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经典义理的阐发重建儒家之道的人文信仰。这一重建活动可上溯至唐代中叶韩愈所撰《原道》一文所引发的儒学复兴运动,其后的学者普遍以重申儒家信仰的“原道”为治经旨归。啖助学派的新《春秋》学亦承此风而始,开始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进行反思,并力求从经典中寻求巩固与绵延皇权制度的良方。新《春秋》学的旨归便是“拨乱反正,归诸王道”,这一思想在宋代影响深远。
理学家程颢便盛赞啖助门人陆淳之学“旨义之深,莫可历数。要其归,以圣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见而立异,故其所造也远,而所得也深”。[13]467并肯定了其延续“圣门之学”的功绩。可见,啖助学派开启的新《春秋》学“攘异端,开正途”,彰显出圣人拨乱救世的意旨。开宋学风气的孙复之《春秋》学就是本于陆淳之学,并增新意若干。因此,孙复《春秋》学的主旨仍然是继续阐发圣人之道。他虽因四举进士不第而隐居于泰山之阳读书讲学,但其隐逸与一般避乱世而隐者不同,其门生石介曾如此形容:“孙明复先生,学周孔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孔之道非独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彼所谓隐者,有匹夫之志,守硁硁之节之所为也,圣人所不为也……若贤人如先生者,遭尧舜之盛,未得进用,姑盘桓山谷,以待时也,非隐者也。”[14]236换言之,孙复以道统承继为志业,沉潜于经术之际,胸中所怀仍是天下国家之事。如其论《春秋》曰:“孔子作《春秋》,专其笔削,损之益之,以成其大中之法。”[4]卷二可见,孙复眼中的“王法”是天子尸之,非诸侯可得专的“礼乐征伐”之权。因此,“大中之法”即为圣人所寓《春秋》之主旨,孔子正是据此以褒贬笔削成一代巨典。欧阳修因此盛赞孙复之学“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朱熹则称曰:“近时言《春秋》,皆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治道,凛凛然可畏,终得圣人意思。”[12]2174
宋代理学家常以“道统”传承者自居,认为周孔之学不传才使得人欲肆而天理灭。因此,程颐曾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圣人性之为圣人,贤者由之为贤者,尧舜用之为尧舜,仲尼述之为仲尼。其为道也至大,其行之也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这种学至“圣人”的治学目标,使得他们治经的目的更加鲜明:“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13]59即研治经典的目的便是“明道”,而圣人作《春秋》乃因“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15]823,此“百王不易之大法”便是《春秋》大义。王皙的《春秋皇纲论》之卷首便明言《春秋》“笃于三纲五常,明于义理之尽而已”。对于《春秋》中诸侯侵犯王权之事均予严责,认为在衰世中论《春秋》可以“拨乱而归正”,于升平之世则可以“润色乎王道”[10]卷一,追求合理道统之意味极其浓厚。
刘敞之《春秋》学“独以陆淳之言为信”[16]卷上,可见其与中唐新《春秋》学的一脉相承。刘攽所作《刘敞行状》之起始历述刘敞举进士前之学业并述及其经术:“其论五经皆欲明王道,……及公为之,正德性,别仁智,举中庸,明天命,条达理遂,交贯旁畅。……至说《春秋》,其所发明尤多。”刘敞认为《春秋》虽据鲁史而修,但是“经”而非“史”,因为“圣人之政”中的“褒贬之理、予夺之义”不可与人共有,因为此乃孔子“王心”所寓[16]卷上,概而言之,“《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万事”[9]卷八。与宋代理学家一样,刘敞坚信“正心以正万物”之理,因此,他认为春秋时期王道衰微的根本在于“上为之,下则有甚焉者矣”,因此,“欲拨乱世、反诸正,则莫若正己。正己而物正矣,故《春秋》于其僭君也必书。必书之者,必正之之意也”[16]卷上。不但君王如此,王者之臣功绩未必皆多,“诚在正本而已矣”,若如此则“必致之仁圣之域、王者之道”[17]卷上。
由上可见,宋儒透过经典诠释所论证的人文信仰具有鲜明的内倾性、伦理性与理性化的特征。他们认为圣人之道蕴含在经典文本中,圣人作经便是阐明王道,因此“学者必以经为本”。[13]1235时人亦谓,经传本身才是通向“圣人之道”“圣人之心”的桥梁,此外是无法获求的。换言之,知“道”的途径“须是自求,己能寻见义理,则自有旨趣,自得之则居之安矣”[17]273。程颐在解答苏季明治经困惑时还说治经“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13]2。具体的方法则是“潜心积虑,优游涵养,使之自得”[13]168。因此,宋儒倡导的天理、太极、阴阳、中和、气、性等范畴都内在于人心,但《春秋》又是“史外传心之要典”,可以将之呈现于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日用、经邦治国的实践之中,因此,程颐强调“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13]1200。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方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18]11。于是,理学家所极力阐发的“身心性命”等理学的基本观念,必然要渗透进对经典的解说中而形成宋学独特的伦理和道德的义理特色。同时,理学化的《春秋》学又推动了理学观念在经典文本中的浸润,使得经学理学化过程加剧,这种用思辨的哲理来论证传统社会秩序与纲常伦理的治学方法,基本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治术:经文主旨与王道之用
所谓“治术”,就是关于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操作技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汉武帝时取得“独尊”的地位,主要靠的是“术”而不是“学”。汉代经学的“经世”,表现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19]56但这些经典在国家机器运转失灵之后,无论是经今文学还是古文学,均无法解决外戚干政、藩镇动乱、豪强割据等乱象,更无法抵御佛、老等思想的侵袭。《春秋》宋学的兴起,正因为宋儒抱持儒学本来就是兼具体用之学的观念,儒家的人文信仰属“体”的问题,而所谓的治术则是“用”的问题。孙复说:“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14]223胡瑗说:“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20]25胡安国作《春秋传》以为经世之法的用心相当清楚:“是故《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21]2因此,宋儒眼中的《春秋》蕴含了王权一统、纲常名分、王霸义利等圣人之用,通“经”以“致用”是治《春秋》学者皓首穷经的终极信仰。
当然,《春秋》及三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其中的确蕴含着若干体现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以及共同心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它们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稳定国家秩序、协调家庭关系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儒家各类经书都倡导一些互不相同的重要价值观念,但《春秋》及其三传却集中阐发诸如大一统、尊王、法天尊祖、华夷之辨、大居正、重民、大复仇、君臣之道以及经权说、慎微说等有着自身特色的思想观念。而且,即使以西汉至近代的历史观之,上述思想观念从来都是以开放的、动态的姿态体现在历代经师的诠释中,在与时代的积极互动中体现了鲜活的生命力。不同时代的《春秋》家以一种宗教似的虔诚向经典文本质询着自身时代的出路,以寻求启示。在这种解释者与经典文本对话的过程中,经典文本中蕴藏的特定价值观念就以诠释者所处时代主题为背景开显出来,从而形成经典自身的历史性与魅力。
《春秋》首重“尊王攘夷”。在理学家程颐及其众弟子眼中,《春秋》被视为“圣人之用”, 蕴含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而治乱安危的关键便是“尊王攘夷”。在新《春秋》学者的渐次阐发后,“尊王攘夷”俨然成了宋代《春秋》学的主流。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书名使得全书主旨跃然纸上,他直言《春秋》一书乃“以天下无王而作”,孔子伤圣王不作终使吴楚迭制中国,最终导致“圣王宪度,礼乐衣冠,遗风旧政,盖扫地矣”。[4]卷十二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会诸侯与戎,因此,《春秋》书“会”者皆贬绝之意。即便齐桓晋文有攘夷之功,孙复亦归之于天子,宋人吕中赞曰:“自孙泰山治《春秋》,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推见王道之治乱,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义。”[16]926刘敞认为:“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时,尽心竭力,致其诚悫专一之意以将之,则所谓子事亲、臣事君之道矣。”[16]卷下因此,“非天子不制度、不议礼、不考文”。[23]卷六对于虽有尊王攘夷之功但又“沛然自得”“矜功而受命”的霸主,则仍不免于贬。
宋室南渡后只蜷缩于东南一隅,但文化大国的自信依然未曾稍减,《春秋》学中亦以攘夷论较为突出,但讲攘夷从本质上讲也是尊王。南宋《春秋》学之翘楚当属胡安国,其《春秋》学中坚守“《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拨乱世反之正”之旨[21]154,他认为《春秋》为天子事,则本无内外夷夏之分,此为“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但夷狄犹如小人,内中国而外四夷,最终是要使之各安其所,“不使乱中夏则止矣”,因此“内中国外四夷者,王道之用”。[21]6
《春秋》还主张固国以保民为本。重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政治传统,也是历代《春秋》学传承的基本思想之一。《春秋》及三传中都有大量有关重民的言论,其中尤以《榖梁传》最为突出。刘敞在疏解《春秋》经文、撰述《春秋》学著述时便继承《春秋》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对重民思想予以重点发挥,甚至将重民与王道政治结合起来,这就丰富了《春秋》学的重民思想。如成公三年“作丘甲”,刘敞传曰:“作丘甲者何?赋丘为甲也。何以书?讥。何讥尔?古者取于民有常,作丘甲非正也。”[23]卷九此是讥讽成公作丘甲而滥取于民。又如刘敞在评述《春秋》所记文公、僖公书不雨时发表了一段精彩论述:“凡南面而治,有国家天下者,患不与民同忧。苟不与民同忧则亦不与民同乐矣。唯有道者不然,己未尝有忧也,民之所忧不可不忧;己未尝有乐也,民之所乐不可不乐。若是者所谓无常心而以百姓之心为心,是故与民同忧者,王事之始也,与民同乐者,王事之成也。”[16]卷上刘敞提升《榖梁传》的思想,从而将儒家的重民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诸家《春秋》学著述中尤为独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有国家天下者应以民之所忧为忧,民之所乐为乐,并以之作为王治成败的基本原则,这就将儒家思想与政治实践高度结合在一起。
南宋胡安国生活的时期,是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迫使思想家与政治家重新考虑国家强盛的根本。国家的强大固然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民”,只有民“效死而不去”才是为国之本。《春秋》庄公九年“冬浚洙”,胡安国批评说:“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城,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而况洙乎?书‘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21]102民即是国家之根本,那么爱民、养民则是政权巩固的题中之义。胡安国在评论“梁亡”时曾论道:轻民力是亡国之道,而王政之根本在于以善养民。所谓以善养民:一是教化其民,一是善待其民。他还引程伊川之言曰:“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21]25程氏此语实际上是对孟子仁政理论的一个解释。对于国家差遣徭役耽误农时,胡安国更是在经解中多处给予批评,如隐公九年“夏城郎”胡安国曰:“城者,御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时……失其时制,妄兴大作,无爱养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轻重见矣。”[21]33对于成公收复故地后仍“税役日重”终至兵戎相见,胡安国论曰:“成公不知薄税敛,轻力役,修德政以来之,而肆其兵力,虽得之,亦必失之矣!”[21]305
综上所述,宋儒首先通过重新阐发《春秋》,在经典辨疑思潮的影响下,大胆疑经辨伪,并通过会通三传的方式抉发注释《春秋》中的经世义理,建立了 以“天理”为中心的知识体系;其次,宋儒在“原道”的旗号下,通过向内反思的方式形成了极具理学化与伦理特征的治经思维,从而重新确立了经典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权威;最后,宋儒治经并未满足于自身的“成学”“成德”层面,而是始终坚持“学术及道德必于政事觅其落实之处所,而政事亦必藉学问及道德为其基础,两者绝不可分为两橛”[24]264。因此,现实中的他们往往努力将“经义”与“治事”融合为一,力图使儒道和儒学最终落实于政治实践。
仅由《春秋》宋学便可发现,宋儒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的思想文化,而且还在儒学、儒道、儒术的几个层面实现了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重新建构,这样,宋学所建构的思想文化是不仅统一全国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1] 朱汉民.文化视界的审视[A].中国思想史论集[C](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3]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 孙复.孙明复小集[M].//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 孙觉.春秋经解[M].//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9] 刘敞.春秋权衡[M].//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0] 王皙.春秋皇纲论[M].//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 赵鹏飞.春秋经筌[M].//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0.
[16] 刘敞.春秋意林[M].//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 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8] 侯外庐、邱汉明、张岂之.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9] 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0]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 胡安国.胡氏春秋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2] 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3] 刘敞.春秋传[M].//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4] 黄俊杰.内圣外王——儒家传统中道德政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A].载黄俊杰主编.天道与人道[C].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