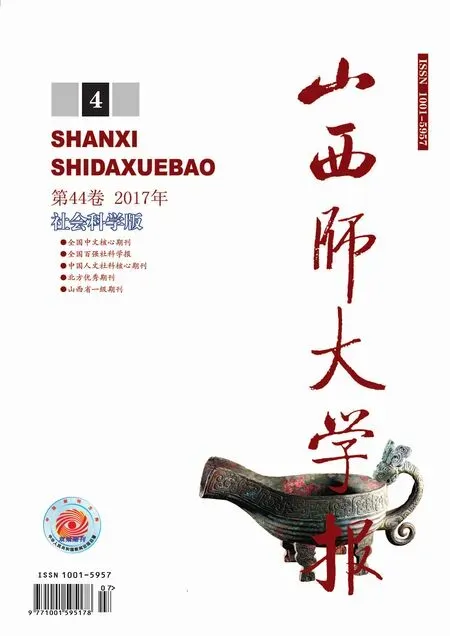弃夫离婚:中世纪妇女的反抗
孙 继 静
(湖南女子学院 教育与法学系,长沙 410004)
中世纪时期,婚姻的产生通常都是经济利益驱使的结果,个人情感在其中所占成分十分微小。正如汤普逊指出:“中世纪的婚姻关系,远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是感情的结合,大多是一种利害关系上的婚姻,也是一种野蛮强制的婚姻。”[1]393无论哪个社会等级的妇女,在经济来源和法律身份上都是从属于父权制的权威与控制的,因此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无法自由选择婚姻,可以说在婚姻开始和进行中都是被动的。同时,中世纪的婚姻生活总被认为是残酷的、充满恶意的、缺乏沟通的,[2]117家庭暴力也是常态。[3]103甚至有学者将这个时期的夫妻关系描述成一种等级关系,而丈夫在法律和社会权利关系上处于主导地位。无论在世俗法规还是宗教教义中,都将丈夫视为家庭的领导者,所有不动产和动产都归其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妻子在经济上和权利地位上对丈夫产生绝对的依附,失去丈夫宠爱的妻子意味着失去一切经济来源并被家庭所驱逐,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艰难的角色。
然而,尽管中世纪的婚姻被描述得如同监牢般不堪,妻子们总是逆来顺受地接受这种处境和安排,有的甚至在丈夫公然明确解除婚姻的情况下仍努力维持着并不幸福的婚姻,但这些并不是中世纪妇女生活的全貌。在仔细考察约克、坎特伯雷及伦敦的宗教法庭、世俗法庭、庄园法庭及皇室法庭的案件后,可以发现在父权制和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中世纪,不少妇女依然做出了许多反社会、反教会甚至触犯法律的出格行为,她们试图与可怕的婚姻命运做坚决的抗争,甚至出现弃夫离婚等离经叛道的举动。
一、 弃夫离婚的原因
中世纪时期,妻子遭到抛弃是件平常的事情,而反过来妻子遗弃丈夫却不是件易事。但这些妻子总会找各种各样充分理由或借口,驱使或者说是逼迫自己铤而走险。
(一)身体虚弱或者残疾
有的妇女因为丈夫体弱多病,生活拮据,加之照顾丈夫过于操劳和辛苦,所以选择遗弃丈夫,当然这种情况是较为少见的。在1388—1395年间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主教的登记案件中记载,一名叫Agnes Wormes的女性离开了她失明丈夫Ralph Irwyn,并且据说拒绝履行夫妻间的性权利和特权。[4]117
(二)虐待
有的妇女感到解除婚姻不那么容易的话,选择法定分居是条捷径。如果说宣布取消婚姻需要明确的理由,但法定分居常常简单得多,其中最常见的理由是虐待配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虐待的例子很少出现在法庭案例中,但很多蛛丝马迹依旧暗示了妻子有被虐待的可能。比如1419年3月,由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郎德镇(Longford)的Margery一直拒绝遵从恢复婚姻夫妻同居权的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不得不求助于世俗力量捉拿她,然而据说她早已以受丈夫虐待为由在大法官法庭和教会法庭都获得了法定分居的判决。[5]185—1861305年伦敦的市长法庭处理过这样一个案子,在丈夫William控告妻子Alice带走其20镑财产之前,教会法庭判决的法定分居的传票已经到了家里,理由就是丈夫虐待妻子。[6]236—237另外,法庭以逐出教会的惩罚强迫德雷顿(Drayton)的John Cutter的妻子Margery重回丈夫身边,但她提出除非丈夫保证今后友善地对她,否则坚决不从。[7]250从Margery坚决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丈夫之前的虐待是她逃离婚姻的主要原因。有时,一些女性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会以受虐为证据达到离开丈夫的目的。1347年,Henry Cook的妻子向罗切斯特(Rochester)法庭控告他对妻子不忠且很残忍。[8]2251292年,Christiana Meynell被指控毒害丈夫,但她辩护称由于丈夫十分残暴,因此她不得不离开他。[9]170,176,177
(三)性无能
性无能也是中世纪时期妻子抛弃丈夫的一个较为常见的动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圆房对婚姻生活而言至关重要,“没有圆房”被格拉西撰写的教会法汇要(1140年)确定为离婚的合法依据。教规规定,如果一段婚姻由于一方阳痿或性冷淡导致无法圆房,这种情况持续三年以上便可宣告婚姻无效。[10]88—89奥古斯丁也认为,针对通奸者和私通者的起诉中,要遵循婚姻是善的,是对犯罪的必要补救这一观点。但对那些丈夫患有性障碍的妻子而言,婚姻则并非一剂良药。[11]346然而,这些严厉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由于女性被定义为充满母性的,三年的时效总是针对她们的。通常情况下,只有女性必须经历三年的隐忍并要证明丈夫确实性无能才有可能离婚,而男性则不必如此。同时,还有一种情况也会令人困扰,即如果在婚姻宣告结束后,性生理问题治愈了,这些夫妇的婚姻该何去何从呢?因此,为了避免某些不道德的夫妻以性无能为由,将自己从婚姻中解放出来,教会权威通常对这种离婚诉求抱有怀疑且十分谨慎,但依然不能妨碍这成为女性弃夫离婚的有力证据和理由。1395—1410年坎特伯雷的离婚案件记录中,有一个关于Juliana Hewer和她女儿Helen的故事。当Juliana因为让女儿拉皮条被带到法庭时,她和女儿都完全否认这些指控。相反,Juliana认为自己是在帮女儿逃离婚姻,因为Helen的丈夫性无能,所以她拒绝忠于丈夫。更为讽刺的是,Helen之后处在一个“老实男人”的监护下,并且生了孩子。[11]347记录中虽然没有提到是基于丈夫的性无能宣告婚姻无效,但依据此案的结局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教会并没有对Helen因为无法忍受不能生育的婚姻而给予责罚。
(四)其他原因
在考察中世纪的婚姻案件时,笔者发现还有不少妻子抛弃丈夫的事实被描述得较为模糊,没有揭露妻子抛弃丈夫的真正原因,这些女性可能出于如财产、重婚关系、近亲结婚和对婚姻的不满等原因选择逃离婚姻的束缚。1388—1395年索尔兹伯里主教登记中写到:“Katherine不愿继续陪伴其丈夫Philip,不愿意接受他回家,也不想与他分享财产”[4]146。记录中没有提及Thomas与Katherine是什么关系,因此对Katherine离开丈夫的理由也充满了猜测。另外,1366年,Joan被逼嫁给了Phillip,对婚后生活感到绝望,之后她与John Cook订婚并成功地逃离了前夫的监护,嫁给了John。[12]921409年,索尔兹伯里主教区案件中有记载Isabel因未和丈夫生活在一起被传讯,但本人没有到场,案件被搁置。[4]96—97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中世纪时期妇女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逃离丈夫和婚姻,有一部分案件留有详细的记录并注明了妻子抛弃丈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无法明确妻子的动机。
二、 弃夫离婚的风险
离婚,即便现代的法律角度和社会角度都已经给予公然认可的情况下,仍然有许多妇女担心由于经济困难、孩子监护权的争夺甚至是被社会或家庭排斥等原因,继续忍受有虐待倾向的丈夫并维持着不幸的婚姻。那么,对于中世纪时期缺乏基本的人格独立性的妇女来说,逃离婚姻的赌注更高,风险更大。
(一)失去经济支持
中世纪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准则是婚姻,这并不意味着男女都会在合适的时间成婚,但对中世纪女性而言,婚姻是经济来源的一种基本期待和依赖,妇女独立生活在当时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威斯敏斯特二世法案法令(1285年)进一步细化了抛弃丈夫的女性的经济状况,法规中宣称一个通奸者在其丈夫死后,除非丈夫已经原谅了她,否则取消其寡妇继承权的资格。[13]24因此,我们更无法想象抛弃丈夫的妇女在失去任何稳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能够继续生活。如同Ruth Mazo Karras所说,中世纪时期在实际操作中“独身妇女”一词可以与“妓女”互换,正是因为独身妇女常常为了生计不得不求助于性交易。[13]2416世纪伦敦参议院书目中对妓女的规范记录中,旁边的注释写着“单身女性”也有这个层面的暗示。[14]167
(二)社会地位受损
对中世纪时期女性而言,婚姻除了有经济意义之外,常常还赋予她们重要的社会地位,这也是许多女性能够忍耐不幸婚姻的原因之一。正如Judith Bennett和Amy Froide说婚姻塑造着女性的生活,成为妻子意味着比其他女性更有管理权力,妻子能够通过丈夫实现某些非正式的政治权力,[15]13包括掌握家庭大权、管理土地和财产、教育孩子、宣布效忠城市并承担市民义务,甚至干预法庭案件审理等。这一点在贵族妇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保全其特权、地位和财产的稳固性,她们提出离婚的事例极为罕见。[16]149另外,在教会的干预下,妻子抛弃丈夫还要面临精神上的压力。12世纪基督教会将婚姻提高到圣事的高度,一直到13世纪都坚决奉行圣经中“上帝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不让任何人分离”的理念。因此,基督教会尤其致力于维护婚姻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婚姻一旦取得教会法律的认可,就是不可取代和不可解除的,即使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近亲结婚,多半也得给婚姻的稳定性让路,正如圣伯纳德所说,血缘关系是凡人的事,而稳固性才是属于上帝的。[17]168因此教会法庭是坚决维护婚姻的完整性的。大多数妇女成长于将婚姻奉为唯一人生目标的父权制社会里,拥有妻子身份是基督徒应该履行的责任之一,这一身份能够保证她在教区中得到相应的尊重。如果女性没有获得取消婚姻的许可或者法庭开据的分居证明就抛弃丈夫的话,她将陷入到无边的灵魂危机中,原本谦逊顺从的形象将被颠覆,社会名誉将会受损,并成为“忘恩负义”的罪人。
(三)触犯法律
尽管存在上述几个风险因素,却依旧有妇女弃夫离婚,而且有的态度还十分坚决,但对这些逃跑的妇女而言存在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最大的风险,即触犯法律。对那些期盼妻子回家或者本质上是想要回妻子卷走的财产的丈夫而言,也往往会求助于法庭和法律,而中世纪时期的各类法庭有各种办法帮他们处理这类案件。
教会法庭有时以逐出教会作为惩罚,强迫妻子重回家庭,但这种惩罚多限于威胁层面,因此有些固执的妻子会想尽办法来规避惩罚,或者直接选择无视。1336年,Emma Herevay被带到林肯郡的教会法庭,要求她回到丈夫身边,否则将以逐出教会作为处罚,但Emma拒绝并表示不会回来。[18]61463年,当Katherine Kyrton因被指控拒绝与丈夫John同居而未现身法庭,威兹比奇主教对她发出禁令,[18]368但禁令是逐出教会中较轻的形式,仅仅不允许参加圣餐和圣礼而已。当然,大多数案件并没有得到这么宽容的对待。1338年,Christine Verner以藐视法庭为由被索尔兹伯里主教判定开除教籍。[4]150这个惩罚比前两个例子要严重许多,它意味着她将受到整个社会的排斥,因为基督徒要避免与任何被开除教籍的人接触或产生交集。开除教籍的人还会被世俗法律排斥:这些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不能在刑事案件中接受审判,因此实际上成为法律严格意义上的无行为能力的人。
当然,被开除教籍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如果有罪之人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有所悔悟,可以将处罚撤销。但抛弃丈夫勇于逃离婚姻的妇女们往往十分固执,大多不愿再回去。于是,40天之后教会只好借助世俗权力将犯罪者逮捕入狱。抛弃丈夫的案件中显示,教会法庭丝毫没有回避召集当地警察来搜捕那些固执的被逐出教会的妻子们。1419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请求世俗力量协助捉拿斯塔福德郡的Margery,她有着富足的财产,因为一直拒绝服从恢复夫妻同居权利而被判逐出教会,尽管事实上她宣称教会法庭和大法官法庭已经给出了法定分居的判决。[19]185—1861417年,达拉谟主教也向泰恩河谷的贵族发出了类似的请求,帮助他逮捕因不愿和丈夫重归于好而判逐出教会超过40天的Joan Buntyng。[20]134从第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如果抛弃丈夫的妻子是有一定地位的拥有土地的妇女,丈夫会更倾向于考虑更猛烈的高压政策,但是否只有在财产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会动用世俗权力则不得而知。然而,至少可以明确的是,教会认为抛弃丈夫是严重的事情,为了以儆效尤,愿意对这些妇女施以法律的强制执行。
一方面,普通法庭对处理弃夫离婚案件有着丰富的经验,有时不仅妻子要被定罪,那些帮助她们的家人和朋友也会受到牵连。法院审理强夺案件的目的不是为了劝回妻子,而是要夺回财产,因为王室司法认为婚姻是神圣的事情,夫妻之间感情的事应由主教掌管,财产的事则交给世俗法庭处理。普通法庭中常常将妻子抛弃丈夫的案件定义为侵权,然而这类案件又有独特之处,它们是妻子和帮助她的家人朋友之间的两厢情愿的诱拐。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妻子离开时带走了财产,那些帮助她的人也将遭到强夺罪名的指控。[13]80当Robert的妻子Isabel在婚后不久发现丈夫与其他女人有不轨行为,于是返回自己父亲家中,其父亲很快发现自己被国王法庭以强夺的罪名指控。[12]80Sabina Herring的女儿Beatrice的案件也同样危及到了她的家庭。尽管她还未到法定年龄就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强制与Henry结婚,但Henry依然信心满满地将帮助Beatrice逃跑的母亲和叔叔以强夺罪告上法庭。[12]80—81更为荒诞的是Bartholomew的妻子Isabel的案子,其中表明法庭有时居然会将“强夺”一词简单地解释为逃跑的妻子提供容身之所。Isabel为了避免灵魂和基督徒身份陷入罪恶危机,她向法庭请求宣告取消婚姻,最终教会法庭同意。威斯敏斯特主教判定Isabel只有在案子完全解决后,才能回到原来的教区,因此她只好暂时轮流居住在儿子和女儿家中。很快,这一做法让她的儿子和女儿的丈夫都陷入强夺罪的指控。[12]89—90在普通法庭中对于强夺罪的惩罚,往往采取支付罚金的方式,罚金通常包括从丈夫那里偷走的财产和损害赔偿,有时这笔罚金数额巨大。比如Stephen de Upton之前的学徒Robert de Heydon被指控强夺了前者的妻子,法庭命令他支付60镑来赔偿他“恶意带走”的私人财产。加上损害赔偿金,Stephen的账单高达126镑之多。[12]73—74如果没有能力赔偿,那么在他找到办法之前会有被强制拘留的可能。令人尴尬的是,有的时候这些所谓“偷窃”的财产本就可能是属于妻子的。
最为令人惊讶的是,中世纪的此类案件中还出现一些教士被指控帮助这些离经叛道的妻子。他们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却恰是这个女人的情人或已经成为家庭成员。在整个过程中,这些教士如同Sue Sheridan Walker所说“扮演着精神导师的角色”。[21]245—2461387年,伍斯特主教Henry Wakefield因强夺John Henley的妻子和女儿以及部分价值40s的财产被指控重罪。这起案件被法庭判为家庭纠纷,主教Henry实际上出于关心抚慰教区中不安的灵魂的目的,想帮助这个女人和孩子逃离John的家庭暴力。[11]346虽然这些公然对抗法律帮助这群妇女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但他们的行为可能随时招致更多的麻烦。Stephen de Beck是一个慈善的教士,为了帮助受虐待的Joan逃离丈夫Hamon Sitich,他派了两名随从去接她。当陪审团问Joan是否是自愿去到Stephen那里时,不知什么原因Joan陈述道之前她已对那两名随从说过,她宁愿回到丈夫身边受惩罚也不想和他们走。因此,Stephen被指控强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12]78—79
另一方面,虽然普通法庭对处理这类案件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正如Maureen Mulholland所说,普通法庭无法对这些小的地方性纷争提供快速便捷的法律制裁[22]88,这时庄园法庭给予了有力补充。庄园法庭不像国王法庭那样,没有昂贵的令状,诉讼当事人和证人也不需要到场,不需要大量的花费。[11]342比如1402年的五旬节,埃塞克斯郡的John Werkman在都不用确定财产被盗的情况下,很快在控告John Crudde进入他的领地并诱拐其妻子的案件中胜诉[37]的事实证明,对被抛弃的丈夫而言,庄园法庭是较为理想的审判处,它们为迫使抛弃丈夫的妻子们改邪归正提供了有力武器。庄园法庭常用扣留财产来保证辖区内人们行为的检点,以及维持社区的秩序,也成为调解夫妻争端的有效方法。当然,庄园法庭不常直接处理这类案件,但婚姻纠纷常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这类法庭中。[11]3421331年,韦克菲尔德法庭的庄园名单中记录了三名男性宣称自己负责监管Thomas的儿子Alice及其妻子Agnes价值60s的财产,他们认为如果Agnes愿意及时协调与丈夫的关系,那么夫妻俩可以将这笔财产收回。[23]189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不管哪个法庭处理强夺案件都较少判处体罚或死刑。但其中的可怕之处在于,有的丈夫将“诱拐”妻子的强夺描述为强奸,那被告就有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了。国王法庭中常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事实上这两类案件之间也总难以区分开来。Emma Hawkes说,这个时期“强奸”一词定义比较模糊,“中世纪的法律文件中一般都将这两类案件混为一谈”,[11]343致使陪审员们不得不十分小心地审查性骚扰性质的案件和妻子常做为自愿参与者的强夺或诱拐案件的控词,因为两类案件的性质和程度完全不同:强奸者破坏了某位父亲的女儿或某些兄弟的姐妹的婚姻完美和个人幸福,或者使某位丈夫的孩子的合法地位受到了质疑,而这通常又和财产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24]149比如Henry de Bongheye同时因强奸和诱拐Hugh Veysee的妻子Katherine和带走Hugh价值40镑的财产为名,被判重罪。[25]98反过来,也有投机者利用两个词的模糊,将本应判为强奸的案件偷换为强夺,这样判决相对会减轻很多。比如一名叫Thomas Walsshman的裁缝闯入了Stephen Irish的家中,引诱并强奸了其妻子Alice,同时带走了价值40镑的财产。后来为了强调这起案件的性质,据说Thomas不得不带着Stephen的妻子和财产远离了先前的住地Coventry。[26]151由此,案件变成了Thomas对Alice的强夺。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不论哪种情况,妇女们的感受是无关紧要的:她们逃离婚姻的举动可能损害了身为父亲或丈夫等监护人的利益,致使那些帮助她们的人被判强奸;而作为直接受害人,她们又可能因为法律的疏忽,没有办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更痛苦的是还有可能成为狡猾的犯罪分子的牺牲品,要与那些伤害她们的人共度余生,同时还可能面临再次被抛弃。
(四)重返不幸的婚姻
对大多数妻子而言,逃离婚姻最大的风险是有可能再次被强制重返不幸的婚姻。[11]344对那些同意回到丈夫身边的妻子们而言,未来日子里无尽的忏悔与惩罚以及是否能成为合格的妻子成为时常萦绕她们心头的恐惧。例如,1412年,Katherine不仅离开了丈夫John ate Mulle,而且挥霍了他的财产,最终她被遣返回家且发誓将不再离开并一直照顾丈夫,如有违反将被处罚100s,并在集市上当众鞭打6下。[4]112—113同样,1347年,Robert的妻子Isabel因负有遗弃和与当地牧师通奸的双重罪名,被要求返回丈夫身边并卑微地顺从他,不能惹怒丈夫,否则将被判仅身着睡衣在Grantham集市鞭打6下,并在Skelinton教堂游行6圈。[11]344这些都是教会为惩戒淫乱、通奸及教士违背独身誓言而给予的典型戒谕,但在弃夫离婚的案件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们不仅仅是犯罪,更重要的是关于对那些有悖纲常不知身份的妻子恢复婚姻等级制度。那些伴随着未能履行妻子责任而来的进一步忏悔与修行,成为另一种威胁,因为重回家庭的妻子会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现在已经分居的丈夫才是判定她是否履行承诺的最终审判者。这就意味着,出于对之前抛弃和逃离的报复与仇恨,这些女性回归后的生活将比之前更加悲惨。
另外,教会法庭的判决总是当即生效,即便夫妻分居时间已经很长了。比如,当Joan现身法庭听取对她通奸和抛弃丈夫的指控时,据说距她离家已经有6年了。[27]92当Joanna Apulbe因没有和丈夫一同居住而被林肯教区传讯时,记录显示夫妻俩实际已经分居4年之久。[11]345在这么多年的分居时间里,夫妻感情疏远淡化,他们可能很难适应重新生活在一起了。偶尔,教会会对这些妻子们抱以同情,准许她们有个过渡期进行准备。比如Nicholas Swayn的妻子Emma被给予8天的时间作为缓冲;Isabel Poterne给了3个礼拜。[11]345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如Margaret一样,被通知立即恢复婚姻,不得延误。[7]250
大约从9世纪开始,由于教会提出不能随意解除婚姻的教义,离婚变得越来越受限制。而对于处在父权家长制下的“被保护的人”——妇女而言,弃夫离婚更不是件易事。她们不得不担心名誉受损、逐出教会、被迫重返家庭、罚款、被捕入狱、监禁甚至处死的危险,同时还极大可能地会连累那些帮助她们的人。但是,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发现,无论何种阶层何种身份,都有不少女性愿意冒险,选择这条艰难的路走下去,同时也的确依旧会有家人和朋友乐意帮助她们。那么,这些逃离了原本不幸婚姻牢笼的女性,接下来的生活如何呢?
三、 逃离后的困扰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作为女性,逃离了原来的婚姻,背叛或者抛弃了之前的丈夫,这一事实为她今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父权制社会并没有给她们更大的宽容,她们努力争取的逃离也并非意味着幸福生活的起点,逃离后的生活可能依旧充斥着无尽的困扰与艰辛。
(一)生计问题
我们之前已经探讨了弃夫离婚所带来的经济风险,那么不难想象妇女在这些行为之后的生存定将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生活拮据,她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有的铤而走险进行偷盗,还有的迫于无奈干起了卖淫的勾当。比如John Roseson的妻子Margery在离开丈夫之后,据说由于偷盗总价值26s.8d的羊毛、麻布和一口铜锅,被判重罪。[26]123有的被迫再次嫁人,成为又一个男人的附庸,这不得不说是这些勇于对抗命运的妇女的悲哀,因此这些被告通奸的案件又常常被描述为秘密结婚。1468—1474年的法庭记录中记载,一名叫Agnes Erby的妇女因为没有与丈夫生活在一起被坎特伯雷法庭传讯,而她实际早已在林肯教区有了另一位丈夫。[5]185—187出于经济需要,许多逃离婚姻的妇女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再次依赖男人的帮助。
(二)声誉问题
逃离不幸婚姻后的妇女所遇到的另一大困扰必然是声誉问题,女性逃离婚姻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现代社会,也没有男人会乐意承认自己成为被婚姻抛弃的对象,尤其是丈夫性无能的情况。男人们因为颜面扫地恼羞成怒,很可能会给妇女及帮助她们的人莫须有的声誉诽谤。1388年,John Wyatt的妻子Alice因为丈夫的性无能想在牛津主教处获得解除婚姻,在这个过程中Alice被劝暂时离开丈夫外出躲避,因为丈夫感到颜面扫地,扬言要对她进行人身伤害。恐慌之下,Alice求得主教的允许到叔叔Henry家庇护,而之后叔叔因诱拐罪名受到皇室法庭的传讯。[12]87之前因为虐待导致离开的Henry Cook的妻子,被丈夫反咬一口,控告她与别人通奸。Joan Grokles因离开丈夫很长时间而受到指控,她被人污蔑成爱责骂的人,常常与邻居发生争吵,并且与一个所谓的陌生人通奸。[4]4Isabella被丈夫说成是“谣言和争吵制造者”。[11]348甚至还有的妇女被丈夫以沦为妓女为名控告,比如Agnes和Katherine都被说成是一般妓女。[28]252如同今天的离婚案子一样,常常是夫妻对簿公堂,恶言相向,丈夫被责问虐待和不忠,妻子则被抱怨喋喋不休与放纵。但在中世纪的妻子抛弃丈夫的离婚案件中,对给予女性的这些指控存有怀疑。这些妇女到底是事实上靠身体赚钱的卖淫女,还是仅仅指道德宽松敢于突破传统的妇女呢?
(三)纠缠与骚扰
在这些记录中,存在一些有趣的现象。对于带走了财产或者有损丈夫颜面的情况,多数会遭到丈夫无休止的骚扰,而事情的另一面,也存在妻子辱骂甚至威胁丈夫的情况。比如1301年的记录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名叫Agnes Day的农夫妻子和一个乡绅生了小孩,她不管在哪里见到丈夫都恶语攻击并粗鲁地对待他,致使丈夫都不敢靠近她。[29]118还有更加恶劣的妻子,她们指使情人或朋友偷偷跟踪并辱骂殴打丈夫。Agnes伙同情人Stephen Sutor袭击并殴打了丈夫John,最终两人遭到逮捕。[11]351John Hack向大法官声称妻子和她的情人正密谋杀害他。[11]351还有其他许多妻子利用她们熟悉的普通法,长期纠缠和烦扰丈夫,致使许多虚假案件的产生。[30]291—316虽然不能简单肤浅地从表面理解这些指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逃离婚姻的妇女并没有那么决绝利落地与之前的生活割离,这种种情况也使得她们无法平稳地在别处开启新生活。
这些案例展现了更为广阔而生动的画面,弃夫离婚的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常见,为我们理解中世纪的婚姻解体提供了新的维度。原先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处于被动顺从的形象有所改变,她们中的部分人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表现出令人惊叹的果敢与坚强。与此同时,虽然存在着不少可以预见的风险和麻烦,但家人和朋友也都为这些女性逃离苦海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时身负家长责任的男性甚至会认为这是他们应尽的职责。这些说明从中世纪早期教会开始强制推行的永恒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理念开始有所松动,人们在习惯上可以接受离婚的观念以及婚姻的流动事实,而其中某些教士阶层的参与使得这种现象更加合理化。这一切都暗示着,尽管中世纪教会依旧极力想将婚姻视为丈夫和妻子之间有约束力的契约,但显然英国民众已经开始并不信奉这一观念了。
[1] (美)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下册)[M].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1500—1800,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77.
[3] Judith M. Bennett, Women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Countryside: Gender and Household in Brigstock Before the Plag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87.
[4] TCB Timmins, ed. The Register of John Waltham, Bishop of Salisbury, 1388—1395, Canterbury and York Society, 1994.
[5] EF Jacob, ed. The Register of Henry Chichel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414—1443, Canterbury and York Society, 1994.
[6] AH Thomas, ed. Calendar of Early Mayor's Court Rolls of the City of London, AD 1298—1307, Cambridge, Eng., 1924.
[7] EM Elvey, ed. The Courts of the Archdeaconry of Buckingham, 1483—1523, Buckinghamshire Record Society, 1975.
[8] Charles Johnson, ed. Registrum Hamonis Hethe, Diocesis Roffensis, AD 1319—1352, Canterbury and York Society, 1948.
[9] W Brown, ed. The Register of John Le Romeyn, Lord Archbishop of York, 1286—1296, Surtees Society, v.123, pp.170,176,177.
[10] RH Helmholz. Marriage Litiga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 Mass, 1974.
[11] Sara Butler, Runaway Wives: Husband Deser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40. No.2(Winter, 2006).
[12] Morris S Arnold, ed. Select Cases of Trespass from the King's Courts, 1307—1399, Selden Society, 1985.
[13] Westminster Ⅱ, c. 34, 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12 Vols., 1963.
[14] Ruth Mazo Karras, “Sex and the Singlewoman” in Judith M. Bennett and Amy M. Froide, eds, Singlewomen in the European Past, 1250—1800, Philadelphia, 1999.
[15] John Stow. A Survey of London, ed. C.L. Kingsford. Clarendon Press, 1908.
[16] Judith M. Bennett and Amy M. Froide, eds, Singlewomen in the European Past, 1250—1800, Philadelphia, 1999.
[17] (以)苏拉密斯·萨哈.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M].林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18] 裔昭印等.西方妇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9] LR Poos, ed. Lower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The Courts of the Dean and Chapter of Lincoln, 1336—1349, and the Deanery of Wisbech, 1458-1484, Recor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ew Series 32, 2001.
[20] RL Storey, ed. The Register of Thomas Langley, Bishop of Durham, 1406—1437, Surtees Society, 1951.
[21] Sue Sheridan Walker. Punishing Convicted Ravishers: Statutory Strictures and Actual Practice in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987.
[22] Maureen Mulholland. Trial in Manorial Court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in Maureen Mulholland and Brian Pullan, eds, Judicial Tribunals in England and Europe, 1200—1700: The Trial in History, Vol.Ⅰ,Manchester, 2003.
[23] JW Walker, ed. Court Rolls of the Manor of Wakefield, v. 5: 1322—1331, York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44.
[24] Lindon E Mitchell. Women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an Culture, Taylor & Francis, 1999.
[25] Elizabeth Chapin Furber, ed. Essex Sessions of the Peace 1351,1377—1379, Essex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53.
[26] Elisabeth Guernsey Kimball, ed. Rolls of the Warwickshire and Coventry Sessions of the Peace, 1377-1397, Dugdale Society, 1939.
[27] AT Bannister, ed. Visitation Returns of the Diocese of Hereford in 1397.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30.
[28] Warren Ortman, ed. Court Rolls of the Abbey of Ramsey and of the Honor of Clare, Yale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1928.
[29] PE Hair, ed. Before the Bawdy Court: Selections from Church Court and Other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Correction of Moral Offences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New England, 1300—1800, 1972.
[30] Sara M Butler. The Law as a Weapon in Marital Disputes: Evidence from the Late Medieval Court of Chancery, 1424—1529.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