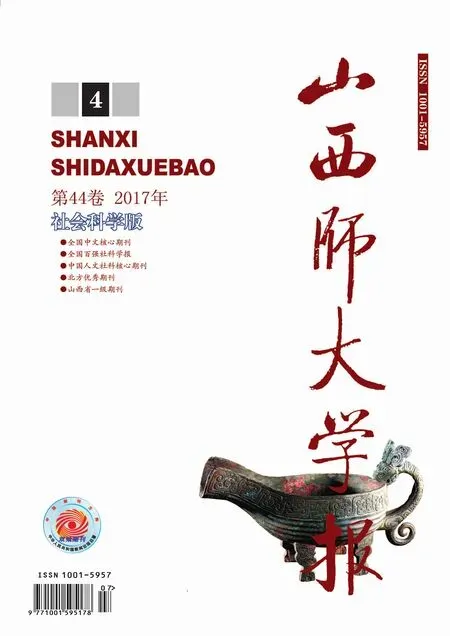电话通讯与民国城市女性社会角色的再塑
霍 慧 新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0)
社会角色“指的是社会对拥有某种社会位置或身份的人所持有的期望”,“每个社会地位,不论是先赋或是自致,都有一个预期角色会伴随而来”。[1]128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主导之下,女性社会角色被固化,贤妻良母是传统女性的毕生追求,相夫教子是她们主要的家庭职责,深闺宅院是其主要活动区域,安分守己、温婉内敛是她们社会形象的最生动刻画。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女性社会角色被重新塑造,社会各界开始通过各方渠道构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新女性角色。电话作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兴产物,成为民国城市新女性装点精彩生活的必备。民国广受大众欢迎的《良友》画报,主要读者群之一即城市女性。画报内容,不时有与电话科技相关的知识介绍。其中一期,封面为手握话筒、做打电话状的当时著名影星胡蝶。电话与女性,科技进步与时尚生活,紧密联系了起来。笔者尝试从近代女性日常生活入手,探讨电话通讯在民国城市新女性社会角色塑造中的作用。
一、期待破冰
电话通讯作为从深闺到外界的最后过渡,促使女性转变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性格,树立起开放、积极的民国新女性形象。随着电话线路延伸至住宅,传统旧家庭奉行之“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的封建礼教受到冲击。原本大多数处于深宅大院、高墙闺阁的传统女性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外部世界接触。
在民国城市电话用户构成中,住宅电话数量所占比例仅次于商号,远远多于戏院、菜馆、旅社、报馆、事务所、医院、银行、工厂、会所、学校、军政部门等。有资料显示,1932年,南京、上海、北平、青岛、威海卫、武汉、天津、镇江、苏州、扬州、抚湖、蚌埠、九江、沙市、太原、郑州、洛阳、烟台、保定等19个城市国民政府交通部办市内电话中,住宅电话用户为8370户,占电话总户数的19.5%。[2]176此项数据统计并不包括当时占绝大部分的私营与外商经营的电话公司用户。以近代上海租界为例,1930年,住宅电话达9638线,占实装总户数的36.7%;1938年住宅电话达20139线,占实装总户数的44.9%。[3]4337住宅电话线路的延伸与增加,不可避免地将原本“与世隔绝”的传统女性与外界联系起来,开始通过电话这种“传声筒”向外界发声。
女性与外界交流的增多,使得传统女性内敛、含蓄的性格特征面临挑战,前所未有的社交新问题也随之出现。1924年5月,时人杜伯超给友人打电话,友人不在家,接电话的女性支吾许久没能做出自我介绍。杜伯超逼问无果,领会许久才知是友人的夫人,造成尴尬。他提出,当时即便是开化的妇女有了自己的名号,也大都不肯宣示出来,如若下次在电话中遇到此种情景,女性究竟该如何自称。[4]男性作为传统社会的主体,通过“电话中的小问题”提出女性社会参与等话题,有利于人们打破世俗偏见,促使两性平等对话。在社会尤其是男性的呼吁、理解、参与和帮助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女性自觉、自发、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我社会角色重塑。
随着电话这种通讯手段的推广,民国城市女性勇敢、大方、得体地宣扬、展示自我,成为一种时代呼唤和社会需求。针对上述问题,有热心读者写信给《良友》出谋划策,认为女性受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约束,因循守旧,生性羞怯,不肯直接对外宣布自己的身份和名字,主张在电话中女性可以讲“某某是我的外子”,这样任谁都明白她就是某某的妻子。[5]采用“外子”此种古时的文雅称呼来回避传统女性直接面对外界的羞涩、尴尬和难堪,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作为电话通讯衍生的社交新问题,民国城市女性如何冲破传统女性解放的最后一道屏障,战胜自我,走出深闺,塑造大胆、主动、积极的新社会角色,成为民国舆论关注的新问题。民国城市女性社会角色的再塑在各方探讨中成为一种可能。
二、心理突破
电话通讯改变了传统的社交方式,成为广大城市女性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纽带,增加了她们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几率。相比于书信往来、见面会商等传统社交方式,电话可以缩短时空距离,节约时间和精力,“语言交通,首推电话,听筒一举,谈吐可闻,殊方无异比邻,缩地竟然有术,不亦便哉”[6]。 在崇尚舒适、快捷、高效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下,电话互通、电话购物、电话定座、电话解决危急、电话约客、电话雇车等时髦生活方式随之衍生,增加了广大女性接触新鲜事物、探索未知世界的机会。
以上海电话公司用户而论,在1931年自动电话尚未通话前,每一用户每日平均通话次数7.12次;自动电话启动后,1934年每户平均通话次数达14.81次。1945年9月,上海每日每线电话平均通话次数为8.37次,每日平均通话总数为480 900次;1947年6月,电话交往愈发频繁,每日每线平均次数为13.24次,每日平均通话总数为755 600次,每次呼叫平均占用时间76秒。[7]与商业电话不同,住宅电话使用次数较为稳定,不会随工商经济兴衰而波动。
使用住宅电话较多者,除了工、商、政以及学术界等相关人士外,大部分为那些富贵人家的太太和小姐。她们经常通过电话谈心,互相交流大光明戏院里新近放映什么电影,四大公司新进了哪些时髦商品,哪家舞厅新装了冷气等;[8]66—70或者通过电话购货让大型商场直接将自己心仪的货品送上门[9],不用遭遇春雨、夏日、秋风、冬雪。人们还可利用电话在影戏院定座,省下不少麻烦,“在京戏馆里电话更其有较大的用处,凡更换戏目,或北方有享盛名的戏子来时,接客的弃目往往先用电话去通知他们的老主顾,同时戏院中最好的几排位子可为他们留下。”[10]正如电话公司广告所言,现代新式家庭中不置电话,“真好似住在独家村,与外界隔绝一样”,如果家里没有电话,“家里有了事,拿什么去告知丈夫呢?拿什么去约姊妹们打牌或作其他消遣呢?”“家中有客来了,拿什么去通知菜馆添菜呢?”[11]取材于近代上海的小说《围城》《子夜》中有不少关于电话使用的场景描写,如九姨太嘲讽完冯云卿后,急于赴约,换好了衣服,坐上了打电话雇来的汽车。[12]135民国新女性是近代住宅电话的最主要受益者。通过电话联络,她们频频出入商场、餐馆、戏院、影院、游乐场、舞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便利了生活,丰富了人生,享受着闺阁以外的精彩世界。
伴随着电话通讯的推广,民国城市女性与外界的沟通频率增加,社会角色的转变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逐渐加快。这也引起了部分人士对电话的怨愤。最富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张世昭。学问、能力、家世都非常不错的张先生,娶了一位“妇女界的美人”“交际界的名花”“文艺界的诗人”“时装表演会冠军”“张太太既喜欢交男朋友,男朋友又喜欢来找张太太,外边来的电话,十回有九回是找张太太,不是找张先生的”。起初张先生还为张太太在社会上所受的欢迎而骄傲,后来,张太太的电话越来越多,应酬越来越多,张先生逐渐由不高兴发展到暴怒。[13]表面上,此位张世昭先生不满意的是原有的正常家庭生活被频繁的电话通讯打扰和破坏,根本问题在于女性社会角色在过渡时期从旧到新的转变,引起了男性社会的不满。电话通讯充当了此种转变的桥梁,成为人们憎恶的对象。
电话通讯密切了女性与外界的联系,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也使传统女性形象遭到颠覆。男权社会在复杂矛盾的心情下,既期待女性的蜕变,又害怕女性的新生。张先生先是得意于夫人众多女性新称谓,但因日常生活中妻子的社交日渐频繁,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民国城市女性社会角色的再塑同时伴随着女性自身的心理蜕变和男权社会的心理调试。
三、身影展现
民国城市女性社会角色的再塑,建立在其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果能如此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失了”。[14]经济地位的改变关键在于职业获取。“女子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经济既能独立,虽不说社交公开,自然会社交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15]电话通讯的发展使得人工接线需求日益增多。由于女性具有先天优势,电话接线生渐渐由年轻、有知识的女性来担任。据统计,其人数还不在少量。女接线生这一新式职业女性群体的产生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层级,传统女性走出家庭,成为社会的主体。
电话通讯的问世和推广,“催生出第一批女白领——电话接线小姐”,她们“堪为新女性楷模”,“从事的绝对是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行业”[16]。女电话接线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电话局和电话公司工作,由于女性更加细心且易于管理,20世纪20年代,近代上海华租两界电话经营机构开始选用女性替代男性从事电话接线的工作;一种是在大百货公司、旅馆、饭店、银行及其他规模较大的机关或公司工作,此类机构“只装了一部总机,各部再分若干分机”,业务繁忙,需要专门的接线人员代为接听,“女子大都是比较男子来得娴静与细心,所以接线几乎都是女性的”[17]。通过电话接线生,普通市民还可以享受天气预报、标准时间、电话号码等信息服务。仅以报时一项业务而言,平日电话公司十几个接线生最忙的时候,每一分钟需要应答两次,夜晚也会有三名接线生值班。[18]22人数最多时,仅上海电话公司一家就拥有女接线生400余人。
女接线生经济独立、收入可观、衣着时髦,在妇女职业中地位较高。工作“每天分为三班,每班八小时工作,逢早、夜班均用汽车接送”,“待遇较任何女子职业为佳”。一说电话局所女接线生“月计45元,较之每月10余元收入之小学教员,有天壤之别”[19];另一说法,每月可拿底薪30元,其他还有生活津贴、米贴等,工资“总和可以相当于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20]。大型公司写字间中听电话者月薪60—90元,比较之下,“旧式商店中职员月薪约30元,一般店员约10—20元”[21]254。她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一般具有中学以上的文凭。据说当时在中西女塾及圣玛利亚的高材生均寻着门路来做接线生。在正式派定工作前,均要通过重重考核。她们工作时不仅需要动作敏捷,还得熟悉各地方方言,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懂日语,才能胜任,因为当时的电话户主中,外地人和外侨占据相当比例。[22]247
女接线生这一新式职业,自诞生起就被作为传统家庭妇女形象——贤妻良母的对立面来看待。民国城市女性外出工作,抛却男性附庸的传统形象包袱,需要冲破重重障碍,最为直接的阻力来自家庭和社会。如近代报告文学塑造的李美珍等女接线生便是怀抱“一颗纯洁的服务社会的心”走上工作岗位,但同时面临“女子的最好职业是出嫁”的传统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困扰。[18]25—37对于女性自身而言,“女子走出家庭,谋求经济独立,减弱了女子对于男子的依赖心,改变了女子被封锁于家庭、事事服从于男子的不平等状况,扩大了女子的眼界,发展了女子的个性,提高了女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23]。女接线生促进了家庭、婚姻观念的变革,冲击着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
一般上海人对女子“抛头露面出去外头混”抱有偏见,对于女性做电话生,“更加不满,怕给人家笑话”,说她们做“电话听筒”。女接线生们自己“固然是为了生活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逃避家庭中的烦恼”,追求自由的生活。对于此类新式女性,当时开放媒体评价为“努力向上为她自己前途而奋斗的女孩子”[24]。1933年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无声电影《三个摩登女郎》,除了大明星和追星族两名陪衬女郎外,主角摩登女郎便是阮玲玉饰演的电话接线生周淑贞。电影讲述了周淑贞如何历经磨练,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故事。[25]1287民国女电话接线生作为都市新女性的典型代表,是时代进步和思想解放的代言人。电话通讯事业的发展,在促使传统女性由贤妻良母到个体人、再到女国民的角色转变,达到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直至投身革命活动及其他政治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四、余论
电话通讯再塑了民国城市女性的社会角色,在促使她们加强与外界联系、走出深闺、走向独立自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电话线路的延伸,创造了相对而言较为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便于城市女性挣脱世俗观念的束缚,扭转传统社会角色的定位。电话与书报、邮信筒、照相机等一样,均是现代生活用品。女性与之发生关联,表明女性开始介入现代生活,真正突破高墙深院的限制,走向庭院、街市乃至郊外等更广阔的公共空间。
传统女性只有在 “声音”上率先突破自我,向外界发声,才有可能进一步做到“身体”上开始走出家庭,活动区域和社交范围才能不断扩展。早在民初,新文化运动先驱杨潮声等人就曾呼吁社交公开,“我们人类在上古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礼教不礼教,就没有什么男女问题。自从有了礼教这两个字,那么男女有起了界域了!有起了礼防了!男女交际秘密起来了!男女的情感变得不可以对人说的了!”[26]439—440。思想观念更新和社会大众倡导之下,民国城市公共空间开始有了新女性的活动踪迹,“最近十年以前,沪地途行之女子,仅属下流社会中人。彼驾车静安寺路者,多蔽以帷幔焉。今则上等妇女,仰首独行,赴肆购物,所在皆是。”[27]12电话通讯使社会氛围更加趋于开放和自由,女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社会狭窄的时空范围之内。电话通讯为女性实现自我突破提供了动力。
民国城市女性通过电话通讯这一媒介,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民国各个电话经营单位,大力宣传电话广告,尤其从1930年开始,电话广告开始大量地针对女性,将之作为潜在的大众消费群体。通过报刊广告,勾勒出一幅幅城市女性使用电话的场景:女性舒适地躺在床上接打电话,女性悠闲地坐在餐桌旁一边喝茶一边拨打电话,家庭妇女通过电话联系医生、救火会、巡捕房等,拨打电话联系朋友约会打牌,等等。
当然,民国城市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女性独立走向外界的过程中必然衍生出许多新问题,如由于电话线路的延伸,致使一些“洋场恶少”可以通过电话轻薄、骚扰女性等。女性做到真正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也要建立在女性内心真正强大的前提之下。
[1] (美)理查德5谢弗.社会学与生活[M].刘鹤群,房智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2]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40年辑)[Z].编者印,1940.
[3]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6册)[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4] 杜伯超.电话中小问题[N].申报,1924- 5- 21(18).
[5] 进留云僧.解决电话中的小问题[N].申报,1924- 5- 23(18).
[6] 电话观[N].申报本埠增刊,1925- 6- 8(1—2).
[7] Shanghai Telephone Company. Federal INC.U.S.A. Business Report( 1945—1949).上海市档案馆,Q5- 3- 5268,Q5- 3- 5269.
[8] 张健.老电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 家有电话,春雨夏日秋风冬雪都不怕[N].申报本埠增刊,1934- 10- 28(6).
[10] 韩德卿.电话与家庭生活[J].上海电话公司杂志.1934,(1).上海图书馆,J- 0920.
[11] 徐永焕.江西路畔牢骚声[J].上海电话公司杂志.1934,(2).上海图书馆,J- 0920.
[12] 吴福辉.茅盾代表作(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3] 电话[J].论语,1937,(113).
[14] 李达.女子解放论文[J].解放与改造,1919,(3).
[15] 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J].妇女杂志,1921- 7- 8.
[16] 程乃珊.趣谈电话[N].上海新闻晚报,2010- 9- 11(13).
[17] 柯洛.女接线生素描[J].新上海,1946,(35).
[18] 王韦.电话接线生.上海内幕[A].孙燕京,张研.民国史料丛刊(696)[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19] 铁儿.地位崇高之妇女职业[J].上海特写,1946,(8).
[20] 林玉.电话公司的接线生[J].海涛,1946,(35).
[21]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2] 霍慧新.上海电话事业研究(1882—1949)[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23] 徐胜萍.五四时期中国妇女地位的变迁[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
[24] 电话事件[J].银行通讯,1948,(54).
[25] 王荣华.上海大辞典(中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6] 杨潮声.男女社交公开[J].新青年,1919- 6- 4.
[27] 润石.中华妇女界之新气象[J].妇女杂志,1916- 2-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