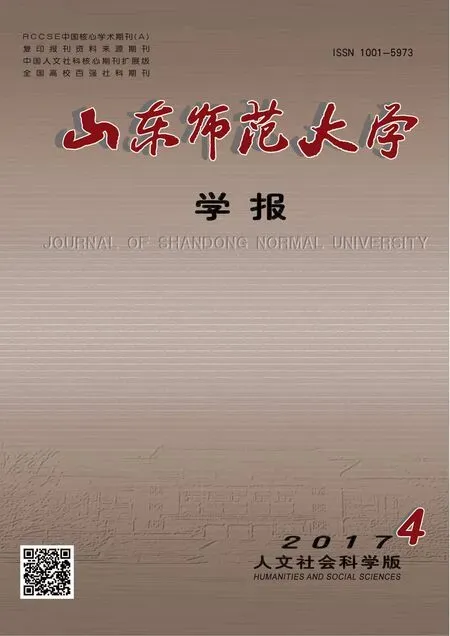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
——为纪念文学革命百周年而作*
朱德发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
——为纪念文学革命百周年而作*
朱德发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胡适立志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他对“白话利器”的本身意义与功能机制的评述,达到了中国语言史和文学史的空前认识高度。胡适认为,只要抓住“白话”这个新文学运动的总开关,就能创造一流的国语文学和标准化的国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白话的活文学,也复兴了平民文学及科学精神与人文传统。实际上,“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当然,胡适有些见解和判断也有绝对化倾向。
胡适;新文学运动;白话利器;国语文学;“中国文艺复兴”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4.001
百年前发生于中华神州大地的五四文学革命,胡适既是首举义旗、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又是登坛点将、呼风唤雨的总策划;既是“为大华造新文学”的设计师,又是建构白话文学样态的实验家;既是新文学运动的亲身感受者,又是白话文学的审美体验者。由于胡适的这种特殊角色与地位,故其终生不忘倡导和营造新文学的初心与矢志,竭力捍卫白话文学,竭诚评估白话文学,使白话文学成为其生命价值的根基。有的学者认为:“文学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它底成功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是非留待后人评!’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后人’,才能作‘盖棺之论’。”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0页。此论不无道理。然而,胡适并非一般的文学革命家,而是集多种身份于一身,故其对新文学运动价值意义或功败得失的评估既标新立异又求真务实,是别开生面。
一
胡适立誓以“白话利器”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他对“白话”本身意义和功能机制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中国语言史和文学史上的空前高度。不论从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系统考之,还是从个案文学构成察之,“白话”作为文字形式或文学工具都是建构一部活文学史或活文学文本的关键一环。也就是说,白话利器的运作决定着活文学史结构系统的形成或新文学文本的结构形体的铸就,否则,既没有文学史上的活文学也没有文学革命的活文学。正如胡适所深刻感悟到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我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活力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递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②《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且不评论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理解是否正确,至少他对活工具即白话之于活文学史或活文学的建构所产生的决定性功能作用的强调,足以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即使在新文学运动历经百年后的今天,也值得21世纪的文学创造者深刻反思。胡适曾在1916年二、三月之际把这种对中国文学问题的认识视为其“智慧上的变迁”,并提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2页。基于此文学观念,胡适在1916年7月6日的日记中,“很确切地表达了我(指胡适)对策动中国文学革命的中心思想”: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当然啦,现在我也了解,所谓“俗vulgar”,其简单的意义便是通俗,也就是能够深入群众。它和“俗民folk”一字,在文学上是同源的)。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语言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
(五)凡文言文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文未必能及之。
(六)白话并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文言文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
1.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2.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例如“舜何人也”变为“舜是什么人”。]我并且举出文法上的变化。多少年后我又特别的写了一篇论文,来讨论[中国]文法的演变。
3.文法由繁趋简。由中古文言的多种文法构造,逐渐简化。例如人称代名词之逐渐简化。
4.文言文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例如文言只能说“此乃吾儿之书”,但不能说“这书是我儿子的”。]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歌曲、诗词。
(八)以白话小说、故事、戏曲为代表的活文学,可能是中国近千年来唯一真有文学价值的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科举专用的八股、笔记等等,在世界文学标准中,皆不足与于第一流世界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必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决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半死的文字决不能产生第一流的文学也。*《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3-304页。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述原文,旨在说明胡适对白话之于一流文学建构的功能意义,认识得如此充分,推崇得如此高。他是对中国文学的语言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并且将白话与文言从能否营造一流文学的美学高度作了具体细微的比较,从而获得了“白话作为工具必能造出一流文学”的理性自觉与实践自信,所以发出了“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的坚定的豪迈的文学革命誓言。可见,胡适并非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而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乃是切切实实地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汉文学白话传统来创构足以进入一流世界文学之林的国语文学。
既然白话作为工具对于营造新文学具有决定意义,那么作为白话文学总设计师的胡适必然要回答“何为白话?”这个既简单又奥秘的问题。也许今天看来胡适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不过在当时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意义:“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胡适:《答钱玄同书》,《新青年》1928年1月15日第4卷第1号。这三个对白话的判断,是选取三个不同角度来释义的:一是艺术的角度以突现戏台上说白的“白话”既含诗性又含个性;二是人格的角度以彰显白话的纯洁性;三是色彩学角度以呈现白话的明晰性。若说这样的白话释义尚不具体,有点抽象,那么胡适把《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学经典都作为“模范的白话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便很形象和具体了,既可以学习又可以传承。虽然这些经典文本的白话是富有诗性特征与个性色彩的艺术语言,切合创造新文学的审美诉求,但它们并非那种纯净通俗的白话,乃是夹杂着不少文言字眼的白话。可见,胡适对现代白话文学构造的“白话”要求并不十分严格,这不仅使新文学的营造有丰富的可选择的语言资源,而且也能使中国传统文学的语言工具更多地被激活、被传承,让古今文学在语言这个关键环节上有机地对接起来;同时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没有以否定传统文学为前提,而是巧妙地以白话为桥梁把古代文学转移到现代文学的轨道上来。
胡适从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以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9-20页。出于对白话这种文学利器的高度重视和理性自觉,胡适把“白话”作为撬动文学革命或语言变革的总开关,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并付诸大胆而创新的实验主义行动,以实际上取得的效果来证明各种文化思想方案的巨大意义。
一是由语言工具的变革牵动各种文体的大解放。虽然文体是文学的整体审美形式或者是有意味的形式,但是文体形式的构成是否是别具一格的新形态,是否具有诗性的审美特征,是否严密完美,重在语言工具机制的卓有成效作用。从这种特定意义上说,语言的革新意味着文体的大解放,文体的大解放也意味着语言的大变革。然而在各种文体大解放过程中,阻力最大难度最大的却是诗体大解放;而诗体解放的难点与阻力重要不在格律音韵上,仍在“作诗如作文”,即白话能否做诗,白话工具能否成为创作新诗的利器。所以,胡适倡导文体大解放先从诗歌入手,除自己亲手尝试以白话作诗,并率领《新青年》派的文学革命先驱们同心协力尝试写作白话诗。“自古成功在尝试。”尽管初步尝试只是取得小成功,创造了胡适体的白话诗,然而这小小的成功既攻克了文学革命的桥头堡,为白话文学运动扫平了道路,又给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打开了通途,为文体大解放创立了范式。由诗体的解放带动了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解放,不仅各具特色的白话取代了文言,而且各种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新文体也在赓续传统文体的基础上来了个文学形态的大换班,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整体转型。从此,白话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时代文体”,并通过新文学运动推出了鲁迅这位擅长于创造白话小说新形式的高手和屹立于现代文学高峰的巨匠。可以毫不夸饰地说,是白话时代文体的创建彰显了鲁迅能够成为伟大文学家的卓越艺术才华,又是鲁迅这位伟大文学家营构的超群的时代文体显示了白话文学运动的骄人实绩。试想一下,周氏兄弟在1909年便以文言翻译出《域外小说集》,而这本小说集10年内仅卖出20本,胡适称此小说集是“古文学末期”的“最高的作品”;假如鲁迅仍坚持以文言翻译或创作小说,其日后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1918年起,鲁迅却遵循“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将令,毅然决然地创作白话小说。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足以证明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形成的时势,造就了鲁迅这位五四新文学阵线的顶天立地的民族文化英雄和光芒四射而照亮寰宇的艺术明星。当然,鲁迅戏称自己写的是“遵命文学”,但这绝对不是盲从和奴从,而完全是建立在他对白话文的理性自觉意识上。因为鲁迅深切认识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文言文的僵死导致中国人处于既聋且哑的“无声的中国”;恰恰是胡适提倡的白话国语运动使“无声的中国”恢复到“有声的中国”。所以,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发誓要竭力捍卫白话:“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鲁迅对白话的坚定态度,正由于白话使鲁迅得以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鲁迅”;而且“整个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内涵与成功法宝正是由于她与白话文工具变革的血肉联系,白话是整个中国文化从旧的范式向新的范式转型的关键”*胡明:《胡适传论》(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31-332页。。难怪胡适一生中对“白话”之于文学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价值,总是念念不忘、反反复复地强调说:“中国的活文字(白话)本身的优点,足以促使运动成功;因为中国的语体文本身便是一种伟大而文法简捷的语文。”
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上转弯抹角的限制;也没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规则形式。这种语言可以无师自通。学习白话文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8页。
所以,“文学革命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便是那些传统小说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后来的讽刺十八世纪中国士子的小说《儒林外史》等名著已为它打下了坚固的基础”,“这些小说名著都是教授白话文的老师;都是使白话文标准化的促成者”。*《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微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7-328页。
二是白话利器的运作,既促使“文体的大解放”,初步解决了文学形式向现代的转型,又推动了文学内容的革新,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或平民主义等现代意识成了新文学的思想主魂。胡适不论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还是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学革命“四条”,都注重文学形式的变革和文学内容的变革,对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虽缺乏深刻的理解,但也揭示了文学革命既要革形式又要革内容的两者不可或缺的关系;即使强调文学形式特别是其中语言的变革是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也是为了先解决内容与形式这对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以带动内容随着形式的变革而变革,表面看这不符合内容决定形式的法则,实质上这是对形式特别是语言的相对独立性的尊重,是合乎辩证思维规律的。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其审美形式与审美内容在功能机制上难解难分。它的审美形式是含有审美内容的有意味形式,其审美内容之所以能呈现出来也是因为它附丽在相宜的审美形式上。所以,文学形式变革或者文学内容的变革都是互相牵动的,尤其是文学语言,它既是文学形式的艺术编码又是文学内容的表意符号,更是创作主体艺术思维的贴身伴侣,因而语言的变革能牵动文学整体结构系统的变革。因此,胡适坚定不移地主张“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胡适全集》(第1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对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则论析得更清楚:“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只有文学形式上解放了,才能充分表现“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新的思想,复杂的感情”,而那种僵化的文学形式或死文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故而,唯有“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方可创造出真正的新文学。*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双十节纪念专号”。虽然有人说胡适当年对文学形式特别是语言的改革谈得多,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性,而对文学内容改革谈得少且笼统,这是不争的史实;但是若全面考察一下并非完全如此,只要认真解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易卜生主义》,那就容易晓知新文学要表现的“新思想新精神”以及复杂的感情究竟所指或能指为何了。前文明确要求文学内容的革命应清除那种“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恐其早谢”的“亡国之哀音”,务必表现那种“奋发有为,服务报国”的积极向上的爱国情怀和进取精神;后文则借着介绍易卜生的剧作及政治思想,集中体现了胡适对新文学内容的要求:既要像易卜生那样以严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淋漓尽致地“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又要像易卜生那样通过文学作品无情地揭露旧“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的种种恶行,以唤醒人的主体意识;也要像易卜生那样通过塑造斯铎曼医生这样的典型形象来弘扬个性主义精神,为坚持真理敢于宣布:“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6月15日第4卷第6号。因为胡适对文学内容革新的要求与周作人同年写的《人的文学》所要求文学宣扬的以个人主义为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是相通的,所以胡适在总评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曾给出这样的概括:“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8页。胡适把五四新文学运动这两面旗帜都高高举起,然而举得最高最久的却是“活文学”这面旗帜,评价最高强调最多的也是后者;这是因为在胡适看来,“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实践和历史已证明,这一“断言”是可靠的亦是可信的。
三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文学革命的根本宗旨,揭示了“国语”与“文学”这两个系统的辩证关系,不仅将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自觉地以白话文学运动驱动国语运动,以国语运动助推白话文学运动;而且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双向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巨大张力,推动了中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向现代转型,实现语言工具的白话化和思想内容的现代化,同时大大促进中华民国统一国语的标准化,真正实现国语的白话化,有力地解决了当时有人提出的“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这一难题。不仅如此,由于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双向并重的推进,文学革命步伐不只加速了期刊报纸等媒体的白话化,也加速了教科书与教学语言的白话化。对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双向互动运动在实践中产生的巨大效果,胡适作为这场新文学运动的总设计师未曾料到:“当我在一九一六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得如此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6页。这应是由衷的满意的评价,就连当时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与廖仲恺也高度评价胡适策划的这场白话运动:“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4页。
二
若说上述胡适着重从国内古今文学或语言这两大系统张力关系中,具体而深切地评述并肯定了“白话利器”对于营构新文学、标准化国语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那么,胡适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以全球视野从比较角度来开掘衡估其价值和意义的,自觉地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世界文学对接,纳入现代学术的轨道而进行中西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胡适之所以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来命名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因为“那时在北大上学的一些很成熟的学生,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他们在几位北大教授的影响之下,组织了一个社团,发行了一份叫做《新潮》的学生杂志,这杂志的英文刊名叫‘Renaissance’(文艺复兴)。他们请我做新潮社的指导员。他们把这整个的运动叫做‘文艺复兴’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这一批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的北大学生,在几位青年教授的指导之下,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思考,他们显然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起的这个新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故“在其后的英语著述中,我总喜欢用‘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一题目”*《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5—336页。。这说明胡适把中国新文学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进行比较,既有深厚的情感记忆,又有清醒的理性认知。
其一,胡适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从新文学、新文艺、新科学和新宗教之诞生开始的,同时也促使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之形成;而中国五四时代崛起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虽然“未涉及艺术”,但却是“一项对一千多年来所逐渐发展的白话故事、小说、戏剧、歌曲等等活文学之提倡和复兴的有意识的认可”,“这实在是彻头彻尾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5—336页。。于是,胡适便从白话语言、平民文学、人文精神等相互关联的多维度考察并辨识了“中国文艺复兴”的丰富内涵及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有意识的传承与新生。
首先是对白话语言的复兴与传承。所谓“白话”,“是我们老祖宗的话,是几千年来慢慢演变一直到今天还活在我们嘴里的话。这是活的语言,是人人说的话:你说的话,我说的话,大家说的话,我们做小孩子都说的话”,乃至全国大部地区“每一个人所说的话,都是白话”。比起欧洲许多文明国家的语言,“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这个语言——活的国语,以及我们国语的文法,是全世界最简明,最合逻辑,最容易学习,最了不起的语言。英国语在欧洲文字当中,是比较进化的。但在世界语言当中,中国话要考第一,英国语要考‘不及格的’第二,因为没有别的话可有第二的资格的。至于学过法文或德文的,以及学过拉丁或希腊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些文字,根本不合理”。由于汉语的白话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功能,不仅最简单也最易懂,“只要认得一两千个字,就很可以看小说,看书”,而且白话是营造新文学或国语文学的唯一利器,亦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话语系统、最丰盈的语言遗产。这是我们老祖宗遗留的珍贵资本。“我们之所以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就因为我们老祖宗有了这样的资本,到这个时候给我们来用,要由我们来复兴它。”胡适曾深沉地回忆,在“五四”运动的当年,并没有借助“一个政府的大规模的力量”,“我们完全是私人、个人、无权、无势、无钱的作家,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叫‘白话’:写白话,用白话做文学。实在说起来这两个字就是‘白话’,要说的详细一点可以用五个字,叫着‘汉字写白话’”。然而,“用汉字写白话这个方法,并不是我个人发明的,也不是我们几个人发明的,还是我们老祖宗在实际需要中想出来的。他们把文言里的汉字充分地采用来,写他们创造的活文学。碰到没有某个字的时候,就另外去借一个字,或者干脆另造一个字。例如这个的‘这’字,从前用之乎者也的‘者’字来讲,或者用遮盖的‘遮’字来讲,后来才用一个‘言’加一个‘走之’。你要查查字典看,康熙字典上那个字不读‘这个’的ㄓㄜ。老百姓的话就是权威,管它字典是怎么说,老百姓说它是这个的‘这’字,几百年来就一直用这个字”*胡适:《活的语言·活的文学》,《中国语文》(台北)1958年8月第3卷第2期。。胡适对于历史上老祖宗“用汉字写白话”所创造的“活的语言”传统,并没有数典忘祖以不孝子孙的姿态彻底反之,乃是竭尽全力来复兴并传承白话传统,并借助五四文学革命的合力完成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正宗地位的使命。
其二,是对老祖宗创造的“活的文学”的复兴与承传。这是因为“老祖宗用汉字写的话的结果,留给我们这么多的短篇小说,好的长篇小说”,而这些好的长短篇小说流行了几百年则成了标准的模范的白话文学;尤其可取的是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胡适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也可以说是两条路线。一个是上层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而上层的文学是贵族文学,文人的文学,其中大部分是毫无价值的模仿的文学,是没有生气的死的文学;与之相对的是无论那个时代都有的下层文学,而下层文学就其实质来说就是民间文学,老百姓的文学,用白话写的文学,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活的文学。例如,《今古奇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小说,都是先在民间由老百姓讲故事流传下来的,到后来才经过无数的人或无数的无名作家的反复打磨和修改,方有久传不衰的白话定本。面对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白话文学,“我们(指胡适等文学革命首倡者)当初有一个基本不同的看法,就是大学教授们号称为学者,都是从古文里打了跟斗出来,从古文里洗了澡出来,在古文里面都站得住了,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地位了,我们愿意放弃这一种古文,采用老百姓活的文学,这是我们所谓‘革命’;其实并不是革命,还是‘文艺复兴’”。这由于“我们的资本——这个语言的资本,是我们几万万人说的语言,是我们文学的资本,文学的范本,文学的基础。是几百年来,一千年来,老百姓改来改去,越改越好,这些名著这些伟大的小说做了我们的资本。所以说‘文学复兴’,正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材料,给我们的基础。我们老祖宗已经做的事,我们来加以提倡,我们来学他们的样子,替他们发扬光大,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吗”*胡适:《活的语言·活的文学》,《中国语文》(台北)1958年8月第3卷第2期。?这不仅表明五四时期倡导并创造白话文学是地道的“文艺复兴”,而且也呈现出白话文学创造主体的鲜明的平民主义立场和为广大民众营构新文学的诚挚感情。不过,在胡适的价值视野里,新文学运动的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揭示了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死文学”的必然性,“白话文学是起来替古文发丧的,下讣文的”,也是历史规律决定的;这是因为“二千年中之白话文学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什么人也不能否认”,而“中国将来之一切著作,切应当用白话去作”这也是大势所趋,所以“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白话文学之趋势,在二千年来是继续不断的,我们运动的人,不过是把二千年之趋势,把由自然变化之路,加上了人工,使得快点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我们对之,应当表示相当的尊敬”。对于文学家来说,“如果尊重新文学,要努力,修养,要有深刻的观察,深刻的经验,高尚的见解,具此种种去创造新文学,才不致玷辱新文学”*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晨报·副镌》1925年10月10日。。
其三,是对平民文学的复兴与再造。实质上,老祖宗以活的白话语言创造的“活文学”也是平民文学,胡适不只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要复兴历史上的有别于庙堂文学或贵族文学的平民文学,而且要再造富有时代特色的平民文学,这无疑导致中国文学在性质上发生变化,即舍弃了古代贵族文学而复兴了平民文学。胡适书写的《国语文学史》*胡适:《国语文学史》,《胡适全集》(第1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页。发现了中国古代文学逮及汉朝大定了“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于是,胡适便从2000多年的古代文学中梳理出平民文学或田野文学与贵族文学或庙堂文学两条线索,也总结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学传统,对平民文学或贵族文学从对象主体与阅读主体两个维面考察其各自的思想艺术特征,从而对平民文学做了充分肯定,也就是肯定了平民文学的优秀传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所创建的现代平民文学提供了美学资源。五四时期是平民主义思潮奔腾的时代,其影响既深且广。正如茅盾当时所指出的,文学先驱们“积极的责任是欲把德谟克拉西(平民主义)充满在文学界,使文学成为社会化,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的文学精神。下一个字是为人类呼吁的,不是供贵族阶级赏玩的;是‘血’与‘泪’写成的,不是‘浓情’和‘艳意’做成的,是人类中少不得的文章,不是茶余酒后消遣的东西”*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920年1月10日第17卷第1期。。周作人则公开提倡与贵族文学相对的平民文学,而“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1月19日第5号。而这种平民文学则是以平民主义为主魂。胡适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所发现的平民文学与五四时期提倡的平民文学发生了对接与交融,不仅能使传统的平民文学得到复兴,也能使五四时期创造的平民文学将现代性与民族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体现出中国文艺复兴所建构的新文学的平民特质,即不是复兴中国古代的贵族文学或庙堂文学,而是复兴内蕴平民主义或人道主义精神的平民文学。因而,胡适一方面指出平民百姓从劳苦中不断地创作出新花样的文学来,所谓“劳苦功高”,实在使我们佩服;另一方面赞赏“有些古人高尚作家不受利欲熏诱,本艺术情感之冲动,忍不住美的文学之激荡,具脱俗,牺牲之精神。如施耐庵、曹雪芹之流,更应使我们欣佩。因为老百姓的作品,见解不深,描写不佳,暴露许多弱点,实赖此流一等作家完成之也”*胡适:《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看法》,《晨报》1932年12月23日。。
通过上述的白话语言、活文学、平民文学三个互联互通维面上的“中国文艺复兴”意义的考察与论析,表明“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使命已初步告成。然而,作为新文学运动领袖的胡适仍有意味深长的诫言,即使对于21世纪当下的中国作家也有深刻的启迪与警示意义:
从“五四”到现在,已经有许多诗人,小说家,创造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这是很可欣慰的。但也有一些诗人,小说家,当他们的创作热过去了,文人的老脾气又来了,重新回过头来走模仿的路子。不但没有进步,而且一天天堕落了。他们只在那里玩弄技巧,忘记了生活,忘记了时代,忘记了艺术;所写的东西,变成文人的玩意儿。文学僵化了,变成化石,文学的生命也就死了。这些人不但对不起我们的语言,不但对不起我们的文学,更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
我们今天不能再模仿古文了,不能再走回头路子了!我们要在已有的文学基础之上,运用活的语言,创造活的文学,创造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文学,然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才会有蓬勃的发展。*《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4页。
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创造了一种回溯式的所谓“古为今用、古今贯通”的思维模式,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人文学术传统来建构现代学术文化系统;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对传统的学术思想也要持批判的态度”*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亦采取“古今联通、古为今用”的回溯式的思维模式,使古代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仅得以继承也能为解放中国人的思想或个性和建构新文化或新文学形态提供用之不竭的资源,这便与欧洲文艺复兴有了趋同性或相通性。
通过回溯古代文化,胡适不但发现了1000多年的白话文学传统,而且发现“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旨在文体的变革,并以此展现出文学的演化规律。“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胡适:《〈尝试集〉自序》,《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不仅韵文通过“革命”是如此演化的,“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议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也。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及何晏,王弼诸人说理之作,都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巨子不仅韩氏一人,初唐之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诗中如李杜韩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胡适:《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胡适全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对于文体或诗体的演变,胡适都视为“文学革命”的观点,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革命”的涵义是有差异的;不过胡适始终认可文学革命有两种互为关联的方式,即文学的自然进化是“文学革命”,文学由人力推动发展也是“文学革命”,如晚清与五四的文学变革都是人力推动的文学革命。在我看来,胡适从中国古代文学演化的史迹中发现的“文学革命”的两种方式,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革命”概念,乃是从丰富的文学史实中总结出来的,是真实可信的文学发展规律,又是有利于文学演变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法则;况且把文学革命定格在文体上或诗体上,这应是独到之见。五四新文学运动首先从诗体革命入手,推动文体大解放,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则创造出一代新文体或新诗体取代了各种传统文体,这也是中国文艺复兴在文学形态上的体现。
中国文艺复兴时期不论新文学样态体现出科学精神或者学术研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还是中国人思想解放所借助的科学人生观,既有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崛起的科学文化潮流的汲取,又有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发掘出的科学的新逻辑、新方法。胡适在《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一文中,把“现代中国”这个概念已提到1000多年前的北宋初期,其主要根据是那时的“道学先生”或“理学家”运用了科学方法来“反抗中古的宗教,和打倒那支配中国思想历时千年之久的佛教和一切洋教”,他们力图“把被倒转的东西再倒转过来,他们披心沥血的来恢复佛教东传以前的中国文化、思想和制度,这便是他们的目标”。于是,他们“便在儒家的一本小书《大学》里面,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在这项从公元第十一世纪便开始的中国文艺复兴里,他们在寻找一个方法和一种逻辑”。这就是培根所说的“新工具”,也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提倡的“方法论”。而“‘现代’的中国哲学家要寻找一种新逻辑、新方法,他们居然在这本只有一千七百字的小书里找到了”。《大学》里有一句从无解释的话“格物”,即“致知在格物”:“格物”这两个字虽然历代解经的学者提出50多条的不同解释,但是其中最令人折服的一家,胡适认为是11世纪的“二程”(程颢和程颐)及12世纪的哲学家朱熹。他们解释“格物”是:“‘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程颐认为“物”无所不包,大及天地之高厚,小至一草一木,皆为“物”;“致知在格物”就是把知识延伸到无限,这便是科学了。在这场“新儒学”(理学)运动中,对于“道德、知识”这两段思潮,最好的表达则是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理学”的真谛,此一语足以道破。“中世纪那种出世的人生观,就是要人不要做人,去做个长生不老的罗汉或菩萨。一个人要去‘舍身’,或焚一指一臂,甚或自焚其身,为鬼神作牺牲——这就是‘中古期’!”而“整个‘现代’阶段”就是以科学方法或科学思维对这种中古的鬼神观念进行反抗,“所以‘现代’的哲学家都是一些叛徒或造反专家”。总之,“这批道学先生和理学家”所开展的“这场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一桩有心推动的运动。它是半有心、半无心地发展出来的”*胡适:《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9-444页。。我们可以不同意胡适的把“现代中国”提前到北宋初期,但是却不能不尊重这是一家之说;而判定是否是“现代中国”,则是以科学方法批判中古神学思想而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如果胡适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文艺复兴提早了近300年,中国的现代化也应起步于北宋初期;这不仅使现代中国历史的起讫要重新考虑,而且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和文学史似乎也要重写了。这些问题有待以后研究,现在要探讨的是宋明理学家从儒家经典《大学》里发现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而梁启超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也是以科学方法或科学精神为根据判定清学200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则认为“程朱的归纳手续,经过陆、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转机。解放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胡适:《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0页。。五四时期的中国文艺复兴承传古代文化中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西方的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相融合,掀起了巨大的空前的科学潮流,波及各个领域。波及文化领域,“科学”成了解放中国人思想的强大精神武器;波及文学领域,“科学”使新文学创作增强了崇实求真的美学品格。若说宋初的中国文艺复兴是半心半意地发展起来的话,那么五四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是文化先驱们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发动的,其规模、其声势、其影响深广、其取得的文化艺术成就都是空前的,是宋初的文艺复兴无法比拟的。试问,这条绵延近千年的中国文艺复兴风景线,能够成为“信史”吗?
无论欧洲文艺复兴或者中国文艺复兴都不能没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质的规定性,而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若说周作人《人的文学》所谈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它来源于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并错误地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从未讲人道、讲人意;那么胡适的人道主义除了来源于欧美的人文主义思潮,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发现。他在《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中明言:“‘自由’这个意义,这个理想,‘自由’可说是一个倒转语法,可把它倒转回来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压迫的意思。”必须强调的是,“自由”是人文主义的核心范畴,因为人文主义对人来说最关注的是个性解放或主体意识觉醒,若是没有自由就根本没有人的解放,也没有人的独立自主的选择和追求,更没有人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理想境界,一言以蔽之,人失去自由就会变成奴隶或奴才或工具或器械,异化为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所以人文主义之于人的思想解放的最高目标则是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己作主”的自由在中国文化里已然形成了“传统”;若说“世界的自由主义运动也就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那么我国“二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与三千多年所记载的历史,对于自由这种权力,自由这种意义,也可以说明中国人对于自由的崇拜,与这种意义的推动”。特别是“中国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批评政府自由,在历史上都有记载”。中国思想界的先锋老子与孔子,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思想,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是孟子给读书人一种宝贵的自由主义精神;春秋时代“自由”的思想与精神比较发达,而秦朝统一后思想独尊儒术则限制了自由,不过王充的《论衡》、范缜的《神灭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原道》,以及王学左派、颜李学派,都体现出一种自由主义精神。总之,“我们老祖宗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由的传统”*胡适:《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全集》(第1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03-607页。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思想遗产,我们后来者既要承传又要弘扬;而五四时期的中国文艺复兴不仅在中国人的思想或人性解放过程中贯彻自由主义思想,而且新文学创建更体现出自由主义意识,尤其胡适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终其一生像崇尚热爱科学一样地崇拜热爱自由,并为之付诸实践奋斗了一生,不愧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旗手和闯将。*朱德发:《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四章。
三
胡适以纵横交错的思维范式和中外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具体而详细地考察分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给出了“白话”是唯一利器、白话文学是中国正宗文学、新文化运动乃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评估;由于史实根据的充分又言之成理,令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诚服。然而,若能对胡适的有关新文化或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的判断或评估深思之熟虑之,就会发现有不少绝对化的判断或不准确不妥贴的提法,既缺乏历史根据、事实支撑,又不符合思想逻辑,经不住推敲,也经不住实践检验。例如,说什么唯有白话才能生产活文学,文言是死文字只能产生死文学;文学史上老百姓创造的是活文学,文人只能制造死文学;“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等等。这些价值判断固然突显了白话国语或国语文学的重要意义;但并不辩证,有些绝对,说得太满太过,不是科学的可信的理论判断。就连费心劳力编译《胡适口述自传》的美籍华人唐德刚也没有为贤者讳,曾对胡适所说的“文言文已经‘全死’;它绝对不可与白话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并存’”的“假设”给予有力的“证实”:
这句话是当时欧美留学生以夷比夏、想当然耳的老说法,因为在欧洲古“希腊文”、“拉丁文”确已“全死”。那些古文字原是当年希腊、罗马“公民”和“士大夫”所通用的语言。可是后来希腊、罗马不但亡了国,甚至亡了社稷。代之而起的却是千百万入侵的“蛮夷”(现代西欧白人的老祖宗)。原先那小撮希腊、罗马的“公民”,早已自历史上烟消云散。入侵的蛮夷自有他们的蛮夷鴂舌之音。他们有一点希腊、拉丁字母就移了(现代越南、菲律宾还不是如此?)可是日子久了,方言进步了,够用了,他们也就不再用希腊、拉丁这些死文字的外国话(foreign language)了。
我国文言文是一种一脉相承,本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孔老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发了脾气,骂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人民骂那些该死不死,祸国殃民的老头子,用的还不是这一句吗?你说它是文言呢?还是白话呢?
……
总之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的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吸收他人之精华,剔除自己之糟粕,原是义无反顾的;但是我们断然不可,因为洋人怎样,我们一定也要怎样。*《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3-344页注②。
此“实证”可信且有说服力,至于笔者的有关质疑就不在此提出了,当下忧思困惑的则是另一些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性质或意义的流行甚广、影响甚远的有相当权威的说法或判断。
胡适对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述,即使存有不少的矛盾、不辩证、不确切之处,也难以撼动其总体估价的正确性、稳定性和科学性及其实证的丰赡性与可靠性。既然认同诚服了胡适的价值评估,那么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另一些评说是何以评说的呢?一是五四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等,乃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王瑶、李何林等草拟:《〈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新建设》1951年8月第4卷第4期。;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双重变奏*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引申出来,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5-19页。;三是“文学的现代化最内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实际上是现代意识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五四’文学革命的最大成果也正是在这方面”*许志英、邹恬:《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的,它与传统文化或文学发生了断层或断裂。如此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述所举四种说法在大陆的学术界已产生深刻影响,若要对其进行重新研讨或重新评估,至少应遵循这样的逻辑前提或学术规则:既要将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评估置于特定的历史范畴,又要坚持“拿证据来”的求真务实的认识路线。前者的特定历史范畴是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起讫时空,20世纪30年代中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赵家璧,认定五四新文学十年,从1917年至1927年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处的特定历史范畴;文学革命先驱茅盾于30年代初则认为,从1917至1921这五年间应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起讫的特定时空*茅盾说:“‘五四’这个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到后二年或三年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火烧赵家楼只能作为运动发展到实际政治问题,取了直接行动的斗争态变,然后也从此由顶点而趋于下降了。这样去理解‘五四’,方能把握‘五四’的真正的历史意义。”见《“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原载《前哨·文学导报》1931年8月第1卷第1期。,惟有在这个特定历史范畴来检讨或评估新文学运动方能理解并把握其真正意义。大多学者认同这两个“五四”特定历史范畴的划定,而胡适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价值意义的评估大致与茅盾所划定的时空相同。后者的“拿证据来”则是强调必须让原生史实说话,也就是说判定或评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价值意义的史实,既要源于“五四”这个特定历史区间的事实,绝对不能移用外于特定历史范畴的史实来替代或冒充,又不要依据某种“公式”或“教条”或“主义”或“思想”的需要而片面地随意地宰割和剪裁史实,应该从原生史实的全部总和与史实的整体联系中去把握史实选择史实,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说,“让史实说话”方可使史实胜于雄辩,方能使史实成为判断五四新文学运动意义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果有志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价值意义进行再发现再评估的学者,真正能遵循上述的学术规则,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给予探赜发微的洞察和求真务实的判断;那么不仅能破解对五四新文学性质意义的忧思困惑,也能将对五四新文学价值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更能从众说纷纭的比较中对胡适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述作出真切公允的评述。
责任编辑:李宗刚
Hu Shi’s Commen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4th New Literary Movement——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Zhu Def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Hu Shi determined to create a new literature for greater China, and commented on the meaning of “the sharp tool of the vernacular” itself and its function mechanism, reaching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ly by seizing the “vernacular”, the main switch of 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can a first-class Mandarin literature and standardized Mandarin be created. Hu Shi always affirmed that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and literary revolution were China’s movement of “Renaissance”, not only reviving the living literature of the vernacular, but also reviving the populace literature and the scientific spirit as well as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In fact, “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is China’s national movement”. Nevertheless, some of Hu Shi’s views are mainly his judgments, but also have a tendency of being absolute.
new literary movement; the sharp tool of the vernacular; Mandarin literature; “China’s Renaissance”
2017-06-15
朱德发(1935— ),男,山东蓬莱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I206.6
A
1001-5973(2017)04-0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