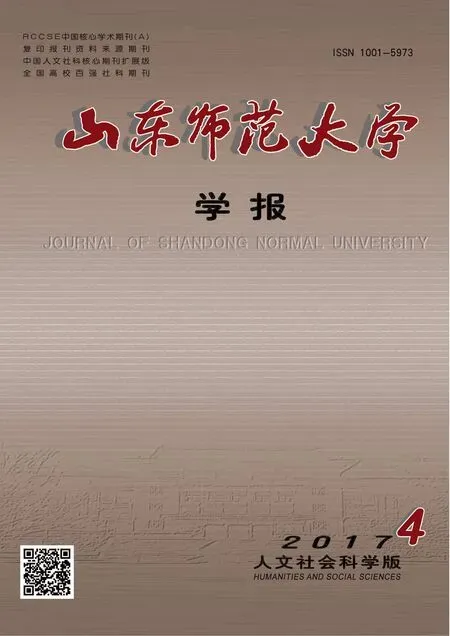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①
韩 琛
(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
竹内好鲁迅研究批判*①
韩 琛
(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
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契机,日本学者竹内好释放了对侵华战争的负疚感,并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表达自己对“大东亚战争”的拥护。在“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本陷入绝境的现状下,竹内好将鲁迅塑造为一个回心于“无”的绝对文学者,以此来否定“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文化,建构“文学的结构”的“大东亚文化”。战后,竹内好则从作为“大东亚战争”之“意识形态翼赞”的“近代的超克”论述里,发明了反近代主义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追求东亚主体性的反近代主义的近代,既是竹内好之始终未变的思想轴心,也是其根本悖论之所在,并形成了一种反人道的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实际上,文学主义的法西斯不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点,而且是20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这使今日世界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竹内好生发于“二战”时期的文学思想、政治思考和鲁迅研究,似乎印证了本雅明对法西斯美学的政治批判: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
竹内好;《鲁迅》;“大东亚战争”;近代的超克;作为方法的亚洲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4.004
1943年,在刚刚完成的著作《鲁迅》的“结束语”中,竹内好声称“我站在了我自己的‘终极之场’”②[日本]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43页。。这个对自身历史境况的描述,当然首先来自于《鲁迅》这本著作的完成③在《鲁迅》中,竹内好最后认为,“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在我看来,其著《鲁迅》的完成也意味着“文学者竹内好”的最后完成,“文学者竹内好”也是无限地生成出“其他竹内好”的终极之场。这个关于竹内好执著于其文学位置、文学的政治的判断,可以在贯穿竹内好一生的追求东亚主体的近代主义的抗争性、批判性姿态中获得不断确证。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42-145页。。实际上,《鲁迅》亦是一个本源性的“竹内好像”的自我完成,“文学者竹内好”通过发明“文学者鲁迅”,也抵达了自己的“终极之场”。在语言编织的以“无”为轴心的鲁迅想象④韩琛:《“无”鲁迅的竹内鲁迅》,《湘潭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中,竹内好彻底实现了自己。《鲁迅》的完成,让他既仿佛如释重负,也好像如临深渊。因为与此同时,竹内好恰恰也处于历史张力紧绷的“终极之场”中:伴随“大东亚战争”的不断深入,整个日本处于一种绝境般“终极体验”之中。故在战争期间,竹内好基于对“大东亚战争”的认同,通过解散中国研究会、废刊《中国文学》等行为,将“文学性的否定意志”实践于个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竹内好本人即将走向中国战场,以肉身性的而非思想性的“行为”——战争、杀戮和死亡,来亲身实践“为了活着而选择死亡”的自我否定哲学。其著《鲁迅》的写作对于身处历史的终极之场的竹内好来说,就是他所定义的那种具有绝对政治性的文学行为。“大东亚战争”亦当如是观。
一、“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
大致上,竹内好的著作《鲁迅》是写作主体处于一个极端自我膨胀、极端自我虚无化的矛盾状态下的产物。因此,对于鲁迅的肯定,不得不建立在否定鲁迅的基础上;而自我主体性的形成,也就不得不建立在不断自我否定的历程中。竹内好挣扎于自我与鲁迅、日本与中国、东洋与西洋、“支那”事变(侵华战争)与“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之间,并试图在挣扎抵抗中自我认同为一个本真性的、绝对性的历史主体,这既体现在《鲁迅》的写作上,也显现于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礼赞中。
竹内好趋于绝对主体性的姿态必然意味着,在通过自我否定完成自我建构之前,无论是鲁迅还是中国,作为外在的对象世界,在终极意义上都必须先被否定/超越。非如此,则不能形成一个完全向内辐射的绝对主体:“作为实际存在的支那的确存在于我之外,但是在我之外的支那是作为必须加以超越的支那存在于我之外的,在终极意义上,它不能不在我之内。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只有在这种对立对我而言是一种肉体的痛苦时,它才是真实的。这就是说,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8页。在这里,所谓“支那”(即中国)是作为“真我”之实现的媒介存在的,而不是应予承认的异我之主体而存在的。仅仅作为一个媒介或者方法存在的“支那”,在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主体构造完成之后,必将以转变为主体的内在者而从外在的世界中消逝。也就是说,主体之我的绝对自由,是建立在克服他者的基础上,没有作为对他者的“支那”的存在与否定,“我”以及日本的存在是不确定的。
将前述这段话——“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中的“支那”换成“鲁迅”,在竹内好那里,也是应该能够成立的。“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被否定,其实也意味着,鲁迅在终极意义上也必须被否定。回心至无的“竹内鲁迅”;也就是在这个终极意义上实现的——只有鲁迅成为无,“竹内鲁迅”才能成为一切。《鲁迅》通过超克鲁迅,而成就“竹内鲁迅”;“大东亚战争”通过对美国开战,就可以否定“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进而成就“大东亚圣战”以及“大东亚共荣圈”。《鲁迅》可以看作是竹内好想象性地建构“大东亚文化”的个人化尝试,这本著作是竹内好挣扎、回心*日语当中的“回心”这个词,来自英语的Conversion。除了原词所具有的转变、转化、改变等意思之外,一般特指基督教中忏悔过去的罪恶意识和生活,重新把心灵朝向对主的正确信仰。竹内好使用这个词,包含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觉或觉醒的意识。在竹内好的批判近代主义的文化视野中,与主体意识充盈的“回心”一词相对的,是无主体意识的“转向”。“回心”是回到原初的自我、第一自然,而“转向”则意味着自我的丧失与他者化。在竹内好战后的论述中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主体性的回心式近代,而日本的近代化则是无主体性的转向式近代。实际上,竹内好的“回心”说,极为类似尼采的“永恒的复归”(又译为“永恒的轮回”)说。海德格尔认为永恒的复归说中“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就是:永恒在瞬间中存在,瞬间不是稍纵即逝的东西,不是对一个旁观者来说仅仅疏忽而过的一霎那,而是将来与过去的碰撞”。在某个关键的瞬间作出个人的决断,从而把握住内在的最沉重和最本真的东西,往往实现在未来与过去的碰撞中。张旭东认为,鲁迅与尼采在“永恒的复归”的层面上具有相同之处,“‘改变方向’正是‘永恒的复归’要做的事情,即不断地把指向未来彼岸世界的时间的箭头拨回到‘过去’的方向,这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过去,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过去,即存在本身,即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意义,它的反面就是堕落和颓废”。竹内好的“回心”说也存在着这种朝向最高价值和最高意义回转的意思,从而在世俗主义的近代性实践中确立一种主体性的亚洲近代性价值,回心就是一种要在有意义、有价值、有尊严的存在中生活的信念。当然,回心也具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排他性倾向。不过我认为,内在的最高价值和最高意义诚然是“永恒的复归”的终极目的,但堕落和颓废等存在方式同样也并非完全负面,也不能排除于所谓最高的价值和意义之外,鲁迅及其文学实际上也常常显示出颓废、黑暗、虚无的一面,这也是人之存在的诸多“本真性意义”之一。鲁迅的文学“回心”抑或“永恒的复归”,其所蕴涵的沉重、本真的东西之中应该也包括“卑贱”如“阿Q”者、以及踯躅于罔两间的“女吊”们。参见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5页;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9-211页;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4页。、抵抗,进而想象一个超越一国一族之个别性文化的“大东亚文化”的思想凝结物。“竹内鲁迅”的“无”、“回心”、“挣扎”等概念的最终形成,可在竹内好之前关于“大东亚战争”的礼赞中见到端倪。意即,“竹内鲁迅”的发生来源于具体历史境遇中的个人体验,并与整个日本昭和时代的思想状况、时代精神和历史危机密切关联。竹内好的个人禀赋、成长历程,交织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对外扩张的冲动、重构世界史的野心,让“竹内鲁迅”最终产生于一个暴力与死亡、理智与狂热、酷烈现实与乌托邦想象彼此混杂交错、难分难解的极端的年代。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竹内好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等文中,表述了日本和自己在“1941年12月8日”——以突袭珍珠港为标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一刻,所生发出的“回心”般的狂喜。这种经由“自我否定”而回到绝对自我的主体意志,最后被投射到了《鲁迅》的写作中。“鲁迅”最终成为竹内好处理“大东亚战争”及其所隐含的“东洋的悲哀”——不能自主的近代化进程——的媒介。沟口雄三认为,“1941年12月这个瞬间,那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日本侵华战争扩大为大东亚战争,但这种扩大不仅仅是战争领域的量的扩大,还意味着战争发生质的转换,把日本推向以国家存亡为赌注的内外压力同时白热化的阶段。对于竹内好而言,适逢这一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拷问着他作为日本人应该具有的态度”,“通过《鲁迅》,他揭示了日本以欧洲为基准、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近代’,如何仅仅是出于主体缺席的肤浅状态;而这一揭示,却是一种扪心自问:他追问和抨击的,是自己和自己祖国的存在方式”*[日本]沟口雄三:《作为“态度”的中国研究》,《读书》2005年第4期。。所谓“质的转换”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美国开战导致了日本将自身陷于孤注一掷的极端境地;其二则是侵华的殖民战争被转换为帝国主义之间的霸权战争。然而,这场战争之争夺亚洲或世界霸权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无论其是欧洲基准的近代主义式的,还是亚洲主义的反近代的近代主义式的。不过,对于当时的许多日本知识者来说,他们的确需要一个契机,来缓解侵华战争造成的道义上的焦虑。
在谈及1941年12月8日的宣战诏书的时候,竹内好表现出极端文学化的浪漫主义亢奋。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一文的开始,他就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时间开始了”:“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日本]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5页。更为重要的是在后面的文字中,竹内好用“大东亚战争”的发生完成了自我否定,否定了自己由于“支那事变”带来的“道义的苛责”。因为“这样看来,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是无法忍受的事件”,“今日的我们基于对东亚解放战争的决意,重新否定了曾经自我否定了的自己。我们在双重否定之后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上”*[日本]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7页。。“支那”,也就是中国,成为日本否定之否定(肯定)自我的媒介,对美国宣战完成了对于侵略中国的道德救赎。侵略在瞬间变成抵抗,东亚殖民于是也就被转化为东亚解放。按照竹内好的逻辑,“大东亚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就是通过自我否定又回到自己的回心之举,而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来说就是脱离欧洲殖民的解放,外在他者的解放与内在主体的救赎在这里是二位一体。这就是竹内好所谓的“在终极意义上它必须在我之内”。那个必须在我之内的“它”,既可以是“支那中国”,也可以是“文学者鲁迅”。
与通过所谓反帝国主义的太平洋战争否定自我之帝国主义倾向,进而将自己置于抵抗西方近代主义的主体位置一样,竹内好通过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完成了对于非主体性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否定,并写下了主体性“宣言”——《〈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中国学者认为此文极为重要,它显示了竹内好在极端的历史状态中的“回心之轴”,并使他遭遇鲁迅:“在理解竹内好的文学立场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因为它正面表述了竹内好的‘回心之轴’,并把这回心之轴外化为真正的行为。从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到主张日本的自我否定,从鼓吹“大东亚战争”的理念到消解国民国家的框架,竹内好使他的文学性构造在1943年那个苦难的年头里附载于一个最费解的形态,这就是在战争这一凝聚和激化了现代性问题症结点的现代性事件的白热化阶段,竹内好试图将世界的哲学性构造转化为文学性构造。他试图把《鲁迅》所揭示的投入和挣扎于自我否定过程的文学精神,转变为处理现代性问题的最大能源。”*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48页。虽然竹内好在《鲁迅》中宣称文学是行动,不是观念,但是文学一旦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就丧失了文学之多元性、机能性、复杂性的内涵,而变成一种完全基于固有立场的政治性表达。文学之超政治的政治性因此也将荡然无存,不但无以抵抗现实政治的侵蚀,而且有与政治意识形态达成合谋的可能。因此,《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作为行为的文学”,而是以文学面目呈现的政治宣言,文学终于在与现实政治的共振中,其实是与残酷战争的共振中,凸显出其趋向于“无”的无用之用的空前政治意识形态性。在我看来,战争不是政治,而是政治破产的后果,政治无法解决的冲突即导致战争,因其去政治化的浪漫主义倾向,战争往往呈现出歇斯底里的文学性。
“大东亚战争”的爆发,为竹内好的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回心”的契机,作为对这场“重写世界史”的战争的回应,竹内好毅然解散了一手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为反对古典汉学和近代“支那学”而成立的,“一方面,竹内好不满于旧汉学的因循守旧和僵化敝俗,而另一方面,他也同样不满于支那学在改造汉学非科学性的同时对于后者的因循和僵化的无形继承”*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竹内好注重中国研究的主体性、批判性和现实性,他最为不满的是“汉学”和“支那学”研究的现实性、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丧失,变成了僵化、封闭的学究化学术。他极力主张以“否定”作为知识生产轴心的“文学的态度”。于是,当他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日益学院化、世俗化、“支那”学化的时候,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通过自我否定的行动,让自己真正嵌入到自我否定的知识生产的历史中去。对于外在的“汉学”和“支那学”的否定作为一种行为,与对于内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自我否定连接起来,在“自他一体”的状况下的否定是为发明新的自我。不断地进行外在、内在的持续否定,必然无限趋向于“无”的境地。不过在竹内好看来,无限趋向于“无”,恰恰是“有”得以真正发生的唯一契机,“大东亚战争”就是可以无中生有的历史关节。
竹内好认为,“支那”与日本休戚相关,日本的成长必须以“支那”的成长为前提,但存在的现实矛盾是,这个“支那”是一个拥有具体肉身的他者“支那”,并作为一个现实物出现在“支那事变”中。竹内好等日本学者对于“支那事变”的疑惑,便来自于这种现实性压抑带来的痛感。只有在否定“支那”的同时也自我否定,连接于具体肉身,现实情感的痛感就会消失,个体便在消除小我、构建大我的历史目的论中完成救赎。在竹内好那里,“支那”和“支那文学”并不是目的性的对象,而是日本和日本文化建构其主体自律性的媒介物,其被否定还是肯定并不依赖于其本身,而是取决于决定改变世界史的日本之主体意志。“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知识是为了否定它而追求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否定”,这一切否定最终在“大东亚战争”中被完成。至少在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竹内好是坚定不移地这样认为的。他确信,对美国开战将重构世界史,近代世界之结构将被重新定义,具体而言就是从欧洲的“哲学的结构”回心为大东亚的“文学的结构”。作为态度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以“大东亚战争”为基点的“文学的结构”的近代主义立场。
二、哲学的结构与文学的结构
在论及“大东亚战争”爆发的意义时,竹内好认为历史往往是由一个行为决定的,对美国开战作为一个行为便具有改变世界史的功能。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竹内好亦试图用一个行为,一个作为态度的文学行为,来将自身重新置于这伟大的历史转折之中,而不是置身其外。这个行为就是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他亲身建构起来的一个学术研究组织。党派性的丧失、对于大东亚建设的无意义、“支那文学”问题未能在日本视野里被主体化的认知,是竹内好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三个关键理由。*[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9-180页。这些理由,无不与“大东亚战争”、“大东亚文化”建设相联系。但实际的情形却恰好相反,正是“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而不是研究会自身的问题,构成了竹内好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决定性理由。“大东亚战争”给竹内好带来“回心”般的启示,并让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存续成为一个问题。要建设“大东亚文化”,则必须否定已然世俗化、日本化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并以之作为“大东亚文化主体”形成的牺牲。
首先,所谓失去了党派性,就是失去了从本源性矛盾中不断否定自己、并不断自我生成的主体性动力。唯有让中国文学研究会消失,才能证明那种本源性矛盾的存在,只有让其“否定至无”,才能“等待原初的生活从无际的大无之中涌出的那一天”。竹内好相信,中国文学研究会曾经具有这样的“党派性”:“我相信研究会曾经那样存在过,我试图从没有形状的、本源性无的世界中求得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来的那个场域。”*[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2页。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是对那种自我保全的文化抗争,并联系于“大东亚文化”的形成。竹内好声称,“大东亚文化只有在超克了自我保全的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我们日本不是已经在观念上否定了大东亚各地域的近代殖民地统治了么?我认为这种观念是无限正确的。所谓否定殖民地统治,也就是抛弃自我保存的欲望。就是说,个体不是通过掠夺其他个体而支撑自身,个体必须在自己内部产生出通过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个体的立场。世界不是通过掠夺,而是通过给予被建构的。这一大东亚理念的无限正确性,必须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末端,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基础,从那里促成新文化的自我形成。只有通过行为,只有依靠自我否定的行为,创造才会发生。只有以行为支撑的观念才是真正的观念”*[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2-173页。。在竹内好看来,中国文学研究会一直没有完成的自我主体建构,却被“大东亚战争”一举完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通过自我解散,从而无限融入到“大东亚战争”所建立的新文化场域中。
但是,竹内好及其同仁赋予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党派性”究竟是什么?让党派性得以彰显的“本源性的矛盾”、“原初的生活”、“主体性的文化”,在竹内好那里是否有具体的内容?实际上,这种党派性最初建立在对于汉学和“支那学”的抵抗上,并企图通过这种抵抗谋求自身的学术独立性,进而“建立对于近代文化整体的批判立场”。“中国文学研究会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理解支那的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对现代文化进行内在批判的意义上也试图成为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虽然在方法上采取了一般的外国文学研究态度,但反过来得以以支那作为媒介批判使得外国文学研究成为可能的现代文化框架。”*[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4页。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最初的党派性是其相对于日本汉学、“支那学”的独立性,以及相对于近代文化框架的批判性,它要从这个由近代主义、传统文化构建的学术环境中分离出自己,并最终使自己处于支配环境的地位上。这就要求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处于不断自我否定的进程中,不如此,则无以从占霸权地位的近代主义模式中脱离出去,也就不能取而代之并占据支配性的位置。不过,所谓“作为态度的党派性”,最终指向的是终极性的“无”,因为只有成为无,才能成为一切,就像“大东亚战争”一样,其目的就是通过自我取消的永恒否定,而取得囊括一切的绝对支配性。
其次,“中国文学这一态度,对于大东亚文化建设而言,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3-174页。,这是一个颇为令人费解、但极为关键的理由。其至少存在着三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中国文学研究会在内外压力下日渐世俗化、常识化,失去了历史性的紧张感,同时也丧失了对于建构文化自律性的渴望;其二,竹内好形成了新的方法论的自觉,“亦已经意识到我们所依靠的一般外国文学研究方法作为方法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一事实”*[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5页。,因为这些方法是从外面强加于日本文化的,而不是从内部通过自我否定发生的方法论;其三,让竹内好认识到中国文学这一态度无用的是“大东亚战争”的爆发,他确信“持这种立场的(旁观的、近代式的)外国文学研究,在不远的将来,不仅会被证实与以超克欧洲近代为使命的大东亚理念背道而驰,而且还会被证实它在学术上也是无力的”*[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7页。。其逻辑在于,如果以“近代主义的文化自律性”作为目的,那么以中国文学作为把握这种文化自律性的媒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面对以反近代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大东亚战争”,确乎失去了历史合法性,于是只能自行了断。竹内好毫不怀疑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合历史性,他相信主体性的东洋的近代必然将在战争的硝烟中确立起来,因此必须要通过对于过去之我的完全否定而建立崭新自我。
竹内好认为:“人们说大东亚战争改写了世界史。我对此深信不疑。它否定了近代,否定了近代文化,它是通过彻底的否定而从否定的深处促成新的世界和世界文化自我形成的历史创造活动。当我们获得了对这一创造的自觉之时,我们才得以回顾自己的过去,理解它的全部。中国文学研究会正因为它正确,它才变得狭隘。这个立场正是在我们的回顾中才得到了理解。中国文学研究会必须否定。就是说,现代文化必须否定。所谓现代文化,就是在现代在这个时代里欧洲的近代文化在我们自身的投影。我们必须否定以那样的方式存在着的自己。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作为从自己内部创造世界史的创造者而存在的。我们必须不依靠他力支撑自己,而是自己塑造自己。否定中国文学研究会,并不意味着复活汉学和“支那学”。我们否定的对象也包括这两者,所以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大否定。换言之,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切的理解者,是通过自我否定而使自己世界化。这不是给既成的自我再添加点什么东西,而是立足于无限更新自我的根本之点。中国文学研究会十年的经营,换来的正是这个自觉。”*[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6页。“大东亚战争”令竹内好意识到,中国文学研究会依然是一个他律性的近代主义研究范式的产物,这也是日本的近代化的基本特征。“大东亚战争”的爆发就是日本决定从他律的近代主义回心为自律的近代主义,从世界史的他者变成世界史的主体。不过,按照竹内好自己的逻辑——“正因为它正确,它才变得狭隘”,他深信不疑的改变了世界史的“大东亚战争”,也应该同样是狭隘、偏执、排他的。所谓无法否定否定着的自我,却恰恰就是竹内好试图否定的近代主义的根本逻辑。
最后,竹内好认为应该主体性地立足于日本文学的立场来认识“支那文学”,但是目前衰弱的日本文学却不能自他一体地确立这种主体性,无法将“支那文学”的问题转化为自身的问题,同样的状况也发生于中国文学研究会身上,因此它必须被解散。竹内好的论述最终落脚于建构日本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上,以为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学没有思想,只剩观念,失去了创造力,与“大东亚战争”不相匹配。日本文学必须经过自我否定的行为,在自己的内部产生“大东亚文学”,没有这种行为,“大东亚文学”就是一句空言。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解散作为一个否定的行为,就与衰落的日本文学转化为新生的“大东亚文学”联系起来。竹内好试图想象一个超越了哲学结构之文学结构的世界,因为只有文学的结构,才能解释并契合于“大东亚战争”:“今天,文学的衰退已经成为无可遮蔽的事实。把它昭示于天下的是大东亚战争。文学的衰退,客观的说,就是世界不具有文学的结构。今日的世界,与其说是文学性的,毋宁说是哲学性的。今日的文学无法处理大东亚战争。因此,它衰竭了。但是,这个事实反过来从内部看,也可以说恰恰是今天,文学被要求回归它原初的狂放。衰退了的文学,可以通过对于衰退了的文学的否定而复生。只有这样才能在自己的内部产生出新的自我。大东亚的新文学,不是被给予的外在之物,而是通过当今衰退的文学的自我否定,从否定的无限深渊中自我涌现的成果。我希望相信的是,日本文学无论有怎样的曲折,总有一天它会成就这种涅槃的。今天,正是反思文学作为本源性的、内在于行为的决意的这一性质的时刻,正是认识文学并非心理的外包装的时刻。”*[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9页。实际上,不是日本的文学不能契合于“大东亚战争”,而是“大东亚战争”建构起一种超越性的文学氛围,当下的文学语言无以描述这种新的文学结构,因为日本近代的文学是西方近代的哲学的结构的产物,因此有必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大东亚文学”形式来。当然,这个文学的结构在竹内好的著作《鲁迅》中,被凝结为一个本质为“无”的绝对“文学者鲁迅”。
世界的哲学化是竹内好对于近代化及其历史的基本判断,其意味着西方近代性及其意识形态——一种抽象的、客观的、理性的知识范式的霸权。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价值观、方法论和知识脉络,当然从未脱离于这个近代的知识典范之外。日本的中国研究的近代化,在竹内好看来不过是欧洲的近代知识在自身的投影;而日本的近代文学的衰落,其实也就是一个近代性的后果。无论是文学创作方面还是文学研究方面,二者所提供的思想、话语和知识,都不能处理正在“否定近代主义”的“大东亚战争”,当然也不可能形成作为“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之“意识形态翼赞”的文化主体镜像。当竹内好强调一个本源性的、内在性的文学结构应是“行动”的时候,正是在暗示“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之基本的文学性本源,从而与那种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性本源相区隔。因此,竹内好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行为是一个源于本质的文学性的行为。其至少在竹内好的认识中,应是日本的知识生产和文学创作的一次“回心”之举:它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近代,同时在双重否定的基础上又达成了自己。文学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个行为,它必须在自我否定的行为中带来新的创造性。于是,日本文学必须自我否定为“无”,才能从内部生成新的“大东亚文学”。只有自我否定至无,才能成为一切,并创造出新的世界。竹内好废刊《中国文学》、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否定到无的姿态,冀望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自我否定,以一个“无限空无”的自我,形成囊括世界的“大东亚文化”。
我相信,大东亚文化只有通过日本文化自我否定才会诞生。日本文化必须依靠否定自身才能成为世界文化。必须成为无,才能成为一切。回归于无,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界。日本文化作为日本文化而存在,不是因为它创造历史,而是因为它固定日本文化,使它官僚化,使生的本源枯竭。必须打倒自我保存的文化,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生路。*[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6页。
三、文学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
作为争夺地缘政治霸权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大东亚战争”,在本质上完全是基于现实考量而发动的战争。对美国开战,乃是日本之大陆扩张受到苏联狙击的后果。诺门坎战役的彻底失败,让日本不得不在太平洋上寻找战略突破口,以应对美国制裁引发的物资危机。太平洋战争首先是一个地缘经济战*余家哲:《东亚近代体系:模式、变迁与动力》,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0年,第121-131页。,而侵华战争同样也是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算计的理性后果,其中并没有道义、文化或美学的任何位置。即使时时有各种浪漫主义战争颂的出现,但也是作为将近代大众重新投入蒙昧与狂热的“意识形态翼赞”而发生的,而绝不会作为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结构性内容存在于战争中。这里指的是任何一种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实际上都没有文学插足的余地。但是,近代社会中的“人类的异化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这便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德]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 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64页。。文学不得不需要乞灵于战争的启迪,因为近代世俗生活如此凡庸,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象力。就像竹内好对于“大东亚战争”之毫无保留的狂热礼赞一样,世人总是会在战争乍起的炽热状态中生出“徒手握住火焰”般的文学性狂想:“大东亚只有在自己的内部、通过否定的行为才能够得以产生。只有这种行为才是创造,只有创造才是文学。文学仅仅是吐出一个话语,但是为了吐出这个仅有的话语,必须要有徒手握住火焰的行为。”*[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9页。不过,文学就是文学,其本质在于创造;而战争,则是对创造的毁灭。
在战后论述中,竹内好认为日本直到1960年为止,“战争都没有结束,战争体验一直持续着”*[日本]竹内好:《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40-244页。,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川端康成文学或小津安二郎电影的唯美颓废有战争的影子。不过,这种唯美颓废并非来自于日本战败之感伤,而是来自于对战争本身的一般性体验,这是一种超越战争之现实性、肉身性的美学性经验。也就是说,战争在瓦解日常经验、生命实感、现实矛盾,确立一种无以抗拒的历史必然性之外,亦会令敏感的知识者陷入某种宿命式的感伤诗意。战争、暴力和死亡总是具有一种莫名的魅惑,居然能让庸常的现实焕发出异样光彩,战争于是经常被升华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性结构。因为用一般的日常语言是无法描述战争的,而文学语言则可以,它是一种置之死地之后的余裕和从容,并在极端震荡的状况中展示出所谓“无”我的“终极的静谧”。有我的主体性个人,其实无法认同于战争状况下的“乌合之众”,而无我之主体大我,则能够将乌合之众的庄严膜拜般的集体臣服,上升到一种意志美学的高度,即如里芬斯塔尔在纳粹时代创作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美]苏珊·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赵炳权译,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2-117页。。我们无法否认里芬斯塔尔纪录片的美学高度,但也无法否认这种美学的法西斯主义意涵,甚至不能用“谁成就了谁”来将二者排序,而只能说它们或者根本就是彼此成就。崇高的美学、意志的胜利,总是包含令人性战栗、理智沦丧的魔性,并倾倒众生。
集矢于无以抗拒的绝对性——死或无,进而让生命绽放出文学式的华彩,并最终站上世界史的峰巅,这抑或就是竹内好的文学主义想象。他也是以这样文学态度来书写《鲁迅》的。所谓抵抗绝望,或从绝望开始的鲁迅,就是战争带来的震惊体验的一般化、形式化,而无以名状的“东洋人的悲哀”,其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从竹内好提及的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人们能够切实地体会到意志的美学与臣服的激情的交织。在小津电影《秋刀鱼的滋味》(1962)中,不时在《军舰进行曲》里穿插对于战争的回忆,战争的尊严、日常的忧愁与时间的流逝居然交织出一种唯美颓废的诗意,如果没有战争体验作为深度背景,是不能形成这种“火焰灼烧后的遗骸”般的美学况味的。如此基于战争体验的历史魅影及其文学再造,于宫崎骏的动画电影《起风了》(2013)中,亦有不可思议的再现。在暴力与静谧、绝望与希望、战争与文学之间的转寰腾挪中,竹内好不得不以虚无作为通往本源内在世界的美学媒介,因为只有在风暴中心的空无之眼中,人们才有可能对暴力、战争和绝望持一种绝对静观的立场。这就是竹内好在《鲁迅》中论及的作为“余裕的产物”的文学之姿态:“文学不在行动之外,而在行动之中,就像一个旋转的球的轴心,是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没有行动便没有文学的产生。但行动本身却并非文学。因为文学是‘余裕的产物’。”*[日本]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34页。
在竹内好的笔下,“大东亚战争”是行动,而且是摧枯拉朽、暴风骤雨般的行动,全体国民都必将被席卷其中。这个行动具有改变历史、国族、人心的绝对力量,导致每个个体产生一种难以克制的恐惧与战栗:“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的光芒,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日本]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5页。竹内好感受到的震撼、战栗是文学性的,其不能够在理智的范畴内用逻辑的话语表达,因此必须以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赞美诗形式呈现。因为除此之外,便无以描述这场战争之本质上的意义匮乏,于是,他只能在文学主义的虚空话语中赋予这战争以无意义的意义。凌空蹈虚或许是对于竹内好的战争礼赞的最好描述,其是如此超凡脱俗,又是如此不知所谓。
相应的,竹内好废刊《中国文学》也是行动。他以决绝之姿态告别旧的近代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进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大东亚文学”研究范式。然而,就像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前纠结于“战与和”一样,竹内好并不能够将自己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理由落于实处。他认为那些可以举出的解散理由,也可以原封不动地理解为不能解散的理由,解散与不解散是互为表里的。最终,竹内好只能用文学式的言语,来描述中国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思想状况,因为他实际上并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如他所言:我们在经过双重否定之后,把自己置于正确的位置之上。他唯一能够落实的心情,则是自己永不能解脱的文学情怀:“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切实的心情仅仅是古人那种浪迹天涯的情怀。恐怕我将来也不会改变自己在虚空中刻写文字的秉性。”*[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80页。在竹内好的想象中,时代的动荡、历史的转折和战争的爆发皆是行动的表征,能够应和、抵御和逆反这些暴烈行动的唯有内在的“文学精神”,也就是内在于整个东洋世界的“文学的结构”——一种原初于东亚本体的“文化自律性”。竹内好认为,无论是“支那”事变或是“大东亚战争”,都使国民生活发生了激烈的动摇,这个动摇是针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洋世界的。“国民生活的动摇,是对文学精神的考验,不仅中国如此,我们现在也正在体验着这种考验。教给我们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日本]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页。而竹内好著作《鲁迅》整个的目的,或者就在于回答文学精神何以能够抵御、应对战争对于生活的激烈动摇。
不过,与《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之新生般的礼赞姿态不同,《鲁迅》是被竹内好以遗书的心境写就的,但二者对于文学精神的钟情却并无分别。因为,只有文学的结构才能指向那无限否定的“无”轴心,而文学精神则是生出其他一切现实行动的终极之场。如前所述,竹内好之东洋中心主义的文学的结构是相对于西洋之哲学的结构而言,并构成了一些彼此连接的二元对立项的出现,例如东洋的近代与西洋的近代、机能性与实体性、抵抗与进步等等,东洋的近代、机能性和抵抗性集束折射于文学的结构中。如果一定要将这个文学的结构指示出来的话,其实际上即是竹内好谓之“鲁迅文学的根源,是可以称为‘无’的某种东西”。虽然为区别于西洋的哲学的结构而建构了一个东洋的文学的结构,但是这个无限趋向“无”的文学的结构,在强调东洋之特殊性内在的同时,也试图在东洋的内部建立起一种囊括一切的普遍性论述。
相对于西方通过将东方不断对象化而自我实体性扩张的理性主义信念,无限否定的机能性的东洋主体意志,同样也不缺乏自我扩张的动能,因为所谓的“无”,虽然什么也没有,但是却可以无限地囊括所有差异性,并催生出一切的有。从表面上看,竹内好彻底到“无”的自我否定精神,是一种强烈的近代主义批判意识的体现,其意在超克日本之追随西方的近代主义倾向,并生发出本土性、主体性的近代文化意识。不过,他针对日本的中国研究以及日本文学的批评并不是真正内向化的,而是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内向化批判,进而达成外向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实际上是通过彻底否定日本文化相对于东亚其他国家文化的特殊性,然后再在克服特殊性的基础上达成一种普遍性的“大东亚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特殊文化,日本文化不具备世界性的特征,甚至作为东亚边缘的日本文化,它实际上都不具备亚洲主义的内涵,所以必须彻底否定之,以建设一个以亚洲为媒介的世界主义文化——“大东亚文化”。
然而,“大东亚文化”并非是一个自然的存在,而是战争的产物,或者说是“大东亚战争”发明出了“大东亚文化”。对于竹内好来说,如果“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是否定了一个“脱亚入欧”的近代主义日本,那么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大东亚战争”则不过是日本殖民/帝国主义行为的深入;其对内的“自我近代化否定”,强化了其对外扩张的动能,对内否定与对外扩张是二位一体的。竹内好想象的“亚洲文化共同体”——“大东亚文化”,是以消除亚洲内在的差异性为目的的。让日本文化放弃自我保持的立场“先行否定到无”,就是使之具有超越差异的先在性,然后再创造出崭新的具有普遍同一性的“大东亚文化”,其可以涵盖并最终彻底消灭东亚的内在差异性。这种试图最终消除东亚内在差异的叙事逻辑,虽然以日本、日本文化的自我否定为基础,但这个“先行否定到无”的行为/理念的关键,却是一个日本中心的国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竹内好宣称,“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的同时,与“支那”相对的近代的日本自我也必须被否定,但是其最终的目的却在致力于这样一个日本如何在否定之后成为绝对主体的问题:“作为外国文学的支那文学在日本文学的视野里被主体化,这是我们不可以转移开视线的问题。就是说,只能主体性地立足于日本文学的立场。”*[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8页。竹内好的《鲁迅》,其实也是在这个日本视野中被主体化、主观化的产物,“竹内鲁迅”之“无”鲁迅的判断,也是在这个层面上获得的。
对于自我的否定性承认与对于他者的肯定性否认,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自我的浪漫主义遐想与对于他者的理性的现实主义分析,也是表里同构。将日本文化“先行否定到无”并不是解构日本的主体性,而是将日本及其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当然最终会被廓大为“大东亚主义”)通过否定之否定之后,臻达能够贯穿于整个“大东亚文化”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的主体将消泯东亚其他文化的特殊性,并将之统统整编于“大东亚文化”的名目下。1942年2月到4月间,竹内好到中国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主要考察关于回教的相关问题。这个考察的基本目的,当然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相关。在《东亚共荣圈与回教》一文中,他一方面惊叹于东亚文化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却又不着边际地笃信,“大东亚文化”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历史文化认同,必然能够最终超克这些多元差异性。
随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能从各个角度讨论一下将来比较理想的构思,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我们也许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真正地去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它是早晚可以实现的,我们决不能失去希望,失去信心。……民族、语言、政治组织、社会结构,一切都是那样的复杂,令人头昏眼花。我感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绝非易事。我们的“共荣圈”包括从以狩猎为生的原始民族,驰骋沙漠的游牧民族到拥有古老文化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民族。单纯从宗教的方面来说,从原始的精灵说到世界宗教范围内的佛教、基督教、回教,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环境和历史,而这些宗教被一直传承至今。这种复杂的程度在世界其他“共荣圈”里是看不到的。为了创造新的文化,就必须首先研究透他们现有的状态。*[日本]竹内好:《东亚共荣圈与回教》,诸葛蔚东:《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按照竹内好之建构“大东亚文化”的逻辑,非但“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一切差异性的东亚文化因素在终极意义上也必须被否定,只有自他之对立的状况完全消解之后,新的“大东亚文化”才能被创造出来。很明显,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关于新的文明范式的任何愿景,只有一颗试图否定一切、吞并一切的野心,其以文学想象来建构,自然是最为合适的。狂热拥护“大东亚战争”、毅然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着迷于空想“大东亚文化”等,让竹内好在文学的结构的行为中,不断实践着自己的否定之否定的主体辩证法。他试图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而达到一个本源性的主体性的内在,即所谓世界性的、当然首先是日本性的文学的结构。竹内好否定之否定的“同义反复”修辞,形成了一种内向的、封闭的、排他的话语逻辑,从而使其几乎对于外在的一切质疑、批判形成了免疫力,因为它自己构成了对于自己之无限“解构性的重构”。所谓“回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指向绝对内在自我的循环式修辞:谁也不能否定一个永远自我否定的主体。当然,这是个不得已的选择,原因就在于竹内好根本无法解决“主体”的混杂性本质。无论是作为想象的主体性大东亚文化,还是“大东亚文化”的象征物——“竹内鲁迅”,当然也包括日本,其实都具有难以否认的混杂性。而正是由于这种无法处理的混杂性,使得主体在建构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内外否认,其根本不能在本质上明确自己到底是什么,于是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倾诉自己不是什么。对于竹内好来说,主体认同叙事其实从来都是一个宣称自己谁都不是、甚至不是自己的话语游戏,而“回心”之旅,也就是一个永远不能抵达自己的旅程。
竹内好在《鲁迅》中不断声称的文学者鲁迅得以诞生的混沌,“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前的日本的困惑,未来的、同一性的“大东亚文化”必然诞生的现实性基础,等等——东亚内部纷繁复杂的文化差异性,皆体现了主体之混杂构成的宿命。对于“杂种性”的涤荡并不能获得根本性的纯粹,于是,竹内好一向热衷的根源性的主体之内在核心,只能用词语环绕的“无”。而“无”同样是一个无限“混沌”之所在,因为表征“无”的词语本身,就是一种与“有/物/存在”相分离的抽象的“物/符/无”。也就是说,你无法用“无”(词语)来表征“无”(词语),当然也不能用自己表征自己,你只能在与他者的差异性比较中意识自己并认同自己。因此,“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承认”,没有这种对于他者的绝对承认,任何自我否认在终极意义上都是“无”所依凭。
四、文学政治与东洋的抵抗
从《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的战争礼赞到《鲁迅》的诞生,贯穿于竹内好论述的基本立场,其实是一个文学政治的立场。至于可以“无故纳万境”的“大东亚文化”,同样也只有在荒废现实感的殖民亚洲的“大东亚战争”之后,才能在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中被发明出来。“竹内鲁迅”之文学性的“无”根源,是竹内好无中生有“大东亚文化”的具体落实——“必须成为无,才能成为一切。回归于无,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界”。竹内好将鲁迅及其文学建构为一个挣扎、抵抗、回心于自我否定过程的绝对文学者,便是以此来表征彻底否定西方近代主义之“哲学的结构”的“文学的结构”的东洋的近代。“竹内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交织现实与想象、狂热与静观、死亡与永恒的“大东亚文化”想象的表征。在竹内好那里,“鲁迅”就是文学结构的“大东亚文化”的回心之轴。
文学结构的“大东亚共荣圈”,直接联结着竹内好战后主张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想象,而他对于本源性的亚洲主体的执迷,则具有一种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实际上,通过发动对西方的战争、否弃哲学的结构的西洋近代、想象一个鲁迅式的东洋文学者,移情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建构起一个无中生有的、本源性的文学的结构的亚洲主体,其实是一个歧途丛生的思想旅程。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或许在于,何以无中生有的文学的结构的另类近代性想象,能够与白热化的“大东亚战争”以及扩张性的“大东亚文化”联接起来,从而构成一种“东洋的抵抗”轴线。
战后的竹内好辨析各种亚洲主义论述,分离并抽象出了自己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他认为:“亚细亚的定义是非常的各色各样的,有些是作为反动思想,有些是作为膨胀主义或侵略主义的别称,有些是把亚细亚主义当作广域圈思想的一种形态。也有与孙文的亚细亚主义、聂鲁的亚细亚主义等个别范畴并列,而处理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日本]竹内好:《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竹内好全集》(第8卷),东京:筑摩书房,1980年,第94-95页。参见张昆将:《关于东亚的思考方法——以竹内好、沟口雄三与子安宣邦为中心》,《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4年12月,第272页。竹内好提出要检讨、批判亚细亚主义幻灭的思想,而返回原型/原初的“亚细亚主义”,即具有普遍性、内在性的亚细亚。这种原教旨的亚洲主义强调亚洲内在的本源性力量,亚洲需在抵抗西方近代主义的基础上不断返回这个原点,即在自我否定和对外否定的过程中重构自己的主体性。这个亚洲主体不是实体性的,而是机能性的,是一个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又不断发明自我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回心”至“无”的自我认同过程。它当然只能在文学的结构中持续发生(想象),而不会在哲学的结构中变为实体性结果。对于文学的结构的矢志不渝的推崇,实际上明确指向贯穿竹内好一生的基本思想的核心,“恰恰是文学的位置与功能问题,所以在更准确的意义上,或许应该称竹内好的精神原点为‘文学的方式’”*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竹内好在想象“大东亚文化”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无”的鲁迅:“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日本]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赵京华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06页。;而在“大东亚战争”中他虚构一个“无”的日本:“必须成为无,才能成为一切。回归于无,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界”*[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6页。;在战后的氛围中他又想象了一个“无路可走又必须前行的”永远革命的中国——永远向内“回心”运动的生产性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日本]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赵京华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14页。。这一切致力于无中生有的抵抗性思想的发生,都是作为基本价值立场的文学政治的显示,此即竹内好所谓的“作为态度的文学”。而“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方法论所指,其实也是这个“作为态度的文学”。站在一个具有内在历史连续性的“文学的位置”上,战后竹内好的亚洲想象实际上并不能与战时的“大东亚共荣圈”妄想摆脱干系。而且,竹内好本人并不讳言自己试图从政治不正确的战时意识形态中获取政治抵抗资源,对于西洋的抵抗——“大东亚战争”带来的“大东亚文化”的自觉,被他通过对鲁迅及其文学的持续“翻译”,再次获得一般性或者普遍性的内涵。这些以“无”为最终旨归的态度、立场和行为,被竹内好笼统地称之为“东洋的抵抗”:“我开始用‘东洋的抵抗’这一概括性的表现来思考,是因为我感到鲁迅所具有的那个东西在其他东洋诸国也存在,并认为由此大概可以推导出东洋的一般性质。说是东洋的一般性质,我并不认为那种东西是实体性的存在着的。”*[日本]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赵京华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96页。“东洋的抵抗”一如不断自我否定回心至无的“文学者鲁迅”,其作为一种指向内在主体自我的否定性场域,是生出各种各样的反西洋的近代的“东洋的近代”的终极之场。
虽然战后的竹内好不再使用“无”来表征东洋(亚洲)的非实体性的“一般性质”,但我们依然会从流动性、机能性、瞬间性等文学修辞中,寻找到“无”的鬼影。而且极具意味的是,战时的竹内好认为,“战争突然降临,在那个刹那,我们了解了一切,一切变得明白无误。天空高远,清光四射,我们陈年的积郁被驱散了。我们这才刚刚觉悟到,原来道路就在这里,回头顾盼,昨日的郁结之情早就不见了踪影”*[日本]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5页。。世界、道路和未来变成透明之物,竹内好在战争爆发的瞬间,觉得日本已经完全掌握了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这里不存在任何不确定、不明了的地方。如果还存有不确定、不明了之处,那就将其塑造为通过持续否定而不断回心自我的“无”,“无”便是不明了的明了。战争胶着状态下写就的《鲁迅》,就是将混沌多义的鲁迅文学归结于“无”,而造就的明了化的鲁迅形象。不过,战后的竹内好似乎改变了策略,会特别强调一种流动性、状况性和机能性的复杂历史情态,而特别反对实体性、本质主义的历史解释。例如他对于远山茂树回应即是如此:“在远山氏那里,人的动机和手段是可以明确区分,并且可以被他者整体上把握的透明实体,对我而言却是流动的、状况性的,而且难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物件,而历史,在远山氏那里是沉重的被给予之物 ,在我这里,是可塑的、可以分解的建构之物。”*[日本]竹内好:《关于学者的责任》,转引自孙歌:《在大陆语境中“翻译”竹内好:进出政治正确的中国论述》,《中国大陆研究》第50卷第1期,2007年。
实际上,竹内好对于历史的瞬间性、流动性、状况性的强调是一直没有变化的,变化只在于战时是试图在历史瞬间之中把握住历史规律,进而破解历史整体的含混暧昧而抵达明了之地,战后则强调在瞬间之中把握历史本质的不可预测性,反对基于结果而对历史过程作出政治判断。战时在“大东亚战争”爆发的历史瞬间明确了“支那”是日本重写世界史过程中的可牺牲要素,因此“支那在终极意义上必须否定”;战后则要在历史的瞬间把握“近代的超克”*简要言之,“近代的超克”反映了近代日本之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其内涵大略可概括为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反近代主义”兴起,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主体悖反意识由此发生。在讨论太平战争期间日本学界发起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时,竹内好认为,“近代的超克”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到了总体战争的阶段,面对解释永久战争的理念这个思想课题的逼迫,而一举爆发出来的,便是“近代的超克”这个讨论。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赵京华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54-355页。等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隐含于其中的“东洋的抵抗”等思想性要素,故此,“近代的超克”在复杂的历史状况下可离析出新的思想史意义。不过对于竹内好而言,前后没有变化的是在不可抉择的、流动的历史瞬间,他都基于某种自我确立的需要通过不断否定做出了抉择,即使明明知道有所牺牲,抑或政治不正确,也在所不惜。因此,在“大东亚战争”爆发的瞬间,他牺牲、否定了“支那”;在战后从“近代的超克”论中择取思想性的“东洋的抵抗”要素时,他牺牲、否定了政治正确。这就是竹内好所谓的“知识若不具备否定它自身的契机(或者说是热情),就不能作为知识而活着。知识应该是为了否定它而追求的。这就是文学的态度”*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竹内好认为,鲁迅即是具有这种“文学的态度”的东洋典范。但是,这种文学的态度其实还是政治性的态度,而非真正反政治化的立场。同样,反对从结果推定的政治正确的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
孙歌认为,从1936年的《鲁迅论》开始,经1943年的《鲁迅》到1948年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性》,竹内好在漫长的思考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关于“文学的位置”的这种机能性的理解。“政治与文学”最终被确定为“场和其中的存在的关系”——“文学”从一个实体性的领域变成了一种内含否定契机的机能化结构,“政治”也不再被看作与文学对垒的实体化力量,而成为一种与社会整体利益相关的行为空间(公共领域)的文学之场。*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2-74页。竹内好在《鲁迅》中建构起一种文学政治的论述:“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的关系,不是相克的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所谓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可以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日本]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34页。而且,“政治的振幅越大,文学把自己破却在政治里的纯粹程度也就越深,这种关系用日常语言是不能表达的”*[日本]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51页。,唯有鲁迅的文学能够表达之。
在战后论及中国近代文学的政治性的时候,竹内好特别以茅盾为例说明,这种政治性是一种国民文学性,并与日本文学的非国民性形成了对比:“我认为茅盾的‘民主与独立’的主张是他的文学性的言论,同时也是高度集中表达这种国民意志的话语。之所以可以这样表达,取决于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就是说文学的国民文学性(规模虽然还小,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它体现了全体中国人的意见。而且正因为如此,它是文学性的。(因为这种话语,是来自于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的,而不是来自于远离生活的抽象的‘符咒’式的东西)”*[日本]竹内好:《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薛毅、孙晓忠:《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431页。竹内好一方面钟情于一种抽象的文学政治,以为文学是机能化实体政治的场域,并解构了政治之狭隘的排他性论述;另一方面又将文学政治视为一种自然的、底层的、自下而上的国民政治,其是所有国民诉求、国民生活的结构性集中。虽然竹内好认为文学政治不是远离生活的咒语式的东西,但他自己对于文学政治的表述,却充满了幻想气质与文学精神,是十足竹内好式的同义反复咒语。
立于“文学的位置”的有机抵抗,的确是人文批判知识分子的重要策略,并使其批判呈现出非凡的力量和强度。但亦需指出的是,文学的流动性、含混性、前意识性,使之既可能是缪斯的低吟,也可能是塞壬的歌声。其中既有理性的思辨,更有非理性的蛊惑;既有有意识的抵抗,也隐含无意识的臣服;既可能是人类解放与自由革命的源泉,也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煽动的工具。竹内好当然倡导的是抵抗、革命、自由、民主的文学政治,不过,从他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之际生发的癫狂诗意和对于中国革命的非理性移情中可以看到,“文学的位置”、“作为态度的文学”、“作为终极之场的文学”等绝对主义文学政治论述,其实往往偏离理性的视野,而滑向一种非理性的神话叙事。“文学者鲁迅是生成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弗洛伊德认为梦与文学之间关系密切,文学就是回归潜意识的白日梦,从而将原始的激情以语言的形式再现出来,因此文学语言总是魔力十足,具有强大煽动性。凡是杰出的政客,皆如诗人一般巧舌如簧,从而蛊惑众生,使之为各种乌托邦话语癫狂不已,至死方休。实际上,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历史实践中也从不缺少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政治论述,学者刘纪蕙即从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论述中勾勒出诸多法西斯妄想及其压抑的痕迹。*刘纪蕙:《三十年代中国文化论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压抑﹕从几个文本征状谈起》,《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0年,第16期。
文学性话语虽然缺乏理性的逻辑、实证的精神,却能够以一种诉诸情感的神奇形式发挥力量,推动个体向前意识层面退行,从有意识的主体降格为乌合之众,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群众运动、战争动员往往不会求助于客观理性的社会分析,而诉诸于文学表达、抒情政治和意识形态蛊惑。“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1页。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激进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表现来看,这些反抗近代工具理性奴役的极端政治运动和社会革命,实际上并不是普通政治,而是一种文学法西斯主义政治。因为它们总是擅长建构各种各样的文学主义的天国王朝和未来乌托邦,而无法就社会关系的完善提出任何可行的方案。在文学法西斯主义政治想象中,平庸的人道主义必须成为可诅咒的虚伪道德,而一种本真的,原乡的,纯粹的我、我族、我阶级想象则大行其道,赞美死亡、牺牲、暴力、战争就成为应有之意。只有这些否定别人的同时又自我否定的绝对形式,才能让我/我们变得如“无”般纯粹、完美,从而能够无限地回到自己的原点去,然后再无限可能地展开自己。
余 论
竹内好对于其“文学的位置”的坚持是始终如一的。战后,在谈及《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时,他依然还是认为那只是政治判断上的错误,而非思想判断上的错误:“现在可以简单说出来,即那份宣言,作为政治判断是错了,彻头彻尾地错了。但通过文章所表现的思想,自己却不认为有错。无论别人怎么定罪,我只有带着那一思想走向地狱。”*[日本]竹内好:《为了了解中国》,赵京华:《竹内好的鲁迅论及其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从竹内芳郎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批评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所谓思想上的正确,也只能是作为文学政治的正确,而不是现实政治的正确。竹内好的辩解还是站在“文学的位置”的辩解,他是一个文学主义的本质论者,并永恒复归于一个“作为态度的文学”本质。竹内好之“向死而生”、“挣扎抵抗”、“先行否定到无”的自我否定意识是极为彻底的,贯穿于他的一生,就像他形容鲁迅的说词一样,其中没有“人道主义插足的余地”*[日本]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赵京华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06页。。也就是说,在竹内好战后的文艺、理论实践中,依然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实际上,文学主义的法西斯倾向不仅仅是竹内好个人的特点,而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历史实践的普遍性特征。而文学、美学与法西斯主义的彼此关联表明,法西斯主义及其历史实践作为现代性后果之一,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思想状况与社会现实。据此言之,置身于这个极端异化的时代状况中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游荡着法西斯的幽灵。因此,祛除法西斯幽灵的思想斗争与文化生产,依然是我们当代人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实践。
责任编辑:李宗刚
Criticism of “Takeuchi Yoshimi’s study on Lu Xun”
Han C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266071)
Taking as an opportunity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Japanese scholar Takeuchi Yoshimi released his sense of guilt about the War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nd expressed his support for the War by breaking up theChineseLiteratureResearchSocietyand stopping the publication ofChineseLiteratureand others. When World War II entered the heated stage, Takeuchi Yoshimi made Lu Xun an absolute litterateur who returned to “nothingness” in order to negate Western modern culture in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and constructed greater East Asian culture in “literary structure”. After the war, Takeuchi Yoshimi discovered taking Asia as method of anti-modernism from his discourse about “overcoming modernism”, a kind of ideology supporting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Pursuing the modern times of anti-modernism with East Asian subjectivity is both a constant ideological axis of Takeuchi Yoshimi and a paradox that results in a fascist inclination of anti-humanitarianism. In fact, the fascism in literature is not only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of Yoshimi Takeuchi, but also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anti-modernist ideology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of all kinds of radicalism since the 20th century, so that in the present world, there still loiters the apparition of fascism. Takeuchi Yoshimi’s literary mind, political thinking and study on Lu Xun formed in the war seemed to confirm Benjamin’s political criticism of fascist aesthetics; “Human alienation in the modern society has reached such a high extent that it can take its own destruction as the primary experience of aesthetic pleasure This i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fascism seeking help from aesthetics”.
Takeuchi Yoshimi;LuXun; nothingness; Greater East Asia War; overcoming modernism; Asia as method
2016-04-01
韩琛(1973— ),男,山东龙口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作为方法的日本鲁迅研究: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16FZW034)”的阶段性成果。
I210
A
1001-5973(2017)04-00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