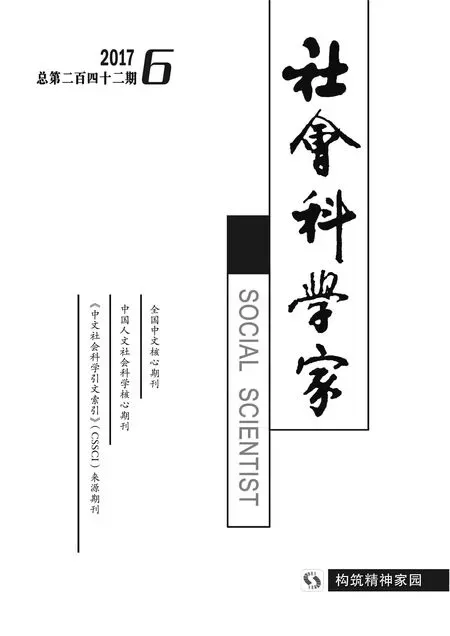拉康与法国精神分析批评
赵靓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2700)
拉康与法国精神分析批评
赵靓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2700)
精神分析学家对文学文本的态度和文学批评家的精神分析文论侧重点和研究目标上必然有所不同,然同时又存在彼此互动的双生关系。拉康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学家,全部著述和讲稿中难见完整清晰的文学理论文本,反之是依傍语言学为中介,衔接文学批评和精神分析,揭示主体和话语之间复杂关系。其对艾伦·坡《被窃的信》的分析、对文字的重视,以及预演“症候阅读”,在20世纪法国精神分析批评的发展史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显示了不同于德里达的另一种哲学文学批评路线。
精神分析学批评;弗洛伊德;拉康;德里达
精神分析学家可以来谈文学?这个问题叫人迷糊。因为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始,就天经地义认定文学和艺术作品是借助想象来表达欲望,是为精神分析的康庄大道。弗洛伊德一度有将精神分析视为适用一切学科之普遍方法的远大雄心,撰于1919年的《大学中的精神分析学教学》中他即称精神分析方法的应用,无论如何不能限于精神病本身,还应扩展到解决艺术问题、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弗洛伊德本人身体力行,以“俄狄浦斯情结”开道,开创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学派。不过在医学界,直到二战之后,仍然在怀疑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实践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他们可能看到的是玛丽·波拿巴的爱伦·坡研究和拉福格的波德莱尔研究,这两位基于病理学前提的技术性分析家的文学批评,可能没有注意到新一代评论家对于新方法的杰出运用。说真的,一个专业精神分析师,他如何来探讨文学?他的文学分析具备足够的判断力和有效性吗?
精神分析学开创于德国,但无论是作为学科建设还是文学乃至文化的分析方法,都在20世纪以来的法国获得了空前发展。弗洛伊德连同他的学说在法国的遭遇开场并不愉快。柏格森的生命绵延哲学和皮埃尔·雅内的心理自动作用说,以及法国强大的学术体系和医学实践传统,构成当时的“反精神分析学文化”,对作为治疗技术和哲学伦理话语的精神分析学,不但态度矛盾,甚至有意拒斥。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才缓慢改观,由于移民分析家团体和法国本土年轻医生团体的努力,1926年“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和《法国精神分析学杂志》才得以创立,就弗氏著作的法译术语展开激烈讨论和艰难界定。与此相反,法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则热情接纳了精神分析学,将之置身于诗学与“文化革命”的核心。文学先锋主义尤其是超现实主义流派,具备医学背景的布勒东和阿拉贡都是中流砥柱,不管在创作还是理论方面,都主动将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同文艺创作与分析联系起来。根据精神分析史学家伊丽莎白·鲁迪内斯科的说法,精神分析学在法国文学和医学领域的传播过程,属于同一个进程和同一种意识形态现象,都在各自领域关涉着法国本土的知识传统和时代精神:“在文学界,倾向于把精神分析学说成是某个真正发现的表现,而在医学界,则倾向于让它去适应所谓的拉丁精神或笛卡尔精神的理想。”[1]鲁迪内斯科没有说错,法国作家对精神分析学的移植有一种狂热,多半是通过理论的误读,性欲、罪恶、自杀、迷幻癫狂、梦境与通灵幻觉、身体暴力等等,战后一代作家热衷的各类题材,我们发现都可以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一个支点。如罗曼·罗兰和纪德,就与弗洛伊德渊源颇深。
拉康的精神分析研究和文学批评同步,开始于这个热情的30年代。作为大众视野中的专业精神分析学家,他的研究在什么情况下真正触及了文学批评?拉康没有专门论述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著作。不像弗洛伊德和荣格,从拉康全部著述和讲稿中,都很难找到一个完整清晰的文学理论文本。毋宁说,在拉康那里,是依傍语言学作为中介,才得以衔接文学批评和精神分析学,揭示主体和话语之间所在秘密的。
一、结构主义文本分析
拉康从50年代初开始,提出“父之名”和“三界”理论,树立起“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即回到精神分析的理论源头,以重建弗洛伊德传统的技术和革命力量,破除是时美国分析界的强大影响,即将精神分析简化为自我心理学,自我贬低为获取成功和幸福的方式。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追本溯源阅读涉及大量基础性文本,不过,对弗洛伊德本人的文艺批评和美学文本,如有关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论述,拉康却很少提及,就连在讨论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时,也很少提及弗洛伊德的相关评论。这可见拉康对文学阅读有自己的看法。弗洛伊德主要是精神分析用于文艺文本评论,偏重梳理作家心理机制;拉康则把文艺作品本身看作是精神分析的文本,偏重文本分析。两人的研究路径和批评观念,其实是有根本差异。
拉康1956年发表的《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报告》,公认是他少有的文学批评文本。拉康在此显示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典型阐释方法,有意借坡这篇小说所包含的寓言,去阐释一个精神分析学的真理:“对主体来说,象征秩序具有构成作用。”[2]小说中的主体有国王、王后、大臣、警察局局长、杜宾,以及叙事人“我”。在拉康看来,所有持有信的主体,或被信持有的主体,都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盲目。拉康判定这是主体受制于“能指的旅程”,他们想拥有这信,可是命运却都受制于拥有的可能性,故而拉康说:
我们的语言的目的是要表明的是信及其迂回规定了主体的出场和角色。因为信是待领的,而吃苦的正是这些主体。因为要在它的影子下通过,他们便成了它的映像;因为要拥有信(语言的歧义多么了不起),信的意义却拥有了他们。[2]
拉康以信为能指的隐喻。这一是因为法语的“lettre”既指“信”,也指“文字、字母”,所以与语言相关。二是由于信的内容从未揭晓,我们只知道它事关重大,决定着主体们的命运。拉康认为,信作为能指代表无意识,对信的角逐和占有实为权力角逐的隐喻。于此能指与所指一刀两断,自由飘离起来,再不是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相互对应的幸福模样。这毋宁说对于德里达以“延异”为核心的解构主义,也是一个呼应。
拉康将故事中呈现的两对三角形结构场景合而为一。第一个是警长前来告诉“我”和杜宾宫中信件失窃的经过,提供了一个三角结构的悬念;第二个是在大臣的办公室,由杜宾窃回了原信。拉康认为两者都是由三种条件构成,而且这三个条件出现并非偶然,是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一个内在结构的显现。简言之,这些条件的特殊地位来自它们同时与三个逻辑时刻的配合,由此形成并决定了主体的位置,在他们之间形成选择。不仅如此,在这两个三角结构之上,还有一个本原固定结构,即每个主体由于位置变化而产生的关系和视阈变化。第一个主体是国王和警长,第二个主体是王后和大臣。杜宾和大臣又构成第三个主体和视阈,它一目了然看出了前两个视阈中视而不见的信。拉康进一步指出,整个故事就是一个隐喻结构,一个关于“欲望的结构分析”,它揭示了欲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系,追寻这封失窃的信的过程,其实就是欲望满足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病症状的治疗过程。
很显然,拉康是以他的文学阅读推演出了自己的能指理论。“能指的游戏”借助于此处“信-文字”的同音异义组合达成。区分能指与所指,强调前者的优先性,在于拉康乃是“回到弗洛伊德”的关键。在《选集》中该文附有一个导论,说明这个侦探故事分析是对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所做评论的一部分。然拉康特别强调能指的作用,认为能指组成了象征界和自我理想,能指链也构成了无意识,后者又把词语转化成症状。这无疑是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思想。
拉康在分析坡的这个故事时无疑引入了结构方法。结构主义的目的在于消解主体,废除主观能动性,取而代之以语言结构的自主性。但是纵观拉康整个学说,分明始终想在这一貌似纯客观的语言结构中为主体找到一个位置。通过这个侦探故事的分析,拉康提出了一个异化理论:主体通过言语进行认同,但是在语言中,主体被驱逐,被迫分离,总是处于匮缺之中。欲望的结构就是中空的,追逐它无异追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该文1966年收入《选集》时,拉康补充指出,这部小说的精义在于表明信可以将其效果带到内部:带到故事的人物上,包括叙事者;也能带到外部:带到我们身上,以及带到作者身上。然而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所有文字的普遍命运。要之,小说文本本身,便被看作一个关于纯粹能指的游戏,一个关于(信的)阅读行为的寓言。
二、“文字”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拉康继续在跨学科领域内进行探索,其一表现在和华裔文学家和思想家程抱一一起研习汉字和中华文化经典,并延伸到对日本文字和书法艺术的探索;其二是与雅克·奥贝尔(JacquesAubert)一起研究乔伊斯的生活与作品。这些探索的集中表现,就是1971年拉康在法国《文学》杂志第3期(本期专题为“文学与精神分析”)发表的短文《文字涂抹地》(lituraterre)。该文谈论了先锋文学的写作、文字与原乐的关系。文章标题是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拉康声称是受到贝克特对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评注的影响,这个评注将“文字”(aletter)与“垃圾”(alitter)做了歧义双关,宣称“文字即垃圾”。拉康追溯这一思想的美学根源为圣托马斯·阿奎那,后者在经历了神秘体验后,断然放弃了《神学大全》第三部的写作,声称自己写下的一切皆如糟粕一般,不久默然离世。拉康常用这个比喻来指分析家的话语目标。这篇短文中,拉康首先道明了精神分析学在文学评论上的局限性,他说:
至于精神分析学,它离不开俄狄浦斯,神话的俄狄浦斯这一点,然而这绝不会使它有资格在索福克勒斯的文本中捞到油水。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文本的提审,也不足以说明文本批评——至今仍然是大学话语保留的猎物——就已经从精神分析学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空间。①标题是拉康根据“littérature”(文学)一词的音节次序颠倒而创造的新词,两词的前缀分别为“涂抹”和“文字”的意思,后缀为“土地”和“涂改”的意思,故可以翻译为“文字涂抹地”。参见拉康:《文字涂抹地》,白轻编《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157页。
紧接着拉康重提了昔年对《失窃的信》的分析,指出自己对这个文本做的是文学批评,顺带影射了玛丽·波拿巴所做的爱伦·坡心理传记。拉康承认精神分析学从文学中汲取了养分,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引用侦探文学来说明精神分析学原理。不过他现在认为精神分析学接触这一文本,只能是显示了自身的失败。然而正是通过这种失败,使得精神分析学证明了自身闯入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如果说文学批评据此确实能够面目一新的话,那么这也可能是由于精神分析一边在此间与文本较量,一边又把握着较量的谜题。
《文字涂抹地》的后半部分,拉康花了相当篇幅讨论日本文字和绘画的特殊性,以期拓展书写的概念。他宣称这是受到了巴特《符号帝国》的影响,雄心勃勃追求用科学来规定文学。这一科学的交流方式就是书写。拉康指出,“文字是更严格意义上的临界(littoral)”②拉康在本文中几度玩味“临界”(littoral)与“书面”(litteral)的文字游戏。前者的拉丁文词源“litorarius”与表示涂改的“liturarius”谐音,本意是“沿海、海滨”等意思,也是海洋和陆地的分界地带。,所谓临界,是说文字构成了知识与享乐之间的界限。说明这一点如何可能,拉康简述了日本文字对他的启示,指出日本文字像汉字一样,具有明显的书写效果,其书法艺术更突出了写作行为,比如“一”字,它制造了沟壑或界线,构成了文字涂抹地。故拉康强调,文字和书写,其描摹的不是能指,而是语言的各种效果,亦即言说者以其语言创造出来的东西。
在《文字涂抹地》的字里行间,拉康再次表达了对德里达的不满。他对德里达的质疑由来已久。1967题名为《从53年的罗马到67年的罗马》的演讲中,拉康再次强调了无意识和话语的重要性,并把自己和结构主义区分开来,③后期拉康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改变在于提倡一种“牙牙学语”(lalangue)式语言。属于这后一种语言的,有婴儿呢喃和前语言阶段的学童语言,或马拉美那种充满音乐性的文字。他暗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不过是从拉康话语泡沫中升起的阿芙洛狄忒。此后在《选集》1969年的Point版说明中,拉康明确指责德里达剽窃他的思想,认为他本人对文字的重视,要早于任何德里达式的“文字学”。拉康同时指责德里达的《弗洛伊德与书写场景》(1966)和《论文字学》(1967)未经许可,便把他自己的思想引入了所谓的“大学话语”。事实上,《文字涂抹地》一文中,德里达的许多术语和参考文献,诸如“涂抹”、“痕迹”、“场景”,乃至弗洛伊德写给弗里斯的第52封信、狼人个案和魔术书写板等,拉康都一一有所提及。拉康在1968年之后被巴黎高师逐出课堂,在移师到索邦校园的新一期研讨会《精神分析学的反面》上,他进而区分了四种话语,而对“大学话语”展开了激烈批判。拉康指出,大学话语中知识占据主导地位,它复灌输给听众一种表面中立的知识,处于一种控制他人的地位。大学话语也是科学话语,飞扬跋扈、趾高气扬。而利奥塔正是基于语言学和后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在《后现代状况》中发起了对科学话语的大反攻。可以说,拉康这类出处影射德里达的论点,应是后者忍无可忍的。难怪乎德里达后者发表《真理的供应商》,对拉康《失窃的信》研讨报告加以猛烈批判。
三、与德里达的分歧
1966年是结构主义全面勃兴的一年,可它也迎来了解构主义的初春。德里达重写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发表了《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首次拉开解构主义旗帜,锋芒直指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德里达、德勒兹、福柯等为先锋,这一批思想家率先对精神分析学科及其批评策略指出了新的研究前景。他们力图促使精神分析学以另类的方式来对文学发问,指出它应当尊重文学能指的独特性,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和审美特点。在《弗洛伊德与书写场景》一文中,德里达指出,“一种尊重文学能指独特性的文学上的精神分析尚未开始,这大概不是偶然。到目前,我们只进行了对文学所指的分析。”[3]这是说,精神分析批评遇到了语言学上的新问题,有待新的探索来加以解决。
德里达1975年发表《真理的供应商》一文,把矛头直指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及其文本阐释方法。德里达不仅反对拉康的基本论题,而且反对拉康关于信/文字的基本假设。在他看来,拉康的论述不仅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且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首先,就拉康揭示出精神分析学真理这一点上,德里达认为,拉康与其说是真理的揭示者,不如说是真理的承办商。“真理”一词向为德里达深恶痛绝,拉康和海德格尔一样虽然被视为拆毁形而上学的大师,然其真理的迷恋,在德里达看来证明他们仍未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羁绊。德里达认为,拉康强调小说的三角结构,却忽略了叙述者这个第四元素,并且还迷恋叙述的真实逼真性,表明拉康没有看到文学虚构对精神分析学知识具有一种不断更新的抵抗。进而视之,拉康选择三元结构的阐释模式,德里达推论道,是精神分析学父母子三角俄狄浦斯结构蛊惑的结果。
德里达断定拉康是将失窃的信与菲勒斯即男性阳物等同了起来,对此德里达采取了反证法来加以论证,指出舍此隐喻,拉康对信的这三种主张就难以理解:(1)信的位置十分古怪;(2)信的不可毁灭性;(3)信总是会抵达它的目的地。德里达由此判定,信的位置最后总是和菲勒斯的位置重合。就第二点而言,“信”(lettre)在于拉康也等同于文字,而不是信件本身。文字与其说表示事物,不如说是事物的缺席,再一环一环引申下去的话,这个缺席的最终所指,正是菲勒斯。
德里达最终影射拉康是剽窃了文字。他的结论是,这个侦探小说中的所有主体,还包括拉康本人,在能指的移置过程中无一幸免。拉康急于从这篇小说/文字中提供一个真理,为此窃取了爱伦·坡的“文字”。拉康60年代以来对德里达多有指责,但德里达予以明确否认:
在我迄今出版的文本中,我的确完全没有参照过拉康。我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不仅因为拉康那种以攫取为形式或为目的的欺凌。在我的《论文字学》出版之后,拉康就大量制造这种欺凌,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或者在私下里,或者公开地在他的研讨班上,甚至在他的每一个文本中。从1965年以来,我倒是在提醒自己来读他的探讨报告。[4]
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真的没有受到拉康的启示吗?对此值得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真理的供应商》的确是德里达积蓄已久的大反击。而面对德里达这一次的批判,拉康再没有公开回应,我们在前面看到,他早就开始注意调整自己的结构主义立场,并反思自己的文学文化批判。站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立场,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之间的分歧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便成为学术界的公案,两人的目也已经达成。德里达也承认,不管我们谈哲学、精神分析和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如果不和拉康进行讨论,没有拉康的刺激,最近十年中改变了思想空间的是好是坏的一切事情,都将不会发生。
四、“症候解读”的先驱
拉康阐述过很多作家作品,包括阿尔托、贝克特、纪德和萨德、莎士比亚等。1958年法国权威杂志《批评》发表了拉康的论文《青年纪德或文字与欲望》,该文对精神病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让·德雷(JeanDelay)的纪德研究《纪德的青春期》作了评论。对乔伊斯的分析也早就进入拉康的眼帘,晚期拉康的乔伊斯研究可称为一个典范,展示了文学批评与精神分析之间的互动典范。
1975年,拉康在巴黎的乔伊斯国际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圣状乔伊斯》的演讲。他还就乔伊斯开设了一整年的研讨班,将乔伊斯奉为“圣状”(sinthome)结构的典型。拉康判定:乔伊斯的作品把三界绑定在一起,并且在自己的成名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了“圣状”。“sinthome”是症状(symptome)一词的古法语,拉康将之拆分成“synthhomme”即合成人,暗指主体的自我创造。拉康指出,从《尤利西斯》到《芬尼根的守灵夜》,都暗示出了主体与语言的一种特殊关系,即以主体私人的享乐侵入象征秩序,经由“圣状”对语言进行破坏性的重塑。
“圣状”作为第四个元素或精神装置,具有纽结的功能,将彼时拉康认为应当处于等价地位的现实界、象征界和想象界互相联系了起来。这里涉及拉康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一个基本观念的变化:从强调“父之名”转为强调“圣状”。也就是说,之前种种事物固定下来的能指都是“父之名”,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保证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确立;如今更重要的不是何为父亲的名义,而是父亲的名义命名了什么。比如某些具有精神病结构的人,却没有表现出成熟精神病的典型症状,这是何故?这是因为他们用某一种圣状做了替代。以乔伊斯为例,拉康认为,面对父亲的名义在童年期的缺失,乔伊斯把自己类似于幻觉的意识流写作变成了一种填补或替代,从而在主体的纽结之中避免了精神病发作。拉康注意到1918年乔伊斯的赞助人建议他去荣格那里接受分析,被拒绝后后者立即撤资。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认为,乔伊斯是一个“saint-homme”(圣人)的典范,而不仅仅是某个理论对象或个案。
借由乔伊斯的圣状分析,拉康最终确定了当分析对象变成为“对圣状的认同”之时,精神分析应该如何定义“分析的结束”。这可见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从文学之中汲取了足够的养分,在此他完成了从“症状”到“圣状”的术语转变。圣状是建立在“症候”之上的。弗洛伊德对症候的意义早就多有关注,认为无论是神经病的各种症候如强迫症、健忘症、忧郁症、癔病、焦虑和自恋,还是常人的普通失误如口误、笔误、遗忘等,都是无意识的结果,另有所指,并在文艺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达芬奇的笔记、歌德的日记与其艺术创作的关联等。弗洛伊德《释梦》、《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等早期著作中所论述的心理运作,从词语之间的联想到症状本身的结构,已经可以见出语言的参与。拉康作为弗洛伊德的重新阐释者,对症状与言语的关联加以深化,不但强调能指的优先性,而且主张在“能指链”的概念中考量各种症候的意义:“能指只有在与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中才有意义。症状的真实存在于这个关联之中”[2]拉康进而引入雅各布森结构语言学的隐喻/换喻概念,得出结论,症状也是一个隐喻。
如果说乔伊斯与“圣状”的关系揭示,向我们展示了拉康“症候解读”的能力,那么“症候解读”作为一种批评模式,最终是在阿尔都塞那里得到确认的。阿尔都塞受拉康的理念和方法论启示,用“症候解读”来分析《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随后有马舍雷将之引入文学批评,更有乔纳森·卡勒对“症候解读”做出了新解和重构。卡勒进而将文学批评分为鉴赏性阐释和表征性阐释,认为前者关联文学研究,后者关联文化研究。“症候解读”的这一发展脉络,正可显示出拉康对于批评作为生产环节的深远影响。
五、对拉康的批评
拉康当然没有少遭非议。除了德里达、德勒兹等的批评,精神分析学内部对拉康绝对导师的地位也日益不满,比如在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双重领域中成就瞩目的安德烈·格林(AndréGreen),其对情感观念的重视,便显示出与拉康不同的路径。拉康引导他走向前语言阶段的著名命题“无意识如语言的结构”,在格林这里变成了对情感、冲动的关注。在格林看来,情感、冲动和感官-知觉等,都是意义的实体成分,在语言中是不可化简的。进而视之,无论是德里达还是格林等非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都是引导法国后女性主义的启明星。伊瑞格瑞、克里斯蒂娃等后女性主义批评家,拉开了针对拉康这个原型父亲的叛乱。对于1966年还是学生的克里斯蒂娃来说,拉康曾经构成了一个绝对事件。拉康以法语为母语的分析策略,向她这个对语言异常敏感的异域求学者散发出了特殊魅力。她认为,拉康在重返弗洛伊德的过程之中,重拾了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对语言的关注,并在结构语言学的环境下加以扩展。他开发了语言的一种力量,来封锁和解锁种种心理抑制、症状和焦虑,这当然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拉康是最自然不过表露了他的法语与法国特质。这里既有巴洛克式的古怪新奇,也更见出文学的天性。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克里斯蒂娃日益感到拉康数模化、游戏化语言的方式存在着局限,认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阐释被迫封闭在词语游戏、语音元辅音的形式化和纯粹解构之中,而情感和冲动的成分受到了相当的忽略。反之克里斯蒂娃主张精神分析的特殊原创性,正在于人类意义活动中不均匀的、“异质性的”概念:它既是(心理)能量和(思想)意义,也是冲动和能指(语音)。克里斯蒂娃终而从拉康走向了格林的立场,并在《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中提出了语言异质性与冲动这一对概念。
综上所述,拉康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将语言学与精神分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结合,指出无意识犹如言语活动,由文本的研究来揭示一个不同以往的主体:他不再是词语的操纵者,而是词语的被表现者。在无意识作为更原初主体这一意义上,作家更是一个被语言分裂的主体。拉康曾经被人贴上批评家这一类标签,称不是个诗人,而是首诗,一首正在写作中的诗,尽管看起来像个主体。但是毋庸置疑,即便拉康拒绝被人称为批评家,甚至有一种反文学、反哲学的野心,然而继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之后,拉康再一次从心理学和医学界的内部,架起了精神分析和广阔思想疆域之间的桥梁,得以和文学、哲学乃至神学等人文科学展开对话。这一超越精神分析本身的人文意义,无论如何是不容低估的。
[1]ELISABETH ROUDINESCO.L'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Jacques Lacan[M].Editions:Le Livre de Poche,2009,1400.
[2]JACQUES LACAN.Ecrits,I[M].Editions du Seuil,1966.14;16;231.
[3]德里达,张宁.书写与差异[M].三联书店,2001年,第301页。
[4]JACQUES DERRIDA.Positions[M].Minuit,1972.90.
[责任编校:阳玉平]
I0-03;B565
A
1002-3240(2017)06-0027-05
2017-02-25
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度重大项目: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和研究,批准号:15ZDB084
赵靓(1980-),女,法国巴黎笛卡尔大学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及法国哲学。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