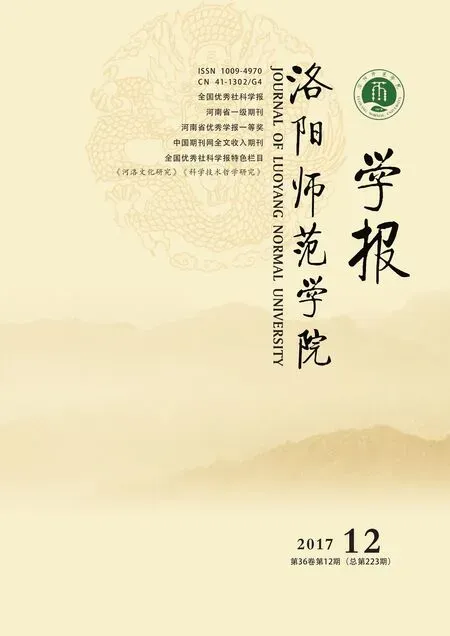语序与汉语主语的界定
周石平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一、 引言
在西方语法传统中, 主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语法概念, 不分析主语(subject)和述谓(predicate), 句法分析就无从谈起。 鉴别一个名词性短语在语句中的功能, 主要借助于格变、 虚词、 谓词的人称和数等特征, 以及语序等四种手段。[1]上述四种手段英语都基本具备, 因此, 除存现句外, 英语主语的界定并无太大问题。
与英语相比, 汉语不具备格变, 也没有谓词的人称和数等特征, 虚词又经常可以省略, 唯一可以凭借的语法特征就是语序。 因此, 在汉语语法研究传统中, 主语的界定就成了一个难题。 有些学者以语序为界定主语的标准, 认为处于谓语之前的一般来说就是主语。[2-5]但是一方面, 语序除了能表示语法关系之外, 同时还是表示语用关系(如话题的表达)的重要手段, 单纯按照语序标准, 很容易把话题和主语纠缠在一起, 这也许就是一部分学者干脆认为主语就是话题的原因[6-8]; 另一方面, 状语也可以位于句首或谓语之前, 只看语序, 不参照意义, 容易把附语也当作主语看待, 如把“今天出发”中的今天看作主语。 还有些学者[9-14]以语义, 即施受关系为标准, 但这样做, 又往往将主语和语义角色(semantic roles)混淆在一起, 尤其无法对被动句中的主语做出合理的解释。
近年来兴起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15,16]把主语、 话题和语义角色分别归属于句法平面、 话语平面和语义平面。 但是, 该理论以及随后的研究并没有提出区分主语、 话题、 语义角色的具体手段, 因而也未能形成有效的主语界定标准。
主语属于句法平面, 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 要界定主语, 当然需要依据句法标准。 要从句法上界定主语, 前提是要把蕴含在语序中的话语特征和语义特征剔除出去。 本文旨在找到将语序中的话语信息和语义特征都剔除出去的办法, 对汉语中的主语做出明确的界定。
二、 语义角色、 论元和句元
在汉语主语研究中, 主语与话题、 语义角色、 论元(argument)等概念往往纠缠不清, 要界定主语, 就需要从主语、 语义角色和谓词论元的相互关系入手。
(一)语义角色和论元
20世纪70年代, 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Chomsky)和格语法的创始人菲儿墨(Fillmore)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关于深层结构中有没有主语和直接宾语之类的语法关系(grammatical relations)的辩论。 Chomsky[17]认为, 语法关系可以分为深层结构的语法关系和表层结构的语法关系, 也就是说, 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中都有主语和直接宾语。 Fillmore[18]则认为, “主语”和“直接宾语”这样的概念只属于语言的表层结构, 深层结构中包含的应该是一种更为初始的关系——由语义格组成的格关系。 严格来说, 这场辩论并没有最后的胜者, 但至少证明了一点:语义格(即施事、 受事, 工具、 与事等语义角色)代表的语义关系与主语代表的语法关系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为了找到语义关系和语法关系的结合点, 迪克森(Dixon)[1]用A(Agent)和O(Object)分别指代及物谓词的施动者和受动者, 用S(Subject)指代非及物谓词的唯一论元, 并把A、 S、 O统称为“普遍语义-句法元”(universal semantic-syntactic primitives)。 Dixon区分了“支点”(pivot)和“主语”(subject), 认为支点是一种表层结构现象, 在“主-宾格”(nominative-accusative)语言中由S/A构成, 在“作格-通格”(ergative-absolutive)语言中则由S/O构成, 主语则是属于深层结构的普适现象, 无论在“主-宾格”语言中, 还是在“作格-通格”语言中, 都是由S/O构成。 罗仁地(LaPolla)[19]虽然也套用了Dixon的“普遍语义-句法元”理论, 却认为所谓“支点”其实就是主语, S/A支点是“主-宾格”语言的主语, S/P支点是“作格-通格”语言的主语(LaPolla实际使用的术语是P, 即Patient, 为了跟宾语区分开, 本文沿用这一术语, 以下凡涉及“受动者”之处, 都用P替代)。
和Fillmore一样, LaPolla认为, 所谓深层结构中的主、 宾语, 其实是混淆了语义和句法的界限, 表层结构中的主、 宾语才是一种句法关系。 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因为Dixon定义的主语是“被动化”(passivazation)或“反被动化”(anti-passivaztion, “作格-通格”语言的特有现象)之前的现象, Chomsky的深层结构也是在被动转换之前, 可见Dixon的S/P主语和Chomsky的深层主语代表的都是语义关系。
然而LaPolla并没有认识到, 他自己提出的A/S主语实际上也是一种语义关系。 以英语和汉语被动句为例, 谓语前的体词性成分并非A或S, 而是P, 但这个P却往往被视为主语, 如“Peterwasscoldedbyhisteacher”中的“Peter”, 或“张三被李四打了”中的“张三”。
可见, 与语义角色一样, 不仅论元A和P是语义关系, 就连不及物谓词的唯一论元S, 也是一种语义关系, 并不对应于主语、 宾语等所代表的语法关系。
(二)论元和句元
进入表层结构之前, 谓词V必须通过添加时态标记或助谓词, 或与其他词组合构成谓词短语, A、 S、 P等谓词论元则实现为谓词短语的论元。 为了区分这两组概念, 不妨把谓词短语标记为V′, 把谓词短语的句元表示为A′、 S′、 P′, 其中A′代表谓词短语的施动者, P′代表谓词短语的受动者, S′代表谓词短语的唯一论元。 最终, V′实现为谓语(predicator), A′、 S′、 P′实现为不同的句元(clause elements, 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句子成分或句法成分)。 首先看英语中的例句:
(1) a. [John] [open] [the door]
A V P
b. John ∣opened∣the door.
A′ (A) V′(V) P′(P)
c. The door ∣was opened ∣(by John).
S′(P) V′ (V) (A)
d. * The door opened John.
(2) a.[John] [come]
S V
b. John ∣came.
S′(S) V′ (V)
c. John ∣is believed to∣(John)∣ have come.
S′(P) V′ (S) (V)
d. * Came John.
在英语中, 谓词的论元A和S的默认位置处于谓语之前, P的默认位置总在谓语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 A、 S、 P和A′、 S′、 P′是对应的, 如(1)b和(2)b。 但是, 在经过某些形式的转化(如被动转化)之后, A、 S、 P的位置会发生变化, 此时A、 S、 P和A′、 S′、 P′不再对应, 如(1)c和(2)c。
在汉语中, A/S的默认位置同样位于谓词之前, P的默认位置在谓词之后, 例如:
(3) a.张三 ∣打开了 ∣门。
A′ (A) V′(V) P′(P)
b.门 ∣ 被张三 ∣ 打开了。
S′(P) V′ (A V)
c. *门打开了张三。
(4) a.客人 ∣吃过了。
S′(S) V′(V)
b.*吃过客人了。
从以上例句中可以看到, 英语、 汉语中的主语都不是由A和S构成, 而是由A′和S′构成。 换言之, 在这两种语言中, 主语由直接构成谓语的谓词短语的论元构成, 而不是由谓词的论元构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 A、 S、 P的默认顺序是语义上的语序, A′、 S′、 P′的顺序才是句法上的语序。
三、 汉语的核心句
施兵[20]提出, 汉语核心句是必有成分按照默认位置构成的主动式、 简单、 肯定陈述句,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主+谓+补”、 “主+谓”、 “主+谓+附/主+附+谓”、 “附+谓+主”(存现句)、 “主+谓+宾”、 “主+把/将+宾+谓+附”、 “主+谓+宾+补”、 “主+谓+宾+述谓”, 以及“主+谓+宾+宾”等9种核心句型。 施兵的默认语序很大程度上是指主语、 谓语、 宾语的默认排列。 不过, 仅仅用主谓宾的位置来界定核心句, 会使核心句的范围大大扩大。 例如:
(5) 作业∣做完了。
(6) 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施兵认为, 像(5)和(6)这样的语句, 实际上是宾语前置加上省略主语造成的。 可是, 在主语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 认为“作业”和“老朋友”不是主语的理由是什么?正因为主语还没有得到界定, 只要我们将这两个成分当作主语, 就可以相应地将(5)和(6)视为核心句。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在于施兵的核心句要以主语、 宾语的界定为前提条件, 但按照他的思路, 主语又要在核心句中界定, 难免有循环定义之嫌。
因此, 在界定主语时, 为避免循环定义, 同时排除语义语序的干扰, 需要重新界定汉语的核心句。 在英语中, 像(1)b和(2)b那样, A′、 S′、 P′按照A、 S、 P的默认位置排列而成的句型就是核心句。 同样, 汉语的核心句也是A、 S、 P按默认位置排列而成的, 如(3)a和(4)a。 在由核心句转化而来的句型中, A、 S、 P有可能发生移位或省略, 如(3)b。 A、 S、 P的原有位置也有可能被其他成分占据, 例如:
(7) a.我∣做完∣作业了。
A V P
b.作业∣做完了。
P V
c.作业∣做完了, ∣我。
P V A
(8) a.十个人∣吃∣一锅饭。
A V P
b. 一锅饭∣吃∣十个人。
P V A
可见, 要界定核心句, 必须借助A、 S、 P的默认顺序。 于是, 本文提出了界定汉语核心句的新标准:核心句是由必有句元构成, 并且除存现句外, A和S直接出现在谓语之前、 P出现在谓语之后的简单、 肯定陈述句。
这样定义的核心句在分类上与施兵[20]没有区别, 依然是9类。 所不同的是, 很多被施兵定义为“主谓”或“主谓宾”的句型被排除在核心句之外, 如“锁已经扭断了” 或“便道走行人”。 此外, 用这种标准来界定核心句, 被动句将被自动排除在核心句之外, 因为在被动句中, A不出现, 或者出现位置不在谓语之前。
四、 汉语主语的界定
在提出了核心句的概念及界定标准之后, 就可以区分核心句和非核心句, 并根据具体情况对非核心句进一步分类, 在每一具体的类别中依据语序及其句元和谓语之间的语义联系, 分析A′、 S′、 P′的组合情况, 从而对主语做出界定。
(一)核心句的主语
如果一个语句中, A、 S、 P出现在默认位置, 并且只有必有句元构成, 就可以认为该语句是核心句型。 核心句中的A、 S、 P和A′、 S′、 P′重叠, 因此, 一旦确定一个语句是核心句, 就可以认定其中的A′和S′为主语。 我们用下画线标记主语, 以下例子中的下画线部分是A或S, 同时也是主语。
(9) 十个人吃一锅饭。
(10) 大字笔写大字。 *大字写大字笔。*A、 S、 P代表的语义关系比Fillmore的格关系抽象程度更高, 但也有一定联系, 如根据谓词意义, A可以由施事、 工具、 来源、 处所等语义格构成, 就是不能由受事格构成。 同理, S也不能由受事格构成。 因此, (10)—(12)中的名词性短语虽然不是谓词的施事, 却是谓词的A无疑。 (10)—(12)中的A和P之间的语序不能交换, 就是这个道理。
(11) 这块玉……只好碾一尊南海观音。 *这尊南海观音…只好碾一块玉。
(12) 驻华大使也换了马歇尔。 *马歇尔也换了驻华大使。
(13) 一转眼三年就过去了。
可见, 核心句的主语只能直接位于谓语之前, 也就是说, 核心句的主语凭借语序就可以判定。
(二)非核心句的主语
相反, A、 S、 P没有按照默认语序排列的语句, 就可以认为是非核心语句。
要界定非核心句的主语, 首先必须确定非核心句的类型。 非核心句是由核心句经过不同的过程转化而来的, 有些转化能导致A、 S、 P的隐现或位置移动, 但不会造成A、 S、 P和A′、 S′、 P′的分离, 有些转化却能导致A、 S、 P和A′、 S′、 P′分离。 我们把前者称为修辞转化或话语转化, 把后者称为语法转化, 语法转化又分不同的情况。 篇幅所限, 本文只分析非核心句中的简单句, 复合句略去不谈。
1.修辞转化(话语转化)
如果一个语句的谓词短语由中心谓词添加时态标记构成, 同时A、 S、 P又不在各自的默认位置, 就可以认为该语句经历了修辞转化。 修辞转化大致相当于施兵[20]提到的信息包装, 包括省略、 移位、 拆解、 添加、 重复、 前置和省略、 合并等转化手段。 本文不谈复合句, 因此把合并排除在外。 修辞转化只能造成位置的改变, 不会改变语法关系, A′、 S′、 P′是跟着A、 S、 P同时隐现或移动的。 也就是说, 经过修辞转化而来的非核心句的主语与核心句保持一致。 因此, 只要将分别A、 S、 P还原到各自的位置, 就能确定主语。 例如:
(14) 一转眼(时间)就过去了三年。 (省略)
(15) 饭吃过了。 (宾语前置+主语省略)
(16) 他头也不回, 言也不答。 (宾语前置)
(17) 作业做完了, 我。*“完”可以理解为动作做“完”, 也可以理解为作业做得“一点不剩”。 理解为前者时, “完”可视为态标记; 理解为后者时, “做完”可视为动补结构。(宾语前置+主语后置)
施兵认为(14)是主语后置句型, 由“一转眼三年就过去了”转化而来, 这种看法并不合理。 (17)才是主语后置的例子, 因为主语后置一定会有标记(在口语中表现为停顿)。 我们可以说“作业做完了, 我”, 却不能说“作业做完了我”, 就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14)应该是个省略句, 由“一转眼时间就过去了三年”转化而来, 省去了主语“时间”。 (15)是宾语前置加主语省略, 由“我吃过饭了”转化而来, 省略了主语“我”。
提出修辞转化, 目的是为了剔除语序中的话语因素。 从(14)—(17)中可以看到, 把经过修辞转化而来的非核心句还原成核心句以后就可以发现, 主语仍然是位于谓语之前的A′或S′。
2. 语法转化
谓词构成谓词短语之后, 有可能会造成A、 S、 P与A′、 S′、 P′的分离。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分辨谓词的论元和谓词短语的论元, 否则就容易把本属于语义特征的默认语序当作语法特征, 从而影响主语的界定。 分析语法转化, 就是为了剔除语序中的语义因素。 语法转化又可以分为以下4类。
一是被动转化。
被动句是A、 S、 P与A′、 S′、 P′分离最明显的例子。 被动句的谓语由语法助谓词“被”和实谓词构成。 不需要交代A的时候, 汉语一般不使用被动句, 但如果A和P同时出现, 要把P置于谓语之前, 就需要使用被动句。 例如:
(18) 早起的虫儿被鸟儿吃。 *早起的虫儿吃鸟儿。
被动转化实际上就是把主动句中的P转化成被动句中的S′, 同时把主动句中的A转化为旁格。 也就是说, 被动句的主语是转化而来的S′, 可以表示为S′V′句型。 可见, 把被动句中的主语称为“受事主语”是不准确的, 被动句的主语只是中心谓词的受事, 而非谓词短语的受事。
二是情态转化。
有些情况下, 由情态助谓词和实谓词构成的谓语也能分离谓词论元和谓词短语的论元。 例如:
(19) 酒要一口一口地吃。
(20) 偷来的锣鼓打不得。
人们通常把(19)—(20)析为宾语前置外加省略主语的例子, 即“酒(大家)要一口一口地吃”和“偷来的锣鼓(咱们)打不得”, “酒”和“偷来的锣鼓”是宾语, 省略了主语“大家”和“咱们”。 这是只看到了中心谓词“吃”和“打”所带论元的默认语序, 而忽视了谓词短语造成的转化。 表达类似意义的例子还有“书要静下心来看” “违法的事情做不得”等。 “要”的意思是“需要”, “……不得”的意思是“不能……”, 陈述的都是谓语前面的名词性短语的性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 (19)中的“酒”已经从“吃”的论元P转化为谓词短语的S′, (20)中的“锣鼓”也由“打”的论元P转化成了谓词短语“打不得”的S′。 因此, “酒”和“锣鼓”才是主语。
三是词类转化。
有些中心谓词在与其他词结合构成谓语之后, 已经失去了行为谓词的属性, 有点类似于形容词或系谓词了。 这类转化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
(21) 中国话容易学, 中国文字难学。
(22) 这个菜好看, 但不好吃。
(21)中的“中国话”和“中国文字”虽然是“学”的论元P, 但“学”与“容易”和“难”分别结合之后构成的谓词短语已经具有形容词的特征。 同样, (22)中“吃”的行为特征几乎完全褪掉,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已经将“好吃”和“难吃”标注为形容词。 可见, 这类语句中的论元P已经转化为谓词短语的论元S′, 成为语句的主语。 第二种情况如以下例句所示:
(23) 你的账记得清楚。
(24) 这种事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25) 锁已经扭断了。
(26) 报纸还没印出来。
这种情况就是汉语谓词的“中动用法”。 以(23)为例, 尽管谓词“记”的论元P是“你的账”, 论元A是“你”, 但是由于“记得清楚”主要表达的是“清楚”, 而不是“记”, “记”在语句中的作用接近于系谓词。 也就是说, 谓词后面需要跟一个表示P的属性或状态的词, 这时“记”的论元P已经转变为谓词短语“记得清楚”的S′, 成为语句的主语。 (24)—(26)也是同样的情况。 可见, 所谓中动用法, 实际上就是述补结构。
述补结构与修辞转化中的“前置+省略”句型, 如“饭吃过了”形式上非常相似, 区别仅仅在于, 后者中的谓词短语由谓词添加态标记构成, 态标记并非独立的词, 因此这种谓词短语并非述补结构(“吃完”“做完”中的“完”除外)。
四是词义转化。
在一些情况下, 谓词词义的转化也能改变语句的语法关系。 第一类是所谓的“主宾换位句”, 例如:
(27) 便道走行人。
(28) 一锅饭吃十个人。
(29) 一间房住两个人。
谓词“走” “吃” “住”的论元A本来都是“人”, 但在(27)—(29)中, 这三个词已经具有“供…走/吃/住”的意思。 在这样的句型中, “人”由“走”的论元A转化成了“走”的句元P′, 而“便道” “一锅饭”和“一间房”则由论元P转化成了句元A′。 这类语句仍然是A′V′P′句型, 主语是转换后的A′, 只是论元A和P互换了位置。 因此, 这类句型应该被称为“论元换位句”, 而不是“主宾换位句”。 此外, 这种转化只是词在特定构造中的临时转化, 因此这样的句型应该属于非核心句。
第二类是由一些特殊谓词构成的语句, 例如“淋雨” “晒太阳” “烤火”“我们明天考语文”等等。 石毓智[21]认为这些谓词具有“双向矢量特征”, 可是这些情况只是这些谓词在一些固定结构中的特殊用法, 算不上固有特征。 因此, 这样的句型也应该归入非核心句, 和第一类情况一样, 也经历了论元换位的转换过程, 主语是转换后的A′。
五、结论
在区分了谓词的论元和谓词短语的论元、 界定了汉语的核心句、 划分了不同类型的非核心句, 以及分析了核心句和不同类型的非核心句中的主语之后,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 核心句是由必有句元构成, 并且除存现句外, 谓词的论元A和S直接出现在谓语之前、 论元P出现在谓语之后的简单、 肯定陈述句。
其次, 除存现句外, 在剔除了语序中的话语因素和语义因素之后, 无论核心句还是非核心句中, 界定出来的主语都是由直接位于谓语之前的谓词短语论元A′或S′构成, 没有所谓的主宾换位句型(P′V′A′)、 受事主语句型(P′V′), 也没有主语后置句型(V′ S′)。
再次, 在剔除了语序中的话语因素和语义因素之后的, 剩下的就是作为语法特征的语序, 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序完全能够作为界定主语的手段。
[1] DIXON R M W.Ergativity[J].Language,1979,55(1): 59-138.
[2] 邢公畹.论汉语造句法上的主语和宾语[J].语文学习,1955,45(9):25-27.
[3]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9-34.
[4]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95-97.
[5]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0-22.
[6] 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26-29.
[7] HOCKETT C F.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M].New York: The Macmilian Company,1958: 201-203.
[8]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5-48.
[9] 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4-25.
[10] 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M]∥吕叔湘,译.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45-480.
[11] 王力.主语的定义及其在汉语中的应用[M]∥《中国语文》杂志社.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56:169-180.
[12] 高名凯.从逻辑和语法的关系说到主语宾语[M]∥《中国语文》杂志社.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北京:中华书局,1956:181-191.
[13] 陈平.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J].中国语文,1994,21(3):23-25.
[14] 邢福义.汉语语法三百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25.
[15] 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2):4-21.
[16] 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57-65.
[17] CHOMSKY N.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65: 128-147.
[18] FILLMORE C J.The Case for Case [M]∥BACH E,HARMS.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New York: 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68: 1-88.
[19] LAPOLLA R J.Arguments against “subject” and “direct object” as viable concepts in Chinese[J].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1993,63: 759-812.
[20] 施兵.汉语中的核心句型和主语[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09:80-107.
[21] 石毓智.语法的概念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35-153.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