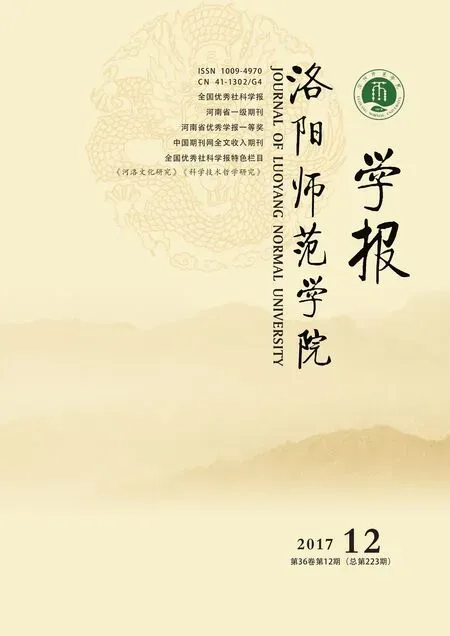并立竞进与折中调和
——评《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胡春霞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8)
《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是张宝明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本著作。作为1995年南京大学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能够与余敦康的《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以及林安梧的《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等当时已成名的专家学者的书籍一同入选“‘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论丛”这一书系, 足见此书的价值和意义。书中提出的许多具有前瞻性、 前沿性的观点, 被后来的学术界一一深化、 印证。这些观点现在看来或许司空见惯, 但是20年前就能够提出, 实属难得。悠悠岁月, 虽然已过去20年之久, 但现今读起来却依然不过时, 依然能够引领读者进入鲜明的历史现场, 感受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纠结, 阅读此书, 仍然能带来很强的启迪意义。
一
阅读此书, 首先让人印象深刻并肃然起敬的是作者沉郁而深刻的现实关怀。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抑或学术论著, 必定饱含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审视、 反思以及质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市场经济勃兴, 伴随着经济的转型, 政治、 文化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那是一个充斥着“读书无用”论、 质疑“教授值多少钱”的时代, 人文精神失落, 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进退失据, 转型抑或坚守, 人文知识分子经受着又一次的“两难”。同时学术界、 思想界批判、 检讨、 贬低激进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在对人文学者的质疑以及保守主义见涨的双重坐标中, 那些具有理想和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如何正视现状、 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也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难”话题, 他们内心的煎熬与苦楚更与何人说?这些“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现象”, 作者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悟, 而这样一个“每一个文学中人或学术中人必须承受的命运”(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4页), 同样也在深深地拷打着作者的内心世界。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嫁接点, 寻求一个“能真正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谐一致的现代化理想境界”([美]舒衡哲著、 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序言第2页)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舍其一生而孜孜矻矻、 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凡此种种, 都需要通过回望过去来看清现在并着眼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选这么一个历史现象去做, 根本着眼点并非为‘过去’而‘过去’, 而在现在与未来, 并通过再现过去而映照生活的未来图景”(导言, 第2页)。一部五四思想史, 其实就是一部激进主义人物思想的演变史, 而伴随演变始终的, 有两条线索, 那就是(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作者正是抓住这了两条主线, 从五四激进派在“启蒙”与“革命”这两种近代中国摆脱困境的“工具”之间的“两难”这一独特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理路。 不但能够更好地“再现过去”, 看清现代中国之所以然的原委, 而且也能够“着眼未来”, 从总体上理解五四以后现代性中国的走向。历史是固化的, 是死亡的, 但是历史的继承者、 研究者却是鲜活的生命个体, 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打捞过去的同时, 再造时代的辉煌, 从而“在死亡的历史的废墟上营造一方生命的绿洲”(导言, 第2页), 为中国的现代性走上坦途提供一个历史注脚——“事实上, 我们在行文中已力求对该团体‘两难’的来龙与去脉、 原委曲折、 正误得失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综合, 目的就在于从中得出对今人不无裨益的启示”(第285页)。
该书所论的“激进派”, 主要是指围绕《新青年》杂志, 以文化批判和思想建设起家的一群思想先驱。由于这一文化阵容人才辈出、 声势浩大, 陈独秀、 胡适、 李大钊、 周作人、 钱玄同、 傅斯年等每一个五四巨子又几乎各领风骚, 各有其特点, 因而不能简单地划一, 同时选择某一个人单独进行个案研究则很可能失之偏颇、 以偏概全。于是作者便选取最具典型意义的陈独秀、 李大钊、 胡适、 鲁迅等四位《新青年》最主要的作者和编辑作为立论的中心, 采用纵(即历时性)横(即共时性)交错的笔法, 追根溯源, 通过对这四位人物思想的综合分析, 以此来捕捉五四时期激进派同仁自身思想的逶迤曲折, 在探幽阐微中发现他们的共识与歧义、 组合与分化, 进而编织出激进派“两难”的心灵图景:一是表现在《新青年》团体内部两个走向的对立与冲突, 即同仁之间“改良”与“革命”的紧张;二是表现为激进主义者自我精神的紧张, 即同仁本身“个人”与“社会”的自我困惑。以此分理, 该书的第一章“文化与政治的歧途”和第四章“提高与普及的走向”、 第二章“多元与一元的转换”和第三章“个体与群体的紧张”分别与“两难”相映照。
对于“第一难”, 自从20世纪最壮丽的精神日出《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诞生之日起, “革命”走向与“改良”走向的纠缠就潜藏在了《新青年》同人的阵营里。前者以陈独秀、 李大钊为代表, 以“社会运动”为使命;后者以胡适、 鲁迅为中坚, 以“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胡适语)为己任。从编辑方针的龃龉、 “立人”之歧义、 “问题与主义”, 到“不党与有党”、 化大众与大众化、 进“塔”与出“塔”等, 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两难的选择。强烈的目标感, 使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以西方民主理想为灯塔, 走上渐进主义之改良途径;急切的现实感, 使陈独秀等革命者在个人与社会的紧张中冲破原有的价值框架, 采取直接、 具体的行动, 走上“根本解决”的革命路途。但是应该看到, 二者在救国拯民、 走向现代性总目标上同气相求。 “改良”与“革命”作为两种不同的路径, 各有自己的功能和价值, 但是当双方都固执己见, 以真理的使者自居时, 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矛盾。
对于“第二难”, 又可理解为激进派同仁自身在“以多元思维模式为本位, 思想上要求个性自由”与“以一元思维模式为本位, 要求集中权力, 统一思想, 在大众意志中实现心中理想”之间的困惑。一方面, 应该看到, 在五四激进派笼统的抑“东”扬“西”的背后, 还有着陈独秀“并立而竞进”(《通信》, 《新青年》3卷1号, 1917年3月1日)的文化韬略以及李大钊的“调和论”等多元思维的价值追求。但是理想归理想, 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对巴黎和会的失望以及对西方国家的清醒认识, 使得志在寻求真理以救国的他们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实用主义理念下, 从现实需要出发作出抉择, 由“学西”转向“师俄”, 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能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从“并立竞进”的“多元”到马克思主义统一综合的“一元”, 从“兼容并包”到“择定一派”, 陈独秀等人被“逼上梁山”而进行价值转向时内心的彷徨、 紧张、 反复、 痛苦昭然若揭。另一方面, 虽然陈、 胡等人极力提倡个人本位主义, 将“个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他们并未将“社会”置之度外, 而是极力让两者在适度的张力中保持平衡。五四启蒙主义者原本的取向是先通过文化运动, 启蒙国人, 实现伦理的觉悟, 中间经过国民运动, 最终达到改造社会、 救国拯民的目的, 但是腐败、 堕落、 散漫、 软弱的国民劣根性又使得文化运动不能在短期内取得理想效果。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是继续坚守启蒙, 还是转向直接革命, 矛盾和痛苦交织于胸。最终, 陈独秀等激进派同人从实用、 速成、 功效的现实出发, 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 “社会”压倒“个人”, 将重心放在了开展国民运动的革命上面。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为了开展革命, 不但要收敛原来个性自由的理想, 而且还要与尚未“化”成全新人格的大众为伍, 一向具有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内心之“两难”可想而知。正如著名汉学家舒衡哲总结的那样:坚信“没有启蒙就不能救中国”“以改造同胞的旧思维习惯”为自己“文化使命”的五四知识分子, “最终不得不改变他们对于已经启蒙了的思想家与尚待唤醒的民众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他们“不得不改变了自视高于或优于平民、 以新文化领导者自居的想法, 而去学习做革命群众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同行者”(舒衡哲著、 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导言第12—13页)。五四激进派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与纠结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应该看到, 作者虽有“两难”之分理, 但是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 四章内容绝不是相互孤立的, 而是互相补充、 互相说明, 充分体现着“两难”的立论意图。
二
作为20世纪的焦点事件, 五四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同时五四又是一个常说常新、 永不过时的话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对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自然汗牛充栋。在众说纷纭的学术界中, 作者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观点, 作出了自己特有的学术贡献。
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 作者撇开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常见理路, 而从论争的哲学背景出发, 探索其源起的深层思想本因, 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两种“主义”的冲突——渐进改良主义与根本解决主义的冲撞, 是激进派同仁内部文化启蒙的渐进(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依托)与政治革命主义(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为背景)两个走向的深化。这一点从胡适后来谈到这场论争时的那段话就足以证明: “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 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 忍不住了, ——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 ——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胡适:《我的歧路》, 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1卷), 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第310页)原来, 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心中所信奉和遵循的“主义”。胡适并不是反对“主义”, 关键在于用哪种“主义”去解决问题。对于“问题”与“主义”, 不能流于字面理解, 认为“问题”就是“问题”, “主义”就是“主义”, 而是论争的双方心中都有自己的“问题与主义”。同时, 作者认为“问题”与“主义”两方本来应该形成共同为用、 并立互补的格局, 因为“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分析对待”, 但是胡适与李大钊两人却“未能在哲学层次形成真正的交流, 结果变成了各自心中‘问题’与‘主义’的统一”(第59页)。
对于五四激进派的激烈反传统, 作者认为, 这需要理清“儒学”(孔学)、 “孔教”(礼教)、 “独尊”(一尊)这三个主要概念。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批儒”, 其实是反对“孔学”被一种无形的政治力量所挟持后, 上升为政治意义上一种统治“工具”的、 独尊僵化的、 用以统一人心的“孔教”, 而非文化概念上的“孔学”和孔夫子本人。进一步说, 即是反对“一元的文化意识”。在此基础上, 作者认为, 中西文化冲突究其根本是“两种文化意识的冲突, 即开放、 民主的多元思维与封闭、 专制的一元思维之对峙”(第94页)。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 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的说法, 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第7—49页), 而当事人胡适曾将此一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71页), 历史学家何干之则将其包含在中国的“启蒙运动史”(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 生活书店1947年版)之内, 舒衡哲更是直接以“中国启蒙运动”([美]舒衡哲著、 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命名, 同时周策纵也认为五四运动“更接近于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美]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471页)。而在该书中, 作者独辟蹊径, 抓住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最本质特性, 并以此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照, 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双重性的结论, 可以说是对学术界的一种“纠偏”, 时至今日亦不能忽视。西方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将“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译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作为文艺复兴的根本要义, 而在中国, 无论是陈独秀、 李大钊, 抑或胡适、 鲁迅, 都将具有独立意识、 完全自觉的“新人”放在第一位, “个人本位主义”成为时代最强音。同时, 开放的世界主义意识亦是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的不懈追求, 这从《新青年》杂志的封面设计上即可领略其意: “以印有五大洲四大洋的地球仪为背景,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这两只手一‘东’一‘西’, 洋溢着东西交流、 对话、 开放的浪漫情趣。”(第148页)因此从五四时期“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这两方面来看, 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置于文艺复兴的坐标之上。另一方面, 从“理智与情感的关系以及科学的倡导两个方面”来观察五四, 其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则亦颇为契合, 因此作者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双重特性的结论。应该说, 此一观点在当时还并不成熟, 有待深化。而在此书出版5年后的2003年, 作者在与张光芒先生的对话中, 又一次重复了这一观点(参见张宝明、 张光芒:《百年“五四”: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对话》, 《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1期), 可谓是在该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
此外, 在鲁迅是否参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激进与保守”等方面, 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在某种意义上说, 朱献贞的《启蒙者如何面对革命——鲁迅革命观的历史分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赵歌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化选择》(《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及其《启蒙与革命——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以及贺照田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读书》2016年第2期)等文章都是此一命题的进一步深化和延展。
三
通读全书,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不偏不倚、 保持平衡、 不走极端、 折中调和的中庸之道贯穿行文始终, 在笔者看来, 这正是作者在激进派的“两难”之中寻找到的出路, 也是作者给世人最大的“不无裨益的启示”。
首先, 我们要用一种多元开放的意识和包容的心态、 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个世界, 而不能用这样或那样的命令语气去杜绝异己、 排斥异类、 扼杀异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20世纪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缺乏的是“多元开放的思维模式和自由思想”(第112页),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西文化问题。本来中西两种文化应是一种相辅相成、 并立互补的关系, 应该在持衡中对立统一, 只有这样, 走向现代性国家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平坦、 愈走愈顺利, 但是个别五四激进派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却将二者看作水火不容的两极, 在“分出”优劣、 高下后取一去一, 致使传统与现代断裂。试想: “把中西医视为水火不容的东西, 用一个否定或取代另一个, 能是最佳处方吗?”(第78页)
文化是多元的、 开放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内部结构和独一无二的价值, 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没有优劣之分, 因此我们要具有“不仅是对多重性的信仰, 而且是对不同文化和社会的价值的不可通约性的信仰”的“多元主义”([英]以赛亚·伯林著, 马寅卯、 郑想译:《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第188页)理念。文化的丰富、 多样需要差异, “差异性与谐同性并不完全对立, 文化的共振、 谐同离不开个性、 差异”(第89页), 正如“蒙娜丽莎的微笑”, 我们每个人都各有其观, 但正是这些各有特色的观点才使其充满神秘色彩。一首音乐的优美, 也正是从高低不同的音符中体现出来的。“并立而竞进”, 这就是文化设计的本质与发展进化的真谛, 其要义就在于“它是以多元思维为前提的自由调适”, 这种“自由调适”的文化设计是在多元思维并存下, 不以单方面的思维模式和价值标准规范、 约束对方, 而是“以双方的互补、 相牵为鹄的”(第117页)。“互补”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驱动力, “相牵”则是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思想并存、 文化多元、 学说竞立, 各种文化形态在并立中互补, 在互补中竞争, 在竞争中发展, 这才是一套良性的文化发展机制。
其次, 要防止在强烈的功利主义心态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物极必反、 欲速则不达, 任何事情都需要辩证看待, 任何一方强调过了头, 就会走极端, 就会一错再错, 因此不能在工具理性的狂热下丧失价值理性的标尺, 造成二者的失衡、 分裂。在启蒙思想家眼里, 西方的那些先进理念不仅仅是一种观念, 更重要的是一种反抗旧社会、 建立新社会的“工具”(手段), 比如激进派同人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 在理念意义上, 它们都是“价值”的化身, 但是在形式意义上, 却又极具“工具”意义。这两种理性在激进派同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和“根本解决”的思维下, 在中国的极端偏执造成了“深刻的片面”:“唯理主义和唯科学主义, 不但未能发挥民主与科学应有的作用, 反而在成为一种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后, 屡屡发生倾斜。”(第162页)应该看到, 现代社会的众多病症都根源于价值理性失落和工具理性的泛滥, 一个真正具有自由人格的人, 要以价值合理性为内驱动力, 以工具合理性为行为准则, “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98页)。
陈寅恪有言:“对于古人之学说, 应具了解之同情, 方可下笔。”因为历史的研究者与其研究的对象之间不但有时空上的差异, 还有时代背景、 社会地位、 生活环境、 思想情感等方面的不同, 因此要“神游冥想”, 与立说之历史人物“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金明馆丛稿二编》, 里仁书局1981年版, 第247页)。进一步说, 即不能用现代的意识去代替历史分析, 而作者抱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钱穆:《国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前言)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书中之所以选择陈、 李、 胡、 鲁这四位人物作为代表, 即是考虑到了激进派同人的个人性情和经历等方面的不同, 于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选取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代表。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 应该看到, 不只是在研究历史时需要充分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 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陈独秀、 胡适等人信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理念, 并用之来挽救大厦将倾的中国, 但是如果忽视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而一味将西方理论“原汁原味地移植”到中国, 缺少必要的与本土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 必将带来水土不服的结局, 而“无所作为”(第34页), 甚至适得其反。
光阴荏苒, 一晃二十年已过, 彼时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 现已成为令人尊敬的、 以研究《新青年》文本著称的知名学者, 从其硕士毕业论文“陈独秀的文化选择”到博士毕业论文“陈、 李、 胡、 鲁”等新文化运动“启蒙四杰”的启蒙与革命之“两难”, 再到整个《新青年》群体, 围绕一个中心, 从一个人物到四个人物, 再到一个群体, 由点及面, 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逐步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 最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园地, 作者的学术研究之路非常值得后学之士借鉴。
一则亦喜, 喜的是我们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 一则亦忧, 忧的是现代物质文明在高度发展的同时也在无情地切割着人文精神。在技术至上、 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文知识分子愈加被挤到边缘地带。技术与人文、 精英主义文化与大众文化、 专业体制化与公共关怀等“两难”也在缠绕着当代的知识分子, 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历史中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借鉴与启示, 我想, 这也是学术界对于“五四”五年一小纪、 十年一大纪的真正意义所在。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面对历史编织的事实, 我们是否配做‘五四’的传人?能否跳出过去的掌心?”(第296页)这, 也即是作者带给我们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