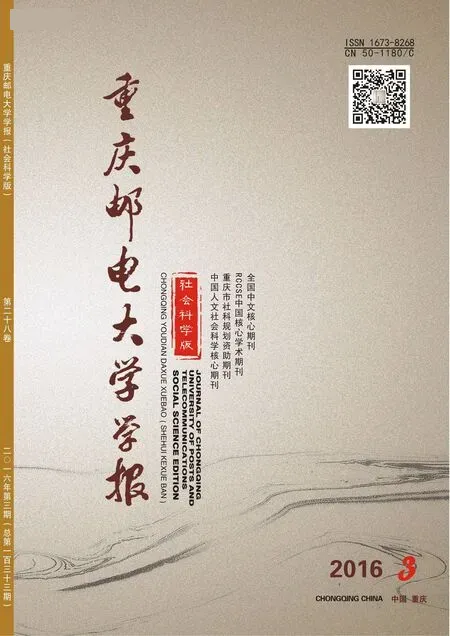风险社会语境下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防控体系之优化*
文立彬
(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澳门 999078)

风险社会语境下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防控体系之优化*
文立彬
(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澳门 999078)
摘要:风险社会语境下,强调把控风险和保障安全,这与日益严重的新型危害行为密不可分。个人信息犯罪作为风险社会孕育下的新型危害行为,具有非接触式犯罪和牟利性犯罪的主要特征。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规定,但部分条款仍有待革新。文章依托风险社会理论对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革新策略,以期推动我国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防控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防控体系;优化对策
一、个人信息犯罪刑事立法概述及困境分析
(一)个人信息犯罪之立法沿革
我国个人信息犯罪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细致的发展过程。在风险社会下,这一方面表明了该类犯罪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和规范违反性,国家通过立法将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强调把控风险;另一方面说明了国家需求与民众诉求具有重合性,个人信息的保护应提高层次,强调安全保障。因此,将个人信息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具有正当性。详言之,2003年至2015年间,《个人信息保护法》经过了专家审议且形成了草案,但目前仍未走到投票表决阶段。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首次规定了个人信息犯罪条款,面对日益严重的个人信息犯罪问题,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施行,一方面扩大了个人信息犯罪主体的范围,增设了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罪状;另一方面增设了有关网络服务者的犯罪规定,就网络数据时代下的刑法规制范围进行了调整。然而,从司法实践的反馈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信息犯罪重要概念界定模糊、刑法规制的手段单一和刑事治理效果不强,这说明刑事立法和实际效果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
(二)个人信息犯罪之本质特征
其一,非接触式犯罪。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骤增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密切,换句话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繁荣了人类的文明,另一方面则是加速了资源的消耗,损害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型犯罪往往具有“非接触式”的特征,如在个人信息犯罪中,受害人的数量之多、地域之广,一方面受害人缺乏被害感知,另一方面造成了案件侦破率低。可知,非接触式犯罪明显区别于传统犯罪中犯罪人与受害人具有的直接接触关系。详言之,犯罪主体广泛且共同犯罪居多,同时正从特殊主体为主转向多种主体共存。就此,《刑法修正案(九)》对个人信息犯罪主体的修订体现了风险社会下刑事立法革新,不再将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圈定于特定范围,而是根据实施个人信息犯罪行为主体的实质,将能够接触到个人信息的主体纳入了刑法体系。同时,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亦属于规制主体范畴。
其二,牟利性犯罪。个人信息所包含的人身特性、经济价值和社会属性,成为了个人信息频繁被侵犯的原因,同时也是刑法保护的重要事由。通过实施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如非法收集、非法出售等,行为人多具有牟取经济利益的犯罪动机。并且,个人信息犯罪还往往引发诸如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二次犯罪。《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六之规定*《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六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特定犯罪的,如诈骗、传授犯罪方法或发布违法犯罪信息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恰好说明了立法者重视该种牵连犯罪的关系。个人信息犯罪作为风险社会下的产物,其行为的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受害人群的广度,还体现于侵害时间的长度,进而在把控风险和保障安全的现状需求下,立法者与民众之间较易达成共识,即以刑法手段规制个人信息犯罪。因此,以行为人牟利目的为主线,体系性地设置刑事规制网络,打击个人信息犯罪及其衍生犯罪,亦是刑法在风险社会中积极介入生活,主动应对风险的应有转变。
(三)个人信息犯罪立法之困境分析
首先,立法模式有待多元化,附属刑法的应有作用有待落实。以立法模式的视角考察个人信息犯罪刑事规制的现状,属于从立法技术的维度出发,对个人信息犯罪的刑事立法体系进行科学分析,因为科学的立法模式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个人信息犯罪的本质属性,为预防犯罪提供有针对性的引导,对打击犯罪提供有力的依据。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模式主要包含刑法典模式、单行刑法模式、附属刑法模式、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模式以及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结合模式。单行刑法是指一部法律就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行为和刑罚措施做出了具体规定。附属刑法是指一部非刑事的法律中包含有涉及犯罪与刑罚的条款。就我国个人信息犯罪立法而言,采用的是刑法典模式,即所有的个人信息犯罪规定均编制于一部刑法典之中,亦被称之为“大一统”式的立法模式。对此,张明楷教授曾指出,“大一统”式的立法模式使得刑法渊源集中且统一,利于维护刑法权威和保障司法适用。截至2016年,我国已经通过了九个《刑法修正案》。然而,采用不断修正刑法典的形式以促使刑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存在诸多弊端,如频繁修正刑法,导致刑法权威下降,更致命的弊端表现在刑法与部门法的脱节,导致行为规范的混乱。张明楷教授亦曾明确提出,将全部犯罪均规定于刑法典之内的方式不切实际,且刑事立法方向应采用分散性立法模式[1]。不难发现,我国九个《刑法修正案》 对刑法修正的内容集中于经济犯罪与行政犯罪,而在风险社会下,新型犯罪层出不穷,反观德国、日本的相关刑事立法,个人信息犯罪这类新型犯罪通常规定于附属刑法之中,进而能够及时调整刑法的规制范围。因此,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益的立法经验,推动我国刑事立法模式朝着多元化发展,充分发挥附属刑法之应有作用。
其次,罪刑法定原则缺乏贯彻。第一,无论是在《刑法修正案(七)》或是《刑法修正案(九)》中,对于个人信息犯罪的罪状描述,均要求“情节严重”*如《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修正案(九)》第十六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实施特定的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前提,在具有严重情节时才追究刑事责任。情节是构成事物的关键环节,缺乏必要的情节就无法追诉犯罪。定罪情节必须在达到足以使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之时,方有刑法学上的判断价值。“情节严重”的表述本身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但何为“情节严重”目前仍未出台法律依据,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混乱。这与风险社会下经由刑法控制风险、保护安全的价值诉求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将“严重情节”具体化及明确化。第二,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出台之时,公民、个人信息等重要概念缺乏明确界定,亦导致了广泛争议。第三,对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等要素的理解亦有颇多争论。唯有进一步厘清上述问题和争议,才能化解当前立法与实践的矛盾。
二、风险社会下反个人信息犯罪立法之理性剖析
(一)风险社会的安全取向与刑法积极一般预防机能之契合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在推动生产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也将风险拔高至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全球性和严重危害性的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风险社会并非具体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状态而是当前人类社会的客观反映。”[2]自“风险社会”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首次系统性提出以理解和反思现代性社会,原本属于社会学范畴的风险社会理论,随着20世纪德国学者普里维特将此理论运用并发展于刑法学领域,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刑法范式,即风险社会理论为刑事立法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对传统刑法进行体系性的反思,在此逻辑下,刑法通过立法转变以积极应对风险社会下新型犯罪的挑战。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实践活动制造的诸多危险,使人类社会踏入了风险社会。概括而言,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其一,风险的全球化,即风险不再局限于单个国家或个别区域,而是影响至整个人类社会。其二,风险的整体化,即风险已经渗透至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三,风险的人为化,即相较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而言,现代社会的风险更多地表现为人为制造。其四,风险的潜在化,即随着风险规模的扩张和程度的加深,风险后果越来越难以预知和控制,且持续周期长久。其五,风险混合化,即风险由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人为风险,从区域性风险发展至国际性风险,由物质性风险演变为非物质性风险,从单一风险转化为多种风险。
个人信息犯罪的现实状况恰好说明了我国正处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科技的高度发展在推动国家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孕育了新型犯罪的土壤,而个人信息犯罪恰为示例。故通过风险社会理论来分析和化解国内严峻的个人信息犯罪现状具有积极意义。在风险社会中,“风险”首先具有人为性,即人为制造的风险,显著区别于传统风险,如地震、火灾、洪水等;其次是国际性,指风险往往跨越国境、波及全球,如个人信息通过社交网络快速、广泛传播;再者为现代性,即风险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还有是危害性,即风险的威胁巨大,一旦发生则难以挽救;最后是不确定性,即风险处于难以控制的状态,一方面难以预警,另一方面补救困难。个人信息犯罪属于风险社会背景下滋生的新型犯罪,故其具有上述风险之特性。因此面对人为制造的风险,施加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行为给社会公众带来更大风险,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可知,风险社会的安全取向与刑法的保护机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强调刑法的保护机能,尤其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理由在于任何社会的良好运行都必须以安全秩序为基础。刑法作为风险社会下的一项社会行为规范应有所转变,从消极的、事后的规制手段向积极的、事前的规制方式演化,从而最大程度地把控风险及保障安全。
(二)个人信息犯罪立法策略之借鉴
Study on Multiple Modes of Reproducing Urban Identity on Nanjing Tourism English Official Websi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OU Yi,WANG Fang,TAO Xiaoting et al 46
其一,强调法典地位和安全保障。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固有成文法的传统,在以刑法手段应对风险社会下频发的个人信息犯罪之时,亦遵循这一传统,即将个人信息犯罪的条款规定于刑法典或专门性立法之中,强调法典的基础作用。德国1970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资料保护法》,在经历数次修订后,目前仍然是德国治理个人信息犯罪重要的法律渊源。德国的《资料保护法》是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性立法,该部法律以信息自决权为宪法基础,将一般人格权作为民法依据,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积极策略,集中体现了刑法保护安全的机能。我国的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亦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定了专门性立法。在刑法典层面,《德国刑法典》第十五章以专门章节规定了侵害公民个人生活和秘密的犯罪,凸显了个人信息犯罪的重要地位,包含的罪名主要有:侵犯通信秘密罪、探知数据罪、侵害私人秘密罪、使用他人秘密罪。在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刑法典》亦对严重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细致规定,如《台湾刑法典》在第二十八章专章规定了妨害秘密罪,其中罪名包括妨害书信秘密罪、妨害秘密罪、图利为妨害秘密罪、持有妨害秘密之物品罪、泄露业务上知悉他人秘密罪、泄露业务上知悉工商秘密罪、泄露职务上工商秘密罪,上述罪名除了图利为妨害秘密罪和持有妨害秘密之物品罪外均属亲告罪,即司法程度的启动需要当事人向司法机关告发。这说明,台湾立法者重视个人信息犯罪的救济,而将刑法追诉列为后续保障措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思想。在我国澳门地区,《澳门刑法典》于第七章“侵犯受保护之私人生活罪”中规定了涉及侵犯个人资料之犯罪,如侵犯私人生活罪、以资讯方法作侵入罪、侵犯函件或电讯罪、违法保密罪、不当利用秘密罪和不法之录制品及照片罪,且规定除“以资讯方法作侵入罪”之外皆为亲告罪。综上,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防控体系以普通刑法和特殊刑法为依据,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形成了双重保障。
其二,犯罪主体覆盖涉及个人信息的个人与单位。在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适用主体涵盖了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团体,同时将不具有营利意图的侵害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也纳入了刑事范畴。在我国澳门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对负有保护和保密公民个人资料之义务者规定了刑罚,保护或保密义务的来源包括法律规定、职务原因、业务要求等。对于实施未经适当许可而查阅、修改、毁坏个人资料之行为人,可依据不当查阅罪、个人资料的修改、毁坏罪追究其刑责。澳门将个人信息犯罪主体范围进行了有限制的拓展,这对于周延的保护个人信息具有肯定作用。
其三,特定的“持有”行为可归责。在我国台湾地区,“持有”特定物被纳入了个人信息犯罪领域,如《台湾刑法典》规定的持有妨害秘密之物品罪。在我国澳门地区,个人信息犯罪可由作为与不作为构成[3],作为包括不当查阅、披露、传播、更改、毁坏个人信息;不作为是指未履行法定的、职务要求的、业务规定的资料保护义务。不当查阅是指行为人在欠缺授权事由之情况下,通过任何方法查阅被禁止查阅的个人资料;披露、传播的实质在于使本不应获知的第三人知晓他人信息。更改、毁坏,包括对个人信息的删除、毁坏、损坏和修改,保护的法益是个人信息的正确性。
三、优化我国个人信息犯罪刑事防控体系之建议
(一)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附属刑法之补充作用
仔细研究我国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不难发现刑事立法模式具有明显的单一性特征,而附属刑法的补充作用仍有待落实。成文法国家多推崇法典化,尤其在刑事立法中,期望经由一部刑法典能涵盖所有的犯罪规定和刑罚措施。然而,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人为风险所具有的危险性已经逐步超过了自然风险,如何在犯罪科技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切实保障安全和有效把控风险成为了当今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具体在立法模式层面,有必要将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进行有机结合,有效衔接非刑事条款与刑事规定,落实附属刑法的补充作用。附属刑法较之刑法典,具有及时性、针对性和补充性的特点,即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犯罪进行立法,提供规制依据,还能为日后的刑法典修订提供可靠参考。从刑事立法视角来考察,德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均将附属刑法列为了刑法典的重要补充,进而在个人信息犯罪领域通过附属刑法的施行,及时将严重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有针对性地预防和打击个人信息犯罪,并且为该国或地区刑法典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修订建议。反观过度强调刑法典的立法模式,该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劣势亦不可忽视,尤其在风险社会背景之下。如在该立法模式下,容易导致刑法典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不协调,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体系缺乏阶梯性等。引导行为、防范犯罪不仅是刑法的重要机能,也是风险社会下重要的价值追求。进而以刑法典为根本,附属刑法为有益补充,通过明确而具体的刑法规定为民众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既能为引导一般民众远离犯罪,威慑潜在的犯罪人,还能为打击个人信息犯罪提供法律依据。
总之,有必要转变我国个人信息犯罪的立法模式,重视和落实附属刑法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罪中增加指引下的条款,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依《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另一方面,针对严重违反行政法、经济法规范的行为,立法机关可在相关的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罪状和刑罚。对于那些已确定的犯罪类型且违犯率较高的附属刑法条款,应移置刑法典之中以确保刑法典之基础性地位。
(二)个人信息犯罪法律概念之明晰
其一,拓宽个人信息犯罪规制主体,建议将“公民”从“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删除。“公民”系法律概念,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或某个地区居民资格的人。“公民个人信息”中“公民”的范围如何界定,这与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范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侵害中国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属于我国刑法规制的范畴,侵犯我国境内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我国刑法效力所及?答案是肯定的。即我国刑法平等地保护处于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十六条之规定,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包含“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提供给他人”,即行为主体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能获得中国公民的个人信息,还可以获取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进而完全可能将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进行出售和非法提供。总之,“公民”属于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不应该通过扩张解释的方式拓展其内涵与外延,进而建议采用“个人信息”之概念。
其二,明晰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针对个人信息犯罪,有观点指出,该类犯罪被置于《刑法》第四章侵害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之中,表明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隐私权,即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受刑法保护,而是个人信息中体现着个人隐私权的那一部分由刑法规制[4]。另有观点主张,个人信息犯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权及公权益关联主体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有,换言之,国家机关以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以外的主体侵害所保有的个人信息,并非刑法规制对象[5]。两种观点都对个人信息的范围进行了限制。第一种观点将个人信息定位于个人隐私权利,排除了不涉及个人隐私的个人信息,如身体、体重等,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实质不仅在于保护隐私权,还在于个人信息所包含的人格权和财产权,因此该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二种观点的基本立场在于公权及公权益关联主体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有,这种观点将与公权或公益无任何关联的普通单位对个人信息的保有排斥于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该观点无疑背离了个人信息犯罪的现状。一方面与公权或公益无任何关联的普通单位,如酒店、网站、中介公司等,均完全可能系统地接触和获取个人信息,将此类行为主体排斥于刑法规制范畴之外,显然放纵了犯罪的产生;另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取消了特殊主体的规定,根据司法实践中侵害个人信息行为主体的特性,拓展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具有合理性。据此可推翻第二种观点的立论。综上,个人信息在一般情况下对应个人法益,特定情形下也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当存在这种需要时则个人信息就具有了公共秩序利益的属性。个人信息的本质在于借此数据能够识别具体的个人。为了精确规划刑法的范围和确保有效的治理效果,“个人信息”概念应尽早明确规定于我国刑法典或附属刑法之中。
(三)个人信息犯罪刑法圈划之拓展
首先,增设非法利用他人信息之罪状。买方与卖方市场的繁荣是导致个人信息犯罪难以有效抑制的原因,因此打击面应进行合理延伸。非法利用他人信息的实质在于行为人缺乏合法事由而利用他人的个人信息。如《澳门刑法典》规定了利用他人秘密罪,该罪责难的是未履行保密义务且利用他人秘密的行为,秘密的范围包括个人信息、企业重要资讯和商业秘密等。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若要构成《澳门刑法典》规定的利用他人秘密罪,需要满足“未经同意”和“造成他人或者本地区损害”者两个要件,损害程度还需法官在审理时具体判断。该罪结果犯的属性说明规制非法利用他人信息的行为,应遵循刑法谦抑行的原则,将犯罪的范围限制在“最小且必要”之内,避免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从风险刑法观来看,对于个人信息犯罪这类新型犯罪,以科技发展衍生性、危害发生潜在性和危害结果严重性为特征,刑法应拓宽对法益的保护范围,提倡安全价值和风险把控。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不难看出,立法者已将未经公民本人同意,向他人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且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本源上预防和惩处个人信息犯罪。为了完善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笔者建议可在我国《刑法》典第二百五十三条中增设“非法利用他人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的规定。
其次,或可设置持有型个人信息犯罪。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转型部分体现在从惩罚结果犯转变为惩罚预备犯、危险犯和未遂犯。其背后的法理依据在于对规范违反说和行为无价值的重视。处罚持有型的个人信息犯罪,其本质在于刑法前置化,防止法律所禁止的风险进一步蔓延。持有行为的实质是行为人事实的或法律的支配、控制特定物品。通过考察持有型犯罪的制度设计,主要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实质预备犯的持有,指的是将行为人持有特定犯罪工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另一种是指具有重大法益侵害直接危险的持有,该种行为方式可以是持有特定物品或是为了掩饰、隐藏重大犯罪行为而持有。第一种持有型犯罪形式,是国家追究实质预备犯的刑事责任而运用的一种立法技术,系抽象危险犯;第二种持有型犯罪的作用在于周延的保护法益,延伸刑法的规制范畴。在个人信息犯罪案件中,行为人掌握着数量庞大的他人信息,在选择受害人时往往能够进行有针对性的侵害。从个人信息犯罪的犯罪链条来看,持有、储存个人信息的行为多处于犯罪链的前端,是发展下一阶段犯罪的前提条件,虽然暂时不会发生显著的危害结果,但是持有行为会高度盖然地引发一连串二次犯罪,如我们熟悉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等。考察到个人信息犯罪具有显著的科技衍生属性和危险潜在属性,使得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显著上升,进而在民事赔偿措施和行政处罚手段无法有效抑制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刑法作为法律最后一道屏障应拓宽其犯罪圈划,设置持有型的个人信息犯罪。
总之,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转型过程总是需要不断审视和思考的,在结合国情和民众认知的基础上,将一步步地推进我国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在个人信息犯罪的治理上,建议转变我国的刑事立法模式,提倡多元化立法和落实附属刑法的补充作用;进一步明晰个人信息犯罪的内涵与外延,建议采用“个人信息犯罪”的概念;拓宽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圈划,将“非法利用”和“非法持有”的行为纳入个人信息犯罪刑法规制范围。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J].中国法学,2006(4):21.
[2]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2.
[3]刁胜先.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形式的分类与构成要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28-35.
[4]蔡军.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立法的理性分析——兼论对该罪立法的反思与展望[J].现代法学,2010(7):108.
[5]赵军.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法益研究——兼评《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争议问题[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2):108-113.
(编辑:李春英)
Optimizing of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rime under the Risk Society
WEN Libin
(FacultyofLaw,Maca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Macau999078,China)
Abstract:The risk society emphasizes on control risk and guarantees the safety. This strateg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new severely harmful behavior. Personal information crime as the new harmful behavior breeds under risk society. Non-contact and profit seeking ar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crime. Although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nine) optimize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rime legislation, some provisions remains to be further innovated. Based on the risk society theory, this paper gives an analysi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rime and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In a word, the study aim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rime in China.
Keywords:risk society theory; personal information crime; crimi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ptimizing measurement
DOI:10.3969/j.issn.1673- 8268.2016.03.010
收稿日期:2015- 07- 03
基金项目:澳门科技大学基金项目:跨域法律协调与合作(0323)
作者简介:文立彬(1987-),男,广西南宁人,澳门科技大学2013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刑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4.3;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8268(2016)03- 0065-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