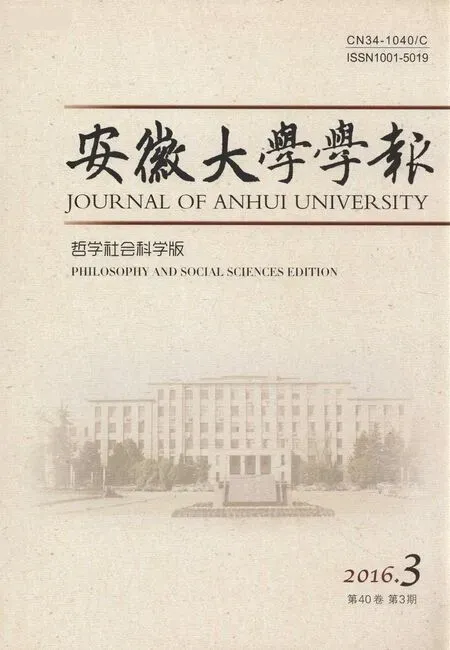案例引证制度的源流
——一个制度史的考察
张婷婷
案例引证制度的源流
——一个制度史的考察
张婷婷
摘要:当前我国对判例法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判例制度与判例汇编。然而,制度发展史的考察表明,案例引证制度同样是形成判例法的重要制度,其重要性甚至远超于判例本身。从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诺曼王朝时期的英国统治者通过引证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基本确立了案例引证制度的雏形;美国则是受“律师职业化”以及法学期刊引证规范的影响,才形成了本土化的案例引证传统;德国仅以职业惯例的方式形成了案例引证传统,而未在制度层面加以确认。反观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恰是由于指导性案例缺少制度化、规范化的引证方式,才导致指导性案例适用率低的现象出现。因此,案例引证制度的构建与发展,将成为案例指导制度后续发展的一大趋势。
关键词:案例引证;制度设计;普通法;法系;案例指导制度
自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来,案例指导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五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案例指导制度的实际效用并不尽如人意。例如:在刑事类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上,有48%的基层法官不清楚最高法院的案例编排与规定,近65%的基层法官选择“根据领导指示”来确定是否适用指导性案例*秦宗文、严正华:《刑事案例指导运行实证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4期。。这表明,案例指导以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意图并未得到良好的贯彻。究其原因,在于指导性案例与司法适用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措施。遍查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可以发现,判例的遴选与汇编虽然构成判例制度的核心与根基,但并未体现判例制度的动态逻辑。事实上,“徒法不足以自行”。判例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得到良好实施,根本原因在于司法职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判例的积极引用,并据此证成一种有利于己方的法律原则、法律依据,从而增加司法说理的权威性*Russell Smyth认为,案例引证能够提升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可接受性。See Russell Smyth,Judicial Prestige: A Citation Analysis of Federal Court Judges,Deakin Law Review, no.1, 2001, pp. 120-148.。在西方,此种判例的动态运用模式被称为“案例引证制度”*由于各国对于“判例”的称谓并不相同,本文在讨论不同国家的案例引证制度时,沿用该国的法律术语,分别使用“判例”“案例”加以表述。但总体而言,“判例”与“案例”具有相同的意义指向。。省察较之,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案例遴选、汇编以及“参考”机制,但就案例指导制度本身而言,该项制度不仅缺乏一种指导性案例适用激励机制(激发法律工作者适用指导性案例),而且在参考、适用过程中缺乏规范的说理模式。
基于此,本文将以一种制度发展史的视角,考察案例引证制度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判例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案例引证制度的生发与制度化,完全同步于判例制度,并为普通法的发展提供了法理基础和制度空间。当然,本文对于域外案例引证制度的探讨,并不构成本文的核心目的。发现以及进化出中国特色的案例引证制度才是本文的最终目标。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会证明,案例指导制度同案例引证制度的相互支持,才能构建起完整的“中国判例法”,从而改革中国司法裁判的说理性与论证方式。
一、制度竞争与案例引证的起源
传统判例制度的兴起历来被认为发源于诺曼时期的英国,判例制度的形成被归功于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然而,法律制度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妙的顶层设计。从梅特兰(Maitland)到麦考密克(McCormick),众多法学家开始检讨亨利二世的改革背景,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传统。无论基于何种学说,判例制度的形成——尤其是习惯法保留与进化——都是诺曼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政治妥协的表现。此外,为了实现全英国范围内的有效控制,诺曼统治者在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同时,引入一系列先进的欧陆法律制度(如巡回法院制度、令状制度以及制定成文法等),试图以制度竞争的方式逐步改革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司法习惯。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英国本土的法治水平,并催生了盎格鲁-撒克逊习惯的司法化现象。最终,这种迫于统治压力的司法继受行为却成为整个英美法律的初级形态。然而,诺曼时期的司法改革只能说明,制度竞争下的司法体系能够接受“依赖习惯的裁判”,却无法明示习惯缘何能够作用于司法。其背后体现的司法逻辑才是案例引证制度的真正核心。既然诺曼统治时期的英国司法继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司法传统,那么,案例引证制度的起源似乎应当远远久于诺曼统治者发起的制度竞争。事实上,史实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些许线索,以帮助我们发现“案例引证”的历史起点。
在诺曼征服之初,习惯在制度竞争中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成功保留了案例引证制度的发生基础。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社会自生自发秩序,习惯可以成为国家治理的催化剂,但同样也能形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保护机制。当外来秩序试图打破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秩序时,除非借助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宣传攻势,否则,单独依靠制度竞争是无法冲破这一原生秩序的——我国元朝与清朝前期统治者推行的“文化认同”等政策亦证明了上述论断——因此,在司法制度竞争上,诺曼统治者一方面面临着制定法缺失的窘境,另一方面又承受着民族习惯法的压制。尤为重要的是,受制于诺曼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数对比,作为统治者的诺曼人无力短时期内改变英国的司法惯例。这就导致诺曼统治者在推行司法改革上全面处于劣势。为了有效掌控英国的司法系统,诺曼统治者只能延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传统。由此,“法源自习惯”“法律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王在法下”的司法惯例得以保留下来,为案例引证制度的兴起奠定了法理基础。
然而,制度竞争的结果并非优胜劣汰,而往往是走向制度融合。诺曼人在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司法传统的同时,也在积极改良英国的司法体系,并成为了案例引证的制度化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制度分别是“巡回法院制度”“陪审制度”“令状制度”。首先,巡回法院制度的设立,开创了现代案例引证制度的制度基础。传统上认为,巡回法院制度旨在纠正地方法院裁判中的不公正现象,但受制于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的“口述性”和经验性,巡回法院的法官(多为诺曼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僵局。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巡回法官开始从过往的案例中寻找相似案件,并援引此类案件做出裁判,从而实现习惯法同巡回法院制度的融合*[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34页。。在制度融合过程中,巡回法院为了提升案例引证的效率,引入案例甄选、汇编机制,最终形成案例引证制度的雏形。其次,陪审制度的引入,提升了案例引证的准确度。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陪审制度的设立旨在“为王室法官提供了一条了解和熟悉各地习惯的有效途径,从而能够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很容易地了解分布于全国的习惯法”*李红海:《亨利二世改革与英国普通法》,《中外法学》1996年第6期。。但对于案例引证制度的形成而言,陪审制度的历史意义远非如此。它不仅解决了巡回法官同当地习惯法之间的对接问题,而且从实质上影响了巡回法官的案例引证行为。这是因为,巡回法官审理的案件往往具有争议性,并且有可能改变地方法院的裁判结果。考虑到地方法院对习惯法的了解程度,陪审制度的引入平衡了习惯法的认知问题,并最终在案例引证问题上获得权威性。再次,令状制度的引入,真正打破了案例引证的职业壁垒,推动案例引证制度在整个司法体系内部的确立。司法意义上的令状制度是指由国王签署的某种命令,指令他人服从国王的决断。但在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中,国王的命令式决断转而由强制性命令发展为指定法院管辖的司法程序。这种令状制度的变革并未引发案例引证制度的发展,直到1285年《威斯敏斯特第二条例》的颁布,令状制度才真正推动了案例引证制度的职业化发展。该条例第24章规定,对于新类型的案件,令状的草拟和颁发可以援引过往相似案例,而仅需在令状中叙明案情*参见李巍涛《中世纪英国令状制度与普通法的发展》,《法律文化研究》2009年第00期。。这种“援例诉讼”(actions on the case)行为,打破了法官在案例引证上的垄断权。而案例作为一种权利的承载方式,开始在整个法律职业范围内具备法的作用。
无论是作为制度竞争抑或制度融合的结果,案例引证制度的生成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司法方式。国家统治者要保证司法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在习惯法与国家司法权之间建立某
种垄断关系,以削弱(乃至消灭)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习惯法上的优势。为此,司法职业化成为案例引证制度得以成型的又一重要举措。从英国普通法的发展进程来看,司法职业化对案例引证制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职业阶层的出现。受到案卷繁复以及普通法的经验传承的影响,案例的准确援引和证成均需要专门的技艺研习,因此,即便盎格鲁-撒克逊人更懂得习惯法的精髓,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繁复的诉讼程序以及高深的辩论技术均为弥散的习惯法提出了制度难题,由此也催生了一些专门致力于司法抗辩的“陈述士”。作为“职业律师”的早期形态,陈述士的出现不仅将司法辩论提升为一种封闭的职业行为,而且在案例引证规范上实现了统一性*密尔松认为,“陈述士以及他们的抗辩,促成了早期普通法的形成”。参见[英]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冬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6页。。此外,14世纪初“律师公会”的出现,进一步催动了案例引证惯例以及法律术语的专门化,保证了司法职业人员内部对“案例引证”式司法裁判的保护和垄断*贝克认为,英国早期的法律,倘若不能归结为判例的话,那么应当归结为法律职业阶层关于什么是法律的“共同认知”。See J. H.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8.。
二是年鉴(Year Book)与判例汇编的出现。应司法职业者对案例引证的需要,自爱德华一世起,案例汇编已经开始在法院内部出现,并由法官确定案例的编纂方式以及引用方式*L.B.Curzon, English Legal History, Maedonald & Evans Ltd., 1979, p.65.。受律师公会以及司法职业化的影响,年鉴的汇编已经难以满足司法职业者的需求,因此,一些私人判例集(private reports)或记名判例集(named reports)逐步代替年鉴,成为案例引证的主要的来源。1865年前后,以律师为主的“判例集编撰委员会(the Couneil of Law Reporting)”着手统一编写案例集以及案例引证方式,并确认了案例引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自此,案例引证成为英国司法审判中一种制度性规则。
三是案例识别技术的司法引入。从令状制度开始,案例引证制度就成为法官“幸福的烦恼”。
原因在于法官已经不再享有案例引证的垄断权,律师、公诉人也可以凭借先例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就导致法官必须在先例相似性上进行选择。然而,囿于案例汇编的不规范性,法官很难在先例的文本记述中获得正当依据。因此,法官试图在裁判过程中引入“案件识别技术”。该项技术一方面采用相似性对比的方式,排除非相关案例的援引;另一方面,法官发挥自身的司法智慧,从相关案例中推衍出某种自然法精神,并据此形成一种全新的判例。由此观之,“案例识别技术”事实上在案例援引上增加了法官的证成义务,从而形成了现代案例引证(援引与证成)制度的基础样态。
二、制度进化与美国案例引证规则
美国承继了英国的案例引证制度,但该过程并非人们预想的那样简单。James H. Fowler 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美国建国之初的几十年中,最高法院并未大量引证先例来裁判案件*James H. Fowler, Timothy R. Johnson, James F. Spriggs II, Sangick Jeon, Paul J. Wahlbeck, Network Analysis and the Law: Measuring the Legal Importance of Precedents at the U.S.Supreme Court, Political Analysis, no.15, 2007, pp.324-346.。这说明,案例引证制度的承接与继受,并未在美国土地上具备当然的法律效力。原因在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在生活方式以及纠纷类型上均有别于英国的传统社会——甚至无法在英国发现类似情况——而且民事案件远远多于刑事案件*根据罗斯曼的研究,在美国早期的案件审理中,民事案件约占案件总量的90%。因此,生活方式的差异决定了英国判例在美国本土法院很难得到适用。See David Rossman, Were There No Appeal: The History of Review in American Criminal Courts,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no.3, 1990, pp. 518-566.。这就导致英国本土的判例很难适用于美国。由此来看,美国司法体系对普通法以及案例引证问题的态度,陷入一种“权威怀疑论(Skepticism of Authority)”的境遇之中,并由此催生了司法体系与法学界关于“引证的权威性(Authority of citation)”的讨论。
“引证权威性”的讨论,反映出制度继受与进化之间的社会压力。生物学知识以及进化论思想表明,事物的进化从来不是原有状态的发展,而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过程。美国早期(殖民地时期)的案例引证即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生物学经验。美国对案例引证制度的改进首先起源于法官的质疑。受此影响,美国早期的法院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是“反对引证说”。该观点的产生受制于美国早期殖民者的知识结构。无论是律师抑或法官,均对普通法的传统以及操作程序知之甚少。因此,美国早期的法院,不仅懈怠于引证先例来说理、裁判,甚至对判决的理由也甚少表述。“反对引证说”的代表人物——塞缪尔·利弗莫尔认为,法官应当按照人际交往的常识来做出判断,“引经据典”则可能阻碍司法的公正*参见[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29页。。基于此种观念,利弗莫尔甚至在同类案件中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裁判。
另一种是“选择引证说”。由于英国判例无法反映美国生活的现实状况,因而无法为司法裁判的说理提供法律依据。在案件裁判中,英国判例在美国法院的引用,应当同美国本身的生活习惯以及宪法精神相适应,否则美国法院可以选择性地修改或废弃它*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页。。这一观念毫无保留地反映在1892年的Van Ness v. Pacard案中*Van Ness v. Pacard 27 U.S. 137 (1829).。该案的主审法官(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在判决书中直言,美国法院并没有完全继受英国的普通法,美国先辈们引进和采纳的仅是适合美国情况(applicable to their situation)的普通法。
再一种观点是“肯定引证说”。该观点主张,引证案例进行裁判,并非引证英国的先例,而是遵循一种普通法的司法模式,即从先例发现某种法律精神,并证明当下判决之正当性的方式。然而,受法官的知识结构与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反对引证说”在美国法院处于主导性地位。可以说,尽管美国司法体系承继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但在案例引证的制度化、规范化问题上,却未延续英国的制度传统。直至17世纪中期,英国法律书籍以及律师执业的专门化,才最终恢复了“引证案例来裁判、说理”的传统。但不同的是,美国案例引证制度的确立,不仅承认了援引判例裁判的法律效力,而且法律书籍等非正式法律渊源也进入司法裁判中,成为法官、律师证明自身观点的依据。
美国对英国案例引证制度的改造和进化远非止于此。受英国案例汇编的影响,美国法院、律师业,乃至法学界均致力于案例集的编纂及引证规范工作。法学家彼得·麦考密克通过考察美洲大陆法院的案例,发现法院对案件的引证基本形成了五类引证方式,从而确立了案例引证制度的基本雏形:
一是层级性引证。这主要是指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裁判结果的引证。出于司法能力与法院层级的正相关关系,人们倾向于相信,来自上级法院的判决一定比下级法院更加专业、更为公正。故此,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裁判结果的引证,事实上旨在引证上级法院的职业权威。
二是一致性引证。该类引证主要适用于同一法院中先例的引证。它一方面显示了法院在某类案件裁判中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表明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以便提升判决的说服力。
三是相关性引证。它主要适用于某些相似性案件的引证,并且引证法院同被引证法院之间往往处于不同的司法层级。因此,同层级性引证一样,相关性引证非常注重上级法院的司法权威。但尤为不同的是,后者适用于相似性案件或相关性的案件说理。这种引证方式在某些新类型案件、疑难案件中较为常用。
四是统领性引证(Leadership Citations)。该类引证方式仅指下级法院引证最高法院案例的模式。理论上认为,最高法院属于国家最高级别的司法机关,具有最权威的裁判指导力。因此,排除案件引证的地域限制,统领性引证是源出于最高法院的判决,故具备通行于全国的司法引证效力。
五是多样性引证。受“法律源自发现,而非创立”普通法传统的影响,多样性引证突破了司法引证的地域与法源限制,将引证的内容扩展至国外司法判例,或者相关书籍、习惯、文化等。可以说,但凡能够有助于说理的内容均属于多样性引证的范围*Peter McCormick, Judicial Citation,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and the Lower Courts: The Case of Alberta, Alberta Law Review, no.4, 1996, pp. 870-891.。
麦考密克的案例引证分类基本反映了美国案例引证制度的现代发展方向。吊诡的是,司法审判中引证方式的规范化,并非首现于司法实务界,而是诞生于法学界。1926年,为了统一法学文章的注释格式,《哈佛法律评论》编辑 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编写了《法律引用指南》(TheBluebook:AUniformSystemofCitation)(后命名为“《蓝皮书》”),以便规范《哈佛法律评论》中论文的编排格式。受此影响,美国各法学院在教授学生法律写作过程中均采用了这一规范格式引证案例。直至Hickory Springs Mfg. Co. v. Evans案*Hickory Springs Mfg. Co. v. Evans, 541 S.W.2d 97, 101. 该案开始引入《蓝皮书》的引证方式,但并未在田纳西州真正确立此种规范。Lewis L. Laska, Tennessee Rules of Citation,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no.4, 1982, pp.547-612.,美国法院才将该案例引证规则纳入司法审判中,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案例引证规范。总体来看,《蓝皮书》并未推动国家司法制度的进步,但实际上,《蓝皮书》的广泛适用的确造就了法律职业者之间的统一性。就司法审判实践而言,《蓝皮书》所确立的案例引证方式不仅深刻影响律师、公诉人、法官、法学教师以及学生(潜在的法律人)的法律文书起草,而且在先例援引、说理以及汇编上,均凸显出强大的制度性。只是这种“制度性”根植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并外放于国家司法体系之中。从此种意义上来看,美国案例引证制度的进化模式属于主动进化型的,它有别于英国案例引证制度的国家建构模式,并产生了同国家建构模式相同的制度效果。尤为甚者,由于案例引证规则形成的自主性、统一性,美国司法界从法学学生的培养开始,便确立了一种司法职业化的发展路径。
然而,恰恰由于美国“案例引证规则”以及案例引证制度的自主性,案例引证的规范模式极易遭受职业内部的挑战。1999年《ALWD引证手册》(TheALWDCitationManual:AProfessionalSystemofCitation)的出版,便深深动摇了《蓝皮书》的司法引证地位*Melissa H. Weresh, The ALWD Citation Manual: A Coup de Grac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at Little Rock Law Review, no.3, 2001, pp. 775-808; Carol M. Bast, Susan Harrell, Has the Bluebook Met Its Match——The ALWD Citation Manual, Law Library Journal, no.3, 2000, pp. 337-352.。相比较而言,ALWD在视觉和关键词释明上更具有竞争力,便于司法职业者查找和阅读案例*Carol Bast, Susan W. Harrell, Legal Cit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Paraleg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no.15, 2003, pp. 15-28.。而在引证格式上,《蓝皮书》侧重于法律期刊的编辑风格,更注重脚注的运用;而ALWD则提供了一个更为专业的法律引证体系,并去除了脚注引证*Jennifer L. Cordle, ALWD Citation Manual: A Grammar Guide to the Language of Legal Citation, University of Arkansas at Little Rock Law Review, no.3, 2004, pp. 573-598.。风格上的差异,导致两种案例引证方式受到不同法律工作者的认可。一般说来,法学教育工作者更倾向于使用《蓝皮书》,而一部分律师和法官正在逐渐接受ALWD的引证方式。目前来看,引证风格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法律职业者获得相关法律信息。律师、法官均能从两种引证风格中发现必要的信息。因此,尚未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何种引证方式更具有优势。
事实上,引证规则的分歧并非当前美国案例引证制度所面对的主要问题。随着网络科技以及数据库技术的发展,案例引证制度正面临着“卷宗危机(Crisis of Volume)”和网络引证难题*Daniel J. Meador, Appellate Courts: Staff and Process in the Crisis of Volume,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1974.。其中,“卷宗危机”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判例的累积与汇编。众所周知,自17世纪中期美国重拾判例制度与案例引证制度以来,判例的数量正与日俱增。浩瀚的判例数量不仅增加了司法职业人员的工作负担,同时也降低了司法运行的效率。从而造成卷宗庞杂且查证困难的司法局面。为此,美国法院以及出版商在编制判例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保留某些典型案例,而放弃某些非典型性案例。但此种选择性汇编方案并未彻底解决“卷宗危机”,相反,非汇编案件的引证效力成为美国司法界的又一难题*Martha D. Pearson, Citation of Unpublished Opinions as Precedent, Hastings Law Journal, no.5, 2004, pp. 1235-1308.。一般说来,但凡经过法院裁判并生效的判决,均可以作为司法引证的案例。其效力不会因为是否进入判例集而受到影响。因此,选择性汇编方案只是在表面上缓解了美国的“卷宗危机”,其结果却违背了普通法传统。
面对“卷宗危机”与“非汇编案件引证效力问题”的双重压力,以及网络数据库的兴起,美国司法界试图以数字化模式重构判例集的汇编与搜索方式。这一改革的确取得了重要的成效,案例数量的庞杂以及搜索问题皆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的方式加以解决。不仅如此,案例数据库(如Westlaw、HeinOnline等数据库)还吸纳了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判决,实现了案例的全球共享*数据搜索技术有效改变了案例引证的方式,降低了搜寻和引证案例的成本。See Casey R. Fronk, Cost of Judicial Citati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itation Practices in the Federal Appellate Court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 Policy, no.1, 2010, pp. 51-90.。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数字案例的案例引证问题如何解决?就英美法系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案例引证格式只适用于印刷版案例集,而不适用于数字版本,后者将面临卷宗和页码的表述问题*Gary Sherman, A simplified system of citation, Judicature, no.2, 1995, pp.60-63.。综上所述,美国的案例引证制度虽然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但在制度兴起、后期建构以及引证方式上均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这表明,案例引证制度的引进与改良必须根植于国家自身的法治基础,而不同的法治环境和司法风格则将影响案例引证方式的形成。因此,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案例引证制度的建构与进化必须内嵌于本国的司法体系内,促成本国司法传统同域外制度的良性结合。
三、制度移植与德国的案例引证方式
案例引证制度在英美法系的成功,促使大陆法系国家重新审视先例引证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并试图借鉴英美法系案例引证方式来增强司法裁判的说理效果。然而,制度移植并非简单的制度学习和制度建构,而是依赖于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众所周知,英美法系的案例引证制度“是一套历史形成的方法,而且需要诸多制度条件和非制度的社会条件做依托”*张骐:《法律推理与法律制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页。。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按照成文法的规则进行裁判,遵循的是民主立法的权威性。显然,仅就司法裁判的法律渊源而言,英美法系案例引证制度的移植就会造成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冲突。
完整地引入案例引证制度的确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奢望,同时也是一种缺乏制度效率的跨法系学习方式。但人们对制度移植的担忧遮蔽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事实,即大陆法系国家对案例引证制度的借鉴、吸收,实际上是关于僵化的成文法适用与司法的灵活解释之间的衔接问题,而非通过研读先例来发现其背后的法律原则。基于此,不同法系之间的制度移植应当确立一种超越于制度(尤其是制度称谓)本身的内在目标,即制度移植应当能够推动国家治理方式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但凡能够弥补本国制度疏漏或推动本国制度完善的法律移植,均可视为“制度移植”的一种表现。由此观之,大陆法系在案例引证制度上的移植,未必完全照搬英美法系的制度传统。承袭和吸收案例引证制度的内在精神,同样可以视为制度移植的重要探索。在此,本文主要探讨德国的案例引证制度,以便明晰案例引证制度如何在大陆法系国家得到推行,以及其在制度移植过程中产生了何种制度变异。
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性国家,德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判例法。即便在众多案例汇编中使用“判例(precedent)”这一表达方式,其涵义也有别于英美法系的传统意义*最高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德国判例考察情况的报告》,《人民司法》2006年第7期。。基于此种差异,德国目前也未建立系统性的案例引证制度。但是,制度上的缺失并不妨碍案例引证的实际存在。德国将案例引证加以改进,转换为三种特殊的方式加以适用,从而缓和了大陆法系同英美法系、制定法同判例之间的紧张关系。
首先,案例引证突出法律的统一适用问题。区别于英美法系的事实相关性引证与裁判结果引证,德国法院在案例引证上仅关注法律的适用问题。“法官在‘先例’中所寻找的是更高权威所做出的类似于规则的表述,而案件事实却被弃置一旁”*[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法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这是因为,“追溯案件事实并发现要旨的真正效力范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些判决要旨中所包含的原则只能作为可供操作的假设对待,人们必须根据后来的案件和变化着的生活需要加以检验,因为有时不得不对它们加以限制、扩大或改进”*[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因此,从判例汇编开始,编纂者即有意识地削弱判决书中的事实部分,而突出法律的适用及解释情况。这样,法官及其他法律职业者可以在不通读判决全文的情况下,了解该案件的法律适用情况。也就是说,德国案例引证的发展,是建立在完备的成文法体系之下的。既然立法者完成了案例事实与法律责任的抽象化任务,那么,如何实现抽象性法律规定与具体案例的对接,就成为法官的一项职责。而案例引证则是司法实践过程中各法官统一法律适用、法律解释的唯一措施。因此,德国的案例引证,立足于完备的成文法基础,而突出解决法律的统一适用问题。
其次,“不违背先例”惯例与案例引证的程序价值。德国法院对待案例引证的态度是非强制性的。也就是说,法院既可以引证案例来证明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也可以不引证案例。总体来看,德国现行法律体系并未规定案例引证的法律效力,也并未形成明确的“遵循先例”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已经形成了“不违背先例”的职业惯例。这一职业惯例不同于“遵守先例”原则。后者强调判例具有正式法律渊源的性质,故英美法系的法官不仅可以引证案例来做出裁判,而且必须有先例作为判决支撑。反观“不违背先例”惯例,它更加注重案例引证的自由性或非强制性,强调判例的从属地位。基于“不违背先例”惯例,德国法院的案例引证分立为不同的诉讼程序:其一,违背惯例可以作为上诉程序的启动机制。倘若当事人发现一审法院的判决违反先例,则可以依据“不违背先例”惯例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多数情况下会遵循先例的判决,予以改判。其二,故意违背惯例以达到纠正先例的结果。在德国,普通法院很少违背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结果,除非普通法院(或联邦宪法法院)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先例在解释或适用法律上存在过错。上述两种案例引证方式,类似于英国早期的“援例令状”,均是以案例引证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启动机制。它有效地提升了德国的司法公正。
再次,案例引证的隐蔽性。除了阐述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以外,德国的案例引证在多数情况下体现出隐性的(内心的)说理、论证功能,即法律职业人员从众多判例中发现某种判决意见,以便证明己方观点能够胜诉的内心论证。在这一过程中,先例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司法机关对某一法律问题的看法与态度。倘若律师(或下级法院法官)发现自己的观点同先例相抵触,那么,其在很大程度上将遭受败诉的风险。而一旦其观点同先例尤其是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相一致,那么其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胜诉概率。在德国,司法职业者对待决案件的内心引证过程几乎是司法工作的首要前提。德国司法职业者认为,若一项法律纠纷缺少判例的支持,那该纠纷很难在诉讼中获得支持。虽然寻求判例支持的过程未必体现于法律文书之中,但这种内心引证行为已经成为德国司法职业者的一种行业惯例。
最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具有直接引证的法律效力。《德国宪法法院法》第31条第1款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所有判决,对德国联邦及各邦的宪法机关、所有法院与行政机关具有约束力。”由此来看,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超越了法律解释和说理的限制,具有了法律上的约束力,并且能够在全国加以适用。而下级法院和专门法院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必须同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相一致,否则将承担被撤销的风险。因此,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能够直接被引用,而无需另寻法律的支持。
根据前文的论述,大陆法系的案例引证制度有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作为成文法的辅助手段。在一个成文法体系比较完备的国家(如德国),案例引证制度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它的作用在于弥补成文法的僵化性和滞后性,并实现司法智慧同成文法体系的对接。当繁复的成文法体系无力应对社会变革以及新生法律关系的时候,案例引证制度将凸显其法律说理功能。二是作为成文法的司法改良手段。众所周知,立法者在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上具有惰性,而且发现其中问题的时间周期较长。倘若司法能够凭借司法裁判的实践理性来判断成文法的质量,并据此加以改善,那么大陆法系国家就可以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立法领域节省大量的法治资源,而仅需要依靠判例制度以及案例引证制度便可以实现法律的进化。
四、制度发展与中国的指导性案例引证
自2011年12月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了十一批(共计56件)指导性案例,用于指导和统一各级法院的裁判。但实际上,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用情况,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案例指导制度的预想。有研究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布的九批44个指导性案例中,仅有13个被应用于司法实践,且每个被应用过的指导性案例的应用率也不高。其中,除指导案例24号被应用过7次外,其他指导性案例的应用均未超过5次”*郭叶、张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司法应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与问题》,易延友主编:《中国案例法评论》(2015年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53页。。由此可以推知两种可能的诱因:
一是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用同“同案同判”的制度构想之间缺乏某种制度动力,难以推动各级法院更为积极地参考指导性案例。倘若以德国的案例引证作为参照点可以发现,大陆法系国家并不排斥英美法系的某些优势制度,但在制度移植与制度实施效果之间,必须确立某种动力机制来推动不同政治、社会、文化的融合。德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并未试图(也不可能)改变司法判决的性质,而是通过法院层级权威以及法律职业惯例来确立案例引证的司法传统。法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者不受判例的强制约束,但违反先例的司法意见将遭受质疑,甚至引发上诉程序。在此情况下,“不违背先例”显然是更为划算的裁判方案*波斯纳认为,减少法官的工作负担,同时增加自由时间,是法官选择遵守先例的重要原因。See Richard A. Posner, Overcoming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141.。由此,德国通过“趋利避害”的普遍心理完成了案例引证的职业化。而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显然未能考虑到此种制度动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若未加参照——实为“内心引证”——也不引起何种不利后果。因此,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效果并不甚理想。
二是案例指导制度同指导性案例适用之间缺乏规范性的引证模式。“应当参照”意在指明指导性案例的司法功能,即相似案例应当参考、遵照指导性案例加以裁判。但问题在于,指导性案件如何体现于待决案件,抑或仅作“内心引证”,案例指导制度均未对此作出详细规定。同时,“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不具有规则自然生成的机制,因而丧失了其提供规则的独特性”*陈兴良:《案例指导制度的法理考察》,《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3期。。故此,各级法院在指导性案例的引证上,往往优先遵循“领导的指示”。当指导性案例的引证模式未加统一,且案件请示制度比案例指导制度更具有制度优越性时,指导性案例的引证就难以产生预想的指导效果。因此,规范性、统一性案例引证模式的缺乏,是造成指导性案例使用率较低重要成因之一。
鉴于以上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例指导制度实施5年之后,开始反思该制度的不足,并着重强化了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用功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指导性案例应当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此外,该实施细则将事实与法律适用的双重相关性作为案例引证的基础,肯定诉讼参与人在案例引证上的权力,并在诉讼程序上确认了案例引证、回应与失效的相关制度。此种案例引证模式明显借鉴了英美法系案例引证制度的精髓,也巩固了大陆法系成文法的法源地位。而相较于德国的案例引证而言,我国更加注重案例引证的制度化、规范化,突出案件事实在判例援引中的识别作用。吊诡的是,受法条结构的影响——法律条款载明“假设”“后果”或“制裁”——德国案例引证在忽略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并未出现案例引证的相关性困局。而我国在保留案件事实部分的情况下,却出现了指导性案例引证率低的难题。
尽管我国在案例引证制度上借鉴了德国的“判例说理”“同案同判”的制度内核,但实际上,我国案例引证制度的确立,缩小了德国案例引证的适用范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案例引证制度中的“案例”,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而不含其他类型的案例。也就是说,在可引证案件数量和指导性案例引证范围上,我国案例引证制度均要窄于德国的案例引证。其次,我国的案例引证缺乏充分的说理空间。虽然案例引证制度试图以指导性案例提升待决案件的说理效果,但事实上,我国在法官自由裁量权配置上,要远远低于德国。在德国,“司法续造”被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重要表现形式。虽然其性质仍是一种法律解释行为,但对于案例引证与裁判说理而言,德国法官的自由度显然要强于我国法官。再次,案例引证尚未构成司法权的约束机制。传统上,案例引证制度具有“法官脱身术”的功能。这是因为,引证先例裁判不仅可以规避错案追究机制,而且免于其他权力的干涉。德国“违背先例引发上诉”的程序控制,即反映了案例引证制度在司法权滥用上的约束力。但我国的案例引证制度尚未具备这一制度效果。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一方面发展了英国、美国以及德国的案例引证制度,另一方面又显现出保守的改革观念。保守的制度改良是一把双刃剑。面对英美法系的制度移植,它可以保护成文法国家的法治传统,避免司法权与国家治理方式的混乱;而面对个案公正,制度设计的保守性则可能延迟司法改革的步伐。这就意味着,案例引证制度的引入和确立,会是一个长期的司法过程,由此产生的制度竞争、制度融合乃至制度进化,都将成为我国未来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制度发展史的经验已经加以证明。
五、结语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未来发展,需要借助某种配套制度来推动指导性案例的运用。本文所言之“案例引证制度”即是案例指导制度纵向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案例引证制度的发展史已经证明,典型性案例的遴选与确定,只为法院引证案例提供案例基础,而普通法的真正精髓在于,法官能够从上述案例的字里行间发现法律的内在规定性,并通过引证该案例中的法理来说明判决的正当性、合法性。由此来看,案例本身不会产生何种约束力,只有经过司法职业者的引证,该案例才能对待决案件产生约束力——无论是法律约束力(如英国)还是事实约束力(如德国)——而英美法系中的多数判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效力。Thom Neale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50年里,加拿大最高法院只有19%的判决能够保留下来,而地方法院的判决,仅有3%仍在适用*Thom Neale, Citation Analysis of Canadian Case Law, Journal of Open Access to Law, no.1,2013, pp.1-60.。由此可见,判例的“引证半衰期”是较为短暂的*John Henry Merryman, Toward a Theory of Cit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itation Practice of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in 1950, 1960, and 1970,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no.3, 1978, pp. 381-428.。丧失引证效力的判例,实际上已经不再具备判例法的性质。这意味着,先例(也指“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用,应当能够反映当下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双重要求,体现并突出先例在成文法国家中的灵活性优势。而这种适用机制是通过案例引证制度的筛选功能来实现的。因此,我国案例引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案例指导制度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
责任编校:徐玲英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3.013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3-0123-10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2015BSCX40);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1CFX074)
作者简介:张婷婷,中国政法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