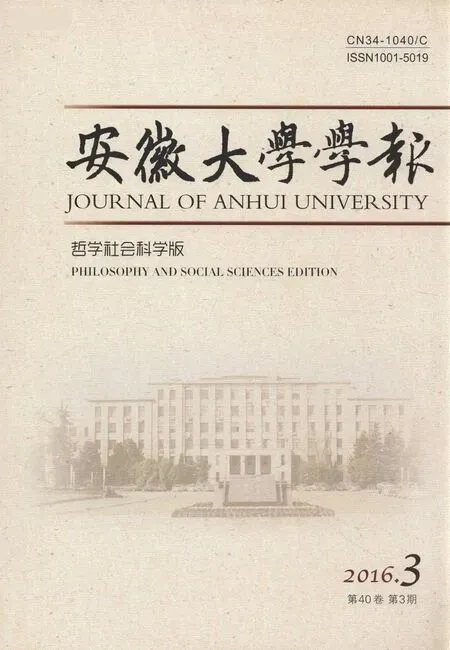无中生有 机变神化
——论古代文艺美学中的文才创造思想
赵树功
无中生有机变神化
——论古代文艺美学中的文才创造思想
赵树功
摘要: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认为,创造性是文才作为文学主体素养的重要潜能,它是才有其能这一特质的具体表现。文才这种特性包容于才的“本始”内涵之中,并通过以下维度获得美学确认:才源血气,循才可以成体;才生文思,极才可以尽变;才易飘扬,骋才可以破缚。
关键词:文才;美学特征;创造性
一、引言
才有其能的思想衍生于才的基本内涵。《说文》释称:“才,草木之初也。从‘|’上贯‘一’,将生枝叶也;‘一’,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同。训释是针对篆字之才而言的,“‘|’上贯‘一’”的“一”即指“才”字左边的一撇。许慎这一训释成为后世诠解“才”义的基础,金圣叹《水浒传序一》云:“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荄分荚,于破荄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荄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古代才、材相通,初始涵摄着未来,未来对初始有着本然的呼应,草木的生长在这个时段上具有自己内在的能动性。
可见,才的本意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代表着初始,定位了初始之际本体的性质,这种初始之际便具有的、不可修正的质性包容着一种主体禀赋之中的潜在优长——当然是相对的优长,无论与他人的外在相较,还是自我不同禀赋的内在比较——在后天人力的激发下这种优长存在转化为独到之能的基础,孕育了突破当下态势的力量,因此才具有对主体未来发展趋势的引领、支持作用。这种合趋势性的力量就是才的涵量,“才的涵量,包含着性能与表现,蕴涵与施展,灵智与风貌”*周汝昌:《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当代学者自选集:周汝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07页。,所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草木之初而枝叶毕寓焉,生人之初而万善毕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蕴也。”
古人将才有其性命之曰才性,才有其能命曰才能,事实上,才就是“性之所近”*冯友兰认为:“才是天生底,所以亦可谓之为性。人之兴趣之所在,即其才之所在,亦即普通所谓‘性之所近’。”参阅冯友兰《新世训》,《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4页。,这种“性之所近”经过后天的人事辅助可以形成能力优长,因此“能”往往被称作“性能”,我们也可以说,才具有性与能的统一性。有鉴于此,将性与能割裂而论才便成为一种偏颇意见,早在宋末元初,戴侗对此已经有了批驳*戴侗《六书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一:“后世之论浸差,直以知术技能勇力为才,温公有才德之分,程子有才与性异之说,皆失之矣。”。而这一点不仅部分前人,即使今人也仍然多有误解。
关于才有其能的明确论述,较早见于王充《论衡·书解篇》:“盖人材有能。”*黄晖:《论衡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4页。东汉后期王逸有“绝人之才者谓之能”的论断*王逸:《楚辞章句》,夏祖尧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页。。汉魏之际,刘邵便在其集才性理论大成的《人物志》中专列“材能”一篇,提出“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刘邵:《人物志》,梁满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0页。。
“文才”就是文艺之才的概称,是指对于具有才华者而言,其性之所近、才之所能在于文学艺术,尤其体现于性情之中的感觉敏锐、体察细微、情怀幽远等等素质。魏晋玄学的深刻影响,使得文才之所能获得了以下定位:就创作之中文才的特征而言,其在无与有之间是无,在本与末之间是本,在体与用之间是体,它以虚灵的姿态现身,呈示为无中生有、乘一总万、溯本达末、明体成用。如此虚灵幻化,其美学本质就是从无到有、从愿景到践行、从单一到丰富的创造与机变,彰显出生命力的灵动与有为。在中国古代文才理论思想中,这种文才的创造性以才有所能为基础,通过以下维度获得美学确认:才源血气,循才可以成体;才生文思,极才可以尽变;才易飘扬,骋才可以破缚。
当然,“文才”仅仅是后世方便学术研究的指称,尽管“文才”命名古已有之,但古代文艺批评对其表达保持了相当的丰富性,以《文心雕龙》为例,吴林伯义疏即称:“本书言人之天赋,或曰才,或曰性,或曰才性,或曰天资,或曰气,或曰才气,或曰元气,或曰分,或曰器分,名异实同。”*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3页。本文研讨文艺创作,所论之才自然属于文才范围,具体论述之中不再刻意标示。
二、才源血气:循才可以成体
所谓体,就是以体裁规范为基础,通过作品呈现的鲜明主体性精神追求与其审美形态,古代文论又称之为体调。
才与体之间有着基本的对应。这种对应关系最早的论述当属于《典论·论文》。曹丕首先通过“清浊有体”的主体差异性得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结论。但他没有为体裁偏长的表面现象所局限,继而又以主体禀气之异推演出体调之不同:“应玚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受到才有偏适特性的影响,不仅体裁,体调也有着内在的偏宜。陆机《文赋》所谓“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也是以如此的才性特征对应着如此的审美面目。陆云将这种能够因我之才而成就自我风貌称为“文体成”*陆云《与兄平原书》:“屡视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耳。然新声故自难复过。”其意即是,文体成则难以变易。,文体成则如孩子骨骼完备,自有其态,这就是体调。当然,从研讨的总体而论,汉魏两晋之际的才体关系论仍以才性与体裁关系的观照为主。
齐梁之际,刘孝绰将曹丕“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转译为“属文之体,鲜能周备”,但对这个论题的阐释却与曹丕迥异其趣。他首先同样肯定了体的多端:其中有“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令;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等体裁之体。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的风格之体。有“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的性质敏迟之体。随之刘孝绰却并未沿着“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申说,而是忽下转语:
深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报笺、卞兰献赋,犹不足以揄扬著述,称赞才章。况在庸才,曾何仿佛?*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梁昭明太子文集》卷首,四部丛刊初编本。
在曹魏之际被视为无可奈何并以之警醒文人不必相轻的体裁难以周备、体貌各有其偏之论,在这里被超越,作者将视野主要投射到茁生于体裁之上的风格体调,并且更为豪迈地确立体调的“兼而善之”“独擅众美”为高标。当然,这种境界依托于远非“庸才”所可仿佛的卓越才气。且不论这种集大成式体调成就的可行性,其对文才创构之体调的咏赞,实则预示了才体关系论由才与体裁为主向才与体调关系为主的转型,表明才与体之间的因果已经成为文艺理论关注的核心之一。
及乎《文心雕龙》,则对才如何影响于风体作出了全面而深入的阐释。《体性》篇中刘勰提出了“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后同,不另注。,詹锳先生云:“因性以练才”就是顺着自己的性情,学习和自己的个性比较接近的风格,这样来锻炼自己的才能*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37页。。这个解释将“练”释为了锻炼,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应当解释为“练选”,也就是选择。因性以选才看似不通,因为才由天赋,与性、气实则一体,既然一致,就有定性,何劳再选呢?问题原来在于:人有体性,从而确定了本初之才的可能性,但这仅仅是一种外在认识状态下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文人对自己的这种方向、定性都有正确、客观的把握和体认,于是经常出现一些文人勉强从事于和自己才性限量不相合的创作,追求与自己才性距离较远甚至不相能的风格等等。这时,确定自我才性之所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练才”。“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就是通过对才性的考量,最终选择符合自我才能的风体。
依照才性创作,最终必然能够体现出与其呼应的风体,这是《文心雕龙》的重要观点,贯穿于本书诸多篇章。
《明诗》云:“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这仅仅是四言五言一般的要求,而无论四言五言,最终作品所呈现的体貌则决定于主体才性,所以刘勰又说“华实异调,唯才所安”,于是“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不同诗人雅、润、清、丽等不同风体的形成,最终归结于各自才性的不同。
《熔裁》云:“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又云:“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才性不同,形成了二陆繁与清两种不同的审美风貌,所谓“随分所好”之“分”,也就是才分。
《才略》总结前代名家成就,以为皆是尽自我之才成自我之体:“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仲宣溢才,捷而能密。”又曰:“张华短章,奕奕清畅……左思奇才,业深覃思……潘岳敏给,辞自和畅”等等。由此延伸,有其才者,无论文笔,皆有其风体之美,此所谓“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才略》篇赞语又云:“才难然乎?性各异禀,一朝综文,千年凝锦。余采徘徊,遗风籍甚。无曰纷杂,皎然可品。”古人创作之所以皎然可品,原因就在于其成乎面目各异的才性。
至《体性》篇,刘勰则超越了曹丕个体才性与文体风格的简单对应之论,建立起了才性与风体的系统对应关系理论。罗宗强先生即总结称:“刘勰论文章体貌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强调体貌与才性之关系。”*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7页。刘勰不仅准确揭示了这一思想,还详明论述了才体之间对应的美学机制:
体就是“才气大略”,即是主体才能、气质的显像,因此与主体才性气质有着“表里相符”的统一性。从审美创作的流程而言,“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而向外显像的能力则决定于才、气、学、习:“才有庸隽,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隽,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主体才气学习的综合便形成了八种风格体式: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尽管这八种风格体式成就于才气学习,但从根本而言,它不能背离才气性情的本然情态:
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就是说,八体形成的核心力量来源于学、习、才、气,但四者对作品风貌的影响不是一致的:体式由于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特征,因此可以通过学习基本掌握,但这仅仅相当于获得了一个共性的模糊皮壳;只有源自血气的才力,浸入情志显现为文辞且最终不会背离这种禀赋的约定,体格由此方能逐步清晰化、主体化,因此“才气”方是对主体到底能够成就何种体式风格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以说才气与风体之间这种对应是“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曹丕关注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存在着因血气不同带来的风格规定性,刘勰不仅认同不同人的作品可以体现出不同的面目,并承认其产生的合理性,而且有意提倡这种不同,才性气质由此成为审美品质锻造的内动力。
体调的形成,既是文士于艺术殿堂登堂入室的象征,又是文士造诣的认证——只有成就卓著者的创作方可成其体调。《沧浪诗话》即专列“诗体”一节,其中诸如陶体、谢体、少陵体、太白体、李长吉体、白乐天体等,皆是自成体调的代表。具有才华者成就其体调,与此呼应,“大抵能变化一代之体者,必擅一代之才”*臧懋循:《冒伯麟诗引》,《负苞堂文选》卷三,上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天启元年臧尔炳刻本。。从主体才性至作品体调,本自血气的才气缘附于体裁,造就艺术风体面貌,这个过程就相当于血气充实骨骼诞育鲜活的生命,正是文才创造性的重要表现形态。
三、才生文思:极才可以尽变
审美意义的创造依托《文赋》所论之“耽思”,《文心雕龙》所论之“神思”,驰骋灵机,淋漓兴会,具体落实于文思。而文思必依赖于文才,这就是才生文思,古代文艺理论中的“才思”范畴便融会了文才与文思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
才生文思的思想在《文心雕龙》研讨才思关系之前已经有了很多隐约论述。《论衡》首发其端,王充将创作数量之繁而速、文章整体圆熟充实、文辞的优美等皆归结于才,一如《佚文篇》云:“文辞美恶,足以观才。”《效力篇》不仅赞许“出文多者才智茂”,且将此类文士品为“多力”。而才之所以可以见乎创作的智慧与力量,核心在于有才者方备精思。《佚文篇》论东海张霸:“能推精思,作经百篇,才高卓遹,稀有人也。”与此相反,《效力篇》云:“少文之人,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将不任,有绝脉之变。”*黄晖:《论衡集释》,第863、581、863、583页。并举王莽时郭路夜定旧说,由于当时博士为五经章句动辄万言,郭路孜孜以效,结果死于烛下,究其原因就是“精思不任”——自身的才学难以负荷如此的精苦之思。其中文思源自才华的基本意旨已经十分明显。继而六朝晋宋之际文人对此也多有涉及:
《抱朴子外篇·酒诫》:“才高思远,英赡之富,禀之自天,岂藉外物,以助著述?”
《抱朴子外篇·钧世》:“古之著书者,才大思远,故其文隐而难晓;今人意浅力近,故露而易见。”
《抱朴子外篇·自叙》:“他人文成,便呼快意,余才钝思迟,实不能尔。”*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99、65、695页。
范晔《狱中与诸甥姪书》:“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沈约:《宋书》卷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30页。
以上资料,但凡论及文才高下,随后之“思”皆与之相契,才高才大者思远,才钝才少者思难思迟,彼此之间呈现为一定的体用、源流关系。
在此基础上,《文心雕龙·神思》实现了才、思关系的明确理论提升。刘勰首先将才分思想引入其理论体系:“人之秉才,迟速异分。”才分所决定的正是创作者各自不同的文思形态:或如司马相如、扬雄等穷日积晷、孜孜以求,为思之缓者;或如枚皋、曹植等倚马千言、悬河倒泻,为思之速者。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没有沿依葛洪等人仅从才之大小论思,才大思优、才拙思钝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基本规律。刘勰选择同样富有才华的文士入手讨论才思关系,又从其时备受关注的才分迟速切入,实则是将才思关系的研讨引向了深入,即不仅才之大小影响文思,同样具有文才者才分不同,也同样影响着文思,故云:“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两种性质的文才,便形成骏发与覃思这两种类型的文思。由此可见,无论文才大小、迟速,最终都直接体现于文思。
就文思而言,其包容异常丰富,不仅兴象激发之际“耽思旁骛,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联想为文思,而且创作中整体的结构拟制、情意斡旋与要素整合也是文思,《文心雕龙·附会》于此也有论述,明清之交廖燕、金圣叹等释才为“裁布”,本意也在于此。
文思以联想为基础,或为审美预想,或为审美回忆,或为二者融会的审美想象。它忽然自有、倏然突发,其瞬间的领悟与直接激发具有对时空的囊括性与对相关信息的重组能力,这一切的赋形成象已然形成对当下、既定甚至传统情态的突破与超越,是才之创造性的主要呈示状态。这种以文才为基础,经由文思(或径直称之为才思)熔铸的创造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理解:
其一,主体极才思则可以尽变化。这一认识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皮日休《松陵集序》首先确定诗歌与才的关系:“诗有六义,其一曰比,定物之情状也,则必谓之才,才之备者,于圣为六艺,在贤为声诗。”随后论称:
夫才之备者,犹天地之气乎?气者,止乎一也,分而为四时。其为春,则煦枯发枿,如育如护,百物融洽,酣人肌骨。其为夏,则赫曦朝开,天地如窑,草焦木渴,若燎毛发。其为秋,则凉飔高瞥,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为冬,则霜阵一栖,万物皆瘁,云沮日惨,若惮天责。夫如是,岂拘于一哉?亦变之而已。
人之有才者,不变则已,苟变之,岂异于是乎?故才之用者,广之为沧溟,细之为沟壑;高之为山岳,碎之为瓦砾;美之为西子,恶之为敦洽;壮之为武贲,弱之为处女;大则八荒之外不可穷,小则一毫之末不可见。苟其才如是,复能善用之,则庖丁之牛、扁之轮、郢之斤不足谓其神解也。*皮日休:《松陵集序》,《唐诗纪事》卷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64页。
本文所论可以引发变化的才,其本质就是针对创作才思而言。备其文才富其才思者,于不同体式法度能够自由运用,于时空往还可以游刃伸缩,如同气的舒卷变化。其所结撰的意象、确立的格局、蕴蓄的意义、寄托的情志、塑造的境界由此因文而异,变化无方又灵动鲜活。
中晚明时期,心学流行释放出文人们昂扬的个性,“极才尽变”说由此产生。如陈继儒评董太史文章:“行文以古铸今,以我铸古,极其才情神识之所如而曲尽文人之变化。”*陈继儒:《代门生跋董太史文抄》,《陈眉公集》卷八,上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万历四十三年史兆斗刻本。陶望龄也称:“古之为文者各极其才而尽其变。”*陶望龄:《徐文长三集序》,《歇庵集》卷四,上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万历乔时敏等刻本。就诗文创作论极才尽变,正是就尽其才思可以创我体格、成我面目而言。从这个意义说,茅元仪“诗不异乌得而称诗”之论貌似刻意,实则有着其于才思深刻的领悟:“人有性灵,非关授受,心具曲折,岂得准符?凡其所谓同者,皆取象于肤,写形于影,北海所谓学之者俗,似之者死。”*茅元仪:《莆田四子诗序》,《石民四十集》卷十六,上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崇祯刻本。“性灵”非关授受,才思不可能等齐,他们对应的是各自独到的创构,各自皆成其变化。
其二,主体极才思则可以“无中生有”。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存在着真与伪、实与幻的论争。在诗文词赋领域,由于“诗言志”传统的坚守,虽则成全了修辞立其诚的艺术伦理,但也对文学本然的创造尤其叙事文学的虚构形成了阻滞。诗文循其才思可以于法度、思致、意象、构词、篇体之中尽其诸般能事,唯独情事不能脱离亲历亲为。但这一论调至宋代受到了挑战,当有人强调不亲历便不能摹绘其情态时,陈师道提出了异议。其《书旧词后》载:
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盖不更此而境也。”余谓不然,宋玉初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境也?*陈师道:《书旧词后》,《后山集》卷十七,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中的“更”为“更事”之“更”,即谓经验;“境”谓写境、造境。晁无咎以为苏轼之词未曾经验而写,意有贬抑;陈师道回答:宋玉写梦中的巫山神女何曾经验?如果说陈师道尚只是以反证论述文学创作可以凭借审美想象,那么元代李治针对“必经此境,则始能道此语”的反诘则揭示了才人之所以不经验而能妙笔生花的奥秘:“不一举武,六合之外,无不至到;不一捩眼,秋毫之末,无不照了:是以谓之才。才也者,犹之三才之才,盖人所以与天地并也。使必经此境能道此语,则其为才也狭矣。”*李治:《敬斋古今蘣》卷十,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3页。虽未曾经验,却心如明镜,烛照幽微,如此悬拟之能以及所绘写的合经验性、合情合理性,便是才思的创造。
四、才尚发露:骋才可以破缚
文才本身具有一种自内向外发散的发露特性,徐桢卿称之为“才易飘扬”*徐桢卿:《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65页。。古人言文才,动曰“才华”,其意就在于视才如花,其生命力源自根系,但所成所就的光华必然绽放而出,一如禽鸟珠玉的光辉,故有“夫天予以才,犹卉木有花萼,禽鸟有文采,珠玉有光辉,夫安得遏之使不露”的说法*王柏心:《蒋节田冰清集遗稿序》,贾文昭《中国近代文论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668页。。才向外所呈现之华,就是才的寄托对象所创生的美质。因此,才的发扬寄托或者对象化的过程就是它的创造过程。这个能够充分发挥才之锋芒的创造过程,是文学新变的根本依托,而新变则意味着对种种束缚壁垒的破除。
纵观文学的流变历程,每每面临着如何从传统与其他强势话语中突围的困境。虽然从六朝开始,“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之论形成了相当的势力,但面对因袭的传统以及约定俗成的审美习尚,真正的创新委实不易,倒是如下两类人物俯拾即是:其一是自馁者,他们“怵于昔人久定之名,动于今人易售之路”,不敢“争奇人魁士所不能致”,又不能“自理其喧寂歌哭以挽神鬼人天之所不能夺”*谭元春:《金正希文稿序》,《谭元春集》卷二三,陈杏珍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权衡才识学力,先行自惭形秽,于是只有顶礼他人格调。其二是拘守者,“拾取于先辈,庄守其故物而不思一变,且以变为非”。这类人表面上似乎傲慢,究其底里:“中实有所愧恨,但才不能变。以为吾既不能变,而示人以欲变之意不可,多人以善变之能又不可,不得已而安其旧,以笑天下之变者也。”意思是说,这些人没有“足以变”的才力,故而以不变遮羞,其本质等同于自馁者,亦可谓诛心之论*谭元春:《潘景升戊己新集序》,《谭元春集》卷二三,第617页。。谈迁《石天堂稿序》总结明清之际文坛,曾为以上诸人造像:“古人善压,今人善跂。”*谈迁:《石天堂稿序》,《谈迁诗文集》卷二,罗仲辉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跂”含有委曲求全、不敢伸张之意,这个总结形象地描画出了部分文士仰人鼻息的可怜相。
归结无所创造的病根,或在于“不暇自伸其才力精魄”*谭元春:《金正希文稿序》。,或在于“才不能变”*谈迁:《石天堂稿序》。。因此,若要成就不与物共贵的局面,不可避免地要任心循才、发我性灵,从破除传统以及其他“霸权话语”的封堵开局,恃才创新与破缚也便纠缠于一体。综合历代文学批评,其间为才所冲击破除的束缚主要包括以下两类:拟古思潮、宗派。
其一,尚才求新则往往与拟古循守形成冲突,破除传统束缚便成为题内应有之意。如公安派袁中郎的创作,宁为七子之徒摈斥唾骂,也不肯蹈袭古人以掩其性灵、缚其才思,被称为诗中豪杰。袁中郎之所以不为拟古积习掩蔽,原因就在于其富于文才,对文学创作而言,“非有才不足以济变”*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江盈科总结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也说:
诗何必唐?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雎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即谐词谑语皆足观感,不必法言庄什矣。*江盈科:《敝箧集引》,《江盈科集》,黄仁生辑校,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398页。
以性灵为依归,则所重者不是既定格调,而是自我的才情、才气。陶望龄的文学思想与袁宏道等呼应,其《徐文长三集序》先提出“极才尽变”之说,随后又具体论称:“人有一家之业,代有一代之制,其漥隆可手摸而青黄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屡迁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有此才之可极,则可破“文左国而诗初唐”的束缚,避免“方其自喜为新奇之时而识者已笑其陋”的尴尬*陶望龄:《徐文长三集序》。。公安派文人这种任我才气的豪情随后得到一定的继承,如金圣叹亦称:
从来文章一事,发由自己性灵,便听纵横鼓荡;一受前人欺压,终难走脱牢笼。此皆所谓理之一定,事之固然者也。……世间妙文,本任世间妙手写到;世间妙手,孰愁世间妙文写完?后人固不必为前人描真,前人亦何足为后人起稿?*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六,周锡山编校,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281页。
性灵不是什么玄虚之物,钱谦益曾云:“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钱谦益:《题徐季白诗卷后》,《牧斋有学集》卷四七,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63页。可见它与才本来就是相融一体,或见乎性情,或见乎灵智。如此性情灵智,生生不穷,必以此冲决趋奉古人的迷信,文坛才有新新相续的万古常新。
其二,尚才则往往要与宗派龃龉,媚俗、依附于是成为破除的对象。但凡一种文学思想呈现为群体性的共识,群体本身便自然形成主其事而张其帜者,辅其右者,及门而拜服者;理论上彼此有呼应,有补充,有推扬流播,甚至有互相的夸助与扬诩,这个群体也便成为了宗派。宗派必有开门立户的思想,而且各自还要秉持、强化甚至采取种种手段维护这种带有自我符号性质的思想,如文必两汉、诗则盛唐之与前后七子,如文当由唐宋循阶而上之与唐宋派,如标榜宋诗传统之与浙派等等。
宗派与流派略有区分:宗派开宗立派,舍我其谁,其建立未必皆源自发端者主观思想的偏执,但信徒们变本加厉强化舍我其谁的局面,便形成了宗派一定的排他性。流派则虽有近似之学,也倾慕彼此之风,其间时有大家发布相关思想,但各自没有刻意的宣扬,没有蓄意的组织,流派的学术意义和影响往往大于现实地位,有的则属于事后追认。与宗派相比,流派没有明显的画地为牢倾向。宗派是派别与其文学主张、文学倾向融为一体的,其纲领的发布者一般就是信徒依附趋奉的教主。对信徒而言,一则秉承其思想,一则依附宗派,二者互为表里。强调才的发露冲决,必然要与宗派统摄、教主权威发生矛盾,摆脱思想的卑服与依附由此便同样不可回避。
如王思任对趋奉历下一派的破除。其《倪翼元宦游诗序》言时人步趋之弊:“历下登坛,欲拟议以成其变化,于是开叔敖抵掌之门,莫酷于今之为诗者,曰如何而汉魏,如何而六朝,如何而唐宋;古也,今也,盛也,晚也,皆拟也。”与其听后人传辗转之法度,何不直接师承李杜?而李杜恰恰不是如此为诗:“李太白一步崔颢语,即不甚为七言;杜子美竟不作四言诗。”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鄙视拟效,乃是“各任性情之所近,无乐乎为今诗而已”,即从事乎才性所近,同时也不愿意追随时流。诗本就出于自我的心领神会,“人之诗也,与己何与”?但能“诗以言己”*陆云龙等辑:《翠娱阁选评皇明小品十六家》,蒋金德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62页。,任我性情任我才性,何必趋奉历下派系?
如钟惺对趋奉公安一派的破除。其《问山亭诗序》论当时宗派习气:“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则人争异之,犹之嘉隆间不步趋于鳞者人争异之也。或以为著论驳之者自袁石公始,与李氏首难者楚人也。夫于鳞前无为于鳞者,则人宜步趋之;后于鳞者人人于鳞也,世岂复有于鳞哉?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石公恶世之群为于鳞者,使于鳞之精神光焰不复见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矣,岂石公意哉!”但成宗派则其各领风骚之日必然不多,前有其盛,倏然而衰,后起之秀成为新的崇拜对象,之前的尊神则黯然隐退,还要饱受昔日膜拜者的讥讽。由此钟惺赞赏其友王季木的诗作:“飞翥蕴藉,顿挫沉着,出没幻化,非复一致。要以自成其为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语。”*钟惺:《钟伯敬先生合集》卷二,上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崇祯九年陆云龙刻本。由“自成其为季木”以期摆脱对公安派的依附。
又如孙枝蔚对趋奉闽派的破除。其《叶思庵龙性堂诗序》从对帮派的批判出发,指出以高棅为代表的所谓闽派尽属门户:
诗为六经之一,而今人恒易为之,何也?且其失复不在易也。自钟记室作《诗品》,谓某诗源出于某后,乃又有江西诗派曰源曰派,皆不过论其门户耳。夫门户犹之面貌也,人不各有其风神气骨与夫性情之大小不同者乎?奈何舍其内者而第求之于其外者,以为诗如是遂足自豪也?故有信《诗品》之说者,其失也,巧者为优孟之衣冠,拙者为东施之捧心矣。有信诗派之说者,其失也,善者太伯逃荆蛮之乡,不善者公孙作井底之蛙矣。
有门户则诗人不从自我面目入手论诗,此为舍我求人、舍内求外。以此论为基础,作者对钱谦益所倡导的闽派提出了批判,以为其代表林鸿与高棅虽然同是闽中健者,但其诗守门户而无大成,其后的曹能始、黄石斋等恰恰因为不从所谓闽派出发,或本之《国风》,或本之《离骚》,发我才性,其诗作反而千古不磨*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一,上海: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康熙刻本。。
以上所论宗派,能够破除其依附的核心力量或曰自我性情,或曰自我风神,或曰自我气骨,皆依托于各自雄才浩气。
五、余论
极才可以成体、极才可以尽变、极才可以破缚,文才的创造特征由此获得了美学确认。但是,文才发扬所形成的力量是不具备方向选择性的,如此一种具有冲决力量的势能,如果没有德器、识力的引领掌控,荡越旧轨便动辄流溢为荡检逾闲,骋才、恃才、纵才、炫才由此在所难免,这又不得不引发历代文人们的反思与警惕。
责任编校:刘云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3.006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3-0050-08
作者简介:赵树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浙江 宁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