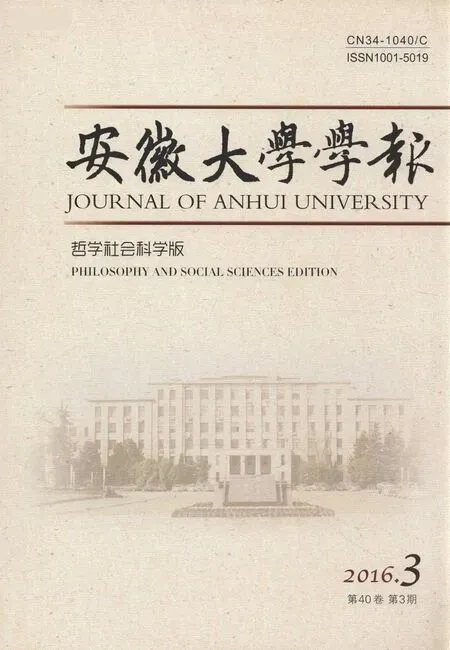资本约束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行为的思考
方 芳,艾子健
资本约束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行为的思考
方芳,艾子健
摘要:自巴塞尔协议将资本充足率约束引入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以来,资本约束监管成为银行安全性经营原则最重要的保障。商业银行在应对资本充足率约束时,更倾向于选择分母(资产)策略,利用监管规则漏洞进行监管资本套利。在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并不健全的背景下,表内资产出表成为监管套利的一个主要工具。表外业务在为商业银行创造价值的同时,降低了资本充足率标准作为审慎监管工具的有效性。为此,需要完善动态资本补充机制,制定表外业务项目披露的统一标准,有效管理表外业务风险。
关键词:资本约束监管;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资本套利;表外业务;巴塞尔协议
银行监管的天然使命是保护社会公众利益,防止银行破产引发系统性风险。因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围绕这一使命,银行监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银行发展的早期,资本并不是银行监管的主要选择,但随着经济与金融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从上世纪末以来,资本已逐渐成为银行监管的核心。这是监管当局不断应对挑战、不断探索实践,所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制度选择,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银行业经营管理三大原则(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中,安全性处于最为重要的位置。经过全球银行从业者、研究者以及监管者的长期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以资本充足率指标为核心的商业银行资本约束监管的共识,资本约束逐渐成为银行业抵抗经营风险、保证安全性原则的制度安排。资本约束的实质,就是要求资本必须和可能产生的风险建立起紧密的内在联系,风险资本必须覆盖风险资产,银行要对可能承担的风险建立起最终准备。
20世纪80年代,由英美等国主导,在巴塞尔(Basel)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协商合作下,巴塞尔协议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标准。其后,巴塞尔协议不断根据银行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变化,进行自身的补充与完善。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也随着资本约束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其行为策略,以达到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此,资本约束监管与商业银行行为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商业银行经营者与监管者博弈的主要内容。
已有研究表明,银行在面临资本约束的条件下,更倾向于选择通过减少风险资产而非增加资本来达到监管要求的资本充足率。Myers等(1984)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股权稀释是银行募集股本的成本,是银行经营管理者所希望规避的成本。因此,银行在面对监管约束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本充足率,短期内普遍采用降低信贷规模,而非补充资本额度的策略。相较于通过新股发行来增加资本,银行更容易通过收紧贷款以减少风险资产。Hyun等(2011)通过一个简单的银行模型证明,在银行的长期贷款余额相对较低时,或者当经济处于低迷时,为保护当前股东利益,即使不存在募集新股的费用成本,银行也可能更倾向于减少贷款。黄宪等(2005)基于Blum(1999)的模型证明了较高的资本充足约束将使银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开展信贷行为,从而降低银行的风险水平,但也将导致信用紧缩,明显使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吴栋等(2006)借鉴Shrieves等(1992)的局部联立调整模型,研究了1998—2004年我国大中型银行的财务报告面板数据,认为资本监管要求有效降低了我国银行的风险水平,但资本金并没有显著提高。温信祥(2006)认为,银行资本充足率高于资本监管要求时,对风险资产几乎不产生影响,反之,银行会通过降低风险资产以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指标。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约束监管下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商业银行的战略调整。
一、巴塞尔协议下的资本约束监管机制
20世纪70年代,由于放松了管制,严重的银行危机大量出现。因此,监管方开始寻找与银行经营行为相容的监管工具。1988年,巴塞尔协议Ⅰ由英美等国主导,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协商合作下诞生。国际银行业在巴塞尔协议Ⅰ中统一了对资本构成的认识以及资本充足率标准。虽然巴塞尔协议文本本身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是一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所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巴塞尔委员会成员也有义务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将巴塞尔规则转变为强制性法律要求。因此,巴塞尔协议的实施深刻影响了银行业的发展格局。
巴塞尔协议Ⅰ统一了对银行业资本构成的认识,将资本分为两类,第一类称为核心资本(或一级资本),第二类称为附属资本(或二级资本)。其中,要求核心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应高于50%,附属资本不得超过商业银行总资本的50%。协议统一了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和资本充足率的概念,设立了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监管要求。协议确定了风险资产的度量,以风险为基础将表内资产划分为五个风险类别(0、10%、20%、50%、100%);对于表外资产,则先用四个信用转换系数(0、20%、50%、100%)转化成等同于表内的风险资产,然后再按照五个风险类别进行加权。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等于风险加权后的表内与表外风险资产之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2)。然而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协议也显露出其固有的缺陷。从风险资产的划分来看,即使是同类资产,其信用风险也存在差异,因此这样简单划分并不能准确反映银行资产的真实风险。同时,单一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并不能完全衡量银行的安全,并非具有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就一定能保证经营的安全性。此外,协议也没有覆盖除信用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且难以有效约束监管资本套利行为。
巴塞尔协议Ⅱ产生于全球金融行业蓬勃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金融创新产品在日益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逐渐成为新的增长源,而旧巴塞尔协议已经无法在剧变的金融市场中保持有效的资本监管,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过于简化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过于僵化的风险权重设计和过于片面的风险分类方式三个方面。为此,新版的巴塞尔协议着力于设计出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银行真实风险的资本监管框架,在旧资本协议的基础上衍生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三大支柱”监管体系。第一大支柱是最低资本充足率,维持8%最低充足率要求不变,为使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更为准确,在已有的信用风险之外又引入了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考量。第二大支柱是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具体规定了四项原则,旨在对银行的风险状况与化解能力进行全面的考察与评估。第三大支柱是市场约束,强调提高银行的信息披露标准,通过市场上的利益相关方来约束银行的风险行为。此外,巴塞尔协议Ⅱ改进了资本和风险的计算方法,以更为高级和复杂的算法对不同规模的银行风险进行详尽的量化。
巴塞尔协议Ⅲ诞生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巴塞尔协议Ⅱ虽然针对全球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进行了大量制度层面的完善与修订,但仍然在顺周期性、系统性风险等方面存在设计缺陷。这些缺陷不但没有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有效地控制风险,相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蔓延。为应对新的挑战,巴塞尔协议Ⅲ确立了新的国际监管标准与规则框架,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最低资本充足率仍保持8%不变,而最低一级资本充足率由4%升至6%,最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约束由2%升至4.5%。并在此基础上引入2.5%的资本留存缓冲要求,旨在防止银行过度信贷风险带来的损失,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有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缓冲资金来源于普通股,在4.5%的最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约束上提升为7%。计提0%~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应对资本监管对经济造成的顺周期性效应。系统重要性银行则另需增加1%的附加资本,增强银行业整体的稳定性。此外,要求杠杆率(资本净额与表内外风险暴露总额之比)最低为3%(巴曙松 等,2013)。第二,提高了资本结构的质量。巴塞尔协议Ⅲ对监管资本的定义和结构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更严格的资本工具的合格性标准,将监管资本分为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和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主要由普通股和留存收益构成,原来规定的优先股等不再含于一级核心资本之列。这样调整之后,银行的实际风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来,并且债权人的利益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第三,建立了流动性监管指标。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Liquidity Coverage Ratio,针对短期流动性管理)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Net Stable Funding Ratio,主要用于衡量中长期支付能力)两个新指标。
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为尽快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提升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监管当局在借鉴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于1995年7月颁布了《商业银行法》,这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制度的开端。自此,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制度逐渐向符合国际标准的资本监管体系过渡。2004年,银监会在参考巴塞尔协议Ⅰ和Ⅱ的基础上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自此,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理念和实践均进入国际化和规范化的新阶段,宣告与巴塞尔协议的资本监管体系正式接轨。我国资本监管新阶段始于2011年,银监会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要求,发布了一系列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进行调整的新文件,紧跟银行资本监管的国际标准。2013年初正式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采取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更加严格的资本定义,在各类资本工具方面还规定了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标准,并设定十年的过渡期,以使商业银行处理现有的不合格资本。《办法(试行)》针对信用风险的计量明确了权重法和内部评级法,其中权重法是在巴塞尔协议的标准法基础上调整了一些资产的风险权重,能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敏感性和激励相容度都比标准法更高,是风险管理方法的主流趋势。此外,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杠杆率要求、流动性风险监管动态监测都纳入监管法规,相关指标得到了改进(刘斌,2006)。
资料来源:根据银监会文件《关于我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2011)整理。
二、资本约束监管下的商业银行表内行为(Balance Sheet Activities)策略
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风险加权资产总额×100%,分子为资本净额,分母为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在分母保持相对平稳的状态下,分子越大,表明资本充足率越高,意味着银行资本覆盖风险资产的准备充分,其安全性高,反之则风险性高。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规定,是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资本安全运营的基本要求。为此,商业银行为满足资本约束监管的要求和持续经营的目标,均需通过筹集资本金或调整资产组合的风险结构来达到监管所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银行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采取行动,以应对资本约束监管,一是补充资本金数量,即分子策略(或称资本策略);二是紧缩信贷供给,调整资产结构,即分母策略(或称资产策略)。
第一种做法,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补充资本金。从长期看,银行可以通过留存收益的积累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实际上未分配利润转化为资本金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很难满足银行在短期内提升资本充足率的目标。另一种补充资本的方式就是发行新股,通过外部渠道融资,但该方式往往并不受银行高层和股东青睐。依据信息不对称和财务学理论,如果一家上市银行进行外部融资补充资本金,市场可能会解读为一种负面信息,认为该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够高,风险资产规模偏高,盈利能力较低等。此类悲观解读会使新股发行面临更高的风险溢价,直接造成银行的融资成本升高。由此可知,资本充足约束提高会导致银行对资本的需求加大,金融市场提供给银行的融资成本也会增加。另一方面,银行的现有股东在新股发行后会面临股权被稀释的情况,如果通过补充资本而相应增加的贷款(风险资产)所产生的利润,不能抵消融资成本和股权稀释所带来的损失,银行就不会有积极实施补充资本金的动机。
第二种做法,采取分母策略的操作思路,即降低风险资产规模。这种做法既可以在总量上减少风险资产组合的总额,也可以从结构上将风险权重较高的信贷资产转化为风险权重较低的其他类型资产(如低风险债券投资)。如果仅在表内业务的范围内操作,那么不论是风险资产规模整体下降,还是资产由高风险业务转向低风险业务,银行的利润都会相应减少。
总之,从银行现有股东的立场上看,分子策略将会增加融资成本、稀释股权,而分母策略降低风险资产也可能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无论分子还是分母策略,在面对更高的资本约束监管时,商业银行都面临利润下降的压力,银行股东的股息下降。但是,两种策略行为带来的股息下降比率会有差异。分子策略对股息下降的影响是股权稀释与利润下降的叠加效果,股息会在稀释的基础上再根据利润下降的比例而减少。分母策略只会造成风险资产规模下降,相应的利润下降带来股息减少。因此,商业银行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分母策略。
三、资本约束监管下的商业银行表外行为(Off-Balance Sheet Activities)策略
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从事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有可能引起损益变动的业务。表外业务不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的经营活动,使得银行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利益。它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表外业务是指构成或有资产和负债的、不会被列入资产负债表的业务;广义的表外业务泛指一切不被列入资产负债表的经营活动,应当包含不属于表内资产负债业务的其他全部业务。目前只有或有负债和承担项目(主要是信贷承担)被纳入了资本充足率约束,其他表外项目资产均不出现在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中。
1.通过表外业务实现监管成本最小化
商业银行在面临资本约束监管的条件下,可以进行监管资本套利,使监管成本最小化。对于普通的银行而言,业务量的增加意味着相应的风险加权资产增加,也就导致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母变大。在资本约束监管下,如果要保持资本充足率不变,就需要提高资本净额,使分子也相应变大。这相当于资本充足率约束给银行带来了一种监管成本。而为了使监管成本最小化,银行就有可能利用金融创新,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规模,以节约补充资本的成本(相当于逃避“资本税”)。然而,商业银行通过资本监管套利并没有降低银行的风险,却使得资本充足率虚假提高,它在为商业银行扩大盈利的同时,也损害了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有效性。
从目前商业银行经营情况来看,广义的表外业务为狭义的“或有风险”表外业务+“无风险”(风险权重为0)的表外业务(详见表2),如代理、结算、咨询等。表外业务的狭义与广义,根本区别在于对风险的界定。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商业银行认为狭义表外业务存在“或有风险”,而其余的广义表外业务部分被认为是“无风险”(风险权重为0)的经营活动。
在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中,风险加权资产总额既包括表内风险加权资产,也包括表外风险加权资产。但由于只有狭义表外业务被认为存在“或有风险”,所以在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实际计算中,受到表外业务影响的只有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部分。存在“或有风险”的表外业务项目,按照相应的信用转换系数纳入风险加权资产。其计算方式为:
风险加权金额=信贷承诺账面金额×信用转换系数×风险加权我国银监会采用的信用转换系数见表2:

表2 表外项目的信用转换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银监会文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2004)整理。
我国目前商业银行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的表外业务是狭义的表外业务,而广义范畴的表外业务包含的项目在大部分银行的披露中并未被明确为表外业务,而是以“结构化主体”或“代客交易业务”披露。按照信用转换系数计算之后,实际上真正被纳入风险加权资产的表外业务几乎只有信贷承诺部分(少量银行有计算衍生金融工具,但数额较小)。在风险敞口的披露中,表外风险敞口也只有“信贷承诺”一项。
需要指出的是,在表外业务概念中出现的“或有风险”和“无风险”都是基于监管法规界定标准的意义,而并不是基于实际经营行为的意义。根据对我国商业银行财务报告附注中有关表外业务披露内容的研究,以表外业务的名义进行风险暴露的只是狭义表外业务范畴的部分,而规模更大的广义表外业务范畴部分则被划入了“无风险”类别,不进行风险暴露。虽然这样的披露处理符合有关监管法规,但我们认为表外业务在两个方面对金融体系构成了实际的风险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上市银行财务报告附注内容整理。
第一个方面是资本约束监管指标失效。资本充足率这一资本约束监管指标的主旨就在于保证银行用充足的资本,以一个安全的比例覆盖风险资产的规模。但是对于表外业务的风险加权资产,要按照相应的信用转换系数计算。一旦信用转换系数低估了表外业务的实际风险,就会导致资本充足率虚假升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所有银行都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并未真正掌握在可控范围内。也就是说,资本充足率指标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剧。在财务报告附注中还有一部分广义表外业务项目并未以表外业务的名义进行风险暴露,即认为对于银行是不存在风险的。在这类项目中,“未纳入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和“代客交易”两类业务(以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和委托贷款为主)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都是“影子银行”较为常见的与银行合作的业务模式。实际上,风险并不会凭空消失,而是通过“影子银行”的业务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我们无法确切地掌握在这些表外业务中有多大比例的资金流向了“影子银行”业务。
在我国目前的财务报告附注中,表外业务项目中的“或有负债和承担”,对应的是巴塞尔委员会的狭义表外业务的定义,纳入了资本充足率约束*“或有负债和承担”的信贷风险加权金额,依据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根据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及到期期限等因素确定,采用的风险权重由0%至100%不等。的框架。但是在广义的表外业务定义下,我国最典型的代客交易的委托贷款业务和受托理财产品业务*指代客交易的理财产品业务(受托理财业务),商业银行不承诺保本。承诺保本的理财产品按规定应计入资产负债表。也属于表外业务范畴。然而,根据我们对商业银行财务报告的研究发现,委托贷款业务和理财业务下的资金目前处于完全脱离资本充足率约束的状态。这里,我们以银信合作为例,阐述我国表外业务的运营形态。
图1是以银信合作为例的一种典型操作方式。如图所示,箭头表示投融资及中介机构各方之间的关系,其中虚线框内表示传统的银行存贷业务,即表内业务;虚线框外部分,即表外业务,解释了表外业务是如何“出表”的。在投融资活动的始末两端都是同样的投资者和融资企业,表内和表外业务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业务操作路径。表内业务是投资者将资金存入银行(形成储蓄),再由银行将资金贷给融资企业。表外业务相对复杂一些,投资者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形成理财资金池),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并向银行出让信托收益权(银行用理财资金购买信托收益权),信托计划再以贷款或名股实债的方式将资金投给融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表外业务实现监管资本套利的逻辑是,对于同样一笔业务,以普通贷款业务处理将造成风险加权资产增大,而以表外业务(如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处理则可以不影响风险加权资产,同时收入的形式由存贷息差变为手续费或佣金,避免了本该增加的资本监管成本,由此实现了监管套利。

图1 表外业务的典型模式(以银信合作为例)
2.表外业务“刚性兑付”的风险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运行框架下,银行对于表外业务不承担风险的说法很难真正在操作中实现。虽然在银行的财务报告附注中会有关于表外业务的免责解释,如“本行只以代理人的身份根据委托方的指示持有和管理这些资产及负债,不需要承担任何信用风险”或“相关的投资风险是由投资者承担的”等。但是,从表外业务的实际操作模式来看,一旦项目出现信用风险,银行在“刚性兑付”的经营环境下往往难以全身而退。
虽然信托计划是由信托公司设立的,但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把钱投给了银行(只是从储蓄变成了购买理财产品),一旦发生兑付风险,投资者首先问责的还是银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刚性兑付意味着银行还可能成为信用违约的“兜底”者。在大规模兑付风险发生时,融资方、担保方以及信托公司有可能出现即使破产清算也无法清偿债务的情况(信托公司普遍高杠杆经营),面对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政府就有可能出面干涉,迫使资本实力相对雄厚的银行来消化信用风险。虽然监管当局和金融企业一直在努力破除“刚性兑付”的禁锢,但是在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信托行业保险制度实施之前,银行依然是潜在的表外业务信用风险承担者。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存在意义即是强制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能够对风险资产规模形成安全的匹配,然而在表外业务规模迅速膨胀的情况下,资本充足水平未必能满足对风险资产应有的覆盖,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会因此受到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约束监管下的经营行为,得出三项结论:
第一,商业银行应对资本充足率约束时,更倾向于选择分母(资产)策略。其原因在于银行在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时,更倾向于避免牺牲股东的利益(股权稀释、盈利下降),从而更不愿意采取补充资本的分子策略。
第二,商业银行在实施分母策略时,需要面对减少资产和保证盈利水平的权衡取舍,因此有很强的动机利用监管规则漏洞进行监管资本套利。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并不健全,表外业务更有利于银行满足资本充足率约束,表内资产出表成为进行监管套利的一个主要工具。银行以表外业务替代表内存贷业务则实现了在不影响风险加权资产的情况下保持收入增长的态势,规避了相应的资本监管,实现监管资本套利。
第三,商业银行通过资本监管套利并没有降低银行的风险,却使得资本充足率实现了虚假提高。如果将现存的表外业务进行合并监管,调整后的资本充足率指标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低于资本监管的最低要求。因此,表外业务在为商业银行创造价值的同时,很可能破坏了资本充足率标准作为审慎监管工具的有效性。
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强化完善动态资本补充机制。
监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引导商业银行将其业务发展的战略规划与监管要求相结合,对资本补充机制进行科学规划,从而使可持续的动态资本补充成为可能。要推动商业银行建立与完善长期资本补充机制。随着银监会、证监会于2014年4月明确优先股可以作为商业银行的非普通股一级资本,目前多家银行已着手发行优先股。在次级债补充渠道趋严的形势下,优先股应成为下一个银行资本补充的主要工具。
第二,制定表外业务项目披露的统一标准,规范财务报告附注相关内容。
我国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改善,目前存在信息不够完全、形式没有统一、非财务信息严重不足等问题。同时,应加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基于已有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进行系统化、具体化的改进,逐步建立与国际水平接轨的表外业务信息披露制度。
第三,探索科学的表外业务监管方法,有效管理表外业务风险。
监管部门需要兼顾金融创新与表外业务风险的防范,应当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套利进行有效识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确认某一种表外业务真正将风险转移出表。如果已转出的风险实际仍对表内资产有影响,却在监管标准中无法被有效鉴别,其危害可能会更大。表外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对监管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应捕捉不同业务模式的风险特征,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监管。
第四,落实杠杆率相关指标的信息披露,补充资本充足监管约束。
巴塞尔协议Ⅲ引入杠杆率指标,对商业银行的表内外资产规模加以无风险敏感性的监管约束。与资本充足率相比,杠杆率不考虑风险因素,但能对包括表外业务在内的资产存量进行杠杆约束,对资本充足率起到了补充作用,具有简单直观、便于监管的特性(袁鲲 等,2014),有助于商业银行主动按杠杆率要求控制经营风险,减少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更能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效能。
参考文献: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文献汇编[M].中国人民银行,译.
巴曙松,陈姝祎,2013.巴塞尔协议III在美国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学术月刊(9):74-81.
黄宪,马理,代军勋,2005.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分析[J].金融研究(7):95-103.
刘斌,2006.资本充足率对我国贷款和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11):18-30.
温信祥,2006.银行资本监管对信贷供给的影响研究[J].金融研究(4):61-70.
吴栋,周建平,2006.资本要求和商业银行行为:中国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8):144-153.
袁鲲,饶素凡,2014.银行资本、风险承担与杠杆率约束——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2003—2012年)[J].国际金融研究(8):52-60.
BLUM J,1999. Do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Reduce Risks in Banking?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3(5):755-771.
HYUN J S, RHEE B K,2011. Bank Capital Regulation and Credit Supply[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5(2):323-330.
MYERS S C, MAJLUF N S,1984.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2):187-221.
SHRIEVES R E, DAHL D, SPIVEY M F, 1992. Capital Market Regimes and Bank Structure in Europe [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Huntsman School of Business, Utah State University.
责任编校:黄琼张朝胜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3.015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3-0141-0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方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艾子健,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助理经理(北京10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