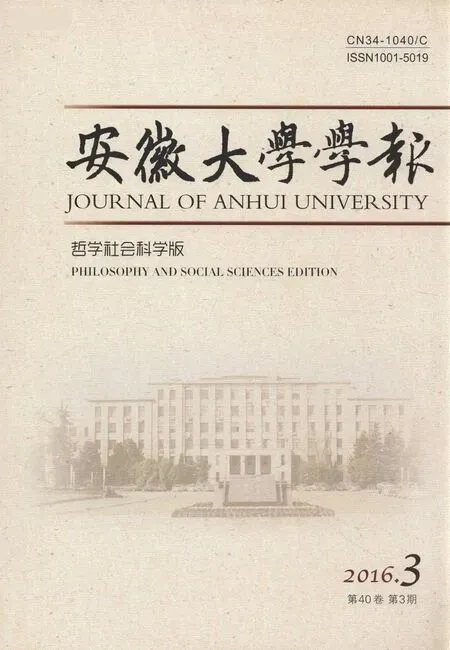培根、迪昂与判决性实验
刘钰森
培根、迪昂与判决性实验
刘钰森
摘要:迪昂所批判的判决性实验在哲学史上来自培根关于路标事例的观点。通过追溯培根路标事例的语境,可以发现,迪昂的批判对培根的观点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对比培根和迪昂的相关著作,或许可以消除这种误读,并且发现培根与迪昂方法论背后隐含的知识论意蕴,以及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相通之处。由此也能对判决性实验的认识论性质和地位做出判断。
关键词:培根;迪昂;判决性实验;纯粹归纳;整体论
迪昂(Pierre Duhem)在《为了拯救现象》(ToSavethePhenomena:AnEssayontheIdeaofPhysicalTheoryfromPlatotoGalileo)中引述了伽利略的一段话:“展示哥白尼的观点并不与圣经(Scripture)相对立的最快捷和最确定的方式是,通过一千个证据显示这个命题是真的而且对立的观点完全不能维持。因此,既然两种真理不能互相对立,被确认为真的观点必然与圣经相一致。”*Pierre Duhem, To Save the Phenomena: An Essay on the Idea of Physical Theory from Plato to Galileo, translated by Edmund Dolan and Chaninah Masch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 109.在迪昂看来,伽利略关于实验方法有效性和使用实验方法的艺术的定义接近于培根(Francis Bacon)后来所明确表达的那些定义。伽利略和培根的方法模仿的是几何学中的归谬法:“经验通过确认一个错误的体系,推出它的对立面的确定性。”*Pierre Duhem, To Save the Phenomena: An Essay on the Idea of Physical Theory from Plato to Galileo, p. 109.由此,实验科学发展中遇到的二难状况都被判决性实验解决。对迪昂而言,这种构想实验方法的方式因为过于简单而完全错误。
迪昂所反对的观点,在培根那里是所谓的“路标事例”(cross instances)*本文所引的《新工具》英译本已译成crucial instances,即迪昂所说的判决性实验(experimentum crucis)。的相关主张。这种观点认为:无论结果如何,一个判决性实验应当清楚明白地支持处于检验之下的两个竞争理论之中的一个。根据迪昂的批判,表面看来,培根以及他的追随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认为理论是孤立地接受证据的检验的。然而贴近培根《新工具》的文本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在这种观点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形式论”:按照培根所说,通过归纳的方法,人们可以逐步发现自然潜在的因果结构,或者形式(form);而“路标事例”是人们藉于发现这种形式的工具之一。
迪昂并没有怎么提及培根关于“路标事例”的主张所隐含的“形式论”,他直接批判的是英国哲学所反映的英国心灵的特色:喜欢堆积事实,而不是连贯推理。在他看来,培根恰好是这种英国心灵的代表。迪昂甚至认为,没必要在《新工具》中寻找方法,因为,“在那里什么都没有”*Pierre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Philip P. Wien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66.。从培根的文本来看,迪昂基于他对各国心灵分类的成见,对培根思想的解读和批判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对比培根在《新工具》中的观点与迪昂在《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和《为了拯救现象》等著作中的观点,也许可以澄清这种误读,并进一步发现培根与迪昂的观点所隐含的知识论意蕴,以及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相通之处。
一、培根的新工具与“路标事例”
培根在《新工具》开篇就批判了自古以来自然哲学的两种倾向:一种把自然法则当作已被搜录出来的清楚明白的东西加以规定,同时断绝进一步的探讨;另一种认为没有什么是可以了解的(指感官的不确定而言)。这些哲学家想要推进理性,却又不是从真出发,也达不到正确的结论。这造成两个极端:对一切妄下论断和不敢希望了解任何事物。较早的希腊人在这两种极端之间采取了较为明智的立场:他们抱怨探究知识的困难而努力追求自己的构思并与自然接洽;他们认为,对于事物是否可了解这一点,辩论并不恰当,通过实验获知才是恰当的。然而这些人又只是依赖理智的冲动,不能应用规则,还把一切都诉诸心灵的无止境和无目的的活动之上*Cf. 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Lisa Jardine and Michael Silverthorne (trans. and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7.。
培根提出一条新的道路:直接以感官验证为起点,并排斥继感官而起的大部分心灵动作,用新的工具像机器那样逐步地引导,循序渐进地达到最后的真理。这是他将智力活动与机械力的活动相比拟而得出的结论。培根指出,获得知识的方法有两种:培养知识和发明知识。培养知识的方法要求从确定无疑的最普遍的原理出发做出判断,进而发现中级公理。在培根看来,这种“心灵的预期”对知识进步是无益的。他推崇的是发明知识的方法,即“诠释自然”,遵循这种方法的人“所关心和关注的,不只是对已经发现的东西和对它的使用感到满足,而是进一步的洞察和理解;不是在辩论中击败自然而是通过行动征服自然;不是拥有美妙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而是拥有可靠的解证的知识”*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p. 30.。
以实际的行动代替论辩的作风,放弃似是而非的观点,从而寻求获得可靠的解证知识的“诠释自然”之路,也就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原理,在逐步而无间断的攀登中上升,最后达到最普通的原理”*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p. 36.。在培根看来,可靠性是可以获得的,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要提供给感官和理解力相应的帮助。就像手用工具为人们的工作提供动力或者引导一样,心用的工具能为人们的理解力提供启示或者警告。
不过,培根也指出,在“工具”帮助下达到确定性的最普通的真理之前,人们最好先把以前的一切成见撇在一边,尤其要弃尽摒绝的是人们熟知的四类假象: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以及剧场假象。这些假象总的来说是由于理解力的一些本性造成的:理解力总把世界中的秩序性和规则性设想得比所见到的多一些,这就形成了一些虚构,参照这些虚构,人们总喜欢和它们相符合的事件,却忽视和它们不符合的事件。理解力本性产生的虚构经常会对事物进行抽象并赋予其本体和实在,这在培根看来还不如直接剖析自然:“我们应当研究物质及其结构,以及结构的变化、单纯的活动和活动或运动的规律”*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p. 45.。
按照培根新的方法论,人们应当深入物质的内部,不仅探求它的结构,还要探求它的内部活动规律。而以往的思辨和探究的对象则是事物所由之产生的一些静的原理,而非动的原理。
通常关于运动的说法也只涉及程度,而未深入自然里面。这主要是由于以往论证的途径出了问题。以往的解证方法依循从感觉和事物到原理和结论的过程,过程中的四个方面分别存在各自的缺陷:因为感觉的失效和欺骗,感觉和印象本身是有缺陷的;概念由感觉印象不充分地抽象而来,其间的界定是不确定和混淆的;不通过排除法和分解法而只是简单枚举的归纳是不充分的;发现和证明的方法,“首先建立最普遍的原则,然后通过这些普遍原则比较和检验中间原理,是错误之母,带来所有科学的毁灭”*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p. 57.。
培根提供给理解力以“新工具”,为的就是摒弃四种假象以及避免以往方法的错误,但这种“新工具”也始于经验,这种经验应该是不超出实际的实验。具体来说,哲学应该像蜜蜂那样地运作,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集来的材料经过变化和消化而放置于理解力之中。这要求人们首先放弃成见,直接面对特殊的东西,也就是坚决地肃清陈旧学说和普通概念,并将肃清后获得的坚定的理解力应用于特殊的东西上面。接着,自然哲学应该依照较好的计划编纂,这需要“光的实验”(illuminating experiments)的大力支持:“只有当自然史能够获得并累积许多本身无用却会帮助发现原因和原理的实验的时候,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才是有根据的。”*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p. 81.
除了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实验之外,自然哲学的编纂还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足以促进和提高感官经验水平的方法、程序和过程,而且经验必须遵循确定的规律前行。培根因此规划的是一种新的归纳法,由于简单枚举很有可能遭遇相反事例攻击的危险,新归纳法将以正当的排拒法和排除法来分析自然:先得到足够数量的反面事例,然后再根据正面事例得出结论。这种方法不仅可用于发现原理,还能用于形成概念,在它们指导下便可以获得新的特殊事物的知识。这种新方法或者新工具更具体来说就是:
首先,必须编制一部良好的、充分的自然和实验的历史作为基础。人们不应当虚构或者想象而是应该致力于发现自然之所为所是。其次,自然和实验的历史要依循一种恰当的秩序表述,以免使理解出现混淆,要编排表格和排列事例(instances),如此心灵才可能按照它们行事。最后,按照这种方法,培根展示了如何初步得到热的形式的过程:概括来说就是分别列出与热相一致的各种事例(在现表,table of existence and presence)、不一致的各种事例(歧异表,table of divergence)和热的各种程度表(比较表,Table of Degrees),最后再用排拒法初步得出所谓的热的形式*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pp. 110-135.。但仅有以上这些还是不够的。培根指出还需要“一些享有优先权的事例”的九个部分的“帮助”,但是在《新工具》中他只展示了“一些享有优先权的事例”,“路标事例”就是其中之一。就像在得到热的形式的展示中提到的事例一样,这些事例指的是一些经验的现象,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光的实验”。培根对“路标事例”做了如下界定:
“在享有优先权的事例中第十四位,我们放置的是路标事例;我们从路标那里取得这个词,路标树立在交叉路口,指示和标识不同的路的走向。我们也称它们为判定性和裁决性的事例;在某些情况下,又叫作神谕性的和诏令性的事例。这就是它们如何起作用:在研究某一性质(nature)时,由于许多性质惯常地同时紧密出现,这就使得理解力难以辨别轻重,并且不能确定应把两个或者(偶尔)更多性质中的哪一个归结或者指定为所研究的性质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路标事例就能表明这些性质当中的某一个与所研究性质的联系是稳固的和不可分的,而其他性质与所研究的性质的联系则是变异的和可分的;一旦认定前一性质为原因,而把后者摒弃和排去,研究就终结了。因此这种事例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也具有高度的权威;诠释的过程有时就在它们之中结束并且通过它们得以完成。”*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p. 159.
培根花了很大的篇幅列举若干“路标事例”。《新工具》的中文译者许宝骙先生在中译本脚注中也转引了拉瓦锡舍燃素说而取氧化说的“路标事例”:拉瓦锡取定量的锡,严封于一玻璃弯颈蒸馏器,称量之后加火煅烧再称量,重量不变。冷却后打开蒸馏器让空气进入,再行称量,发现重了十英厘,取出锡称量,发现多出的重量都在锡上面。按培根的观点来看,这个实验就是一种路标事例,它决定了氧化说的成立和燃素说的失败*参见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7页译者脚注。。
培根“光的实验”就是通过一个事例或者说实验来判定特定的原因,这也属于探究动力因、物质因、潜在过程和潜在结构的物理学的研究范畴。就如前所述的热的形式以及路标事例来看,培根所探究的仅仅属于物理学范围内的自然的潜在因果结构的层次。这一层次也被他称为形式或者定义(definition),尚未达到他所划分的另一种形式,即探究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层次。培根方法论的出发点在于试图摒弃一切成见,这是他将自己的方法论与以往的方法论区分开来的立足点,这也使他的方法论被视为一种素朴的方法论。在批评者看来,培根忽视了实验在获得自然隐藏的因果结构形式之前,可能往往避免不了要与一些成见还有相关的经验内容联结起来,这可能使得路标事例失效。迪昂对培根的批判之一看来正着眼于此。
二、迪昂对培根方法的批判
培根要求摒弃一切成见的观点,被克劳德·贝尔纳(Claud Bernard)表达为“心灵的自由”:“致力于自然现象探究的科学家不得不践行的第一个条件是,基于哲学怀疑,保持心灵的完全自由。”*Pierre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 180.理论可以启发实验,但是实验过程以及对于实验的表述,理论不能干预。比如生理学家在报告他的实验时,他报告的必须是对事实的自然状态的描述(raw description)。然而迪昂认为,不被理论干预的实验及其表述是不可能的。如他所指,在做物理学实验时,物理学家心灵中有两种不可分割的仪器:具体的玻璃和金属的仪器;还有图式的和抽象的仪器,即数学符号所表述的抽象概念。虽然在化学和生理学的一些分支中数学符号的表述还未被引入,但是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在研究中也要依赖对物理学理论的信任。因此迪昂认为,无论化学家、生理学家还是物理学家,他们对实验的表述都隐含着对整个理念群的信任*Pierre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 182.。
迪昂接着提出著名的应用实验与检验实验的区分。应用实验,顾名思义就是把已知的理论应用到实验中,让它在实验中重现。这种实验对于实践有所助益,对于科学进步却没有贡献。迪昂着重讨论的是检验实验,这种实验源于物理学家对于理论的怀疑,以被怀疑的理论为前提,按照归谬法设计实验,如果实验不出现该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则可判定该理论不适用。迪昂反对这种观点,如前所述,迪昂认为实验表述隐含着科学家对理论群的信任,当预期结果不出现时,出问题的可能是理论群中的某一个理论,而不是被检验的理论。他以维内尔实验和傅科实验为例,认为这两个例子中,通过调整理论群就可以拯救被检验的理论。
在迪昂看来,培根的路标事例也属于归谬法的应用。比如,按照培根的路标事例来看,傅科实验就是宣判波动假说成立而发射假说谬误的判决性实验。但是,迪昂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傅科实验背后,存在着牛顿体系与惠更斯体系的较劲。除了理论整体带来的负担可能使归谬法无效之外,还存在着竞争的理论假说的第三种可能,比如在发射假说和波动假说之外,还有麦克斯韦提出的光是在电介质中传播的周期性扰动的第三种假说。
在归谬法之外,直接证明应该是几何学最完善的证明方式。那么,物理学能否模仿这种证明方式呢?培根要求从特殊的事物中抽取知识,牛顿也要求健全的物理学的每个命题都从现象引出并用归纳法概括。但这种对直接证明方式的应用在迪昂看来在物理学中却是行不通的。牛顿基于理论是演绎自实验规律而声称理论具有绝对确定性。但在二十世纪之前,“演绎”这个词被过于宽泛地使用了,它既被用于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演绎,也被用于可导向最佳解释的归纳推理和论证。牛顿的演绎其实是归纳的普遍化。牛顿认为万有引力理论可分解为各自分离的基本原理,每一原理因演绎自现象而被确立为真,它们的确定性来自源自观察的开普勒行星运动律的确定性。迪昂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突破口,他论证道:如果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正确,则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律错误,因为依照万有引力理论,行星之间是互相干扰的,而由于其他行星的干扰,没有行星或行星的卫星刚好就像开普勒的规律要求的那样在椭圆轨道上运动*Pierre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 193.。
迪昂得出这种观点的根据是整体论,他认为牛顿理论的确定性涉及整个假说群与整个事实群相比较的问题。这种比较将得出为天体运动做自然分类的原理,而这进一步又与他所认为的物理学理论的自然分类目的观相关联。在迪昂看来,物理学理论不是由异质的不相容的模型构成,它在逻辑统一的必要条件下倾向于自然分类。从科学史上分析牛顿和安培的失败可以得出,依照纯粹归纳法来构造理论的方式是走不通的。迪昂提出他自己的关于理论形成的方式:
1.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这主要是定义所谓的“简单的性质”并测量它们。2.假说的选择。这些假说就是作为理论基础的少数原理。3.理论的数学展开。4.理论与实验的比较。迪昂强调,这四个步骤与说明实在无关,或者说它们的目的不在于说明。他认为,界定简单性质的数学符号与物理性质之间并没有本质联系,它们之间只不过是记号和被记号的关系。在理论的数学展开中,理论的各个假说(原理)按照数学分析规则组合起来,物理学家只需满足代数逻辑,并不要求影响他计算的量是物理实在。因为假说并不陈述物体性质间的真实关系,物理学家的操作是否对应于真实的物理转换也无关紧要,只是他的推论要有效,计算要精确*Pierre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p. 19-21.。
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步是理论与实验的比较。迪昂认识到,如果坚持整体论的比较,那么看起来那些不可胜数的和混乱无序的实验律可能会使这种比较不可能进行。但是科学史表明,通过逐渐进化,作为理论基础的物理学假说可以消解这种整体论的负担。从迪昂对万有引力假说的形成的详细表述来看,人们可以发现,万有引力假说相关的理论整体的各个部分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地经受实验的检验,直到最后,大地测量的结果使牛顿能够将令他疑惑的部分加以计算并且消解疑惑,从此得出成熟的理论*Pierre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 252. 在皮卡德(Picard)大地测量结果出来之前,因为地球的尺度不精确,牛顿算出来的关于月球所占位置的引力值比他理论预期的结果高了六分之一,这使得严格奉行经验方法的牛顿推迟发布他的理论。而大地测量结果出来后,牛顿根据新数据算出来的结果完全符合预期。。
由上述可见,迪昂对培根的批判从培根方法论的出发点“摒弃一切成见”开始,在他看来这种做法导致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摒弃作为整体的理论的影响,将单个假说孤立起来接受实验的归谬检验,从而产生判决性实验。即使不使用归谬法,按照培根开启的纯粹归纳法进行的直接证明在牛顿那里也产生了矛盾。除了批判培根方法论的出发点以及他的归纳法在应用上遇到的问题之外,迪昂还认为在培根的《新工具》中根本没有方法可言。迪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发现按照培根的那些列表,呈现出的只是大量混杂无用的报告。对于“享有优先权的事例”,迪昂认为培根没有进行分类和分析,欠缺精密公式的表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培根执着于具体的和实际的东西,对于抽象和演绎却抱着无知和厌烦的态度。
总的来说,相对于培根方法论的素朴,迪昂方法论的形成奠基在培根之后科学发展的成就之上。他对培根方法论的批判所根据的主要就是他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及物理学理论的自然分类的目的观。但是,迪昂之后,培根所强调的摒弃虚构以及完全面对事实,从特殊的事物抽取知识,并用以指导新的实验的进路所体现出来的原则,也就是被牛顿所认同和继承的东西,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在近些年还被所谓的解证归纳的支持者用来作为支撑判决性实验成立的论据。
三、培根、迪昂与判决性实验
就迪昂的整体论来看,如果人们总是在面临反例的时候通过调整理论整体来拯救理论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不承认有什么客观标准足以评判两个竞争理论之间的优劣,从而也没有做理论选择的必要。迪昂对判决性实验的批判,带出的是基于证据的理论的非完全决定性。这在追求客观性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还是有人用从经验出发的方法来追求一种理论选择的客观标准,从而与理论的非完全决定性相对抗。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的解证归纳(Demonstrative Induction),它的原则类同于培根方法论的一个前提,即排除“人心的预测”所带来的虚构。解证归纳的支持者相信存在一种类似培根的“形式”的确定性标准。
在马西米(M. Massimi)的《解证归纳能为对抗非完全决定性做什么:玻尔、海森堡和泡利论光谱的不规则性》一文中,引述了牛顿的两段原文:
“牛顿的旁注在回忆了笛卡尔的星体漩涡学说的困难之后,有力地捍卫了万有引力律,但是同时辩解性地表明:‘我迄今不能从现象发现这些引力的属性的原因,并且我也没有捏造假说。因为无论什么理论,如果不是演绎自现象,都将被称为一个假说。任何假说,形而上的或者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地位。’”
“在实验哲学中,我们将收集自现象的一般归纳的命题看作是真确的或者非常接近于真的,而不支持任何相反的可能被想象的假说,直到其他现象出现,通过这些现象,假说或者被构思得更精确,或者更易于做出预期。我们必须遵从的是这个规则,那就是假说不能逃避归纳论证。”*Michela Massimi, What Demonstrative Induction Can Do Against the Threat of Underdetermination: Bohr, Heisenberg, and Pauli on Spectroscopic Anomalies (1921-24), Synthese, 2004, vol. 140, no. 3, p. 256.
从牛顿的观点来看,他排斥“可能被想象的假说”,而“将收集自现象的一般归纳的命题看作是真确的或者非常接近于真的”。这“真确的或者非常接近于真的”命题就是马西米等人推崇的解证归纳的客观标准所在,也就是他们用来反对非完全决定性的大前提(major premise)。但解证归纳也面临一些问题:它的大前提几乎从来不是确定的(因为难以检验),或者因为预设了必须被证明之物,大前提的确定性回避了可能产生的问题(比如作为源头的感觉经验的不确定性)。解证归纳与假说-演绎法之间界限模糊,所谓的大前提的知识基础因其无限后退的弊端而不能获得解证归纳的鉴定。背景知识(大前提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由假说构成。然而马西米搁置了这些问题,坚持用解证归纳的框架解决一个科学史案例中的非完全决定性问题,最后得出:相对于其他竞争理论,泡利的光谱理论最具有经验充足性并最终是理论充足性的。
马西米的观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也许可以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另外一种补充,即用一种与经验相关却又具有先在性的大前提(在他看来,大前提能够作为客观标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理论充足性),以保证理论选择有所依从。这种先在性的大前提还包括背景知识,由此就并不绝对否定整体论。而从培根得出热的形式的那些步骤来看,他也需要背景知识,不过从他列举的在现表、歧异表和比较表来看,这些知识的确更像是迪昂所说的混乱无序的一大堆实验律。
无论如何,摒弃一切成见的出发点并没有让培根把接受实验检验的理论完全孤立起来。而且这个出发点也并非培根方法论的核心。在培根看来,“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单纯地累积和使用;理性主义者,就像蜘蛛,从自己身上编织网络;蜜蜂的道路介乎两者之间:它从花园和田野的花那里采集材料;不过它有能力转换和消化它们”*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p. 79.。言下之意,好的科学家不像蚂蚁(比喻经验论者,盲目地收集证据)或者蜘蛛(比喻理性论者,编织空洞的理论),而如同蜜蜂,将自然转换为有营养的产物。培根意图寻找介乎经验论者和理性论者之间的路线。迪昂所批评的,培根的《新工具》中只有杂乱的材料而没有方法,从培根上述的观点看来其实正是他反对的。培根所追求的“中间路线”可以引申出科学家工作的目标在于多产性。而迪昂提出的物理学理论的非形而上学说明的自然分类目的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物理学理论的多产性,即在预测方面的成功。二者恰有一定的一致性。
培根的《新工具》中所枚举的列表和诸多事例在迪昂所处的时代看来是有着诸多谬误的,它们的排列的确也显得缺乏分析和分类。但是细看培根新方法的三个步骤,在进行归纳之前,培根要求编纂一个良好的自然史,还要求进行有序的排列,所以,即使培根自己没能实现他的方法论要求,他的先见之明也依然带有整体论的意味,而且也与迪昂的自然分类目的观一样强调秩序和结构。如前所述,培根在反对理解力本性所带有的虚构及其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实在和本体的同时,要求剖析自然,研究物质、物质的结构及其变化。迪昂也反对把形而上学说明当成物理学理论的目的,而取代以自然分类。
培根把他的哲学标榜为“自然哲学”。照克利的说法,这属于由自然做主的立场*Robert Klee,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tting Nature at Its Seam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3-64.。培根认为通过他的新归纳法,能够引导人类心灵逐步获得关于自然隐藏的因果结构的知识。迪昂也认为,如果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是合乎理性的,要具备知识的价值,它就应当教给人们超验的东西,这些东西使得理论应当是对“一种形而上学的越来越清晰精确的反映。对超越物理学的秩序的信念是物理学理论存在的唯一理由”*Pierre Duhem, Logical Examination of Phys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Peter Barker and Roger Ariew, Synthese, 1990, vol. 83, no. 2, p. 187.。如彼得·佩希奇(Peter Pesic)所解读的,培根并不主张人类有能力“拷问”自然,他预想了实验的自然出现的特征,并把自己当作号手或者传令官而非战士。培根认识到人类能力有限,要探究自然的深度,就必须通过艰巨的实验。培根描述的是尚未成形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捍卫实验的合法性,实验能为感觉提供帮助,纠正它的错误。培根对于实验一词的使用,强调的是内在于实验一词的检验或者试验的意义*Peter Pesic, Wrestling with Proteus: Francis Bacon and the “Torture” of Nature, Isis, 1999, vol. 90, no. 1, p. 82.。由此可见,认识到实验艰巨性的培根并不认为通过某个实验就能一劳永逸地获得自然的秘密。被后世称为判决性实验雏形的路标事例也只不过是诸多优先性事例中的一个。
从迪昂反对形而上学说明而主张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在于自然分类来看,迪昂也认为物理学家的能力有限,不能达到对实在的说明的层次,而只能对实在的关系加以分类。加上在迪昂看来,完美发展的理论具备符号化和近似度两个特征。因此,他认为实验方法的论证价值并没有培根和牛顿他们说的那么绝对,它们起作用的条件也比较复杂,对于它们的结论的评价也须得谨慎。迪昂虽然反对经由纯粹归纳获得的假说体系,但是他也认为归纳可以指明获得某些假说的路径。从本文前两部分所介绍的培根获得“形式”和迪昂获得理论的步骤可见,培根将实验当作获得形式的基础,而迪昂却认为,实验证实处于理论的“拱顶”。除了是否认同“摒弃一切成见”之外,恐怕培根和迪昂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此。
迪昂对培根的误读主要在于,他根据培根限于时代局限所列举的表格和关于“优先性事例”的排列混乱而认为《新工具》中根本没有方法可言,他似乎把培根“摒弃一切成见”的出发点以及纯粹归纳法视作培根思想的全部。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培根的思想与迪昂的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处,而这些相通之处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他们都认识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以及在这种有限的能力之下,人类对于自然知识可以如何探究。在这种观点之下,判决性实验其实是有意义的,但是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培根所谓的直接的指示,而是在于间接性的作用。就如同爱因斯坦评价迈克尔逊实验对于他的狭义相对论的意义时所言:物理学家面对自然的难题而不断斗争,他们试图获得的每个结论都是通过非常不直接的方式获得的。实验对于科学进步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促成一个理论体系的往往是多个实验,而并非是单个判决性的实验*Cf. Gerald Holton, Einstein, Michelson, and the “Crucial” Experiment, Isis, 1969, vol. 60, no. 2, p.158, p. 197.。
LIU Yusen, lecture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Philosophy,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Center for French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责任编校:余沉
Bacon, Duhem and Crucial Experiment
LIU Yusen
Abstract:Duhem’s critique of crucial experiment is based on Bacon’s views on cross instances. By tracing the origin, Duhem’s critique is found to be a misreading of Bacon’s views. A comparison of the works of Bacon and Duhem may clarify this misreading. Furthermore, common grounds and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underlying their methodologies can be discovered. Evaluation can thus be made on the epistemological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crucial experiment.
Key Words:Bacon; Duhem; crucial experiment; pure induction; holism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3.004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3-0026-08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5XZX06)
作者简介:刘钰森,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法国哲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广东 广州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