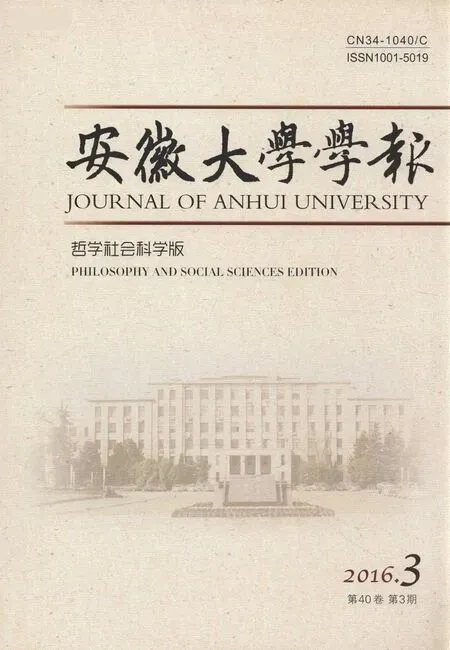人类的视域与其他物类的视域
章启群
人类的视域与其他物类的视域
章启群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為夭。”*《续古逸丛书·宋刊南华真经》影印本。其文意从字面直译很简单:如果天下莫大于秋天大雁的豪毛之末,则泰山因而为小;如果短命的婴儿为长寿,则千年之寿的彭祖亦为夭折。然而,从思想和逻辑的层面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则非常困难。历代注《庄子》大家对此大多止于联想臆测之说,不得其旨。下面将代表性解释略引几例。
今人蒋锡昌《齐物论校释》云:“此谓设彼不见大山,只见秋豪之末,与小于豪末万倍之物,则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矣。设彼不见豪末,只见大山,与大于大山万倍之物,则大山为小矣。设彼不见彭祖,只见殇子与寿命短于殇子之人,则天下莫寿乎殇子矣。设彼不见殇子,只见彭祖,与寿命长于彭祖之人,则彭祖为夭矣。盖万物之真相,以观者之异,可至各不相同;《德充符》所谓‘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庄子此文,系言万物之异。异即百家之学,乃儒墨等辩士所据以争论是非者也。”*蒋锡昌:《庄子哲学》,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第146~147页。蒋氏之说意在说明,《庄子》揭示出每个人自己的局限,即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会看出不同的结果。因此将此句与“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类同。他的解释虽然涉及视域问题,然而在言及万物之后,又归结为每个人的视域,因此又远离《庄子》旨趣而去。王叔岷之说意亦与此相近。他认为:“《庄子》意在破世俗之大小、寿夭之执。然《庄子》之言亦不可执著,若必以秋毫为大,大山为小;殇子为寿,彭祖为夭,则又非《庄子》之旨矣。”*王叔岷:《庄子校诠》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1页。此说更有简单化之嫌。蒋、王二人的解释虽然没有落入“《庄子》郭象注”之窠臼,把我们的理解导入常识层面,然而,他们对于《庄子》此句意涵的理解却也没有根本的破局,仍囿于表面字义的藩篱。
在众多解释之中,陈鼓应注释颇值得注意。他说:“在经验世界中,一个常人认为极大的东西,若从更广阔的空间上来衡量,却显得十分微小。相反的,一个常人认为极细微的东西,逼近了看,却可发现其中含藏着无尽丰富的内容。《庄子》虽然有意忽略相对事物中的绝对性(即在特定的关系中,大和小的区分是绝对的;如在狗和蚂蚁的特定关系中,狗为大而蚂蚁为小是绝对的),然而《庄子》的目的,却不在对现象界作区别,乃在于扩大人的视野,以透破现象界中的时空界线。若能将现象界中时空的界线一一透破,心灵才能从锁闭的境域中超拔出来。”*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1~72页。他的解释并不十分清晰,而且最后又把《庄子》此句的意旨归结为“心灵”“境域”的“超拔”,因而把属于常识和经验层面的道理玄虚化了,变得神乎其神。但是,他毕竟引入了两个概念,即“时空”和“绝对与相对”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概念有可能使得文本阐释进入一个更加开阔、深入的层面。
我认为,《庄子》此处着重提出的是“视域”问题。“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是从空间视域来说的,意思即,如果一种微生物,它们生活在一个空间只有“秋豪之末”大小的微观世界中,所有的事物包括“泰山”,当然都是小的。人之所以以泰山为大,以秋豪之末为小,那是以人的“视域”来衡量的。而“莫大于秋豪之末”是与人类不同的另一些物类的空间世界,它们的视域与人类的视域具有不可比性。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微生物的存在已经是常识。因此,我们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产生困难。相反,对于古代的《庄子》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油然敬佩。
第二句“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是从时间的视域即生命的长短来论述的。此句意思是说,如果有一种物种只有夭折的婴儿的生命长度,那么,再长的寿命(例如彭祖)它们也是无法认知的。人之所以认为彭祖为寿而殇子为夭折,是以常人的生命时间为衡量标准的。人类一般不过百岁(《古诗十九首》:“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大约超过七十岁则为寿(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以此作为尺度,则彭祖当然为寿,而襁褓死亡的婴儿当然为夭。但对于那些只有殇子那样生命长度的物类,看待生命长短的标准就完全不同了。可见,《庄子》在这里提出的是人类视域之外,其他物类可能的空间世界以及生命长度的标准问题。在这些物类的视域中,“大山为小”和“彭祖为夭”,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庄子》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
在现实世界几乎所有的普通人,观照世界都离不开自身的视域。无论是市井小民、帝王将相,还是文人骚客、商贾游侠,他们关注的对象虽有不同,或是日常生计,或是宫闱秘事、军国机要,或是琴、棋、书、画,或是商战生意、江湖义气,等等,但都是与自身相关的社会活动。作为思想者的百家诸子虽然讨论人生与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也没有跳出人类自身的视域。他们也是以国家、社会、家庭或个人为中心来提出各种思想理论,为人类设计各种美好的方案。然而,《庄子》的视域与所有这些视域不同。《庄子》的极为可贵之处在于,它意在打破人们习以为常以人类自身的视域观照世界的观念,进入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类观照世界的视域。因此,《庄子》的这两句话,不仅提出了普通人从来没有想到的视域,也达到先秦诸子所未达及的境界:即人类只是世界万物中之一物,人类对于世界的观照和解释只能是基于自己的视域。但是,这种只是人类自己的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不能够达到其他物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因而也根本不能揭示世界万物本身的旨归。简言之,人类以自我的尺度作为地球万类的尺度,是没有合法性的。人类一直以自己为中心的意识,是一种无意识的人类自大症。《庄子》的目的就是试图打破人类自身的这个视域之障碍,引领思想者进入地球全方位的视域。《庄子》之“齐物”主旨,皆在于此。由此可见,《庄子》不仅指出人类之中因立场、角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观念,如出现儒墨之间“是其所非,非其所是”的无谓争论,而且还指出整个人类以自身尺度为万类尺度、无视其他物类的自大盲区。这个思想的深刻之处不仅超越了当时思想界的儒墨二家,而且千古独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着巨大的思想震撼力。
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涉及这个问题。当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认为:“探讨世界的本质,不是探讨世界在观念中之所是,如果我们已经使世界成为讨论的主题的话,而是探讨在主题化之前世界实际上为我们之所是。”其实,人们在谈论世界之前,实际上已经将世界人为“格式化”了。人类谈论的“世界”,只能是人类的“世界”,而不是其他万类所感知的“世界”。属于人类的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我们的知觉建构的。在知觉的建构之后,“世界不是我掌握其构成规律的客体,世界是自然环境,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鲜明知觉的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意识都是知觉的意识”。“意识的观点认为,一个世界首先是在我周围展现和开始为我存在。”而知觉首先是身体的知觉。身体是一个“原始存在”,一个整体。人对于空间的把握首先来自于身体的知觉。“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身体的空间性显然是在活动中实现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实际上是用身体来衡量环境的。“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世界。”“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与之一起形成一个系统。”*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页、5页、495页、3页、137~138页、265页、261页。人类的“世界”就是由身体、知觉和意识建构起来的一个系统的外在时空对象。梅洛-庞蒂的理论具有切实的经验实证性,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体验加以证明。他的理论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庄子》所说的“天下”。
概而言之,“大山”与“秋豪之末”之大小,“彭祖”与“殇子”之寿夭,在人类的“世界”与在其他物类的“世界”中都是不可比的。只有跳出人类的视域,我们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庄子》“齐物”的要点在此,高度和深度亦在此。
郭象注云:“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豪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茍各足于其性,则秋豪不独小其小,而太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则虽太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太山为小,则天下无大矣。秋豪为大,则天下无小矣。无小无大,无寿无夭,是以蟪蛄不羡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贵天池而荣愿以足。”*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1页。郭象是将事物之外在形状与自身性分进行分别,认为《庄子》之意旨在适性,而无视外形。成玄英疏亦承其意旨,文字大同小异。郭象“性分说”为注庄史上最广泛通行之解释。而郭象与《庄子》文本思想之差异,亦为学界之共识。此处显然看到《庄子》与郭象二义不同。仅就“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言,郭注语焉不详,忽略而过。如果仅仅着意于性分与外形之辩,则蟪蛄与大椿、斥鴳与大鹏之喻足以尽意。而稍加比较即可发现,此处文意之深之广,远大于性分与外形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