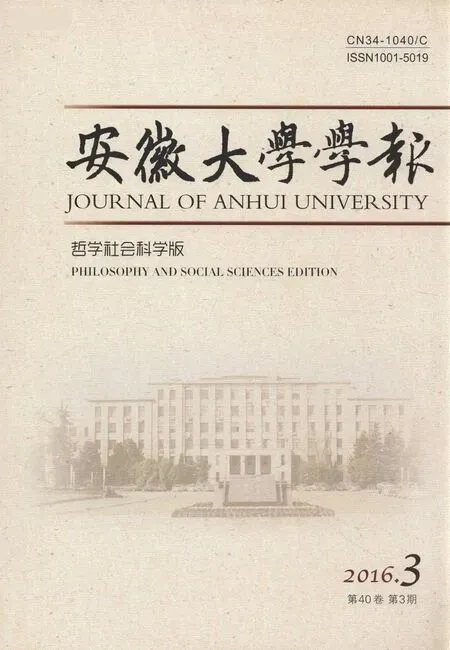再论王艮“保身”说的得与失
罗高强
再论王艮“保身”说的得与失
罗高强
摘要:王艮因现实政治的刺激、非法贩盐的恐惧和孝亲的伦理精神,提出“明哲保身”说。此说的积极意义在于纠正当时士人因一些不正当的观念和理由而做出枉顾性命的偏激行为,提醒士人以保重身体性命为首要任务。王艮的论证策略是提升个人身体的重要性,将身与道合一化,再以“一体之仁”开拓出保身爱人的伦理行为。可是,论证中出现了一些在逻辑上较为勉强的失误,这些失误让我们看到王艮“执本而用末”的“保身”原则在肯定意义上维护了道德的完满性,但在否定意义上又丧失了道德的实用性。简言之,王艮的“保身”说在历史背景下有其救正道德时弊的审美感,却容易成为不道德的庇护所。
关键词:王艮;“保身”说;一体之仁
嘉靖五年(1526年)冬,王艮的同门王臣(世称瑶湖先生)奉调北上。临别之际,王艮作《安定书院讲学别言》与《明哲保身论》两书赠别。《明哲保身论》虽为友朋之间的赠言,亦是有感于士大夫宦海为官,或直谏至死,或罹难遭逐的现实处境,企盼同仁好友能以保全性命(即“保身”)为重*据王艮的《年谱》记载:“时同志在宦途,或以谏死,或谴逐远方,先生以为身且不保,何能为天地万物主,因瑶湖北上,作此赠之。”(参见王艮《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页。)。在此,王艮虽未明确指出具体的事件,但查验当时的朝野环境,不难推想这与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相关,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刘谨用事”。然而除了政治因素的直接刺激,还有更为内在的机缘导致王艮的思想对个体生命(身体)的重视,那便是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和伦理实践。王艮出身“灶户”*在宋代,“灶户”又称“亭户”(参见《宋史·志第134·食货下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426页)。其后,元、明两代皆沿用。灶户的身份是世袭的,受到官府的严密监督,不可能随意的转业而脱离“灶籍”。但户不脱籍旨在确保政府差役和军队补给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所以实际上,只要国家能征发到足够的差役和兵员,政府并不在意供给差役和兵员的家庭真正从事什么工作,正如王艮,身为灶籍,却也可以读书讲学。(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21页、200页;或见薛宗正《明代灶户在盐业生产中的地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早年因生活困苦,故而被迫从事贩卖私盐。可是在明朝的成文法中,私盐贩卖之罪乃为“至死”的极刑,所以王艮早年时常面临极高的生存风险,这使他明白保护生命的重要性。王艮违法行商,既是由于家庭贫困,更是出于他见父亲辛劳而于心不忍的孝亲观念。因此,王艮的“保身”思想还潜存着重要的儒家伦理基因——孝亲。据《年谱》记载,王艮于1507年开始研究《孝经》,并且撰写了《孝箴》和《孝弟箴》。《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胡平生:《孝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这其中蕴含着浓厚的保身思想。王艮继受了这一思想,同样强调孝敬父母则必须爱护和安顿自身的身体,才能做到真实的孝敬,否则就会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而变得不孝*王艮:《答问补遗》,《王心斋全集》,第37页。。综上所述,王艮提出“保身”说有三个缘由:一、政治环境的直接刺激;二、早年贩卖私盐的违法体验;三、对孝亲的伦理期待和实践。
一
“明哲保身”语出《诗经·大雅·烝民》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后为《中庸》所引,固被儒者所熟知。孔颖达将“明哲保身”解释为既能够明晓善恶,又能够辨知是非,所以才可能避免祸害,保全自身*阮元注,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台中:蓝灯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年份不详,第675页。。同样,朱熹也认为“明哲保身”并非根本性的道理,只不过是平常的行事原则,用于日常生活,可以保护人体的生理性存在和依存性的社会关系,但绝不能成为“趋利避害”的保命原则*朱熹:《朱子全书》第1册、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9页;第2820~2821页。。依朱熹所言,身体及其依存性关系的持存不能作为高阶的伦理目标浸入生活实践,而只成为循理(即道德性原则)实践的效用现象。这种观点与王艮的“道身一体”和“以身为本”的理论趣向截然不同。在王艮看来,“道与身原为一件”,“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则“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贯”。“修身立本”的思想便成为理解王艮“明哲保身”的理论前设。
《明哲保身论》曰: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王艮:《王心斋全集》,第29页。
在王艮看来,“明哲”不是伦理经验中的“明辨是非,知晓善恶”,而是“不虑而知”的良知,具有先天的必然性。所以对于等同良知的“明哲”而言,保护和尊重身体就是一项无须从经验中学习的“良能”。这种观念近似于生物的自然反应,即任何一具身体(包括其他生物)在自然的生理反应面前都必须以先在的方式获得存在。反言之,生物之身不可能以非存在方式出现在生物自身面前,如被称为鸟兽的东西则不可能以鸟兽尸体的方式出现在鸟兽自身的面前,人类也是一样。因此,拥有身体并使其保存便是生物先天必然的本性。同理,人也需要率先以生物之身进入存在的领域,这种方式对于王艮而言具有先天必然性,故而称为“良知良能”。或许,倡导“舍生取义”的人会对此嗤之以鼻,然无可否认“取义”之前的人必须是生存着的,否则无法行使“舍生”的理性行为。换言之,当人之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与道义性的精神存在发生冲突时,人的道德理性(良知)会让其做出不保存身体(生理之身)而要彰显更高价值的“道义”选择,而这种智慧的选择与实现之所以发生必然是由于生理之身(形骸之身)在先持存着。
为了证明“保身”如何可能实现,王艮选择了“一体之仁”的感通性作为理论方法。王艮认为对己身之爱(敬)基于“一体之仁”必然也会推及他人,即施爱(敬)于他人,同理,受爱(敬)之人也必须由“一体之仁”回馈于所施之人,如此就可以使施爱(敬)者在这种“爱(敬)的回环”中得于保存。换言之,由于“一体之仁”的互动式感通,施爱(敬)者与受爱(敬)者都必然会在“保身”的行为中回避掉负面消极的情感——厌恶和轻慢等,因此“保身”的伦理实践不会遭受自私情感的消解。同时,这种方法也被王艮进一步拓展到己身与家、国、天下的关系中。
接上述引文,王艮继续说:
以之齐家,则能爱一家矣。能爱一家,则一家者必爱我矣。一家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国,则能爱一国矣。能爱一国,则一国者必爱我。一国者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以之平天下,则能爱天下矣。能爱天下,则天下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莫不尊亲,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谓至诚不息也,一贯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为气禀物欲之偏。气禀物欲之偏,所以与圣人异也。与圣人异,然后有学也。学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王艮:《王心斋全集》,第29页。
这段论证的逻辑与上文大体相同。稍需注意的是,在儒家看来,家、国和天下并不是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而是出于血缘、地域或民族等因素自然组合成的,故而无须讨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儒家的讨论中,对于家、国与天下的理解更多地会回归到具体的个体之中。换言之,儒家强调对家、国的爱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回归家、国概念涵盖下的具体个人。因此,当人们施爱的对象足够多,以致可以通过血缘、地域等原则组成一个“家”“国”“天下”的范畴时,人们就达到了“爱家”“爱国”和“爱天下”。上文提到人们爱护自身的情感可以由“一体之仁”推己及人,同样所及之人也可能由“一体之仁”反推之。可是,当人们所爱之对象是“家、国、天下”时,“家、国、天下”何来“一体之仁”的感应反推?所以儒家只有将家、国与天下的概念进行拟人化的处理,如此,就会出现“一家者必爱我”“一国者必爱我”。质言之,家、国、天下不会以主体的方式爱人,而论其爱人,那必然是也仅能是以家人、国人或天下人的方式去爱。这就不难理解,家、国和天下不是以组织结构的方式,而是以人格方式出现时,才能完成对“家、国爱我”现象的合理性辩护。
就其本然状态而言,“一体之仁”必须是“至诚不息”的“一贯之道”,也就是说此仁(人之本性)是“最高的、不息的真诚”和“贯穿一切的一”*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58页。。可是在王艮看来,这种人性会由于“心理物理构造决定的对外部事物的愿望”而产生偏斜的倾向。事实上,普通人常常因为偏离推己及人的感应之仁就与道德完善的理想人格(圣人)擦肩而过。正因为这种偏离现象的存在,人们则应该通过道德修习来修正这种偏离,使其接近理想人格。而在王艮看来,正确的道德修习便是聪明而智慧地保存和尊重自己的身体。
倘若一味地强调保存自身性命,那么会不会很容易走向自私自利呢?王艮的回应是肯定的,所以他接着说:
如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此自私之辈,不知本末一贯者也。若夫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故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必至于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己。此恕也,所谓致曲,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为大。”孟子曰:“守身为大。”曾子曰:“启手启足”,皆此意也。*王艮:《王心斋全集》,第29~30页。
在这里,王艮认为如果只知道一味地关心自身的保存,就容易走向“利己害人”,同时,他人也会因为被无礼地对待或处在缺乏足够尊重的关系中表现出报复的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利己者也无法保护自身利益。或许应该这样理解会更加恰当,即当我们赞同以自私的方式作为行为的普遍准则时,利己的现象就不可能发生,因为一种自私行为所欲求的内容与其他的自私欲求会出现无法消除的敌对关系。以王艮的话来说,利己必定与害人联系在一起,利己的所得便是他人的所失,这近似一种“零和博弈”,所以人与己在利益上形成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同样,当其他人也以利己原则行动时,其所造成的损失就是“吾身”的切己利益,包括基本的生存和生命。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不应该纯然利己,而应该全心全意地敬爱他人呢?但对王艮而言,仅仅知道爱护他人也不是符合最高标准的道德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容易极端化为“烹身割股”和“舍生杀身”等自残行为,这被王艮视为“不知本末一贯”而“逐末忘本”的行为。这就使得王艮的“保身”伦理实践跃入到利己与利他的中间状态,而达到这种状态的方法就是“以己度人”的君子之学。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还须收摄到“保身”(“敬身”和“守身”)的根本原则中,即吾身的保存和爱护,只不过,这已经是一种否定了利己与利他的辩证原则。
虽然《明哲保身论》开篇就强调“明哲保身”就是良知良能,可是对于王艮而言,一个身体的消失就意味着与之相配的“道”和“良知”的隐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身体对于王艮而言还处在更为源初的地位,如其所言“身与道原是一件”,“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王艮:《答问补遗》,《王心斋全集》,第37页。,“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王艮:《年谱》,《王心斋全集》,第75页。。个体与天道在价值上是一体共在的,彼此不可分离,故而“道尊身尊才是至善”。换言之,“道”不可能高于“身”而存在,只有在做到“身”的价值获得充分维护和彰显——如爱身、敬身、尊身、保身、安身的情况下,才能称得上“道”的完善。这点充分体现在他对“明明德”“亲民”与“止于善”的关系的阐释中。甚至在此基础上,王艮否定了其师王守仁的解释*罗洪先在《冬游记》中记载,1540年1月29日和30日,他两次拜访王艮,是年为王艮离世前一年(见罗洪先《罗洪先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2页)。这次访谈的感受在《冬游记》中说得较为曲折委婉,而在回京后罗洪先就向王畿说出了他更真实的感受,他认为王艮的学问不同于王守仁。这致使王畿写信提醒王艮注意他对王守仁的偏离。王艮收到信后,立刻做出了回应,承认自己与王守仁有所不同,并且强调他自己是接续孔子之旨,阐发孔子之学。这封回信可见于《王心斋全集》中的《答王龙溪》。。
“明明德”以立体,“亲民”以达用,体用一致,阳明先师辨之悉矣。此尧舜之道也。更有甚不明?但谓“至善”为心之本体,却与“明德”无别,恐非本旨。“明德”即言心之本体矣,三揭“在”字,自唤省得分明。孔子精蕴立极,独发“安身”之义,正在此。尧舜“执中”之传,以至孔子,无非“明明德”、“亲民”之学,独未知“安身”一义,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透悟此理,却于“明明德”、“亲民”中立起一个“极”来,故又说个“在止于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王艮:《答问补遗》,《王心斋全集》,第33页。
由此可知,王艮认为王守仁提倡的良知本心仅仅守住了尧舜“执中”的精义,并没有达及终极的完善。对王艮而言,王守仁的“最高的善”(至善)只等同于“光明的德性”(明德),而未能将“‘最高的善’理解为隐含着社会安置的‘自己个体的安置’”*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第473页。。虽然王艮已经看到王守仁的 “至善是心之本体”,却未能深入领会王守仁所谓“最高的善”“未尝离却事物”的说法*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页。。换言之,王守仁并不是简单地将“最高的善”理解成与其“作用”——亲民相对应的“实体”之“光明的德性”,而是诠释为“光明的德性”与“对人民爱护”的极致原则,即所谓“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王守仁:《亲民堂记》,《王阳明全集》,第280页。。正如王守仁在《亲民堂记》中就曾批评过佛老二氏只知“自明其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在于亲民”,还指责了春秋五位诸侯霸主(“五伯”)以智谋权术亲民,而不懂得“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接着阐发“明明德”与“亲民”必须以“至善”为最高的原则,如其所言:
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度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制矣;轻重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则矣。*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第280~281页。
由是可知,王守仁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与王艮所说“于明明德亲民中,立起一个极来”几乎一致。因此,王艮并不恰当的批评所要实现的理论企图就是要突显“身体”的重要性,将隐默在良知心体中的“身体”提升到更为本源和完善的地位。
综上所述,王艮首先从“立本”——身体本源性的角度提出“保身”的必然性。其次,从儒家“一体之仁”的感通性推论出“爱身”必须走向“爱人”,同时“被爱的他者”也必须以同样的原则回应“爱身者”,所以“爱身者”与“被爱的他者”在“一体之仁”的相互感通中推及对方,从而实现“爱身”(“保身”)的伦理要求,而且“不恶”“敬”和“不慢”等人际关系中的情感表现也同样在这种“一体之仁”的“爱身”之“爱”中得到“适中”的表达与回应,进一步坚实了“保身”的伦理要求。再者,王艮指出如果“保身而不知爱人”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时,那么这种“保身”的伦理要求将无法实现。同时,王艮也不赞同只“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因为这是“忘本逐末”,即忘却了“敬身”“守身”和“保身”乃是君子之学的根本要求。
二
表面上,王艮的论证看似自洽,却在一些关键环节潜藏着逻辑谬误。这些谬误将使得“保身”说建立在一些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其中两个非常奇特也最为可疑的逻辑环节是:一、“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另外两种情感——“敬和不慢”亦复如此;二、“如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面对这两个环节,人们难免会生出这样三个疑问。第一,一个只关注自身利益和价值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关爱他人呢?第二,即使一个人能在爱护自身的条件下做到关爱他人,那么他人又为什么必然会以关爱的情感和方式回应这个人呢?对此,耿宁的研究也有同感,他说:“王艮对‘良知良能’的逻辑建构中的最为奇特和最为可疑的环节肯定是这样一个思想:如果我爱和敬重其他人,他们必定会爱我和敬重我,如果我不恨他们和怠慢他们,他们也就必然会如此对待我。”*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第464页。第三,不爱护他人的人为什么就必然会伤害他人呢?
关于第一个疑问,儒家(包括王艮在内)惯用的回应方式就是“一体之仁”的推己及人,即如孔子所言“仁者,爱人”。换言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是关心他人利益的,这是德性的定言命令。对“仁者”而言,“爱人”并不是可选择的劝告,而是无条件的命令。如果说仁者可以选择不爱人,那么这种说法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有逻辑矛盾的,这就好比用“母亲”来称谓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孩子的人。质言之,仁慈的人去敬爱他人,是一种本己性的道德要求。由此可以推论一个道德的人必须做出敬爱他人的行为。然则“爱身者”是否必然为一个道德的人呢?王艮的辩护理由是爱(保)身是良知良能,是先天必然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原则,因此,“爱身者”就其充分展现出这种先天道德意识而言,是一个道德的人,所以他们依此原则推及他人,就会表现为爱护他人。这种辩护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爱护自身个体性的原则是否可以作为普遍的道德原则。无疑,王艮“修身立本”的“身本论”坚持这样一种原则——“爱身者”爱其身必然是一条客观普遍的道德原则,所以“爱身者”必然就是道德的人,同时也定然会以“一体之仁”的道德情感将“爱身”之“爱”推至其他人,即“爱身者,必爱人”。
可是,“爱身者,必爱人”与王艮所言的“爱身者,则不敢不爱人”却有很大的差别。“必然爱”蕴含着自由的自侓,以“爱人”本身为目的,而“不敢不爱”却似不然。“不敢不”透露出行为者在某种目的胁迫下的无奈选择,很难窥见自由之义,甚至也称不上他侓道德。在《明哲保身论》中,“不敢不爱人”是以“爱身者”能保护其身为目的,即所谓“不知爱人”则“吾身不能保”。由此可知,王艮在论证“保身”的合理性时选择了两条道路,即“明哲保身,良知良能”的先天德性论和“保身而不知爱人,则不能保”的功利后果论。可是,这两种论证策略会产生冲突。以先天德性论来看,“保身”的合理性等同于“目之能视”或“耳之能听”的自然合理性,便不需要以“一体之仁”去论证“保身”的先天道德性。而从功利后果论来说,“保身”就不具有先天的道德性,而只是伦理策略中可选择的一项目标。因此,作为“良知良能”而言,“保身”是先天必然的,而作为行动目标而言,“保身”就不存在必然性。倘若如此,那么王艮所谓“爱身者,则不敢不爱人”无疑在论证策略上出现了问题,导致不能恰当地说明“爱身者爱人”的原则。总言之,“爱身者”不是“不敢不爱人”,而是“必然爱人”,才符合“明哲保身,良知良能”的义理本旨。
第二问题暴露了王艮的论证更加随意和混乱。面对“能爱人,则人必爱我”这句话,人们太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即使我们能在爱护自身的条件下做到关爱他人,那么他人为什么必然会以关爱的情感和方式回应我们呢?按照耿宁的理解,要想他人以关爱的情感和方式回应我们的爱,只可能是一种强迫性的活动*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第464页。。不过,耿宁并未分析这种强迫采取了怎样的形式?强迫既有外在式的,如以解雇来迫使员工拼命工作;又有内在式的,如以远大的理想来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运用王艮的原则,一个人以“礼物”的方式去关爱他人,那么他人必然以某种友爱的方式和情感回应这个人,此即所谓的“礼尚往来”。倘若“收礼者”(被关爱的人)未能回馈,那么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便是“失礼”。失礼之人极可能受到外部舆论的弹压,进而被迫规范行为,回到“礼节”之中,准备回赠礼物,这可以称为外在式的强迫。如果“收礼者”出于羞愧等情感而回赠礼物,便可视为内在式的强迫。
用“强迫”的方式来解决由“我爱人”到“人爱我”的必然推论,或许难于得到王艮的认同。王艮喜欢把自己的解决方案称为“感应之道”,他说:“爱人者人恒爱之,信人者人恒信之,此感应之道也。”什么是感应之道呢?王艮说:“于此(按感应之道)观之,人不爱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君子为己之学,自修之不暇,奚暇责人哉?自修而仁矣,自修而信矣,其有不爱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有未深,处之有未洽耳,又何责焉?故‘君子反求诸其身’,‘上不怨人,下不尤人’。”*王艮:《勉仁方》,《王心斋全集》,第30页。不难看出,王艮认为“我爱人”而“人不爱我”是由于“我”的修身不充分、不彻底。也就是说,如果“我爱人”是一种道德行为或是一件正确的事,而这种行为没有得到“人爱我”的道德回应,或得到“人不爱我”的错误回应,王艮就会认为这是因为“我”的道德不够完善,或“我”做得还不够正确。这样的逻辑不妨描述为正确的(善的)行为没有得到正确的(善的)回应是因为正确的(善的)行为不够正确的(善的)。由是可知,王艮的解决策略是以自我道德无限纯化来应对外部世界的非道德性,如其所言“爱人直到人亦爱,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第4页。。
这种策略会面临两大限制:其一,个体行为的有限性和关联性;其二,外部世界不可知性。为了更加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不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甲将房屋租赁于乙,乙承诺在到期日前会准时搬离,同时甲便向丙承诺丙在到期日可入住。可是,乙在到期日并没有搬离,而是以各种理由拖延,并且在心中盘算着一种对自身极有利的方式搬离。随后,乙又多次以一边承诺一边失信的方式拖延了很长时间。如果按照王艮的原则,甲应该再容忍这种情况,甚至要无休止地容忍。因为这样做对甲而言,是一种修身,以自我道德净化的方式来完成改善他人的态度和行为。然而倘若如此,甲首先面临的是对丙的再三失信。其次,甲极可能没有打动乙,让其及时搬离。甲便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即失信的不道德感和宽容的道德感同时存在。失信是因为自我道德净化行为的关联性和有限性,而宽容却未能有效地改变事态是由于外部世界的不可知性,比如说不可能知道乙在自利面前是否有道德感动的可能或者何时会感动。由此可见,这种通过无限纯化道德行为来改变他人的行为和态度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甚至就哲学而论,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错误,透露出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第三个问题是不爱护他人的人为什么就必然会伤害他人,即“保身而不知爱人”为什么可以推进到“利己害人”呢?结合上下文,王艮提出这个说法无非想说“利己者”害人,会招致报复性伤害,终致不能“保身”利己。观其文义,王艮似乎带着威胁的口气来劝诫人们在保身利己的同时,还得爱护他人,不能以伤害他人的方式来保全自身。这一说辞就其劝善目的而言无可指责,但是作为“保身者”必须去敬爱他人的理由却显得很不充分。以是否要扶起摔倒在地的老人为例,有人不想扶、不敢扶,其原因是这种道德的行为可能遭到被扶老人或家属的诬告或勒索,因此他们需要爱护自己,避免自己和家人招来麻烦。我们首先搁置这种行为的道德性讨论,而来关注这种自保而不爱人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害人”的程度。一种肯定性的辩护是当事人袖手旁观极可能造成摔倒的老人错失救治的最佳时机或者加大了发生其他意外的几率。此类辩护的前提是老人摔倒与当事人的切己性关系,即认定当事人是唯一可能扶起老人的行为主体,进而得出否定性行为是带来可能性风险的唯一或首要的原因。无疑,这类辩护已经发生两度抽离:首先将当事人个体从当事群体中抽离;其次又将当事人从个体有限性中抽离。第一度抽离会造成当事人与事件关联的开放多样性变成唯一的可能性;进而第二度抽离又造成了当事人对事件的可能性认知变成溯源性归罪。这里不是为当事人的否定性行为进行合理性辩护,而要提出事件的复杂性,从而遏制草率的归罪判断。因此,从“自保”原则出发,当事人极可能走向否定性行为——不想扶、不敢扶,却又无法得出事件可能发生的危险由这类否定性行为来承担的结论。简言之,自保(保身)可能利己,却不一定会害人,所以就无从谈起遭到受害者的报复。在现实情境下,倘若因为各种理由(如怕麻烦等)使老人未能得到帮扶,并且发生了意外或者伤害,那么受害者或其家属都是没有理由采取报复性行为的。当然,有人又提出这类受害者或家属可能会因为自身的遭遇而丧失行善的动机,从而加剧社会道德沦丧的风险,最终让利己者(保身者)自食道德环境遭受污染的恶果。这种“蝴蝶效应”式的讨论实则忽视了道德环境和道德行为的复杂性。换言之,个体的道德动机并非单一性驱动,另外,社会中的道德现象也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因此,绝不可悲观地认为,受害者从此永无道德,同时,社会的道德系统也因此遭受污染,渐至道德绝迹。其实,更反讽的是,被求助者因为各种理由(不了解实情或恶意索赔)反而要求施助者承担更多“责任”,让施助者感受屈辱和损失,从而减损他的行善动机,使得社会慈善之风萎靡。因此,王艮所谓“保身而不知爱人”进至“害人”,最终反受“利己”之害而不能“保身”的论证只能是一种类似于“我不助人,人不助我”的世俗劝诫,并不具有更多道德理性的意义,自然就无法为“明哲保身”者需要爱护或者道德地对待他人作合理辩护。
三
现实政治的刺激、贩卖私盐的恐惧和孝亲的伦理精神让王艮有充足的理由选择保重肉身性命(保身),进而形成独特的“身本论”思想。从上文对王艮“保身”说的阐述中,不难发现他以“一体之仁”来论证“保身”亦能敬爱他人,而被爱(敬)之人也能以同样的敬爱之情来回应,进而达到王艮所说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似乎形成了一个论证的连环:从“保身”到“爱人”,再到“爱的回应”,最终获得“爱”的保护。实际上,这个连环并不牢固,面临着几处断裂的风险,即如:保身者没有理由必然爱人;被爱者也没有充分理由回应爱人者;自利者也不一定会受到报复性伤害。而且这些风险有机会变异成为自私辩护的理由。换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保身者都有可能不去敬爱他人,而沦为自私自利。虽然王艮强调“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吾身不能保”,但是这种“虚构的”必然性对现实而言从来就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甚至在理性上也无法充当辩护的理由。保身者要爱护他人或者被爱者的感恩回应,既不是现实功利上的最佳选择,也不是纯粹的理性事实。既然如此,王艮的“保身”说无论是在道德原则上,还是在社会伦理上,都不能称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客观地说,“保身”说只是王艮“身本论”在道德伦理上的理论延展,并且恰好为他所理解的某些现实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如他所说:“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为下矣。危其身于天地万物者,谓之失本;洁其身于天地万物者,为之遗末。”可是,这套坚持以身为先的方案对解决道德困境而言难以提出有益的指导。当面临“安身”与“安心”相冲突时,按王艮的保身原则应该以安身为先,即“安其身而不安其心”。而在这套方案中,却没有相应的评价。可是,这类评价又恰恰是道德抉择的关键地带。道德选择的冲突模型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变形,进入人们的意识中,使人们做出明确的选择。换言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若以保身为指导原则极有可能偏向自私自利的一方(即遗末),而不是更有可能处在王艮所谓“执本而用末”的“中庸之道”上。“处中”状态的“保身”原则在积极意义上维护了道德的完满性,如顾及生命和积极的个人利益,而在负面意义上又丧失了道德的实用性,太容易沦为“识时务”的诡辩之辞。易言之,王艮的“保身”说在历史背景下有其救正道德时弊——不惜身命,抵抗强权皇命的审美感,却极易成为不道德行为的冠冕堂皇的庇护所。
LUO Gaoqiang, Postdoctoral candidate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责任编校:余沉
A Reflection on the Loss and Gain of Wang Gen’s Theory of “Making Oneself Safe”
LUO Gaoqiang
Abstract:Provoked by the political reality, fear of smuggling illegal salt and the ethical spirit of filial piety, Wang Gen advanced the theory of “being worldly wise and making oneself safe”. The positive side of this theory is that it redressed extreme behaviors of scholars due to wrongly-held thoughts and logics. Scholars are thereby reminded of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themselves safe. Wang Gen’s argument promoted the importance of self in harmony with Dao. By upholding “oneness of benevolence”, he advocates caring for others by means of making oneself safe first. However, there were logical incoherences in Wang Gen’s argumentation. The principle of “making oneself safe” maintained moral perfection, while neglecting moral practicability. In short, Wang Gen’s theory of “making oneself safe” possesses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correcting wrong behaviors in a given socio-historical background, but prone to be a safe haven for immorality.
Key Words:Wang Gen; the theory of “making oneself safe”; oneness of benevolence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3.002
中图分类号:B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3-0011-08
作者简介:罗高强,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博士后(江苏 南京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