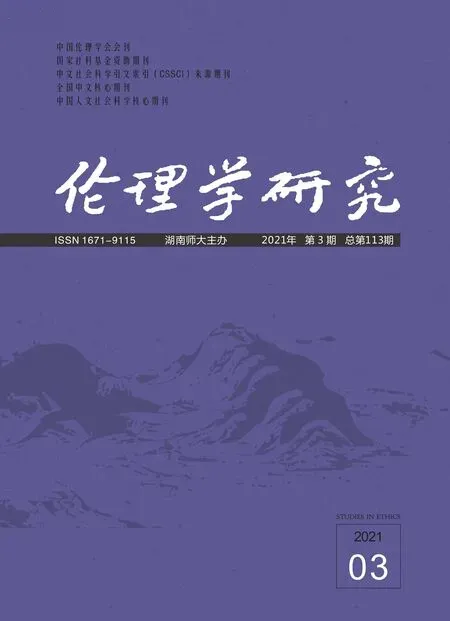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杨 明,马 洁
自孔孟肇始,政治治理便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治理”具有统治、政治、管理等思想内涵,并在思想中呈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王艮作为泰州学派的开山鼻祖,他正视明中叶的社会危机,并且不囿于其师王阳明的治理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身”为本、心怀百姓的路向,将政治治理付诸实践,凸显了“平民儒者”的天下使命。正如梁启超所言:“阳明活用孔孟之学,而泰州又活用阳明之学者也。必如泰州,然后阳明学乃真有关系于社会于国家也。”[1](P519)王艮在“治理”论域中展开对“身”与“生”、“身”与“安”、“身”与“心”等关系的思考,从治天、治世、治心等方面系统地构建了以身为本体的治理体系,展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独特理解。
一、“身”生:治天思想的特质
宇宙论视阈下万物的根源问题是宋明理学家讨论的主要议题,各大家对万事万物本体的探寻所形成的道体观在其理论体系中处于形上之端,是理论系统中其他方面如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及存养之论的理论依据。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理气说明万有的本质,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虽也以“理”作为宇宙万有的本质,但他以心释理。阳明认为“心即理”,以心为本体,开出了理学发展的新路向。“心学”立场无疑是阳明学研究的重心。然而,陈立胜教授却看到王阳明万物一体观中的“身—体”立场,指出阳明“身体”之“身”并不“单单是现代个体意义上的‘身躯’(‘躯壳’),这个‘身躯’是‘嵌在’万物一体这个‘大体’(‘整体’)之中的,是‘一体’的一个‘单位’‘环节’”[2](P8)。作为阳明的高足,平民出身的王艮将论点聚焦于人之“身”,他突破形上本体的抽象性与玄虚性思维,将“身”确立为万物的根本,以简约命题阐释其对万物根本之“身”的理解。其以“身”为本、“安身立本”的学说,开辟了阳明心学新的本体论视阈。
1.以“身”为治理之本
“身”作为“修齐治平”的逻辑起点,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政治理想的根本。孔子以“身”为本,此“身”为己,个人追求理想人格希冀成为“君子”,将理想秩序对象化为现实世界;孟子则推行“仁政”,并提出了“存心养性”的修身学说,以“民”为本是其治理思想的特质。可以看出,孔孟将“身”视为家国天下治理的关键。在此,“身”更多指涉“修身”,即个体道德境界的提升。不同于儒家先哲对“身”的理解,王艮视“身”为治理之本。他将“身”提升至本体论视阈进行探讨,并进一步提出“身之本”的问题,聚焦于“身”及“身之本”展开治理思想的构思。
(1)以“身”为物之本
王艮对“身”的本体论阐释是在传统儒家格物的思维框架下展开。他将身与天下国家统一于一物,就此物展开孰本孰末的论证。王艮提出“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 本末’之谓”[3](P34)。首先,从“与”字来解读“身”与“天下国家”的关系,按照王艮的本意应解为“和”,将两者理解为“一物”整体中的部分,并非“我”与“他者”的并列关系。也就是说,身与天下国家是“一物”中的组成部分,表达出“万物一物”的思想。其次,万物既然为“一物”,按照《大学》所言“格物”的修养工夫论逻辑,应遵循以“本末”格此物的理路。故以此来解读由身与天下国家组成的“物”时,得出“吾身为天地万物之本”[3](P44)的结论。王艮明确“吾身”为万物之本。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此物,按其弟子王栋的理解,“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谓吾身与天下国家之人”[3](P147)。在此,可以看出王艮理论聚焦于人,围绕天下国家之人展开。
王艮的理论旨趣在于,在治理视阈中论证治理天下国家之本在“身”,他将命题概括为:“治天下有本,身之 谓 也。”[3](P28)还反问道:“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3](P34)具体来看,他说:“以之‘治国’,则能爱一国矣。能爱一国,则一国必爱我矣。一国者爱我,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以之‘平天下’,则能爱天下矣。能爱天下,则天下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莫不‘尊亲’,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3](P29)分析上述文本,王艮之所以认为“身”是天下治理的根本,是因为首先,“保身”与治天下之间是一种在互惠互利价值原则支配下的利益关系。他从国、天下与“身”的关系——在这里“身”指涉个人——也就是从天下与个人的关系入手,指出国家存亡与否决定着个人利益是否会得到保障。国家兴旺,个人利益就会得到满足;而个人为了争取生存利益与发展权利,国家也会欣欣向荣。其次,个人与天下国家利益关系中也蕴含着推己及人的人伦逻辑。他说:“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3](P29)每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了能够保身而爱人。他人也从爱人出发,而我也必然被爱,故吾身便可保,所以王艮说:“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3](P29)可见,王艮认为应避免利己害人的行为,因为害人后人必将报复我,利己害人就变成了害人害己。由上观之,在互惠互利原则支配下,在推己及人的人伦逻辑中,王艮的理论推进是由保自身出发,至保君父,进而保天下国家。
(2)以身“生”为吾身之本
从“一物”出发,王艮视“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在以“身”与“天下国家”组成的“物”为对象进行治理时,又将“身”视为治理的根本。“身”成为王艮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在王艮的治理思想中,“身”呈现出三种样态。其一,以“吾身”出现的“身”,即具体的人,可将其理解为己抑或个人,相对于天下国家而言。其二,王艮定格于“吾身”的“身”,他认为“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3](P13)。也就是说,王艮此时对“身”的定义已具象化为个人躯体,躯体的生命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那么,一己之身的根本问题便是使此躯体之“身”具有生命。换言之,生存就要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使人有饭吃、有衣穿。在个体生命层面上,王艮意识到“身”的生命存在与生生不息才是一切治理活动展开的根本,这为引出“生”为身之根本的思想做了理论准备。其三,在王艮看来,“身”不仅指拥有感性生命的个体,也指抽象意义上的“身”,作为个体的人应秉持一定的价值观而挺立人间,如王艮说:“问节义。先生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几乎?”[3](P14)在此,“身”表现出人的价值意蕴。由上可知,在王艮思想中,“‘身’已不仅指向了良知主宰下的涵具着道德理性的抽象的本质之我,同时,亦指向了真实的个体化的生命存在”[4]。
从王艮对“身”的定义来看,有着从抽象到具体、从肉体到精神的立体式认知。在其中,他意欲强调“身”的根本问题即“生”。也就是说,使“身”生才是天下治理的最根本问题。他说:“《大学》曰‘物有本末’,是吾身为天地万物之本也。能立天下之本,然后能知天地之化育。”[3](P44)王艮把握住天地化育的关键在于个体的生命延续,将视角定格于人的生活。人之本是“身”,而“身”的根本问题在于“生”,即躯体有生命。反之,如果不能使“身”生,那么作为天下治理之本的“身”即不存在,也就不涉及个人境界问题。在此,身“生”成为王艮“身”本论的核心思想,并可以推衍出“身”生是吾身之本的结论。
从“一物”出发,王艮将“身”视为本末之本,而在对作为本的“身”进行分析时,他强调“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性,突出“身”生之根本性,进而得出结论:“身”生是身之本。在治理视阈下,“身”生便成为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所在。由上观之,王艮治思理路已疏离形上的思辨与空疏的教化,而具有亲近现实个体以及社会生活的理论气质。
2.尊“身”为“道”
王艮阐释身“生”显现出平民儒者对人生存欲求与生存权利的渴望。既然王艮将身“生”欲望看成人的本性,那么,诚如《中庸》之“率性之谓道”,王艮便以“身”阐释“道”。他用贴近日常的“生活日用”阐释“道”,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使“身”表现出形上意蕴。这也体现出王艮对传统“道”体的独特理解。
(1)即事是道
在王艮看来“道”既不是抽象、深奥的概念,也不是空疏、脱离实际的玄学,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归纳,正所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3](P13)。具体来看:一方面,他认为遵循“道”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只是在做平常事,并不神秘,所谓“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P5);另一方面,他用“家常事”阐释抽象的哲学范畴。例如,他用“童仆之往来”情形解释“中”,如“或问‘中’,先生曰:‘此童仆之往来者,中也’”[3](P5)。道隐匿于日常生活中,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由上观之,王艮不仅以生活的态度阐释方法论层面“道”的内涵,而且进一步将本体论层面的“道”视为生活化的呈现。
回观宋明理学时期,诸大儒对“道”的诠释仍然延续抽象化传统。朱熹以“理”为道,他说:“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5](P184)阳明反对程朱理学将“理”外在化、客观化,提出“心即是理”,旨在强调维护人伦关系的道德秩序主体化、个体化。王艮继承了阳明理论注重主体生活实践的气质。不同的是,王艮将生活化融入对传统形上本体“道”的理解中,将鲜活的生命及其日常生活视为“道”之内容,从根本上改变了“道”的理论样态,使本体呈现出通俗化、生活化的新面向。
(2)身即是道,道即是身
在王艮道论中,“道”并非玄虚的形上概念,而是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王艮道体思想的特色在于,在生活视阈察觉道体的样态并加以论证。首先,他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都是一致的,圣人也不例外。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生命,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以衣食为主的物质需要。也就是说,王艮再次强调作为社会性的人,在“生”的问题上是平等的,“身”的生存仍然是最根本的人性表达,这是普遍法则。其次,“生”是人生存的最基本需求,这种需求是自然欲望。“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则知性矣。”[3](P6)在王艮看来,此性就是人作为生物的自然属性,针对自然欲望并不存在价值判断。最后,从自然本性视角看社会生活,归纳人类社会遵循的“人道”,王艮指出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才是真正实现“人道”。因此,王艮将“身”生视为自然之道,又从社会生活角度看“身”生的根本性,由此得出自然与人伦视阈下“道”与“身”统一的观点。这正如他所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3](P86)
这一理论创设的关键在于,王艮由身本出发,在社会生活的视阈中体察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在论证中,他将社会中每个抽象个体具体化为生动的“身”,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以经验为素材归纳出“身”是人伦社会中“道”的命题。王艮对“道”的论证体现出理论分析视阈由自然视角向生活视角的转变。
综上所述,王艮从分析“万物一物”之“一物”本末出发,将“身”视为万物之本,进而体察并论证“身”生为身本中的根本问题。他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分析“道”的内涵,使玄虚形上之“道”转而回归生活领域,提出“身即是道”的命题,进而将“身”的生与活视为“人道”。在此,王艮完成了形上层面本与末的理论创设。
二、安身:治世思想的重心
在王艮“万物一物”思想中,身与天下、国家被视为“一物”,按照“天下一个,万物一体”逻辑,王艮建构了来源于日用生活的形上本体“身”。在“体用”思维支配下,他围绕体“用”推进理论。王艮基于明中叶恶劣的政治环境与萧条的社会生活,以平民儒者的身份思虑社会治理,将治理之本落实于感性的“身”,从个人之“身”与社会之“身”两个层面展开阐发。王艮说:“‘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3](P33)于是,王艮的治世思想围绕“安身”展开。
1.个人之安身
王艮将个人安身视为社会治理的根本环节。他以古本《大学》为文本展开诠释,他说:“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3](P33)如果不注重、尊重个体的生命,治理天下国家只以仁义为原则,那么这并不是真正做到了对本的治理。在王艮看来,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将个体之“身”安放于社会生活中,在日常实践层面去体悟个人应如何安身。
首先,“明体达用”是个人安身的实践法则。王艮以“一”与“精”来诠释他对传统儒家“明体达用”思想的理解,他说:“不能一切精微,便是有碍,便不能一切精微。”[3](P43-44)所谓“一”指以“身”为道体,“精”则表示在日用琐碎中体现“用”。在实践“明体达用”时应避免狂简与琐碎的流弊。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安身”,王艮认为:第一,不害身。他以仕为例,“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与道也何用?”[3](P8)王艮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对“为禄而仕”有过论述,他认为为仕分为为贫而仕与为道而仕。为贫而仕,道在其中,但并不是真正的行道。第二,不危身。王艮所言“危其身于天地万物者,谓之‘失本’,洁其身于天地万物者,谓之‘遗末’”[3](P4),具体来说就是在危与洁中找到平衡谓“中”,即“于止,知其所止”[3](P3)。王艮认为舍生杀身是忘本逐末的表现,杀身成仁是贤人的表现,而圣人蹈仁却并未伤害自己的生命。同时,他也不主张“独善其身”,王艮认为儒家“无道则隐”的人生取向也不是安身之举。王艮推崇的大丈夫情怀表现在:“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进不失本,退不遗末,‘止至善’之道也。”[3](P13)出仕不要忘记民,不入世也不要忘记个人的社会责任。第三,不安于险。所谓“学者不知‘以意逆志’,则安于险而失其身者有之矣”[3](P9),再如“‘仕、止、久、速’,‘变通趋势’,‘虑’也;如是而‘身安’”[3](P35)。在王艮看来,安身而动抑或身处危险而不安于危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巧智。
由上可知,安身,也是保身。王艮表达的是以个体作为对象的“身”之安放。就个人治理而言,不仅要做到“身”在物质条件上的安,也要做到在社会中的安身立命。所以,安身就在于“‘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已”[3](P29-30)。
2.社会之安“身”
在社会治理中,王艮并不仅仅把“身”对象化为个人,他独具特色地将“身”群体化,认为个人组成的群体也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于是,社会治理之本就群体化为“百姓”抑或“愚夫愚妇”。从表面上看,将百姓视为天下国家治理的根本,是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沿袭。但王艮民本思想却有区别于传统的特质。这体现在:第一,百姓作为群体,是在作为“身”的个体群体化逻辑下推出的,而非先验的群体概念。其二,他以“格”来诠释天下与百姓之间的关系。王艮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矩 则 知方之不 正,由矩之 不 正也。”[3](P34)“格”字作“量度”[6](P247)解,即治理国家时,用百姓来匡正治理的得失。在此,王艮将百姓视为社会治理的标杆,社会治理应以百姓的需要为需要,社会治理的好坏取决于能否满足百姓的需要。相较于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被重新思考,正如杨国荣教授的理解,在王艮思想中,“吾身即自我,以吾身为矩而正天下国家,意味着将自我视为决定天下兴衰治乱的终极力量”[7](P254)。其三,反观“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3](P6)的命题。可以看出,王艮将百姓或者愚夫愚妇视为“行道”的主体。在此,治理的主体由小众转向大众,由圣人扩充到百姓。由上可知,大众百姓成为社会治理的根本与施行的主体,相较于阳明的治理思想而言,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守仁的良知学,本来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哲学。但真落到社会大众手里,自然和在士大夫阶层不同。单从这一点讲,我们却该认泰州一派为王学唯一的真传。”[8](P82)
就社会治理的方法而言,王艮推崇“学”,个人“学”道便不会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忘记安身。由个人推向家国天下,则“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3](P28)。在此,他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百姓何以要“学”。既然行道的主体是百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3](P10),那为何认为百姓是愚昧的,百姓为何需要教化?王艮将其概括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需要圣人以先知觉后知,正所谓“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一知一觉无余蕴矣”[3](P43)。
王艮由“万物一体”的本体论视阈通过“体用之说”转换至道德实践领域,本着“明体达用”的实践精神展开社会治理的思虑。王艮社会治理思想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社会中安放“身”。就个人而言,他提出保身,具体表现为不害身、不危身、不安于险;就社会而言,他将百姓视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以百姓的需要匡正社会治理。在王艮看来,个体相较于群体而言更为根本,因此,社会治理的落实又回归至个体之身。
三、修身:治心思想的落实
“工夫的展开以本体作为逻辑前提和出发点,并在展开的过程中受本体的监督和引导。”[9](P85)按此理路去思考王艮对身本、安身与修身间的关系,可理解为“ 修身即是立本,立本即是安身”[10](P95-102)。在工夫论中,王艮继承阳明“致良知”的修身论,不同的是,“他将王阳明的‘致良知’改为‘良知致’,因为他认为‘致良知’的‘致’字还有某种人为努力的痕迹,而他坚持认为良知本身是自自然然的,是现成自在的,不须任何人为的做工夫”[11](P474)。“良知致”体现了“身”本思想在王艮理论中的一以贯之,如何修身使良知自然显现成为王艮工夫论的主要问题,王艮的修身围绕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两个方面展开。
1.顺性乐心
王艮视“良知”为“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3](P217),其修养论的指归定格于回归天下之本的率性、快乐的本然状态。他提出应顺从本性而达到乐心的境界。首先,王艮将“性”诠释为天然自有的自然本性,并从自然本性入手诠释人性之本,他说:“天性之体本自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3](P19)在此,他先从生命的角度将人与飞鸟池鱼视为同类,而后诠释飞鸟池鱼本性活活泼泼,进而将本自活泼之性推衍至人性,得出人性与天性一体同然的结论。其次,他认为自在活泼的快乐就是心之本体。王艮将“心之本体”解读为“说”,即“‘不亦说乎’,‘说’是心之本体”[3](P8)。追溯阳明哲学,陈来将“心之本体”的内涵解读为“内心的本然的、先验的结构”[12](P69)。阳明也将“乐”视为“心之本体”的一个方面,认为“ 乐是心之本体”[13](P207)。两者都将“乐”视为心之本体,但两者是建立在对“心”本体的不同理解上。王艮对“心”的解释见于:“有学者问‘放心难于求’,先生呼之即起而应。先生曰:‘尔心见在,更何求心乎?’”[3](P17-18)王艮认为“心”在于感知“身”的本性。他对心的理解是建立在自然本性论基础上的,因而跳出了阳明哲学中关于“心之本体”的话语体系。
由上观之,在王艮看来,修身养性之说,就变成了顺从自然天性、以“乐心”为修养指归的学说。王艮作《乐学歌》指出,“人心本自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3](P54)。于时,良知之学就是“简易快乐,优游餍饫,日就月将,自改、自化而后已”[3](P31)。在此,“把‘心’或者‘良知’作为人的生理自然需求,是王艮对‘良知’说的重大修正”[14](P42)。他的修养工夫遵循自然天则,不假人力安排,推崇至简至易,与传统理学中庄敬持养的工夫论相比无疑有所不同。
2.反己自修
“反己自修,皆是立本工夫,离却反己,谓之失本,离却天下国家,谓之遗末,亦非所谓知本。”[3](P75)在此,从两个层面对“己”进行分析。从个人修身养性的层面上看,与孔孟相同,王艮认为“诚意”“忠恕”“强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但王艮要凸显的是在社会层面阐释反己自修的途径与方法,因此“反求诸己”也可诠释为“反求诸其身”。他认为上述修身工夫中,最核心的方法就是“忠恕”。在修养过程中,应将夫子的“忠恕”之道“一以贯之”,他说:“故君子之学,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则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恶,则知人之所恶。”[3](P29)王艮在修身中强调的“推己及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在逻辑是以“保身”为目的的爱人,这也正如杨国荣教授所分析,在王艮看来“个体存在是否得到维护,归根到底便由自我本身所决定”[7](P252)。王艮的修身说重点在于强调个体自觉,他的工夫论突破传统“独善其身”的理路,反己自修的重心由精神境界的提升转移至社会生活的处理,蕴含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这也是对阳明学修身功夫理论的推进。
总体上说,王艮修身工夫论中包含着身与心两个方面,分别指涉躯体与精神。在阳明看来,“心者身之主宰”,心是身体活动及一切行为的中枢和主宰。而王艮认为两者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安身与安心也是相对独立的关系。具体来看,王艮说:“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者,斯其为下矣。”[3](P17)也就是说,身与心是个人修养的两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多种可能性。而就“安身而安心”与“心安而身不安”两种情境对比,身安是根本的原则,这也正是王艮哲学体系中“身”本思想的体现。所以,王艮所谓的“乐”,并非“孔颜乐处”之乐,只有达到“身”与“心”合安的状态,方为活活泼泼的自由境界,才能实现“真乐”。
“己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谓通天下之。故圣人以此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3](P76)在王艮看来,治平愿景的实现落实于一己之身,在修养工夫论中遵循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的统一,才能达至“真乐”之境界。总之,注重治理主体的本性与肯定主体的作用,构成了王艮修身工夫论的主要内容。在此,王艮从“身”本体出发,在修养工夫上向“身”的本性回归,这种回归也体现出其思想理论的圆融。
结语
王艮围绕“身”展开政治治理,以安身与修身为指向,由肯定“身”而突出个人物质生活需求的重要性,又由确认“身”为天下国家之本而彰显个体对于天下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正像岛田虔次所言:“在心斋那里,是把人作为这种社会存在、行动存在的积极性而强调的。”[15](P50)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的逻辑看,治理中君与民的互动是以君对民的绝对统治为潜在话语,这是封建专制下的不平等性的体现。在政治治理中,传统儒家认为统治者应注重“仁政”,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在王艮的治理思想中,一方面,他将“身”视为天下国家治理的本体,注重“身”生;另一方面,他突破了“位”与“政”的单向思维,扩大了政治治理的主体,将由“身”生引申出的具有必然性与必要性的“百姓”放置于社会治理的本位。在此,他尤为强调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社会使命感,将社会治理落脚于个人反己修身的工夫。王艮的以上看法,也赋予阳明学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理念以多方面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