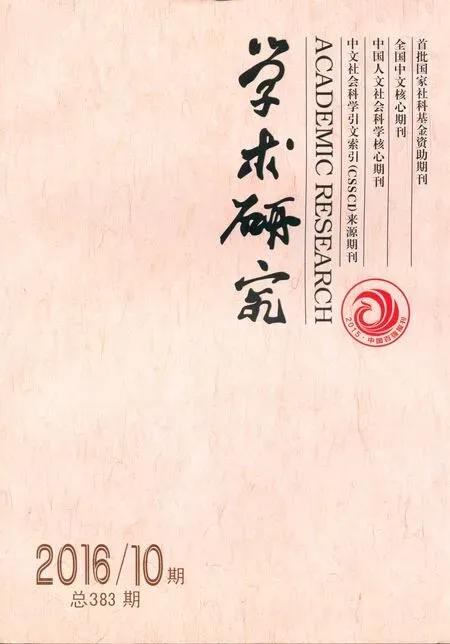百年来汉传因明研究方法之反思*
张栋豪 张晓翔
百年来汉传因明研究方法之反思*
张栋豪张晓翔
在一百多年的汉传因明发展过程中,学者们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西方现代逻辑理论解析的方法等对汉传因明进行探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与学术发展相比还显滞后。汉传因明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方法的革新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在保持和完善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一方面可以吸取中国逻辑史中的研究方法,比如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另一方面还要提出新的方法应用于因明研究,比如创造性诠释学和科学革命结构论的方法。
汉传因明研究方法反思
近代因明研究复苏以来,涌现出许多研究因明的专家和学者,一些院校开设了因明课程,招收了因明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有很多论著出版或发表,为因明的研究与弘扬做出了卓越贡献。回顾百年来的因明研究,虽然学界从不同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文献分析等不同方法对因明进行了诸多探索,但仅就研究方法而言,仍有进一步提升与发展的空间。
一、比较的研究方法
在因明研究中,比较的方法是最为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
(一)因明与墨辩、西方逻辑的整体比较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近代以来的因明研究,首位采用比较方法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一节为“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其中他提出:“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学者,印度五明之一也。其法为因、宗、喻三段,一如希腊之三句法。而希腊……至亚里士多德,而论理学蔚为一科矣……中国虽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之言,然不过播弄诡辩,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后亦无继者。”[1]在这节中,他还想把先秦学派与印度学派进行比较,只是梁启超认为要想比较就必须对印度学术思想的变迁进行论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部分暂付阙如。后来,梁启超在《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中对中国逻辑、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三种逻辑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
谢无量在《佛学大纲》中有一编专门论述佛教论理学。在该篇中,他对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学做了比较。“因明学之兴,固远在论理学之先,其推理之式,有相通者……”[2]“已上于同异二品立九句,如论理学所立之范畴。”[3]他认为二者之间是相通的,甚至认为二者是属种关系,将因明称之为“佛教论理学”。虞愚在《因明学》第五章“因明与演绎逻辑”中对因明和演绎逻辑的异同做了简要的区分。同时该书在附录中收入了《墨家论理学的新体系》,对墨辩和因明进行了比较研究。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对因明和西方逻辑做了比较研究,阐明了二者之异同。他在《佛教逻辑研究》中也主要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对古因明和新因明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4]
吴志雄认为三大逻辑学说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推理及证明的理论,主要推理形式都具有演绎的基本性质。三种学说对论式的要求也有某些共同之处,他同时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亚氏的证明只采用演绎推理的推论式,是科学证明;因明及墨辩用以证明的推论式除具有演绎的基本性质之外,还兼有归纳或类比的性质,是辩论的证明。亚氏形式化程度最高,墨辩最弱;对于无效证明的研究,因明家特别重视,亚氏次之,墨家更次之。[5]
谷振诣也在分析三大逻辑的共同性基础上,分析了各自所具有的不同逻辑特征:因明学以论证为重心,中国古代逻辑在类型上接近于印度的因明学,以“立辞”为重心,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以三段论(演绎)为重心的推论逻辑。因明是与宗教哲学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辩论的特点是与现实的伦理政治联系紧密;古希腊的辩论与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几何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东方的辩论与宗教哲学、伦理政治联系紧密,而很少受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影响。这是东方逻辑异于西方逻辑的一个根本原因。[6]陈克守对归纳在三大逻辑中的表现形式、所处的地位做了考察,并评价了其研究归纳的意义。[7]
吴志雄认为三大逻辑学说都把矛盾律作为最重要的思维规律,作为逻辑的起点。但三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对逻辑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同,形式化程度不同,对谬误重视及研究的程度不同,历史命运及对后世影响不同。[8]姚南强指出因明与墨辩都产生于论辩,都属于古典的类推演,都已具备逻辑基本规律,属于古代的内涵逻辑,在推理形式上都已具有类比、演绎和归纳三种最基本的形式,与墨辩以朴素唯物论的反映论为哲学前提不同,因明拘于对教义的论证。[9]
(二)因明论式的比较
因明论式的比较主要是陈那三支论式与西方逻辑三段论的比较,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二者等同的比较,主要是异中求同,二是有区别的比较,主要是同中求异。
1.异中求同。谢无量在《佛学大纲》中单独列出一章对因明学和论理学做了比较。他说:“因明论之三支法,与论理学之三段法,甚若相类。”[10]1906年,胡茂如翻译了日本大西祝的《论理学》,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形式论理,第二编为因明,第三编为归纳法,其中第二编就对三支作法与三段论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因明中的三支作法对“中词”的处置方式具有非常明显的特色,喻支是在形式上保证前提真实的有效措施;三支作法运用曲全公理(三段论公理——引者注)的范围仅限于三段论的第一格全称式。从这个角度讲,三支作法是亚氏三段论的一个子系统。[11]郑伟宏认为,三支作法只能划归为三段论第一格的第一式即AAA式,并且它是纯演绎的,在论式上不具有归纳的性质,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证明的推理,并且从遮诠不是否定命题、三支作法不设特称命题两个方面展开论证。[12]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他不再持此观点,而认为三支作法是一种最大限度的类比推理。
2.同中求异。1909年,章太炎在《原名》中对三大逻辑起源的论式做了具体比较。他指出:“辩说之道,先见其旨,次明其柢,取譬相成,物故可形,因明所谓宗、因、喻也。印度之辩,初宗,次因,次喻。大秦之辩,初喻体,次因,次宗。其为三支比量一矣。《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大秦与《墨子》者,其量皆先喻体后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其短于因明。”[13]在这里,与我们现在经常把西方逻辑看做一个典范或者标准不同,章太炎把因明作为比较的标准,他认为在《墨经》和三段论中都少了一个喻依,所以与因明相比它们都是有缺陷的,都是不完美的。太虚的《因明概论》是1922年武昌大学的讲稿,于1936年出版。该书对新旧因明和因明与逻辑做了比较研究。他在比较因明和逻辑时指出:“今世所知立论之学可分为二:一、为逻辑,二、为因明。逻辑为希腊亚里斯多德创立,不论为何事物,皆取之规定入吾人之思想轨则中者也;略同于因明论中自悟之比量。与因明目的在立言悟他,故注重发明立言所据之因者,不同。”[14]然后他从形式和性质两个方面说明了因明和逻辑的不同之处。虞愚在《印度逻辑推理与推论式的发展及其贡献》一文中分析了陈那如何从古因明的五支论式发展成为三支论式,并把三支论式和三段论做了比较,他认为陈那三支论式的特点是“从特殊到特殊”的类比推理。[15]崔清田认为三支作法属于命题逻辑,其推理过程是:
(x)(Hx→Fx)→(x)(Hx→Gx)
(x)(Hx→Fx)
所以,(x)(Hx→Gx)
而三段论属谓词逻辑,其推理过程是:
(x)( Fx→Gx)
Fa
所以,Ga(a为个体常项)因三相是与命题推演相适应的,三支作法与三段论不同。[16]巫寿康也认为三支论式和三段论是互不包含的、相互独立的两种推理形式,在推理、命题、词项、处理对象、判断标准以及处理主词不存在命题方面都有差异。[17]沈剑英认为古正理及古因明的五支论式属于比较原始的类比法,亦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例证推理。他对因明三支作法和三段论做了比较,认为新因明三支论式的逻辑性质是演绎与归纳的结合。[18]郑伟宏在《佛家逻辑通论》中专门分析了陈那三支作法的推理性质,他认为三支作法并不是演绎推理,并没有改变类比推理的性质。这也是在与西方逻辑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19]另外,1981年出版的石村《因明述要》也对三支论式和三段论做了比较。还有一些有关二者比较的成果,但在理论观点等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不具有代表性。
(三)其他方面的比较
谢蒙在《佛教论理学》第三章“因明学与论理学之比较”中提出,西洋论理学“仅就形式分肯定、否定,而不问其内容意义之如何”,而因明“则有形式与内容之区别,分有体无体”,显然更为完善。谢无量在《佛学大纲》中对因明和论理学中命题的种类,因明有体、无体的论式和论理学三段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崔清田认为因明的“因”、“喻”与《墨辩》的“故”相当,分别在两大逻辑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并直接与客观事物的类属关系相连,但是在表现形式、种类划分、谬误分析乃至所处的地位等方面均不相同。[20]曾昭式认为“喻”与“理”、“类”的作用相同,“喻”的种类与“理、类”的种类是一致的。[21]孙中原还对“自语相违”、“说谎者悖论”和“言尽悖论”的异同做了探讨。[22]
总之,三大逻辑学说反映的都是人类的思维规律,具有共同性:都产生于论辩中,并逐渐总结了一些规则,遵循基本逻辑规律,在推理中已蕴含了演绎性质,并关注对谬误的考察。但由于三者产生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当时各自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又具有特殊性。其一,形式性表达的程度不同,西方逻辑程度较高,墨辩则弱。其二,对谬误的重视程度不同,因明最高,墨家最弱。其三,价值取向不同,西方逻辑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求“真”为中心,因明与宗教哲学相关,主要拘于对教义的论证,以求“胜”为目的,中国古代逻辑则与政治伦理紧密相连,以求“善”为中心。其四,历史命运不同,西方逻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东方逻辑则一度沉寂。其五,研究重心不同,西方逻辑以“推理”为重心,因明以“论证”为重心,中国古代逻辑以“立辞”为重心。
二、历史文献的方法
汉传因明的研究首先是对从古至今所有汉传因明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整理、校勘、考证、训诂,只有研究的资料是准确无误的,所用的本子是恰当的,我们研究的成果才可能正确,所以因明研究首先是历史文献的研究,其次才是对因明内容的研究。近代学者对于历史典籍的研究工作非常严谨,在其著作中都会首先提及在考证历史文献时所用的方法。比如,吕澂在《因明纲要》里提出了三个研究方法。一是辨别古今。“立破轨范,说必从新。剖析旧言,宜详古式。”[23]要想确立自己的学说,批驳他人的言论,就必须要研究最新的成果;而如果要研习经典,就要仔细阅读第一手资料。二是旁考外宗。“古因明说,多取诸外,正理宗言,尤为关合……今此经本,梵言英译合而刊行,取证内典,既见渊源,愈明义蕴。”[24]一个学说要想考证是否正确,就应该综合其他的证据来论证,比如汉传因明,就可以用梵本和英文版的因明著作来对照。三是广研诸论。“以是恒言不悉因明莫通诸论,今谓非研诸论难晓因明。善知方便,反复相成,取证兹编,应为可信。”[25]
虞愚在《印度逻辑》一书中专门列出一章讲述研究印度逻辑的方法。他指出,研究印度逻辑史,宜注重史料之搜集,史料之审定,及整理史料校勘训诂贯通诸方法。如果研究逻辑理论,宜注重其理论来源与其资料,施以分析与综合之研究。他在此指出了两种方法,即普通之方法和特殊之方法。普通方法适用于在学校或家中有志研究印度逻辑的人,主要包括:认定门类、搜集资料、鉴别资料、阅读方法、辨别古今和发展新资六种方法。特殊方法用以研究印度逻辑的特殊问题,使其学问日臻完善,主要包括:选择适当之问题、采用适当之方法、寻求充分之证据和构成精确之报告四种方法。[26]虞愚在《因明学》中提出了研究因明的三个方法。一是覃思本文。就是要深入思考研习文本,“因明本文,精论越世。一辞一文,确有依据。非心气粗浮者所能望其项背,故读者须静心定气求之,方可悟入。”[27]二是鉴别古今。这一点虞愚与吕澂提出的“辨别古今”一致,他甚至还引用了吕澂对因明发展五个阶段的界定。三是旁考经论。“学者欲考核因明学发展程序,于外当旁考有关于因明之书籍。于是援引事实,根据理由,以为参证之助。于内当精研经论,以比较其得失、审察其关系,内外并进,当有大成也。”[28]
在近代汉传因明的著作中,往往都会提及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方法,但是到了现代以后,汉传因明的著作却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汉传因明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整理和考证训诂已经相对完善,不太需要研究者对此再下太大工夫,另一方面则是学者们弱视了文献搜集、整理、校勘的重要性,重点关注了因明理论的分析与论证,这与蓬勃发展的逻辑理论是相辅相成的。但是,21世纪以来也有新的因明文献被发掘出来,比如敦煌的本子,还有因明相关的一些典籍,沈剑英等学者对此有专门的研究,但就相对众多的因明研究成果而言,比重相对较小。而文献的考证是因明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还需要引起因明研究者的广泛重视,运用史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研究;再者,对因明理论及其本质的研究,也离不开因明文献的解读,而这又是建立在拥有正确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缺失了史学的研究方法,忽略了作为一个研究者所应该保持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西方现代逻辑理论解析的方法
西方逻辑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演绎逻辑的天下,直到近代培根、穆勒提出了归纳法,发展到现在已不仅限于传统的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的内容,还包括了数理逻辑、集合论、语言逻辑、模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多值逻辑、弗协调逻辑等等,而且也不局限于逻辑学这单一的领域,还与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联系、交叉。可以说,西方逻辑在近代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因明还停滞在对传统经典义理的解释与阐发上。因明、中国名辩和西方逻辑同为逻辑,有共通的一面,用西方的逻辑观念或者形式来研究因明必然能开阔视野,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陈望道的《因明学概略》是1928年在复旦大学的讲稿,于1931年出版。该书吸取了日本学者村上专精、大西祝等人的研究成果,用现代逻辑工具来分析因明义理,书中附有8幅欧氏图和图标20余幅。1938年出版的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更为系统地用西方逻辑(主要是形式逻辑)来分析因明义理。巫寿康的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的研究》以数理逻辑为工具,研究《正理门论》的逻辑思想。沈剑英用现代逻辑的观点对《理门论》进行了今注今解。[29]郑伟宏的《佛家逻辑通论》运用西方逻辑对因三相的逻辑结构进行了分析,对三支作法的推理性质进行了研究,指出三支作法不是演绎论证,它并没有改变类比推理的性质。[30]霍韩晦的《佛家逻辑研究》首先讨论了因明是不是逻辑和因明的论式结构能否写出一纯形式的推演历程,然后对因明三支比量进行了逻辑解析。[31]张忠义和张晓翔的《三支三物与证成》则运用苏珊·哈克提出的“证成”思想,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对因明三支、名辩三物与证成进行了比较研究。[32]
用西方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因明,实际上即是用元语言来研究对象语言的方法。孙中原曾提出希尔伯特的理论研究分层论、塔尔斯基的元语言分层论与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的五境界说,可以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论的借鉴。[33]而因明研究也属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所以也可以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因明研究之中。在运用这种方法的同时,也还或多或少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把因明与西方逻辑进行对比,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一般都会用到几种方法对某些领域或问题进行探究,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实际上多种方法的运用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因明看得更为透彻和清晰,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因明。
四、因明方法之反思
从近代因明复苏开始,研究因明的方法到目前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从梁启超、章太炎、虞愚、陈望道、吕澂、沈剑英、郑伟宏、姚南强、张忠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所用的方法变化不大。更多的因明学者专注于因明义理的诠释与解读,片面孤立地运用因明的知识来解释因明。然而因明并非是脱离社会、纯粹形而上的精神财富,它是来自于现实、来自于生活的思想财富。因明在现实社会中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也需要与现实生活的实际有所联系,有所用处,只是阳春白雪,必然曲高和寡,注定会逐渐停滞不前甚至萎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明想要取得预期和理想的成果,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明研究一方面要注重典籍的整理、义理的阐发,另一方面研究方法的提升与完善也同样重要。
(一)考证训诂
因明自南北朝时期传入以来,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程中,因明自然也具有了史学的特征,因此考证训诂的方法也是研究因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顾颉刚认为:“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34]考证训诂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资料收集。汉传因明是以因明文献为研究对象,所掌握相关因明的资料和文献越多,论述其思想和观点的证据也就越多。其次是资料复核检验。我们在引用原始文献时,一定要确定其真伪;引用他人的资料时,要检查其与原著是否相符,解释是否得当。再次,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并不是对因明资料的简单罗列,而是要从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有所创新,而这必然要用到归纳与演绎的方法。近代以来的因明学者也提出了治因明所需要用到的方法,如吕澂提出的辨别古今、旁考外宗、广研诸论的方法;虞愚提出的覃思本文、鉴别古今、旁考经论的方法,研究印度逻辑史宜注重史料之搜集,史料之审定,以及整理史料校勘训诂贯通诸方法等。实际上,这些也属于考证训诂的范畴。我们不能因为前人做了一些工作,而对所要用到的文献资料的校勘正诂有所松懈,更何况我们现今处在一个数据极度丰富的时代,所拥有的因明资料也比前人要多得多,这其中必然有一些是没有经过考证训诂的,所以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
(二)比较与参照
三大逻辑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较大的变化。不仅有对三个逻辑理论学说整体的比较,而且还有对三者论式之间的比较,以及更加细微之处的比较。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逻辑的比较研究“首先是一种比较,是存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所区别的逻辑思想或理论之间的比较,也就是有差别才有所比较……所谓有所区别,是指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对立统一。同时,这种比较研究也不是无标准的、盲杂的比较,必须具有一整套严格的标准体系”。[35]因此,异类不比,把因明与西方逻辑、中国古代逻辑进行比较,是因为这三者都属于同一类,都是关于人类思维规律的学科。三者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异中求同主要是求三者之间本质上的共同性,同中求异主要是三者之间非本质属性上的“异”,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是在比较中不能把某一方作为评价标准,因为任何一方都是比较的对象,对象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
中西印逻辑之间既有共同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胡适指出,《墨辩》的逻辑学有不同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地方,墨家的名学在“法式(Formal)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的逻辑……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都说得很明白透彻。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这是第一长处。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却能把演绎归纳一样看重……这是第二长处”。[36]沈有鼎在《墨经的逻辑学》中认为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和逻辑形式是没有民族性也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语言却是有民族性的。[37]逻辑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是作为两种逻辑比较研究标准的逻辑学具有的性质。这种性质不仅为两种逻辑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客观基础和依据,同时也决定了两种逻辑比较研究的要求和内容。无论在论式,还是其他方面都可以比较,因为三者之间有共同点,人类的思维规律本质上是相通的、一致的。只是由于各国在社会文化、民族语言及风俗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其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各具特色而已。但正因为如此,比较中生搬硬套是不可取的。
从百年来汉传因明与西方逻辑比较看,研究多聚焦于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与三段论的比较,分析论证三支作法是不是演绎推理,有没有达到三段论的水平。过度地对汉传因明的局部内容与西方逻辑进行比较,这并不是比较研究的初衷和所要达到的要求和目的,我们应该从宏观和整体上对汉传因明和西方逻辑或者中国逻辑进行比较研究。杨百顺在《比较逻辑史》一书中对比较方法进行了详细而又系统的说明,他认为比较逻辑史不能只是横向静态比较,应该加之动态、纵向比较及与其他科学的“旁比”研究。[38]具体地说,“比较的方法包括以下方面:一、首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还要结合其他方法,如分析、综合、系统方法等。二、联系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联系派系、学者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三、以往的比较研究横向比较多,广度、深度都有待加强。”[39]所以,我们对汉传因明应该从纵向、横向、静态、动态等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进行比较。
我们现在往往习惯于把西方逻辑当做比较研究中的一个范本或者标准,无论是因明的比较还是中国名辩的比较,都通常是因明与西方逻辑或中国名辩与西方逻辑进行比较,或者三者之间的比较,而很少把因明与名辩单独进行比较。这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逻辑一词来源于西方,潜意识中想当然地认为西方逻辑最为正宗,因明或中国名辩都应该与它进行对比,而且喜欢从中找出西方逻辑的痕迹,过于求同于西方逻辑,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倾向,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以注意。
另外,我们不要总是对三大逻辑分支进行具体内容的比较,而应该全面地比较它们产生的背景、过程、内容等方面。可以说,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氛围导致了不同逻辑思想的产生。末木刚博的《东方合理思想》从印度的思想特征和中国的思想特征出发,指出印度的逻辑是通向省悟的逻辑,而中国佛教的逻辑思想包含在对现实的肯定、整体论的真理观、多样性的统一之中,中国古代思想的逻辑则是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统一。[40]
(三)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
崔清田提出了《墨辩》研究的一种方法——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41]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受此启发和影响,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逻辑思想,涌现出一大批中国逻辑研究的成果。汉传因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并不是无缘无故凭空出现的,必然要有它产生的原因、背景、发展过程,而我们要全面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汉传因明就必须知道和熟悉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也就是它因什么而生,因什么而长,它是为什么而服务的。汉传因明也是逻辑思想,因此我们要用逻辑的观念和逻辑的方法来梳理其中的逻辑思想;这个逻辑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关于证明的思想学说,并具有工具性、形式性、规范性的特点,[42]这是我们系统挖掘和分析汉传因明的基本依据。汉传因明是世界三大逻辑之一,我们在研究时必然要用逻辑的观念去解读。因此,逻辑解读的方法其实就是逻辑观念的问题,是对逻辑本身的理解问题。目前,国际逻辑学界对逻辑的研究和界定五花八门,许多学者使用各种工具、观念或手段对逻辑进行研究,我们应该秉持开放和包容的逻辑观念,深入挖掘经典文本中的因明思想,这样汉传因明才能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我们在研究汉传因明的时候不要总是局限于本学科方法论的研究,还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例如,我们从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历史发展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任何学科要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创新,都需要我们从其他学科和领域里汲取和借鉴相关的研究方法。
(四)创造性诠释学
旅美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创造性诠释学的五境界说。第一“实谓”,指原典实际上怎么说,原典校勘和考证。第二“意谓”,指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是“实谓”的意义,原典训诂和语义分析。第三“蕴谓”,指发掘原典蕴藏的深层义理。第四“当谓”,指原思想家应当说出的,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如何重新表达,为原思想家说出应当说出的话。第五“创谓”,指为解决原思想家未完成的课题,现在必须创新地说什么,从批判继承者转化为创造发展者,救活原有思想,消解其难题和矛盾,为原思想家完成创新思维的课题,促进世界思想传统交流,培养创新力量。[43]我们在研究汉传因明的时候也可以分为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个是考证训诂汉传因明原典实际上怎么说的;二是分析论说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三是深入梳理因明典籍蕴藏的义理;四是把因明著作中想要表达而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充分论述出来;五是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推动汉传因明的前进。
(五)科学革命结构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了科学革命结构论,他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是研究范式转化的过程。研究范式转换导致了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变革,标志着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汉传因明的研究只有跳出旧有的研究范式,创造新的研究范式,才能把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和高度,让汉传因明焕发生机和活力。
总之,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方法,我们在研究时也不可能脱离方法而孤立地讨论问题。总结一百多年来汉传因明研究成果中所采用的方法,分析其取得的成果和优缺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认清因明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希望能对因明研究者有所启迪。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35页。
[2][3][10]谢无量:《佛学大纲》,《谢无量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0、165、200页。[4][18]沈剑英:《佛教逻辑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4-256、564-569页。
[5]吴志雄:《古代三大逻辑学说证明理论的简单比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6]谷振诣:《东西方逻辑探源与比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7]陈克守:《墨辩、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比较》,《齐鲁学刊》1989年第6期。
[8]吴志雄:《因明、“墨辩”、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9]姚南强:《墨辩与因明的逻辑比较》,《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11]李延铸:《因明三支作法与亚氏三段论》,《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12]郑伟宏:《因明三支作法与逻辑三段论之比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13]章太炎:《原名》,《国学的精要》,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25-126页。
[14]太虚:《因明概论》,http://www.fjdh.cn/wumin/2009/04/11520038152.html。
[15]虞愚:《印度逻辑推理与推论式的发展及其贡献》,《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
[16]崔清田:《三支作法与三段论辨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17]巫寿康:《三支论式和三段论是互相独立的两种推理形式》,《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
[19][30]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8-104、70-86页。
[20]崔清田:《试析〈墨辩〉的“故”与因明的“因”、“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
[21]曾昭式:《论因明学之喻与墨辩之理类》,《南都学坛》1996年第1期。
[22]孙中原:《印度逻辑与中国、希腊逻辑的比较研究》,《南亚研究》1984年第4期。
[23][24][25]吕澂:《因明纲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13-14、13页。
[26]虞愚:《印度逻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6-20页。
[27][28]虞愚:《因明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7、118页。
[29]沈剑英:《佛家逻辑》下卷,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年。
[31]霍韩晦:《佛家逻辑研究》,台湾:佛光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32]张忠义、张晓翔:《三支三物与证成》,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
[33]孙中原:《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层次和方法》,《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4]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序。
[35]翟锦程:《比较逻辑研究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3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37]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0页。
[38][39]杨百顺:《比较逻辑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40][日]末木刚博:《东方合理思想》,孙中原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41]崔清田:《显学重光——近现代的先秦墨家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9-160页。
[42]翟锦程:《用逻辑的观念审视中国逻辑研究——兼论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43]王赞源:《创造性的诠释学家:傅伟勋教授访问录》,《哲学与文化》1997年第12期。
责任编辑:罗 苹
B81-09
A
1000-7326(2016)10-0036-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因明研究”(12&ZD1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汉传因明的方法论研究”(2012M5107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传因明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2YJC72040002)的阶段性成果。
张栋豪,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天津,300071);张晓翔,临沂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 临沂,276005),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北京,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