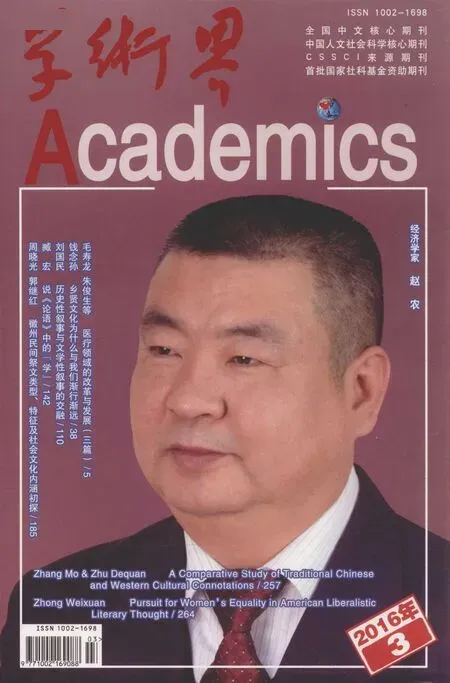儒教重建:走儒教发展的民间道路〔*〕
——由韩星教授《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引起的思考
○ 解光宇
(安徽大学 哲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儒教重建:走儒教发展的民间道路〔*〕
——由韩星教授《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引起的思考
○解光宇
(安徽大学哲学系, 安徽合肥230039)
韩星教授的新作《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一书认为,历史上儒家的“教”不仅仅是狭义的教育之教,更有教化、宗教的含义,是“教化、教育、宗教之综合”。儒教以道为教,最终落实的还是尊天重地前提下的人文主义精神。儒学发展的主流不可能走宗教化的道路,但并不否认在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融会过程中,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有民间儒教的发展道路。韩星的观点平实中道,为当今中国大陆的儒教建设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
儒教;重建;民间儒教
儒教问题是当今学界具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热点。目前儒教重建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但具体怎么重建,学界和社会仍然不能达致一致,出现了多元化的探索。韩星教授对此问题有长期的研究和关注,他的新著《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即是对近代以来孔教在大陆和海外发展的全面展示,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同时也对儒教的现代重建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观点平实中道,值得关注。
一、当今儒教重建的不同路线
当今儒教重建代表人物蒋庆、康晓光提出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之说。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说:“在今天,儒教崩溃,要重建儒教,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具体来说,就是‘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此‘儒化’是董仲舒‘复古更化’之现代形态,此处之‘复古’即是在当今中国恢复中国古圣王之教,‘更化’就是用古圣王之教即儒教转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两个要点:一、通过当代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即建立具有现代宪政功能的‘太学监国制’与‘议会三院制’,以儒教的宗教义理与文化传统规范约束中国国家权力的运作和行使,以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在超验价值与历史文化上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完整周全的合法性基础。二、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把儒教经典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养教育的主要内容。”
“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宗教性的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的基督教会或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会’,以‘儒教会’的组织化形式来从事儒教重建与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国儒教会’同中国的其它宗教教会和宗教协会一样,是在现代法治框架下按照法律建立的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宗教社团组织,‘中国儒教会’既是承担儒教重建任务的宗教组织形式,又是作为组织化宗教的民间儒教本身。‘中国儒教会’虽然是一民间的宗教社团法人,但与其它的宗教组织的关系并不是平面的平等关系,‘中国儒教会’因为儒教是中国历史中长期形成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由于儒教过去是中国的国教,将来也必须重新复位再次成为中国的国教,所以‘中国儒教会’在中国诸宗教中的地位相类于英国圣公会在英国诸宗教中的地位。‘中国儒教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与基础教育制度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奠仪式的特权,以及有其它种种特权。‘中国儒教会’既不像一般宗教团体完全脱离政治是一纯民间社团组织,又不像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完全与政治合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间又拥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特权的并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社团。”〔1〕
康晓光更有一整套建立“儒教国”的设想,他认为“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儒化的原则和策略是什么?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2〕
此外,陈明提出“儒教公民宗教说”,反对儒教国教说,主张政教分离和宗教平等,认为应尊重公民个人选择,使儒教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把儒教建设成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平等竞争的一员,并借助儒学作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天然优势向公共领域逐步拓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室赵法生近两年来在农村进行乡村儒学的实践,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也越来越认识到儒学是乡土信仰重建的一粒种子,最后可能要实现私塾学堂、家族祠堂与民间信仰教堂三堂合一的乡土信仰系统重构,促进传统乡土信仰的现代转化。〔3〕
二、儒教重建:走儒教发展的民间道路
韩星教授《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对近代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孔教活动及其思想理论,以及波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作了全面梳理,在思想史的基础上,对儒教相关理论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第一,道与教、儒学与儒教的关系
韩星教授不仅仅从宗教的角度考虑问题,他通过深入解读儒家经典《中庸》的“修道谓之教”,认为历代对“修道之谓教”虽然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大致都是说所谓“修道”指的是修学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是以人伦为主体的人道;“教”是说这是一种教化过程:对他人而言是教化、教育,对自己而言是自修、自证。《中庸》将人们的这种对圣人之道的修学称为“教”,可见此时的“教”是同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一致的。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但也有宗教的蕴涵和必要的宗教形式。儒家讲修道之教,不是佛道离世孤修的心灵生命修炼,而是儒者在自我修养的基础上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正己正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在“教统”上的体现。儒教以道为教,最终落实的还是尊天重地前提下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儒教不是讲鬼神迷信的宗教,而主要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以圣贤人格为楷模,以道德精神为依归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化,以及必要的宗教性礼仪形式。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往往是通过相互联系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指儒家在内在心性修养中有“内在超越”的宗教体验,如《孟子》《中庸》的“诚”,《大学》中的定、静、安、虑、得,都涉及儒家的宗教性体验与道德实践;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三祭之礼。三祭之礼是宗教性礼仪形式,所以也能使人们产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文言传》)“外在超越”的宗教性体验。
对于儒学与儒教的关系,韩星教授是在对中国文化基本结构宏观重构的基础上来理解的,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系统和结构,即以道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圆锥结构。道统作为价值系统与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等应用系统是体用本末的关系,道统与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分属不同层面,道统可以统摄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就其生成次序来说是一道开五门,由道开出政、学、教、文、法,下贯而又上通,并最终形成一个立体的动态的网络系统;就其现实构成说,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就是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以相辅相成、相维相济的方式发挥作用。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政统、学统、教统、文统、法统时而断,断了可以再续起来,惟独道统不能断。道统一断,缺乏一而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他各统就会偏离正道,走向异化。所以,属于学统、教统的儒学与儒教关系就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互相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儒学是儒教的学术基础,儒教是弘扬儒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他还提出儒学、儒教怎么与现代社会结合?最主要的是与现代经济结合,也就是儒学、儒教与儒商的结合或联合。儒学、儒教、儒商,是现代社会传承儒家思想、复兴传统文化三位一体的三个根本方面:儒学是学术核心,儒教是组织形式,儒商是经济基础。儒学为国民提供清醒的理性思想,儒教为国民提供神圣的精神信仰,儒商为国民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儒教复兴的民间道路
韩星教授认为,儒教复兴只是儒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宗教一脉,并不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方向,也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能走宗教的道路,他的基本思路是:以儒家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这里的“诸教”是指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传统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近代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历史上儒家对道教、佛教经过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已经完成了以“儒”为主的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学这一儒学的新形态。但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开始了儒家与天主教、基督教的冲突、交流、融合的历程,今天仍然在进行当中。尽管在中国大陆,儒学发展的主流不可能走宗教化的道路,但并不否认在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融会过程中,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有民间儒教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说,如果要建立儒教,也可能是民间儒教,即由儒家学者和民众共同建立非官方非政治化的儒教组织,当然也并非与政治无任何关系,而是以文化的方式实现政治的目标,即儒家寓治于教,以教化政、教以导政、政依教立的传统。儒教发展的民间道路起码应该有两种功能:一是社会教化的作用,以教育的方式面对普通民众;二是宗教的方式,以宗教的形式弘扬儒学和传统文化。实际上二者应该结合起来。他特别强调的是“民间”立场:一是作为宗教形式的儒教实体,必须是民间力量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有广泛民众基础;二是符合社会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是社会化的,属于公共领域的文化现象;三是非政治化的,以免由于政治的急功近利而失去其长远的文化价值。
关于目前可以展开的民间性儒教的活动,他以为最基本有三个方面:
其一,宗教层面:农村宗族、家庭的祭祀,民族圣贤英烈以及地方先贤的祭祀,书院先师祭拜等活动正在不断复兴。这些活动开始重新发挥传统上的认祖归宗、培育孝道、民德归厚等教化功能。而城镇的状况令人忧虑,完全是“失教”状态,给影视、网络、地下宗教、家庭教会乃至黄、赌、毒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所以要尽快建设城镇书院、文庙、先贤祠等信仰场所,满足越来越扩大的城市人口信仰需求。 其二,教育层面:针对现代教育危机,试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指导制定新的教育方案,从幼儿读经到经学讲解到儒学研究为主体内容的系列教育,先是作为现行教育的补充或并行,时机成熟了再替代现有教育体制。在补充阶段,可能主要是体制外的恢复;到替代阶段,则就是体制内的重建。 其三,教化层面:在各地农村和城镇社区、企业,建立孔子讲堂、道德讲堂,对不同社会职业、社会阶层进行广泛的切合实际的儒家文化教育,目的是化民成俗,救正人心,和谐社会。
第三,儒教复兴要坚守儒家人文理性的基本精神
人文理性精神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以人文理性为主,以神道设教为辅的特点。在中国文化中,神和宗教始终是围绕人世问题活动的,是被当作为人事服务的工具对待的。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不会迷狂,他们所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重人事、轻鬼神的特色。从西周“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产生之后,以及西周后期疑“天”思潮的兴起,人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极被动地祈求上天的恩赐,而是把着眼点放在人事和社会上。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慢慢上升。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对传统神人关系进行了新的人文思考和理性构建,最终导致了神人关系的重大突破,完成了春秋时期价值观的根本转向,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尽管后来在中国文化中,宗教观念和活动并没有彻底消亡,但却一直未能充分发育一元独大的宗教。即使外来宗教传入,也往往会变形、走样,被中国化、人文化,否则它就难以在中国立足、生存和发展。所以,外来宗教被中国文化以及人文精神的涵化,也就失去了在产生地的某些宗教成分,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总之,宗教观念和对神的信仰始终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次要的地位。
韩星教授对海外孔教与儒学、儒教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指出以孔教学院为代表的海外孔教,曾经在殖民地的文化以及其他多元文化的氛围中以宗教为形式,以儒家人道为本质,弘扬和护卫中华文化,成为海外赤子心灵的寄托,感情的归宿,同时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海外孔教在思想理念上是以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为教主,实际上是以孔子的伟大人格和思想为依归,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承和发挥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与儒学有更直接的承续关系。他们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在很大意义上是在宗教的活动方式上,在宗教的组织形式上来宗教化,而不是把孔子的学说变成神学,进行顶礼膜拜,搞成迷信——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孔教运动是传统儒学的民间化、现代化,在思想上仍然保持了传统儒学人文主义的基本品质。因此,对于当下建设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特别是重建儒教的呼声越来越高,韩星教授的态度是积极的,又是谨慎的。他在不同地方反复强调儒教复兴要保持儒家人文理性的核心精神,避免宗教狂热和排他性,造成宗教和文化冲突。
注释:
〔1〕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http://www.chinarujiao.net/p_info.asp?pid=3141.
〔2〕康晓光:《我为什么主张“儒化”》,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1178/.
〔3〕赵法生:《乡村儒学讲堂参与乡土信仰重建》,“乡村儒学与乡土文明”会议论文集,第1-17页。
〔责任编辑:嘉耀〕
解光宇,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儒学与儒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韩儒学发展路径及其现状比较研究”(15BZX067)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