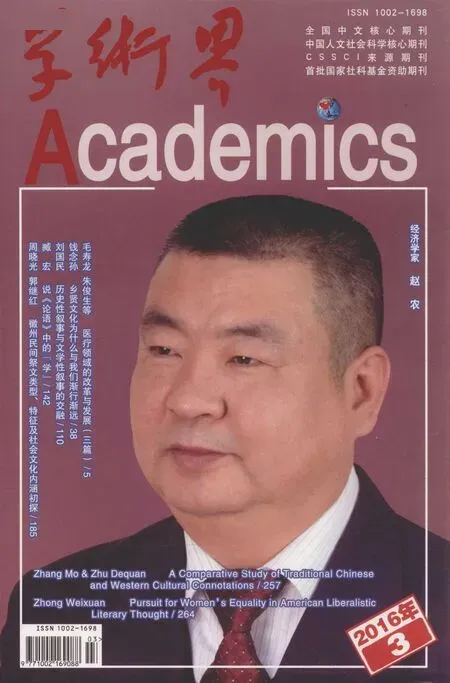医疗服务的秩序维度:扩展秩序、权利结构与医疗领域的治道变革
○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学术探索·
医疗服务的秩序维度:扩展秩序、权利结构与医疗领域的治道变革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100872)
中国医疗领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是管理问题,有些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很多问题仅仅依靠管理的改革难以解决,需要从秩序的角度来理解,并提出解决的方法。医疗服务自身具有内在的秩序,政府只有理解了其自身秩序的逻辑,并尊重其自身逻辑,理清楚医疗领域的传统治理之道,并实施从权力治理到权利治理的治道变革,才能真正在治理层次建设好公共治理,并在治理层次解决管理难以解决的问题。
医疗服务;扩展秩序;治道变革
一
现在中国医疗领域总体问题是,医疗准入高门槛,导致供需矛盾,总体供给不足,需求大于供给。医疗资源行政配置,呈现单中心集中,摊大饼式分配格局。政府对医药和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严格管制,导致高价格,需要更严格的、更系统的管制。政府财政对不同人群的补贴呈现逆向补贴格局,收入高的,反而给予更多的补贴。对穷人进行补贴,反而出现了低收入人群好于中等收入人群的问题。另外,医患关系也非常紧张,医闹不断。
所以,医疗服务领域存在很多公正和效率的问题。从公正性角度来说,现在大家把医疗服务当作基本公共服务,追求全覆盖、均等化。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内在矛盾的标准,即使一组人分一块蛋糕,全覆盖是值得追求的,但全覆盖很可能包括不想吃蛋糕的人。公正,可以是数量上均分,可以是价值上均分,也可以是按照需求分配,而需求可能是现实需求、未来需求、可能需求、风险需求,也可以按照约束条件来分配,比如按照支付能力和意愿来分配,按照消费能力来分配。而这些公正的标准显然是具有内在冲突的,而同时要满足这些公正性要求,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现实上即使逻辑上可能,执行上也极其困难。根据罗尔斯正义原则,初次分配按照市场原则,二次分配基于低收入者优先原则,同时还要符合低收入人群获得优先之后不得好于未接受优先分配的中低等收入人群。〔1〕罗尔斯原则自身都很难在逻辑上符合要求,尤其是不能让低收入者等于或者好于不享受再分配的中低收入者。如果加上这些公正标准,其分配更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而且矛盾重重。简单的蛋糕分配是如此,复杂的医疗服务,显然更存在难以调和和实现公正性原则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数量是很难计算的,计算用药量?就诊数?用药价值?就诊满意度?门诊的级别?住院床位?医院距离?还是医院的装修水平?高科技水平?其要计算的因素更加复杂,而且也基本上不可能。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既然无法处理那么多复杂的因素,它就会挑选其中可管理的因素并加以简化来作为管理的抓手。把不可管理的忽略掉,而把可以管理的作为重要的管理抓手。而这显然会忽略掉公正的很多因素,而在理论、政策和执行之间制造很多显著的鸿沟。现在实际管理中,管理者为了某个管理目标,任意选择某个指标,进行数量管制,而跟理论上的公正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可管理的和理论上的探讨具有巨大的鸿沟。
和公平类似,效率也具有很多具体的内容。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效率意味着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有更适当的病人,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病例,更好地提升技术。更好的医生专业等级当然好,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对病人来说,首先是有更好的咨询,因为去医院之前病人一般都是自己了解病情需要去医院,或者向朋友咨询需要去医院才去看病的。而确诊后需要治疗时马上就有床位可以及时住院。医生有合法执照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医院也是需要投资的,过去依靠医生自己的投入,后来大多依靠资助,现在来源于政府拨款或者第三方付款,但更好的融资和投资,可以让医院得到更好的发展。要有更好的投资,就需要有可能性得到更好的回报,就需要有有效的市场模式。这时就会突破管理的很多模式,比如医生的编制管理、国家职称管理、薪酬管理,甚至是处方管理等等。现在统计上往往重视医疗服务的宏观效率,比如万人均有多少医生,有多少个床位,床位的利用率,有多少人均投入,医疗服务分布的均衡性和不均衡性,这些指标忽略了医生、病人和投资者的因素,往往只是管理者眼中的效率。
现在医疗服务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医院自身的商业模式的选择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管理的问题。以定价问题来说,挂号费到底高价好,还是低价好,甚至是免费好,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答案。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医生劳务价格的问题。但从市场模式来说,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银行和餐馆,挂号只是替代排队的一种技术,可以让顾客不排队,坐着就可以排队,都是不收费的。医院通过排队挂号来收劳务费,也只是一种市场模式。要不要收费,医院自己可以决定,并不需要政府来规定要不要收费,收多少费用。当然,在排队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号贩子,那就是供给的问题。说明我们医院的发展不够,医生太少。现在很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医生工作只好改行,而医院的号资源还那么紧张,说明供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通过号码资源的管理来解决供给短缺的问题,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挂号费提升到几百元一个,也未必能够调节供求平衡。短缺问题依然会存在。
医生收红包的问题,在管理者看来是腐败的问题,但在商业模式中,服务业领域的小费模式其实就是红包。如果医生可以拿红包,那就是相当于是小费。如果商业模式规定医生不拿红包,那就意味着不让拿小费。如果医院具有独立的管理权,那么拿不拿红包,红包相当于诊疗费的10%或者15%,那就是医院的事情,不一定要有固定的费率。如果医院不具有独立的管理权,把医生当作公务员,其报酬和服务没有关系,而且禁止拿红包,那收红包就是腐败的问题。
如果对全国的医院都进行统一管理,这时候就需要几个管理的抓手,比如要建设多少床位,医院和医院的管理人员需要进行管理级别的管理,还要对其进行编制和薪酬管理,并对领导职数、专业岗位进行数量控制。同时,对计费方法、价格确定、价格水平、处方量、住院天数等进行数量控制。在鼓励发展民营医院的情况下,还需要对医院自身进行分类管理。管理越多,可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管理层次上产生了更多的问题。结果,管理越多,问题越多,问题越多,要求管理更多。产生了恶性循环的问题。
所以,中国医疗领域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商业模式还是管理模式的选择问题。若视为管理模式的问题,仅仅从管理角度来探讨,势必无法走出改革的误区,很可能越改革,问题越大,而且无论怎么改,这些问题很可能都一直存在。如果从商业模式来考虑,这些问题其实都很好解决。本文从秩序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模式的选择问题,并思考一下为什么管理模式存在那么多的内在问题。
二
从秩序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秩序中。比如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我看到的经济学家朋友是活生生的,他高兴我也高兴,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我看到我的学生,也是活生生的,他生病,我会担心,会难过。但是其他与我不太相干的人高兴了,我就不一定高兴,陌生人生病了,我也没什么感觉。另外很多人生病了到医院反而释然了,为什么?因为到医院看那么多人和自己一样生病,就释然了,他们都是同病人。这是我们生活的原始的社会秩序,范围比较小,人与人之间很熟,有很多情感交流。与此相对,是扩展社会,规模大,人与人之间存在比较正式的结构,它既高度流动,又有一定稳定性,在这种社会中,需要有符号来识别人,需要姓名、身份证来确认你是谁,需要居住地址,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人与人之间比较冷漠,很少情感交流,但比较自由,比较需要抽象的规则,来确定各自的边界和合作框架。
除了上述两种秩序外还有更大范围的国家秩序、官僚秩序和市场秩序。国家秩序与兵和权力有关。过去王是国家秩序的核心,具有主权性质,它掌握生杀大权,而且可以免于妄议。比如就国家秩序来说,王有特权可杀掉任何人,谁都不可以妄议它,即使他说错什么话大家也要歌颂他,他说错的话、做错的事,要往对的方向理解。用法律术语来说,王具有豁免权。国家主权不会犯错,错了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公法责任和民法责任。官僚秩序也是大规模的扩展秩序,它的特点是等级性和专业性,官僚是等级化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但还需要依靠专业知识,管理水利要懂水,管理医疗要懂医疗。市场秩序也是一种扩展的秩序,是在自由交易的基础上形成的扁平化的交易和合作秩序。做买卖的,到英国买东西,到美国卖东西,到全世界投资房地产,从而形成了不断扩张的秩序。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扩展秩序。可以说古代文明往往和国家秩序和官僚秩序的发展有关,现代文明则和官僚秩序尤其是市场秩序有更密切的关系。
医疗服务和上述的各种秩序都有关系。在原初秩序中,一个人生病了,首先是自己判断自己不舒服。自己是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在自己身上,自己的病自己负责。人的心情好,习惯好,就会有健康的身体。若习惯不好,晚上老熬夜,熬夜伤身体,就会抑郁,就会生病;不喜欢跟人交往,朋友就会少,多走亲戚,多交朋友,就会有发达的原始秩序。在这个结构当中,生病的人和买烟喝酒的消费者是不一样的,买烟喝酒是自己做决策,但是看病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个病治还是不治,到哪儿去治,保守治疗还是激进治疗,是家庭决策并承担负责的。网上有一个段子,有一个小孩子说为什么要生二胎呢,因为只有一胎,他如果老了,躺在那儿了,呼吸机拔不拔,谁决定呢,一个人决定。现在生个二胎,他们俩至少商量一下要不要拔,老大说拔不拔,老二说不中,可能就不拔了。家庭结构扩大,实际上有利于维护一个人的利益。所以家庭是医疗的基本消费单位,也是基本的决策单位、责任单位和支付单位。生病后治疗、签字、画押、付钱、照顾,先是家庭负责,然后亲戚、朋友帮忙。所以,好的家庭、亲戚和朋友是良好健康的医疗服务的后盾。政府制定医疗政策需要考虑家庭单位以及医疗服务的社会资本。
走出原初社会,人不再易动感情,不再动不动着急。在扩展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抽象的人、规则中的人。在哈耶克看来,它们是自由发展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也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和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2〕在扩展社会中,人们需要有正式的规则来界定权利和责任。需要有公共的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大城市都是一个个扩展社会,农村、火车站、旅游点、包括小区, 都是高度流动的扩展社会。如果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生病了,首先是联系他的家人、亲戚或者朋友,若这种原始社会秩序没有,就只能依靠扩展社会的正式救助机制,比如依靠红十字会,依靠保险公司。这种秩序相对比较稳定,实际上就是扩展社会的互助机制。它类似于原初社会,但规模比原初社会大,专业化以及资源集中的能力、可负担力,都要比原初社会大。有很好的原初社会,再加上很好的扩展社会互助机制,一个人的医疗服务,就得到了再次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官僚秩序的医疗保障,可能不如原初社会和扩展社会的医疗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养老金与其交给国家,不如交给家族、单位或者社区。一般社区养老机构,可能要比国家养老机构靠谱。医疗服务也是如此。国家的医保只保个人,但原初秩序中医疗服务单位却是家庭。现在很多国家的医保忽略了家庭、家族、朋友圈,也忽略了扩展社会的互助机制,这在政策上显然是不合适的。
当然,医疗服务自身也有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医疗自身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服务性,而这两点经常界限模糊,很难区分。它是科学,意味着很多东西都在探索中,根本不明白其中到底是什么道理。比如说医生在用药的时候发现,本来是治胃病的药,却把并发症心脏病治好了。这样医疗科学家就明白这个药治疗心脏药效好。一位老人家因摔跤骨折去住院,本来耳朵不灵,头发白了,但一住院打些点滴回来,忽然发现她头发变黑了,而且耳朵也灵了。这个药显然对她的耳朵和头发都有治疗的作用,但对其他人是否有用,这需要临床的进一步探索,而且治疗结果并不确定。这就是科学。科学不确定,而且如果结果并不好,科学家也并不承担责任。比如吃一种药,病却没有好,一般来说药费是不退的。但如果看电影没有看成,飞机误点,却是要承担责任的,至少是退票。这说明,医疗服务作为科学,与一般的服务是有差别的。
当然,医疗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服务,它可以出售给病人。治好病人的病,医生则收取费用。有些医生也的确如此吹捧,包治百病,不灵不要钱,治不好病不收钱。这是很好的营销模式,但实践上这两者是很难区分的。政府非要把医疗从科学拉向服务,和一般的服务那样来进行管理,并在科学和服务之间强行拉一条界限,就会有问题。例如只要新药没有严格的临床试验结果,就不能用于临床。这看起来是确保了服务,其实却损害了很多病人的利益。因为假定这个新药有10%的把握能够治好病,但90%不可控,政府肯定不会让其广泛用于临床。其结果是,一万个人都去世了,而本来其中1000个人是能够救活的。这9000人就成了试验品。政府的严格管制,让这9000人避免成为试验品,但结果是这9000人一样离开了人世,还让另外一千人失去了活命的机会。这个时候,应该考虑的事是,政府不能替代病人及其家属和科学家来进行决策。科学上的事情,科学家来决策。是否接受有风险的科学服务,由病人来决策,病人无法做决策时,则由家人来决策并承担责任。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和医生是最终的决策和责任单位。政府可以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但不能替代他们,从而让医学的进步和服务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多样性的机制。
实践表明,现代医学是一个专业,它表明,现代医学有严格的操作规程,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需要临床实习,需要当很长时间的全科医生,然后变成专业的医生。就病人来说,在医疗的专业秩序中,病人是需要有知情权的,即使重病限制病人的知情权,家属肯定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相关的免责权。在这里,病人和家属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医生作为科学家有豁免机制,动手术前家属要签字,麻醉的时候若出现问题,归为麻醉事故,医生可免责。医生的免责权和老师的免责权是类似的。一个学生博士生论文没有写好,没有毕业,学习失败,交的学费是不退的。一个学生毕业了,拿到了学位,结果教育部派人去查他的论文,发现有一些问题,结果通过倒查机制,停止其导师博导资格。这个责任机制是过分的机制,因为导师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然后答辩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决策权和责任就被虚置了。但从管理上来说,抓导师是比较好的抓手。但这个抓手显然破坏了自然形成的教学秩序。
三
医疗秩序作为一种专业秩序是一种内在的秩序,医生职业选择的时候是有良心的,对生命存在敬畏。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融入到这个专业秩序里去,只要花功夫,好好学习。即使不好好学习,久病也能成良医,给人提供比较好的健康咨询。好病人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了解自己的感觉,自己对生命的重视程度。从秩序角度来说,病人享受更多的选择权、决定权,而不是因为缺乏一个床位而不得不延迟,乃至放弃治疗。如果病人就是内在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医生和病人,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权力和责任结构。这样的秩序是自由的医生和自由的病人共同形成的自发秩序。
医疗作为一种管理的秩序,就可能是一种外在的强加秩序。内在秩序,可能存在病人和医生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这种信息不对称,可以内在的解决。如果政府要通过管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会破坏这种内在的解决机制。比如病人的确很难了解医生的质量,政府就把医院和医生都分为三六九等,这看起来好像便于病人选择,其实反而遮蔽了医生的真实水平。因为这样一来,医生就纷纷去努力满足行政的标准,而不是真正的医疗的标准。很多好医生完全可以跨国执业,但政府外在的强制秩序使得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了。中国则干脆不让医生异地行医。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医疗秩序。显然,外在强加的秩序,只是符合行政标准的秩序。医疗改革需要让这种秩序让位给医疗内在的秩序,让医学真正成为科学,成为专业,而不是行政管制的对象。
在中国的古代,这种强加的秩序就是兵的秩序,帝国的秩序。在一般人眼里,最大的兵是皇上,但在医生眼里,最大的兵也是病人,与一般人无区别。然而,在最大的兵眼里,他自己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作为其太医、御医,作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医生也不是一般的医生。曹操打败董卓当了宰相,是实际上的皇帝,他得了头痛病,问天下名医是谁,他是天下老大,一定要找天下医生的老大。医生是拿手术刀的,曹操拿的是杀人刀,手术刀比不过杀人刀,华佗就只好拿着手术刀去给曹操看病。华佗问诊提出治疗方案,即要开颅才能治疗。医疗方案一出,曹操就认为他可能是董卓余孽派来的刺客,就把他当刺客宰了。一代名医就此丧生在曹操的杀人刀下。所以在兵的秩序里,伴君如伴虎,也同样适用于御医,稍不如意就被杀了,没得商量。
由此可见,医生资源根据兵的秩序来配置,由于兵的内在秩序是排斥医生的。医生若要生存保命,则一定要有策略行为:回避有风险的手术,不愿意尝试新药,凡事都求保险。同时在治疗方面也容易出现过度用药、用好药、用贵药,遇到像曹操一样的病人,就将最普通的药翻一百倍价格卖给他,而且还报喜不报忧,即便皇帝病情加重,也会谎称皇帝的身体即将康复。
这就是兵的秩序,传统的帝国秩序,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医,莫非御医。最好的医生的确可能是御医,但并不限于御医。帝国是单中心的,等级制的,医生秩序也开始有了等级,而且按照单中心来分级。医生如果是御医,即获得最高级别的成就。给普京大帝看病的医生,自然有更高的地位,也会有更好的市场。
现代国家秩序,核心不再是兵的秩序。但官僚秩序依然有兵的特征。差别是多了一个专业化的官僚部门,即技术官僚部门。技术官僚的特点是存在等级制和身份制。
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卫生部门进行严格的行政管理,医院分行政级别,医生也有行政级别,还有技术级别。医院由行政主管管理。公务员一个系统,事业单位一个系统,然后是不入流的市场部门,还有黑医游医部门。在医院这个事业单位内,还有行政系统、后勤系统、专业医护系统,医生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但行政地位未必最核心。专业医生和医护系统走技术级别,其他走行政级别。
医生在这种行政秩序下,也会有自己的策略选择:第一种策略是努力去当官。当官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切资源,但这势必会影响到其医疗的专业水平。第二种是努力去当好医生。同时写论文、写书,争取各种荣誉称号,以提高自己的职称。这种医生会写文章,但未必医术高明。多写文章,显然会影响医术。第三种是努力去创造收入。国家给一部分钱,但有严格的管制。医生必须想尽办法创收,变成了官僚企业家,其医术显然也会受影响,甚至医德都会受到影响。
就这样,医疗服务里原始的自然秩序,先被兵秩序破坏,然后又被官僚秩序破坏了。接着我们来看看市场秩序。
市场的秩序实际上相对于医生秩序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秩序。医疗系统行政化,医生行政化,同时经营模式准市场化,其结果是医疗系统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依然处于被高度抑制的状态。一方面看病贵,一方面又看病难;一方面医生都忙得累死了,满负荷运作,一方面医学院的学生还找不到工作,还要改行。
在当前,中国有医疗保险市场,但保险市场是官僚的。而投融资市场包括医院产权市场,医生劳务市场都没有发展起来。医生劳务市场基本上是封闭的没有流动。有技术级别、行政级别的,大家都往高级别的、有职业发展前途的大医院去,能进不能出,行政主导。其结果是行政机构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无权的医生无话可说,专心用专业方法对付强大的管制。这一体制必须改革,但医疗改革,越改,管制越多。这说明,仅仅求助于更强的管制,着眼于对医院和医生的高度技术性的控制,并不能解决医疗服务所面临的问题。着眼于技术控制目标的改革,只能让行政化的治理结构越来越强化,医疗体制的疾病积重难返。
在市场秩序中,官僚们一般只看到实体的看得见的产品市场,但对于服务市场、产权市场、投融资市场及保险市场,官僚们是看不到的。即使看得到,也理解不全面。在他们看来,市场中的过剩是浪费。服务、产权、投融资和保险等不受控制,就会跌入深渊。
其实,产品只要有市场,就会有过剩供给。否则价格就会上升,就会有供给来补充。产品没有过剩,消费者就没有选择权,就不存在市场。一旦产品过剩,消费者就有选择权,也就有了市场。供求平衡的市场是偶然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消费者没有选择权,实际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服务只要有市场,就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协议,就不会像现在那样病人去医院,几十秒解决问题,一锤子买卖。医疗市场自身有一个很好的协议结构,它和保健市场也应该会结合在一起。不会是简单的买卖即分的市场。医院如果有股权,就会有股权市场。投融资就会有更多的金融参与。金融一旦参与,就可能出现泡沫化地迅速发展。这样的泡沫可能造成浪费,但却是某个专业市场快速发展所必经的阶段,就像人在青春期肯定存在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市场化,是一个市场制度的逐步演进,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很多问题不断展现,多中心的发展和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医生、医药都会因为市场而充分发展,并且因为市场而变得很有价值。所以,市场秩序是亲医疗服务的秩序,不像兵的秩序是排斥的,官僚秩序是限制的。市场的治理结构,是一个扩展的秩序,它可以让医生和病人,处于一个扁平化的结构里,在那里,每一个人的主观价值选择,包括公平和效率的种种理解,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在这一结构中人是主动承担责任的,而不仅仅是有明确的权利,所以是有扩展的效率的。
所以,良好的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多中心〔3〕,以人为本、以医生为本、以病人为本的多级市场。作为普通人、专业的医生、管理者,或者投资者,在市场里都是人。各种身份和角色都是市场结构的细分而已,都承担终极的责任,并享受责任范围内的权利。
四
从理论上总结一下,我们看到医疗在乌托邦的状态中有四种理想的秩序:第一种是理想的兵的秩序,它与医疗秩序是排斥的,医生不可能内在地产生,它扼杀产生医生和医药的秩序,形成等级命令的秩序。
第二种乌托邦秩序是官僚秩序,它与医生和医药也是不兼容的,除非具有确定性的医药和医生服务。也具有扼杀性和消耗性,是一种计划经济的秩序。它的行政抓手,牢牢地抓住医院,让医院和医生等同于它可控的床位数量、门诊量等。
第三种乌托邦的秩序是扩展社会秩序,是多中心的秩序。医生自身就是一个专业社会,扩展的医生社会,可以形成多中心的内在专业秩序。病人也一样,在扩展的社会秩序里,有自己的相对稳定的生活圈。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过年了,北京很多单位领导带着单位互助资金去医院慰问本单位的职工。很多朋友圈微信群,群里有人病了,就给其踊跃捐款。老师病了,师门的学生纷纷去照顾。这都是扩展社会秩序的作用。
第四种是理想的市场秩序,是多中心、扁平化、结构化和动态的秩序。在兵和官僚结构里,床位是无差异的。但在市场结构里,每一张床位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每个医生的价值也不一样。包括每一块钱医疗投入、资本的结构都是不一样。拉赫曼在《资本及其结构》中提到,资本结构就是每一块钱是有结构支撑的。〔4〕所以在这个理想的秩序中,人、医药和供需满足,投资和生产,服务供给,融资,都将结构化,并在结构化动态的市场里,实现其价值。这个秩序可以支撑任何一种差异性的东西。它是越来越复杂化,但越来越增进个人自由和能力的秩序。
当前中国的医疗,还是兵和官僚为中心的秩序,市场和社会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中国医疗实际上实行的是政府全方位管制,甚至连抗生素的种类数,点滴使用的病种,都有严格的管制。高度管制催生出普遍的策略行为。医院则高度官僚化、行政化。公立医院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民营医院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整个系统存在普遍的策略行为,医生也不得不精于策略行为。如果不适应策略行为,就转行,去经营管制较少的医疗器械市场,甚至去做广告、媒体,自己寻找市场化的机会。
而且病人也被划分为特定的群体:公费群体、社保群体、农保群体和没有保障的群体。群天下的格局很明显。有些人因为缺乏保障,看病倾家荡产。虽然这个市场看起来有一定的公共性:只要花钱,任何医院,都可以去看。有了这个公共性,市场和黑市,就发展起来了。结果中国的医生成了全世界最忙的医生,一天看无数的病人,中午吃饭还有人找上门,在办公室也有熟人介绍的病人登门。中国的病人也变成全世界求生欲望最强的病人,但平时都不注意保养,他们的车都会去4S店定期保养,所以车的健康状况普遍很好,但中国人普遍不对自己进行定期保养,好像车比人还值钱。
其核心是中国医疗领域的治理结构是权利放两头,管制摆中间。到处是权力为中心的简单秩序,市场又很粗俗,很初级,发展空间受限,结果就产生了医患权利不清、责任扭曲和医闹不断等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从秩序定位可以看出,中国医疗领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治理结构内生的问题。权力身份等级结构,必然内生出这些问题。依靠技术性修修补补,甚至依靠物品理论来确定公益性和私益性的边界,依靠收入水平来确定不同群体,都很难解决其内在的问题。
当然,高度管制的秩序结构,要放权、要搞活、要市场化,也会出现很多乱象。过去计划经济转轨搞双轨制,就出现了很多乱象。药品市场是如此,医生服务也是如此。其之所以是乱象,并不是市场乱了,而是转轨中所出现的双轨制,不仅让权力的控制作用放松了,而且其寻租的作用也释放出来了。双轨制问题的核心是,治理结构还是权力,并没有转变为权利。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结论是在医疗领域需要进行治道变革。这个治道变革简单说就是从等级权力的秩序结构转变为利益的、权利的秩序结构,在这个权利结构里面,人的权利和责任、家庭权利和责任、医生权利和责任,包括医院、医生、社会的权利和责任,政府、政府部门权利和责任,都需要思考,如果从奥地利经济学的角度,奥地利经济学是治理经济学,思考权利而不是思考权利结构,会更好地理清楚新的治理结构的生长机制。
比如,社会互助机制,就比政府强制规定企业出多少,个人出多少,国家出多少,然后都交给大一统的政府要好。比如新药,让病人和医生有更多的决策权,比国家有更多的决策权要好。比如处方,让医生开处方,让医生同行来评价相关处方,甚至住院时间要比国家去规定处方要强。权力是简单化的治理结构,会让医和药越来越简单,以适应官僚化运作的需要。权利,是复杂化的内生发展的治理结构,会让市场越来越复杂,从而让官僚无法运作,凸显人、医生的作用,甚至投资者、管理者、保险公司的作用也会越来越突出。这样医疗领域就不会出现看病贵,但看病依然难这种很奇怪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医疗行业存在很多问题,有管理的问题、理论问题,或者医院本身的营销模式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很多都是秩序和治理的问题,需要从秩序和治理层次去理解,并在这些层次去解决。第二权力治理导致治理意义上的问题,所以需要用治道变革来解决。第三,新的治理治道是以权利和责任为基础的治理结构,这个时候我们说跟其他的概念一样,限制权力,张扬权利,尊重人的权利,尤其是尊重医生作为专家的权利。
这才是正确的医改方向。
注释:
〔1〕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参见F.A.Hayek,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2,vol.1,p.2.
〔3〕有关多中心,参见Michael Dean McGinnis ed.,Polycentricity and Local Public Economies:Readings from the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Institutional Analysis)1999.
〔4〕路德维格·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熊越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
〔责任编辑:力昭〕
作者简介:朱俊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作者2016年1月14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城市公共事业中心主办的“医疗资源配置的公正与效率研究报告发布会”的演讲修订稿。本文也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7137316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ZD042)的部分研究成果。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