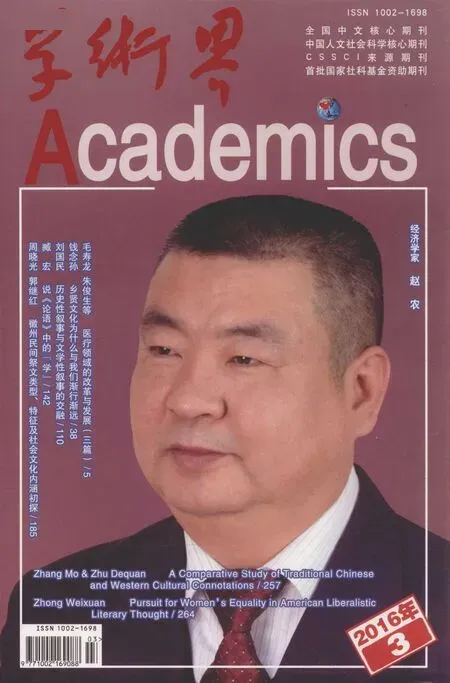论当代家族小说的主题呈现〔*〕
○ 张太兵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2.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12)
论当代家族小说的主题呈现〔*〕
○张太兵1,2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200234;2.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安徽滁州239012)
当代家族小说叙事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村落史模式、家族史模式、权力斗争史模式,在主题呈现上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民族、家族、个体的整合;二是宏大主题的消解;三是个人话语的重建。上述特征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整与文学向本体回归的走向。
当代文学;家族小说;主题呈现
法国著名叙事学家格里马斯将叙事模式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契约型,故事涉及契约的设立与悔毁,常与人际的抗拒与调和有关。例如《红楼梦》中所谓“金玉良缘”“木石前盟”等就属于这种类型。二是任务型,包括奋斗追求,斗争与任务的执行等。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显然属于这种类型。三是离合型,涉及邂逅分手,迁徙流离,相会相失等。这种类型的作品很多,稍微近一点的例子如张爱玲的《十八春》。〔1〕当代家族小说也有三种主要叙事模式:一是村落史模式即以村落的兴衰沉浮作为小说框架展开叙述。《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分别以白鹿村、马村的变迁来探求一个民族的秘史,属于这种模式。二是家族史模式即以家族的兴衰浮沉作为小说的框架展开叙述,《穆斯林的葬礼》《旧址》精心描述了玉雕专家韩子奇及银城盐商李乃敬的家族变迁史,属这种模式。三是权力斗争史模式即围绕权力展开争斗,《红旗谱》以农民与地主的斗争拉开序幕;《尘埃落定》以藏族土司围绕罂粟种植权展开斗争;《古船》以隋、赵两大家族围绕洼里镇粉丝大厂经营权展开争夺。尽管这些小说的叙事模式不同,但在主题呈现上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民族、家族、个体的整合;其次是宏大主题的消解;再次是个人话语的重建。
一、民族、家族、个体的整合
当代家族小说的创作数量较多,文本的社会生活容量巨大,为何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家族这一叙事视角呢?选择这一视角的思想文化渊源是什么?民族、家族、个体三者整合的内在肌理是什么?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肯牺牲身家性命。”〔2〕但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出现了亡国灭种的空前的民族危机,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亡之路,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空前高涨,“没有国,何以有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人开始觉醒,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国族主义”开始在民众的思想意识中逐步增强。
由于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封建思想已渗入民众骨髓,传统文化教育体系麻木了民众神经,闭关锁国政策遮蔽了民众视野。正如赵世林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种传承文化,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完备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世界古老文明史的发展中,中华文化表现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整合力,其内在的根源就在于此。〔3〕由于民族危机导致国家民族意识的增强与中华文化表现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整合力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凝聚在每个个体身上。换言之,就是把民族(国族)主义、家族主义的冲突整合在每个个体身上。纵览家族小说的创作,不难发现,绝大部分作家对宗族主义和家主义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而对国家主义是赞成的。因此他们在创作中有意无意的对“家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由于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观念使得“家”具有了“国”的隐喻,对“家”的批判必然导向对“国”(传统王朝国家)的否定,而对于传统封建王朝的否定正是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们通过对家族生活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积淀,瓦解了残留在人们思想中的封建意识,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红高粱》《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旧址》《丰乳肥臀》《尘埃落定》《檀香刑》《古船》《故乡天下黄花》《最后一个匈奴》《生死疲劳》《蛙》等在作品主题呈现上的共同特点是把个人命运放在家族生活中展示,把家族生活放在民族命运中展示,从而实现了个人、家族、民族命运的整合。
在土匪身上的整合。《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是个“圆整型”人物,从个人品性来看,他品性不佳,胡作非为,违法乱纪,匪气十足。无论戴凤莲嫁单扁郎,对于戴凤莲是何等不公,人们情感上如何无法接受,戴父如何不负责任,但这桩婚姻也只能在道德范围内来评价,任何组织、个人都没有权利擅自剥夺单家父子的性命,但余占鳌却杀害了单家父子,肆意践踏法律,视生命为草芥,他视生命为草芥同样体现在对待劫匪的行为上,劫匪用一支假枪行劫,抢劫失败后落荒而逃,余占鳌完全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他痛下杀手、毫不留情。在家族生活中,余占鳌骄奢淫逸,一夫二妻,家庭矛盾丛生,两妻经常殴斗。作为主要人物形象,按照这样的性格逻辑发展,余占鳌毫无可取之处,天才的莫言让其形象发生急转,令读者流连忘返、赞叹不止,莫言将民族战争元素整合在余占鳌身上,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余占鳌率领游击队袭击日军,游击队损失惨重,战斗悲壮惨烈,我奶奶壮烈牺牲,战斗中的余占鳌置生死于度外,充满血性,充分展示了我们民族不可征服的品格。在个性元素、家族元素的基础上整合揉进民族元素,使一个视生命为草芥的土匪,肆意践踏法律的杀人犯,骄奢淫逸的莽汉轿夫变成了一个溢彩流光的英雄。
在地主身上的整合。《丰乳肥臀》中的司马库是一个“土地主”,吝啬如葛朗台,他有一辆漆黑的德国制造的世界有名的丽人牌自行车,也是高密东北乡开天辟地之后的第一辆自行车,上官福禄趁人不注意摸了一下车把,惹得司马库黄眼珠子冒蓝光,如此吝啬的“土地主”,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斗中却能置生死于不顾,以酒为燃料火烧日军的车队,富有创造性的打击敌人,自己的多名亲人也受到株连,惨遭杀害。被日寇屠杀的乡民尸体高度腐烂、臭气熏天、乌鸦与苍蝇缠绕着尸体翻飞,司马库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乡民进行掩埋,体现了对乡民的挚爱,对生命的敬畏。为民族大义,司马库牺牲自己的亲人,民族、家族、个人有机地整合在司马库身上。
在资本家身上的整合。《穆斯林的葬礼》的主人公韩子奇是孤儿,梁亦清收其为徒,视如己出,将雕玉技艺倾囊相授,韩子奇聪慧好学,技艺提高迅速。梁亦清去世后,为替师傅还债,韩子奇给玉器销售商蒲绶昌做义工三年之后,重返奇珍斋,与师妹梁君璧结为夫妻,育有一子韩天星,家庭生活其乐融融。然日寇侵华战争摧毁了韩子奇宁静和谐的家庭生活,为保护收藏的玉器珍品免遭战火,韩子奇带着玉器抛妻别雏跟随沙门·亨特避乱伦敦,妻妹梁冰玉尾随而至在牛津大学留学,他们寄居在亨特家,亨特的儿子奥利佛·亨特执着地追求梁冰玉,可在一次德军对伦敦的轰炸中,炸弹无情的夺去了亨特年轻的生命,也让梁冰玉与韩子奇这两个飘零异乡的游子走到一起,在伦敦遭受轰炸的恐怖日子里,梁冰玉向韩子奇倾诉了爱慕之情。民族冲突与战争因素整合到韩子奇生命的年轮中,战争让韩子奇与梁冰玉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相濡以沫,战争促成了他们的结合并生下女儿韩新月,如没有战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是他们的结合给梁君璧带来了巨大的无以言传的苦痛,深深地伤害了她,韩子奇与梁君璧、梁冰玉的情感纠葛是韩子奇家族内部最尖锐的矛盾,另外一夫两妻且两妻是孪生姐妹的情形与穆斯林宗教伦理水火不融。为保持回族血统的纯洁,回民拒绝与汉人通婚,而实际上韩子奇恰恰是汉人遗孤,梁君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其结婚,直到临终前韩子奇才将真相告诉她。这样中日民族矛盾、回汉文化冲突、宗教伦理禁忌、家族婚姻纠葛便整合在韩子奇身上。
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整合。王安忆在《纪实和虚构》中将家族历史与个人历史进行整合,产生一个新的维度。王安忆的母亲是孤儿,由奶奶抚养成人,从小缺乏母爱,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母亲的奶奶带着母亲去姨母家,母亲在楼梯下磕三个响头,上面就扔下一块钱,这次拜访深深的刺痛了母亲,母亲常说:“亲戚算什么?这就是亲戚。”母亲的遭遇与所受的伤害导致母亲极力想忘却家族史。母亲后来参加了革命,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因此她只认同生命中的横向关系,想尽办法忘记、消除与家族的历史纠葛,在上海生活,母亲只和同事交往,只讲普通话,尽管她的家乡话讲得很好,可她从不讲家乡话。母亲对自己的母亲知之甚少,感情疏远。母亲对家族、家族史的漠视代表了一种生命观,这种生命观拒绝历史,只认同现世及现实社会关系并把它作为生命的全部内容。幼年的刺激让母亲竭力忘记个人生命的历史维度,战争时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让母亲极度重视横向生命维度。但在我看来个人生命由两个维度构成,一是历史维度,一是横向维度。生命无法离开历史维度,血缘、家族、亲戚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没有血缘、家庭、亲戚的支撑,个人生命就会感到自卑、孤独和压抑。王安忆在历史的追寻中找到了个人的存在。民族、家族与王安忆个人生活整合在一起。
个人、家族、民族的整合使得文本主题含混多义,文化底蕴丰厚,情节错综复杂,人物形象圆整。作家获得巨大的创作空间,读者获得无限的想象空间,读者、文本、作家、历史之间展开对话,作家、读者享受创作、阅读带来的乐趣。
二、宏大主题的消解
从题材的角度看,宏大主题一般是书写重大历史事件,以家国、民族、人民为表现对象。一般来说这种题材往往以歌颂为主基调,要求作家具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思考力、感悟力和成熟的艺术技巧,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历史风云中撷取在他看来堪称典型的宏观画面,然后从细节切入,拓展自己的抒写战略。
宏大主题的发展经历了解放区文学的萌芽,十七年文学的强化,文革文学的登峰造极三个阶段。解放区文学是宏大主题的萌芽阶段,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解放区及非解放区的文学运动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把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推进到新的阶段。文学创作在主题方面出现崭新面貌。作家、艺术家开始关注宏大主题,解放区文学大都是写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反映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及翻身后的崭新的精神面貌,歌颂共产党、歌颂抗战、歌颂劳动者、歌颂新英雄人物成了时代主题。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欧阳山等创作的小说,李季、柯仲平、阮章竞、田间、张志民等创作的诗歌,《白毛女》《刘胡兰》等新歌剧都集中的反映了这种主题。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得到贯彻,文艺对革命事业的配合更为有力,主题上突出反映和歌颂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生活、新气象。
如果说解放区小说创作是宏大主题的萌芽阶段,那么“十七年”文学则是宏大主题的强化阶段。“十七年的相当一部分作家,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4〕作品题材主要选择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创作手法上忽视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技巧,导致作家的创作个性、风格特色没有能够得到广泛充分的表现;人物形象塑造上普遍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因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而缺少较高的审美价值。
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是宏大主题的强化阶段,那么文革文学则是宏大主题的登峰造极阶段。文革期间,文学创作基本上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文学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为开展政治斗争服务。具体表现为“主题先行论”“根本任务论”“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创作中的贯彻执行。“主题先行论”是指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要打倒。“根本任务论”即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5〕代表性的作品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8个“样板戏”,“样板戏”迎合当时形势,用作品来影射政治,具有非常明显的类型化、脸谱化、雷同化的创作倾向,它是“思维大于形象”的产物,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歌颂工农兵、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所谓“经典”,至今仍是“文化大革命”的“形象代言人”之一。尽管打着文学的旗号,但其政治意义绝对大于文学意义。文革时期的宏大主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主题呈现上的多义性与模糊性。多义性与模糊性主题构成了对宏大主题的消解,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是《白鹿原》,在《白鹿原》的扉页上陈忠实借巴尔扎克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小说观:“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认为历史的真相和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历史书写是一种充满虚构和想象的叙事,是一种叠加着人类现实渴望和梦想的记忆机制。正如克罗齐所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作家对黑娃参加革命动机的描写与其他作家对农民参加革命动机的描写差别很大,他没有把黑娃参加革命的动机写得那么高尚、纯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而是强调了黑娃革命动机的模糊性,黑娃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父亲鹿三和他都是长工,黑娃由长工变为革命者,由革命者变为土匪,由土匪变为炮兵营长,最后由营长变为一个求学的儒者。他把白嘉轩对自己的帮助看作是上层对底层的歧视与同情,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开始于他对田小娥深深的怜悯与同情,田小娥俊俏的模样对血气方刚的黑娃产生了巨大的吸引,绝不像鹿兆鹏所说的:“黑娃是白鹿原上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顶住了族法族规的压迫……太了不起太伟大了!”〔6〕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是人性使然,根本没有反礼教与反宗法的色彩,黑娃的革命也是一样,几十年的流离失所让他如一片叶子漂泊不定,他一直被别人带动着生存,他的所谓革命行动也是一样没有明确目标,黑娃并不清楚革命的本质,所凭的只是一时的冲动与好奇,铡恶霸也只是平复心中积怨已久的仇恨,这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农民革命的真实心理。黑娃集土匪、国、共、儒家信徒等身份于一身,历经曲折坎坷,最后被新政权处死,走完他悲剧性的人生历程。陈忠实放弃传统历史叙事中清晰的“客观”表述,综合运用象征、反讽、黑色幽默、魔幻现实等手法,使《白鹿原》的主题有别于传统历史叙事主题,传达出一种对历史模糊多义的个人化理解,构成了对宏大主题的消解,表现了陈忠实先生对人性、民族和历史的哲理化思考。
叙事策略上摒弃宏大叙事,选取人物故事。摒弃宏大叙事,选取人物故事同样构成对宏大主题的消解。当代家族小说创作显示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冲突与叛逆,不仅迥异于“十七年文学”中的“国家”“人民”“集体”等观念,而且也区别于朦胧诗中的个体自我、自由独立等启蒙思想,特别注重选取人物故事作为表现对象,放逐本质、永恒、崇高、理想等宏大主题,用罗兰·巴尔特的话来说,就是“陈旧的价值不再被承继,不再被流传,不再引人注意。文学遭到了非神圣化的洗礼……但这并不是说文学已被消灭,而只是说它不再被看守了,因此这才是真正从事文学的时代”〔7〕家族小说摒弃宏大叙事,讲述各种故事。
首先,家族题材的虚构故事。在《纪实和虚构》中,为寻找个人生命的历史性维度,王安忆对家族的历史进行追寻,创造了一个家族神话。在“茹”姓家族的历史变迁中,王安忆讲述了五个重要人物的故事,一是祖先木骨闾,他建立自己的部落。二是社仑,在“茹”姓部落衰落后他使部落再度中兴。三是成吉思汗的横空出世,他让“茹”姓家族辉煌天际。然后家族历史由一“茹”姓状元茹棻接续,最终抵达外祖父。外祖父是个典型的败家子。但王安忆却认为,破坏与创造是一样的,是生命力朝气蓬勃的表现,家族史其实是个体生命蒸腾的历史,它构成个人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维度,对历史性维度的追寻,是生命自身的需求,由于生命中历史性维度的存在,生命才具有独特性。
其次,家族题材的真实故事。《红高粱》真实记录了余占鳌英勇豪迈惨烈悲壮的抗日故事。在国共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丧心病狂的日军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余占鳌带领烧酒作坊的伙计们拉起一支凌乱不堪、缺衣少枪的抗日队伍,斗志昂扬地前去青沙口袭击日军,和日寇展开了惨烈的战斗,我奶奶在战争中壮烈牺牲。余占鳌拒绝收编,按照自己的人生信念出没在高粱地里,豁出命与鬼子打伏击,他抗日的动机也许没有那么宏大,更多的是出于对生活的渴求和保障,但却展示了不屈不挠的品格、强大的求生意志及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斗争意志。余占鳌敢爱敢恨纵情尽性的快意人生令人神往。
再次,家族题材的恐怖故事。《丰乳肥臀》讲述了许多让读者感到恐怖的故事。大姐的故事让人揪心,解放后大姐上官来弟接受“组织”指定,与荣归故里的残废军人哑巴孙不言结为夫妇,哑巴双腿截肢,大姐与其毫无感情可言,大姐的屈就,多少还是考虑到全家人的安全,婚后大姐被变态的哑巴折磨得死去活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姐与三姐夫“鸟儿韩”(三姐已病故)产生感情,“鸟儿韩”曾被日寇掳到日本做苦役,逃跑后躲进深山穴居十五年,受尽磨难才归国还乡,母亲对饱受苦难的“鸟儿韩”充满同情与感激,自觉担当了大姐与“鸟儿韩”非法恋爱的保护人,但最后还是被孙不言发现,在孙不言与“鸟儿韩”的决斗中,大姐用门栓砸死了孙不言,也因此被枪毙,结束了自己悲苦的一生。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不让玉女和外甥挨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时先将粮食偷偷吃下,回家后用手抠嗓子,将粮食呕吐出来,玉女和外甥吃呕吐出来的粮食才免于饿死。为让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成为真正的男人,年过古稀的母亲放下自尊到“独乳老金”处为儿子拉皮条。这些故事让人感到恐惧,却彰显了母亲身上博大的“爱”。
最后,家族题材的传奇故事。《檀香刑》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为背景,通过叙述泼辣而深情的孙眉娘与其亲爹、干爹、公爹的恩怨情仇,生死较量,展示了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戏曲文化。一桩桩骇人听闻的血腥酷刑,一曲曲粗犷而惊天地、泣鬼神的猫腔,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作者以他高超的小说技能,用心用情讲好了这个完整而精彩的“中国故事”,张扬人们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与悲壮。这种中国民间的传奇故事,是民族的悲歌,也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样本。
人物塑造上“去英雄化”关注小人物。《蛙》《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尘埃落定》等家族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的英雄人物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文本注重刻画小人物,充分揭示小人物身上的高贵品质,余占鳌、赵甲、司马库、我姑姑等人是当时社会中普普通通,平凡而又渺小的人物,但这些小人物身上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大”精神。赵甲是个“刽子手”,从事着“最卑下”的职业,却有着非凡的敬业精神,为了练好行刑技术,赵甲买来猪,刻苦训练自己的刀功,让行刑技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先割哪里、后割哪里、条理清晰、逻辑井然;节奏快慢、力度大小都恰到好处;动作优美、干净利落、富有观赏性;五百刀“罪犯”毙命,一刀不多、一刀不少,最后一刀,刀落人亡。再者赵甲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他清醒的认识到刽子手这个职业是非常卑下的,与乞丐绝没有什么两样,干这一行是为了谋生,因此每年他都挤在乱哄哄、脏兮兮、歪七扭八的乞丐队伍中去城隍庙抢和尚们布施的粥,仰望上苍的同情与怜悯,这是何等的自醒!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赵甲心中有国、心中有家,他自觉地把自己行刑的水平与大清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行刑是为了震慑不法分子,宣扬大清国的国威,体现大清国的精、气、神,维护大清国的国家利益。《蛙》中我姑姑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非常深刻,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姑姑内心倍受煎熬,却能背负误解、忍痛割爱、大义灭亲、毅然决然的执行国家的计生政策,付出了巨大牺牲!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我姑姑身上的“大”精神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家族小说中,宏大主题、英雄主题被多义性、模糊性主题消解;宏大叙事被人物故事消解;英雄形象被小人物形象消解;战争、土改、合作化题材被平民百姓题材消解;崇高美被悲剧美、喜剧美、黑色幽默等消解。
三、个人话语的重建
个人话语是与集体话语相对的一个概念,前者侧重叙述人物故事,后者侧重叙述宏大历史;从人物形象上看,“个体话语”叙事在塑造人物方面特别强调“这一个”,强调独特性与典型性。“集体话语”则强调英雄人物与工农兵形象塑造,导致人物“类型化”与“雷同化”。个人话语的重建努力使小说创作重回“人学”本位,创作主体重回人道、人情、人性立场,尊重人的价值,关怀人的命运。
集体话语的主导。在宏大主题的高压下,“我们”代替了“我”,人物形象被模式化,“十七年”文学塑造了许多工农兵出身的“英雄形象”来确保文学的政治追求与政治属性。由于强大的意识形态介入作家的创作,在文本主题上、人物塑造上理念先行,根据预设的先验主题展开人物活动成为这一时期“集体话语”叙事的重要特征。革命过程也被书写成合乎历史规律的既定路线,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基本上只有一个相似的结果,以“大团圆”的胜利方式激励鼓舞读者。这种“集体话语”叙事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把人民、把工农兵看得过于简单,把他们心灵世界的要求和灵魂的挣扎简单化甚至庸俗化。“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文本《创业史》对“家”的讲述是按照这样的路线来进行的,从讲述“我家”的故事到讲述“我们国家”的故事,“家国同构”成为“集体话语”叙事的一个重要表征。文本中“家”的观念被“国家”所替换,人物在革命大家庭中获得了安全感。如主要人物梁生宝的行动很少和小家发生联系,梁生宝经常开会、搞活动,他与家的关系被淡化了,以至于我们感受不到他和自己的家庭有多少联系。从亲缘关系来看,梁生宝很少与父亲梁三老汉及母亲聊天,更勿论精神上的交流。梁生宝是蛤蟆滩革命大家庭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精神与实际行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革命大家庭展开的。除此之外,《创业史》有意淡化蛤蟆滩千丝万缕的家族渊源。郭振山依靠郭家的血缘关系最后被证实不仅不可靠,还成为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羁绊。当蛤蟆滩的贫农陷入困境,富农姚士杰、中农郭世富不肯借粮食给困难户时,郭振山一筹莫展,不如逃难来的梁生宝。无论是革命觉悟还是工作能力,梁生宝都略胜一筹。“国家”的话语强权完全占据了主导,削弱了其他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形成“个体——国家”的单向联系,成为有追求个体的精神归宿。但是个体与家庭的联结遵循的是天然的血缘,在个人走向新的国家时不免会有惶惑和陌生,因此,“集体话语”叙事下的代言人这时就会站出来,正确指导这些孤独的个体聚集在一起,使他们放弃个人抗争的方式,投入革命洪流中,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团圆”模式。
个人话语空间的重建。文学创作的边缘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既是政治——文化一体化社会体制解体后的被抛现象,也是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主动撤出文化中心地带的表现。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这样一些边缘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任何政治权威,站在边缘位置审视与批判社会现象和文化传统。如鲁迅的打破“铁屋”“掀翻这厨房”的立人主张。胡风的“现实主义创伤”“精神奴役说”。但后来随着阶级学说和“皮毛理论”的盛行。知识分子边缘化处境被推向了极致,启蒙思想的传播者一变而为被启蒙的改造对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当代家族小说作者们走出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怪圈,自觉地行使个人话语权力,把文学创作从主流意识形态和公众代言的“他者”角色中解放出来,进入到另一个鲜活自由的话语空间,实现了个体的重新定位。随着市场因素的大举介入,文学迅速从意识形态中心撤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进一步加剧,甚至沦为“自言自语”似的独白,落得“无人喝彩”的境地,家族小说的个人化写作即是证明。当代家族小说作家们普遍意识到文学创作的边缘化,他们坚持从知识分子的再启蒙立场展开小说的创作,在当代社会中形成一个自由生活的阶层,以自由的精神、理性的向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评判现实、甄别优劣和重建价值的作用。
当代家族小说之所以如此引起研究者与文学界的关注,是因为她代表了经历过“十七年”“文革”历史过程的一代人对“自我”的确认。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怀、对人的心灵和生命的尊重,是“文革”灾难在他们这一代人心中唤起的最珍贵的觉悟。他们反抗迷信,反抗专制,反抗愚昧,反抗群我,尊崇个人,体现文学是人学的理性精神,面对现实进行理性批判,走入历史深处,以极大的勇气表达对民族历史及个人命运的思考。正是这种人的意识的觉醒与“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在文学创作中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与深化。当代家族小说的创作与“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实现了遥远的对接,重建了个人话语空间。
个人话语重建的代表文本。 当代家族小说创作有力反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创作经验,继承了新时期朦胧诗创作的光荣传统,重新确认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作为个体的人都生活在“国家”“集体”“绿叶”“螺丝钉”等“大我”观念中,不把个体的生命需要和生命祈向当回事。诗人顾城深刻的概括了这一现象:“我们过去的文艺、诗歌,一直在宣传另一种非我的‘我’,如我在什么什么面前,是一粒沙子、一颗铺路石子、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总之,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会思考、怀疑、有七情六欲的人。如果硬是说,也就是个机器人,机器‘我’。这种‘我’,也许只有一种献身的宗教美,但由于取消了作为最具体存在的个人的人,他自己最后也不免失去了控制,走上了毁灭之路。新的‘自我’,正是在这一片瓦砾上诞生的。他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他相信自己的伤疤,相信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相信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8〕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以“个人话语”为主导的小说叙事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十七年”时期大量以“集体话语”面貌出现的长篇小说建构方式。小说以留学海归知识分子倪吾诚一家人为描写对象,揭示了倪吾成追求个人价值与尊重的艰难而又心酸的生命历程。尽管倪吾诚千方百计想摆脱包办婚姻,但是包办婚姻的枷锁最终还是套在了他的头上。婚后不久,倪母亡故,他变卖家产,出国留学,两年后回归故里,在北平一所大学任教。倪吾诚有一些“洋理想”“洋知识”但缺乏能力,他深爱妻子和孩子,为吃上一顿好一点的饭菜并给孩子们买份礼物,到处借钱。倪吾诚喜欢酒肉,喜欢舞会,喜欢洗澡,喜欢西洋文明,由于留学的经历,他觉得西洋文明比中国好上百倍,对西洋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心理认同。倪吾诚也曾试图给子女们一些“洋”知识。教女儿挺起胸走路,带儿子上澡堂,给他们买洋玩具——活动变人形。可惜,这一切家人群起攻之,故收效甚微。倪吾诚的这些爱好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的合理需求,是从理想、国家、英雄、集体、沙子、铺路石、螺丝钉等集体话语下解放出来的具体表现,是当代家族小说抛弃宏大主题回归个人价值与尊严的具体体现。由于岳母姜赵氏和婆姐姜静珍的介入使倪吾诚的家庭生活变得乱七八糟、支离破碎,他每天都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几乎绝望。他逃到解放区,解放后终于和姜静宜离婚,但再婚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幸福。在一次次运动中,他如小丑般热情高昂地赞美领袖的英明,避免了不少皮肉之苦。这是倪吾诚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自保的一种策略,让读者深深地体会到人的价值与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残酷。在倪吾诚那里“国家”“集体”“社会”等“大我”观念,沙子、铺路石、齿轮、螺丝钉等“无我观念”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倪吾诚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是新时期文学对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重新确认,是作家摆脱宏大叙事,宏大主题重建个人话语空间的具体体现。
四、结 语
与主题呈现相似,当代家族小说在美学上呈现以下特征:由英雄意识高涨到平民意识回归;由崇高美到悲剧、喜剧、黑色幽默、滑稽等;由宏大叙事到家族叙事;由单一的敌我矛盾冲突到矛盾冲突的纠结缠绕;由单纯的审美到“审美与审丑”并存的多元化审美。总之,家族小说主题呈现上的特点体现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整与文学向本体的回归。
注释:
〔1〕童庆炳主编:《文艺理论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2〕《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7页。
〔3〕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4〕〔5〕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6〕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7〕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31页。
〔8〕顾城:《请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第30页。
〔责任编辑:黎虹〕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思维变革与制度创新”(批准号:15YJA820030)和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批准号:15SKG01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两江学者”团队课题资助。
王怀勇,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宋二猛,法学硕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