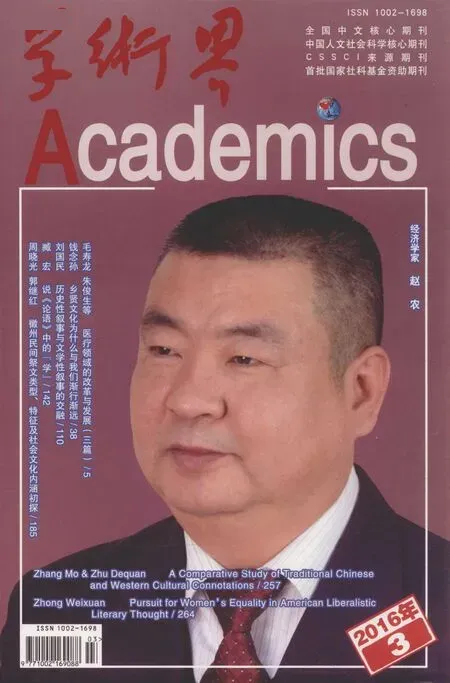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交融
——兼与傅修延教授商榷
○ 刘国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 北京 100089)
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交融
——兼与傅修延教授商榷
○刘国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北京100089)
历史文本以历史性叙事为主,交融文学性叙事。虚构并非文学性叙事区别于历史性叙事的本质特征。“史有诗心”要比“史有诗衣”“虚毛实骨”贴切。历史性叙事的基本特征有四:第一,叙述历史事实;第二,骨架性、概略性叙事,较少涉及血肉;第三,断裂性、跳跃性叙事,难以构成一个结构完整的故事;第四,外在性叙事——重视人物行动的描写而较少透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中,以史家的叙述语言为主,语言直白、明确而少有隐曲委婉的言外之意。在《史记》《汉书》中,《汉书》的历史性叙事较强,文学性叙事较弱,可称为典范的历史性著作;《史记》的历史性叙事弱于《汉书》,文学性叙事强于《汉书》,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的“诗心”“文心”。
虚构;史有诗心;历史性叙事;文学性叙事
叙述或叙事,即通过对某件事情或某些事情依时间顺序的描述,而构成一个可以理解的场景或有意义的文本结构。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共同特征是叙述或叙事。文学文本的叙事主要是文学性叙事。历史文本的叙事主要是历史性叙事,也交融文学性叙事,即所谓“史有诗心”“史有文心”。〔1〕
一
叙述或叙事分为历史性叙事和文学性叙事。历史性叙事和文学性叙事各自具有什么特征呢?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傅修延在《先秦叙事研究》一书中说:
虚构是文学性叙事区别于历史性叙事的本质特征,叙事中的虚构性因素多到一定程度,它的性质就会由历史向文学转化,由实录性叙事向创造性叙事(creative narrative)转化。历史性叙事和文学性叙事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前者要求尊重历史真实,后者则可以驰骋想象,创造出艺术中的“第二自然”。〔2〕
《左传》中含有较多虚构成分固然已为不争之论,但这部史著中事实与虚构是怎样交融互渗,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节标题在钱钟书“史有诗心”之语上稍作改动,“史有诗衣”表示左氏是披着文学大氅的历史骑士,说得更精确一些,《左传》叙事是“虚毛实骨”——事实为骨架而虚构作毛羽。《左传》中的骨干事件大体真实,但敷衍其外的微细事件未必皆可信……“史有诗衣”也好,“虚毛实骨”也好,都是强调《左传》中历史与文学是体与衣、骨与毛的关系,因为就本质来说《左传》仍属历史。〔3〕
傅修延认为,历史性叙事是叙述历史的真实,真实是历史性叙事的生命;文学性叙事是叙述可能的生活真实,虚构是文学性叙事的生命;因此,虚构是文学性叙事与历史性叙事的本质特征。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
其一,历史性叙事要叙述历史事实,这不容置疑;但文学性叙事主要是叙述“生活的真实”,也可以叙述历史的真实。所谓“生活的真实”,即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虽有别于实际发生的事情,但也是基于生活事实的基础上。文学性叙事并非一定要以虚构为主,而排斥对真人真事的叙述,如现代流行的“非虚构文学”、报告文学类等纪实文学。以虚构为主的叙事,并不是历史性叙事,也未必是文学性叙事,因为文学性叙事还有其基本的特征。因此,把虚构作为历史性叙事和文学性叙事的本质区别,是不合理的。
历史文本以历史性叙事为主,也交融文学性叙事。文学文本主要是文学性叙事。历史性叙事要叙述历史的事实;文学性叙事以叙述生活的真实为主,也可以叙述历史的事实。文学性叙事主要不在于叙述真实的事件还是虚构的事件,而在于叙事是否具有文学的特质。高小康说,“从美学的角度看,历史和文学的根本区别不是在于二者的虚实比例究竟应当如何分配”,而是历史叙事中的故事不能称为真正的故事,只能称为故事片段,因为它们不具备独立完整的结构,而文学叙事的故事有独立的时空结构。〔4〕虚与实不是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本质区别。历史性叙事是断裂的、跳跃性的叙事(下文详论),并不能构成前后相连的完整故事结构;这是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重要分别,并非是“根本区别”。常森在《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一书中说,《左传》是历史质素、文学质素和经学质素的统一;《左传》的文学质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塑造、再现了一批极富个性的人物;二是非常注重细节的描写;三是有比较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四是作者根据人物的个性,利用悬想来设置故事。〔5〕常森列举的前三项是文学性叙事的基本特征。列举的第四项涉及《左传》的虚构,从其具体论证来看,主要侧重于人物之个性化语言。《左传》之代言和拟言,有虚构的成分,但着重再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因此,在常森看来,文学质素的基本特征并不主要在于虚构。要之,笔者不赞同傅教授之谓“虚构性(fictionality)是文学性叙事的生命”。〔6〕
其二,傅教授把《左传》之叙事,命名为“史有诗衣”“虚毛实骨”,即其叙事大体真实,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是虚构的,像穿在身体上的衣服,像附在骨头上的皮毛。笔者首先认为,《左传》的文学性叙事并不只是表现在虚构上,文学性叙事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具体生动的细节、个性化的语言、亲切感人的场景和人物形象等。笔者其次认为,历史文本中的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是交融在一起的,正如傅教授之谓“事实与虚构的交融互渗”,〔7〕而不能认为文学性叙事像衣服或皮毛那样可从历史性叙事之体或骨上脱下或剥下。钱钟书先生所谓“史有诗心”,即史家的诗心随处流露,具体地融化在历史性叙事中。“史有诗心”要比“史有诗衣”“虚毛实骨”贴切。
二
傅修延认为,《左传》“诬谬不实”有两个层面的显现,一是浅层的,主要表现在左氏对神异的记述,包括卜筮、灾祥、鬼怪、报应、梦兆等;二是深层的,《左传》在叙述真人真事时有一定的想象虚构成分,例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等,且《左传》所记历史人物的语言,多是“代言”“拟言”。
《左传》宣公二年:
宣子骤谏,(晋灵)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8〕
鉏麑慨叹之言,是心口相语,涉及其心理、语言,第三者无人得之,是钱钟书先生所谓“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9〕乃是出于史家的想象和虚构。历史文本中人物的语言,其虚构最为典型。一是历史人物的语言在当时很难记录下来;二是历史人物的自言自语,第三者无从知晓。因此,钱先生认为,史家的记言,“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10〕“想当然耳”,即虚构。钱先生进一步指出:“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毎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11〕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左传》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想象和虚构,但其想象和虚构契合历史的特定场景与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身份,而有合理性;二是历史人物的语言最能体现史家的虚构,其历史人物的语言有个性化的特征。因此,钱先生说:“顾此仅字句含蓄之工,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尤足为诗心、文心之证。则其记言是也。”〔12〕“史有诗心”“史有文心”,不仅是指历史文本的语言有委婉含蓄的文学性特征,即“微”“讳”“隐”;且单从“代言”上来说,一方面是指史家通过想象而虚构;另一方面是指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即契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境,从而表现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诗心”正在于此,这是文学性叙事的根本特征。傅修延把钱先生之“史有诗心”理解为纯粹的虚构,即“史学家多斥史著中的虚构为谎言,文学家则称之为‘史有诗心’”,〔13〕而改成“史有诗衣”“虚毛实骨”,似没有把握到文学性叙事的实质。虚构只是文学性叙事的一个特征,文学性叙事有更为重要的特征——具体生动的细节、个性化的语言、亲切感人的场景和鲜明的人物形象等。如果“代言”仅仅是想当然的虚构,不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则不是文学性的叙事;如果虚构的事件没有鲜明感人的形象,则不是文学性的叙事。
就历史文本的虚构性而言,某些具体事件的不实成分还是次要的,而故事结构的虚构才是主要的。史家从无数的历史事件中选择出一定数量的事件,根据某种情节安排的模式,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故事。首先,史家选择了一些真实的事件,舍弃了另外的一些真实事件,故在总体上是不实的。其次,同样的一组事件,史家在不违背时间顺序的前提下,可采用以下的方法——使某些事件核心化,而将另外一些事件排挤至边缘的位置;或把一些事件看作原因,而将其余的事件作为结果;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样的一些事件;聚拢一些事实而拆散其余的——而构成几种故事,体现出几种不同的意义。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认为:“同样的历史系列可以是悲剧性的或喜剧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关键问题是多数历史片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造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14〕因此,史家的这个做法不是在历史中发现故事,而是从根本上说是文学的做法,即创造故事。故事首先要具有曲折动人的完整结构(情节),故结构的虚构是历史文本的最大虚构。周作人引作家废名之言说:“我从前写小说,现在则不喜欢写小说,因为小说一方面也要真实——真实乃亲切,一方面又要结构,结构便近于一个骗局,在这些上面费了心思,文章乃更难得亲切了。”〔15〕傅修延只注意到历史文本中具体事件的虚构、人物语言的虚构,而未论及结构的虚构,是不足的。
三
在先秦两汉的历史文本中,因文史不分,故历史文本中的叙事方式是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交融,且以历史性叙事为主。我们可以根据《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文本,归纳出历史性叙事的基本特征。
(一)历史性叙事是叙述历史事实。晋人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归纳《春秋》之体例五,〔16〕其中,“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首先,直与曲相对,直书其事而不隐讳之,即直接明白地叙述史实。其次,叙事而不污,“污”,《孟子·公孙丑上》谓“污不至阿其所好”,污,洿,“夸”之假借,即《庄子·人间世》之谓“溢言”。不污,不夸大修饰而言过其实,即叙事要符合历史实在,信而可征。
(二)历史性叙事是骨架性叙事,较少兼及血肉。所谓“骨架性叙事”,一是主要叙述大事件和大人物;二是概略性叙事。《春秋》是典型的历史文本,其叙事方式具有这两个特点。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所叙之事是较大的事件,且叙事概略,只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消极意义上,这不能如实地叙述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的真实本是丰富复杂的;但积极的意义上,这不违背历史的真实,避免因详叙而需要想象和虚构。《左传》对此事件的过程及其因果有详细的叙写,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有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有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有史家的道德评价;这些内容所含的虚构成分较多。因此,《左传》的叙述融进了较强的文学性叙事。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司马迁主要记录张良行事中关涉天下存亡的大事件、关键事件。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往事如烟,无数的小事件、小人物微不足道,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只有大事件和大人物能留存下来,且也是骨干,那些血肉多已腐烂殆尽。二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风云中,无数的事件和人物宛如天上的繁星,不可胜记,只有大事件和大人物才能进入史家的法眼,否则不胜纷繁。三是概略性叙事最大可能达到不违背历史真实的结果。
(三)历史性叙事是断裂性、跳跃性叙事,一系列事件之间缺少内在的有机联系,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春秋》《左传》等编年体史书,是“依时叙事”,史家按时间顺序叙述重要的历史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同一事件在此后的数年中仍有发展,或一系列事件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但因《春秋》《左传》的编年体例,它们被分割在不同的年代里,湮没于无数的事件中,其发展过程、因果联系湮灭难见。例如《左传》桓公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一言一行的两个细节,写尽了他对孔父之妻神魂颠倒的情状。《左传》桓公二年:“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娶其妻。”这两个事件有一定的因果联系,但被湮没在诸多的历史事件中。《左传》分别在僖公四年(重耳避乱出逃),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流亡列国),僖公二十四年(重耳回晋为君),僖公二十七年(重耳中兴晋室),僖公二十八年(重耳败楚称霸),叙述了重耳一生的主要事迹。这些主要事迹被分割在不同的年代里,被分散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而很难展示其曲折发展的历程。《史记》《汉书》,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历史著作,主要叙述历史人物一生的重要事件,许多中小事件或为原因或为结果而遭到遗弃,这往往割断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而有跳跃性,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遭际也难以得到脉络分明的展开,且不能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完整性。《春秋》的叙事是典型的历史性叙事,王安石谓之“断烂朝报”。
(四)历史性叙事是外在性叙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人物行动的描写,很少透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人物的行动是外在性的,一系列的行动推进事件的发展,故“动词为叙事文之眼”。〔17〕心理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能充分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是文学性叙事的基本特征之一。心理描写是叙述者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上,发挥其想象而予以虚拟;史家面对历史对象,只能采取限知角度叙事,难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否则即不实。历史性叙事只涉及历史人物的外部表情,很少叙述内在的主观情感。《史记·项羽本纪》叙述了项羽在垓下四面楚歌中与虞姬生离死别的场景。项羽悲歌慷慨,泣下数行,表现了英雄失败时一腔不平的悲愤,展现出英雄末路多情而无可奈何的心情。清人吴见思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史记论文》)这段文字是文学性叙事,浓烈地抒发了项羽在穷途末路时的复杂情感,文学是以情动人的。二是历史性叙事以史家的叙述语言为主,较少述写历史人物的语言。史家记事要比记言容易。古代没有录音设备,人物的语言容易消逝在历史的时空中;且人物的私密性语言,只有当事人知晓,其他人难以窥知。史家叙写人物语言,自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代言”“拟言”,是“想当然耳”,这就冒着违背历史事实的风险。且史家在述写人物语言时必须设身处地,根据人物的个性、身份地位以及当时讲话的实际语境来模拟人物的语言。这便给史家造成了相当多的困难。因此,历史性叙事是史家的叙述语言多、历史人物的语言少,所谓“事多言少”。史家的叙述语言往往枯燥无味;而历史人物的个性化语言,生动形象感人。三是历史性叙事的叙述语言是外在性的语言。外在性的语言直白、明确,没有隐曲委婉的言外之意。
文学文本的叙事方式是文学性叙事,其基本特征有四:
其一,文学性叙事可以叙述历史的事实,也可以描述生活的真实,但以描述生活的真实为主。亚里士多德认为:“两者(史家和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绘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8〕亚氏过分贬低历史的价值,历史当中也含有普遍性的规律。广义的诗即文学,其普遍性也是基于实际生活的基础上。
其二,文学性叙事要把骨架与丰满的血肉结合起来,具体、细致、生动地叙述生活的事件,从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
其三,文学性叙事要有完整的故事结构。文学性叙事重视叙述一系列事件之发生和发展的历程,形成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且各个情节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井然而有序,从而构成完整的故事结构。
其四,文学性叙事是内在性叙事。一是叙述者一般以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具体地展示人物之复杂的心理和情感,以揭示人物之立体的性格特征。文学性叙事的基本目的之一,是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物之独特、鲜明和复杂的性格特征,展示人物一生之曲折动荡的命运。虽然行动和语言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具有作用,但心灵活动的描写乃是揭示人物性格的核心手法。二是叙述者重视人物之个性化语言的描写。人物的对话是置于具体的语境当中,且根据不同人物的个性而设置,一方面能体现人物的个性品格,另一方面能展示具体、形象的语境。因此,个性化语言的较多运用,易于造就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三是文学性叙事的语言是内在性的语言,具有委婉含蓄、意在言外的特征,有隐喻、象征的意义。
四
《春秋》《左传》是编年体的历史文本。《春秋》之叙事基本上是历史性叙事,叙述的史实真实可信,所叙之事是大事记,是标题式的;叙事具有典型的骨架性、断裂性、外在性的特征。傅修延指出《春秋》叙事的三个特点:一是叙事依从时序;二是叙事简约凝炼;三是叙事体现倾向。〔19〕历史性叙事含有一定倾向的价值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价值倾向虽对历史性叙事的真实性有所贬损,但也是必要的。因此,历史性叙事是以叙事为主,价值倾向是次要的。后世多夸大《春秋》叙事“以一字为褒贬”的价值评价,范宁《春秋谷梁传序》谓“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归纳出《春秋》笔法之“五例”,其中,“五曰‘惩恶而劝善’”,即指《春秋》有是非褒贬的价值倾向。钱钟书先生说:“盖‘五例’者,实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20〕《春秋》文本并没有实现“五例”之目的。笔者认为,《春秋》有一定的褒贬倾向,但没有后世渲染得那样突出,故对叙事之真实性的影响甚小。《左传》是以《春秋》为纲,其叙事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叙事方式是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交融,但以历史性叙事为主,故《左传》文本仍是历史性著作。《左传》的文学性叙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不仅表现在虚构上,更表现在其叙事有较为曲折完整的结构,有细节的刻画,有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有生动鲜明的场景和人物形象等。
《史记》《汉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文本,其历史性叙事皆占主体的地位,因而成为历史著作。其中,《汉书》的历史性叙事最强,文学性叙事较弱,可称得上是典范的历史性著作。《史记》的历史性叙事弱于《汉书》,文学性叙事强于《汉书》,故《史记》比《汉书》有较强的文学性,更能表现司马迁之“诗心”“文心”。我们以《汉书·董仲舒传》为例来说明。
传记开始说: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21〕
传文接着详细地记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是文史资料的保存,占这篇传记内容的十分之八。
传文进一步叙述董仲舒之人生遭遇中的重要事件:一是对策;二是出为诸侯王相;三是言灾异;四是以修学著书为事等。这几件事情的叙述相当简略。作为西汉的大儒,他一生经历了文帝、景帝和武帝三朝,两次出任诸侯之相,其人生遭遇是动荡复杂的,但《汉书》叙事既文字量小又平淡无奇,文本与故事严重不对称。〔22〕班固的叙事又是断裂性的,事件之间缺少发生和发展的关系,更谈不上曲折生动,因而不能构成完整的故事结构。传文也揭示了仲舒的某些性格特征,“进退容止,非礼不行”“遂不敢复言灾异”“为人廉直”等,但过于简单,仲舒的形象平面而抽象。传文主要是史家的叙述语言(除《天人三策》外),基本上没有仲舒在特定语境中的个性化语言。因此,正是班固主要运用历史性叙事的方法,从而保证了《汉书》成为较为纯正的历史文本。
《史记》的文学性较强,司马迁在历史性叙事当中,较多地融合了文学性叙事。一般而言,史家如果特别喜欢传主本人,或特别喜欢传主的某些事迹,则往往狠下功夫,其叙事具体、生动、形象,而偏重于文学性叙事。韩信是司马迁最为欣赏和赞佩的伟大军事家,他的人生遭遇又是悲剧性的,深为司马迁所同情。《史记·淮阴侯列传》偏重于文学性叙事,例如萧何追韩信: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23〕
此一事件被后世小说和戏剧演绎成“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无疑受到了司马迁之文学性叙事的重要影响。此段文字主要用萧何和刘邦的对话组成,他们两人的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尤其是刘邦,其人是天才英雄,盛气凌人,且个性中具有艺术性的风姿,喜欢骂人但不伤人,悟性甚高,有灵活性。“上大怒”“上且怒且喜”“骂何曰”“上复骂”等描写了刘邦的情感表现及其发展历程。此事件的最后,叙写“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尤具有戏剧性和惊奇性,这完全是文学家的一腔胸怀。如果从虚构上来说,则刘邦和萧何的对话语言,正是司马迁根据具体的语境和人物的性格而悬想出来的。
总的来说,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有些篇章较多地运用文学性叙事,其文学性是强烈的;有些传记主要运用历史性叙事,文学性叙事较少,例如《樊郦滕灌列传》基本上是几位传主的大事记。这几位传主皆是楚汉相争时刘邦的重臣,不能不写,但他们并不为司马迁所激赏。在《史记》的同一篇传记中,各部分叙事也表现出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交融时之强弱的区别。例如《曹相国世家》,前后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曹参的战功,基本上采用历史性叙事,按时间顺序概略记录,没有涉及战役的具体描写,也没有表现曹参的精神个性,传文因而毫无生气。传记的第二部分叙述了曹参代萧何为相,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是司马迁最为赞赏的。此段文字最有精神,是曹参传记的精彩出色之处。司马迁较多采用文学性叙事的手法:一是重视细节的描写;二是写出曹参与惠帝、曹窋之间的冲突关系;三是以人物的个性化语言为主。最后,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说:
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司马迁认为,曹参只是一员战将,之所以功多,是因为跟随元帅韩信之后,这是对曹参战功的轻视;但对曹参代萧何为相后,继续实行的清静无为之道极为赞赏,故倾注感情,描写生动传神,这也造就了后世盛传的“萧规曹随”的佳话。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从《史记》之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的交融来说明。《史记》的文学性叙事不仅分量充足,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注释:
〔1〕〔9〕〔10〕〔11〕〔12〕〔20〕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165、165、166、164、162页。
〔2〕〔3〕〔6〕〔7〕〔13〕〔17〕〔19〕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211、212-214、273、205、175、182、178-181页。
〔4〕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
〔5〕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8-270页。
〔8〕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95-596页。
〔14〕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15〕周作人:《立春以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16〕“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治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成恶而扬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20页。
〔18〕亚里士多德:《诗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21〕本文引录《汉书》的文字,参见班固:《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2〕傅修延说:“一定的故事内容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文本篇幅与之匹配,才能传递故事包含的诸多信息,此所谓‘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也。”参见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23〕本文引录《史记》的文字,均参见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责任编辑:黎虹〕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清代桐城《诗经》学家马瑞辰学术渊源研究”(AHSK
Q2014D99),扬州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马瑞辰《诗经》学研究”(201310)成果。
于春莉(1977—),扬州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