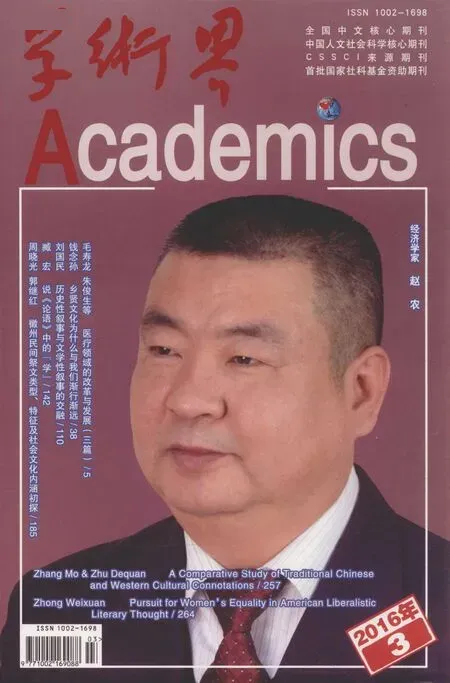《创业史》、“文学柳青”与底层形象呈现问题〔*〕
○ 钱 雯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61)
·学术批评·
《创业史》、“文学柳青”与底层形象呈现问题〔*〕
○钱雯
(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合肥230061)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创业史》已被反复讨论。一部并不复杂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时期,作了各种观念交锋的场地,结果使作品本身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学界提出“文学柳青”问题〔1〕“文学柳青”不仅是文学史问题,也是底层形象的文学呈现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底层不能自我表述,只能通过与知识分子建立对话关系才能表达自身。〔2〕这种说法是以利益表达为主要线索的,不能解决底层人的形象与尊严如何呈现的问题。《创业史》从文学的意义上回答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令人尊重的价值。
《创业史》;“文学柳青”;底层形象
1960年代的严、柳之争把柳青和《创业史》卷入文学评论的漩涡,并对《创业史》的接受造成长期的后果,影响至今。
考察这场作者与评论者之争,其中包含建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共同意愿,但是,从文学上理解规范还是从规范上理解文学,划出两者思想分野。评论者的认识会随着政治的要求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事实上也是如此;作者的立场则通过作品的内在完整性和自我解释功能表达出来,比较起来,更具有稳定性。从《创业史》本身出发,柳青的意见其实更值得尊重。
柳青不接受严家炎对梁生宝形象的褒贬意见,还包含对评论者“特殊理解和特殊爱好”,即评论的主观性的批评。经历1943-1945年的“转弯”,尤其是1953年后移居皇甫村的生活,柳青把他的生活与创作从根本上转换到对象世界,由此发生对文学深刻和彻底的理解。这个“文学柳青”形象,在严、柳之争后,与柳青的作品一起被评论界所忽视。
严、柳之争还有另一条线索,柳青未作直接回应,即对梁三老汉形象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柳青与鲁迅的联系,〔3〕也值得深入探究。
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与柳青的问题
在我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首先在鲁迅的小说中得到呈现,其呈现的困难和问题也在鲁迅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尖锐。这是理解“文学柳青”的一个背景。
1935年,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中,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他所称为“乡土文学”者,指侨寓北京的作者对乡土的叙述。〔4〕按照这个定义,鲁迅的小说大部分可归入“乡土文学”范围,如《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作为以“启蒙”自任的小说家,鲁迅在乡土文学中,不仅面临启蒙他人的问题,而且要面对启蒙者自身的问题。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它考验着创作的真诚。比如:启蒙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启蒙他人(农民)?以“启蒙”自命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做好对自身的启蒙?在启蒙者与他人(农民)之间,真正需要对方的是哪一方?事实上,启蒙者本身所遭遇的困难在鲁迅的小说中占据更大的份量。比如,小说所批判的农村人如孔乙己、阿Q、七斤等,很难说不是启蒙者自己;再如,对启蒙对象的批判最后又转回到对启蒙者自身的怀疑上,如《狂人日记》《故乡》《祝福》;第三,《在酒楼上》《孤独者》诸文,更是把笔力集中到启蒙者身上,直面启蒙者的精神困境。在启蒙者和启蒙对象之间倚重倚轻的描写,使鲁迅小说中农村人形象非常不稳定,甚至给人一种难以达到对方的陌生感。此在《故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与杨二嫂之间的“隔膜”,直至与农村生活世界的“隔膜”,划出了“我”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启蒙”从何说起呢?是不是仅限于个人的意志?启蒙的意义又何在?是不是自蔽于自身?《故乡》的写作不在于解决闰土的问题,而在于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其中的农村和农民形象不是从对象世界自身活动起来的。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小说结尾发出“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那一段议论,这段议论是针对“我”自己并为了“我”自己的。
关于“乡土文学”,鲁迅有一段评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5〕我觉得,涌动在鲁迅“乡土文学”中最内在最积极的东西,即是他所说的“乡愁”,这是经过启蒙式自我磨洗后出自个人“胸臆”的“爱”,这种“爱”通过对乡土的否定也是对启蒙个人主义的否定被“隐现”、被指示出来,它无法现实地呈现,因此无法支持来自乡土本身的书写。基于这个理解,我认为,鲁迅以后,不再有“乡土文学”,具体地说,不再有以纯粹作家(知识分子)身份书写的、启蒙式“乡土文学”。
柳青1942年写了两篇农村和农民题材的小说:《在故乡》与《喜事》。两篇小说的结构形式与鲁迅的“乡土文学”相似,即写“我”与“故乡”之间的事;其中的问题也相似,交织着乡土批判与自我反省的意味。就其自我反省的一面来说,小说远远没有达到鲁迅小说的自觉和彻底性。因此,在整体上,两篇小说是比较“光滑”的,它们涉及非常丰富的农村生活素材,但缺乏把材料贯穿起来并为之灌注内在生命的明朗的“意图”。这是关涉对文学的理解的问题,即“为什么”的问题。我们看《在故乡》写七老汉死后,发生在乡间的一场对话:
“他的那些本家也是……”伯父说,“老汉死后不过头七,就往他住的那破土窑子里满满地填了一窑子干草。”“人家嫌堆在外面雨淋哩,”父亲却冷漠地说,“雨淋了,生了霉,牲口不肯吃。”“窑还用说,”我的一个表兄走来,“七老汉死后,三晌地归还了公家,就不知有多少人去问乡长,要租得种哩……”“噢,地好么,”父亲立刻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爱土地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但随即又冷淡下来,说,“问不问,还是原租户种,没个旁人种的道理。”
我听了这种对话,倒有悲怆的感觉。七老汉生在富贵家门,却过了一生赖皮狗的生活;最后还是这样的下场。但也无法,故乡既变做另一个世界,时代便铁面无情地丢弃了他。
父亲的“冷漠”和“兴趣”显然也反映着伯父与表兄的心情和态度,“我”的“悲怆”感觉却从这场对话上“滑”过,它关注七老汉自身的命运,这个命运却不是对话中的众人造成的,接着发生的时代感更与这场对话无关。对于父亲、伯父、表兄,对于七老汉,对于“故乡”,“我”是旁观者,而非事中人,“我”有取于农村和农民的批判材料是从“我”的眼光、根据“我”的思想感情选择出来,并用以表达“我”的心情和态度的,这种心情和态度的形成与农村无关,与农民无关。进一步来说,在鲁迅的小说中,强大的自我反省的力量把启蒙者自身塑造成自我运转的形象,这是鲁迅小说的内在统一性,而在柳青的这篇小说中,“我”的形象本身是可疑的,它缺乏自我解释,也就是说,缺乏把“我”的各种感觉和态度凝聚在一起的内在力量。这也就决定了“我”无法把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世界作为整体来理解和呈现。所以,与自我形象的散乱相一致,小说中写到的农村和农民形象也是新鲜而散乱的。下面是接着那场对话的叙述,也是小说的最后两段:
正月初五,我便又束装出门了。往年在元宵节后,村人才开始劳动;今年因为节令都早,我走时,村里已非新年气象了;阳光已经照得人肌肤作痒。各处的住宅旁边,都有人将棉袄脱到一边,在场子里碎粪。那健康的肩背上,汗水反射着阳光。村道上,常有人赶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往山里送粪;因为冰雪开始解冻,路途十分泥泞,所以处处响着喊驴的声音,警告它们:“滑啦!滑啦!”
我离开这美丽的故乡,渐行渐远;但却时而回转头来,依恋地看看那些山水,树木和人家……〔6〕
这里传达着柳青与农村、农民的生活世界心心相印的敏感,埋藏着《创业史》形象的萌芽,但也深深地包涵着写作者对自我形象的并非自觉的爱惜。这种爱惜,一方面阻碍柳青通向鲁迅的道路,一方面阻碍柳青思想和感情的农村化和农民化。1980年,陆耀东评论《在故乡》时说道:“这篇作品存在的问题,不只是艺术上的,也有认识上的问题,思想感情上的问题。我们从一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可以发现:他们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理智上,也知道要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一切人、一切社会现象,然而碰上较复杂的人和事,就往往用小资产阶级的悲天悯人的观念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7〕评论切中肯綮。这个时候柳青在创作上存在的问题,是“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包含对文学的理解的问题。在小说家的世界和农村、农民的生活世界之间,他还没有找到思想感情的落脚点,因而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
在这个背景上可以看出《创业史》的转向及这个转向的文学意义。从柳青来说,他通过《创业史》写作,彻底解决了思想感情的问题,即不仅完成生活实践的对象化,而且找到通向艺术创造对象化的道路;从文学上来说,让农民自己站出来,让农民自己表现自己,这个在鲁迅那里未曾实现的目标,经《创业史》崭露出它现实的轮廓。如果限于从鲁迅“乡土文学”提出的问题来考察,那么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农村和农民,前有鲁迅传统,后有柳青传统。
《创业史》农民形象的呈现
毫无疑问,柳青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忠实信仰者,这个信仰之于柳青的意义,不是政治条文或者艺术条文的指导,而是源自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无限接近的体认,是建立在思想感情上的服膺和觉悟。在《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一文中,柳青写道:
历史向现代中国作家出了三个试题:(一)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二)是革命感情上满腔热情地接受呢?还是由于当今中国社会性质的限制不得已接受呢?(三)是仅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观点的角度上接受呢?还是同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观点的角度上接受呢?
柳青把所有这些问题,归结到“作家的生活道路问题”上,把纸上的条文,转变为作家在生活实践中、在思想感情上自觉的选择。〔8〕此选择有其不容置疑的道理。任何时候,文学上关于“为什么”的选择,都不是由作家个人决定的;文学世界中各类人物的地位与秩序,也不是由文学本身决定的。启蒙式“乡土文学”中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关系秩序及启蒙者的力量优势,传达着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为之所决定,鲁迅依据这个传统写作并在文字上摧毁了这个传统;同样,《讲话》出现的背后,有着整个时代的巨大变动,政治、社会秩序的巨变颠覆了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甚至颠覆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它使农民形象有力地、有声有色地走上政治、社会活动的前台,从而有可能作为、并且要求作为独立自主的形象得到文学的尊重,走上文学的前台。时代的巨变重新铸造了文学的观念,柳青在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体会”并捉住了它。
但摆在柳青面前的困难之大是难以想像的。一篇研究论文写道,《创业史》对农民的描写,需要克服两个难题,一是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趣味如何“扭曲”以适应对农民的描写,二是如何接着赵树理关于新文学大众化的工作,又吸收“五四”新白话在生活表现上的优势,在农民描写的语言与趣味上实行“一次飞跃”。〔9〕在柳青的创作实践中,可能确实存在这两个难题,但最关键、最基本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从生活到艺术上对农民的“发现”。必须把信任交托给农民,让农民自己活动起来,农民形象才可能在文学中站立起来。为此,柳青必须研究农民,并在生活与文学中寻找到支持农民精神生活和行动的内在的力量,此端赖他作为皇甫村民的生活,也有赖于他对艺术传统的领会及在艺术表现上的创造力。〔10〕《皇甫村的三年》忆及他在1953年开始推动互助合作的事:
我发现我们的要求和事实的距离很远。在七个行政村里只有三个村达到了目的,而且一村搞起不久就散了,重点组长刘远峰远远地看见我就躲。
我追上他,他痛苦地发誓说人心不一,他这辈子再也不闹这事了。插秧的时节,有一天晚上,我帮助十字村郭远文重点互助组开会解决纠纷,他们说找不到副组长郭远彤。我满村打听,谁也没看见他。我到他家里,门上挂着锁。我用手电棒往里照,他在炕上用被蒙着头睡了。他在多半夜长的会上,除了重复坚决退组的话,再没吭过一声。结果这个组退出了两户,郭远彤不久搬到三村去住了;到那里,他进了一个寡妇的门。这个在土地改革中分配果实的时候被人称为大公无私的郭远彤,过他的小日子去了。我没办法把这个穷到三十几岁讨不起老婆的生产能手巩固到互助组里,是我去年最难受的事情。〔11〕
实际工作中数说不尽的挫折和无力感,实实在在地说明:皇甫村的历史行进在“我们”之外,不深入到皇甫村民的生活世界,不去探索、发现、理解并尝试解开他们的生活之结,不去体认他们“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则不能理解和解释皇甫村的历史进程,不能理解和解释由皇甫村民们创造的新时代和新生活。这是《创业史》的源泉,农民形象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创业难……”这一句“乡谚”,印在《创业史》的扉页上。小说家深刻地发现并极为真切地感受到,支持闰土们的生活并改变他们命运的力量不在他人身上,不在另外的世界里,而是蕴蓄在他们自身之中,这种力量乃被苦难所激发,与苦难结伴而行,已经存在几千年了。“题叙”以一幅宏大的场景和穿入历史深处的叙述,把这种力量抉发、指示并塑造出来。
“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题叙”以这句话开头。“饥饿史”3个字组成整个“题叙”的关键词。这个词向前延伸进农民几千年的受难史,在眼前则展开为梁三父子和宝娃他妈在苦难面前不屈不挠的生存选择和意志。“题叙”没有旁观者,叙述人的存在也无足轻重,整个故事在苦难与遭难人之间进行,每个人作出的选择被苦难本身所决定,也是向苦难作出的不得不然的抗争。四十岁的梁三为草棚院里宝娃他妈带来的“生气”感到不知所措,他像孩子一样兴奋,夸下“创立家业”的海口。苦难曾经压倒了他,外乡女人的到来,唤醒他的热情和信心,他从对抗苦难中寻回失去的尊严。“瘦骨嶙峋”的宝娃他妈,在立婚书的夜晚说道:
“我说,宝娃他叔!这是饿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费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书,没这婚书,都一样嘛。千苦万苦,只为我娃……长大……成人……”〔12〕
这种向苦难求取生存的意志,排除了加于故事之上的一切人为增附。宝娃他妈不需要婚书,不需要立婚书的场面和仪式;对整个故事来说,不需要故事之外的眼睛:鼓励,同情,批判,歌颂……跃动在苦难深渊中的力量剥落叙述的光华,向苦难展开了它真实、凛然的形象,——这是农民自己展开自己的形象。“题叙”奠定了《创业史》的叙述风格:这部“生活故事”,仿佛早就存在于那里,已经进行了几千年,还在继续进行下去,叙述人的任务不过是修剪这个故事的枝丫,使它固有的尊严在纸上成形。
1961年有一篇文章论“题叙”:“这种在整篇前冠以‘楔子’‘扣子’或‘得胜头回’的手法,几乎是我国所有白话小说的程式。……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必定有个综览全篇、俯瞰整体的‘题叙’。而我以为《创业史》的‘题叙’是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巧妙而有效地继承与发展了这一艺术传统的。”〔13〕这是从艺术形式上立论。从柳青所面临的任务看,他从“题叙”中准确、深刻地捕捉到农民在苦难的土地上自己站立起来的形象,明确、清晰地找到了叙述农民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农民真正成为蛤蟆滩世界的主角,成为文学世界中令人尊重的主角。
《创业史》人物由此展露出属于自身的深度,并给予我们异乎寻常的陌生感。这是以主人身份挺立在文学世界中的农民带来的陌生感,是与闰土给予我们的不一样的陌生感。在《故乡》中,“我”的世界被反复追问,闰土的世界则隐在干枯的面容背后,与我们之间隔着无法穿透的“厚障壁”。在《创业史》中,叙述的障碍被撤去,这个世界被层层打开了:每个人都有一部受难史,每个人都是在与苦难的抗争中争到现在的位置;每个人都在争取有尊严地活着,并为此经受极其复杂的心灵搏斗;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是一个令人尊重的世界,他们的言语行动,表现出各各不同的面貌;这些感觉世界的现象,被他们自己的历史和心理所解释,却令我们感到奇异而陌生。这些人包括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包括梁三老汉、王二直杠、梁大老汉,包括郭振山、郭世富、梁生禄,在广泛的意义上,包括富农姚士杰、兵痞白占魁、“名声不好的女人”李翠娥、可怜的赵素芳、矛盾的徐改霞……事实上,包括蛤蟆滩上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土地的儿子”,为了土地和生存,为了尊严,他们努力“发家创业”,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作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深度描写中,我们看到鲁迅小说的影子,不过文学的光芒,这时直接聚焦在闰土们身上,鲁迅小说中那无法呈现的“乡愁”,现在被这个光芒所照耀。从鲁迅到柳青,文学世界发生了倒转性变化。
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回想起严、柳之争,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同样是在这个世界上生长出来的形象,为什么梁三老汉形象的“真实性”能得到承认,〔14〕梁生宝形象就遭到怀疑?是不是因为梁生宝形象更为陌生?或者,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真正的尊重,因而对我们来说,陌生的是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梁生宝,包括对认识梁三老汉形象,我们其实也没有做好准备。那么,这是柳青的问题,还是评论者的问题?
《创业史》的时间性
《创业史》第二十四章,以诗一般的语言写到时间:
一九五三年春天,和过去的一千九百五十二个春天,一模一样。
一九五三年春天,渭河在桃汛期涨了,但很快又落了。在比较缺雨的谷雨、立夏、小满、芒种期间,就是农历三月和四月的春旱期,渭河在一年里头水最小了。
一九五三年春天,秦岭脱掉雪衣,换了深灰色的素装不久,又换了有红花、黄花和白花的青绿色艳装。现在到了巍峨的山脉——渭河以南庄稼人宽厚仁慈的奶娘,最艳丽迷人的时光了。待到夏天,奶娘穿上碧蓝色的衣服,就显得庄严、深沉、令人敬畏了。
一九五三年春天,庄稼人们看作亲娘的关中平原啊,又是风和日丽,万木争荣的时节了。丘陵、平川与水田竞绿,大地发散着一股亲切的泥土气息。站在下堡乡北原极目四望,秦岭山脉和乔山山脉中间的这块肥美土地啊,伟大祖国的棉麦之乡啊,什么能工巧匠使得你这样广大和平整呢?散布在渭河两岸的唐冢、汉陵,一千年、两千年了,也只能令人感到你历史悠久,却不能令人感到你老气横秋啊!祖国纬度正中间的这块土地啊!……
但一九五三年春天,人的心情可和过去的一千九百五十二个春天,大不一样。
一九五三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画、交响乐和集体舞。……
一九五三年春天——你历史的另一个新起点啊!〔15〕
这段出现在小说中间的诗性叙事,与“题叙”遥相呼应,它所铺展的质实而宏伟、明朗而厚重的场景,接续着“题叙”中那不可被屈服的土地之爱,却又把其中的阴霾一扫而光了。这是《创业史》叙述的基调,真正具有“综览全篇、俯瞰整体”的作用。因此,说到小说的“楔子”“扣子”或“得胜头回”,似乎又在这里。有论者说,伟大的小说都有几个开头,小说由此组织起主题与生活内容的繁复交响,如《红楼梦》。〔16〕柳青殚精竭虑,似乎也在努力构筑这样的效果。由“题叙”延续而来的“时间之眼”,在这里被“一九五三年春天”擦亮。
第二十四章所写的是蛤蟆滩姑娘徐改霞离开家乡,到县城投考工厂的事。插入事件之前的这一段,作为事件的背景介绍,重点不在农村描写,而在描画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大规划,描画中国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开始的工业化建设图景。徐改霞的人生选择,联系着蛤蟆滩外更为广大的世界,联系着被这个世界所震动的贯通几千年的时间视野,也联系着在此视野上浮现的新中国、新历史和“新起点”。蛤蟆滩的生活世界,因为这幅新图景的引入,变得新鲜、亲切、深沉和庄严。“一九五三年春天”的阳光,照亮了徐改霞形象在小说中的特殊意义,照亮了《创业史》的农村描写。这个描写,同样具有显著的文学转向意义。
与梁生宝形象不同,徐改霞形象引起的争议主要不是发生在评论界,而是发生在普通读者之中。从出场之频繁、小说着墨之多,可以看出徐改霞在小说中所占的份量不亚于梁生宝。这么重要的一个形象,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充分关注,却被普通读者热烈地议论着,这一方面反映出读者的敏感,另一方面也印证着柳青对读者的信任。1961年,柳青专门撰文,参与到读者对徐改霞的评价和争议中,〔17〕其意犹未尽之处,又申述在《美学笔记》中。他说道:“不是为了写恋爱而写改霞,是为了写梁生宝而写改霞。既然要写,又不愿意写得很概念,自然就占了不少篇幅。……要从安排情节来看作者的意图,不是光从几个形容词或一段描写。”〔18〕这有两个意思。第一,如果说梁生宝形象是陌生的,那么,“为了写梁生宝而写”的徐改霞,同样会不免这种陌生感,因为他们都是在蛤蟆滩土地上出现的“新人”;但是,梁生宝形象可以自我解释,徐改霞形象也是如此。对读者来说,作者所要提供的,是“全部形成改霞性格的基础”,这正是柳青在小说中花了“不少篇幅”写改霞的原因。第二,“为了写梁生宝”,为了写蛤蟆滩,必须把二者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上,必须让包括梁生宝的变化在内的整个蛤蟆滩世界的变化在小说中获得自我解释的功能,为此,需要把蛤蟆滩世界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不是从政策条文上,而是从生活上连接起来。徐改霞是这样一条线,她不仅是立于蛤蟆滩上的典型人物,而且是书写蛤蟆滩世界的时间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个来源,不通过徐改霞,也需要通过其他人物引入。为使这个来源不至于“写得很概念”,柳青花了“不少篇幅”。按照柳青的设计,到第一部结束,徐改霞的任务也基本完成。〔19〕其中原因,我以为是,通过她这条线,蛤蟆滩世界在古老而新鲜的中国土地上立起来了。
韩毓海讨论《创业史》的时间性,把它归结为一种“现代时间观念”。他着重从工业化背景上,从现代工商业精神即所谓“清教时间伦理”的“彼岸”理解《创业史》的时间秩序及其意义。他认为:“正是这种与劳动、工作和使命伦理相关的时间观,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根本基础。正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而《创业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或者表现了这一根本性的变革,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20〕这种偏向工业化一端的思路或许不能准确地抓住《创业史》的时间意识。从国家意义上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现代时间观念”并没有抹平历史的沟壑,反而是在更为清晰、有力地雕凿由历史来定义的国家形象,源于历史的精神而非“清教时间伦理”才是支持第一个五年计划、支持工业化的深层基础。小到蛤蟆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光亮中,它的历史走向敞露出来,与此同时,它的全部的历史具体性,尤其是由“题叙”所塑造的,几千年来与苦难相伴、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历史意志——“创业”的意志也醒目地矗立在时间视野中,这不是韩毓海所说的工业化与“现代时间观念”可以一笔抹去的。事实上,“一九五三年春天”——通过徐改霞引入的时间视野对于《创业史》的意义,乃在于为蛤蟆滩世界的自我呈现提供叙述的可能。惟有在新中国的母腹中,才有蛤蟆滩世界的新生;惟有在新世界的曙光里,蛤蟆滩才清晰展露出它庄严、深沉、令人敬畏的历史皱折;最终,惟有在依靠自己并通过自己选择和实现的新变化中,蛤蟆滩世界才树立起它内在而固有的、并且面目一新的尊严。这里隐涵着属于蛤蟆滩自己的时间观念和历史深度,隐涵着蛤蟆滩世界的主体性。因此,《创业史》不是因为表现“现代时间观念”,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相反,它是因为塑造了蛤蟆滩自身的形象,因为“正确”“深刻”地表现了蕴蓄几千年的历史形象被“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激活、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内在转化,才加入到“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行列。〔21〕
就此可以说,《创业史》既是一部关于蛤蟆滩的历史,又是一部由蛤蟆滩自己书写的历史。前者意思是,统一的“中国时间”打破了蛤蟆滩乡土的平静,把这里所有人的日月都编织进“一九五三年春天”所指示的时间的经纬里,蛤蟆滩的历史由此才得到辨认。后者则是说,这部历史是由蛤蟆滩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支持历史行进的力量来源于它自己。在前者的意义上,小说确定历史叙述的整体观念和框架;在后者的意义上,柳青则需进入蛤蟆滩内部世界,从每一条生活的细流一直辨识到它们共同的源泉,从而把它们疏引和汇集为通向新的时代的宽阔的河流。正是通过后一方面的工作,农村世界才没有被历史所淹没,《创业史》才从历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小说。
农村描写与时间感
农村形象首先是农民形象。《创业史》写到性格、历史、境遇、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各不相同的众多人物,他们组织起蛤蟆滩的自然秩序,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又或凝聚或散落在梁生宝周围,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态度和选择,这是小说叙述的基本线索。毫无疑问,从个性、地位到思想感情上的种种不同制造了蛤蟆滩上复杂万端的矛盾,小说也正是从各种矛盾入手,相互镂刻矛盾中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但是,另一方面,沿着这些矛盾向前追溯,处于矛盾冲突中的这些人都是蛤蟆滩的庄稼人,他们无一例外地从土地上争取生存,无一例外地怀揣着从劳动中创立家业的梦想,他们的形象和尊严,从土地和劳动中取得,并被他们自己所感知。这个共同的庄稼人形象,构成蛤蟆滩矛盾斗争的共同背景和基础,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区别,是在这个基础上映现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方向,也是由此得到支持。潜行在小说人物冲突中的庄稼人形象和劳动叙事,构筑起《创业史》历史叙述的底座。
小说从欢喜眼里写到贫穷的任老四趁春闲出门打土坯的形象:
“四爹,你做啥去?”欢喜问。“到郭家河去。”任老四说,“揽下人家一千土坯。”“说了多少钱?”“这!”任老四高兴地伸出一只手,岔开五个指头,摇了两摇,嘴里溅着唾沫星子,满意地说,“能量几斗玉米。欢娃,你也该出去打听点活干啦。这春荒时节,甭蹲在屋里等人请。甭放不下学生架子!瞅空子干几天吧,给家里跑闹点口粮要紧。生宝买稻种回来,山路硬了,咱互助组进山呀嘛。”任老四说着,脚步带劲地从土场北边几棵桃树中间的斜径上走过去。……〔22〕
任老四不是因为仅仅在政治上拥护互助合作,而是因为劳动,包括通过互助组结成的集体劳动,才在蛤蟆滩土地上找到自信和尊严,“脚步带劲地”走起来的。这个形象不仅见之于支持和参加互助合作的任老四一方,也从不热心于此的郭振山一方见出:
春雨过后,太阳一晒,空气里散发着一种令人胸闷的气味。好像地球内部烧着火似的,平原上冒着热气。你抓起一把关中平原的黑胶土,粘糕一样,一捏一个很结实的窝窝头。温暖的初春的阳光啊!你从碧蓝的天空,无私地照着所有上身脱光的庄稼人打土坯。……
郭振山和他兄弟郭振海,在土场南边的空地上打土坯。彪壮的郭振海脱成了赤臂膀,只穿着一件汗背心,在紧张地打坯子,他哥供模子。兄弟俩准备拆墙换炕,弄秧子粪哩。〔23〕
事实上,这样的文字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中农郭庆喜,“贪活不知疲劳”,外号叫“铁人”。瞎眼的王二直杠,“他是这样一种性子,做起活来拼命,恨不得爬下去用脑袋犁地的庄稼人啊!”世富老大,在种地上有着超乎常人的“精细”和敏感。甚至在富农姚士杰身上,作者也不吝惜劳动描写的文字,说道:“姚士杰的劳力是很强的。他眨眼工夫,在后园里整出了种茄子和种辣椒的地,用锄头给韭菜松了土,给两架大葡萄浇了水。”至于梁生宝和冯有万,“在蛤蟆滩来说,算庄稼行里数一数二的把式,犁、耙、锄、割、扬秧、插秧,除了铁人郭庆喜,没有比得上他俩的。”以梁生宝为中心的互助合作,所展开的又是集体劳动的场景,并成为小说集中描画的形象……所有人都从劳动中照见自己的形象,并把这个形象映现在“碧蓝的天空”下。土地、阳光和庄稼人诚实的劳动,给予庄稼人做人的自尊和全部生活的根据。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够创立家业,就变成偶然的历史事件,如梁三老汉与秃顶老汉梁大的遭遇;进不进互助组,采取不采取水稻密植,也变成可以选择的了,虽然前者除作为劳动组织形式的选择之外,还带有政治选择的意味。经历活跃借贷、买稻种、进山、新法育秧、白占魁入互助组等矛盾丛生的事件之后,《创业史》以粮食统购统销为第一部收束。在这个国家行为中,不仅互助组的劳动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性,使互助合作最终成为蛤蟆滩人共同的选择,而且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也交出蛤蟆滩最多的粮食,这是他们的劳动成果。小说以这种方式,肯定了蛤蟆滩所有人的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形象,整体地带到“一九五三年春天”所指示的时间光亮中。蛤蟆滩在劳动中实现它的时代转身。
风俗人情是农村形象的另一面。这里有着最多的历史印记,也是农村题材小说最丰富的资源库。柳青从创业的矛盾上进入风俗人情的描写,从农民自己的思想感情上,把农村生活故事写得风生水起。有论者从这个方面认识《创业史》的价值,提出:“《创业史》以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作为表现线索,作者给人物确定了政治性身份。而充盈丰富的描写穿越了作者对人物的阶级预设,深厚又精细地展现了人性与人情。‘生活故事’上面确实套着一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框架,即使这框架倒坍了,生活故事的生动性和魅力依然存在。”〔24〕评论表面上是为“挽救”《创业史》,使它的价值从“时代局限”中挣脱出来,但如此隔岸观火、雾里看花式的评论能否道出小说风俗人情描写的真实性与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主要原因是,《创业史》生活故事如此紧密地结成内在整体,以至整体“倒坍”,生活故事也将不复存在。这不仅指生活故事前后映照、相互解释,尤其指每一个生活故事下面都涌动着复杂的生活的涡漩,并深深地嵌入历史的河床,它们如同泛动在阳光下的波纹与浪花,被看不见的潜流推涌着。《创业史》生活故事的“生动性和魅力”,根源于此。
小说第一章,写到梁三老汉大闹草棚院。故事起于细末,却酝酿已久,两个要强的人在创立家业上的矛盾,被各自的行动驱动着,形成梁家草棚院两股生活的暗流,到这天早上,它们撞出激烈的水花。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冲突中,作为冲突的另一方——梁生宝,却缺席于现场,他在晨光熹微的时候,早早出门买稻种去了。梁生宝缺席的行动,一方面把父子俩的矛盾继续掩映在生活之下,另一方面,却又构成对梁三老汉近在眼前的结结实实的挑战,老汉终于忍无可忍:
老汉大嚷大叫,从小院冲出土场,又从土场冲进小院,掼得街门板呱嗒呱嗒直响。他不能控制自己了,已经是一种半癫狂的状态了。生宝不在家,正好他大闹一场。再没有这样好的机会了!
“不行!”他甚至在街门外的土场上暴跳起来,“只要我梁三还有一口气活着,不能由你们折腾啊!老实话!”他又跳了一跳。
老汉的心气随着怒火上扬,这个时候,他仿佛回到二十几年前掌舵梁家、意气风发地创立家业的时光,因此,他不由自主地挖出往事,既冤且怒地质问起生宝他妈:
“三岁上,雪地里,光着屁股,我把他抱到屋里。你记得不?你娘母子的良心叫狗吃哩?啊?我累死累活,我把他抚养大,为了啥?啊?”〔25〕
十分明显,这场吵闹既是梁家草棚院两股力量交锋的转折点,也是梁三与梁生宝父子关系的转折点。梁生宝以不在场的回应,从继父的愤怒和委屈中,正式接过了草棚院创立家业的主导权;而对梁三老汉来说,他选择生宝不在家的时机发动这场吵闹,乃是向他积压二十几年未曾申张的创业志愿作出最后的致意,并为之向自己、向这个家庭、向这个时代发出最响亮也是最空洞的反响,他从此在思想感情上把家庭交给养子,并且“下定决心对‘梁伟人’的事,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了”。
梁三父子的冲突是从创业矛盾上发起的,并非养父子亲情危机。梁大老汉看得很清楚:“你三叔是把白铁刀,样子凶,其实一碰就卷刃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梁三老汉在彻底交出家庭的主导权后,他的主要牵挂,就转移到养子的事业上,这是他虽“决心”不管却割舍不下的事。他观察蛤蟆滩生活的流向与力量的消长,并把它们反映在为梁生宝起起伏伏的担心上。围绕互助合作事业的亲情书写,从此成为《创业史》风俗人情描写的基本线索之一,发生在这条线上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如生活的航标一样标识着下面的涡漩的变化,并在整体上指示着蛤蟆滩“矛盾和统一”的方向。荸荠地里父子争论的那一幕,还留有老汉未完全消失的不满,到生宝率队进山前,父子告别的那一幕,隐含了老汉多少隐忧和牵挂!拴拴在山里受伤,他瞎眼父亲为此哭闹梁三老汉草棚院,当消息传到老汉耳里:
韩培生回头看时,在榆树底下,梁三老汉昏倒在地上了。手里的玉米糊糊撒了一地,碗也扣在他穿着庄稼人粗布裤子的屁股后头。〔26〕
蛤蟆滩暗流涌动的反对梁生宝事业的力量,随着王瞎子的大闹惊天动地而来,前一分钟还在谈笑的老汉,后一分钟被这个消息打倒了。懦弱的老汉在与梁生宝一起,承担着这份事业所给予的巨大压力。
所以,到第一部结局,我们可以理解老汉这时的心情。蛤蟆滩生活之流开始转进时代的宽广的河床,儿子站上了潮头,在这个形势下,老汉对儿子说出下面一段话:
“……你好好平世事去!你爷说:世事拿铁铲子也铲不平。我信你爷的话,听命运一辈子。我把这话传给你,你不信我的话,你干吧!爹给你看家、扫院、喂猪。再说,你那对象还是要紧哩。你拖到三十以后,时兴人就不爱你哩!寻个寡妇,心难一!”〔27〕
所谓“寻个寡妇,心难一”并非单纯的亲情表达,它包含了老汉理解儿子及其事业的曲折过程,也是基于儿子在事业上对父亲完全的理解和信任。养父子感情与蛤蟆滩事业深刻地统一到一起。正是以此为标志,小说把蛤蟆滩风俗人情,也转写到历史的“新起点”上。
风景在《创业史》世界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它是这部生活故事单纯、明净的起点。小说从风景写进来,自“早春的清晨”(第一章)到“初夏的夜晚”(第三十章),结成生活故事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风景随节气而变化,并渗进每个人的生活里,它像小说中“新法育秧”的秧苗,不管人们的喜怒哀乐,不管人事上的变化,只管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按照自然界的规律生长。〔28〕比如第十九章和第二十七章开头的描写。自然的节律隐涵着与劳动节律的一致,隐涵着对劳动的召唤,《创业史》通过这个特殊的处理,把风景与劳动一起独立出来,从而把风景真正融入到蛤蟆滩整体的生活秩序之中,使它与劳动一起,筑成这部生活故事坚实的底座。
在此基础上,风景描写仍然是心情的写照。从劳动中发生的自信和尊严向内刻画着庄稼人的形象,向外涂写着风景的情调。我们看下面的一段,这是梁生宝带队进山的场景:
秦岭里的丛林——这谜一样的地方啊!山外的平原上,过了清明节,已经是一片葱绿的田野和浓荫的树丛了;而这里,漫山遍野的杜梨树、缠皮桃、杨树、桦树、椴树、葛藤……还有许许多多叫不起名字的灌木丛,蓓蕾鼓胀起来了,为什么还不发芽呢?啊啊!高山的岩石上,还挂着未融化的冰溜子哩。生宝走着走着,不断地听见掉下来的冰块在沟壑里摔碎的声音,惊得山坡上的野鸡到处飞。听见脚底下淙淙的流水声,却看不见水。啊啊!溪水在堆积着枯枝败叶的冰层下边流哩。〔29〕
清明节气作为农村生活和劳动秩序的标记,在山里山外展开为不同的自然景观。在这里,节候的差别与新的事业、新的劳动相结合,生发出奇异、新鲜的生活感受,时间好象重新开始了。这种抒情笔墨,是《创业史》,是“文学柳青”让人感到陌生的地方。有的论者说,这是叙述人语言对人物语言的干预,是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30〕有的论者说,这是叙述语言的书面化与人物语言的口语化之间的分裂,〔31〕还有的论者说,这是柳青知识分子趣味的体现,〔32〕所言都离开了作品本身。不从小说内部自我解释的功能出发,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评价这种抒情文字。自然,站在生活对面的知识分子,也难以理解劳动中的情感、劳动者的情感。“劳动人民真正过着最深刻、最丰富的内心生活。”〔33〕柳青沿着劳动的场景,勾画出他们意会于心而难以言传的心情意绪,相互刻画庄稼人形象和如诗如画的风景,这是从内部写进农村的手法。柳青说道:“《创业史》第一部试用了一种新的手法,即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描写),糅在一起了。……我想使作者叙述的文学语言和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尽可能地接近和协调,但我的功夫还不够。”〔34〕如果可以“责备”,我们“责备”的应该是柳青“功夫还不够”,却不应该是这个“手法”本身。
从风景与劳动一起构成的时间场景中,小说进一步剥露出广大、深远的生活背景,这就是秦岭的形象。谜一样的秦岭,蕴藏着多少新的生活的可能!在广泛的意义上,它属于梁生宝,属于所有进山人,属于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小小的进山团队,在秦岭的丛林里,感受着它的深邃和高远。另一方面,宽厚无私的秦岭,为这一群穷人的生计和劳动,为梁生宝的事业,奉献着无言、无尽的支持,这使梁生宝和冯有万们,在秦岭的丛林里,又感受着它的新奇和亲切。秦岭的形象,在劳动者的事业中,焕发着温厚、明朗的光辉。这是《创业史》风景描写的制高点。我们在小说第一章的开头,就看到它巍峨的身影,此后,在小说的每一章,在蛤蟆滩人生活故事的背景里,几乎都能看到它的形象。
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风景描写,散落在所有人的生活中。错综的叙述路线从共同的风景中引申出来,编织起以风景的节气性变化为线索的既统一又多样的时间格局。《创业史》以人物为中心,〔35〕人物活动又自成段落,在以人物为中心的活动中,自然风景构成几乎所有活动的场景,并加入到具体人物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之中,复杂多样的生活故事同时组织起变化万端的风景故事。从此出发,小说描画出以秦岭的形象引领的、包括了所有人生活的蛤蟆滩世界全景图。《创业史》是一部农村生活史,风景描写是农村描写的标识,深入到农民生活和思想感情中的时间风景,描画着“一九五三年春天”的景观,也恒久地标示着《创业史》温暖农村的文学价值。
“文学柳青”与底层形象的文学呈现问题
农民首先是有尊严的主体,然后才能谈到政治选择或者利益选择的问题。这种尊严又不是依附于阶级或者知识分子取得的,而是来源于农民自身,来源于他们向苦难的抗争,他们在阳光下的劳动,来源于农民向土地争取生存的意志。正是以此为支持,农民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建立起包括农村在内的生活世界的主体性。
历史又是由包括农民在内的底层人推动的。在农村,真正的历史转向,首先是农民的精神意志的转向,是农民的主体性转向,只有真正出于农民的自觉选择,历史的选择才有可靠的根据。这种选择又回到农民的主体性之中。因此,农民的主体性又是农村世界的历史主体性。
面对这个世界,作家、评论家除了收起“特殊理解和特殊爱好”,尊重它,信任它,无声地倾听它自己发声,没有别的选择。
《创业史》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令人尊重的农民形象和农村形象。
关于小说主旨,柳青说道:“《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36〕这段话表达着两层意思:第一,小说具有明朗的政治倾向和明确的结论;第二,作为对这个政治问题的回答,小说需要具体地、合理地表现农村人物在行动、思想和心理上的变化过程。《创业史》的价值,不是由这个结论体现的,而是由这个“过程”实现的。建立在农民和农村世界主体性基础上的“变化过程”,把结论变成了一种选择。有选择才有必然,这是《创业史》在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意义;有选择才能刻划出真正的主体性,这是《创业史》延续至今的意义。
有论者说道,底层并非事先成为主体,而是“在多重对话中产生出来的主体”,“这种对话关系之中,知识分子与底层互为‘他者’。”“从底层与一系列‘他者’——除了知识分子,还有官员、企业主、商人等——的交叉网络之中认识他们,远比‘本质主义’的肖像更富有历史动态感。”按照这个说法,底层的主体性是在文字世界、文字网络中呈现的,文字网络又映现着底层与知识分子、官员、企业主、商人等复杂的现实关系网络,底层的主体性便通过这个关系网络分层、多向展开,并回返到这个网络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底层经验表述复杂而丰富。”〔37〕这是当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所肯定的不是底层的权利,而是知识分子、官员、企业主、商人的权利,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权利。文字世界出自知识分子之手,不是由底层制造的。几千年来,农民和其他身处底层的人是我国文字世界、文学世界“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拥有文学,也没有将自己加入到文学世界的需要。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说道:“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38〕六十多年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此。只要有农村和农民,就有不依赖于文字的劳动和生活,不依赖于文字的形象和尊严。梁三老汉、宝娃他妈、任老四、冯有万……他们是不识字的庄稼人,梁生宝的识字量不足以支持阅读和写作,归根到底,他是“泥腿庄稼人”。在文字世界之外,庄稼人挣扎着生存,创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讲述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这个故事世界,不经过文字,托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五四”以后,农民形象在文字世界、文学世界大量出现,他们在文字世界被构造为“他者”,被知识分子构造为“他者”。这个在鲁迅小说中令人敬畏的“他者”,在鲁迅之后,被知识分子层层“打开”了,于是有所谓“农民气质”问题,有农民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问题,有像不像农民的问题。〔39〕所谓呈现农民形象的文字网络,就此铺展开来。可以说,1960年代的严、柳之争,柳青的对方即是在这个意义上辨认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的。
文字世界、文学世界的关系网络,实质上是指向构造者自身的网络。当知识分子通过区别于自己构造出与自己相对照的、并依附于自己的“农民主体”时,其中所呈现、所打开的农民形象,何尝不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形象?有人提到沈从文一脉,“力图以写作复原乡土本身的美和价值”。〔40〕一位追求“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的知识分子,把他的追求寄托于“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的“边城世界”,〔41〕并因此对眼前的农村和农民视而不见,则其所谓乡土书写,难道不是在写他自己吗?与“沉默”的农村和农民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进一步说,知识分子通过掌握文字的权力来结构这个网络,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农村和农民形象依附于比文字权力更大的权力网络上,究其实质,乃是把自己依附于比文字权力更大的权力上,在今天,即是论者所说的“官员、企业主、商人”的权力。“多重对话”也好,交叉网络中的“主体性”也好,掩盖着真正的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关键不在知识分子如何自我标榜书写的真诚,而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责任:面对农村和农民,他如何给出自身存在的根据,如何证成自身存在的可能性?
由此看到柳青和《创业史》的价值。从“题叙”的苦难叙事开始,柳青把书写农民的权力交给农民自己了。生宝妈对立婚书的质疑,是不识字的农民对文字的质疑,也是小说对传统文字世界的质疑。《创业史》以人物为中心的设计,因此是文字追随人物的设计,人物的问题,不是由统一的“中国时间”规划的,而是由人物自己在生活与劳动中提出来的,它首先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从农民全部的生活世界中发动的问题。这个把“一村人团结起来”的问题,因此不是叙述的起点,而是叙述的结果。《创业史》通过这种方式,把分散的庄稼人形象,引领到“一九五三年春天”,把他们的意志和愿望,表达在统一的时间网络即论者所说的“交叉网络”中,也即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所编织的秩序世界里。柳青——这位在皇甫村安家落户的普通劳动者,一位把生活彻底“对象化”的知识分子,创造了一种以“对象化”世界为主体的文字形式,〔42〕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文字的垄断。
农民在土地上立起来,农村世界在“工业化”时间中立起来,是农村小说的生命所系。市场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对农民利益的剥夺,可以通过底层农民与官员、企业主、商人结成的“交叉网络”受到多方、多层的制衡,但是,农民的形象不仅仅实现于由此获得的经济补偿中,农民的主体性不存在于这个“交叉网络”中。失地农民的悲哀,是整整失去生活世界的悲哀,是他们的价值和尊严被摧毁、是身在“故乡”却流落“异乡”的悲哀。知识分子不能左右官员、企业主、商人的权力,然而可不可以放弃文字的立场,走进权力的背后,去亲近和感受这个世界、这个在今天依然喑哑无声的世界呢?
正是在这个方面,《创业史》呈现了它仍然令人尊重的价值。
注释:
〔1〕参见萨支山:《当代文学中的柳青》,载《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赵学勇、王贵禄:《经典的剥蚀:“柳青现象”的文学史叙事及反思》,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刘纳首先提出从“艺术的标准”评价《创业史》的问题,她的观点在以上两篇文章中受到重视。见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在此之前,《天涯》杂志2004年第2、3期登载有关“知识分子与底层表述”问题讨论的文章,可看作南帆讨论的一个背景。
〔3〕在“写中间人物”的论争中,梁三老汉形象成为其中的论题。邵荃麟、严家炎提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洪子诚对此说道,“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在这点上,邵荃麟等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原先的论敌胡风的立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2-103页。)我以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柳青与鲁迅的联系。
〔4〕〔5〕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6〕柳青:《在故乡》,《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7〕陆耀东:《谈柳青的早期创作》,《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第84页。
〔8〕柳青:《二十年的信仰与体会》,《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
〔9〕〔32〕吴进:《〈创业史〉对农民的描写及其知识分子趣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23-24、29页。
〔10〕为寻找合适的艺术结构方法和表现方法,柳青精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有以取择。参见吕世民:《柳青与外国文学》,《小说评论》1988年第6期,第76-81页。
〔11〕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出自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载《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12〕〔15〕〔22〕〔23〕〔25〕〔26〕〔27〕〔28〕〔29〕柳青:《创业史》,《柳青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8、330-332、61、62-63、27、372、433、375、299页。
〔13〕林家平:《“题叙”小论》,载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8-409页。
〔14〕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16〕骆冬青:《〈红楼美学〉序》,见何永康:《红楼美学》,广陵书社,2008年,第1页。
〔17〕柳青:《怎样评价徐改霞?》,《文汇报》1961年10月12日。
〔18〕〔34〕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302-303页。
〔19〕《创业史》第一部初版期间,柳青致信出版社,说道:“我还要在清样上改一改,主要增添二、三处关于改霞的情节,使这个人物更加清楚一点。这个人物在这一部基本上算完成她的任务了。”见王维玲:《追忆往事》,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写的人》,1982年,第56页。
〔20〕韩毓海:《我们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梁生宝》,《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8日,第32版。
〔21〕“正确”和“深刻”是柳青对作品提出的要求。他说:“无论如何,作品的正确性是深刻性的基础。说不正确的作品写得深刻,是不对的。”(《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24〕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第24页。
〔3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31〕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载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33〕柳青语,载杨友《回忆在皇甫村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写的人》,1982年,第126页。
〔35〕柳青谈《创业史》:“作品转动的轴承是什么东西?就是人物。人物是你小说构思的中心,也是结构的轴承。没有人是不行的。”(《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页)
〔36〕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原载《延河》1963年8月号,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孟广来、牛运清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3页。
〔37〕南帆:《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58页。
〔38〕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39〕参见李杨对此问题的撮述。李杨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一见到‘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我们就会发出‘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呢?换言之,关于农民的‘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这一类品质是农民本身的特点,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的创造呢?”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7-141页。
〔40〕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载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41〕沈从文:《烛虚·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42〕“对象化”是贯穿柳青创作和生活的最重要的理念,包括“社会生活实践的对象化”和“艺术创造的对象化”。他在《美学笔记》中说道:“作家对象化的功夫,决定艺术形象化的程度。……作家如果没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象化,即熟悉和懂得他的‘描写对象’,他就不可能在艺术创造中对象化,即一切情节发展要通过人物的行为,感觉和思维。这才是语言艺术的主体。”(《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271页。)
〔责任编辑:黎虹〕
刘国民(1964—),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哲学和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