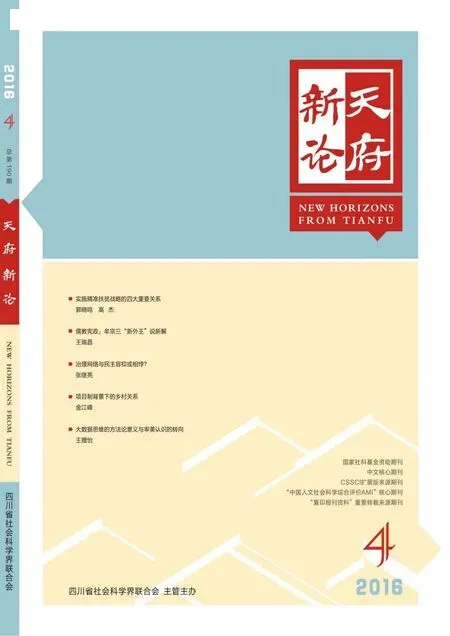公民能力与宪制民主
齐 伟
公民能力与宪制民主
齐 伟
摘要:政治权力实践中,宪制与民主的相互构成、相互依赖,为规范性的宪制与民主的概念性联结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利用赫希曼归纳出来的保守主义三个命题,可以发现传统应对策略的反动性。传统应对策略的失败,一方面为我们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激励和教训;另一方面,对民主的忠诚,则要求一种更为充分的解决方案。以动态宪制和公民能力为基础,能给分析宪制民主“问题”予以更多的补充性说明,对民主价值的重新诠释也将对宪制的理解产生进一步的启迪。
关键词:民主 宪制 规范性价值 公民能力 动态宪制
一、超越宪制民主的“悖论”
宪制、民主、法治以及人权,这些规范性的价值和原则都是我们有理由珍视和追求的。然而,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坏,以至于简单地将两种或者更多的规范性价值和原则放置在一起,从而构成一种新的事物之时,其中的不和谐、冲突立刻便显现出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我们通常信奉并珍视的诸种积极价值之间,并非最终都是相互包容或是相互支持的。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现实世界,乃是伯林所指出的价值多元论这一客观事实。人的目的是多样的,而且从原则上说它们是不相容的,这就使得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冲突和悲剧的可能性便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在各种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便构成人类状况的一个无法逃脱的特征。”〔1〕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把宪制和民主这两者整合在一起,便出现了学者所谓的宪制民主的悖论。①See e.g.,Martin Loughlin and Neil Walker(eds),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Kevin Olson,“Paradoxe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51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0(2007);Bonnie Honig,“Between Decision and Deliberation:Political Paradox in Democratic Theory”,10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007).
在概念方面,我们必须首先问的是,民主与宪制之间真的存在悖论吗?还是说,它们之间的悖谬只是由于我们随意使用特定的基本概念所引起的?一般认为,悖论,即通常意义上在逻辑上的不一致、不相容,经典的情形是A与非A不应该同时为真。②See Matthew Tugby,“The alien paradox”,75 Analysis 28,28-37(2015).如果不一致能够解释,悖论就被解决了;如果没有,它就仍然是一个悖论。在传统的理解中,英国政制话语中的议会主权概念就提出了一个悖论。议会是主权,这意味着议会能够制定任何它欲求的法律,但为了保持主权历时上的延续性,议会不应该包括约束它自身及其后继者的权力。然而,宪法并不仅仅是抽象意义的概念,还包括这些概念在实践上的运用和实施。据此,一些现代英国宪法学者认为,议会主权在概念层面上的悖论,就可以通过在宪法的运作层面上予以解决。①See e.g.,James Tully,“The Imperialism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in Martin Loughlin and Neil Walker(eds),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D.J.Galligan,“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 or the Potential of Constitutional Theory?”,2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43,348-351(2008).就像议会主权这个悖论所展示的那样,主权可以被重新界定为不是绝对的,而是要受制于例外情形,即一个议会不能够限制自身或者另一个议会。因为没有这种重新界定,议会主权这个概念在实践中就是不可应用的,或者说应用起来会导致不可接受的政治后果。
可见,一些概念层面上的悖论,可以通过实践上以及规范性的考虑予以解决。实际上,我们很难将人民主权这个抽象概念与规定人民主权的实践表达以及实施的规则二者予以彻底分开。因为人民主权要想对宪法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性和含义,规则就部分构成了人民主权这个概念。导控主权使用的规则本身并没有必然减少主权本身的范围和权力,就好像有关语言使用的语法规则并没有削减语言的范围和权力一样。没有规则,在政治权力实践中我们很难想象主权是如何能够被具体运用的。实践中有关代表的选举规则、议会程序运作规则、政党的组织规则等,实际上正是通过这些规则,主权才得以运用,而没有必然出现所谓的悖论。悖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则的特质,而不是规则的有无。此外,导控主权使用的规则还具有实践上的优势,提供了政府行为的确定性和预期性。②See D.J.Galligan,“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 or the Potential of Constitutional Theory?”,28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43,349 (2008).主权的导控性规则一定程度上也免除了人民每次决定主权的含义是什么、如何使用它的麻烦,因为这些事情必然是争议性的,它们的解决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实际上,所谓宪制民主的理想之所以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其中贯穿着两个似乎看起来冲突的假设,即一方面,合法性的唯一源泉是人民自我决定的意志,民主应该成为制度构成中的 (唯一)组成因素,但同时应该有一些基本原则,对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能够在何时合法地进行立法做出限制,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首先,就政治权力的组织和运用而言,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是人民自我决定的意志,存在于人民主权的宣示当中。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的统治,那么,在政治实践中,民众就享有在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重新定义规则的自由,而且不应该依赖任何给定的定义。在民主主义者看来,宪法是民主程序的结果,需要经受重复不断的定义和再定义。通过把分权制衡、司法审查、照顾少数权利以及个人自由等观念也包括进民主这个概念之中 (这些观念曾经被认为是与民主对立的,现在却被认为与大众选举的立法机关中的多数意志一样民主),〔2〕民主因此变得比任何试图替代它的东西都更加可取。
另一方面,宪制主义者指出,世界上存在许多不同模式的民主,它们对民主规则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当人们想到许多民主国家的宪法曾经将一些重要的人群,特别是妇女和没有财产者,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曾经为大众意志的行使设置严重的障碍时,例如代表的间接选举,我们就需要对民主的批判保持开放的可能性,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③See e.g.,James Tully,“The Imperialism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in Martin Loughlin and Neil Walker(eds),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因此,关于政府的组成和安排,就应该有一些基本原则,通常表现为权利,从而能够对人民主权在制度构成中的运用做出相应的限制,正如米歇尔曼所指出的那样,应该存在着一种立法的原则 (laws of lawmaking)。④See Frank Michelman,Brennan and 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4-11.
在宪制主义者看来,宪法的限制可能合理地胜过民主,他们提出了防止民主自相矛盾的四条途径。首先,宪法对政治的某些限制被认为对于保护前政治或非政治领域是必要的,这些领域中,不管其他人有什么意见和利益,都应与外在的干预隔绝。对个人隐私或基本人权的保护与政治程序无关,应该归入这一领域。⑤See e.g.,Philip Pettit,On the People's Ter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assim.第二,宪法能帮助人们解决集体行动中的问题,预防部分人民薄弱的意志和短浅的目光。①See e.g.,Hans Lindahl,“Constituent Power and Reflexive Identity:Towards an Ont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in Martin Loughlin and Neil Walker(eds),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三,宪法能帮助政治使那些具有爆炸性和分裂性的议题远离议事日程。这种务实的考虑能支持对宗教信仰自由和私人财产采取超越民主的保护。②参见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以下。第四,宪法能保护民主所固有的权利,比如在自由而公平的政府官员选举中进行投票的权利,竞选选任制职位的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组织和参加独立的政治组织的权利,有效获得独立的信息来源以及其他自由和机会的权利,这些自由和机会对于大规模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是不可或缺的。③See Robert A.Dahl,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36-137.这样,宪法是鼓励而不是限制了人民主权。民主是由一些价值构成的,比如自治和平等,但这些价值并不是自己产生的。程序和过程的某些构成性特质和条件,正是它们充实以及具体化了民主自治 (self-rule)的规范性理想,没有这些规范性特征,就根本就没有程序上的民主合法性。④See Arash Abizadeh,“On the Demos and Its Kin:Nationalism,Democracy,and the Boundary Problem”,10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7,870-872(2012).
可见,关于宪制民主,尽管存在着诸多理论分歧以及争议,但对于争论者而言却存在着相同的努力和方向:一方认为宪法既是民主程序的结果,又与政治体系的制度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构的;另一方则将民主整合到宪制中去,并强调权利和自由的架构作为政治的必要假设的重要性。但是,民主对于具有宪制意义构成条件的依赖,显示了这里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问题。具体而言,宪制的起源及其政治权力实践之所以是不民主的,存在所谓的合法性危机。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是因为我们依靠着一种得到良好界定的民主概念。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民主概念本身的正当性,就会发现,民主并不是一种先于政治存在和发生的东西,相反,民主需要在一种具有宪制意义上的政治构成条件中才能够孕育和运用。因此,民主和宪制的这种相互依赖,为我们分析宪制民主所带来的问题,可以说既隐含了风险,也暗含了希望。之所以说隐藏着一种风险,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每一个概念的充分界定都需要对方的概念的充分界定为依据。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一种希望,我们可以借此发现解决宪制民主问题的诸种策略。
二、传统应对策略的反动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意在产生某种结果的行动方法,例如,铁匠给予铁水某种形式,医生治疗患者使其康复,科学实验者得出可以应用于其他情况的结论,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正确的反应方式应该是在其结果得到检验之前,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尝试、不确定的,都必须看作假说。在这一部分,利用赫希曼所归纳出来的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即悖论命题、无效命题以及危险命题,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对于宪制民主问题的应对策略的不充分性。⑤按照悖谬命题,任何旨在改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某些特征的、有意识的行动将恶化其希望救治的状况;无效命题则认为,社会改革的努力将是徒劳的,他们将不会“产生效果”;危险命题认为,有意识改革或改良的成本是如此之高,将危及先前某些宝贵的成就。参见 〔美〕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王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传统应对策略的失败之处,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探究一种更为可取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指引和教训。
(一)主张策略的悖谬性
就宪制和民主在构成上的互相依赖所带来的问题,政治理论学者所采取的第一种态度是主张(asserting)策略。特别是,主张策略的学者认为,宪制民主之间的张力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两难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这是因为它们两者所内涵的价值原则都是我们现代民族国家 (nation-state)所珍视的,宪制方面所体现的是法治 (law-rule)以及权利 (right),而在民主方面体现的是自治 (selfrule)以及意志 (will)。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坚持一种价值原则而牺牲另一种价值原则。不仅如此,逻辑上存在的这样的张力关系是富有生产性的,更是宪制发展及其转型得以保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⑥See Chantal Mouffe,The Democratic Paradox(New York:Verso,2000),p.5 and passim.因此,主张策略认为宪制民主的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时刻谨慎获取的机会。⑦See Paulina Ochoa Espejo,“Paradoxes of Popular Sovereignty:A View from Spanish America”,74 Journal of Politics 1053,1056(2012).
然而,主张策略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意识到民主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排除产生政治性的民族主义(politicized nationalism)风险。⑧See Bernard Yack,“Popula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ism”,29 Political Theory 517,523-530(2001).我们知道,理论上产生宪制民主悖论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人民主权这种抽象的学说。根据人民主权学说,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人民应该是某一领土范围内政治权威的最终源泉。居住在某一领土范围内的整体人民,被设想为国家权威如何被建构和运用的最终裁判者。然而,当我们追问谁是主权人民时,所谓的悖谬性便产生了,正是这种悖谬性在实践中容易导致具有政治性的民族主义的产生。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意义上,人民是指受制于某一政治制度的那些人,他们服从同样的政治制度便构成了一定范围内人的某种共享特征。换言之,政治权力的运用仅仅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当的,即在某种意义上由受制于政治权力运行对象的授权和同意。①See Allen Buchanan,“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112 Ethics 689(2002).然而,对于人民的这种界定,与现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含义并不一致。因为如果人民先于政治制度的建立,并且在政治权威消解的情形下整体人民仍然存在,那么,他们的共享特征就必然独立并超越与政治权威的某种既定联系。因此,特定人群之中的共享特征就一定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民,这样将会产生循环论证:为了确定谁是公民,就必须首先有一个合法的政治制度。进一步,我们不能民主地确立选民的界线,因为一个选区必须预先建立。因此,如果民主仍然需要人民主权,为了避免陷入悖论,人民的界定性特征就一定不能是具有政治制度依赖的公民联合。
换言之,人民必须由先于政治制度、具有非政治意义上的因素来界定和识别,在这里文化、语言、生活习惯、宗教、种族等因素就成为了人民的识别性特征,民主首先将导致民族 (nation),民族成为国家 (state)的社会基础。进一步,为了使民族成为主权者,民族作为某一领土区域内的唯一政治权威源泉就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共享的主权,在现代的意义上是自相矛盾的。为了确保民族成为排他性的政治权威源泉,特别是与国家领土范围完全吻合,必然要求对于局外人的排斥。最终,国家则成为法国政治学者罗桑瓦龙所说的一个被接受的再分配空间,“近代公民不仅是一个福利国家的成员,也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两者不可分离。这正是公民身份不可消除的界限得以通行之处。它在民族还未成为一个再分配的国家时贯穿了民族内部本身,并在这之后区分了不同的再分配形式。”〔3〕
在政治实践中,当政治家和意识形态的坚持者认为需要弥合人民主权和实际的政治构成的鸿沟时,悖谬性的后果便产生了。如果不是唯一的话,种族排斥和清洗主义就成为这种政治思考的必然结果。正如印度经济学者阿马蒂亚·森所言,“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况。代替这种支配性分类观及其所造成的对立的,不是不现实地声称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相反,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意味着人们同时具有相互交叉的不同身份,它有利于我们反对按某一坚硬的标准划分人们而导致的、据说是不可克服的尖锐分裂。当人类的丰富差别被压缩进一种恣意设计的单一分类之中时,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也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4〕基于民主所产生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政治构成意义,它将大大有助于加强我们与他人,比如邻居、同一社区的成员或同一国公民,以及同一宗教的教友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同样重要的是,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可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使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主张策略认为宪制民主的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坦然面对的客观现实,就有逃避判断责任的风险。
(二)解决策略的无效性
与主张策略不同,解决策略承认宪制及其实践的不民主,但是,解决策略将宪制的不民主限定仅仅在奠基这一立宪时刻。特别是,解决策略的主张者认为宪制奠基的不民主,并不影响在宪政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将宪制不民主的缺陷予以渐进地纠正和相应的补足。②See Joel I.Colon-R?os,Weak Constitutionalism: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the Question of Constituent Power(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2),p.3.实际上,在解决策略看来,正是因为立宪时刻的不民主这一政治现实,才使得宪制发展及其转型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解决策略以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最为出名,当然其也引起了学者更为广泛的争议以及批评。
概括而言,宪法爱国主义认为,展现为宪制民主中的基本权利和民主原则,它们其实是在一种具有具体内涵的互动关系中得到相互支持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谁先谁后的逻辑顺序,自然也就不存在相互冲突、不相容的可能性。权利并不优先于国民意志,也不限制它;它们也不仅仅是那种意志在偶然意义上的反映。宪法爱国主义“以一定的方式把两个原则看作是同等本原性的。一个原则离开另一原则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无需一个原则给另一原则加以限定。”〔5〕我们宁愿假设宪制中蕴含的权利是理解民众意志的民主品质的条件,而且民主政府本身就预设了其公民拥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自由和机会。宪制及作为其核心概念的权利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用来说明真正的政治到底是什么的方式,是一种解释在各种情形下民主的自我立法到底是什么的一种方式。
对于宪制及其实践的非民主方面,宪法爱国主义便诉诸这样一种观念,即应该将宪制及其实践看成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螺旋式的、历史的学习过程。宪制不是静态的、一次性作业,毋宁是应被看作一个有明确的开始时间的、建立于传统之上的工程,是一个后代通过实现被宪法的最初文本放弃的、仍未实施的、规范的、实质的权利系统来进一步努力完善的工程。①See Alessandro Ferrara,“Of Boats and Principles:Reflection on Habermas'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29 Political Theory 782,784-792 (2001).从政治上看,这一判断使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与祖先共同承担了同一项政治工程,要建立一个公民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我们历史上制定的、目前正在实施的宪法就是这种理想在法律上的反映。
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回答什么时候以及在哪里可以发现这种政治共同体。而且,即便是人们被要求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同样的标准和从同样的观点出发处理宪制问题,甚至用同一种批评方式,那么,人们在什么意义上能被认为具有了自由的制定者身份呢?如果人们要继承他们的祖先去实践先人的政治自治,而绝对不是他们现在正在实践的政治自治,那又会怎么样?如果人们学习的过程被说成是“自我更正”的过程,那从什么意义上讲他们才能被说成是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的呢?②See Bonnie Honig,“Dead Rights,Live Future:A Reply of Habermas'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29 Political Theory 792,795-805(2001).作为未来,其特征是无法由未完成的进步来保证的。在经济世界中,某些取舍是必要的,但关于进步的假设也要付出代价。对进步的信念甚至对它的辩护往往鼓励了自满和破坏了民主所急需的实践,即民主自身所赖以存在的自我检验、代系继承和批评。
不仅如此,解决策略没有注意到的是,如果宪制奠基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不民主的,那么,任何后续的制度实践和政治努力,都很难产生民主的作用和效果。按照赫希曼归纳的无效命题的构想中,人类行为或动机受挫,不是由于它们引发了一系列副作用,而是由于它们试图改变不可改变的事物,因为它们忽视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无效命题的倡导者将世界看作是高度结果化的和按照内在法则逐渐演变的,人类行为试图改变世界是无能为力的。在这个意义上,无效命题能够向我们展示以下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治权力实践中,通过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及授予无权者以权力,或是通过福利安排改善穷人境况的政策并实现良好的效果,那么,它实际上只是保持并巩固了现存的权力和财富分配而已。这是因为在经济世界中,那些负责制定政策的人恰恰也属于政策的受益者之列,因此就会产生如下的怀疑,即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完全清白或者出于好意的。
基于无效命题,这些政策制定者的诚恳必然会受到质疑,人们会认为作为政策追求正当理由的社会正义和其他类似的目标,可能仅仅是隐藏他们最自私动机的烟幕。因此,民主的宪制要想成功,就必须需要有一个民主的起源,尽管不同的分析论者及其宪制实践者对民主概念有不同的界定。③See Hans Agné,“Democratic founding:We the people and the others”,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836,840-843(2012).
(三)消解策略的危险性
与主张策略和解决策略不同,消解策略则是放松假设条件,或者对于概念假设的重新界定。消解策略认为我们可以消解宪制民主的整个问题本身。消解策略最为精致的理论模式,便是阿克曼的二元民主论。概括而言,二元民主论认为,通常所理解的宪制与民主之间的悖论,在根本的意义上是有缺陷的,是建立在对民主概念的简单、粗糙的理解之上。经过充分阐释和界定的民主概念,不仅不与宪制原则和理想相冲突,而且宪制原则本身便是民主含义的必然引申和当然组成部分。民主和宪制相互表达、相互蕴含、相互支持。为此,阿克曼认为我们需要在“常态政治”与“立宪政治”之间进行区分。
概括而言,宪制原则和理想反对简单多数主义民主,这对“常态政治”来说是有效的,但对“立宪政治”来说却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常态政治时期,人民不是用一个声音来说话,而是分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集团和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程序以一种“经济的”模式被使用,它将投票者刻画成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投票机制。因此,在常态政治之中害怕多数人的暴政完全是正当的:司法审查,区分代表制和麦迪逊式的制衡都是为了尽可能约束这种趋势。相反,立宪政治只是在国家发生危机时才出现,此时,危机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并引导他们超越自己的私利而考虑共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决策在本质上是协商产生的,而不是考虑什么是最经济的政策。在这里,集体利益的聚合和交换让位于基于公开的有正当理由的公共辩论和协商。其目标不再是所有人的意志,甚至连一般意志都不是。结果,对多数意志的反对不再那么有力。代替最大多数人偏好聚合的是多数的协商,前者对那些与多数人喜好不同的人施加了影响,后者则反映了基于每一个人的规则和原则的一般意见。在后一种情形中,投票者在他们做出决定时已经考虑了其他人的权利,甚至会尽他们所能给予最大程度的考虑。
在阿克曼看来,如果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说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不是贵族制或寡头制或两者的新混合,那一定是大量的普通美国人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持久参与。美国民主的宪制实践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普通美国公民的特质就在于它既非完全的公共公民,也非彻底的私人主义,而是阿克曼所谓的私人公民。阿克曼认为,美国公民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对政治生活投入同样的时间和精力,这是高级立法双轨制的基石。相反,美国宪法的二元主义传统已经赋予私人公民的美国特质以生命和实质。正是这一关联,才为美国人对美国宪法良心上的支持提供唯一的、最佳的理由。私人公民一方面承认公民身份具有价值,但是他并不认为,公民身份总是要压倒私人生活所具有的价值。私人公民,只有在诸如内战或20世纪30年代的大失业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动员公民并使他们参与旷日持久的、全神贯注的、具有公共精神的、内容深入的、协商的讨论,这正是制定高级法的特征。美国宪制的发生及其历史实践表明,私人公民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政治现实。
问题在于,阿克曼的消解策略能够成立吗?就当下的目的而言,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加以批判审视的是二元论的问题,而不是它对理解美国宪法及其实践的所提供的答案。为此,我们需要检视二元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即私人公民身份和双规制立法,而前者是更为根本性的。显而易见,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个人都拥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参与不同的社会关系,进行不同的社会生活。当我们作为公民,工作勤奋而高效的时候,政治生活特别是体现阿克曼意义上的高级立法就为深思熟虑提供了框架。而当我们作为私人行为,工作散漫而无效率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常规的立法框架当中。如果这些制度性的体系运作良好,那么,大量普通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就是常量,而不是变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普通公民在大多数时候能够在“常态的”讨价还价的经济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形式和“立宪的”理由交换的深思熟虑的政治参与形式之间转换,在合适的时候,甚至能够将两者予以结合起来。经济民主和协商民主就最好不被视为两者择一和相互排斥的民主模式,而应被视为提供了相互补充的政治理性的种类。①See Richard Bellamy,Dario Castiglione,“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27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5,610-618(1997).
另一方面,将私人公民视作为一种政治现实,消解策略的危险性在于它使得政治权力实践不去训练它们公民的批判或寻求答案的能力,也不发展他们任何特殊的、被认为有可能揭示真理的洞见和直觉的能力。诚如阿克曼所言,“作为美国人,我们既不是绝对的公共公民,也不是完全的私人。美国宪法是由这样一些私人公民组成的,他们拥有的语言和程序使得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民主自治成为可能。和所有的语言一样,它可以成就大善,也可以作恶多端。”〔6〕当阿克曼做如此陈述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像他承认的那样,这取决于普通公民的私人选择。
然而,有关普通公民的政治概念设想对于宪制/民主的政治含义,要比阿克曼所认为的重要以及复杂得多。我们知道,经济学关于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作为理性效用最大化者的普通公民,甚至不会去了解政治问题,因为反正他个人的不重要性使其政治能力无足轻重,对政治表现出普遍的冷漠、不关心和毫无兴趣对普通公民反而是明智的。由于同样的原因,普通公民也不会参加选举,哪怕他生活在一个拥有一部有利于他的宪法的民主社会中。因此,在经济世界中,自己不谋求国家公职的普通公民便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谁来贯彻一部符合他利益的宪法呢?普通公民作为宪法的利益人,并不拥有任何国家权力手段,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成为法治国家宪法的利益人,而无法成为这样一部宪法的捍卫者。在这里,不存在掌握强力的、愿意作为宪法的担保者、代表普通公民立场的行为者。
因此,如果“人民”将权力移交或无力调动潜在的权力,普通公民就会发现这些权力被用来同自己及自己的利益作对。如果没有个体的、自愿为实现共同利益承担公平份额的意愿,这些人由于接受社会公平原则的约束而跨越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鸿沟,符合普通公民利益的民主宪法的贯彻和执行这一集体产品问题就得不得解决。显然,这种公民理想需要严格训练和不断培育。在经济世界中,假设宪法本身生效且已经得到保障,而且扮演“利维坦”角色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原则上不会反对一部约束自己的宪法,显然是与政治现实不相符合的。人民的无力乃是利维坦的权力,这是一个不进则退的政治状况。据此,我们更有理由将私人公民视为一种政治建构,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现实。私人公民不仅是宪制/民主的受益者和创造物,更要成为宪制/民主的捍卫者和创造者。
当然,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以上三种应对策略在实践中一定会出现悖谬性、无效性和危险性,但理论上这三种反动性的存在,却暴露出了传统应对策略解决宪制民主问题的局限性和弱点,它们不足以解决宪制民主的问题。之所以做如此判断,不仅仅因为传统应对策略自身所具有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对于民主的价值及其标准的承诺,为我们拒绝传统解决策略提供了理由。正如达尔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试图去决定政治机构民主实际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甚至更依赖例证和经验的判断。然而即使在这里,我们所期待的,也部分取决于我们之前关于民主意义和价值的判断。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关注民主机构在现实世界中的形式,是因为民主价值及其标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7〕对民主的真诚要求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充分、更为民主的解决方案。而在之前,我们必须对民主的价值及其标准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揭示。
三、民主的特质
很显然,宪制民主的构成性问题不能够诉诸民主的程序和过程,例如多数投票程序,予以解决。因为在通常的理解中,民主主要是一种决策制定或者集体自治的方法,这种意义上的民主当然不能够对逻辑上优先的问题,即集体自身的构成产生作用,因为集体的存在是民主所预先假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够诉诸民主理论予以解决。①See David Miller,“Democracy's Domain”,37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01,201-204(2009).实际上,对民主的这种刻板式的窄化理解,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作为规范性理念的民主价值与作为一种程序和过程的民主方法之间的差别。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正是一些被充分理解的根本性的价值,例如政治平等、政治自由与个人自治,是这些规范性的民主理念正当化了民主的多数投票程序。②See Wojciech Sandurski,“Legitimacy,Political Equality,and Majority Rule”,21 Ratio Juris 39,60-63(2008).而且,多数投票的民主仅仅是民主之一种形式和方法,而不是民主的全部。
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究民主理想自身的某些构成性要素、规范性理念,以此追问诉诸隐藏在民主理想的根本性价值能否引导我们思考并解决宪制民主的合法性问题。换言之,民主自身还必须回答道德上的权威性问题,即为什么一种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构成这一事实,就可以为受制于这种制度构成及其实践的人,服从政治制度及其实践提供了道德上的理由。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和其他任何政府一样,为了其自身的有效统治和持久存在,也必须依赖于人民内在地接受它,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一些为保存民主政府所必要的事情,愿意履行政府施加给他们的义务和职能。
在通常的理解中,民主作为一种多数的决策程序和政治统治方式,一个重要的依据便是多数决策和统治较之于一人、少数人决策和统治,能够产生更为明智的决策和良善的治理。一个民主政体之所以取得合法性,是因为它的决策来自其主要群体、组织和代表之间完全、开放的商议。这里,商议被视为一种观点的形成过程:开始,参与者不应该形成完全的或不可更改的观点;他们要进行有意义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应准备好根据别的参与者的论点,以及在争论的过程中依据得到的新信息不断地修正自己最初所持有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分散性的、掌握在个人手中的知识和信息。原则上民主是没有界限的,必须将可能多的个人纳入人民 (demos)的界线之内。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民主具有产生真理汇聚的作用。因此,民主所暗含的一个重要价值便是认识论上的真理性。
然而,真理性并不是民主的全部。如果真理性是民主的唯一目的,那么投硬币也是民主,因为它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机会,来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在我们的通常理解中,投硬币并不是民主。因此,民主当中一定存在着除真理性之外的其他规范性的价值。例如,父母在做出重要的家庭决定时,他们有理由询问他们孩子的意见,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孩子的意见必然能够为父母的决定更为明智提供一种帮助,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认为他们咨询孩子的意见是正确的方式。同样,在民主的政府治理过程中,一些涉及重要的尤其是影响到每个人生活的政治决定,每个人都应该在决定制定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不是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正确的结果,而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每一个人的平等参与显示的是对于他们作为公民的内在尊重。正如艾丽斯·M.杨所指出的那样,“现实中存在的民主政治被各种对决策拥有不平等的影响力的群体或者精英所支配,而其他人则不能对那种决策制定过程及其后果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而是被边缘化。从这种直觉来讲,强有力的并且在规范上正当的民主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应当平等地包容所有那些会受到决策影响的人。”〔8〕为了获得那种关于行动的最明智和最恰当的政治判断,包容性的政治讨论应该成为民主政治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观念的核心便是在决策制定中实现尊重,而对政治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不宽容、种族主义、男权至上主义、经济剥削与掠夺以及其他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就各种诸如此类的政治排斥存在的程度而言,所谓的民主社会是不会兑现其承诺的。在这里,民主的规范性承诺所显示的并不仅仅是对于认识论上真理的尊重,而是道德上的对平等的公民同胞的尊重。
因此,认识论上的真理性仅仅是民主光谱的一极,光谱的另一极则是道德上的平等性。民主所蕴含的规范性理念和承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识论上的效率和专家知识,另一方面是道德上的平等性和包容性。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民主规范性承诺的这两个方面,而且还要理解真理性和平等性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张力。①See Eric MacGilvray,“Democratic Doubts Pragmatism and the Epistemic Defense of Democracy”,22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Number 105,115-117(2014).这是因为某种特定的人群 (people),要想能够作为人民 (demos)而发挥功能,米勒 (David Miller)认为该群体必须拥有以下四项品质。②See David Miller,“Democracy's Domain”,37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01,208-209(2009).(1)同情性的身份,它要求可能隶属于人民 (demos)中的那些个人,在政治生活中需要与群体中的其他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以此来调试他们之间有时相互冲突的利益和确信。换言之,人们不应该将群体中其他人当成追求自己目的的障碍,复数性的人的存在应该是政治生活中协调一致行动 (act in concert)的必要条件。(2)伦理原则的潜在共识,这种共识并不意味着对每一种原则的完全同意,实际上对此存在着合理的分歧。其所需要的只是要在基于政治共同体承认的显见 (prima facie)有效的原则以及基于私人确信的原则之间做出区分。只有具备了这项条件,民主审议才是可能的。(3)人际间的信任,即在民主的游戏规则中人民 (demos)中的成员必须保有充分的信任。信任意味着要遵守民主的决定,即便是一个人发现他处于失败的一方。不仅如此,信任也在决定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参与人不得不相信其他人所提出的论证是真诚地做出的,相信用正当性证明其立场的原则。(4)群体的稳定性,稳定性使得群体成员在时间的流逝中持续性聚集在一起,以决定一系列不同的议题成为可能。稳定性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稳定性联结着真诚与信任。在某一点做出的决定能够为将来的类似决定提供参考依据,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期待决定的持续性。因此,作为一种政府组成形式以及治理方式的民主,其中所暗含的人民不可避免地有着内在的界限和范围。
换言之,虽然民主在原则上是没有限制的,必须以最大程度的平等性和最大范围的包容性为旨归,民主需要保持不断更新和进步的可能性,但民主功能的有效发挥却要求在实践中,合理地将平等性和真理性拉向彼此相反的方向之上。因此,民主理论的核心也是困难之处,就在于在民主的真理性和平等性这两个充满张力的道德承诺之间做出合理的取舍和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概念上含有真理性和平等性的民主,在实践中便孕育富有弹性和语境依赖的制度性安排和选择。有时候,就像在形成一些涉及复杂技术性的公共事务决策上,我们遵从于专家的职业性知识,即便这是以平等和包容性为代价;有时候,例如在涉及代表的选举上,我们给予每一个人平等的投票,即便这会导致并非明智和非理性的结果;有时候,例如在陪审团审判中,我们将平等性和认识论上的真理考虑结合在一起。在每一种情形之下,我们都是通过权衡民主的真理性和平等性这两种价值,来思考这种张力关系在某个特定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政治性含义。
总之,民主的道德品质就在于民主所具有真理性和平等性这两个存在着张力的价值原则。换言之,任何能够解决宪制民主问题的工具,必定是能够同时含有这两种价值原则的概念。在这里,问题便在于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价值概念吗?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正是在公民能力那里,我们找到了解决宪制民主问题的一个方案。
四、作为构成条件的公民能力
众所周知,西塞罗在 《论共和国》中曾对国家做出了如下著名的界定,“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这种联合的首要原因主要不在于人的软弱性,而在于人的某种天生的聚合性。”〔9〕在西塞罗那里,国家是一种道德共同体,亦即由那些共同拥有该国家及其法律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团体的成员身份乃是其全体公民的共同财富,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相互帮助的好处和正义之治的好处提供给其成员。
在这个意义上,对政府的一般构成来说,公民能力应当成为民主政府的一种构成条件。用密尔的话说就是,“一切旨在成为好政府的政府,都是由存在于社会各个成员中的一部分好的品质为管理集体事务而组成的。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赋予他们以在政府中较之在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响。虽然在任何组织形式下,他们所具有的影响都是政府中一切好事物的根源和阻止一切坏事物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制度所能组织的这种好品质越多,组织形式越好,政府也就越好。”〔10〕既然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是组成社会的人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对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们都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可望的品质。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政府,就很可能在其他一切方面也是最好的,因为政府的实际工作中一切可能的优点正是有赖于这些品质,就政府存在于人民中来说。
从性质上讲,公民能力这个概念,既是描述的,也是规范的。在现代政治社会,主权关系到政府行为的正当性,而主权权力的共享则意味着此种正当性和人民之间的诸种关联。在人民主权的政治话语之中,我们能够将政府决策之权威追溯至人民自己,而且,这一权威必须是广泛的。同时,人民必须有决策的空间以及犯错误的余地,人民自己应当参与政府,虽然他们的参与可能存在着程度上的区别。最重要的是,人民以及他们的代表必须有能力去行使他们的民主责任。①See James Bohman,Democracy Across Borders:From Demos to Demoi(Cambridge,MA:MIT Press,2007),p.5.他们应当具有参与和有效治理的工具,诸如信息、教育以及可行资源。人民与其政府之间的这种关联,就要求在政治实践中,“解释的机构与方法在设计时务必使得这一形式的自由既可以历时可持续,又有能力将人民的意志转移为合理的政策。”〔11〕为了实现更充分的民主,一个国家必须提供有效参与所需要的权利、自由和机会,平等的选举权利,充分理解政策及其结果的能力,以及公民全体得以维护对政府政策和决定的议程进行充分控制的手段。正如经济学者阿马蒂亚·森所说的那样,“成功的民主不仅仅能设计出所能想到的最完美的制度。它不可避免地取决于我们实际的行为模式以及政治和社会互动。将民主问题寄托在绝对完美的制度可靠性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像所有其他制度一样,民主制度的运行依赖于主体人在利用机会实现合理目标上的行为。”〔12〕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公民能力反映的是公民参与政府的程度、意愿、动机以及可行资源。
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公民能力隐含着对于道德平等的内在承诺,这就使得它能够作为评估宪制民主合法性的一个标准。在这里,道德判断的含义是说,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内在价值;谁都不在价值上比别人内在地更优越;而且,每个人的善和利益都应该得到同等的考量。在这里,公民能力是与监护统治相对的一种主张。②参见 〔美〕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2页。在政治公共生活中,虽然我们把一些非同寻常的决定委托给专家,但并不等于我们放弃了对最终控制权的掌握。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教育在政治中不起作用,因为在政治中我们必须和已经受到教育的人打交道。任何想教育成年人的人,其实是想假装成他们的保护者并阻止他们参与政治活动。”〔13〕完整的教育只有当每一个人按其能力参与其所属社会组合的目的和政策制定时才能实现。实际上,在政治公共生活中,正是这一事实树立了民主的重要性。在杜威看来,民主不能被看作宗派的或种族的事情,甚至也不能被看作已获宪法认可的某种政府形式的尊崇。民主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名称,即“人性的因素只有在参与指导共同事物,为此男男女女组成家庭、实业公司、政府、教会、科学协会等群体的事物时,人性才能发展。”〔14〕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公民能力作为民主政府的构成条件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且能够为解决宪制民主的概念性联结提供一种指引。但应该指出的是,公民能力本身仍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切入到宪制民主所产生的实践问题当中,而不仅仅是宪制民主在概念上的相互构成以及相互依赖。换言之,我们必须将宪制民主所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实践问题,而不仅仅是两者在概念上的相互构成与相互依赖,纳入我们的分析视野之中。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更为充分、也更为可行的解决方案。
五、动态宪制的考虑因素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知道宪制民主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宪法问题,即政治权力的存在以及运用必须符合某种规范性的标准,这些标准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先在评价依据,而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构造和组成问题。就政治构成而言,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和选择,不同的政治构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主缺陷,出现民主的赤字,成为宪制民主“问题”。①See Denis J.Galligan,“The Sovereignty Deficit of Modern constitution”,33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703(2013).但是,政治实践中政治构成的这种通常存在的民主缺陷,并不总是演变成为宪制“反民主问题”。更为准确地,我们可以说,宪制和民主这两种规范性价值和理想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问题,便是一种政治制度是民主构成的 (即便是部分,有缺陷的),并且获得了人民的自愿服从和遵守这一事实,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对于实践中政治权力的运用提供正当性证明。在这里,假定了政治权力的持续存在这一政治现实。正如罗尔斯所强调的那样,自由主义合法性原则是与民主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的两个独特特征相联系的:一是政治关系是公民生于其中并在其中正常度过终生的社会之基本结构内部的一种人际关系。其二,在民主社会里,政治权力总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在政治正义的语境中乃是一种公共权力,它永远是作为集体性实体的自由而平等之公民的权力。〔15〕特别是现代宪法国家,宪定权力(constitutional power)运作的合法性,尤其需要一种民主理论予以正当性的证成。因为宪法的修改和完善、政府的日常治理、人民界线问题的强制执行等问题,这些组成了政治权力运用于人民的最重要的方式。
我们知道,在政治权力实践中,宪制民主问题的各种争论通常是由引进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提议一种新的政治方案时所引起的,这时候公民应该如何通过他们的投票来恰当地相互履行他们的强制权力。或者说,我们必须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和理想来行使并评估这种政治权力的运用呢?如果我们这样做,对于自由而平等的他人来说是能够被证明为正当的话。关于宪制民主,问题便在于我们在分析动态宪制时,我们需要将何种因素考虑在内,从而不违背对于民主价值及其标准的忠诚。笔者认为,结合上面有关民主特质以及公民能力的分析,以下四个方面是分析宪制民主所产生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因素。
政治权力实践存在于、发生于一种现存的,特别是具有宪制意义的制度框架之中。这种现存宪制实践框架,为民主合法性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基准线和参考依据。
(1)我们对于现存宪制实践框架的民主忠诚,起源于民主所具有的两个存在张力关系的理想和承诺:道德上的对于人的平等尊重的承诺,认识论上的现存宪制实践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
(2)有关现存宪制实践框架在理论以及实践方面上的怀疑,为政治变革提供了一种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当然,在民主的意义上,对现存宪制实践框架的怀疑,既可以出自道德上的现存宪制实践框架对于人的平等尊重,也可以来自于认识论上的现存宪制实践框架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
第一,有关现存宪制实践框架的诸种怀疑,可能或者典型的是多元的,但它们必然是特殊的。针对的是现存宪制实践框架中的某一或某些组成部分,在适应不断变更情势方面的能力。试图一次改变整个现存宪制实践框架,既不可能,也不融贯。
第二,在更少民主的意义上,即朝向更少的平等主义和包容性的方向上,改变现存宪制实践框架,有时候可以取得民主的合法性。如果这样做是以下两种情形的唯一方法的话,即要么为建立某种现存宪制实践框架,要么为保存现存宪制实践框架以免于恶化乃至发生制度崩溃。
(3)尽管有某些公民的怀疑,当政治变革被采取或者不采取时,无论这种政治变革是由民主的多数,还是一个政治上决定性的少数利益群体,或者是由一群技术性专家提议的,在正当的认识条件下,如果这种政治变革能够向所有的普通公民提供正当性证明,那么拟议的政治变革也可以取得民主的合法性。
第一,拟议的政治变革为了能够被证明为正当的,拟议的政治变革以及政治变革的原因必须是公共的,通过自由而公开的质询,遭受广泛的批评和质疑。
第二,所有的政治变革都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公共理由本质上便总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预期性。这也就决定了政治变革必然要诉诸于并局限于迄今为止所搜集到的证据以及所拥有的经验。因此,所有的民主合法性主张,一定意义上是可错的,受制于新的证据以及经验的修正。
第三,作为取得民主合法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政治变革的提议者有义务根据政治变革自身具有的理由和正当性证明的公共标准,对各种不利于拟议政治变革的证据和论证予以回应和关注。那些反对拟议的政治变革的人,同时也就有充分的动机来提供这些论证和证据。另一方面,政治变革的提议者根据它自身的正当性证明的标准,也就没有义务对那些并非不利于拟议政治变革的证据和论证予以回应和关注,因为对正当性证明标准的理解和运用有时候存在着合理的分歧。
(4)是否选择并采用拟议的政治变革,最终需要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考量之间进行权衡。一方面,拟议的政治变革,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改进或者恶化当前制度框架在民主决策制定方面的能力和绩效。另一方面,现存宪制实践框架向民主方向的每一种拓展,都应该保有民主自身的有效功能为前提。
第一,根据民主本身的规范性价值,现存宪制实践框架切实发挥的功能怎么样。如果我们赞同民主的真理性方面认识论承诺,我们就必须清楚现存制度框架达成明智的决策的能力如何;如果我们主张民主平等性方面的道德上理想,我们就必须理解现存制度框架是否排除了应该纳入民主领域的情形。当我们已经有一个功能良好的民主时,这里就存在着一种不去改变现存制度框架的显见理由。
第二,现存制度框架的改变将如何改变民主自身的特质,又将如何改变普通公民之间的固有联系。拟议的政治变革对于公民之间相互信任以及当前制度框架的共享理解,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拟议的政治变革对基于某些特别的原因,仍然没有被包含在当前制度框架的局外人,可能会产生何种性质和范围的外部效果和影响。同时,这种影响是系统、制度性的,还是偶发、个别性的。
第四,当我们能够预测相关的外部效果和影响时,控制它们是否实际可行。例如,建立某种更高级的制度将强制性措施强加到局外人之上。如果这样做,局外人所在的 (政治)共同体又会做出何种反应性的政治行为。此外,也会存在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应该由谁来建立、依据何种程序建立等问题。
总而言之,以公民能力依据来分析宪制民主所产生的问题,特别是判断拟议政治变革的民主合法性,它在以下三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应对策略。首先,不同于主张策略坚持的每一种特殊的情形都需要它自己特殊的对策,由于将现存制度框架纳入了分析视野,公民能力视角更加注重制度发展及其转型的路径依赖特征。任何制度的发展及其转型都是在现存的某种既定框架之内进行的,总是新旧不同的制度组成部分在新的情势下不断试验、相互竞争和调试的产物。其次,由于公民能力视角强调宪制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以,它就不同于传统的宪法爱国主义,公民能力视角在解决宪制民主的问题时就能够对政治体的内在结构保有清晰的认识,可以避免解决策略所可能出现的无效性。同时,由于公民能力视角引入了民主自身的特质,这就使得它能够批判性地看待各种以民主的名义提议宪制发展及其转型的政治要求,体认到宪制民主发展本身的限度。最后,以公民能力为视角分析宪制民主问题,由于更强调普通公民在政治权力运用过程的参与,所以它也就不同于消极策略将公民能力视作一种政治现实,而是将其看作是需要科学界定、认真培养的政治构成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普通公民有权利要求政治权力的运用必须获得正当性证明,政治行为者也有义务向受制于政治权力的普通公民做出正当性证明。①See Rainer Forst,Justice,Democracy and the Right to Justification:Rainer Forst in Dialogue(London:Bloomsbury,2014),p.6 and passim.公民能力视角下的普通公民,不仅是政治权力运用过程中的参与者,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权力运用的实行者。
重要的是,以动态宪制和公民能力为基础,我们可以说在政治现实中没有任何一种现存的制度及其实践,能够完全地符合民主合法性的理想和标准。这一事实意味着民主与完美事实上是不可达到与飘忽的,人类的手永远不能够触及它,它既鼓舞你成功,同时又不让你成功,它的作用是便于把人力中各个部分里的事理联系起来。我们需要寻找的是现存宪法的精神,而不是一部更出色的宪法。最终的问题就不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宪法是否满足了最高的道德标准,世界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宪法曾经接近过这一标准,而是它是否足够良好,从而值得怀有尊敬的和良心上的支持。诚如阿克曼所言,如果现存宪法,就其历史成就的道德性质而言“足够好”,就其提供了接近现有争议的合理公平的办法而言“足够好”,就其将未来开放给允诺进一步政治成长的民众政府而言“足够好”,①参见 〔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那么,比起推到重建,我们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它,将取得更大进步。
用达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并不是一次性的发明,或者只是存在于某一地方。”〔16〕无论何时,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能够被独立地发明和再发明。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合法性,就不是一种确定的状态,也不是一种未完成的事业,毋宁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恒久政治作业。只不过,民主作业的这种实现,应该始终掌握在普通公民的手中,如果我们选择继续保持对民主理想的忠诚和信仰的话,我们尤其应该记住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 〔M〕.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217.
〔2〕〔美〕戈登·伍德.民主与宪法 〔A〕.佟玉平译.佟德志编.宪政与民主 〔C〕.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7.
〔3〕〔法〕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 〔J〕.吕一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52-353.
〔4〕〔印〕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 〔M〕.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4.
〔5〕〔德〕J.哈贝马斯.民主法制国家:矛盾的诸原则之间一种背谬的联结?〔J〕.薛华译.世界哲学,2002,(6).
〔6〕〔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 〔M〕.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350.
〔7〕〔美〕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 〔A〕.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7-28.
〔8〕〔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 〔M〕.彭斌、刘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4.
〔9〕〔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 〔M〕.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9.
〔10〕〔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 〔M〕.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24-25.
〔11〕〔美〕斯蒂芬·布雷耶.积极自由:美国宪法的民主解释论 〔M〕.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1.
〔12〕〔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 〔M〕.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29.
〔13〕〔美〕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M〕.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166.
〔14〕〔美〕约翰·杜威.哲学的改造 〔M〕.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119.
〔15〕〔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 〔M〕.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200.
〔16〕〔美〕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 〔M〕.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
(责任编辑:谢莲碧)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法治中国的理论与实践”、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辽宁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5LSLKTZIFX-0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6-05-16
[作者简介]齐伟,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实验教学中心讲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法学。 辽宁沈阳 110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