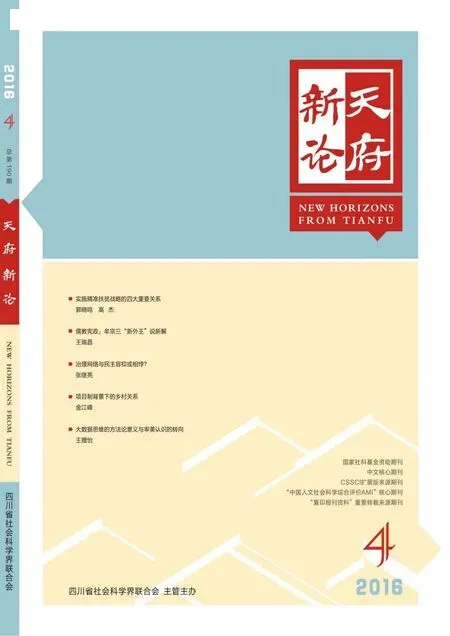畿服之制与天下格局
齐义虎
畿服之制与天下格局
齐义虎
摘要:畿服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是古人对于天下格局之政治思考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历史上的畿服制主要有“三服制”、“五服制”、“六服制”、“九服 (九畿)制”等四种说法,其所对应的地理空间分别是方三千里、方五千里、方七千里和方一万里。其中最为流行的当属“五服”说和“九服”说,“三服”说和“六服”说可分别看作它们的附属简约版。近代的康有为曾试图借助畿服制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近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整合问题。在中国崛起复兴的过程中,畿服制的差序格局依旧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关键词:畿服制 五服 九服 天下格局 康有为
一、引言
畿服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是古人对于天下格局之政治思考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中国一词便来自于这种空间政治学的自我定位。畿即王畿,方千里,是天子直辖的区域。贾公彦注疏云:“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国城,面各五百里,制畿界。”〔1〕服则是对王畿之外区域的统称,包括封建之诸侯及四方之蛮夷,其本意乃是服从。郑玄注云:“服,服事天子也。”〔2〕韦昭注云:“服,服其职业也。”〔3〕根据与天子关系的密切程度,服又可以由近及远分为多个层次。整个畿服制便是以王城为中心的一套政治空间之差序格局。
基于盖天说,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大地就像一个正方形的棋盘,向四周延展。所以对于地理空间的畿服制构想也正是一圈一圈朝向四方的回字形外放,就像北京层层扩张的环路一样。这种类似俄罗斯套娃的空间秩序结构反映了大一统天下格局下多层次治理的封建政治礼制。借用周振鹤教授的话说,如果九州制是一种“分块式结构”的话,那么畿服制则可被称作“圈层式结构”。〔4〕只不过这里的圈不是圆形的,而是方形的。
当然,这种畿服制的礼制安排既有史实的依据,也有理想的成分。对于今人而言,与其费尽心力去考证其历史的真实性,不如将之视作古人对我们的智慧启迪。从畿服制这一理想模型的设计中,我们不仅可以获得一种观察当今世界的不同视角,更可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自身。在中国崛起与复兴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人正逐渐恢复文明自信,这使我们在思维上有可能跳脱出现有之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从古老的畿服制中寻找灵感,重新激发出中国人对于新天下格局的想象和规划能力。
历史上的畿服制主要有“三服制”、“五服制”、“六服制”、“九服 (九畿)制”等几种说法,其所对应的地理空间分别是方三千里、方五千里、方七千里和方一万里。在三服制和五服制中,王畿本身即是一服。但在六服制、九服制里,王畿则不算在其中。如果加上王畿一服,则六服实乃七服,九服实乃十服。虽然各种畿服制的地理空间大小不一,但每服一千里则是统一标准。①后世有的学者对此或有不同意见,下文将具体讨论辨析。在这四种畿服制中,最为流行的当属“五服”说和“九服”说,“三服”说和“六服”说可分别看作它们的附属简约版。
此外,近代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和康有为对畿服制也有所论述,但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廖平主要是力图从学术上弥合五服制与九服制之间的今古文分歧,以此应对来自西方之现代地理学对于中国中心说以及传统经典的挑战。康有为则出于其热切而冷静的现实考虑,试图借助畿服制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近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整合问题。出于本文之写作目的,将仅对康有为的论述予以简单介绍,廖平的相关学说另文讨论。最后还将探讨畿服制对今日中国之启迪。
二、五服制与三服制
关于五服制最权威的记载出自 《尚书·禹贡》②除了 《禹贡》之外,还有两个文献对五服制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荀子·正论》:“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埶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国语》与 《荀子》的记述大体一致,应该来自于同一个版本。《禹贡》中的第三服——绥服在这里被写作宾服,“宾”亦有服从、归顺的意思,与“绥”大意相同。只不过以祭祀为标准的“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朝贡制度似乎比 《禹贡》的更简略也更为严厉。: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所谓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东西南北每个方向各以五百里为等差递推,两面相合则每服一千里,总计方五千里。处于中心位置的甸服是天子的直辖统治区,其余四服则是封建的诸侯国和蛮夷部落。各服根据其距离之远近对中央的天子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义务。《禹贡》之“贡”便是诸侯向天子纳贡的意思,孔安国对这个题目的解释便是“禹制九州贡法”。不过,这里的“贡”实则还包括“赋”。孔颖达的注疏云:“赋者,自上税下之名,谓治田出谷。”“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5〕赋与贡的区别在于:“赋出于百姓,贡出于诸侯”;“赋止甸服,贡兼九州”;“赋止中邦,贡兼四海”。〔6〕
五服中的甸、侯、绥三服,地方三千里,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由于其文化程度高于要、荒二服,故谓之中邦。在中邦,天子与诸侯皆可以向其各自辖区内的百姓直接收税,是为赋。此外,诸侯还要从他的赋税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采购换取当地的特产,进献给天子,这就是贡。对天子而言,甸服之内可以直接收取赋税,甸服之外则可获得上贡;赋属于直接收入,贡属于间接收入。要、荒二服的君长,虽不在中邦之内,以其慕义向化之诚,亦可有所贡献,唯不加强制而已。如此一来,从贡赋制度上看五服便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区域:最内圈的甸服需要治田纳赋,属于天子直接统治区;次一级的侯、绥二服要定期定额③胡渭认为:“诸侯以什一之法取民,谓之赋。出其所赋什之一,市土物以上贡天子,谓之贡。”二者皆执行十分之一的税率。见 《禹贡锥指》,第667页。向天子上贡,属于间接统治区;最外围的要、荒二服负担最轻,没有进贡的硬性规定,属于非统治的羁縻区。
以上只是粗略的划分,具体到每一服内部又有更细致的区别。比如甸服又被等分为五个一百里宽的环形地带。最近的一百里由于交通方便,所以要纳总。孔传曰:“禾槀曰总,入之,供饲国马。”〔7〕收割下来的禾类作物要连带着禾杆一起送到王城,其中的禾杆可用作草料饲养马匹。二百里的地带开始稍微远了一些,为减轻运输负担,只需交纳剪下来的禾穗,免纳禾杆。三百里的地带更远了点,且处于甸服的中间区域,所以他们只需缴纳秸秆,同时负责转运四百里和五百里的粟米,以劳役代替赋税,不必缴纳粮食。④“金氏 (履详)曰:服役独在三百里者,盖酌五百里之中,为转输粟米之赋也……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复言纳。盖不远纳于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转而输之于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远郊之米粟而为之转输,力若劳而赋则省。”见 《禹贡锥指》,第667页。四百里和五百里只言粟米而不言纳,可见不必亲自输运至王城,而粟米之别在于有壳无壳,有壳易于保存,无壳不可长久。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将禾类作物在本地预先进行初步的加工处理,便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中途运输的重量。
甸服之外的侯服,由于毗邻天子的王畿,地理位置格外重要。如果说甸服为天子提供的是经济财政保障的话,那么侯服为天子提供的则是军事安全保障。“侯,候也,斥候而服事”〔8〕,“以为天子之蕃卫也”〔9〕。“百里采”,因临近天子直辖区,用于分封天子畿内卿大夫之食邑。“二百里男邦”,用于分封子男之类的小国。“三百里诸侯”,余下的三百里地带则用于分封公侯伯之类的大国与次国。用林之奇的话说:“输赋税,则远者轻而近者重;建侯邦,则远者大而近者小。”〔10〕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呢?这正是封建制的均衡机制。首先,以百里采邑为王畿与诸侯国之间的隔离缓冲地带;其次,小国在内便不得不依附于天子;再次,大国在外则可以有效抵御外侮。故吕祖谦评价说:“男采在内,既足以护王畿,又去王畿近,强悍诸侯,不足以陵之。此圣人制内外之轻重,不差毫末,所谓天下之势犹持衡也。”〔11〕
接下来的绥服,依旧是用来封建诸侯的区域。孔传云:“绥,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政教。”〔12〕从下文的“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来看,这里的“安”乃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诸侯安服于天子之政教,一方面则是诸侯拱卫起王畿之安全,一文一武,并行不悖。金履祥对此之解释最为全面,他说:“内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华夏之教,以抚要、荒;外二百里奋武卫,所以御要、荒之变,以安华夏。”〔13〕
前文曾提到,甸、侯、绥三服又合称中邦,中邦亦即中国。胡渭云:“古之所谓中国者,《禹贡》甸、侯、绥方三千里之地也。所谓四夷者,要、荒方二千里之地也。”〔14〕与作为文明高地的中国不同,要、荒二服主要是少数民族所在的区域。四夷又写作四裔,裔的本意指衣服的边缘。《说文·衣部》:“裔,衣裾也。”后来借指边远的地方。故对此区域,天子不过羁縻之而已,依其本俗自治,一般不加干涉。要服之要读作yāo,约束之义,意在保证其有所约束、不至捣乱即可。荒服之荒,王肃解作“政教荒忽”〔15〕,韦昭解作“荒忽无常”〔16〕,金履祥解作“四远蛮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谓之荒”〔17〕。相比于尚有所约束的要服,荒服则更为放任,来者勿拒,去者勿追。班固云:“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 使曲在彼。”〔18〕
至于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可分别对照观之。南蛮、东夷皆是族名,举蛮夷自然包括戎狄在内。就其字义而言,“夷,易也,无中国礼法,易而已。”〔19〕“蛮,慢也,礼仪简慢。”〔20〕蔡读作 sà,与流皆有流放之义。此外,流还有“其俗流移无常”〔21〕、“流行无城郭常居”〔22〕等意思。依据流放距离的等差亦可见服制内外之别。《大学》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尚书·舜典》有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孔传曰:“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23〕《唐律疏议》中这段话的引文稍有差异:“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疏议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24〕可见,在唐人的理解中,四裔相当于海外,千里亦即中国。对于天子而言,最轻的流刑是将犯人逐出千里王畿,中等的流刑则将犯人逐出华夏九州,最重的流刑则将犯人驱逐至更为遥远的四裔海外。后世每等流刑之间相差五百里也刚好与畿服制中每服之距离相当。胡渭认为,“大罪四裔,即荒服所谓二百里流……其次盖要服所谓二百里蔡……又其次则当在绥服奋武卫之地。”〔25〕但这里有一个矛盾之处,胡渭以五服皆在九州之内,那么要服之二百里蔡和孔传所说的“九州之外”便明显不合。这就进一步涉及到关于九州范围的问题了。
关于九州之疆界,《尔雅》《职方》《王制》与 《禹贡》在记述上皆不同,战国时更有邹衍之大小九州说。暂且撇开大九州说不论,单只华夏九州便有小中大三种之说,分别是方三千里说、方五千里说、方七千里说,与服制相对应亦可称作三服说、五服说和六服说。贾公彦疏云:“先王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26〕关于中国,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标准。狭义的中国即天子之千里王畿,自居九州之一;广义的中国则泛指整个华夏文明区,除了天子王畿之外还包括各个诸侯国。贾疏这里的中国应作广义之理解,其七千、五千、三千之次第刚好与此大中小之九州三说若合符节。畿服制中的三服说便与九州之范围界定密切相关。
《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则九州大小相同,各方千里,其全域总计方三千里。其在服制上的划分便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这里的采服相当于 《禹贡》的侯服,盖取其“百里采”之名;这里的流服相当于 《禹贡》的绥服,盖取其流于千里之外,若“二百里奋武卫”者也。天子自居中间一州,王畿千里,谓之中国;四周八州环列,方三千里,谓之九州;九州之外则夷狄所居,王者不治,谓之四海。①《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中国 (一服)—九州 (三服)—四海 (三服之外),便是 《王制》所展现给我们的天下格局。与 《王制》一样主张三服制的还有 《逸周书·王会篇》,其文云:“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是皆朝于内者”。〔27〕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言:“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只是三服的名称各家有所不同。
对于三服制之规模,《吕氏春秋》有这样一个解释:“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28〕按照当时的统治技术,方千里之国应该是一个极限了,再大则不便于管理,虽有若无,所以天子之王畿最大也就是一圻之地。而从语言的覆盖区域来看,华夏各国之间或有方言之差异,但毕竟属同一种语言,彼此无需翻译,这个区域大概也就方三千里,正好是三服制和五服制下中邦的范围。故三服制实即五服制之中邦,五服制则是三服制之扩展,二者都以方三千里作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只不过五服制又开拓了要服与荒服两个边疆羁縻区而已。
胡渭对 《禹贡》中的五服、九州、四海等范围有一个总结:“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四海之内,分为九州。九州之内,制为五服,以别其远近。甸、侯、绥为中国,要、荒为四夷,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余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蛮之地,不登版图,不奉正朔,王者不以治治之,是为四海。此《禹贡》五服、九州、四海之名义也。”〔29〕按照这一说法,自内而外可以形成“王畿(一服)—中国 (三服)—九州 (五服)—四海(五服以外)”这样一个政治空间的差序格局。但为了化解前文所说之“九州之外”的矛盾,我们可以结合三服九州说对胡渭的说法做一个修正,即以王畿为中国,以三服为九州,以要、荒二服为四裔 (又作四夷),以五服之外为四海,另外再结合《尔雅》四海之外更有四荒、四荒之外复有四极的说法,形成如下一个新的内外空间次序:“中国(一服)—九州 (三服)—四裔 (五服)—四海—四荒—四极”。
三、九服制与六服制
关于九服制的记述主要保存在 《周礼》中,分散于 《大司马》《职方氏》《大行人》等几部分。其中大司马是夏官之正卿,为主管征伐之军事长官;职方氏为其属官,职在制定四方之贡赋;大行人则隶属于秋官大司寇,主管朝觐会同之礼仪。由此可见,九服制与天下的军事安全、朝贡职责密切相关。
《大司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30〕
《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31〕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32〕
此外,在 《逸周书·职方篇》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乃辩九服之国: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拜国,大小相维,王设其教。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
其所有。”〔33〕
与五服制相比,九服制将天子直辖的方千里之中央王畿单独列出,虽然在称谓上有国畿、王畿、王圻的分别,但不再作为一服则是其共同特征。故九服制名为九服,实则十服。按每服单面五百里、双面一千里计算,则九服所覆盖的区域已经达到方万里,远远大于五服制的方五千里。如果忽略掉九畿与九服在通称上无关紧要的细微差异,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于三服制在专名上的混乱和不统一,九服制虽然在服制上更为复杂,但各服专名却高度一致,除了《大行人》将“蛮服”写作“要服”外,基本上自内而外可以划分为“王畿—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值得注意的是,九服制下侯服与甸服的位置和五服制下的顺序完全相反。廖平对此的解释是文字误倒,主张应改与 《禹贡》一致,甸服在内而侯服在外。〔34〕但九服中的甸服并非王畿,似乎不可与五服中的甸服等同视之。且 《尚书·康诰》里的“侯、甸、男邦”,《尚书·酒诰》里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以及 《尚书·周官》里的“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其顺序都是侯在甸前,二者之位置似不可轻易改动。裘锡圭先生认为:“《国语·周语上》和 《尚书·禹贡》的五服说,则把王畿称作‘甸服’,跟‘侯甸男卫’的‘甸’实际上捏合不到一处去的。有的学者认为甲骨、金文里的有些‘奠’字应该读为畿甸之‘甸’。那么,五服说的‘甸’跟九服说的‘甸’,也许本来并不是一个词。”〔35〕如果九服中的“甸”通假于“奠”,是“举行某种仪式,表示新邑正式落成”〔36〕的意思,类似我们今天讲的奠基,那么这里的甸服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含义了。
与廖平持同样观点的郭声波认为:“《禹贡》五服制反映的是春秋以前的情况,那时还没有出现介于王畿和诸侯之间的郡县,所以 《禹贡》的甸服就是指王畿。而 《周礼》九服制反映的是战国以后的情况,九服内容可能是汉武帝时人所加,其甸服应该是指作为王畿外延的郡县地区,这样才能解释上述矛盾。”但结合着战国时代新兴的郡县制,他又说:“郡即‘君邑’的合体,县 (通悬)即悬绝在外的飞地,用甸服来表示是极为恰当的。”〔37〕照他后面的说法,甸服虽在侯服之外,隔着中间的分封诸侯国,但作为飞地依然可以是直属于天子的统治地带。而且从军事安全上看,这种类似汉代郡县与封国并行的犬牙交错布局,在封建体制下未尝不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均衡性牵制。此外,林欢在对商代方国进行研究时也发现,在只有内外服之分的时候,“商代外服从管理权上分,就是诸侯 (附属国族)所有和商人直接控制两种 (多田、多奠),后者就是‘甸服’的前身。”〔38〕考虑到周公斥大九州、加封五等之国的新封建之说,九服中的甸服很可能是王畿在千里之外进一步开辟的直辖区,非如此不足以增强王畿之实力、维护天子之权威。
从名称上看,除了侯、甸是旧称和镇、藩是新造外,男、采、卫、蛮、夷这几个都可以在 《禹贡》的五服制中找到根源。按照贾公彦的注疏:
“云‘侯’者,候也,为天子伺候非常也。云‘甸’者,为天子治田,以出赋贡。云‘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职事。云‘采’者,采取美物以共天子。云‘卫’者,为天子卫守。云‘蛮’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系之以政教。自此已上六服,是中国之九州。自此已外,是夷狄之诸侯。此蛮服出 《大行人》,云‘要服’,亦一也。言‘要’者,亦见要束以文教也。云‘夷’者,以夷狄而得夷称也。云‘镇’者,去中国稍远,理须镇守。云‘蕃’者,以其最远,故得蕃屏之称。此三服总号蕃服,故 《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指此三服也。”〔39〕
名者实之宾也,通过字义的解释便可初步窥见九服各自不同的政治责任。与五服制可以区分为前三服与后二服类似,九服制也可进一步划分为前六服与后三服,前者属于九州以内,后者处于九州以外。正如前引 《大行人》一段所揭示的,这种前六后三的区分是与其政治义务相对应的。侯服紧邻王畿,故须每岁朝见,贡献祭祀所需的牺牲等物。甸服次之,每二岁朝见一次,贡献丝枲等妇人所为之物。按照依次递减原则,男服每三岁一朝见,贡献尊彝等器物。采服每四岁一朝见,贡献玄纁絺纩等衣服之物。卫服每五岁一朝见,贡献珠、玉、石、木、金属、象牙、皮革、羽毛等八种材料。要服每六岁一朝见,贡献龟贝等充当货币的财物。至于后三服,因其路途遥远、文明未完全开化,仅需终其一代朝见一次即可,所贡献之物也无特别要求,只以其所视为珍宝之物来献即可。与 《禹贡》的五服制相比,九服制除了纳贡的职责外还多了定期朝觐的义务:“侯服比年朝,甸服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卫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六服从王巡守。”〔40〕如此频繁的朝觐有利于天子与诸侯国的政治沟通和联系。
如前文所述,《王制》以方三千里为九州,《禹贡》以方五千里为九州,此处之 《周礼》更以方七千里为九州,显示了中国人活动空间的逐步扩大。廖平认为,“《王制》的‘甸、采、流’三服之制是孔子对中国本身的规划,而 《周礼》的‘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之制是孔子对世界的规划。”〔41〕贾公彦疏云:“先王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结合着“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来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便是:衰乱世夷狄内侵、版图缩小,华夏文明区只有方三千里,另外周边有方二千里的羁縻缓冲区;升平世尊王攘夷、稍微扩大,华夏文明区拓展到方五千里,周边方二千里的羁縻缓冲区亦得相应外推;太平世天下一统、文教兴盛,华夏文明区进一步拓展到方七千里,剩余方三千里为夷狄所居,向义慕化,内外相安无事。从服制上看,《禹贡》与 《王制》的五服说和三服说接近于衰乱世之制,《周礼》与 《逸周书·职方篇》的九服说和六服说则更像太平世之制,至于升平世之制则其详不得闻焉。①《河图括地象》有比较简略的记载:“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不过我们须知,衰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只是一个理想的逻辑顺序,而不必然是一个线性的时间顺序。不可据此判断 《王制》在年代上一定早于 《禹贡》,《禹贡》又一定先于 《周礼》。正如郑玄所言,五服之名乃尧之旧制,“唐虞土方万里,九州之内,地方七千里”,“禹承尧舜而然矣”,“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42〕按郑玄所说,时间上的次序是先下落再上升,即先从唐虞的太平之制退化为殷汤的衰乱之制,然后又从殷汤的衰乱之制再次进化到周公的太平之制。这期间既有进步也有退步,乃是一种回环往复,而非单一的线性进化。
与三世说的区别对待不同,针对九服制方万里与五服制方五千里的差异,历代学者基于实际疆域的客观考虑,多有不愿接受者,于是千方百计在理论上进行弥合。其弥合的方法总结起来不外三种:一是区别鸟迹与人迹——鸟迹即空中之直线距离,人迹则地上之曲线距离。贾公彦认为:“若据鸟飞直路,此周之九服亦止五千。若随山川屈曲,则《禹贡》亦万里,彼此不异也。”〔43〕也就是说,《禹贡》之五千里是鸟迹距离,《周礼》之万里是人迹距离,二者之里数虽有不同,实际所指却无别。胡渭对此观点批驳说:“按二经里数皆以开方言之,无计人迹屈曲之理。贾说非是。”〔44〕二是将五服的五千里拉升至万里。郑玄抓住 《尚书·益稷》中的一句“弼成五服”,将 《禹贡》中对每服五百里内的详细阐释也看作是五服之外的又五百里扩展,所谓“五服已五千,又弼成为万里”。〔45〕但 《尚书》原文在“弼成五服”之后紧接着的一句便是“至于五千”,而非“至于万里”,可见郑玄的解释未免牵强。也许正是由于看到了郑玄之说的困难,于是有人又发明了第三种说法,即将九服制的万里降到五千五百里,从而向五服制的五千里靠近。陆佃在其 《礼象》中说:“郑氏谓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读 《周官》之误也。盖 《禹贡》言面,《周官》言方。言方则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46〕也就是说,五服制的每服单面即五百里,双面则一千里,而九服制的每服单面只有二百五十里,双面合计才五百里。这样一来,九服双面总计四千五百里,再加上畿内一千里,一共五千五百里,比 《禹贡》的五千里还是多出了一个“藩服”。而且,按照 《周礼》的封建制,公国之地方五百里,侯国之地方四百里,伯国之地方三百里,子国之地方二百里,男国之地方一百里,以单面每服二百五十里的宽度,公、侯、伯之国岂不是要兼跨两服之地了吗?以上三种弥合之说皆有其不足,反不如三世说的解释更为合理。
畿服制的通则是详内而略外,九服制亦然。要服以内谓之九州,九州之外谓之藩国。方七千里之九州所对应的正是六服制。“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贡之岁,四方各四分趋四时而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觐秋,或遇冬。”〔47〕如果将天子直辖的王畿视作内圈,那么六服之九州便是中圈,三服之藩国则是外圈。外圈乃夷狄所居之地,“王者之于夷狄,羁縻而已,不可同于华夏”。〔48〕故 《白虎通》有天子不臣夷狄之说,华夏的各种礼仪法度主要实行于六服以内。对于六服其实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不包括王畿的六服,即侯、甸、男、采、卫、要;一种是包括王畿的六服,即畿内、侯、甸、男、采、卫。①《尚书·周官》中有“六服群辟,罔不成德”和“六年,五服一朝”之说,为协调六服与五服之前后矛盾,蔡沈将六服解作“侯、甸、男、采、卫并畿内为六服”,朝觐则除畿内外刚好五服。见 (宋)蔡沈注:《书集传》,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23、226页。相比之下,孔颖达的疏解云:“计六年大集,应六服俱来,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为侯、甸、男、采、卫,盖以要服路远,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朝,故宽言之而不数也。”此种解释未免牵强臆测。见 《尚书正义》,第707页。这其中的关键便是要服。要服又称蛮服,依据前文的释义,“要”有约束于文教之义,故许其进也;“蛮”则有礼仪简慢之义,故退之与夷、镇、藩并列。一字之别,《春秋》褒贬进退之法尽在其间。
四、中国崛起与天下格局
近代以来,西方的炮舰毫不留情地把中国从天下之中心驱逐到了世界的边缘,甚至差一点开除球籍。相对于欧洲这个新的世界中心,昔日的中央之国变成了地理上的远东、政治上的半殖民地。但幸运的是,中华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经受住了一系列的生死考验。经过150多年的全民族奋斗,中国逐步走出了衰败的窘境,不仅没有像奥斯曼、奥匈等老大帝国一样分崩离析,反而因善于学习而愈加强壮,在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后来居上,成为多极世界中的巍巍一极。按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口等综合国力来衡量,中国、美国与欧洲无疑是第一梯队的全球性三极,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则属于第二梯队的区域性四极。这又将是一个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大时代。
从历史上看,世界的文明重心主要在北半球,南半球多处于从属地位。中国与欧洲分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美国则横亘北美大陆,三者皆有背北面南、君临天下之势。相对于北半球的三大区域,欧洲之南是非洲,中国之南是亚太,美国之南是拉美,作为南半球的后三者更像是前三者的后院和势力范围。区域性四极中,俄罗斯、日本处于漫长的衰退之中,尤其是人口危机,使之短期内皆难以重振雄风;印度和巴西则在慢慢上升,但其内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尚不具备挑战第一梯队的实力。至于美国和欧洲,虽然已经出现颓势,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撼动其霸主地位。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既然短期内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唯一中心,那么就不得不在中—美—欧的三极大格局中与其他各极长期共存、彼此制衡。
从前面我们对畿服制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还是三服制、五服制、九服制,其共同的治理原则就是“别内外”,这也正是公羊学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一科三旨的礼治精神所在。在今天这个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越是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越是要首先坚定自己的国族立场,避免被西方的经济学意识形态洗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外利益输出,拿中国人的资源和劳动补贴别国的消费。中国的发展首先应有益于中国人民,其次才是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进步。所以,经济发展的成果绝大部分要留在国内,为本国人民所分享,而不能被国际资本拿走。古代有农本商末之说,今天可以发明一个“内本外末”之说,即国民经济应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占的比例不宜过高。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内部的共同富裕,避免我们自身分裂为贫富分化严重的三个世界。“内外有别、先内后外”应该成为我们的经济国策。
中国国土之大、人口之多,本身就是一个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超级社会。为了更好地落实别内外的国策,我们不妨借用畿服制的模式,对我们的国土及势力范围做一个差序格局的空间安排。在朝贡体系下,明清时期的中国大体可以划分为“朝廷—行省—内藩—外藩”四个层次,朝廷是中央所在地,相当于畿服制中的王畿;行省相当于诸侯国,但比封建制更为强调中央集权;内藩是国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以本族的土官治理为主,中央政府给予其高度自治权;外藩也即藩属国,形式上乃是独立的国家,唯在政治关系上承认中国为其宗主国,如朝鲜、越南、尼泊尔等。
晚清时期,康有为为了维护中国的版图完整,也曾设计过类似的畿服制治理结构。在写于1903年的 《官制议》中,他说:“昔 《禹贡》分别五服,极有旨意,后世不知此义矣。今分国为二服,凡东、西、南、北、中五部曰甸服,辽、蒙、回、藏四部谓之卫服。甸服专用中央集权之法,卫服专用分设政府之法,云南僻远而界英、法,属多土司,可略采卫服之制。”〔49〕其所谓甸服,就是将原来的汉地十八行省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此外又设置四个边疆部,即东北三省曰辽部、内外蒙古曰蒙部、新疆曰回部、西藏曰藏部,组成卫服。甸服五部,相当于皇帝直接治理的区域,所以实行中央集权制,也即郡县制;边疆四部,相当于内藩,实行分设政府的间接统治之法,也就是封建制。
到了1912年,康有为在其 《废省论》中更进一步将原来的甸、卫二服制细化为甸、要、荒三服制。“今吾欲划中国为三服,其长城及截海以内,中国旧壤,曰甸服,以府州利尹治之,府即州也。……沿边要地,命曰要服,以道治之。若滇、桂之边,琼州之岛,东三省之边,四川之边,新疆之近边,内蒙古之近边,是也。道立巡抚,若必不用旧名,则今之名宣抚、镇抚、观察皆可也。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三省之边,命曰荒服。此可用今制之都督治之。……藏总督驻拉萨,新疆名不文,汉名西域宜用之,西域总督驻伊犁,外蒙古总督驻库伦,内蒙古总督驻归化城,如英之印度总督、法之安南总督、荷兰之爪哇总督、日本之台湾总督之制,兼总兵财、民政。”〔50〕在康有为看来,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实行的正是类似 《禹贡》的五服制。“考之英之自治,英伦甸服也,士葛兰、阿尔兰采服也,故三岛已分内外矣。其待奥洲、加拿大,羁縻之荒服也。印度蕃服也。香港、新架坡等,卫服也。唐之有羁縻州,亦待荒服之义。”〔51〕
由于受国势和时代的限制,康有为当年的设计主要针对的是国境以内,今日崛起之中国由于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当有更为宏阔之视野,不必局限于本国领土。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不妨规划为“京师—郡县 (甸服)—边疆 (侯服)—与国 (绥服)—友邦 (要服)—对手/敌国 (荒服)”的新五服制。京师即首都,只是坐标原点,不作为一服;郡县是中央直辖区域,实行单一制,包括今天大部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当于王畿;边疆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域,实行民族地方自治,主要指西藏和南疆地区以及港、澳、台三个特别行政区,相当于内藩;以上甸、侯二服为中国本土。与国也即盟国,属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儒家文化圈,安服于中华文教,相当于绥服、外藩,在将来大体对应于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另外非儒家文化圈的中亚五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不丹等国,因其政治和地理的亲近也可纳入外藩序列;友邦则指合作互利、友好交往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相当于四海;对手或称敌国指的是那些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中国与它们是敌体关系而非敌对关系,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平等的竞争性的大国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新五服制既体现了地理上远近关系,但又不完全一致,主要还是以政治上的亲疏关系为主。比如印度、俄罗斯,地理上皆是中国的邻国,但在服制上却属于最外层的荒服。日本的情况更为特殊,整合得好可以成为同文同种的与国,整合不好便是一衣带水的敌国。
新五服制下的政治建设依旧是按照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次序逐步展开的。只有我们首先完成了内部同化,接下来才可能带动外部整合。清代公羊学家刘逢禄云:“《春秋》欲攘蛮荆,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52〕在这个民族国家的时代,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为更大范围的文明同化提供了可能的条件。文明同化同时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但这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汉族吞并少数民族。毋宁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乃是旧民族自我更新、新民族化合诞生的过程,历史上从华夏到汉族的演变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以科学的名义画群为牢,人为地打断了族群融合的可能性。我们的民族政策既要重视民族平等、尊重彼此差异,更要推动族群融合、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历史上依据归化程度对于少数民族有生番、熟番之别。以此标准来看,如今的55个少数民族,除了西藏和南疆地区由于语言和宗教信仰等原因,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基本上皆可视作熟番。这就需要我们的民族政策与时俱进、区别对待。比如对于熟番,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生育、高考加分的优待等方面,就要逐步淡化其族群分别,慢慢实现政策上的改土归流,从法律上承认并巩固民族融合的历史成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征,除了西藏、南疆两个主要地区以及局部的单一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50%的零星区域作为内藩继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外,其他地方应该一律实行郡县制,拆除人为的制度法律障碍,为民间自发的族群融合过程打开方便之门。当然,同化的过程并不等于同质化,原有的民族特征转化为地域特色可以继续保存。比如即便同为汉族,依然还会有山东人、福建人、四川人的差异,这就叫大同不害小异。
完成内部同化之后,接下来面对的便是外部整合。中国作为世界三极之一,若要保持长久的优势不衰,便不能不有一群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与国。如果像现在一样,我们家门口的邻国动辄被某大国挑唆向中国寻衅滋事,那么至少说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还没被广泛接受和尊重。借助组建东亚共同体这个区域整合的机会,中国可以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文明辐射区,慢慢将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以及东南亚国家纳入与国的范围,远期还可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并收入,形成西部亚太的大整合。当然,这需要我们首先有足够的智慧突破现有的国家主权理论和 《国际海洋法》等国际法权体系,化解中国与邻国之间纷繁复杂的领土和海洋争端。这种智慧便来自于传统的王道。不同于美国的区域霸权,中国早已庄严向世界宣告:“我们永远不称霸!”但不称霸不等于不称王。美国行的是假仁假义假民主的霸道,中国志在追求的则是真仁真义真民本的王道。只有奠基于天地人三才思想的王道才能使我们具备真正的文明自信,具备批判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高度,具备赢得人心的道义资源。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欧美之外的国家的崛起,更是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价值体系的文明的崛起。所谓中国道路就是天下归往的王天下之路,就是中国引领世界各国为全人类开辟的一条走出资本主义人性异化和强权体系的中正和平之路。只有作为世界文明的一极,中国才算实现了作为天下中心的复兴,才能对全人类做出与我们的国家地位相称的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2〕〔26〕〔30〕〔31〕〔32〕〔39〕〔43〕〔47〕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 〔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3,877,878,763,877,1003,764,765,1004.
〔3〕〔16〕〔22〕(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M〕.中华书局,2004.202,205,206.
〔4〕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 〔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41.
〔5〕〔7〕〔8〕〔12〕〔15〕〔21〕〔23〕〔45〕〔48〕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90,241,242,243,245,246,100,174,701.
〔6〕〔9〕〔10〕〔11〕〔13〕〔14〕〔17〕〔18〕〔19〕〔20〕〔25〕〔29〕〔44〕〔46〕(清)胡渭.禹贡锥指 〔M〕.邹逸麟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671,676,676,678,685,682,682,680,683,685-686,13-14,690,690.
〔24〕唐律疏议 〔M〕.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5.
〔27〕〔33〕黄怀信,等.逸周书丛校集注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10,991-994.
〔28〕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慎势 〔Z〕.
〔34〕(清)廖平.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 〔A〕.廖平选集:下册 〔C〕.巴蜀书社,1998.645.
〔35〕裘锡圭.甲骨卜辞中见“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 〔A〕.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C〕.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62.
〔36〕〔38〕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6,59.
〔37〕郭声波.中国历史政区的圈层结构问题 〔J〕.江汉论坛,2014,(1).
〔40〕(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六册 〔M〕.中华书局,2013.2975.
〔41〕魏怡昱.孔子、经典与诸子——廖平大统学说的世界图像之建构 〔A〕.儒藏论坛:第二辑 〔C〕.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496.
〔42〕(清)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6.
〔49〕康有为全集:第七集 〔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00.
〔50〕〔51〕康有为全集:第九集 〔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77,377.
〔52〕(清)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诛绝例第九 〔Z〕.
(责任编辑:赵荣华)
[收稿日期]2016-03-11
[作者简介]齐义虎,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四川绵阳 62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