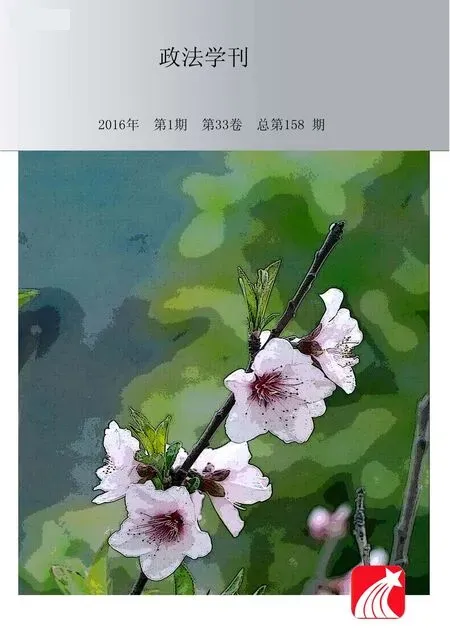民法总则立法视野下的诉讼时效制度研究
——基于利益衡量的选择
张继承,王廷杰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民法总则立法视野下的诉讼时效制度研究
——基于利益衡量的选择
张继承,王廷杰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自我国继受诉讼时效制度以来,该制度在立法正当性,届满效果和期间长短等方面就存在争议,现在重启民法典编纂工作,总则中的诉讼时效制度相关问题值得进行讨论,这对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规则设置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是贯穿本文的一条主线,在利益衡量的选择下,我国在民法典总则中而应继续沿用称“诉讼时效”的概念,不必改称“消灭时效”;设立诉讼时效的正当性理由在于利益衡量,且应更倾向于保护原始权利人的利益;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应当是权利人取得了抗辩权;目前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设置过短,应修改为5年较为合理。
关键词:民法总则立法;诉讼时效;正当化理由;期间;利益衡量
2014年10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编纂民法典,这是民商法领域的一个重大立法决策,意义深远。在民法典的编纂中,首要任务是编纂民法典总则,在201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中和多位专家教授主持完成的民法典建议稿中诉讼时效制度均置于总则之中*参见中国民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八章第二节,2015年4月19日公布;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8-428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页。,可以看出诉讼时效制度在民法典总则中是必要内容之一,这种体例也被大多数国家立法所采纳。
自我国法律继受时效制度以来,诉讼时效制度的研究和实践均取得了巨大成果,尤其是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诉讼时效制度的解释适用作了统一的规定,现在民法典编纂工作再次启动,诉讼时效制度应以何种价值理念为依托以及在民法典总则编纂中如何整合我国现行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制度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当性来源、届满后的法律后果和时效期间的设定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对民法典总则中的诉讼时效部分的编纂有所裨益。
一、概念:“消灭时效”还是“诉讼时效”
民事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地经过法定期间,即产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民事法律制度。[1]240通说认为,诉讼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的裁判官法时期,罗马法将诉讼时效称为“消灭时效”,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多沿用该称谓,如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
我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王权至上,法律方面重刑轻民,在律令典章中没有完成的普遍适用的民事时效规定,仅有一些零星的表述和记载,“中国古代法重绝对真实,时间在法律价值上并无实际意义。因此,中国古代法并不存在着基于诉权而发生的近代法意义上的消灭时效制度。”[2]110另一方面,“欠债还钱”、“父债子还”的观念也深入民心,因此在近代以前我国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民事时效制度。
在我国法制史上,第一个条文中正式规定了时效制度的法律是《大清民律草案》,该草案在第一编总则中设立时效一章,其中包括通则、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但该草案并没有实际实施。中华民国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在其颁布的民法典总则编中规定了消灭时效,“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铭文规定时效制度并得以实施的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制定的民法中的时效制度。”[3]76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并得以实施的时效制度,至今仍在台湾地区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民法理论继受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诉讼时效的概念,该法典取消了取得时效制度将其称作诉讼时效,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也采用了这一概念,正式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
在传统民法中,时效制度有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并无诉讼时效的称谓。我国继受苏联诉讼时效概念沿用至今,诉讼时效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容易让人认为诉讼时效制度仅仅适用于诉讼中,是程序法的一部分,而实际上诉讼时效本质上是民事实体法,因此,一些观点认为我国应与大多数国家保持一致,在民法总则立法时将诉讼时效制度改为“消灭时效”,也有人认为采取“消灭时效”也存在一定问题,因我国现行法均以诉讼时效为概念,法律学者和民众亦已接受,保留诉讼时效称谓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
对两个概念进行分析,虽然民法学界存在“诉讼时效”与“消灭时效”的概念之争,这两个概念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谓诉讼时效,亦即消灭时效”[4]246诉讼时效概念更符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也更容易为学者和民众所接受,因此从法的延续性角度而言,在民法典总则中应称“诉讼时效”,而不应称“消灭时效”。
二、正当化理由:基于利益平衡的选择
依据普通民众的常识,诉讼时效制度并非十分容易理解和接受,因为诉讼时效制度与传统道德观念相悖,甚至有学者提出应取消或者部分取消诉讼时效制度,[5]因此讨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当化理由十分必要。“民事设立时效制度,着眼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因时效期间届满而发生与原权利人利益相反的法律效果。因此,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4]245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在于,一旦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所形成的事实状态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存在,则法律就不再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而转向保护事实上的占有人或债务人。
在《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关于诉讼时效立法的叙述中提到,立法目的首先表现为是保护现有社会秩序之稳定,诉讼时效的立法并非要剥夺侵权人的权利,而是要给予义务人以保护,是一种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手段。[6]912002年德国债法进行了修改,其中也对诉讼时效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官方的解释中说“旨在保持法律活动安全及保持权利和平、避免争议”。[7]13在日本,时效制度的正当化理由主要有保护非权利人·实体法说、保护权利人·诉讼法说和多元说。[8]346-349我国台湾学者在论述时效制度的正当化理由时,并没有区分讨论,对于时效制度王泽鉴教授的论述为“1)保护债务人,避免因时日久远,举证困难,致遭受不利益;2)尊重现存秩序,维护法律平和;3)权利上之睡眠者不值保护;4)简化法律关系,减轻法院负担,降低交易成本。”[9]492
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提出“诉讼时效的重大功能有:1)稳定法律秩序;2)作为证据之代用;3)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10]378我国通说认为,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通过诉讼时效制度,消弱长期不行使权利的人权利甚至使其丧失权利,以此来督促权利人及时行权。二是作为证据之代用,节约诉讼成本。在诉讼中,要证明谁是真正的权利人,但是一种事实长期存在,可能会导致证据泯灭,增加举证困难,因此诉讼时效届满,可作为证据代用,保护事实状态中的权利人。三是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的稳定,推翻长期持续存在的事实,就会破坏以该法律事实为基础的多种法律关系,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因此为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法律秩序,需要设定诉讼时效制度。*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24-245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版,第190-191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241-242页。在通说之外,还存在以下表述:一是减轻法院受案负担。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在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司法资源是有限的,这决定了现有司法资源不能对所有民事纠纷提供救济,因此诉讼时效制度是对权利的救济进行选择的方式,起到合理配置司法审判资源。二是权利上的睡眠者不值得保护。也就是说诉讼时效立法在于鼓励权利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提起诉讼,如果权利人没有在一定期间内提起诉讼,则他有可能失去司法保护。
对于上述理由,部分学者进行了反思,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仅仅是诉讼时效制度的客观效果;二是作为证据代用混淆了举证责任和诉讼时效之间的关系;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提法在我国“私权神圣”观念并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不十分适合。[11]130-138在我看来,诉讼时效制度是对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的利益衡量的立法选择,在我国民法总则立法中还是应当设立诉讼时效制度,具体分析如下,因为这种选择体现了法律对基于权利长时间不行使而形成的权利休眠状态的新秩序的认可和对债权人可能主张权利的旧秩序的否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权利人的权利,对权利人有些不公平,但而置于整体利益的衡量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损害是有价值的。因为诉讼时效制度具有一定的矫正性,能够促进效率或维持法律关系的稳定。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因为诉讼时效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违背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打破了利益的合理均衡状态。在民法典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设计时须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原始财产人利益的衡量中寻求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如何在制度设计时兼顾权利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性利益,是否有必要全盘复制大陆法系的诉讼时效制度,如何使法律真正地呈现出“善良与公平”的基本特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在更深的价值层面上提出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正当化理由。
三、效力: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
关于诉讼时效届满后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我国《民法通则》并无明确规定,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期间是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条文并未明确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法中,诉讼时效届满的直接效力是当事人获得抗辩权。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各国立法体例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实体权利消灭主义。日本是这一立法例的代表,《日本民法典》第167条规定“(一)债权,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二)债权或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因二十年不行使而消灭”。[8]379,381此种立法模式将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利。二是诉权消灭主义。法国民法典采用诉权消灭主义。《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过三十年的时效而消灭,援用此时效者无须提出权利证书,他人亦不得对其提出恶意的抗辩”。此种立法模式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本身仍然存在,消灭了起诉权。三是抗辩权发生主义。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采抗辩权发生主义。《德国民法典》第222条规定“消灭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得拒绝给付”;又规定“为履行已经时效消灭的请求权而为的给付,虽不知时效消灭而为给付者,也不得请求返还”。
分析上述三种立法模式对我国民法典总则诉讼时效制度立法有重要借鉴意义。实体权消灭主义强调了法律对意思自治的干预,未考虑当事人主观意愿,如果义务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履行的,权利人构成不当得利,造成了道德与法律的紧张关系,采用此种立法例的国家均在时效立法其他领域中弱化它的效果,如规定时效利益抛弃规则、援用规则等。在起诉权消灭主义立法体例中,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之权利本体不消灭,但起诉权消灭即程序诉权消灭。起诉权是程序法上的权利,而诉讼时效制度是实体法,因此规定程序法上的起诉权之得失依赖于实体法上的时效制度逻辑上说不通,即使在采用起诉权消灭主义的国家,立法中也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诉讼时效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只能由当事人自行主张。我国现行法确立了抗辩权发生主义,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胜诉权消灭说在我国处于通说地位,但是诉讼的胜败在当事人起诉之后是不确定的,胜诉只是法院审判的结果,具有可变性,且胜诉权消灭主义违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完成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是否保护其权利,应取决于义务人是否抛弃时效利益,而胜诉权消灭主义规定法院主动审查时效,一旦查明诉讼时效已完成,则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干涉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因此在民法总则立法中,宜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因为抗辩权发生主义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精神,时效届满的直接后果和援引时效条款所产生的后果明确,且有利于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自愿履行债务。在确立抗辩权发生的同时,还需要明确的有以下两点,一是法院不得主动释明诉讼时效规则。在我国现行法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院不得主动释明诉讼时效规则,法院不主动释明有利于当事人利益平衡也更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二是应当规定放弃诉讼时效抗辩和当事人自愿履行的法律后果。
四、期间:2年抑或其他
关于诉讼时效的期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诉讼时效期间设置多长合理。“当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长些,意味着法律倾向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反之,当诉讼期间规定的短些,意味着法律倾向于保护义务人的利益,立法者正是通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赖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12]126我国《民法通则》目前规定了三种,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特别诉讼时效为1年,另外还有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保险法、海商法、票据法等法律也对其中的请求权规定了不同的期间。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2年普通时效期间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短的普通时效期间。例如《法国民法典》规定普通时效期间为5年,特别时效期间为10年、20年,长期时效期间为30年。《德国民法典》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2001年德国新债法修正),长期时效期间为30年。新《荷兰民法典》规定的普通时效期间为20年,特别时效期间为5年、1年等。这些时效期间的长短看似没有规律,但是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30年,到1896年《日本民法典》规定10年(普通消灭时效期间)和20年(所有权外的财产权),又到1911年《瑞士民法典》规定10年,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规定3年。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一个规律,越早制定民法典,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就越长,反之则越短。我国规定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主要是受苏联民法思想的影响,且80年代初期人们对私法原则及制度的了解普通不深,为了强化人们的时效意识,促使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到底设定多长合适,这是权衡各方利益,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关键。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过短。2年的时效经过,债务人就拒绝还债,与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诚实信用原则相抵触,而且有不少债权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并而导致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冲突影响,目前2年的诉讼时效没有体现出社会诚信缺失的回应,时效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利益的衡平,不在于限制权利本身,虽然世界的潮流在不断缩短诉讼时效的期间,但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议民法典总则立法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延长至5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保持为20年。
结 语
诉讼时效制度引进我国短短不过百年,而时效制度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诉讼时效制度的引进,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欠债还钱”才是理所当然,权利人不去主张,并非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正当性理由,而诉讼时效恰恰是以时间作为一种限制工具,对权利人进行限制。“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滥用会导致义务人为免责而不宜不主动履行义务,甚至躲避权利人的追债,待时间经过而以诉讼时效抗辩拒绝履行义务,这显然有违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13]3从诉讼时效制度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诉讼时效更多的成了债务人逃避债务的理由。
因此基于利益衡量的选择是,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部分立法时,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对权利保护和权力限制的衡量,将对权利人个体利益、债务人利益和不同的第三人利益放在一起,结合我国社会实际,合理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和届满后的后果,更好的维护社会诚信,对传统文化道德和社会习俗给予现实关怀。
参 考 文 献:
[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李求轶.消灭时效的历史与展开[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3]邹开亮,肖海.民事时效制度要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4]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李锡鹤.重构民法时效理论体系[J].法学,2005,(6):118-123.
[6]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 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朱岩,编译.德国新债法条文及官方解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8]山本敬三.民法讲义(1)[M]. 解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王泽鉴.民法总则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1]杨魏.民法时效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2]蒋浩.正义名义下的利益考量·诉讼时效制度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13]张雪楳.诉讼时效前沿问题审判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马睿
On the System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Code Legislation-On the Basis of Choice of Equilibrium
Zhang Ji-cheng,Wang Ting-jie
(School of Law,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adoption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there always exist disputes in this system as to the concept, legislation fairness, legal effects and validity period. Currently China is restarting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Therefore, the issue of limitation of actions is worth discussing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base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concrete rules and system of civil code. The principle of equilibrium is the just cause for the existence of limitation of actions. Under this principle, the concept of "limitation of actions" shall not be changed. Equilibrium is the cau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system and aims at protecting the benefits of antecedent right holders. The legal effect of limitation of act is that the right holders have gained right of pleadings. The validity period of common limitation of actions shall be changed into 5 years and for some special cases it can last 20 years.
Key words:Civil Code legislation; limitation of actions; just cause; period; equilibrium
收稿日期:2015-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2YJC820136)
作者简介:张继承(1976-),男,湖南醴陵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民商法学研究;王廷杰(1988-),男,河南许昌人,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45(2016)01-01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