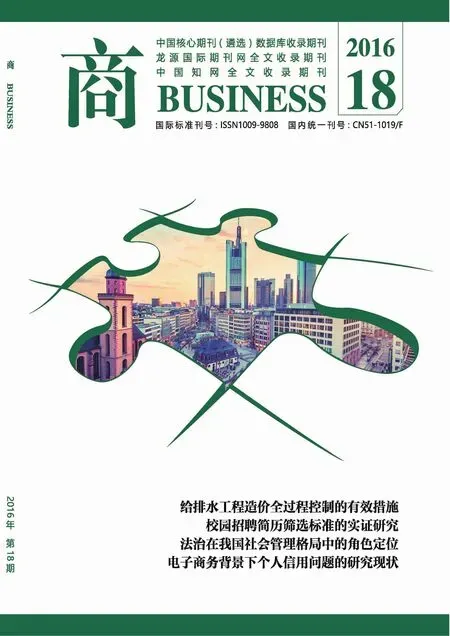司法裁判“利益衡量”的现实问题
朱力
摘要:法官审理案件,在案情事实查清后,不急于去翻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厉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这就是利益衡量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这种模式已广泛应用于各国司法实践,但大陆法系国家并不予与书面承认而已。随着利益衡量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应用实践的问题也就越突出。
关键词:利益衡量;法律解释 一、 利益衡量的涵义
(一)利益衡量的概念。法官裁判案件时,在查清案件事实后,并不急于寻找适用该案件的法律规则即大前提,而是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一些其他现实条件,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利益之冲突可能是法律规则中所忽略的一种自我内心的裁判即一定要比较出孰轻孰重。利益衡量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各种利益冲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和斟酌,以得出自认为合理结论的过程。而就法官而言,是对上述利益冲突从不同的方面作比较,于内心得出自认为合理又合法的判断,以兹在司法审判中作出一个能使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甚至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判决结果的过程。据此,利益衡量是指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发生两个或以上的利益冲突,由法官对该利益冲突进行权衡而作出孰轻孰重选择的过程。
(二)利益衡量的性质。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司法实践中的利益衡量到底和价值判断是何关系呢?上文已述利益衡量之实质是对利益冲突的比较选择而作出合理判断之过程,既然说利益衡量其实就是一个过程,那么在此过程中,衡量者(法官)不断的分析、评价每个利益(价值)及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利益(价值)相互之间的权衡、参详,即持续为价值判断。因此,利益衡量实质上是由一连串互相影响、层层推进的价值判断锁链组成,在性质上当属价值判断的过程集合,它与价值判断本身不是一个面相上的问题。①
二、 利益衡量的应用的条件
(一)利益衡量应用的前提。利益衡量得出实质判断后,一定要找到法律根据,不能直接从实质判断得出判决,仍然是从法律规则得出判决,即必须遵循前面讲的裁判的逻辑公式。②换言之,利益衡量仍然要遵循司法三段论模式。利益衡量不仅要满足上述的法律条件,且要满足一定的适用条件。利益衡量司法应用的基本前提就是出现了法律规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抑或是法律规则所遗漏的对合法利益的调整。而法律的正义是使每个人与其所应得到的东西(包括利益在内)之间的均衡状态,③当然解释者对于利益的选择与放弃并不一定就会和每个人应得的利益一一对应。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不能紧抓利益不放,还必须结合案件的事实及法律的精神进行综合的考虑。且并非每一个案件都需要利益衡量的,利益不应是决定因素而是参考因素。若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明确,根据该当法律要求一方利益必须得到保护,那么不管该当利益与其他利益比较多么的微不足道都应当得到保护,这是法律的正义要求。因此利益衡量论首先应当确定自己适用的前提,即它只能在法律与事实的法码能够对等的各种利益冲突中适用,离开这一语境,利益可能会成为恣意的借口,正义将得不到维护。④
(二)利益衡量应用的法域条件。最初的利益衡量理论是由民法学家提出并运用及完善于民事法领域,后经发展其他法学部门法律实践也会涉及利益衡量。但有学者认为利益衡量理论就只适用于民法领域,而有学者则认为不单单是民法,其它各部门法都可以并得到相当有效的应用。如日本利益衡量理论代表人物加藤一郎就认为:“现在来看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所说的利益衡量,不限于民法,凡涉及一切法律判断,亦即法的解释,就有利益衡量问题。只是法域不同,则利益衡量的方法有相当的差异。”⑤而我国的大部分学者主张利益衡量理论仅适用于民事法领域,但梁慧星老师和胡玉鸿教授主张利益衡量是一种普适性的法律方法,即应当应用于各部门法领域。
三、 在我国司法领域“利益衡量”所面临的困难
(一)利益衡量的正当性及标准问题。“利益衡量”现今已广泛应用于各国的司法实践中,但作为司法过程的伴生物,其在运行过程中的正当性值得商榷。利益衡量的最大优点就是弥补法律的空缺以实现个案的正义,但个案的正义是否等同于法律的正义呢?在一个案件中所作的利益衡量可能是正当的,但是换到别的个案中就不一定具有正当性可言。据此,如若“利益衡量”不能建立一套相应的规制规则,那么就很难真正的实现法律的正义,而仅仅是实现了个案的正义。且法官在作出个案的“利益衡量”时缺乏一个长期有效的标准,法官为何作出此种利益高于彼种利益的“衡量”?利益衡量必然会涉及价值判断的因素,若法官没有任何方法原则为依据,而仅依其自定的标准作出裁判,对于依“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所作的裁判即无从控制,法官也可以堂而皇之依自己的主观见解来裁判。⑥
该当问题应引起反思,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法官作出一系列的“利益衡量”必然会涉及主观与客观的冲突,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法官在缺乏客观标准面前的无奈。因而,前述的种种困难归根结底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利益衡量”的客观性标准,使得法官在依此作出的“利益衡量”即实现个案的正义又实现法律的正义,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本杰明·卡多佐所追求的“自由的科学研究”这一崇高的目的。⑦
(二)利益衡量理论体系尚不健全。虽然在法学理论研究领域,利益衡量一直被作为概念法学的对立面而被研究和关注,且并没有直接的应用于司法实践,但其已成为司法实践的普遍模式。然而此种模式存在着理论上的研究不足以及在实践中的程序缺乏确定性和系统性。
就其理论体系而言,体系框架缺乏完整性。无论在概念理论还是方法论研究方面均缺乏体系化。⑧国内外理论界各自为政,观点冗杂,各自秉承自我理念,既无相互借鉴也不能相互说服。利益衡量理论体系的不健全以及自身的不确定性必然会牵涉到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法官在裁判中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基点更别说是寻求更为合理的理论体系支撑了,所以利益衡量理论体系的健全是不可忽略的目前理论和实务界的头等大事。
(三)法官的恣意规制问题。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作出的利益衡量是一个很难做到可以忽略自我观点的过程。作为法官前提是他是一个人,有自我喜好的社会的人。且中国的法官素养不高,各地区的法官自身的法律修为参差不齐,这必然会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出现法官恣意问题,这也一直是横亘在学者心中的隐忧。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律方法总体上说是立足于一种超越于法律的视角,它要解决的是概念法学式的法律适用所会造成的个案判决结果的不妥当、不合理性问题,然而,利益衡量在实现这一目标同时却增加了司法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利益衡量的运用超出必要的限度会形成法官的态意,危及法治秩序甚至会颠履法治。
(四)“利益衡量”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脱节。利益衡量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司法实践,其价值也要在司法实践中才能得到实现。纵观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可见,两者关系处于松散的状态,利益衡量理论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这源于理论研究者与司法实践者的工作任务、目标不同所致。司法工作者所面对的是大量的亟待解决的现实案件,法律思维路径必须紧密围绕案情展开,在这个大前提下既要讲求司法公正,又要讲求司法效率。此种情况下,理论研究者就不可能顾及司法实践者的要求,而一味的追求自身理论研究的成果问题,而司法实践者也不一定会采纳一个尚未被理论界以及实务界所认可的理论成果,所以必然会导致“利益衡量”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严重脱节。
参考文献:
[1]孟庆东.论作为民法学方法论的利益衡量[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3(2).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75.
[3]徐显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6.
[4]李军.利益衡量论[J].山东大学学报,2003(4).
[5]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79.
[6]胡玉鸿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题[J].现代法学2001(4)..
[7]汤晓江.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及其优化[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