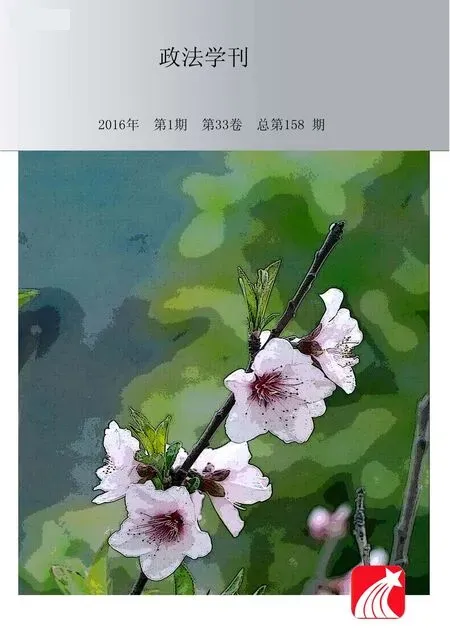群体聚众行为的场所限制
——以集会游行为中心的分析
王江伟
(江西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群体聚众行为的场所限制
——以集会游行为中心的分析
王江伟
(江西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摘要:对集会游行等群体聚众行为施以场所限制是发达国家以法律规范集体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集会游行的场所限制大致分为公物使用限制、禁制区限制和私人场所限制三种。公物使用限制主要集中于“公共用物”和“营造物用物”使用限制两个方面,“公共用物”对集会游行的限制较少,而使用“营造物用物”举行集会游行则应以不对该营造物本身功能使用造成较大妨碍为限。禁制区之于集会游行的限制,除特殊情况外,乃属绝对禁止性限制。私人场所也可绝对禁止集会游行的举行,但对于那些具备“准公共场所”性质的私人场所,仍涉及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公民表达自由之间关系的问题。借鉴发达国家限制聚众群体行为的法治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群体聚众行为;集会游行;群体性事件;场所限制
尽管群体性事件研究是当下海内外学界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但是对于如何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的治理轨道仍然缺乏系统的探讨。实际上,作为民众诉求表达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抗议等群体聚众事件几乎天天发生,其频率和规模远高于国内的群体性事件,然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却并没有陷入“维稳”的重压之下,民众享有充分的表达权利,而社会仍然稳定有序。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在治理群体行为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西方国家,针对公民集会游行和示威抗议等群体聚众行为均有非常完备和细致的法律加以约束,以使群体行为不危及公共秩序。这些法律规范对于群体行为的约束主要可以分为程序限制、方式限制和场所限制三个方面。程序限制是指集会游行和示威抗议等群体行为应当事先向警察机关申请许可或报备;方式限制是指集会游行和示威抗议等群体行为应当遵守和平义务和禁止暴力行为;场所限制是指对于集会游行和示威抗议的举行所使用场所的限制。对于程序限制和方式限制,笔者已有另文论述,本文将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探讨群体聚众行为的场所限制,以期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有所借鉴。
一、集会游行与公物使用限制
行使集会自由权所使用的场所通常涉及公物使用问题,因此可借助行政法中的“公物”概念来分析集会游行场所使用的限制。所谓“公物”是指经提供公用,直接用以达成特定公目的,适用行政法之特别规制,而受行政机关公权力支配之物。依公物使用的不同目的,可分为“公共使用公物”(亦称“公共用物”)、“行政使用公物”(亦称“行政用物”)、“特别使用公物” (亦称“特别用物”)以及“营造物使用公物”(亦称“营造物用物”)。[1]1033“行政使用公物”系为达成行政任务,仅供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内部使用,典型的如政府办公大楼。集会游行使用行政公物的可能性非常小。“特别使用公物”是经主管机关许可特定人以为特定目的之使用的公物,而非任何人皆可自由使用,典型的如因水利目的而使用水资源。集会游行通常也不会涉及此类公物使用。因此,本部分乃以使用“公共用物”和“营造物用物”来讨论集会游行使用公物的限制。
(一)集会游行使用“公共用物”的限制
“公共用物”系行政主体直接提供公众使用的公物,典型的如道路和广场等。公共用物的使用方式又分为两种:依该公物的性质和设置目的而为的通常使用称为“一般使用”,如使用道路通行;超出该物通常使用范围则为“特别使用”,如在路边摆摊设点。[2]135-136集会游行通常都是在“公共用物”上举行,亦即“公共用物”构成为集会游行的主要场所,如街道、人行道、公园和广场等。但集会游行对这些场所的使用则属于对“公共用物”的“特别使用”,故而相比于对这些场所的“一般使用”有较多的限制。在发达国家,由于广场和公园本身有供民众集会、休闲和娱乐之用的目的,一般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或报备,使用此类场所举行集会游行所产生的问题不大,通常均能获得批准。使用这些场所的限制主要在于不能影响和干扰他人对这些场所的使用。如李震山教授所主张的,对于“公共用物”之使用,应遵守公众能接受之原则,即其使用不能造成其他权益人持续重大损害,或完全排除其他利益人之使用。[3]
集会游行最常使用的“公共用物”中,最需要探讨的是街道、人行道等公共道路的使用。“保持交通畅行”或“维持交通秩序”是城市当局管制集会游行使用公共道路的最为常见的正当理由。在英国历史上,用以限制在公共道路上举行集会游行的便是普通法上的“通行权”(right to passage)概念,若集会游行妨碍了他人的道路通行权,哪怕是细小的妨碍,都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妨碍”而判罪。并且与传统的刑罚相比,以妨碍通行来管制集会游行更具有非政治性,因而“妨碍法”(nuisance law)成为经常被用于管控街头示威的主要手段。*对英国历史上的“通行权”概念与集会自由管制的详细讨论,可参见Racjel Vorspan.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the Right to Passage in Modern English Legal History[J]. 34 San Diego L. Rev. 921 (1997); A. L. Goodhart. Public Meetings and Processions[J]. 6 Cambridge L.J. 161 (1937).而在现代西方国家,以保障“交通畅行”为由,对民众行使公民权利而使用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管制的“交通逻辑”(traffic logic)亦无所不在,并且由于此种管制视角至少在表面上的非政治性,而成为一种非常有力的管制方式。*以“交通逻辑”管制公民利用城市公共空间的详细研究,可参见Nicholas Blomley.Civil Rights Meets Civil Engineering: Urban Public Space and Traffic Logic[J].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22, No.2, 2007.此种“交通逻辑”当然也包括对公民集会游行使用公共道路的管制。
“交通逻辑”的背后主要在于保护他人交通出行的权益,因为集会游行通常会牵涉到影响他人出行之安全、健康和行动自由的权利。通常会有诸如《交通法》和《道路法》等法律对道路使用予以管制,集会游行使用道路自然也受这些法律的规范。但也有以维护交通秩序为由直接在专门规范集会游行的法律中对此予以规定。如《韩国集会示威法》第十二条即赋权主管警察部门“如认为有畅通交通之必要,可以禁止在大城市主干道上集会或示威,或为维持交通秩序而施加具体条件限制之”。陈新民教授将集会游行因使用道路所可能妨碍的他人权利称之为“交通法益”,包括“交通安全”和“交通畅通”两个方面,前者涉及驾驶人与行人的生命及健康权,后者主要指集会游行所造成的交通不便。[4]429由此,对集会游行使用公共道路的管制便涉及到对集会游行之表达权利的法益和他人出行之交通法益之间的衡量问题。由于任何集会游行通常会涉及对他人交通法益程度不等的影响,因而该问题的核心在于,集会游行对他人的交通法益影响到何种程度,主管当局才可以禁止或限制该集会游行。
德国慕尼黑高等行政法院在1984年即有判决主张若示威使该地区的交通全部中断或无改道之可能时才可禁止(不许可)一个示威的举行。[4]429该判例所揭示的是若集会示威并非严重侵犯他人之交通法益,例如致使他人通行几无可能,则一般公众对此集会示威所必然会带来的交通不便应负一定的忍受义务。一般而言,只要集会游行依照许可或报备时所确定的集会地点或游行路线举行,并遵守相关的道路或交通法规,该集会游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封锁交通或占据要道,主管当局非但不能干涉该集会游行的举行,反而应当保证该集会游行的顺利举行,此即为公民集会自由权的国家保护义务。此外,仅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集会游行使用道路会受额外限制,比如禁止在高速公路或交通繁忙时段举行集会游行。
至于具体如何权衡集会游行的法益和交通法益,笔者以日本相关法规和判例做一讨论。日本《道路交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使用道路须获得地方警察署长的许可。该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前各款列举之外,以行进之形态或方法使用道路,如在道路举行祭礼活动或户外摄影等显著影响一般交通之行为,或在道路聚众显著影响一般交通之行为,为维持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经公安委员会依道路交通状况认定必须申请许可者”,应申请许可。该条第二款继而规定警察署长对于申请使用道路应给予许可的情形:1)该项申请行为不会对现时交通造成妨害之情形;2)该项申请行为不会对交通造成妨害,且该行为亦有遵照申请许可所附加的条件;3)该项申请行为会对现时交通产生妨害,但该行为为公益上或社会习俗而不得已之情形。日本尚未制定《公安条例》的地区,集团行动 的自由受《道路交通法》的规制;*在日本,“集会、游行和示威”统称为“集团行动”。而在有《公安条例》的地区,则与《道路交通法》形成双重规制。[5]189-190
从该《道路交通法》第七十七条本身规定来看,其对集会游行使用道路的规定已经较为明确具体,产生较多争议的地方主要在于何为“对一般交通产生显著影响之行为”,对于此种不确定性法律用语,该以何种依据或标准来做判断以决定是否授予道路使用许可。
日本曾有判例指出,于公用道路上散发传单,只要在不妨碍到大众通行之状况下进行,即不得以违反《道路交通法》第77条而予以处罚。[6]84而在日本最高法院于1975年9月10日所做的有关德岛市公安条例的判决中,则具体讨论了《道路交通法》第77条的法律明确性问题。该判例指出,判定集团行动是否会对交通造成较大的阻碍,应以“具有通常判断能力之一般人的理解”为其判断基础。但日本学界对此基准较有争议,认为其仍属空泛的基准。[7]119-120此后在1982年11月16日最高法院所作出的一项有关违反《道路交通法》的判决中,确立了现行的判断标准。该判决中指出,对于使用道路举行集会游行而依《道路交通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不予许可时,应仅限于“依该集会游行预定之规模、态样、路线、时间等加以考虑,如认为举行该集会对于道路之供一般交通使用之功能,可能产生严重妨害,且分局长纵附加条件许可,亦可能发生无法防止严重妨害交通之事态发生”[8]275之情形,除此外,警察机关对使用道路的申请不得做出不予许可的处分。日本最高法院所确立的该判断标准,基本上仍属于依具体个案进行衡量,若结合前一判例所确立的依“具有通常判断能力之一般人的理解”的标准,或许更有助益于该衡量的判断。
(二)集会游行使用“营造物用物”的限制
欲理解“营造物用物”须先了解“公营造物”的概念。“公营造物”系指行政主体为达成特定公共目的,所设置的集合人与物的手段之机构。“公营造物”一词是日本行政法学者从德文翻译的概念,所谓“营造”之“物”必须结合人的运作才能发挥其功能,因此是“物”与“人”结合的整体。如若改称为“公事业”、“公物事业”、“公事业机构”等或许更为妥当,[1]1010亦较易理解。“公营造物”依不同标准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分类,若依据利用可能性进行分类,则分为不可利用公营造物与可利用公营造物。不可利用公营造物是指不属于该公营造物组织及公营造物主体的人,不能直接予以利用的公营造物,典型的如监狱、要塞等。而可利用公营造物即为“营造物用物”,是一般民众可以直接利用的公营造物,如公立学校、图书馆、体育馆等。[1]1014因不可利用的公营造物不属于“营造物用物”,各国和地区也一般性地禁止在此类公营造物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因此,本部分所要探讨的是,开放给公众使用的公营造物,即“营造物用物”是否可以被用于举行集会游行活动。从国外经验来看,集会游行使用“营造物用物”大多数仅限于公共设施,兹以美国和日本相关判例作一介绍。
在美国,使用公共设施用作表达活动,只要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且不对他人的使用造成严重影响,法院通常会判定支持使用公共设施从事表达活动。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布朗等人诉路易斯安娜州”(Brown et al. v. Louisiana 383 U.S.131(1996))案涉及的是在图书馆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的案例。本案中的图书馆系路易斯安娜州一家公共图书馆,因对该馆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不满,布朗等五名年轻的黑人男性于1964年3月7日进入该图书馆抗议图书馆的种族歧视政策,图书馆管理者要求他们离开,但被拒绝。随后五人被地方治安官逮捕。至被逮捕前整个抗议活动持续了约15分钟。依路易斯安娜州的治安法规定,在公共场所或建筑内聚集或集会,意图激起破坏秩序或导致有破坏治安的情形发生,经执法者或其他有权者命令其离开或解散而不听从者,犯有破坏治安罪。地方法院依该法判处布朗等五人破坏治安罪成立并处以罚款。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了布朗等人的上诉请求,福塔斯(Fortas)大法官陈述了法庭意见,其首先指出,上诉人进入图书馆是合法的,因为图书馆是向公众开放的公共设施。不能因为白人不欢迎黑人进入图书馆而拒绝他们进入。其次,福塔斯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布朗等人的抗议示威有意图破坏秩序或导致破坏秩序的情形发生,且本案中的示威抗议并没有干扰到图书馆内他人的正常活动。[8]139-141因此,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另外还发展出一种用于判定公共设施是否可被用于表达活动的方法,即判断该公共设施是否是一个公共论坛(public forum),若属于公共论坛,则表达活动通常会获得支持。*有关“公共论坛”原理的发展过程及"公共论坛"的判定标准,可参见Robert Post. Between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Public Forum[J]. 34 UCLA L. Rev. 1713 (1987).1987年的“机场当局诉耶稣犹太社团”(Airport Comm's v. Jews for Jesus, Inc.)案便属此类。该案涉及禁止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任何的“第一修正案活动”的机场规定是否违宪的问题。1983年该机场管理当局发布了一项规定,禁止使用机场场所从事任何有关“第一修正案活动”,本案的被告是一个非营利性宗教社团,于该机场航站楼区域的人行通道上散发传单,被机场治安官阻止。他们遂于加州地区法院起诉该机场,认为侵犯其表达权利。地区法院判决认为,机场的航站楼区域属于传统的公共论坛,因而禁止在机场航站楼区域举行任何第一修正案活动的规定违背宪法。机场当局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以同样的理由维持了原判。*Airport Comn's V Jews for Jesus,Inc., 482 U.S.569(1987).
再以日本判例为讨论。在日本使用公共设施必须得到设施管理者的许可方可使用,但此种许可并不完全属于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因为日本《地方自治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除非有正当的理由,否则不能拒绝居民利用公共设施”。[5]185日本自1970年代开始,法院裁判了许多有关公共设施利用许可问题的案件,其中与集会自由有关的著名案件是“泉佐野市民会馆案”。[5]该案中,计划举办“反对关西新机场全国总决起”的集会者向泉佐野市政府申请使用该市市民会馆以做集会之用,但市政府以本案集会是由所谓的“中核派”(即激进的全学联反战青年委员会)所主办,考虑该集会前后的示威游行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而导致混乱,依据《市民会馆条例》第七条规定“有扰乱公共秩序之虞”及同条第三款“其他认为会阻碍会馆管理之情形”而做出不许可处分。诉讼人先是向地方法院诉讼请求救济,地方法院认为不许可处分并不违宪,日本最高法院受理此案时亦支持原判决,并在此案判决中,提出了如下三点可供日后政府当局判断是否准予许可公共设施供集会游行之用的依据:
1.公共设施的利用,只要不违反设置的目的,原则上应该允许利用,而且拒绝利用者的情形,除利用的申请相互竞合外,仅限于若提供给集会利用,将有害于其它基本人权或损害公共福祉的情形。
2.依上述原则,《市民会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应限定解释为,相对于保障在本案会馆举行集会自由的重要性,为了避免、防止由于在本案会馆中举办集会而导致他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以及公共安全受到危害的必要性更为迫切的场合。而且这种危险性,依据客观事实判断,应当是明显而且紧迫的危险发生乃是可被具体预见的。
3.是否有上述事由的存在,不能仅凭有许可权者的主观预测,而必须对照客观事实能具体明确预测的情形进行判断。本案不予许可处分的作出,系从“中核派”在当时反对关西机场建设,并不断使用违法实力,以暴力不断地与其他对立团体进行抗争等客观事实而判断,若允许其在会馆举行集会,将发生团体间暴力冲突等问题,这将有损于公共秩序及他人生命财产。
日本最高法院的此一判决,系对《市民会馆条例》的合宪性解释,并且将该条例的不予许可事由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定。此一限定较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集会自由以及防止主管当局滥用裁量权力。一般而言,与“公共用物”相比,“营造物用物”通常有其自身的使用目的和用途,因此对其使用的前提均须获得管理者的事先许可。而管理者的不予许可的理由,一般有如此六种[3]104:1)不合提供公用使用之目的;2)事实上的障碍,如该设施正在改建或属关闭期间;3)基于危害及违法行为之理由,如事先可知悉当事人或其他人有意毁损设施中的设备或准备从事犯罪行为;4)为避免反制行动之危害;5)必须保证租借者、使用者有给付能力;6)其它严重妨害公共安宁之情形。
二、集会自由与禁制区限制
“禁制区”所禁止的乃是公物的周边地区,尤其是在“行政物用物”和“营造物用物”周边范围禁止集会游行,它是集会游行法中对集会自由行使使用场所的一种特别限制。“禁制区”的原型来自于英国法。英国基于议会特权的理念,普通法上禁止在议会附近集会,英国学者对此种议会特权有如此表述:“为使两院议员不受阻扰地参加议会会议,国会可以命令指示大都市警察局长在会议期间保持通往国会的街道自由畅通,并且不得妨碍两院议员的通行。警察应采取任何措施保障议员不受妨碍地通过街道和到达议会,为此目的必要时可以对交通进行管制……若混乱的集会人群已经阻挡了街道、走廊和通道时,警察有权将其驱散。”*Michael Supperstone. Brownlie's Law of Public Order and National Security (2th ed). London: Butterworths, 1981.英国成文法中也有对议会特权的保障,例如英国1817年《煽动性集会法》(Seditious Meetings Act)规定:“在议会开会期间,凡聚集五十人或五十人以上,在距离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正门一里以内,不论其目的为上诉、请愿或诉愿,均属违法。”*彭绍瑾.群众与集会游行之研究[M].桃园:台湾桃园地方法院检察处,1989.
而最早的禁制区立法产生于德国,它源自于一次政治事件。在魏玛宪法时代,当议会于1920年1月13日审查《企业职工法》时,左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采取极端的抗争方式,强行闯入议会。帝国议会随即招来军队以保护议会,并因而发生冲突,导致42人死亡。鉴于此次惨痛教训,帝国议会在1920年5月8日通过《帝国议会及邦议会建筑物安宁法》,并在同月17日以行政命令宣布了禁制区的范围。[13]94现行德国集会法继承了魏玛时期的做法,于该法第十六条规定“联邦或邦立法机关及联邦宪法法院之禁制区内,禁止露天公开集会与游行。联邦立法机关及联邦宪法法院之禁制区由联邦法律定之,邦立法机关之禁制区由各邦法律定之。其详细内容由联邦及邦之禁制区法定之。”由该立法可见,德国集会游行的禁制区仅限于“联邦或邦立法机关及联邦宪法法院”周边地区,而至于为何在这两个地区设置禁制区,德国学界有的观点认为,设置此类禁制区的目的在于保障作为宪法机关的国会和联邦宪法法院能独立行使职权,免受来自“街头压力”的干扰和影响,即保障特定宪法机关的独立性。[12]95不过,禁制区亦有例外许可情形,依德国《禁制区法》第三条规定:“联邦内政部长得会同联邦议长及联邦参议院议长例外許可在联邦宪法法院之禁制区内露天公开集会或游行”。[13]39
现代各国限制集会游行的立法或判例中,均有禁制区或类似于禁制区的规定。日本没有明确规定集会游行的禁制区,但通常禁止在国会附近示威。依据1960年东京都公安委员会决定,自《东京都公安条例》制定时起,对于在开会中之国会周围道路所为集团行动,采取不予许可的方针。至1967年,东京地方法院的一项判决确认仅可在途径国会周围的道路上举行集团游行,而禁止在国会周围道路举行集团示威运动。[14]147-150俄罗斯的《关于集会、示威、游行和纠察的联邦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总统官邸、法院建筑和执行刑罚之监狱场所附近区域”禁止集会游行。*Federal law on Rallies, Meetings, Demonstrations, Marches and Picketing, 2004.韩国《集会示威法》第十一条则规定有“国会大厦、各级法院及宪法法院;总统、国会议长、最高法院院长和宪法法院院长官邸;总理官邸(游行经过时除外);驻韩外交使馆或外交使节住所”的周边100米范围内禁止举行室外集会或示威。匈牙利《集会法》第四条禁止“在国会大厦邻近地区”组织和举行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葡萄牙《关于保证和制定集会权利的规章的第406号法令》第十三条禁止在“距离政府当局总部、军事和准军事机关和兵营、监狱和教养机关、外交代表机构和领事馆以及政党总部不到一百米的公共场所举行集会、群众大会、示威和游行”。
在集会游行法中设置禁制区是限制集会自由权利行使的较为普遍做法,就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国家机关的功能运作而言,故无不可。但诚如李震山教授所言,禁制区往往是集会游行者最喜欢使用之地区,因为其产生之效果最佳。[3]106因此,如何设定集会游行的禁制区,同样涉及公民集会自由保障与限制之间的平衡问题,若设置范围过宽,对集会自由的限制便会有过当之虞。
三、集会自由与私人场所使用限制
表达自由可否在私人所有之场所行使,在英美国家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讨论议题,它涉及两个非常重要的权利,即表达权和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问题。一般而言,所有者对私人所有的场所拥有绝对权,可以排除或禁止任何人使用自己所有的财产。欲使用他人之私人财产从事表达活动,除非经所有者同意,否则便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犯。
但就集会自由而言,由于传统的公共场所逐渐转变为私人所有在英美国家已成为一种趋势,其中明显的趋势就是传统上公众经常用于举行各类集会的商业区(downtown business districts)被私人所有的商业购物中心(shopping centers)所取代。私人所有的购物中心在多数美国大城市成为公共商贸场所,同时这些购物中心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商业区的功能。购物中心有银行、餐馆、舞厅、停车场、邮局、图书馆,有些甚至还有教堂,有些也可提供召开商业会议之用。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购物场所,而且还是散步、闲坐、会友和参与各类社区活动的场所。它不仅是商业活动场所,也已成为人们沟通和表达信息的重要场所。由于很多购物中心的私人所有者通常将那些使用其场所用于表达活动之人排除于使用该场所之外,如果民众仅可以在政府所有的公共场所从事表达活动,那么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所带来的变化,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便会不够充分,因为传统的可用于民众表达的公共场正变得越来越少。因此,是否可以利用私人财产从事表达活动便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面临着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公众表达自由之间的问题。1946年的“马修诉阿拉巴马”(Marsh v. Alabana)案是此类案件的最早判决。该案所争议的问题是阿拉巴马州对未经所有人同意而在私人公司所有的是市镇内散发宗教传单施加刑罚是否符合宪法。本案中位于阿拉巴马州某市郊区的一个名为“契卡索”(Chickasaw)的市镇是由一家造船公司所开发设计并拥有所有权。该市镇除了是由私人所有外,与美国其它市镇并无不同。上诉人马修是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的成员,因未经市镇所有人许可而在该市镇商业区邮局附近的人行道上散发宗教传单,被该私人公司管理者要求其离开。马修拒绝离开,治安官将其逮捕并且地区法院以侵入私人财产为由判其有罪。但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布莱克大法官发表法庭意见认为,所有权并不总是等同于绝对的领地。该所有者越是将其财产开放用于公众使用,他的私人权利就越要受制于使用该私人财产之人的宪法权利所限制。由于该市镇的设施主要是用于服务公众,因此其本质上具有“公共功能”(public function)。该市镇的功能与其他市镇并没有不同,私人公司任命的管理者不能剥夺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和权利,法律对其施加惩罚亦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此外,布莱克最后指出,当在所有者的财产权和公民的出版和宗教权利之间进行权衡时,后者优先于前者,第一修正案的自由乃自由政府之基础。*Marsh v. Alabana, 326 U.S.501 (1946).
布莱克大法官在“马修诉阿拉巴马”案中所阐述的私人财产的“公共功能论”被进一步应用于1968年的“食品联合雇工工会诉洛根瓦利商场”(Amalgamated Food Employees Union v. Logan Valley Plaza)一案中。本案中的上诉人是工会成员,为抗议雇员未获得工资和其他报酬而在被告商场的装卸货物区域和停车场附近举行纠察和示威抗议活动。被告依据本州《侵入法》(trespass law)认为该活动侵犯了其私人财产权利而向法院申请并获得禁止上诉人举行抗议活动的禁令。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援引“马修诉阿拉巴马”案的观点认为,因为本案私人购物中心是作为社区商业区并向公众开放和允许其自由出入,因此该购物中心与“马修诉阿拉巴马”案的商业区“功能相当”(functional equivalent)*Amalgamated Food Employees Union v. Logan Valley Plaza, 391 U.S. 308 (1968).,故推翻了下级法院的禁令。
不过,联邦最高法院也仅在上述两案中表达了支持公众可以在具有“公共功能”的私人场所行使第一修正案的表达权利。在四年之后的“劳埃德公司诉坦尼尔等人”(Lloyd Corporation v. Tanner et al.)一案中最高法院即改变了前述立场。该案中的示威抗议者同样是在私人所有的购物中心散发传单以抗议征兵和反对越战。下级法院依前述两案的判决认为该购物中心向一般公众开放,且具有公共商业区的同等功能,因而认为公民享有在该私人购物中心行使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但最高法院却一反过去所主张的观点,由鲍威尔(Powell)大法官宣读的法庭多数意见认为,被告散发传单与中心的兴建和使用的目的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并且其表达活动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给所有的公众成员,而不仅仅是商业中心的顾客。因而,上诉人可以在任何公共街道、人行道和公园或该市的公共建筑内散发传单。*Lloyd Corporation v. Tanner, 407 U.S. 551 (1972).故而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不过,该案是以5:4做出的判决,法官的意见之间存在很大分歧,马歇尔、道格拉斯、布伦南和斯图亚特四名大法官均发表反对意见,认为抗议者有依据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在购物中心散发传单的权利。但仅在两年之后的“休金斯诉劳工关系委员会”(Hudgens v.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一案中,*Hudgens v.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424 U.S. 507 (1976).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判定,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在对所有者私人财产侵犯较小的其它地方举行集会抗议活动并非不可能或没有效果,因此禁止雇工在私人商业中心设置纠察警戒线抗议不公平的劳工政策并不违背第一修正案保障的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未对公民在私人所有的财产上行使第一修正案的表达权利提供更多的保护。但州宪法在保障个人权利方面却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州法院通过州宪法给予比联邦最高法院提供给公民更多的保护。不过,正如布伦南大法官所言,州宪法也并非绝对保障公民使用私人财产行使表达权利,而仅是禁止具有传统公共功能的私人财产所有者排除希望合理地利用其财产举行表达活动。*William Brennan.State Constitu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J]. 90 Harv. L. Rev. 489 (1977).因此,若要在私人场所行使集会自由的权利,其受限于该场所是否具有“公共功能”以及对该场所的“合理使用”。并且也并非所有的州都提供利用私人场所行使表达自由的优先保护,它主要存在于那些州宪法以“肯认性语言”(affirmative language) 表述公民权利的州中。*美国各州宪法可分为三类:与第一修正案使用相同的“消极性语言”(negative language),有12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属此类;以“肯认性语言”表示言论表达权利,有18个州属此类;“肯认性语言”和“消极性语言”表述的结合,此类有20个州。参见Kevin Francis O'Neill.Disentangling the Law of Public Protest[J].45 Loyola L.Rev. 411, 454-55 (1999).也就是说,美国各州对于使用私人场所从事表达活动的限制并不相同。比如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马萨诸塞和新泽西仅认可有限的进入使用私人所有的购物中心行使言论表达的权利,而密歇根、纽约州、俄亥俄、明尼苏达、华盛顿等十个州则对此给予更多的保护。*Kevin Francis O'Neill.Disentangling the Law of Public Protest[J].45 Loyola L.Rev. 411(1999).
在英国,同样出现了城市空间的私人化趋势,公民是否可以在私有购物中心举行集会等表达活动亦成为重要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于2003年判定的“阿普尔比等人诉英国”(Appleby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案是处理类似问题的一个新近案例。该案中一群人在私人所有的购物中心集会收集签名和派发传单以抗议地方政府兴建公园的计划,被购物中心的保安人员阻止。欧洲人权法院审理此案认为,虽然人口、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变化导致了人们相互之间交往方式发生了改变,但这并不会自动创造出进入使用私人财产的权利。*Appleby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no. 44306/98, 6 May 2003, para.47.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法院最终是依据上诉人有在其它场所集会和收集签名而认为拒绝使用私人所有财产从事表达活动并不违背《欧洲人权公约》第十条的表达自由和第十一条的集会自由。在此案之前,无论是英国国内法院还是欧洲人权法院,亦有多个案例涉及在私人购物中心行使表达权利的问题。法院通常以普通法中的非法侵入他人财产为由正当化限制在私人财产上行使表达权利。*Nick Taylor.Trespassers might be Prosecuted: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 to Assemble[J].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1998(3).但由于私人购物中心不仅是商业和购物场所,它也越来越成为公众聚集和举办各种活动的场所。英国学者亦呼吁应当借鉴美国各州的做法,允许公民合理使用诸如购物中心之类的具有“准公共场所”(quasi-public place)性质的私人财产从事表达活动。*可参见Kevin Gray and Susan Francis Gray. Civil rights, Civil Wrongs and Quasi-public Space[J].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1999(1): 46-102; Jacob Rowbottom. Property and Participation: a Right of Access for Expressive Activities[J].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2005(2): 186-202.
四、集会自由与场所使用的其它义务
集会游行需要使用一定的场所,那么可否对此种场所使用收取费用或施加一些特定义务呢?若是使用私人所有的场所,毫无疑问是可以的,但如果使用的是公共场所,是否可以施加此种义务则成为一个问题。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向集会游行举办者或组织者收取为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费用和为保持公共卫生的场所清洁费用。
美国在1941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考克斯诉新罕布什尔州”(Cox v New Hampshire)一案中确立了一个准予向示威者收取费用以补偿政府因言论表达活动而产生开支的先例。*Cox v New Hampshire, 312 U.S. 569 (1941).该案中的示威者希望在公共人行道和街道举行游行,而地方法规规定示威者应当申请许可并支付不超过300美元一天的许可费。一群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因未申请许可被起诉和判罪,联邦最高法院受理该上诉案后判决许可制合宪并认为收取许可费用的要求也是合宪的,法院的判决指出,许可费用从300美元至仅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是一个可以允许的合理范围,对于游行或庆祝集会而言,都会导致为应对此种事件的公共开支,并且该费用并非财政税收,而仅是对为维护公共秩序而额外产生的行政开支的补偿,因而限于此种目的而收取费用并不违背宪法。*David Goldberger.A Reconsideration of Cox v. New Hampshire: Can Demonstrators Be Required to Pay the Costs of Using America's Public Forums[J]. 62 Tex. L. Rev. 403,(1983).该案是美国最高法院针对示威游行收取费用是否合宪做出的仅有的一个判决,此后并没有类似的判决,其原因是因为美国管制集会游行的权力属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并非都对集会游行采许可制,并且在采许可制的地方又同时规定必须缴纳许可费的则更少,因此,因收取许可费用而产生的过分限制公民集会自由的问题并不普遍和突出。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些地方法规规定在街道、人行道或公园等公共场所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比如芝加哥公园区要求为了获得在公园集会的许可,申请者应当支付许可费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要求示威者支付警察在下班期间维持秩序的费用;克利夫兰市则要求示威者支付因示威活动产生的清洁费用;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市则要求示威者在公共街道举行示威游行前支付责任保证金。[25]不过这些地方法规也未引起是否合宪的诉讼,至少联邦最高法院未做出此类的判决,由此可见美国对于是否对集会游行收取费用,基本是属于地方政府的裁量权范围内。
德国的集会法中没有对集会游行收取费用的规定,但是判例及道路法中确立了集会游行必须负担道路清除费用。联邦宪法法院在1988年9月6日做出的一个判决中表明了法院对集会游行施加此种义务的立场,该案中法院认为,举办集会若导致道路污染之结果,虽然集会法上并未规定有清除义务或费用偿付义务,但各邦道路法对此有规定,并不因集会法未规定而受排斥。不过,集会游行举办者对道路污染所负责任必须是道路污染超过一般程度,并且道路污染必须是由示威举办人直接所导致,例如示威举办人供给参与人饭菜、饮料等,或因示威参与者分发传单导致道路污染时,可认为该道路污染为示威举办人所直接导致。产生此一道路污染情形,集会游行举办者必须承担道路清洁的义务,若未履行该义务者,则必须承担相应的道路清洁费用。[11]61-62依据该判决,在德国使用道路集会游行时,若导致道路污染超出一般程度并且该污染与集会游行的举办直接相关时,必须对此承担相应的道路清洁义务。至于可否向集会示威者收取警察维持公共秩序的额外费用,德国部分各邦法及实务上均肯认此种做法,但德国学界大多却对此持否定态度。[11]60
以维持公共卫生为由而限制集会自由的做法,通常较能获得肯定并有制定法上的明确支持。《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依据法律,符合民主社会之需要,基于国家安全或公众安全的利益、为了防止失序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或维护他人自由及权利诸原因”可以对和平集会自由权施加限制,其中的“保护健康”可以视为是为维护公共卫生而限制集会自由的立法例。日本东京都所制定的《集会、集团行进及集团示威运动有关条例》第三条第六款规定,为“保持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可对集会游行附加必要条件的限制,亦属于此种立法例。
集会游行虽属于暂时性活动,但由于是群体聚集活动,尤其是在大规模集会游行活动中难免产生人为垃圾和损害环境而影响他人健康及城市卫生的问题,以“公共卫生”为由限制集会自由的立法规定有其合理性。至于集会游行者到底该对此承担多大的环境清洁责任,依上述各国判例或立法,一般而言,集会自由权的行使如妨碍交通一样,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卫生环境问题,因此对于在公共场所的集会游行,基于保障集会自由行使考虑,对于集会游行所产生的一般性垃圾污染问题,政府应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此系保障集会自由之政府责任,而对于超出一定限度的环境污染,由集会游行者承担此部分的责任。对于因集会游行导致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费用问题,若是在警察执勤上班期间,维持公共秩序属警察本职工作和政府责任,此费用属政府应承担的公共开支;但若非在警察执勤上班期间,因集会游行所生之维护公共秩序问题,对集会游行者收取恰当比例的警察费用,亦不违背宪法所保障的集会自由。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对于集会游行等群体聚众行为施加了诸多场所限制以确保公民权利行使有序进行。场所限制主要为公物使用限制、禁制区限制和私人场所限制三种。集会游行的公物使用限制主要集中于“公共用物”和“营造无用物”使用限制两个方面。一般而言,“公共用物”如公园和道路等对集会游行的限制较少,而使用“营造物用物”如体育馆和公立学校等举行集会游行则应以不对该营造物本身功能使用造成较大妨碍为限。禁制区之于集会游行的限制,除特殊情况外,乃属绝对禁止性限制。而私人场所原本也可绝对禁止集会游行的举行,但对于那些具备“准公共场所”性质的私人场所,仍涉及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公民表达自由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上,集会游行的场所限制的核心是集会游行权与他人对该空间场所使用权利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欲解决这种权利冲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处理权利冲突的规则安排以及管制者和权利行使者对于权利行使的边界和规则具有基本的认同。本文基于发达国家的法治经验,阐述了对于集会游行等群体行为施加场所限制的法理,希图能够对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以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的规范轨道提供参考。
参 考 文 献:
[1]陈敏.行政法总论[M].台北: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
[2]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李震山.论集会自由与公物使用间之法律问题[J].东海法学研究,1995,(9).
[4]陈新民.示威的基本法律问题[M].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
[5]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M].林来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邝世泰.日本国宪法中集会自由权的法理研究[D].淡江大学日本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
[7]陈建儒.自由权公约机会自由研究——以日本国内为中心[D].淡江大学研究所论文,2012,119-120.
[8]因示威游行违反道路交通法等案件[M].日本国最高法院裁判选译(第1辑).林素凤,译.台北:“司法院”印行,2002.
[9]李英毅.集会自由的概念及其限制之研究[D].辅仁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
[10]施宇轩.现行集会游行法之检讨:以集会自由保障为中心[D].台湾大学硕士论文,2008.
[11]张嘉政.人民集会游行权利之规范与保障[D].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责任编辑:林衍
On the Place Restriction for Mass Gathering Behaviors-Centering on the Analysis of Assemblies and Processions
Wang Jiang-wei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Jiangx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Nanchang 330003, China)
Abstract:Implementing place restriction for such mass gathering behavior as assemblies and processions is one of the major legal means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to regulate collective actions. Place restriction for assemblies and processions can be classified as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public property, restriction of prohibition area and restriction of personal places.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public property mainly includes public goods and public facilities. Prohibition area belongs to the compulsory restriction exclusive of special cases. Personal places also prohibit assemblies and processions.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refer to the legal experiences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restricting mass gathering behaviors.
Key words:mass gathering behaviors; assemblies and processions; group events; place restriction
收稿日期:2015-12-1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发达国家社会冲突治理比较研究”(15ZZ09);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基金项目“发达国家聚众抗争活动的法律规范研究”(CCPDS-FudanNDKT15004)
作者简介:王江伟(1988- ),男,江西丰城人,江西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从事社会冲突治理法治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45(2016)01-0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