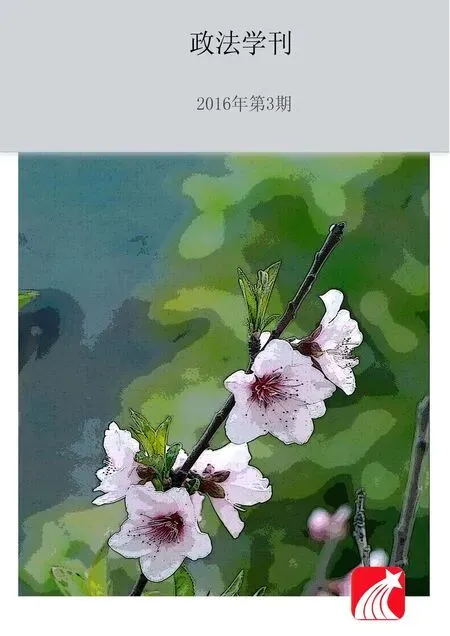论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
——对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的重新考察
李红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论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
——对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的重新考察
李红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法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基于投保人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假定与人身保险合同兼具投资属性的认识论,我国《保险法》的立法者认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道德风险,并据此规定了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要求投保人于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应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目的在于控制投保人的道德风险。然而,该规则不仅存在功能定位错误之缺陷,且滋生出了若干问题,一种旨在替代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的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也远未能解决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所面临的困境。
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
一、引言
道德风险又称为道德危险,其含义可分别从保险学和保险法两个角度进行界定。在保险学上,道德风险是指“个人在得到保险之后改变日常行为的一种倾向。道德风险有事前和事后之分。事前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得到保险后就丧失了阻止损失的动力。……事后道德风险是指在损失发生后被保险人丧失减少损失、减轻损失程度的动力。”[1]37在保险法上,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为诈取保险赔偿而违反法律或合同,故意引起或扩大保险事故的危险。”[2]32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由于保险事故发生的本体为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一旦道德风险发生,必然危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也会给保险人的正常经营带来冲击和挑战。为防范此种道德风险,我国仿照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在《保险法》 中通过多个条文规定,投保人于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应对与其存在特定关系的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其所订人身保险合同无效。本文将该等条文所规定的内容称为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对于该规则,学者之间赞同者有之[3],否定者也大有人在,并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4]
本文虽不赞成“存在即合理”的说辞,但认为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的出现也是“事出有因”。笔者坚信,假如我们未能确知《保险法》作出如此设计的深层次原因,纵然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保险法》修改的研究中,并提出一系列完善建议,也可能面临“种下龙种,收获跳骚”的尴尬境地,或者说,我们开出的药方并没有显著疗效。有鉴于此,本文不打算提出完善《保险法》的对策建议,而只是着眼于尽可能客观地描述该规则的构造,讨论该规则的不足,揭示该规则得以产生的原因,并对学界提出的用以补救保险利益规则不足之处的替代规则作出初步分析,以彰显《保险法》改革的复杂性。
二、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的基本构造
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是一个规则群,涉及到《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三、四、五款和第三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综合这些规定可知,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包含两项具体规则:其一是投保人保险利益确定规则;其二是投保人保险利益存在时间规则。前者涉及特定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问题,后者涉及特定保险利益应于何时存在的问题。以下分别讨论这两个规则:
(一)投保人保险利益确定规则
《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保险利益确定规则的目的是对投保人的资格予以限制,其实质意义在于划定投保人的范围,以便筛选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不会故意施以危害的人。该规则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求投保人应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一、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由于投保人可以是被保险人,因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二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因此,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所具有的保险利益也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投保人对自己的寿命或身体具有的保险利益,本文将之称为自体保险利益;二是投保人对他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的保险利益,本文将之称为他体保险利益。
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保险事故发生的本体即为被保险人自己,尽管也存在被保险人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可能性,但防范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显然不是投保人保险利益确定规则的主要任务,而是诸如自杀条款等相关规则的意义所在。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由于保险事故发生的本体不是投保人自己,而是被保险人,因而投保人似乎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以骗取保险赔偿金的可能性。为控制此种情况下的道德风险,《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要求投保人应具有他体保险利益。根据该条的规定,认定他体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规则是,只有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或获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时,他体保险利益才得以存在或视为存在。这种特定关系或者为特定亲属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或者为金钱利益关系,如抚养人与被抚养人、扶养人与被扶养人、赡养人与被赡养人或雇主与雇员。可见,按照《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逻辑,只有在他体保险利益场合,投保人保险利益确定规则始真正具有控制道德风险的功能。
(二)投保人保险利益存在时间规则
《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据此可知,在我国保险法上,投保人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为“保险合同订立时”,即在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必须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人身保险合同无效;在特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该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对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不发生影响。
“合同的订立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为意思表示、达成合意而成立合同的过程和状态。”[5]60此所谓过程是指各方当事人为使合意得以达成而实施的接触和洽商等一系列动态行为。人身保险合同是合同的一种,其订立当然也历经接触和洽商等缔约过程,该等动态行为主要包括“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保险人同意承保”等。 因此,《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所称的“保险合同订立时”究竟是指“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时,亦或是指“保险人同意承保”时,即人身保险合同成立时?从《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范意旨看,此处的“保险合同订立时”似乎应指人身保险合同成立时。这是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将“保险合同订立时”认定为人身保险合同成立时也与《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相一致。然而,在人身保险合同的成立时间与生效时间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投保人和保险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生效条件或附始期的时候,就不宜将“保险合同订立时”认定为人身保险合同成立时,而应将“保险合同订立时”解释为人身保险合同所附生效条件成就或所附始期到来的时候,因为在此之前人身保险合同并未生效,保险责任期间也未开始起算,应该不会出现投保人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情事,因而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无任何意义。
三、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的内在缺陷
按照《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设计,投保人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应具有保险利益。审核这种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标准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具有某种特定关系,或者在这种特定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的行为是否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之所以要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具有某种特定关系是因为,这种关系通常是基于血缘、婚姻等因素建立的,这种关系的背后存在着经济利害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防止利用保险毁灭他人寿命以非法获利的重要手段。”[6]52此种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存在特定关系来审核他体保险利益存在性的规定称为利益原则,以投保人是否获得被保险人同意为由认定保险利益存在性的规定称为同意原则,即《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在确定他体保险利益的存在性问题上采取的是“利益、同意兼顾原则”。[2]35很明显,《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认为,在“利益、同意兼顾原则”之下,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具有防范投保人道德风险发生的功能。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尽管保险利益制度具有“防止有人将保险作为赌博的手段”[7]73,进而控制道德风险的作用,但将该制度推及到人身保险合同领域则缺乏坚强的理论支撑,且会导致对该制度的功能发生定位错误的危险。
按照《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立法构想,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他体保险利益具有防范投保人道德风险的功能。然而,此种要求与投保人道德风险的防范并不相干。实际上,在他体保险利益场合,投保人根本就不存在道德风险,遑论防范?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事故发生的对象为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因此,被保险人始终是损害的承担者,只不过这种损害与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损害不同,前者为抽象性损害,后者为具体性损害。基于损害填补的理念,被保险人恒为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者,“此赔偿请求权之归属于被保险人并非由要保人指定受益人所致,乃是基于保险之内容在补偿真正受损害之人之结果。”[8]125相反,投保人并非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其只有在经被保险人指定为受益人后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因此,当投保人未经被保险人指定为受益人时,其并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因而其不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主观动力;当投保人经被保险人指定为受益人时,其始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因而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主观动机,以致危害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不过,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之所以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主观动力,并不是因为他是投保人,而是因为他是受益人。于此之际,《保险法》应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防范受益人的道德风险。不过,这已与《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立法构想无关了。
或许有学者认为,即便在投保人因未被指定为受益人而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况下,其虽不能成为直接的受益人,但很可能是一种具有间接利益的关系人。例如,在投保人与受益人具有夫妻关系的场合,作为丈夫的投保人不是受益人,不能直接从保险事故中受益,但作为妻子的受益人则可以直接从保险事故中受益,由于夫妻关系的存在,因而作为丈夫的投保人也可以间接受益。因此,投保人也就有了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主观动力。也就是说,在此种场合,投保人也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道德风险,因而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也具有防范道德风险的作用。应该说,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的确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主观动机,因而似乎存在遵守他体保险利益要求的必要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于此种场合之所以存在道德风险并不是因为他是投保人,而是因为他基于同受益人具有某种利益与共的关系而成为具有间接利益的关系人,并能从保险事故中间接获益。换句话说,正是投保人所具有的“间接利益关系人”身份才使得其产生了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主观动机。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道德风险需要采取措施加以防范。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对于这种道德风险是否可以通过保险利益制度予以控制。本文认为,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具有“间接利益关系人”身份的人很多,比如受益人的父母、子女,他们都可能为了获得“间接利益”而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如此一来,难道我们能要求他们都应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吗?如果不能,我们怎么能仅仅要求同样具有“间接利益关系人”身份的投保人应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呢?难道投保人与其他具有“间接利益关系人”身份的人相比,其道德风险更大?窃以为,我们不能作出这种区别对待。实际上,防范包括投保人在内的具有“间接利益关系人”身份的人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法律机制是侵权责任制度和刑罚制度,而不是保险利益制度,那种认为可以通过保险利益制度来控制投保人道德风险的观点无形中扩大了保险利益制度的功能,甚至是赋予了保险利益制度本不具有的功能。
总之,在投保人与受益人并非同一人的情形下,投保人无从基于其投保人身份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获利,即便其因与受益人存在利益与共的关系而能够从保险事故中间接获利,但此种获利与其具有的投保人身份无关。因此,站在投保人身份角度看,投保人自然不会有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动因。当然,若是基于间接利益关系人身份观察,投保人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主观动机,然而控制此种道德危险并非保险利益制度的功能。有鉴于此,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他体保险利益并无实益,甚至还会由此增加法律操作的复杂,进而抑制保险业的发展。[9]69实际上,这种对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功能的定位也与保险实践不甚吻合,实践中投保人无须具有保险利益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单位为更好地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为其投保团体家财险、人身险;政府为见义勇为者投保意外伤害险等等。[10]69
四、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的设计动因
(一)投保人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假定
本文认为,《保险法》第三十一条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或保险金受领权。因此,如果投保人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他体保险利益,其就没有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以骗取保险金的主观动力。这是因为,如果投保人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他体保险利益,则基于“损害乃保险利益之反面”的基本观念,在特定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所具有的他体保险利益也会受损,因而投保人遭受损失也是势所必然,但其未必能获得保险赔偿,甚至还会因此面临刑事追诉。 考虑到这些情况,一个理性的投保人断然不会产生通过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以骗取保险金的念头。反之,如果投保人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不具有他体保险利益,则其在主观上就具有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以骗取保险金的动机。这是因为,对于特定保险事故的发生,投保人不仅不会遭受损失,而且还可能成功地骗到保险金。当然,尽管其未必能获得保险赔偿,甚至还会因此面临刑事指控,但这对于一个理性的投保人来说,总是可以“赌上一把”的。这一点,在《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看来是极为可能的,这应该是《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立法理由所在。
对于《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理论假定,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这种假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命题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是“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其最大的特征就是负有向保险人支付约定的保险费的义务,而没有向保险人主张保险赔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归属于被保险人,因为被保险人是其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也就是说,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并不因其与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而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或保险金受领权。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获得被保险人同意后将自己指定为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将其指定为受益人,然而此时其之所以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不是因为他是投保人,而是因为他是受益人。这种身份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投保人保险金请求权的有无,还意味着道德风险控制机制的构建,即在投保人不具有受益人身份时,因其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而不存在道德风险,因而也无需为其设计道德风险防范机制;在投保人兼具有受益人身份时,因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而存在道德风险,因而必须设计道德风险防范机制,但该机制应围绕受益人的道德风险而设计,与投保人道德风险的有无没有关联。
(二)人身保险合同兼具投资属性的认识论
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投保人保险利益存在时间规则,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所具有的他体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为“保险合同订立时”,在特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该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对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不发生影响。这一点显然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 对于二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有学者指出:“人身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之所以不同于财产保险,究其原因在于:……如于保险利益消失后即认为保险责任终止,对保单持有人有失公允。因为其将来所应得的保险金是过去已缴保险费及其利息的积存,对投保人来说,具有储蓄性质。如其在保险合同订立后因保险利益的消失而丧失原来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应得的保险金,无异于使其权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因此,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不必限于保险事故发生时。”[11]86
从这种解释中可以看出,正是为了确保投保人在丧失他体保险利益后仍然能够获得“原来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应得的保险金”,《保险法》第31条才规定他体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为“保险合同订立时”。隐藏在该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人身保险除了具有补偿性外,还具有投资属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具有投资性保险的色彩”。当然,要求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享有他体保险利益,且该利益于保险合同订立时存在即为亦足的做法也存在于境外一些国家的保险法上。例如,在英国,尽管有学者认为,根据1774年《人寿保险法》第一条和第三条的文意判断,保险利益需要同时存在于投保时和保险事故发生时,且早期的判例也持这一看法,但该判例所确立的规则并没有为此后的案例所遵循。相反,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即便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享有的他体保险利益已经丧失,保险人仍然会向其支付全部保险金。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基于人寿保险的市场规划。在美国,1854年的一个判例明确指出,保险利益仅仅需要存在于保险合同生效之时,而无须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仍然存在。该判例得以确立的部分原因是保险人的商业习惯,部分原因是基于人寿保险合同非补偿性的理论以及避免导致人寿保险高额保费全部丧失状况的出现。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及英美等国保险法将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享有他体保险利益的时间限定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身保险兼具补偿性和投资性,尤其是人寿保险的实质属性更是被定位为投资性,而不是补偿性。应该说,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的投保人保险利益存在时间规则不仅有利于投资性保单的流动性,而且还可以保障人寿保险交易的完整性,既保留了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又确保了合同允诺的稳定性,因而这种规则有其实效性,对于投保人和保险人都是有利的。对于投保人而言,按照《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逻辑,只要其在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拥有他体保险利益,即便此后丧失了该保险利益,其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仍然有权领取保险金。此外,投保人还可以凭借这种保单的流动性来融资。对于保险人而言,这种具有流动性的保单增强了人身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产品对投保人的吸引力,这无疑有利于保险人开展此类保险产品的市场营销活动,进而增加其收益。不过,这只是沿着《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逻辑进行的推导,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原因在于,即便是那些主张人身保险合同具有投资属性的学者也承认,只有在长期的人寿保险合同项下,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才具有储蓄的特点。[12]95而人身保险合同除长期人寿保险合同外,还包括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和健康保险合同等,在这些保险合同项下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不具有储蓄特点,因而这些保险合同在性质上与所谓的“投资性”并没有关联。也就是说,以人身保险合同的“投资性”来证成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保险利益存在时间规则的合理性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
五、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的替代设计
由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并不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因而其没有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动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保险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不具有防范道德风险的功能。然而,这不意味着在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不会遭受道德风险的威胁。事实上,这个威胁就来自于受益人。 原因在于,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在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相异的情况下,受益人就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动机。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如何设计一种制度来控制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对此,《保险法》规定了受益人指定规则。根据该规则,被保险人和投保人都享有受益人的指定权,但“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且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均享有受益人变更权,但“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可见,尽管《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享有受益人的指定权和变更权,但投保人在行使“指定权和变更权”时应受到被保险人“同意权”的限制。实际上,被保险人的“同意权”已经架空了投保人的“指定权和变更权”,被保险人才是受益人指定权和变更权的真正主人。对于这种受益人指定规则,有学者认为,该规则已足以防范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其理由是:“被保险人作为一个理性人,应当有能力识别和判断将他人指定为受益人对自己的寿命是否会造成威胁,……在受益人的指定上应当充分尊重被保险人的意思自治。”[13]本文将这种观点称为“理性人假说”,其学理基础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寿命具有无限的保险利益,并且假定被保险人不会指定一个更乐意他伤亡而不是存活的人为受益人。
但也有学者认为,“理性人假说”并不可靠,因为拟制的逻辑依据在于被保险人不会指定一个可能杀害自己的人作为受益人,但不幸的是由给付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实施的谋害行为时常发生。因此,该学者主张,为更好地控制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道德风险,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上述受益人指定规则,还应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一番“添加”作业,以替代不具有道德风险控制功能的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具体设计是,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应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且该保险利益不仅需要存在于保险合同生效时,也需要存在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同时,受益人的指定还应获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但是,在一般性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指定仅应获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受益人无需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理由是,“由于逻辑依据并不可靠,在一般的给付性保险中原则上还可以忍受这种风险的存在,但在可能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死亡给付性保险中则有必要谨慎待之。”[4]可见,这种“添加”作业的实质内容是,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要求受益人应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终始”性的保险利益,笔者将之称为受益人保险利益,并将这种要求称为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显然,按照学者的这种设计,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应同时遵守受益人指定规则和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而在一般性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仅需遵守受益人指定规则即可。此外,在该学者看来,在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之下,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的保险利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家庭情感利益,称为情感型保险利益,如受益人对作为被保险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具有的保险利益;另一类则是对于被保险人的继续存活具有法定的或实质上的经济利益,称为经济型保险利益,如受益人对作为被保险人的抚养人、扶养人、赡养人、雇员所具有的保险利益。
上述受益人指定规则和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构成了控制人身保险合同中道德风险的两道闸门。然而,相对于受益人指定规则,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更有讨论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前者为法定,后者为学者所设计,更重要的是因为后者事实上替代了《保险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按照该学者的见解,一方面,由于投保人不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因而其没有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动机,进而专门为防范投保人道德风险而设计的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由于“受益人系保险事故发生得请求保险金之人,因而可能引发道德危险之人应是受益人。……若要避免道德危险之发生,必须对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之关系加以严格限制才是。”[8]71而进行这种限制的工具就是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显然,这是一个控制方向的变化。不仅如此,在存在时间上,后者对前者也作了修正。在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中,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所具有的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为一个时段:从保险合同生效时至保险事故发生时;而在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所具有的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为一个时间点:保险事故发生时。
显然,与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相比,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认清了道德风险的来源,推翻了“投保人当然享有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假定”,因而在防范道德风险上更具有针对性,可谓是“有的放矢”。同时,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也否定了“人身保险合同兼具投资属性的认识论”,认为将人身保险合同定位为“投资性合同是欧美国家将各种金融产品的衍生特性过度演绎的一个缩影”[4],人身保险合同既不是损失补偿合同,也不是投资性合同,而是一种损害弥补合同,其价值在于提供安全感和确定性,而不是流动性。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若不再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就意味着他没有遭受损害,因而也应丧失受益权;如果此时坚称受益人仍然享有受益权,就无异于变相地鼓励受益人去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如此,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就失去了控制受益人道德风险的作用。有鉴于此,为控制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就没有必要为了保持保单的流动性而不要求受益人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毫无疑问,这种对于人身保险合同属性的认识客观上也助于防范受益人的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寿命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该替代设计的核心是,要求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同时执行受益人指定规则和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那么,这两个规则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首先,根据受益人指定规则,受益人的产生要历经被保险人“指定或同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保险人通常能够识别和判断出他人是否会为诈取保险金而对自己的寿命采取行动,并据此作出是否将该他人指定为受益人或同意其为受益人的决定。这说明,通过“指定或同意”过程被保险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那些有可能为图谋保险金而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人排除在受益人之外,并因此可以避免一部分道德风险事故的发生。当然,在这只是基于前述“理性人假说”作出的推论。实际上,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这种推论并不完全可靠,或者说,被保险人的“识别或判断”也存在失败的可能。为了应对在此种“识别或判断”失败情况下存在的受益人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道德风险,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就派上了用场。这是因为,如果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且该保险利益自保险合同生效时至保险事故发生时一直存在,则基于“损害乃保险利益之反面”的观念,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也必将遭受损害。这就意味着,如果受益人意图诈取保险金而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即使其能够获得保险赔偿,也将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致其遭受损害而得不偿失。考虑到这一点,一个理性的受益人就会抛弃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以诈取保险金的念头。于是,受益人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道德风险就得以避免。
然而,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未能解决的问题是,既然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并会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遭受损害,且享有保险金请求权,那么,受益人就是名副其实的“其人身或财产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即成为被保险人。如此一来,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就是同一个人。换句话说,只有在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才会存在“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并会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遭受损害,且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况。但是,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却是为解决在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相异的情况下受益人的道德风险而提出的,这是一个悖论!
六、结论
在我国《保险法》的立法者看来,人身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当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且人身保险合同具有投资的属性。基于这种假定和认识,该等立法者认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道德风险。为控制这种道德风险,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就“粉墨登场”了。然而,这种认识与实践并不相符,该规则的逻辑前提即投保人存在故意制造或扩大保险事故的道德风险也不存在,这导致该规则面临自始“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局面,并增加了法律操作的复杂性。作为投保人保险利益规则的替代设计,受益人保险利益规则虽然认清了道德风险的来源,因而在防范道德风险上更具有针对性,但其仍然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一个本来旨在控制在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相异的情况下受益人的道德风险而提出的法律规则为何只能适用于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
[1]孙祁祥.保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温世扬.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邵海.人寿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归属与法律适用[J].社会科学家,2011,(6):86.
[4]温世扬.给付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制度构造——基于比较法的视角[J],中国法学,2010,(2):82-90.
[5]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陈欣.保险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傅廷中.保险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8]江朝国.保险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9]杨芳.可保利益效力研究——兼论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反思与重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0]刘宗荣.新保险法:保险契约法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2]傅廷中.保险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3]姚军,于莉.被保险人意思表示对人身保险合同的意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5):129.
责任编辑:韩 静
On the Rule of Insurable Interest of Policyholder in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Li Hong-ru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olicyholder surely has the right to insurance claims and on the epistemology that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has investment properties, the lawmakers of Insurance Law of China argue that the policyholder will have the moral risk of deliberately creating or expanding insurance accident in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Accordingly, Insurance Law of China prescribes that the rule of insurable interest requiring policyholder shall have insurable interest on the life or body of the insured at the time of entering into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which aims at controlling moral risk of the policyholder. However, this rule does not only has defects of functional positioning errors, but also causes a number of problems. An alternative rule of insurable interest of beneficiary far fails to resolve the plight that the rule of insurable interest of policyholder faces.
life insurance contract; policyholder; insurable interest; rule
2015-04-21
李红润(1974-),男,河南信阳人,法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从事公司法、银行法等研究。
DF59
A
1009-3745(2016)03-003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