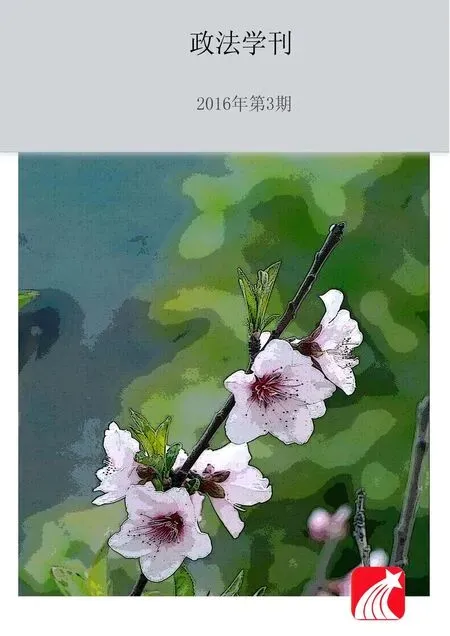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效力改革研究
刘 晓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效力改革研究
刘 晓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
《欧洲人权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效力问题,此类判决效力仅约束诉讼当事国。随着积案问题以及判决执行难题的加重,法院从判决效力角度采取了改革。引导性判决改革打破了法院针对具体案件作出特定性判决的裁决思路;非当事国判决改革打破了一般国际法判决仅约束诉讼当事国的传统。这在国际法上具有极大创新性,体现了欧洲人权法院不再仅仅依靠部长委员会监督判决执行,而不断重视自身在判决执行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欧洲人权法院不断重视国内人权保护机制,人权保护由国际保护层面向国内保护层面转移。
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公约;引导性判决;非当事国判决
欧洲作为区域人权保护最早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最发达的区域人权法律保护机制,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比如,针对最为突出的法院积案问题,1998年《欧洲人权公约第11号议定书》改革机构设置,建立了单一常设人权法院,人权委员会从此不再享有审案权利,“双重机制”退出历史舞台;2004年《欧洲人权公约第14号议定书》改革案件受理标准,对个人申诉设立了“严重损失”(significant disadvantage)受案标准;第14号议定书在案件审理程序方面,新设独任法官制度,对事实清楚的申诉可以作出不可受理或将其从待审案件名单中删除的决定;设立三人委员会制度,对于重复性案件可以由三人合议庭通过简单程序迅速作出判决;2013年通过但尚未生效的第16号议定书更是提出设立欧洲人权法院新咨询管辖权(advisory jurisdiction)制度,成员国国内最高法院或法庭可以向欧洲人权法院请求咨询建议,进而试图进一步解决法院的积案难题。立足于欧洲人权法院改革问题,本文主要着眼于研究欧洲人权法院以判决效力为视角采取的改革,揭示其中的大胆创新性,探究其中的改革理念及对国际社会的启发意义。
一、一般判决效力改革(res judicata effect)
一般判决是指欧洲人权法院作出的通常性判决,为了与引导性判决与非当事国判决区分,将其称为一般判决效力,从而突出引导性判决和非当事国判决的特殊性。在探究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效力改革的内容特点之前,有必要对《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明文规定的一般判决效力的内容以及作为监督机构的部长委员会对法院判决执行问题进行的改革探索做出简要分析,从而与欧洲人权法院采取的引导性判决和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突出欧洲人权法院改革思路的创新性与独特性。
(一)一般判决效力的条文规定
欧洲人权法院作为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的司法监督机构,法院判决效力问题专门规定在《公约》第四十六条。《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1、各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遵守法院的最终判决。2、最终判决应当转交给部长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由其监督执行”。公约这两款,一方面规定了缔约国对法院判决遵守的义务;另一方面规定了法院判决的监督执行机构。需要注意的是,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判决效力问题,是指缔约国有义务遵守其作为诉讼程序参与当事国的判决,也就是说第四十六条的判决效力仅仅约束参与诉讼程序的当事国。我们通常也把此种判决的效力称为“既判力”(res judicata effect),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res judicata effect是指“已判决的事项或案件”,它所强调的是判决的确定性、终局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大多数国际性法院或者法庭所做出的判决都具有此种相似效力,即仅仅约束参与诉讼程序的当事国。[1]223-262比如,《国际法院规约》第五十九条规定:“法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美洲人权公约》第六十八第一款规定“本公约各缔约国承允对它们是当事国的任何案件服从法院的判决”;《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关于建立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的议定书》第三十条规定:“议定书的缔约国应当遵守其作为当事国的案件判决,并保障判决的执行”。
(二)一般判决效力的执行情况
《公约》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由部长委员会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但是公约并未对监督程序作出具体规定。部长委员会每年都要召开四次定期会议来讨论判决的执行问题,成员国也需要提交执行法院判决所采取的行动情况。如果国家对于一个案件的执行采取了充足的行动,委员会将对其作出一个最终的决议,这些最终决议会出现在有关判决执行的重大文件中,并且是公开的,其他各国都能查阅到。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给成员国带来压力,产生一种潜在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成员国执行判决。但是,欧洲人权法院一般判决的执行,主要还是来自于成员国的配合。部长委员会自己也承认对判决执行的监督可以看成是一项需要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任务,而非由部长委员会以审讯式方法独立完成的工作。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一般判决效力并没有强制约束力,它的执行并不构成直接的国际法义务,国家可能被施压(be pressurized)来执行判决,但是他们不能被强迫(be compelled)执行。[1]223-262根据2012年成员国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在部长委员会等待执行判决最多的国家有8个,按照数量递减的顺序依次为:意大利(2569件),土耳其(1861件),俄罗斯(1211件),乌克兰(910件),波兰(908件),罗马尼亚(667件),希腊(478件),保加利亚(366件),[2]当然上述8个国家案件申诉量也占到法院案件总负荷量的75%。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法院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判决执行压力。
(三)部长委员会对一般判决执行的改革探索
针对法院面临的执行难题,各方积极呼吁作为监督机构的部长委员会采取相关改革措施。比如,2004年《欧洲人权公约第14号议定书》中,各方曾呼吁能够在《因特拉肯宣言》中建立制裁措施,如经济制裁(征税)和非经济性制裁,建议建立准司法机构来执行判决,力求通过这些努力,最终形成一种对成员国政治问责的良好环境,来保障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执行。2010年《因特拉肯宣言》中,强调“全面、有效、及时的执行法院最终裁决是绝对必要的”。[3]2012年《布莱顿宣言》中,虽然在执行问题上没有提出一些切实的改革,但也以一种不明确的表述规定:“对于成员国未能遵守公约第四十六条情况下,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并且请求部长委员会“考虑对于成员国未能及时执行判决的行为是否有必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4]《因特拉肯宣言》和《布莱顿宣言》针对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虽然仅仅做了模糊性的规定,但这也可能会为法院将来增加一些目前尚不存在的执行惩罚措施起到一定的准备作用。[5]238此外,有些外国学者在文章中提出各国国内的配合作用是执行的基础和关键,并提出由国内哪个部门来承担配合作用会直接影响政治意愿,进而影响到判决的执行。[6]639-653总之,判决执行难是法院目前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作为判决执行监督机构的部长委员会其内部改革的进度及成效均有限,而案件判决的执行积压间接加重了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件受理量。对于任何机制,判决是否得到充分执行代表着其有效性的发挥;而减少判决执行压力的路径有两种:一是由监督执行机构采取改革措施提高执行情况,这是部长委员会一直的改革思路;二是由判决的作出机构从源头采取改革,这正是欧洲人权法院采取的改革路径。法院面临日益严重的积案问题,不再仅仅着眼于改革法院机构设置、提高案件受理标准、设立简易程序等措施,而是转向判决效力的改革路径,创设引导性判决程序和非当事国判决效力。
二、引导性判决改革(Pilot Judgments)
(一)引导性判决的创立背景及内涵释义
欧洲人权法院不仅面临着执行难题,也面临着严重的积案问题,两者紧密相连。如果法院做出的一般性判决得不到充分执行,成员国没有积极修改国内措施,这将会使得更多案件诉诸于法院,进而造成法院案件严重负荷。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2010年因特拉肯会议前,法院有119300个未决案件,其中19859个(17%)重复性案件;在2012年布莱顿会议前,法院未决案件149450个,重复性案件达到36060(24%);截止到2014年4月1日,法院共有96050个未决案件,重复性案件达到41375(43%)。[7]由此可以看出,欧洲人权法院的严重积案中存在很多重复性案件,这些案件所涉及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在以往判例法中均处理过。更有数据显示在法院受理的重复性案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可接受案件是由于一国法律秩序内体制性问题(systemic violations)造成的人权侵犯。[8]1231
引导性判决程序正是针对欧洲人权法院存在的大量重复性案件创设的,这种重复性案件特点是需要法院在基于各成员国国内相同的体制性问题引发的众多案件中重复性的做出违反公约的规定,而在这一过程中法院不会提出新的法律问题,这种重复性的诉求给法院增加了繁重的负担。[9]147引导性判决的英文表述是 pilot judgment,pilot 一词有“试验性的” 或“引导的” 的含义,刘丽博士在《欧洲人权法院权利救济新举措——引导性判决程序评析》一文中,将其翻译为“引导性判决”。本文借鉴此种译法,“引导性”的译法能直接反映此类判决的性质是引导性的,引导被告国国内采取一般措施解决问题,直接突出此类判决的特点。引导性判决程序创设的初衷是为减少一国国内体制性问题引发的重复性案件诉至欧洲人权法院,减轻欧洲人权法院案件负荷压力,在改革路径上具有大胆性和创新性。
引导性判决程序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适用。就具体内涵来讲,它是指欧洲人权法院对于源自同一国家的同一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systemic violations)引起的案件进行集中处理,不再对这些案件各自作出独立的判决,而是在认定被告国国内存在某一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上,向被告国政府发布指令,要求被告国在国内层面通过采取一般措施( general measures) 对其司法或行政上的缺陷进行修正,从根源上杜绝对类似的权利的系统侵害,并要求被告国对所有受害者进行赔偿。[10]39-42适用引导性判决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确认国内立法或者行政实践存在体制性问题;第二,这种体制性问题能够引发后续大量有依据的申诉;第三,认识到一般性措施是必要的,并且为修复体制性问题所采取的一般性措施的形式提出建议,具体分析引导性判决;第四,中止来源于同一体制性问题的其他未决的个人申诉;第五,法院以判决执行的方式来加强被告国国内采取的一般性措施义务。[11]69-75
(二)引导性判决的特点及理论溯源
与欧洲人权法院做出的一般判决效力相比,引导性判决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引导性判决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源自同一国家的案件,并且这些案件是由国内存在的某一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导致的。 第二,若适用引导性判决程序,法院并不对案件作出直接判决,只是规定被告国应采取一般措施(general measures),从国内层面对受害人的权利进行救济。第三,在适用引导性判决程序时,法院会暂时中止受理(adjournment)的其他所有源自同一国的相似案件,在作出判决之后将这些相似案件送回国内。引导性判决程序是法院从改革判决效力角度做出改革的最鲜明例子,它涉及到一个转变,即从宣告式判决到指导性判决的转变,[12]打破了针对具体案件作出具体判决的裁决思路,这也是欧洲人权法院应对重复性案件的一大创新。总而言之,这类判决超出了具体特定案件的是非真相,而是由法院引导国家如何去消除体制性问题,从而减轻案件重复导致的法院案件负荷量沉重的状况。
引导性判决程序的创立在理论溯源上体现了辅助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辅助性原则是欧洲人权法院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辅助性原则,人权的立法及其实施都是由国内政府来决定的,只有当国内政府不能发挥作用时,才需要动用国际权力来监督。可以这么认为,虽然国际人权法建立了普遍标准并且创立了监督机制,但它是作为国内人权法的辅助机制来运行的。欧洲人权法院作为区域人权保护的典范,一直被认为具有辅助性质的区域人权保护的机制。实际上,通过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实践可以看出,法院从不表达被诉的立法机关规制某一特定领域的措施的恰当性,法院的任务被限定在只是裁决立法机关采取的措施及其产生效果是否与公约相符。在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中,国内法官是“第一线”的法官,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机制是辅助于成员国国内法官的。[13]49-71引导性判决程序不作出具体裁决,而仅仅作出一个引导性的判决,依靠国内政府采取一般性措施救济。这体现了人权保护的权力由欧洲人权保护机制向国内政府的倾斜,积极发挥国内政府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也正是体现了欧洲人权法院辅助性原则的精神。
(三)引导性判决的实践及影响评析
1.布洛诺斯基诉波兰案(Broniowski v. Poland)
2004年,欧洲人权法院在布洛诺斯基诉波兰案(Broniowski v. Poland)的判决中首次适用了引导性判决。本案是一个有关二战前波兰东部省份(也被称为“布格河以外的领土”)财产损害赔偿的案件。具体案情为,由于波兰领土的变化,该地区被纳入苏联。从而有超过100万的人不得不离开这一地区。尽管许多遣返者在波兰西部获得了土地,但仍有接近8万人没有获得赔偿。1946年以来波兰立法就已规定,遣返者有权获得因放弃原有财产造成的损失赔偿。然而,在以后的50年中,波兰有关赔偿行为的几部立法都已相继无效。对此,有关“布格河索赔”的问题,国家给予了一种新的权利支持,波兰立法机关和宪法法院称之为“信贷权”(right to credit)。这种“信贷权”具有特殊性质,它独立受宪法保障,并且允许遣返者收购国有财产。然而,实践中,由于波兰当局不愿采取有效、必要的行动,导致只有很少的几个“布格河索赔”问题在“信贷权”体制系统内获得赔偿。1996年,第一个“布格河索赔”请求被诉到欧洲人权法院。申请者声称“信贷权”制度已经证明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价值,因为大部分的国有财产都基本在竞标范围之外。2004年,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赔偿原告损失。在判决执行中,法院发现,原告权利的违反源于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内立法和实践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实现“布格河索赔”的“信贷权”问题。对此法院提出:被诉国家应当采取适当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来对其余的“布格河索赔者”提供同等的保护,欧洲人权法院引导性判决从此创立。在“布格河索赔”问题上的请求者不会只是一个,如果众多的请求者均陆续就索赔问题诉至于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件负荷会明显增多,加剧积案问题,如果众多的案件在法院积压未决进而会直接影响到欧洲人权保障机制的效用。应当看到,引导性判决的创设初衷是很明确的,减少因一国体制性问题引发的案件重复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尽管引导性判决效力改革并没有纳入《欧洲人权公约第14号议定书》,但从2004年至今,欧洲人权法院共做出了6项引导性判决。2006 年该种判决适用于修顿·查普斯卡诉波兰案( Hutten -Czapska v.Po-land) 中,2009年,法院又作出了另外四项引导性判决:布尔多夫诉俄罗斯案( Burdov ( No.2) v. Russia) 、奥拉鲁和其他人诉摩尔多瓦案 ( Olaru and Others v. Moldova)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伊万诺夫诉乌克兰案 ( Yuriy Nikolayevich Ivanov v. Ukraine) 和舒利亚吉奇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案( Suljagic v. Bosnia and Herzegovina)。上述这些案例可以看做是对引导性判决的适用具有典型示范性和指导性的先行判例,也是理解引导性判决最为重要的参考。之后,2011年,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有关引导性判决程序的第61号法院规则,[14]这为欧洲人权法院以后引导性判决的做出提供了规则指导,是引导性判决在欧洲人权法院的新发展。
2.引导性判决的影响评析
引导性判决使得法院只需判断缔约国是否存在潜在的体制性问题,并协助缔约国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督促缔约国积极建立有效的补救措施。这是一种从判决效力出发寻求的改革新思路,即不再对所有案件直接判决,而是引导国家消除自身存在的体制问题,从而实现案件的集中处理。从积极影响来看,它一方面避免了重复性案件被诉至法院,减轻了案件的积压状况,提高了公约机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由被告国消除体制性问题,采取一般性措施进行救济有利于提高国内人权保护的水平,更符合欧洲人权机制辅助性原则的精神的。
然而,如前所述,引导性判决的特点之一是法院会中止受理(adjournment)其他所有源自于同一国的相似案件。一方面,中止受理削弱了个人基于《公约》第三十四条所享有的个人申诉权利。另一方面,法院的中止受理还会造成迟到的正义非正义。[8]1231一旦申请人所在的缔约国基于引导性判决采取了补救措施,这些中止的申诉案件最终将会被驳回。尽管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充分,欧洲人权法院会重启中止案件,但是引导性判决并不能反应违反公约的所有事实及法律问题。[15]125-159可以看出,对于引导性判决同样存在质疑与担忧的声音。欧洲人权法院为了保证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的有效性,减少法院积案,采取引导性判决程序,但引导性判决程序却减少了成员国国民的个人申诉权,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法院在采取引导性性判决程序时,如何在保证个人申诉权和保障机制有效性之间取得平衡。引导性判决自创立以来法院仅适用过6次,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其利弊衡量尚有待时间的考验。
三、非当事国判决效力改革(res interpretata effect)
(一)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内涵及特点
除了针对重复性案件的引导性判决,法院在改革实践中,还从判决效力的角度提出了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理论。非当事国判决效力(res interpretata effect)是与《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一般判决效力(res judicata effect)相搭配的一对概念。[16]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英文表述为res interpretata,法语表述为:l‘autorité de la chose interprétée,直译为“权威的解释”,采用直译的方法并不能反映此类判决效力自身特点。非当事国判决效力最大的特点在于针对诉讼当事国做出,但对其他非诉讼当事国也具有约束力,由此本文将其译为“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突出此类判决的特殊之处。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一般判决效力仅对参与诉讼程序的当事国双方有约束力,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特点在于强调欧洲人权法院对诉讼程序当事国所做出的判决对其他非诉讼程序当事国的影响。也就是说,法院做出的判决或者决定对于其他非当事国也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它能够促使其他非当事国主动去改变他们的国内法律及其实践,从而避免在以后在相同或者相似的案诉中被判决违反人权。[1]223-262由此可以看出,欧洲人权法院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提出本身也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与突破,打破了一般国际法判决仅约束诉讼程序当事国的传统。就目前来讲,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层面都鲜有对诉讼程序判决效力的此种思路与突破。因此,有必要深入揭示这一理论背后的创立原因及理论支撑,分析该理论得到的反响与回应,思考其中的改革理念对国际社会以及国际法的启示意义。
(二)非当事国判决效力创立原因及法律渊源
1.非当事国判决效力创立原因
关于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创立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关于非婚生子女平等继承权问题,马祖雷克诉法国案中(Mazurek v. France),法国花了20年的时间来等待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事实上,早在1979年著名的马克斯诉比利时案中(Marckx v. Belgium),法院就已公布对非婚生子女继承权问题的判决。类似地,早在1981年达吉恩诉英国案(Dudgeon v. United Kingdom) 中,同性恋的非歧视化就已经成为公约的一项准则。然而,塞浦路斯并没有对此作出适当的法律变化,直到1983年才在Modinos v. Cyprus案 中被认定为违反了公约。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法院之前就某一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过裁决,之后可能会出现其他国家会就同一问题重复诉至法院的情形。而如果法院已作出的裁决对未参加程序的非当事国也产生法律效力,是不是之后就会减少或者不再出现法院早已就同类问题做出过裁决的类似申诉重复诉至法院,从而也缓解法院的积案压力?而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理论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创立的。
2.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效力渊源
对于非当事国判决效力,公约第四十六条以及其他条款均未对其做出具体规定。然而,只有找到一定的效力渊源,此种判决效力才会有说服力,才可能被成员国所接受。法院在改革思路上是从条约法的角度为其适用找到了合理依据,并且最终定位在了公约的第一条和第十九条,即从公约一般性的条款找到了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法律渊源。[1]223-262
公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应当给予在它们管辖之下的每个人获得本公约第一章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本条可以被解释为公共国际法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员国声明要接受欧洲人权公约的约束,应当善意的遵守国际性公约,这项义务来自于《维也纳公约》的第二十六条。根据《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六条规定:“ 条约必须遵守——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在公共国际法下,善意遵守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禁止采取与国际法义务相违背的措施;二是国家有义务执行来自于依据国际性条约对申诉做出的判决或决定。此外,根据《维也纳条约》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此项规则不妨碍第四十六条”。成员国有义务解释国内法使得其与国际性条约相符合,有义务执行基于国际条约适用而做出的判决或者决定。[17]对于其他非诉讼程序当事国而言,非当事国判决效力虽然不是针对其做出的,但却是欧洲人权法院基于条约适用做出的判决,其他非当事国作为欧洲人权公约的成员国,有义务承担善意遵守国际公约所产生公约义务。
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为了保证各缔约国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应当设立欧洲人权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由此看出,欧洲人权法院作为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的司法机构,是为了保障公约遵守而设立的,作为司法机构,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实践中具有解释公约及其特定条款的义务。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理论立足点在于,如果成员国受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约束,那么他们也受到公约实质性条款(material provisions)的约束,因为这些实质性条款是由作为公约的唯一有权解释者欧洲人权法院解释的。具体而言,对于非当事国判决效力,虽然它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对成员国的效力,但是它属于公约的实质性条款(material provisions)的内容,根据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成员国也应受到实质性条款的规定,法院判决可以对为非参与诉讼程序的成员国有约束力。时任欧洲人权法院院长的Jean-Paul Costa也认为,非当事国判决效力是从公约解释的角度给予法院判决创设新的约束力。这种公约解释的约束力超出了既判力的范围,它是条约法进步的最新体现。[1] 223-262应当认为,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提出具有合理的法律基础,即条约法基础,通过条约解释和公约约束力的扩大解释来引导成员国(不论是案件当事国还是非当事国)均对欧洲人权法院做出的判决采取执行措施。非当事国判决效力从实质上看是法院判决约束力范围的扩展,从改革路径上看,是试图通过扩大法院判决约束力范围,增加判决的影响力,使其他非当事国在没有成为欧洲人权法院的被告国之前就积极采取国内措施,减少未来成为被告国的机会,从而减轻欧洲人权法院积案压力。
(三)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发展与适用
1.非当事国判决效力在软法文件中的体现
非当事国判决效力并没有在公约中明确提及,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的一般判决效力仅仅约束诉讼程序当事国。非当事国判决的效力,或者说有关公约解释的判例法效力问题规定在欧洲人权法院软法性文件中。比如欧洲部长理事会的建议中;2006年欧洲理事会NO1516号有关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执行的议会大会的决议中(PACE);2009年12月为准备因特拉肯会议而召开的有关法律事务和人权的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中,非当事国判决效力问题被重点强调。
2010年《因特拉肯宣言》,对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理论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发展。这是首次非当事国判决效力在此种高级别的欧洲理事会政治性文件中被定义出来,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成员国的义务。在本宣言中,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理论被称为辅助性原则的一个方面,成员国和欧洲理事会对公约机制的有效运转有着共同的责任。并且,在《因特拉肯宣言》的行动计划中,呼吁个成员国遵守如下内容:考虑法院发展中的判例法,从判决的结果中发现其他国家对于条约义务的违反,以及考虑在自身的法律系统中也可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18]2012年,布莱顿峰会上通过了《布莱顿宣言》,宣言中强调,成员国的主要任务是遵守条约义务,它重复了有关对各成员国判决执行的主要指示。在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理论的背景下,宣言声明了公约下法院做出的判例法的作用。特别是,它鼓励成员国采取具体措施来支持法院的判决:考虑到公约的相关原则;考虑法院做出判决的判例法;使得当事人在国内司法程序上没有不必要的障碍,使国内法院考虑公约和法院管辖的相关条款。[19]由此可以看出,非当事国判决效力问题虽然在公约中没有规定,但是却广泛存在于欧洲人权法院软法性文件中。非当事国判决效力存在于相关的软法文件中,没有强制执行力,更多是缔约国自愿接受。
2.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实践适用情况
非当事国判决的效力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被动效力和主动效力。其中,被动效力是指,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被用作人权保护的普遍标准或者用来检验立法和行政实践或者在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的裁决中适用。在欧洲,这种被动适用欧洲人权法院裁决的情况尤其是法院非常普遍。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对被动效力的贯彻会相对少些。主动效力对于国家的要求更高,它需要国家积极了解法院的最新判决,此后对本国法律、实践以及现存先例做出充分改变。它需要国家对待非当事国判决以对待针对本国判决的相类似的方式。如果一国确定法院对非当事国做出的判决,本国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着相同的问题,该国应当执行法院对其他国家做出的判决。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这需要改变立法,有时甚至包括修改宪法。[1]非当事国判决主动效力的实施在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中很少,仅仅只有少数成员国表现了积极努力。
但尽管如此,近几年,还是有成员国根据法院对第三国的判决来修改本国国内立法及实践的例子。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2005年 Hirst v. United Kingdom 案判决作出后,许多国家对于囚犯投票权问题做出改革。比如,塞浦路斯和爱尔兰都修改了其选举法。相当有趣的是,那时英国作为当事国还没有执行法院的判决。此外,在Goodwin v. United Kingdom 案后,荷兰对保护新闻来源的途径做出了修改;在Burghartz v. Switzerland 案后,法国于2002年通过一项有关姓名归属的平等规则;在De Cubber v. Belgium 案后,瑞士联邦法院和西班牙宪法法院的审判规程的改变。关于非当事国判决的效力实施,不得不提的是波兰,在Copland v. United Kingdom 案后,波兰就发起了有关员工在工作场所隐私权规定的讨论。在Kiss v. Hungary 案判决公布两周后,波兰监察专员就要求司法部长声明波兰宪法和公约的一致性。在Uzun v. Germany 案后,展开了有关波兰是否应当详细规范使用GPS系统监视嫌疑犯问题的讨论。通过上述案件可以看出,在欧洲还是存在一些国家在积极配合实施法院非当事国判决的主动效力。
四、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效力改革理念及启示
《欧洲人权公约》是一个“活文件”,欧洲人权法院处于不断变革之中。可以说,从1998年欧洲人权法院成为独立的常设司法机构开始,法院就在不断尝试新的改革。而欧洲人权法院引导性判决以及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改革,反应了最近欧洲人权法院在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对其改革思路进一步剖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更深层次的改革理念及启示。
(一)重视发挥法院自身在判决执行中的作用
公约第四十六条规定了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是法院判决执行的监督机构,法院判决的执行有赖于部长委员会的监督。但是,欧洲人权保障机制缺少强有力的执行监督机制,判决的执行主要是来自于各成员国的配合,部长委员会监督的有效性远远不够。面对此种严重的积案问题和判决执行难题,法院不再仅仅依靠部长委员会的监督执行,而是选择更加重视发挥自身在判决执行中的作用。以往法院负责作出判决,部长委员会负责监督判决的执行。引导性判决和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改革展现了法院在判决执行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法院不再只是针对具体案件做出针对性判决,然后将判决的执行交给部长委员会,而是选择从法院判决产生的源头出发,增强、扩展法院判决自身的约束力,让更多的非当事国也积极遵守判决,从而增加法院判决的执行力和影响力。欧洲人权法院的此种改革思路有种曲线救国的意思,如果直接增强一般判决效力的成效及进度均有限,何不增强判决对非当事国的效力,总是有一些成员国对法院改革持积极态度。当然,部长委员会在判决执行中仍然发挥主要作用,法院的司法实践仅仅是一个补充作用。总之,非当事国判决效力的改革具有创新性与大胆性,这种重视发挥法院自身在判决执行的思路,实际上是对执行监督角色的一种提前,发挥法院判例法的作用,促进法院判决的执行。
(二)从条约法角度为改革寻求合理依据
任何一项改革的提出必须具有合理的依据和支撑,欧洲人权法院的引导性判决以及非当事国判决从条约法的角度为改革找到了合理依据。正如前文所述,时任欧洲人权法院院长的Jean-Paul Costa认为,非当事国判决效力是从公约解释的角度给予法院判决的约束力。对于非当事国判决,虽然条约没有明文规定其效力,但是它属于公约的实质性条款(material provisions)的内容,而这些实质性条款是欧洲人权法院解释公约的结果。应当认为,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对公约的解释,找到了公约中暗含的实质性条款,给非当事国判决效力找到了合理依据。当然这种条约法的思路,在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效力改革中并非初次适用,欧洲人权法院在许多改革举措中均体现了条约法解释的魅力。比如,欧洲人权公约没有明文规定环境权,基于条约解释给予环境权间接保护;欧洲人权法院国家裁量余地原则并非为欧洲人权公约所明文规定,基于条约解释在法院实务中逐步创设。当前,许多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都日益关注条约法解释问题,欧洲人权法院这样一种基于条约法解释所支撑改革或者说创设新制度的改革理念和方法,相信会对国际社会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重视发挥国内人权保护机制的作用
从引导性判决来看,法院对源自同一国家同一体制性问题引发的案件不再各自作出独立判决,而是进行集中处理,在认定被告国国内存在某一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的基础上,向被告国政府发布指令,要求被告国在国内层面通过采取一般措施(general measures)对其司法或行政上的缺陷进行修正。法院作出的只是一个具有引导性的判决,最终需要国内采取具体措施进行救济,从而更多发挥国内人权保护的作用。就非当事国判决效力改革而言,不论其主动效力还是被动效力均强调国内层面为执行法院判决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这两类判决改革背后隐含的正是欧洲人权法院对国内人权保护机制的重视以及对欧盟法辅助性原则的发挥,这一理念也反应了欧洲人权法院近年来最新改革发展趋势。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国家裁量余地原则(margin of appreciation)近年来也颇受重视。二战后,人权保护进入国际领域,欧洲建立最早的区域人权保护机制,国际力量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被逐步重视并且日益提升。而近年来,欧洲人权法院的改革举措,正体现着力量的转移,人权保护由主要依靠国际层面到依靠国内层面的转移,从而更多依靠国内力量具体落实人权保护的实效。
[1] Bodnar, Adam. “Res Interpretata: Legal Effect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Judgments for other States Than Those Which Were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Human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IUS Gentium 30 (2014).
[2] http://www.assembly.coe.int/CommitteeDocs/2013/ajdoc142013.pdf, 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8日。
[3] Interlaken Declaration, 19 February 2010, at p. 2.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2010_Interlaken_FinalDeclaration_ENG.pdf, 访问日期:2016年4月3日。
[4] Brighton Declaration, 20 April 2012, at para. 29,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2012_Brighton_FinalDeclaration_ENG.pdf, 访问日期:2016年4月3日。
[5] Glas, Lize R.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Neth. Q. Hum. Rts. 30 (2012).
[6] Elizabeth Mottershaw,Rachel Murray. “ National responses to human rights judgments: the need for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6 (2012).
[7] Reply to Committee of Ministers request for comments on the CDDH Report on Execution,9 May 2014.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2014_Comments_on_CDDH_report_on_execution.pdf, 访问日期:2016年4月3日。
[8] Fyrnys, Markus.“Expanding Competences by Judicial Lawmaking: The Pilot Judgment Procedur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German LJ 12 (2011).
[9] Sainati, Tatiana. “Human Rights Class Actions: Rethinking the Pilot-Judgment Procedure at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rv. Int'l LJ 56 (2015).
[10] 刘丽.欧洲人权法院权利救济新举措——引导性判决程序评析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
[11] Wildhaber, Luziu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verwhelmed by Applications: Problems and Possible Solutions[M].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9.
[12]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Speech_20130920_Spielmann_Gottingen_ENG.pdf, 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8日。
[13] lugato, monica, "state-sponsored religious displays in the us and europe: 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between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subsidiarity." j. cath. leg. stud, no 52, (2013).
[14] Rules 61 of the rules of court ,Inserted by the Court on 21 February2011.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Rule_61_ENG.pdf, 访问日期:2016年3月20日。
[15] Helfer, Laurence R. “Redesigning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mbeddedness as a Deep Structural Principle of the European Human Rights Regim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1 (2008).
[16] Dean Spielmann.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ffects and Implementation.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Speech_20130920_Spielmann_Gottingen_ENG.pdf, 访问日期:2016年4月3日。
[17]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f 13 July 1954 in case “Effect of Awards ofCompensation Made by the United Nations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available at: 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p1=3&p2=4&code=unac&case=21&k=d2,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8日。
[18] Point B (c)——Interlaken Declaration.Action Plan,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2010_Interlaken_FinalDeclaration_ENG.pdf, 访问日期:2016年4月3日。
[19] Brighton Declaration, point 9 (c) (iv). http://www.echr.coe.int/Documents/2012_Brighton_FinalDeclaration_ENG.pdf,访问日期:2016年4月3日。
责任编辑:林 衍
Study on the Reform of Judgment Effects in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Liu Xiao
(School of Law,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rticle 46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stipulates the Judgment effects in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which is only confined to the proceeding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With the burden of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ourt tries to conduct re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gment effects. Pilot Judgment reform breaks the tradition that specific case has specific judgment; non-participating country judgment reform breaks the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law that the general judgment only binds litigation parties. It is a great innovation and reflects that the court constantly pays attention to its own role in the enforcement rather than just relies on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supervision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domestic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As a result,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ransfers from international level to domestic level.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pilot judgments; non-member country judgment
2016-04-27
刘晓(1989-),女,山东临沂人,南开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经济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研究。
DF983
A
1009-3745(2016)03-004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