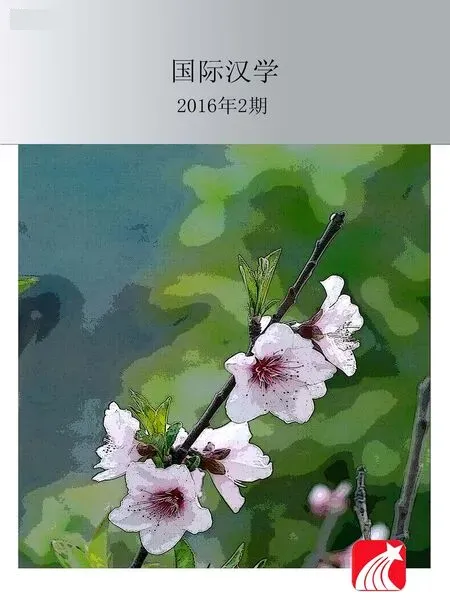身体、想象与催眠—毕来德与庄子的思想对话*
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先生重新诠释《庄子》经典文本,著有两本法文著作《庄子四讲》(2002)、《庄子研究》(2004),在国际哲学界和汉学界均引起反响,也由此逐渐兴起“新法语庄子研究圈”。在其著作《庄子四讲》里,他开篇明义地指出,他所进行的庄子研究从“原则上的平等关系”出发,实际上意味着展开与庄子所论及的“具体的经验,或是共通的经验”的对话,并体现出作为诠释者的“我的经验”与庄子关怀的经验的“交会”或者说“印证”之处。①Jean François Billeter, Leçons sur Tchouang-Tseu. Paris: Editions Allia, 2002, pp.9-12. 参见该书中文版:毕来德著,宋刚译:《庄子四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毕来德对《庄子》的重新诠释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以现象学为方法指导的日内瓦学派(Ecole de Genève)的意识批评方法,②参见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即强调诠释者的批评意识与文本的经验相呼应、相体认,在“同感”的基础之上揭示出作者经验的独特性;可以说,毕来德正是在对《庄子》文本的“整体性”的关注中勾勒出其中呈现的经验的“力量的线条”(ligne de force,在此借鉴让·鲁塞[Jean Rousset]的术语),由此出发重构《庄子》文本的精神内涵。需要提到,在毕来德先生的学术培养与背景中,现象学思想的影响无法忽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融合现象学原则的日内瓦学派的精神氛围中,他传承这种批评方法,可谓也是在中国研究中寻找新的突破点的“日内瓦学派”新一代学者。当然,毕来德先生更超越日内瓦学派的意识批评方法所强调的“同感”的层面,以其独立的、深邃的哲学思考与《庄子》文本相回应,在文本批评与诠释的基础上提出卓有创见的见解;透过这些思考的补充与发展,他也深刻反思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由中国思想的深度研究出发汇合法国当代哲学中针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关键性的“突围”,以其《庄子》的诠释工作融入法文哲学范式的革新运动的思潮之中。
一、身体图式与“自身的身体”的意义探寻
在围绕《庄子》描述的“经验”的重新探讨中,毕来德将“亲身经验”放置在首要的地位,他将此定位为庄子的首要哲学关注,正是在 “亲身”(Corps Propre,即“自身的身体”,)经验的视阈中,毕来德重新诠释庄子所描述的“无限亲近”与“几乎当下”的现象等问题。庄子对“道物融通”的体悟关联到他的身心观,即身体作为身/心、形/神、现象/本质、体/用不二的交融体。毕来德如此归结:“提到身体,我们所指的,不是解剖学上的身体或作为客体的身体,而是自身的身体。”他将“身体”界定为“在我们身上的各种已知的与未知的力量与才能的整体”。①Jean François Billeter, Etudes sur Tchouang-Tseu. Paris: Editions Allia, 2004, p.248.在毕来德对庄子身体观的探讨中,“自身身体”指的不是纯粹物理性的身体,也不是意识的身体,而是身心交融的身体图式。在此,“亲身”“自身身体”的概念使用靠拢了在知觉现象学中对于“自身的身体”与“作为客体的身体”的区分。在《中国书法艺术》(2005)中,毕来德也提到他对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与米歇尔·昂希(Michel Henry)的阅读,当涉及“身与心、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区别”时,他明确强调在现象学中的重要区分:②Jean François Billete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Genève: Skira, [1989]2005, p.136.“自身的身体,指的是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在场,以永恒的方式感受到的在场;而“客体的身体”指的是他者的身体,也就是我们从外部感知为客体的身体,并对之形成视觉的再现。”
在推进“对存在的基本元素”的考察中,毕来德更进一步将自身身体的知觉放在存在经验的首要地位,他还指出:“我们还需承认,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将对我们的存在毫无感觉,也对我们自身毫无意识,而‘我’‘自我’这些词也将失去了意义。”③Ibid..在这一点上,毕来德尤其汇拢身体现象学的范式,即从笛卡尔的“作为意识的我思”迈越到“作为身体性存在的我思”,突破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纯粹意识、先验主体的局限性,引入“身体—主体”的图式作为知觉活动与世界在场的联结点。④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取自康德的“图式”的提法,也同样具有原本所指的“在知性与感性之间的一种沟通协调功能”,但并不是在康德意义上“为了解决感性和知性之间的机械割裂而事后引进的一个补救性概念”,而是“知性与感性的原初母体”,属于现代以来将康德的图式更朝向感性活动而非解为意识活动的哲学改造的倾向之一。关于两个概念的区分,请参见张尧均:《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第27页。此外,“身体图式”也借鉴了神经科学里的术语,即鲍聂尔(P. Bonnier)在1893年提出用“图式”表示与身体意识有关的“空间性”。只有理解这个概念的鲜活悖论性,方才有可能接通毕来德以庄子研究为途径所传达的身体思想的丰富性。
毕来德以书法为例,阐明在中国传统艺术体验中有“一种直觉”,这“似乎处在中国思想的核心,将现实构想为一种不断的涌现,正如从潜在到实在的过渡,正如一系列的形象或具象构造以不间断的方式,从一个看不见的、无处定位的源泉,从现实内部的源泉涌现出来”。⑤Billete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p.246.这段表述也对应唐代画家张璪(约735—785)提出的艺术创作法则“内师心源,外师造化”。随后,毕来德用作为整体、动态的身体观念归结中国思想,而他认为,中国人“将自身身体作为全部现实的范式之根本”,心、神并置、包容、整合在“身体图式”之中。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身体图景“充满空间,从内部不断更新”,既是自身身体的图景,又与外部空间互相蕴涵、呼应,这是“身体—客体”模式出现之前的“身体—主体”的模式,也正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之所在。由此出发,毕来德彻底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身心、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他也认为这种差别会投射在书写活动里,即中国书法是“从自身身体的自然范式出发发展出的一种完整的文明”;而西方字母文字的抽象符号及其组合旨在打断这种自然范式并朝向“让自身身体顺应抽象思维”的重构。⑥Ibid., p.248.
毕来德指出,知觉现象学在总体上具有过于静态的局限性,在对庄子身体观的考察中,他尤其着重关注自身身体的动态活动,并将“外在行动”(action)与“内在活动”(activité)做了三个层次的明确区分。⑦Ibid., p.269. 1.内在的活动(指我们自身的活动)在向外呈现出来之前是内在的,而行动对我们来说总是向外的;2.内在的活动是持久连续的,而外在的行动只是断续的;3.内在的活动没有外在于其自身的目的,而外在的行动必然有一种外在的目的。他认为内在的活动比外在的行为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并归纳“中国人的视角”旨在将自身内在的活动看作首要的现象而将外在的行动看作次要的现象,①Ibid..但显然对他而言,内在的活动不同于意识、意向性。那么,如何解决这种悖论呢?毕来德的秘诀之一在于引入“活动机制”(régime d’activité)的提法,②参见《庄子四讲》第9页译注1,宋刚先生指出,“‘机制’转译法语régime一词。该词的一个含义,可指一台发动机的转速,因转速的高低产生发动机功率的强弱。笔者借用于此,比喻我们主体的不同活动方式,作为阐释庄子思想的一个关键词,因以‘机制’译之”;第33页,毕来德先生说明,动能机制“是借用引擎机不同转速所产生的不同功率来比喻我们主体的不同的活动方式”。从而解决问题的纠结,他划分出不同活动机制的层次,认为机制之间的过渡与转化对应庄子对“意识的不连续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诸种悖论”的关注,以此奠定为一种“主体性的基础物理学”的学问的基础。③《庄子四讲》,第51页。在这种视野里,毕来德将依从意向性的行动归结为“人的机制”,而将依循事物本性、机体主体性的活动归结为“天的机制”。因而,在庄子思想内在的“天”与“人”的范式对立与转化中化解这个难题,而修养工夫则被归结为引导人由“人的机制向天的机制上升”④同上,第44页。的渐进过程。
关于“自身身体”图式的整体性,毕来德做出如下陈述:“要进入庄子的思想,必须先把身体构想为我们所有的已知和未知的官能与潜力共同组成的集合,也就是说,把它看作是一种没有确凿可辨的边界的世界,而意识在其中时而消失,时而依据不同的活动机制,在不同的程度上解脱而来。”⑤同上,第107页。
意识的虚位,意味着让意识活动妨碍行动有效性、造成阻隔的方面消失,从而更充分地进入体现官能感知与意识合为浑然整体的身体图式,促进身体行动的自由,保证活动机制之间的自如转换与变化过程的自然发生。在这种整体性关照的视野之中,毕来德指出在 “庖丁解牛”(《内篇·养生主》)⑥原文如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的范例中蕴涵的“技进乎道”的认知价值:“[庖丁]他不局限在用灵巧的技术解牛,而在于他在行业中实现了一种活动的高级形式,并由此深入到了事物的运作之中。宗旨在于通过这个行业,找到内在活动的高级形式,并由此进入‘事物的运作’之中。从一种有用的活动,发展为一种艺术,从艺术而成之为认知的方式。”⑦Billete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pp. 270-272.
毕来德将庖丁解牛的“神会”境界作为追求完美的“内在活动”的范例,试图理解用不同活动机制的递进来诠释“神”从内在活动到外在行动的转化力以及深入“事物的运作之中”的穿透力。“‘神’不是外在于庖丁的某种力量,也不是他身上行动的某个殊异力量。这个‘神’只能是行动者本身那种完全整合的动能状态。”⑧《庄子四讲》,第9页。这也对应原文中体现出的动能状态:“官知止而神欲行”,将限于视觉感官层面的孤立感知悬隔,“从手放意,无心而得,谓之神欲”,⑨参见向秀《庄子注》,收录《庄子集释》上,第三版,(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6页。即处在自发状态的“神”化成在骨节、经络的空隙处自由游走(“行”)的穿透性力量。“神”在法文语境中的翻译,毕来德先生在此将这一绝妙的现象归纳为“自发行动的力量”(force agissante),①在《中国书写艺术》中,毕来德也借鉴《黄帝内经》提出:“不是身体赋予精神的救赎,而是精神赋予身体的救赎。身体的拯救得到‘自发行动的力量’(force agissante,jingshen)的保证,即出于在更高级层面上整合的一种自身活动的效果[……]。”他还明确地说明,在翻译选择的原则出于对“精神”与“身体”的非二元论的理解,强调精神的物理性、身体性与能动性:“精神(jingshen)这个词通常翻译为esprit,但我们回避这种翻译来提示一种与身体相异的原则,但它指的是一种有效的力量,仅仅来自自身活动的良好组织。”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p.172.消解了在法文翻译中运用“精神”(l’esprit)、②这 种译法 是 较 常 采用的。 参 见 L’oeuvre complète de Tchouang-tseu, traduction, préface et notes de Liou Kia-hway, in «Connaissance de l’Orient », collection UNESCO d’oeuvres représentatives. Paris: Gallimard, 1969 ; Ryckmans, Shitao, Les propos sur la peinture du moine Citrouille-amère. Hermann, Editeur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1984, pp.113-114. 毕来德本人阐明根据不同语境选择“精神”(esprit)或“自发行动的力量”(force agissante)来侈译《庄子》文本中的“神”。参见《庄子四讲》,第36页。“精神性”(le spirituel)、③François Jullien, Nourrir sa vie, à l’écart du bonheur. Paris: Seuil, 2005, p.28.“精神向度”(la dimension d’esprit)、④Ibid., p.78.“精神能量”(énergie spirituelle)⑤Romain Grazianni, Fictions philosophiques du Tchouang-tseu. Paris: Gallimard, 2006, p.73.等词汇所会触及的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交织的身心二元论的诸种障碍,从而在身体现象学的意义上将庄子的哲学理念提纯、提炼为以“身体—主体”为脉络的思想。
在吸收与容纳当代法国哲学的一些表述方式的基础上,毕来德将“庖丁解牛”解读为“对于客体的取消与对主体的取消,同时进行”的“协同” (synergie)过程。其一,他将学习解牛的初期阶段描述为主客尚且处在绝对对立的二分阶段,即人将物视作对主体的欲望构成障碍的整块的“客体”,与自我对立;其二,伴随技术的精进,主客绝对对立的状态发生转变,客体在主体的目光中分解为“部分”,这也要求意识给予更多的专注,即以科学的、分析的、精确解剖的方式对待对象;其三,“不以目视,而以神遇”,在练习19年技艺之后,庖丁在解牛活动中进入意识的最大程度的专注,却也同时达到悖论式的意识消解,即进入主客两忘的状态,不再把物当作客体加以剖解、分析,超出感官感知的表面化层次,“而以神遇”,通达“天”的机制即自然、自发的状态,乃至与手中的刀刃(工具的身体性)合二为一,而以“无厚入中间”,以“游刃有余”的方式在牛体的间隙之中自如穿梭,穿透屏障。毕来德如此评述:“当完整的协同活动实现,内在的活动发生了转变,并过渡到一种高级的机制范围中。”以神遇之,即意味着把内在活动加以“协同”运作,超越主客二分的差别思维,同时遗忘、放下主体的意识,在完美的协同过程中,转化为具体的、切实的身体行动;这也配合技术层面的纯熟和精准的程度,不再需要意识多余的判断介入,从而以最少能量的消耗进行实践,并在游刃有余、驾驭自如的行动中促使能量在身体的内部环流。最终,“神”的活动指向养生的价值,而以身体作为认知世界的途径,以提高活动机制而达到修身养性的境界。在“以神遇之”的解牛过程中,人的身体内部的遮蔽打开,在穿越外物的屏障的同时,也实现内在的打通,这种由内向外又返归到内的修炼,实现外在行动(穿越屏障)的效能与内在养生的奇妙汇通。个体如此才有可能抵达焕发“效力与活力的源泉”遂达到“养生”的效果,并完成自由自如的外在行动,“神动而天随”(《外篇·在宥》)。
从“机制”(régime)到“效能”(efficacité,或译为“有效性”),毕来德先生巧妙地实现从自身身体知觉到关注世界的身体性、复归到修养自身身体的理论上的贯通,内化知觉现象学的视角,又在与《庄子》的对话中为现象学的身体观作了具体而微的跨文化的补充。毕来德采取的这种研究进路也凸显出在理论重构方面其独特的一致性。正因为着重突出《庄子》思想中的“身体性”的向度,毕来德的庄子研究进入从身体哲学到哲学肉身化的法国后现代思想的语境。在重新诠释《老子》的一篇文章里,毕来德也谈到,要理解道家的文本,应当从重视“客体—身体”优先性的西方传统中走出,面向中国思想中的“自身身体”范式的首要性。他指出:“自身的身体是我们与之持有直接的、连续的接触的唯一现实。它对我们来说是即刻的现实。”“感官并不是仅仅增加到传统的五官官能(视、听、触、味、闻)”,而是构成其共同的地基,并在其间构成巨大的转换性的功能。因而,毕来德甚至认为:“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的《知觉现象学》可以从中国的视角得以重写。”①Jean François Billeter, “Essai d’interprétation du Chapitre XV du Laozi,” Etudes asiatiques, N. 39/ 1-2, 1985, pp.7-44.他将转化的能量与行为的实现的根基奠定在身体的内部,不是将不同的感官官能分隔为单独体,而在知觉现象学的视野里领会为各个部分彼此相通、融合为一体的“自身身体”。而在毕来德对《庄子》文本研究的部分段落,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他所进行的对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加以“重写”的尝试,或者说我们尝试从知觉现象学的角度重读毕来德的《庄子四讲》的一些段落。
在《内篇·达生》中,庄子讲述了让孔子惊讶的一个男子在悬水30仞处游水的经验。孔子发问:“蹈水有道乎?”答:“亡,吾无道。吾始于故,长乎性,成乎命。”在《庄子四讲》中,毕来德指出,游水男子的动作完全是“自发的,无意的,不由他主体意识来支配”,也就是“相当于说我们通过长期练习而达到的那种自然的行动”。②《庄子四讲》,第22页。毕来德更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从一种机制到另一种机制、更高超的机制的穿越,以自然而然、必然的方式来行动,③《达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毕来德在诠释《庄子》的这段文字时,把“命”译为“必然”。他做了如下说明:“游水男子已经能够与激流漩涡完全融合,他的动作是完全自发的,无意的,不由他主体意识来支配,换句话说,对他来说是不是‘必然’的了。”《庄子四讲》,第22页。因而达到自由的境地。这也是在“轮扁斫轮”(《外篇·天道》)的经验中,“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以刻苦锻炼达到的行动之自然、熟能生巧的工作经验,这一类活动机制的获得都是基于身体知觉。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里也举过一个关于“乐器演奏家”的类似的例子论述来说明:“为什么习惯不寓于思想和客观身体中,而是寓于作为世界中介的身体中。”在梅洛·庞蒂意义上的“前反思、前对象、前概念”的身体观摆脱了西方传统意识哲学对于反思意识的依赖;而毕来德先生在法文语境中对《庄子》中的两则对话的诠释对应这种批判性的思考。
梅洛·庞蒂提问“作为身体图式的修正和重建的习惯的获得”与“身体作用”之间的关系:“如果习惯既不是一种知识,也不是一种自动性,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在习惯的获得中,是身体在‘理解’。[……] 恰恰是习惯的现象要求我们修改我们的‘理解’概念和我们的身体概念。理解,就是体验到我们指向的东西和呈现出的东西,意向和实现之间的一致,—身体则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④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91页。毕来德则认为,在庄子描述的“轮扁斫轮”的身体实践经验中,身体(“手”)对“数”(“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即“寸劲儿”在整体上的把握,是出自于“一种综合”,在其形成自然动作之前的深层基础上,“心将每一个尝试的成果记录下来,一点一点地从中抽离出有效的动作模式”。⑤《庄子四讲》,第14—15页。因而,这种综合工作与意识活动不可分,又在身体习惯的获得中自如呈现。这也可从梅洛·庞蒂“身体图式”概念呈现的知觉统一性的角度理解。刘国英先生将这种统一性诠释为“知行合一”的方式:
我的各个肢体和器官虽然分布在我的身体的不同部分,但身体图式提供了身体的感官和运动机能的统一性(l’unité sensorimotrice du corps),使它们能在前反思状态下就可以和谐地协同运行。[……]我们之能作出这些或多或少的、具不同程度的复杂性的知行合一式的动作,就是身体图式把身体各个器官统一协同运用的结果。这也在显示了肉身主体是一能动的主体。[……]我们理解到一个统一的知觉意义(unitary perceptual meaning)如何可能:它是我们的肉身主体的各个器官与肢体之整体组织与协调之下,给予我们一个统一的知觉对象的结果。在这里,身体作为一个能动的运动主体起着统一意义之构成的关键作用。①参见刘国英:《梅洛·庞蒂的肉身主体现象学及其哲学意涵》,载刘国英、张灿辉编《修远之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六十周年系庆论文集·同寅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9,第510—513页。另亦可参见刘国英:《视见之疯狂—梅洛·庞蒂哲学中画家作为现象学家》,载孙周兴、高士明编《视觉的思想—“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第32页。“[……]我们的身体拥有一套身体图像(schéma corporels),它们是我们从事各类运动时知行合一的来源。身体图像在我们的视觉、触觉与听觉经验之间建立一对等和互通的系统;由于我们的知觉经验中视觉、触觉与听觉元素有一对等系统,这就确保了我们的知觉世界在前谓语判断层面(pre-predicative level)已有统一性。这同一的知觉世界成为各类型的表达行动的共同参照项,无论这些表达行动是最基本和最简单的身体动作,抑或是最复杂和细致的智性示意活动。”
杨大春先生则评述如下:“身体具有某种整体图式,它指向事物的整体,但却是通过部分来实现的,这就是透视与各个视角的关系。身体所实现的整体不是被理智占有的观念统一体,而是朝向无限视角开放的整体。”②参见杨大春:《杨大春讲梅洛·庞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01页。毕来德在《中国书法艺术》中则进一步提出,通过自身身体、身体经验的投射与空间性,从内部认识中国书法艺术。他写道:“正是通过自身的身体,内部与外部相互沟通,我们与世界产生了所有的交流。它是全部空间性的源泉,也是空间的全部布局[……]。”③Billete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p.136.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梅洛·庞蒂对“身体的空间性”的描述,即“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身体图式”因而是在身体空间与外部空间相互蕴涵的“双重界域”揭示“自身身体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④《知觉现象学》,第138—139页。也是凭以真正领会存有与世界的方式。
在对“轮扁斫轮”的诠释中,毕来德还强调“言语”在这类实践经验中的无能为力,“当我们用心关注一种外在的或内在于我们的感性现实的时候,言语便从我们的意识的中心消失了”。⑤《庄子四讲》,第17页。由言语与感性现实的差距出发,毕来德说明,在翻译活动中,在词法与句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最根本的支持还是“经验”。他将“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较为灵活地译为“人在知觉的时候,就不曾言说;在言说时,就不能知觉”,在法文中选用“知觉”(percevoir,或也可译为“感知”),而不是“确定的知识”(savoir)来对应《庄子》文本中的“知”。在此,笔者认为,毕来德的诠释或许也受到梅洛·庞蒂现象学思想的启发,即认为先于语言的知觉的产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所表达的不过是第二思想,而更深层次的语言内在于世界之中,也可称作“沉默的语言”,即存在的声音,是原初的、在世界中运作的语言。梅洛·庞蒂在追踪“从沉默世界到言说世界的过渡过程”时,指出意义“是词语链之所有差别的整体,它和词语一起被给予了那拥有耳朵的听者”。他也引用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另译梵乐希)对语言的定义:存在的语言,“就是万物,因为它不是人为的声音,因为它是事物、海浪和树林的声音”,⑥梅洛·庞蒂,罗国祥译:《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191—192页。此处译文略有修订。这也正是庄子感知到的“吹万不同”之包含无限多样性的“天籁”的召唤。
通过“庖丁解牛”“轮扁斫轮”“吕梁”游水者三个关涉身体实践经验的具体例子,⑦在对“庖丁解牛”的例子的诠释中,毕来德也将这个例子与吕梁游水者的经验相比较,并指出细微的差别所在:“他的行动已经达到了高超的效能,但是,是否已经变得像游水男子所说的那样,合乎‘必然’(命)了呢?……在某一些时刻,他还是继续用心控制自己的行动的,还没有完全进入‘天’的机制当中”。《庄子四讲》,第23页。毕来德说明:如果能够协同运作外在和内外于我们的所有力量,顺应天性,方可最终深入到“事物的运作”(fonctionnement des choses)的机理之中。他指出,庄子“在出人意料的当时,让我们领会到只有任随身体—如此构想下的身体—自由地运作,我们才能够保障自身的自主性”,⑧《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133页。具有自主性的身体经验在此是抵达行为自由的前提,这也正是庄子所谈的“不为物役”“物物而不物于物”(《内篇·山木》)的实践主体性的高超境界。难道我们不可以说毕来德在某种程度上用彻底回避审美主义倾向的“身体图式”翻转出《庄子》“内在的超越”实践性境界,也以另一种方式接通如劳思光先生所提倡的祛除“形躯我”“德性我”之误执的“情意我”自由境界;①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90—215页。徐复观先生所讲到的“艺术精神主体的自由与超越”;②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8页。汤一介先生所强调的内在精神上的超越作为真正自由的超越境界?③汤一介:《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23页。在围绕“身体图式”建构的这种视域里,“身体”可构成对精神的“遮蔽的去蔽”(Unverborgenheit du Verborgen),可构成精神释放与自由的场域。是否在这层意义上,毕来德先生以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尤以庄子的身体观为例超越了他本人所留意到的知觉现象学的局限?以“身体图式”重构的庄子的身体主体性由于经历“淡然无极”“顺物自然”的去主体化过程,或许更多地清除主体性哲学的残余,摆脱了“还原论”?因而,不凝滞于塑造成主体的身体的知觉,经由身体朝向物的开放、在世界中的融入,在身体的行动性与精神的独立性之间建立转化融通的联系。
二、运作的想象:洞见与催眠
在庄子所探索的“自身身体”的经验中,如果说“坐忘”“心斋”是以专注、沉静抵达“更高的活动机制”的可能性条件,那么,正如毕来德在其“身体图式”的视野中所指出的,“想象”的活动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具有为“自身的身体”赋予“产生意象”的权力,从而揭示出在庄子身体观中蕴涵的宏大活力场。毕来德将《庄子》文本中涉及的“想象”活动描述为具有“一种谜语般的力量”。在此所指涉的“想象”是庄子尤其在一些对话中所体现的一种有效的对策,即一方用意象的方式打通另一个空间,亦即“他性”的空间,引入全新的经验;在“相异性”的冲击下,使另一方在经历不同经验的同时实现根本性的自身转变。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毕来德以新鲜而奇特的方式把《庄子》文本与当代催眠理论联结,在这种跨界比较解读打开的多重视野中,身体图式凸显为经验显现的场域:“虚静”是前提,“想象”是动力,“转化”则是轴心。
毕来德在纵向轴上深度挖掘庄子的思想与当代催眠理论的可沟通性、在精神深度层面的接近性,从而在对《庄子》文本的个案解读之中,他也在横向轴上与催眠术做了一些比较尝试或大胆的推测。需要指出,毕来德借鉴的是吸收了现象学还原法的当代催眠理论,或者更具体地说,即艾瑞克森(Milton Erickson)学派以来的催眠理论。④关于艾瑞克森的催眠理论,毕来德主要参照J.黑利(J. Haley)的《艾瑞克森:非同寻常的催眠大师》(1990)一书。艾瑞克森的理论超越了传统催眠术的或以主体的“强大力量”作为独裁式的威力的催眠或“关注受试者的易感受性”的标准派催眠的局限后,试图建立“人际互动式的催眠状态”,也就是“合作派”的催眠。⑤斯蒂芬·吉利根著,王峻、谭洪岗、吴薇莉译:《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第9页。而毕来德的好友之一,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弗朗索瓦·鲁斯唐(François Roustang)在这一基础之上,进而发展出“催眠的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hypnose)。⑥毕来德主要阅读、参照弗朗索瓦·鲁斯唐的以下著作:《影响》(Influence, 1994)、《何谓催眠》(Qu’est-ce que l’hypnose,2000)、《治疗师与他的病人》(Thérapeute et son patient,2001)、《只需一个姿势》(Il suffit d’un geste,2003)。
在《庄子研究》的第一章中,毕来德把《庄子》的三则对话与当代催眠理论相融合。⑦Billeter, Etudes sur Tchouang-Tseu, Chapitre I,pp.11-43.比如,在解读《外篇·秋水》的一则对话时,毕来德分析了这一节所采用的言论方式与催眠术的近似之处,另辟新意。他指出,其中的关键性奥秘在于实施引导想象的方法。自以为善于辩论的公孙龙在听到庄子的言论后茫然迷惘,去向魏牟求教,“不得其方”。毕来德将这个始发的情境诠释为公孙龙的“精神危机”,并着重强调了解答者魏牟在面对公孙龙的焦虑时的反应,即魏牟没有为其焦虑的情绪所影响。在此,毕来德确立了魏牟的态度、回应方式与公孙龙的心理的对应关系。首先,魏牟“隐机大息”,这个动作在毕来德看来对对话方公孙龙具有平息、平和的作用;随后,公孙龙仰天而笑,毕来德特意强调在“仰天”的动作里包含视阈的打开,召唤对话者进行视觉的想象(imagination visuelle),在论述其观点之前,魏牟运用这两个动作使对方进入了“接受”,而不是存有意念的状态,亦即接近于艾瑞克森的催眠术中的初始状态。在此,毕来德的论述对应的是艾瑞克森的催眠方法中使来访者体验到“失去控制”的症状,进而采取自然的“催眠诱导”的取向。毕来德在对魏牟的一些态度的细节刻画中继续挖掘这种相似性。魏牟没有直接回答公孙龙的苦恼,却以提问的方式(“子独不闻夫坎井之蛙乎?”)召唤对方进入一些想象的情境,尤其是井底之蛙、东海之龟的不同空间体验与生活处境,从而起到启示(révélation,或译为“发见”)的作用。毕来德认为,通过这种想象的邀游,魏牟使他所提到的意象(images)在公孙龙身上发生作用,即让公孙龙获得全新的空间体验与感知方式,“坎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毕来德先生搁置了这段对话中后一部分的“论战性”,而强调前一部分立足在催眠术的机制认知的层面上。随后,他还列举了艾瑞克森的两个催眠实践的例子(一是如何让兴奋的孩子入睡,二是引导病人走出艰难的危机)来说明庄子与催眠理论在引导“意识让位给身体”这种策略上的近似性:用其他的经验转移注意力,引导对方进入想象的空间,从而实现内在情绪的转变。
毕来德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把庄子设想为催眠师,沟通了两种经验的共通性,即完全进入“运作的想象”(imagination opérante, opératoire);也就是说,这种机制为对方带来“洞见”的可能,带来全新的视觉,并在想象所打开的场景面前保持平静、不动。毕来德还区分三种想象的活动:一、日常的想象,让人产生疏忽即逝的幻觉;二、梦中的想象,处在一片混沌之中;三、运作性的想象,即让想象的活动运作、具体实施到“自身的身体”的经验中。毕来德在当代催眠的还原法中找到近似的方法源泉,尤其当催眠师在一个催眠阶段(transe)的后期结束想象的历险,邀请对方睁开双眼,面对白昼的日光,以日光取代内观的景象,近似“虚怀以观物”的状态,重新面向被遗忘的“现象”。引用毕来德的说法,“现象”也就是“我们思维主观划分出来的事物”;①《庄子四讲》,第66页。这或许也对应在梅洛·庞蒂意义上的“现象”,即并非“意识状态”或“心理事实”,超越笛卡尔设立的内部世界(res cogitans,广延之物)与外部世界(res extensa,内容之物)的二元对立,作为“显现”,并不受意识控制的投射,而是在身体的知觉中呈现出的世界的本来面貌,亦即立足在身体图式基础上得以还原的“事情本身”。
还要指出,在20世纪初,由于行为主义的发展、弗洛伊德对催眠的排斥以及对其神秘色彩的过度渲染,在二战后,一度被遗忘的催眠术因其临床治疗的效果重新得以被关注。②《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第31页。当代催眠理论与实践唤醒人类自身的一些根本的官能,比如“想象的才能”,这是弗朗索瓦·鲁斯唐所重新揭示的“创造性想象”的重要作用,也是遭到自柏拉图以来的希腊—西方传统所轻视的功能之一。这正是毕来德在《庄子》文本的一些对话中所领会到的,以焕发直接体验的强度调动对方的想象活动,从而使人在想象的空间里经历自身意识的转变,抵达惯常思维所无法触及的“本质直观”。笔者认为,在此,毕来德从想象的角度描述的庄子经验也呈现出与当代催眠理论的另一种相似性,即身体经验与想象经验的统一,自我与他者的统一,在想象的空间、想象所抵达的经验空间的统一。这显然与萨特在论想象时将想象经验与身体的分离、以他者为绝对对立的地狱的观念迥异。在《庄子》的相关范例中,所指涉的想象活动与自身身体的经验密切相关,从而接近梅洛·庞蒂基于“身体图式”对想象的现象学还原,即身体图式是意识所不能控制的空间情境投射的根基,位于想象活动的源起之处,而通过身体的感应与想象的活动经验,自我与他者、世界之间产生交流、分享的可能性,从身体图式的视角推进了康德将想象作为联通感性与理性的理念,想象不再只是两种活动的共同根基,也不是超越感性和理性的“第三种能力”,而是立足在融通感性与理性、身体性与精神性的知觉现象学“身体图式”之上探索想象活动的更本原的创造力。梅洛·庞蒂反对将 “主体性”(subjectivité)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相分离,他在后期对“肉身”的探讨中隐含“主体间性”的思维或者说自我与他人的关联,是作为与存有建立“共通感”(Einfühlung)、①《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第317页。对话性关系的深刻根基。艾瑞克森在其催眠理论与实践中也强调,通过催眠师与来访者的互动,在催眠经验的分享中,自我与他人的分离感消失了。在毕来德的跨文化研究视野中,这也许正是《庄子》与身体现象学、艾瑞克森学派的催眠理论两方面产生跨时空链接的内在缘由之一。
毕来德还分析了《杂篇·徐无鬼》里的一则对话的例子。徐无鬼不是采用说理的方式,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论述对不同层次的狗与马的识别的有趣经验,引发魏武侯的想象;在毕来德看来,这种方式唤醒对方进行一种“不同的存在的欲望”。于是,魏武侯不再如在对话之初时用意识来反问、干预,他“倾听、为之着迷”,而最终“大悦而笑”,从而获得在精神层面上的放松与愉悦。与此相反,他的佐相女商常对魏武侯讲述《诗》《书》《礼》《乐》,也就是儒家教化的方式,但魏武侯“未尝启齿”。在这则对话里包含了两个案例,徐无鬼先后与魏武侯及女商进行对话。最终,他以“越之流人”的生存处境对应国君的孤独感,向女商阐明他让武侯欢悦的秘诀所在:“以真人之言謦咳君之侧。”他以“真人之言”,促动国君去展开想象,调动他的想象力。“运作性的想象”(Imagination opérante),毕来德使用这个关键词来指具有实施力、可在他者的身上引发实际效果的想象策略。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主体必须首先自我放松、放空,进入“无己”之状态,以感知对方的精神状态中入侵的杂音、症状—侵扰他的精神状态的因素,包括在表面上不明显的因素。主体本身先进入催眠的状态,这也就是艾瑞克森所提到的“自我催眠”“再生性自主催眠状态”。这也是艾瑞克森所界定的“受控的自发状态”,作为有效的催眠交流者(即催眠师)的特征。②《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第55—67页。这意味着与他交流的对方同时达到“放任”的状态,并进行充分的合作。毕来德指出,自我催眠,“这是大多数人偶尔会使用的一种天生的才能”,“催眠属于人类所内在的根本而具有普遍性的官能之一”。③Billeter, Etudes sur Tchouang-Tseu, p.18.正如艾瑞克森所言,这是一种“跨情境的普遍现象”,④《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第27页。可以说具有深层的哲学与实践的意义。
毕来德如此描述这种催眠式对话的进行过程:一方先进入一种松弛的状态,以完全接受的“被动性”,达到几乎通灵式的“洞见”(voyance),在敞开的接受状态中移化对方,这对于实施者也同样可谓是一种修炼的“游戏”。正如对艾瑞克森学派而言,催眠实践也是一种“精神的游戏”,在身心相融的整体图式中达到身心放松与生命更新的游戏。在毕来德对《庄子》第三则对话的分析中也体现同样的维度。这指的是《杂篇·庚桑楚》里南荣趎与老子的对话,南荣趎向老子说明生存的困境,即他的心灵困境(“心之所患”)。在探讨老子的化解艺术时,毕来德特别强调老子面对南荣趎“若眉睫之间”,并将老子本身的状态描述为“没有分化的接受状态”(réceptivité indifférencié);在这种状态下,老子向对方传授“卫生之经”:“身若槁木之枯,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从而引导对方从困境的蔽塞中释放出来。属于艾瑞克森学派的亚瑟·德克曼(Arthur Deikman)描述一种“外部取向的催眠状态”的现象学式体验,引领人们通过专心贯注而进入这种状态,随后渐渐抛弃“习惯化的分析性思维和知觉模式”。⑤Arthur Deikman, “Experimental meditation,” in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orders. Balimore: Williams & Wilkins, 1963.转引自《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第66页。这种状态具有五个主要特征:1. 强烈的真实感(如:一切事物都好像第一次看见的“新鲜视觉”);2. 非同寻常的感觉(无论是内部想象和认知还是外部知觉);3. 一种统一体验,通常会感到“自己与他人”的分离消失了;4. 不能言表(即无法用语言向他人描述体验);5. 超感觉现象(即超出正常的感觉形式、想法和记忆的体验)。
综观毕来德在三则对话分析中将《庄子》文本与催眠术所做的切近比较,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归纳:(一)魏牟为公孙龙答疑,(二)徐无鬼为魏武侯宽慰,(三)老子为南荣趎解惑。在三则对话里涉及的都是一方在面对另一方的苦恼或困惑,解决途径如下:
1.如何使对方松弛并进入自由想象的境地,在想象活动中,打开视见之局限,体悟未得之道。
2.如何使自身的身心也松弛,进入接纳性的状态,以更好地捕捉对方的精神中产生侵扰的因素,从而抵达“洞见”。
弗朗索瓦·鲁斯唐也深入地论述想象在催眠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催眠所引发的根本性的“转变提示要悬搁我们所有的协调系统,这只有当我们借助于想象的时候才成为可能”。①François Roustang, Qu’est-ce que l’hypnose?. Paris: Minuit, 1994, p.16.而在毕来德对庄子的“想象”的价值认定中,把想象作为对西方现代占据主导的理智主义思维范式的反驳,作为一种具有生命力、可能性、运作意向性、通向洞见的理想模式,也是超越西方当代文明的危机的一种出口、医治文明疾患的一种药方。毕来德具体归结为对危机的根源即“意识、控制、知识与再现的首要性”(la primauté de la conscience,du contrôle, du savoir et de la représentation)的超越的可能,②Billeter, Etudes sur Tchouang-Tseu, p.249.也就是借助于在道家意义上的“不知、弃智”、在梅洛·庞蒂现象学意义上的知觉至上,以及当代催眠理论的现象学范式。
三、虚静与催眠:活力与再生
在论述庄子所谈到的庖丁、轮扁和游水男子的“共通经验”时,毕来德强调在身体活动中随其技艺的升华而经历的先后转变,即在“机制转换”中达到的高超境界。借助这三个例子,毕来德也说明庄子所描述的经验与现象学所论述的“感觉或知觉”的差异所在,即他认为现象学所描述的“一般主要是感觉或知觉,有时则是记忆或思维的片刻。[……]现象属于自我与自身的一种清醒的、持续的、静的关系”。③《庄子四讲》,第32页。毕来德更强调,在《庄子》文本中所体现的“动态”所引发的“转变”以及相应产生的“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可以说,毕来德在庄子与催眠术之间展开的联系与对话似乎恰恰补充了他所察觉到的知觉现象学理论的一些未及之处。而在艾瑞克森学派的动态催眠观念中,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催眠状态,而存在一些催眠的“情境”“过程”或“态度”。
毕来德还论及在《庄子》文本中的一个特殊机制,即酒醉的状态,“夫醉者之坠车,虽疾而不死”,④同上,第35—37页。“神全也”,指的是在非意识的状态中,完整的“自发的活动能力”而得以保全。毕来德也提到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对笛卡尔的“自由意志”的虚幻性的批判,并点出身体的玄机有远远超出人智的地方,比如“梦游者”在睡梦之中的行动。对“身体单凭其自身的规律的行为”的认识,在毕来德的诠释中,这构成斯宾诺莎与庄子的思想的交会处。“更何况天乎”?“意向性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为人独有的,也是错误、失败、疲惫与死亡的根源。而浑全、必然且自发的活动,被称作‘天’的活动,[……] 却是效力、生命与更新的源泉。”⑤同上,第42页。这种祛除意向性的境界,提供生命更新的(régénateur)能量,在“活动的一个机制向另一个机制的过渡”的状态中,意识会消失,或者部分地消失,“无法成为它自身消失的见证人”,或是“改变功能,或是发生变化” ,⑥同上,第55页。因而生命主体从意识的宰制中解脱出来,深层的、沉默的生命力量由此得以释放而转化为可能具有创造力、革新能力的生存状态。这种境界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梅洛·庞蒂前期所提出的第三种“我思”,即他所称之为的“沉默的我思”,①《知觉现象学》,第507页。亦即我的“生存本身”对自身的体验。或者说,在《庄子》中体现出的“身体—主体”图式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是“沉默的我思”与“身体意向性”的结合,更倾向于梅洛·庞蒂在后期提倡的返归到与世界肉身确立的一种更沉默、更源初的关系之中,即“朝向世界的敞开”的状态,抵达对自身与世界的双重体认。
在艾瑞克森学派的催眠理论中,“催眠被定义为一系列体验式专注的交互序列,该序列将产生一种改变的意识状态,在其中,自我表达开始自发发生(即没有意识的干预)”。②《艾瑞克森催眠治疗理论》,第5页。艾瑞克森学派催眠理论正是确信人自身的“再生性资源”,但这究竟如何实现呢?这种催眠理论的首要环节定义为“深层的体验性专注”:“自然产生的催眠状态营造出一个理想的氛围,来访者可以通过接触、承认,然后再转变基本的体验关系来达到深层的系统变化。换言之,进入催眠的来访者可以在一个较深层次的自我评价的背景下根据经验去连接问题状态背后的各个方面,然后利用种种资源来实现转变性变化。”③同上,第15页。在《内篇·应帝王》中,壶子向列子呈现向神巫展现一系列变幻莫测的状态,由入静的死寂到“太冲莫胜”的守气境界,再由静而动,最终“未始出吾宗”,“虚而委蛇”,即“同于大道”(《内篇·大宗师》)、“合于天伦”(《外篇·刻意》),从而使“神巫”望难而却。这种见证对列子的触动颇大,从而促使他随后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三年不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这种 “复归于原初”的道家境界,也正是毕来德所强调的“返归自身”的促使生命革新与焕发深层活力的修养工夫。
毕来德将《应帝王》中壶子对列子展现的几个阶段描述为“下降到大虚静”的过程。毕来德在《庄子四讲》中也提到,在习惯性的思考或活动经验中,“精神退身出去,让身体来行动”,“必须让自己进入一种虚空,我们所有的力量才能聚集起来,产生那种必然层次上的行动。我们也知道,失去了这种进入虚空的能力,就会产生重复、僵化,甚至于疯狂”。④《庄子四讲》,第87页。毕来德将这种经验界定为“活性的虚空”,即认为庄子的主体性的吊诡“介于虚空与万物之间”,处在可以促成转化可能性的充满活力与潜能的敞开状态。毕来德还指出,这种虚静所指涉的“不是一种孤独的沉思,而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深邃的虚静为想象赋予了当我们处在日常生活的躁动中所不能获得的一种力量”。他还再次将列子与壶子展现的经验与催眠术相对应,“两个人进入了虚静之中,彼此面对,并任由他们的想象共同飞跃,进入交互共鸣的状态,或化成可彼此沟通的空罐”。⑤Billeter, Etudes sur Tchouang-tseu, pp.34-35.庄子倡导在“凝神”“心斋”“意守”⑥庄子对“入静悟道”的记述颇多,比如,“其神凝”(《逍遥游》)、“吾丧吾”(《齐物论》)、“心斋”(《人间世》)、“无视以听,抱神以静”“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在宥》)、“忘汝神气”((《天地》)、“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刻意》)、“心若死灰”、“齐(斋)以静心”(《知北游》)、“卫生之经,能抱一乎”(《庚桑楚》)。的虚静中达到“逍遥游”的自由境界,“游于太虚”“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杂篇·列御寇》)!毕来德从自由与必然的角度肯定“游”的机制的哲学意义:“因为其中既有对必然的认识,也有一种由此而产生的,游对必然的静观所产生的第二性的自由。”⑦《庄子四讲》,第57页。而这种“游”的经验的共通性,毕来德借助与催眠术的对比诠释使之充分地凸显出来。
鲁斯唐在论述“催眠的还原”时指出:“催眠的现象学与我们在实验科学中的理论知识相违背,因为它并不是同样建立在反射性行为的模式上。”反射性的行为(action réflexe),总是需要来自外部的一种刺激,它如何具备使它自身再生的力量?需要召唤另一种秩序的权力,另一种层次的逻辑,为了让“可能性的世界”可以在反思的第二种模式之上涌现出来。⑧Roustang, op. cit., p.12.这也正是所谓“催眠还原”的效果,鲁斯唐指出,催眠还原“从普通感知的终止”(arrêt)开始,其次达到悬搁我们所习惯的对事物与他人的确定的成见,这不免会引起一种混乱;再次,新的可能性萌生,因为我们从与存有的各种构成元素的过于紧密、明显的联系中释放出来①Ibid., p.15.。鲁斯唐也强调从孤独的个体经验出发,通过催眠的实践,“找回我们从中分离的连续的景深(fond)”,或许正是原初的、无分化的状态,通过催眠的现象学,作为一种修身的途径,作为“日常生活的有效力的、含蓄的配料,一种生存的艺术”,用于对抗“西方个体主义的疲乏”,走出“自我忧虑”(Souci de soi)带来的“文明的疲乏”。②在此,鲁斯唐引用皮埃尔·帕歇(Pierre Pachet)对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的论述。自诗人米肖以来,当代不少法国诗人批判、直面这种自我的过度,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借鉴了道、禅思想中的“无己”“不知”的精神资源,用自我隐退的诗学经验融入了与当代哲学思考相同步的“归隐之路”。而毕来德的中国诗学、思想的研究也对这种伦理转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比如他在《中国诗歌与现实》一文中结合道家思想对中国诗学中“忘我”与“求真”的精神评述如下:“我们在固定的模式(此外在许多时候也是有用的、必要的、丰富的)之后回避了真实,我们需要与思维习惯做一种决裂,需要一种把握引向美好的忘我。”毕来德以中国思想为范例所呈现的“忘我”与真实的重新发现,引导一些具有哲理倾向的当代法语诗人通过克制自我、谦卑内敛,重新面向感性世界,引领诗歌走出西方抒情传统的危机。
在解读《外篇·田子方》篇时,毕来德并没有将这则对话与催眠术作直接对应的分析,却将重点放在田子方在对话中向魏文侯所描述的“东郭顺子”的德性:(一) “为人也真”;(二)“人貌而天虚”(对应“人”与“天”的范畴);(三)“缘而葆真”; (四)“清而容物”;(五)“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毕来德在此处从对“真人”的品质的描述中找到催眠方法的钥匙。归根结底,这涉及庄子思想中的一种根本的机制:顺其自然,接纳万物,抵达“天虚”即入“天”的机制。毕来德认为,这是一种最恰切的方式,并可会通于艾瑞克森学派的催眠策略,即以极其“专注”“大静”的反策略途径,觉察到对方意识的骚动状态之荒诞性以及努力的虚妄性,并帮助对方打消意念的侵扰。在这一段中,魏文侯的最终反应如下:“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他感叹:“吾所学者,直土梗耳!”以顺子为例,庄子呈现他所提倡的“修养”的工夫,解构了魏文侯所受的儒家礼教,说明如何达到“真人”的境界,也近似于老子《道德经》倡导的“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的“玄德之人”的境界。道家思想强调“静中体验”,对“虚”的境界的“体知”,都在于排除私心杂念,凝聚精神,存养本心,对身体进行自我调适、修身养性,在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调整中获得对生命本真的自觉,同时营造与他人互动的恬淡根基。这种修养哲学在偏重知识论的传统西方哲学中通常遭到忽视③参见何锡蓉:《修养:从事中国哲学的途径》,载周山著《中国哲学精神》,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第226页。“中国哲学是讲求身心休养、讲体验认知的哲学。这种哲学重在人的内在省察,反观自我之心灵,注重身体与心灵的一体,以获得身心境界的提升;强调个体生命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知识的获得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为一体,视求知为一个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同时,强调修养的实践性,不断地把这种内化的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之中,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应对社会人事;而且,就个体生命而言,修养又是一个接受教化、融入群体的过程,是见证人类精神、存续文明脉流的不息活动。中国传统哲学所注重的修养方式,纳不进传统哲学的视阈。但是这种修养的哲学方式是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发展的合适的方式。当今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对修养的重视,或许会成为今后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汇通处或贯通点也未可知。”;而毕来德所借鉴的如鲁斯唐所革新的法国当代催眠理论却结合现象学的理论、借鉴中国思想进行催眠对自身关怀以及生命的身心修养的探讨,在从修养问题推动中西会通的层面上富有对话的潜能。
在毕来德诠释的《庄子》文本涉及的“机制转换”的进程中,有一个关键词是“信”,另一个则是“变”(转变、转化)。毕来德借鉴德国神学思想中④毕来德如此评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思想:“救赎来自信仰,而‘信’出现了,善的行为便自然出现,而且完全无私”,他随后也指出,“我提出这一对比是想顺便指出庄子虽是看上去那般轻灵,却触及到了神学当中某些核心问题”。参见《庄子四讲》,第54、55页。对他者的接纳、信仰、无私、去我,强调实现意识对身体的信任。毕来德分层次地描述这种意识的非清醒状态:一是信任身体,二是与身体保持距离,以旁观的方式观看身体的活动。“意识这样信任身体,它自己便获得了一种自由,可以转向别处,而行动却不会由此中断”,“意识一方面对身体的活动很了解,主要是通过机体知觉与运动知觉,但同时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处在一种旁观者的位置。意识在观看一种不依靠它来执行,而且是以必然的方式在进行的活动”。①《庄子四讲》,第56页。意识“由于脱离了一切外在的任务,只是观看我们自身内部发生的活动”,“悖论在于意识处在活动与悬隔之间、关注与超脱之中”,或者说介于系与不系的状态的“两者之间”的状态。毕来德认为,庄子的“游”的机制指涉这一向度,②毕来德指出,“在《庄子》一书中,‘游’与对活动的静观体认相关联”。《庄子四讲》,第57页。他也进一步指出“游”的机制与身体—主体的关系:“当一种活动对我们来讲变得很自然,意识会减弱对它的控制,从而可以或是转向别处,或是回到正在进行的活动之上,从内部以观察者的身份来检视它。这便是庄子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使用‘游’这一字眼所指称的机制。而在此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状况:意识面对的不是一个运动中的身体浑整的行动,而是身体本身处于静止时内在的活动。”《庄子四讲》,第83页。而他又将“游”的经验与当代催眠术的理论相接通。这种意识的悖论状态在表述的实质上对应于鲁斯唐所定义的“悖论式的醒”(veille paradoxale)的状态,它“有助于让想象展开,以转化我们与其他个体以及事物的关系”。③Roustang, op. cit., p.14.鲁斯唐也描述了在这种状态下的“倾听”,即不试图去听见,而仅仅让声音在自身之上回响,同样的经验可以涉及其他感官,这是发现根本的真实性的一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与庄子描述的“倾听”经验相近似:“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内篇·人间世》)气化的身体成为朝向事物敞开的场域,接纳、汇集、呈现,“听之以气”,意味着不停留在官能的客体化、表象化、符号认知的感知层面,而是回到气息贯通的自身身体的整体性,以全神贯注的状态捕捉“天籁”之中蕴含的千差万别。因而,“心斋”即从“吾丧我”的无己、平淡、虚静出发,一方面从体虚的主体性朝向构成主体性的基础的对自身活动的“自我知觉”,④《庄子四讲》,第85页。另一方面也是抵达对作为大写他者的世界的深度感知与领会的一种修炼途径。在庄子的精神世界中,这种体虚的状态不仅具有体察事物与身体行动的有效性,也具有在静与动之间旨在遵循天道、内外兼养的修身养神的效果:“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外篇·刻意》)在鲁斯唐论述的“催眠还原”的活动中,通过自我内在的虚空,顺从引导,在催眠阶段的后期,在介于睡与醒之间的状态,意识既有感知力,又以接纳的方式朝世界敞开,从而最终促使逐渐实现自身内部的根本性转变,一次次实现生命的革新与再生,也达到与世界的沟通与相会。因而,鲁斯唐最终将具有明显、独特现象学直观特征的催眠还原界定为另一种“在世的方式”,即注重身心修养的“生活的艺术”。
在《庄子研究》中,除了前四章与催眠理论有会通的研究外,在后面附录的“补充”中,毕来德还辟以专门的一节“论催眠”,明确提到他在对《庄子》文本的重新诠释中借鉴艾瑞克森与鲁斯唐的催眠理论的观点⑤Billeter, Etudes sur Tchouang-tseu, pp. 235-237.。他结合《庄子》的对比解读,把催眠诠释为“不同活动机制构成的整体,在其中,尽管意识清醒,但不介入身体的本能的活动”,作为对西方理性主义范式及其主体模式的反驳来重新界定。⑥同上,第248页。毕来德究竟是借鉴催眠术的表达革新了庄子的解读,抑或在道家的意义上重新构建当代催眠理论?也需指出,在《何谓催眠》中,鲁斯唐引用庄子的“庖丁解牛”的范例,并引用毕来德先生的评述,进而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舍弃思考,而是重新引向事物本身,“故而提出一个伦理的问题,作为态度的狭义的伦理”,即与世界建立共通性经验作为深度感知的一种形式,在与外界的接触中触发“循虚而行”的内在转变作为一种交流的条件。①Roustang, op.cit., pp.171-173.我们可以说,在毕来德与鲁斯唐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交互影响。这种理论探索上的互动显然具有跨学科、跨文化对话的鲜活意义。在毕来德庄子研究的理论背景中,虽然催眠理论只是参照的一种,其比较探索也不乏局部的牵强之处,但这启发我们在身体现象学、当代催眠理论的西方视域中深入体会这种融通中西的研究进路,及其诠释中揭示的具有显著当代意义的根本性问题。
结论
毕来德将庄子与当代催眠理论的切近尝试在庄子研究方面独树一帜,②自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对《庄子》的研究中建立诸多与西方思想的对话,比如严复、梁启超分别以庄子比卢梭的自由平等、复归自然等学说,蔡元培将庄子与柏拉图并列,曹受坤糅合笛卡尔、柏格森、罗素各家之说解《庄》,牟宗三在庄子与康德之间进行会通,徐复观在庄子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之间搭起了桥梁,当代也有不少学者如陈鼓应、刘笑敢、陈荣灼等在庄子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之间的比较尝试。参见方勇编:《庄学史略》,成都:巴蜀书社,2008;刘固盛:《老庄学文献及其思想研究》,湖南:岳麓书社;2009。赖锡三先生综述分析“后牟宗三时代”老庄之道在存有论、美学、神话学、冥契主义等方面的多元诠释,参见赖锡三:《当代新道家:多音复调与视域融合》,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在汉学领域至今也是绝无仅有。而这也与他对庄子的思想中的身体观、虚的体验等问题方面的创见相对应,也汇集了法国当代现象学自梅洛·庞蒂以来对身心二元论、对意识哲学的深刻批判与超越;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有所超越的强化以身体为主体的哲学肉身化的趋势。此外,这也对应自现代物理学对“虚空”的发现以来西方思想中重新认识“虚”的积极意义、从哲学到艺术的领域探讨“虚”的意涵到容纳“虚”的当代思考的轨迹中。毕来德也可以说在庄子思想的研究中既吸收了当代哲学的新进路,也以中国范例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为当代西方哲学对“身体”与“虚”的思考提供异域思想的深厚资源,构成当代西方思想与汉语思想对话的具有启发性的新探索。
归根结底,毕来德的庄子研究或许正达到其本人在字里行间所颂扬的“穿越的能力”。其研究与翻译经验正是向我们展现了这种能力,正如在明澈的音乐之中逐层升级、穿越屏障的境界。毕来德在传译庄子时注重舍弃“形似”,又探求“恰当的语调”,可谓正是在对他者的专注倾听中,在整体上“以神遇之”,从而达至 “化境”。正是有了这样面向古代经典文本的翻译观、诠释观,毕来德与庄子跨时空的思想对话,才真正成为既有切合,又有神游的敞开的空间,进而与法国当代的身体哲学、催眠现象学产生深度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