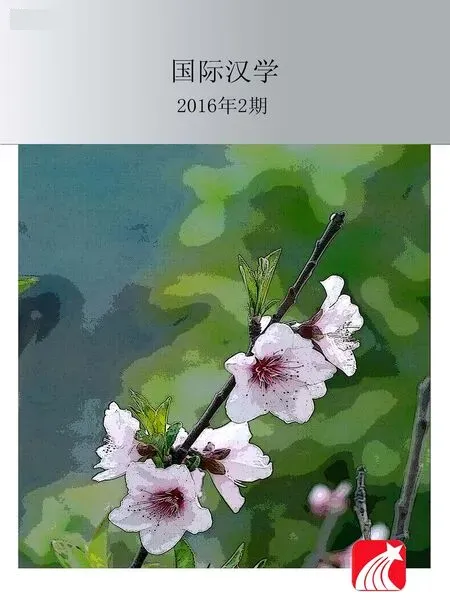我的新汉学观:走向“语义环境”互鉴
国际汉学面临一个向直观比照诠释新汉学转变的新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一个对旧汉学时期的觉醒,对旧汉学困难的克服;它将开启一个文化之间平等、恰当交流与对话,减少误读、误解、误判,较为切实相互理解的新时代。朝着这个新方向迈步的标志,就是在文化间,特别是中西文化之间,实行在彼此语义环境间对照阐释两个文化意义的差别,取代历来所用的将阐释对象的中国事物装进西方语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中去分析的方法,后者留给我们的多是遗憾的扭曲与误解。
一、一批汉学家、比较中西哲学家的意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 1893—1979)提出,如果将西方的“分析”作为理解孟子的方法论,就会把整个西方世界观和整套思想体系“走私”到孟子思想里来。①I. A. Richards, Mencius on the M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2, pp. 86-87.比较中西哲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1919—1991)则提出,西方汉学家在自己母语中找不到切合“仁”“德”的词汇,要是用“benevolence”和“virtue”去附会,两个传统的深层结构性差异就会被误导;一边是印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宇宙论,另一边是中国传统,根本没有这样一套结构。②A. C. Graham, 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p. 322.此外,尼采(F. Nietzsche, 1844—1900)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也得出,特定宇宙观沉淀在特定文化的语言及概念系统结构之中。葛瑞汉确切地说,中国自古形成的对宇宙的认识,不是通过一个唯一外在、远在天边的超越本体源头来叙述的,而是将万物都认识为相系不分、互相依存的。③Ibid., p. 287.比较中西哲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认为,我们现在的词典简直是一大灾难,以“天”“道”为例,现在的汉英词典承载着一种与其所要翻译的文化格格不入的宇宙观。④安乐哲:《孟子哲学与秩序的未决性》,载李明辉《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1995年抽印本,第42—43页。
二、旧汉学留下遗憾—糟糕的“不对称文化比附”
从上述一批汉学家、比较中西哲学家提出的意见去考虑,今天必须要强调,新汉学的前途是要做中西哲学文化的比照诠释。汉学是在四百多年以来西方了解中国的大潮中,一些人研究和解读中国的工作,它的影响不可谓不广泛和深刻,但不容忽视的是,汉学一直有个很成问题的做法,即对中国传统的解读采取的是糟糕的“不对称文化比附”—总是习惯地按西方哲学假设范畴,对中国传统施以“理论化”,无顾忌地使用“鞋拔子”,把中国事情硬往西方的概念框架里塞。例如人们常说“墨子是个功利主义者”,却不会说“穆勒(F. Max Müller,1823—1900)是个‘墨家’”;还会说“儒学是道德伦理学”,却不考虑亚里士多德将会怎样解释‘天’”;人们几乎不问为什么西方没有形成“道”“德”“仁”等的观念。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前些年德国汉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一面把郝大维(David L. Hall)、安乐哲同黑格尔、韦伯放在一起,说他们是同一出发点,但在另一面却用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儿童心理学范畴的伦理认知逻辑阶段论,去附会中国古代春秋之辩的历史现象。①田辰山:《西方对中国哲学诠释的危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国际研讨会”的发言,2010年5月30日。这太明显了,会使人感到很不安。科尔伯格的儿童心理阶段论,跟诸子百家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范畴、逻辑和结构!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对于西方特有的普世思维逻辑而言,这十分典型,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中国互系性的思维来说,却很蹊跷!
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存在相当流行的不对称诠释问题。这个误导性诠释是伴随兴办西方教育、提倡白话文改革而来的,也是时逢“现代性”文化帝国主义潮流的一个结果。因为是在一个大体西方式假设框架结构当中,哪怕人们是用汉语讲话,其中也隐含着这个结构。总之,这个不对称诠释酷似一个“鞋拔子”,做了将一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脚硬塞进另一个西方文化传统的鞋里去的事。所以旧汉学走过的是一条“不对称文化比附”的路,似乎中国思想文化只是在遇见西方传统之后,才有了看待自己的标准,如果没有西方概念与理论框架,中国的事情就找不到自己“体”了。这样的效果,其实必然地导致了对中国思想文化以及各种中国问题的扭曲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中国文明发展及其历程一直是通过一套与自己不相干的西方假设推定途径表述的。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使汉学成为世界性学问,呈现出一种新局面,人们已开始呼唤“新汉学”或“大汉学”。中国作为一个成为世界了解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或国家,明显表明了她在世界的意义、影响或更潜在的意义和影响。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不对称文化比附”是长期以来导致误读、误解、误判中国事物的障碍,清除这个障碍必须提到日程上来。
三、“比照诠释”—让汉学回归到中国语义环境去
今天的新汉学要实行的“比照诠释”是在纠正旧汉学“不对称文化比附”意义上的一个概念。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比较哲学文化与恰当的文化阐释,就是让历来被不对称比附的旧汉学从跟中国语义环境脱离、硬是塞入西方语义环境的中国文化,重新回到自己的原本语义中去,让中国文化讲自己的中国话,讲它自己。这尤其对汉学在当今逐步演变到作为专业,由对中国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哲学乃至敦煌学、考古等等,转入对当代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形成一个广义的“汉学”这样的状态,意义更为现实、重大,否则不能适应当今中国与世界深刻变化中日益凸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新汉学需要面对三个大问题:1.如何认识与解读中国和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对世界的意义与影响;2.如何应运时变,让汉学与国学、世界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更具有对话的能力;3.如何梳理传统汉学与当代研究的承续以推进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沟通。重要的是“新汉学”这些研究方向新特点,最后有必要归结到一个根本特点,即如何解读和诠释一个更接近于自己本来面目意义上的中国,它这样就成为了一个需要克服“不识庐山真面目”肤浅认识倾向的问题,这个问题又直接连带着对待话语权问题,也即是为了追求单方、单向、单线、为某一方政治服务的话语,还是一个双方、双向、多层次地鼓励恰当相互关系,考虑到众方利益,达到众方共赢的友好话语。
世界上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一项调查显示,5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带来经济威胁,51%的人认为是军事威胁。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发展一个必然趋势,但中国并不想称霸世界,而要的是和谐共存、相互理解。20世纪西方哲学家对中国传统抱矛盾的态度,他们不愿将中国传统视为一种严肃哲学探求,不承认它作为哲学学科的合法地位,这一切都可归结到翻译者们对中国哲学理解的语汇匮乏。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实证主义方法导致对他者文化和历史的边缘化,让哲学专业人士难以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兴趣。所以,加强对中国的理解,提高汉学的学术意识,不能是天真、简单化的,而是必须有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精神。一旦着手汉学,首先必须做的,就是让你入手的汉学题目从西方理论语境脱离出来、使它返回自己原本的语境去。这意味着,在其汉语语义环境中,想办法弄懂它所指的是什么,也即将它所受浸染的那些西方文化假设推定实行剥离,让它显示原本特有的内在性,对中国宇宙论在西方话语说来不同寻常的那些反差特点与不同,实行直观的对照性诠释。
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精神,简明地说就是在西方概念话语叙事作为我们经验的一半之外,需要总结出经验的另一半—一个中国的语义环境,也即中国哲学叙事产生的那种语境;只要想做出名副其实的汉学,想得到一个更接近于自己本来面目意义的中国,它所处于的那种语境就必须要考虑进去。应当说,《易经》提供的自然宇宙观语汇,就中国传统诠释语境而言,是根本的。在这个诠释语境提供条件下的中国思想文化讲述自己,同时在汉译英的西方诠释语境中难以想象的中国本来面目是:中国事物首先是“准无神论”;中国的“天”不是从西方假设而来的超绝外在“本体”的“天主”或“上帝”;中国智慧不需要上帝这个理念;中国的“伦理道德”不是西方神性的那种;中国的“人”是关系而不是个体;中国传统的“民主”资源与内涵都是丰富的;中国是富于群性感的社会,不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产生的国情; 从中国语义环境看,“人性不变”是个哲学谬误;中国不是神性文化,而是人性文化;西方求的是“绝对真”,中国的持久努力用于把持中庸之“道”。现代中国成功避免了西化进程最糟糕结果,没有迹象能说明当代中国是抛弃了任何中华文化的重大内在要素;当今中国社会仍是个“礼仪之邦”。
走向“比照诠释”的新汉学,让汉学从“不对称文化比附”西方语义环境脱离出来,重新回到自己的原本中华语义环境中去,让中国文化讲中国话,讲它自己,具体步骤是:第一阶段:1.唤起对旧汉学“不对称文化附会”的敏感;2.确认“不对称文化附会”使用语汇在西方语义环境的形而上学超绝与二元主义寓意;3.这时油然意识到西方语汇的汉学潜存着扭曲与误读;进入第二阶段:4.唤起对现代汉语汉学表述的敏感,关注某一西语概念的汉语译词在中华“一多不分”语义环境的原本含义;5.查阅诸如《说文解字》或《康熙字典》,发掘某一现代汉语作为西语某概念翻译词汇,其原本与宇宙论“万物互系”(或无超绝无二元主义的寓意);6.一旦找到某一现代汉语与中国宇宙论相关的寓意,便会油然认识到,某一汉学题目在汉语与西语表述上存在各自不同语义环境的结构。这里的“比照诠释”,实际是中西语义环境的直观互鉴,其过程本身是在修正历来西语汉学“不对称文化附会”(“概念对号入座”)造成的误读、误导与误解,这一过程也同时成为中国话讲述的接近中国本来面目的汉学。
中国与西方“一多不分”同“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直观互鉴,必然是新汉学基本方法。“一多不分”语义环境(interpretive context),是在与西方“语义环境”的直观互鉴中得到的。“一多二元”中的“一”(“基督教上帝”或唯一真理)是西方形而上学假设推定的凌驾宇宙之外、超然绝对的主宰宇宙本源体;“多”是由这个“一”创造或派生出的一切“独立、个体”物(包括人);“二元”是“一”与“多”之间的单线单向主宰与被主宰关系,作为“多”,一切“独立、个体”物之间由于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一旦相遇,则导致“非此即彼”对立与冲突的紧张性,构成单线单向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一多二元”的特质是:“一”的超绝性(transcendentalism)与一切个体间的二元对立性。“一多不分”则是非超绝性和非二元对立性的万物相系不分与通变之道。
四、新汉学的独特价值与当代意义
新汉学的独特价值与当代意义是它倾向于让人们用恰当的视角与话语了解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意义,它追求汉学与国学、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对话能力,致力于恰当梳理传统汉学与当代研究的承续,推进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实现积极的沟通。而当今汉学这样的价值与当代意义,其获得的保障与坚实落点,在于它有助于人们认识与阐释一个更接近于本来面目的中国,而这一价值乃至当代的世界意义,有赖于矫正世界性的“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肤浅认识。
新汉学研究的扎实性,来自下列几点:它增强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的对话能力;这一能力植根于中国能够做到确凿回答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能用适当话语,做到跨文化(特别是跨到西方)的诠释;它弥补了传统汉学陷于对中华文化误读、误解、误判的缺憾困境。它犀利的学术指向,深刻揭露造成对中国误解的原因,是把中国塞入西方概念和理论框架。新汉学展示的是一个本来面目的中国,信服地告诉人们中华价值更为符合世界未来的人类福祉,是人类可持续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当今汉学的恰当性与健康方向,取决于它有利于加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与世界适宜与积极的关系,而不是削弱与分离它们的关系。新汉学价值与当代意义的重要标志,是它能够打通传统与现代中华文化之间断裂的表象,揭示其延绵不断的一以贯之结构,揭示中华传统的现代承续性与承续形态。
今后的汉学研究如果不具备上述价值与当代意义,则不是直视,因而不能适应当今正在深刻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就是它的失当,就须引起注意,思考它是否走向了不得当的方向。新汉学于今天的发展价值与当代意义,必然反映出于什么目的认识和解读中国,对中国最后所做的解读是为什么利益服务的,是加深了还是损害了中国与世界的恰当关系。
如何才能开拓汉学新领域,推进汉学新发展,要看它关系到的是否是世界的问题、根本的哲学问题、哲学的危机。人类要走出当今的困境,必须要找回哲学。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须接受哲学统领。在世界人类命运问题上,不是竞争,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而是要把思维转变到“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要么是共赢,要么是共输”;而“共命运”“共赢”的哲学,是新汉学所应提供的,其强有力的源泉恰恰潺潺流淌在中国的哲学文化之中。其根据就是它万物互系不分,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天然、自然、适当关系出发、以关系为本的宇宙论、思维方式及崇尚观的哲学。抓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开拓汉学新领域、推进汉学新发展脉动的霹雳机缘,就登上了学术高地制高点,就掌握了最过硬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