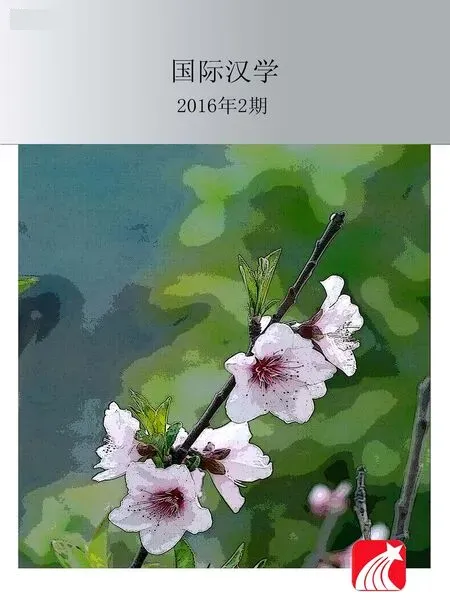文本、叙事与神学—司马懿教授访谈录
访问人: 吴 青
访谈按语:司马懿(Chloë Starr)是近年来活跃在汉学研究领域的一位西方青年汉学家。她出生在英国,父母都精通中文,父亲司马麟(Don Starr)是英国杜伦大学的汉学教授。司马懿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理解。在其求学和研究道路上,她涉猎广泛,从中国文学到中国基督教神学,并将研究中国文化作为她的终生志业。笔者于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访学,司马懿是笔者在耶鲁访学期间的联系教授。笔者有幸在访学期间旁听她的研讨课程,参与她组织的学术系列讲座,并与她近距离探讨学术和人生,获益匪浅。本文是对司马懿教授学术研究的一个介绍和回顾,访谈内容涉及她的成长背景、学术训练、目前从事的研究课题等方面。希望通过这个简短的学术访谈,让更多中国学人有机会了解司马懿和她所代表的西方学界目前正在进行的汉学研究的情况。
问:据我所知,您与中国结缘是缘于您有一位汉学家父亲,可否谈谈您个人的成长经历?
答:我的父母亲都是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伦敦亚非学院(SOAS)念的大学本科,学习的中文。如今在西方学习中文的人一般都有机会去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语言学习。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没有办法去中国内地。我父亲一直以研究东亚,尤其以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文化为他的终身志业。他曾在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习晚清中国哲学,并专门研究晚清儒学大师章炳麟。之后他到了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做教授。1982年至1983年是我父亲的学术休假年,这一年他到日本京都大学做研究。当时我刚好十岁,跟随他到了日本读小学,这是我第一次到亚洲。还记得在香港转机的时候,我们的飞机降落在香港,我在飞机上清楚地看到香港海面上星星点点的渔船。在日本的一年,每周我们都会去不同的寺庙,参观不一样的建筑,我很喜欢那里的建筑和文化。我感觉日本文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学。我生命里的美学观念,究其根源,很多是来自日本。日本的建筑艺术以及静谧安宁的文化氛围,给我很深的感受。这就是我第一次在东亚的经历,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后来我回到英国继续读书。在英国,很多准备上大学的学生,高中毕业后都会有一个间隙年,学生一般会利用这一年时间去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学习和实践。因为我很早就有了去剑桥读书的想法,并且立志要学中文。所以中学毕业后的这一年,我在父亲的帮助下来到中国。19岁的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人大附中当外教,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我每周教8节听力课,住在人大附中后面的宿舍。在担任外教的同时,我也请了一位中国朋友教我中文,因此这一年时间里,我的中文进步很快。尽管聘请中文老师的费用不菲,但我的工资是每月五百人民币,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非常高的收入了。我每月的工资不是从银行领取,而是校长直接将现金交到我手里,很有意思。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我经历了用粮票购买面粉的计划经济时代。在我印象中,北京是一个很美的城市,12月的天气尤其舒服。我很享受北京的生活,早晨我经常去人大附小跟一群老人练习太极拳,也经常去人大的留学生楼,跟那里的中国老师学习中国书法和国画。现在我办公室墙上的这幅山水画就是我当年在人大的时候画的,当时画了很多幅,这幅画其实不算最好,但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学习笔法确实很不容易。在北京的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的各种事物,经常骑自行车去各个地方。从人大到北京音乐厅骑车半个小时,从人大到天安门骑车四十分钟。如果到颐和园,也是骑车去,门票只要一毛钱。此外,我还经常骑自行车去城中心打国际长途,那时候自行车可以随便停在任何一个角落。在北京的时光是一段特别的日子,也是属于我的美好回忆。1989年至1990年的那一年中国没有国际学生,故从1990年至1991年开始,开始有第一批留学生到中国,比如杜伦大学从1990年起每年有二十个留学生到人大学习。我父亲有个二年级的学生,叫董莎莎(Sarah Dauncey),现在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汉学教授。那个时候外国留学生比较自由,经常收到来自各国大使馆的邀请参加聚会,或能见到中国摇滚的领军人物崔健。我们在假期经常乘坐大巴或者火车出去旅行,一路上目睹大西北的荒漠,最终到达新疆喀什、乌鲁木齐和甘肃敦煌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西部城市。尤其记得1991年的8月,我、妹妹和妈妈三人坐火车从北京回英国的难忘旅程。我们乘坐的火车在西伯利亚铁路上前行,途经蒙古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在进入蒙古之前,我们所坐的火车经历了换轨的过程,整个车厢都被举起来,旅客全部在车上,列车从宽轨换到窄轨。在进入莫斯科之前,我们得知苏联发生了政变,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九”政变,当时我们一群外国人在车厢里守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尽管遇上政治风波,但后来我们还是顺利进入苏联,这趟旅程一共历时一周时间,最终我们回到了英国。在中国的那一年,我的中文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尤其是口语。所以到了大学,我在一年级的时候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选择入读剑桥的地理系,但同时也旁听文言文。到了第二年,我才从地理系转到中文系,开始系统学习历史、文学、文言文和哲学等课程。我的专业领域也确定为当代中国和现代文学。
问:可否谈谈您一路以来所受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对您现在从事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答:一直以来,我对中国文学特别感兴趣,当时教我们当代文学的是杜博尼教授(Bonnie McDougall),她那时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教授,非常有名。因为剑桥教这门课的教授(Ng Maosang)英年早逝,所以杜博尼教授就每周从爱丁堡坐火车过来教课。当时教我们汉代文学的教授是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教我们唐代文学的教授是麦大卫(David McMullen),他是研究唐代文学和历史的大家,现在他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我大学毕业的论文是研究高行健的,具体的题目是研究他的话剧《夜人》《绝对信号》《车站》及它们与法国荒谬剧的对比。当时高行健还没有得诺贝尔奖,也没有很多人研究他,我选择高行健做我的本科论文,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可以说,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最早研究高行健的成果之一。在英国,一般16—18岁的年轻人都会选择3个领域进行深入学习。我选择了法语、俄语和地理,所以我读了很多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的作品。我本科毕业时获得了一级荣誉学位,并获得肯尼迪纪念奖学金(Kennedy Memorial Scholarship),到哈佛大学东亚学系学习一年。在哈佛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 1927—2014)和李欧梵教授(Leo Ou-fan Lee)等,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教授。其中韩南教授被誉为“研究中国明清小说第一人”,他的研究领域是晚清小说,我开始跟随他学习和研究《海上花列传》《风月梦》等晚清小说。尽管在哈佛的学习很有收获,我也已经得到了继续攻读博士的名额和奖学金,可以留在哈佛读博士,但考虑到美国和英国的博士训练过程不一样,最后我还是选择去牛津大学读博士。美国的博士训练一般是在开始博士论文写作之前需要有两年的课程学习和一年的系统阅读,然后才开始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因此读博士可能需要七八年之久。而英国博士训练的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自身,你可以选择开始写作博士论文的时间,这样你读博士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尽管美国的学术训练更扎实,也可能更好,但我还是选择回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杜德桥教授(Glen Dudbridge),他也是著名的汉学家。我研究了六本中国晚清小说,分别是:《海上花列传》《风月梦》《品花宝鉴》《九尾龟》《花月痕》和《青楼梦》。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晚清青楼小说研究》(The Late Qing Courtesan Novel as Text and Fiction)。在我读博士的1996年至1999年,那时候研究晚清小说的人还不是很多,也没有很好的数据库,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中国。因为这些小说在19世纪的中国都还是禁书,所以中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而且研究兴趣也不太一样,西方学者对性别问题和性意识关注较多。
问:鲁迅曾将青楼小说称为“狭邪小说”,而您却执着于这类小说的研究。您的专著《晚清红灯小说研究》(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①Chloë F. Starr, 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Leiden: Brill, 2007. 关于该书的书评有: Margaret B. W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08/2009, Vol. 68, 3, pp.960-961; Keith McMahon, NAN Nü, 06/2009, Vol.11, 1, pp.150-152.是在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可否就您的这本专著谈谈您对晚清青楼小说的研究心得?
答:长期以来,晚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处于一个配角的角色,不受学界重视。中国作家鲁迅曾对青楼小说和武侠小说这两类小说体裁进行评价,贬称其为“狭邪小说”。受鲁迅的影响,后来的很多中国学者也视其为粗陋的艺术,有伤风化,并未重视这类小说的价值。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这类小说在文学批评中虽有其一席之地,但就其具体的单篇小说而言,却很少有学者持续的讨论。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青楼小说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如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和贺萧(Gail Hershatter)的研究,他们几部重要的著作多是从青楼小说的视角研究晚清中国的社会。在文学领域,王德威一些散论中有所论及,将之称为“堕落小说”(novels of depravity)。而韩南、马克梦(Keith McMahon)、曾佩霖(Paola Zamperini)等学者对青楼小说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我认为青楼文学虽然是一种简陋与底层的文学,是有关男人和妓女的文学,但我感兴趣的并非青楼,而是写作。我认为写作是有关意义的写作,我阅读青楼小说中的历史,但历史只是背景。我真正关注的对象其实并非女性和性,而是写作和文本。我研究这种文学的叙述方法,文本如何去表述它本身。此外,写作的意义还不止于文本本身,如何去理解写作本身,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我的书集中关注文本和写作这两点,简而言之,就是研究不一样的形式,不一样的文学,如何表达自身。我非常喜欢近距离的阅读和文本研究,做非常具体的考察。
我的这本专著选取了1840年到1910年间的六部青楼小说并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与以往学者关注这些小说的青楼女子不同,我在突出青楼这个场所的同时,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嫖客。我的目标是将文学批评与文本结构、历史相结合,以揭示这些小说虚构的自觉,证明各种版本在接受传播中的变化。因此,小说的虚构性和文本性是我研究的主题。虚构性是“语言的编码”(linguistic codes),也就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语义文本和内容详略等。而文本性即“书目的编码”(bibliographic codes),也就是出版印刷、不同版本中的文本布局等。我认为两者不可分割,书目的编码不仅是语言编码一个必要的条件,而且在创作与接受两个方向上都形塑语言编码。
访谈者说明:尽管上述研究成果对司马懿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但在英语世界里,真正从文学视角专门对晚清青楼小说进行系统研究的,司马懿可以说是第一位学者。她的专著《晚清红灯小说研究》分为序言和四章内容:
第一章为“文本和处境”。这一章也是后面三章的基础。主要梳理了三大领域的脉络:文学的分类,虚构的源流和晚清的文本性。第一部分,围绕“晚清”“妓女”和“青楼”等概念展开讨论,梳理介绍了相关研究。第二部分,则讨论明代短篇小说和明清之际才子佳人小说,以及18世纪后期著名小说《红楼梦》,这些对晚清青楼小说影响极大的小说。最后,她从关注“虚构性”转向“文本性”,这里司马懿对清代文本刻印技术的发展、文本的流通、包括在文本创作和传播过程中,禁书、作者的权利、相关角色,以及出版商等,都作了全面而有力的考察述论。
第二章为“叙事者的构架”。主要集中在叙事者的建构,论证了“叙事者与文本、叙事者与意寓的作者间的复杂关系是这类作品中虚构的中心。” (p. xxiv)
第三章为“情景中的特征”,分析了三部小说,以得出结论:19世纪小说的个性化反映在不同的层面,如诗歌、个性群体等,虽然个性次于情节等,不是小说最重要的关注点,但这一特征在21世纪已变得更加重要。多数小说凸显了作为一个建构的角色地位,因此给读者以“摹写与综合的双重意识”(p. 189)。
第四章“结构:文本的自我表征”并不代表一个“结构形式的综合调查”,而是一个核心观点进入几个相关领域的扩展。首先小说使用这样几个精心布局,如诗、酒戏和戏剧化的对话,组织它的文学结构,以建立人物性格的对立关系,密谋发展中标志阶段;和共时性的文本结构,即语言的与形象的插叙和文本混合结构前景性质,这本身也表明了在19世纪虚构文本整体变迁状态,与当时技术的进步,出版业的发展,叙事结构和虚构性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对20世纪青楼小说形成过程中叙事结构产生影响。司马懿将之与英格兰维多利亚时期进行比较,考察了定期书刊的出版业兴起(对小说)所带来的影响,并以《花月痕》的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她这项研究成果的突破是,重新评估了鲁迅压倒性的对十九世纪小说的评价及影响。该著最后一节集中在文本的物质性,这导致了对中国大陆最后出版的青楼小说版本有趣的反思。尽管与鲁迅的分类有所不同,但青楼小说出版系列一直被标以某种类型或强调其类属。司马懿对文本和它的出版史用心考察,提供了编辑对小说意识付诸影响的洞见。在她看来体裁是一个编辑实践的产物,即使她论证了该类小说的源流和特色,但司马懿并不承认青楼小说作为一种体裁或流派的地位。这个论证有力地批评了后鲁迅时代青楼小说在中国被贴上类型或流派标签的做法。但是,如第一章所引述的,这些青楼小说缺少丰富的来源,它们明显地参考其他青楼小说,叙事者相似的角色也都表明了青楼小说作者单一的写作模式。
西方学者如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和韩南已经对青楼小说中的叙事者、作者和文本的关系作过犀利的分析。如其他青楼小说研究一样,司马懿的研究亦重视文本与叙事的关系,并有力挑战了鲁迅对这类小说的评价。她的贡献不仅是对贯穿所有这类小说最初动力的自觉虚构性有新的洞见,而且在回溯青楼小说发展一直到中国“五四”这一时间段中,将叙事和文本系结在一起,这帮助她跨越了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学的裂口。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司马懿看重作者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她认为晚清青楼小说一直流行并多次再版的原因是这些小说远非一些失意文人的“下流”作品,而是在对待嫖客、妓女与文本关系本质上,它们扮演了一种挑衅者的角色,并对理解19世纪自我与文学价值的广泛变迁提供了洞识。总之,晚清青楼小说挑战了文学史的定论,激发了进一步研究这些小说艺术的未来前景。
问:您为何从研究中国晚清文学转向中国基督教研究?
答:关于转变,就是从晚清小说到现在的中国神学研究,我觉得是个转变,但是转变没那么大。我关注文学,并将研究文本和版本的这种方法运用到中国神学的研究中。我现在做的神学研究和正在写的书,都是有关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本研究。比如我研究徐宗泽,研究他刊登在《圣教杂志》上的文章,称为“随思随笔”,也就是他的笔记。我研究他的文本,对这些文本进行深入思考,因此读得特别仔细,非常注重细节。我对徐宗泽等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用文学方法诠释神学非常感兴趣。其实,我们研究神学不能脱离这些基督徒学者写作的文学方法,尽管他们用文学方法,但是表达还是要用神学的方法。如我研究赵紫宸的《耶稣传》,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说。除此之外,我也阅读杨慧林、刘小枫等人的作品,他们这些学者都很看重文学与神学的关系。我认为不能用西方的分类法来研究中国神学。神学在中国可以有很丰富的内容,如带有文学色彩的笔记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笔记是友谊,也是网络。另外,神学可以是有关任何主题的,而并非只是三一论或基督这样的议题。
再回到转变的话题,对我来说,这种转变主要是研究对象的转变,我运用这种方法从研究文学转到研究神学,我认为两者不能分开。这也是我现在所写的这本书的主题思想,我现在的这本书从文学角度研究中国神学。中国神学有非常丰厚的历史,因此中国神学不能仅用西方的形式来书写,也不能用西方的分类法来归类。因为中国神学就像徐宗泽的随笔,像赵紫宸的《耶稣传》(1935),是一种真正的本色化。中国神学必须用中国文学的形式,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来诠释神学的内容。因此人们必须学习这种形式,人们学习神学,书写神学。之前我研究文本,现在我更看重写作的形式,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尝试做的。当我关注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这群人,即关注书写的人,他们都是主流教会的人。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关注当代基督教的人物。此外,我现在正在翻译《汉语神学读本》,这本书是香港道风山杨熙楠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主编的,我负责翻译这本书,希望通过翻译,可以有更多的西方学者来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基督教。因为这本书里有很多古文,翻译起来比较慢。我希望可以利用接下来的这个安息年假完成这个工作。而明年我准备开始研究中国当代的基督文学作品。
访谈者说明:司马懿的新书已于2016年1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从其对赵紫宸《耶稣传》、徐宗泽《随思随笔》的研究,可窥见其对中国近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神学创作的研究路径。对于赵紫宸,司马懿更多地关注《耶稣传》作为小说的虚构和想象,她深入探究了文本结构与神学表达之间的关系。该章节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背景,司马懿在这一部分对赵紫宸个人生平经历和社会处境的矛盾性张力展开层层分析。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学术的真理和神学真理如何成为真实,这也是赵紫宸在《耶稣传》的序言中需要细思冥想的问题。可以说,在虚构与真实之间,虚构性是司马懿首要关注的问题。第二部分为全文的核心,针对赵紫宸的代表作《耶稣传》的内容展开分析。该部分又分为三个小节:第一小节“叙事的形式”,从标题即可清楚反映她将研究晚清小说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宗教或神学文本的研究中。在司马懿看来,赵紫宸在序言中所暗示的困境“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是一个深刻的矛盾。因为赵所思考的是,借着耶稣写自己的生平,他的出发点是写小说,而耶稣生平是以历史性方式建构的。正是存在着这样的深刻矛盾,所以整个文本叙事游动于评论和描述、第三人称和作者的声音之间,这种类型对于晚清小说的读者来说,显得非常熟悉。第二小节“弥赛亚”,则着重分析赵紫宸神学中的文学的想象。第三小节“阅读的土壤”,进一步分析晚清以降,小说对人们阅读方式和观念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神学的观念和表达。例如中国的游记小说,如徐霞客的作品如何影响赵紫宸对经典的阐释,这是她所关注的内容。最后一部分则是结论部分,司马懿认为,在20世纪20—30年代,赵紫宸与其他神学家一样,都面临着非基督教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他的神学亦强调科学、理性和基督教社会建设等方面。这是将宗教建基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人文和民主精神上,这些都在赵紫宸的《耶稣传》中得以反映。对赵紫宸而言,非基督教运动是要求宗教有更深呈现的一个信号,宗教需要寻求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总之,赵紫宸的论文和随笔呈现了十分不同的思想和关切。除了热衷于青年人的教育、国家经济等问题,赵氏的文本中还存在一个深层的潜流—革命思想,这在早期“弥赛亚”中已流露出强烈的痕迹。在1927年的一篇论文中,赵则公开地对国民革命军结束军阀割据从而统一中国,尤其是毛泽东发起的土地革命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她(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从坚固的过去转向憧憬的未来,……根据这样的信念,不仅政治体制需要一个激进的变革,伦理和社会体系也需要击碎再造,以适应现代国内国际的需要。自从1910年以来,整个国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已经出现了加速变革的过程,知识、社会、经济、政治甚至宗教正在经历着一系列临盆的阵痛。”①Zhao Zichen,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repr. in The Collected English Writings of Tsu Chen Chao, Vol.5, 1927, p.248.在其他地方,他写道:“我们相信通过普遍唤醒大众,国家正打造一个真正统一,为国家而战斗的人民,不是为政党的私利,而构成红色的统一战线”,“我们相信,通过分享大众尤其是我们国土上的农民在民族斗争中的牺牲,人性的救赎,尤其是我们自己,即将来临。”②In “Christian Faith in Chin’s Struggle for Freedom,” repr.in Ibid., pp.473, 472.
在对徐宗泽的研究上,司马懿也同样从文本和文学的进路关注徐宗泽的思想世界,进而关注与徐氏同时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世界。如果说赵紫宸在《耶稣传》中是通过一种文学的虚构和想象来呈现其左翼甚至激进社会革新思想,那么徐宗泽则是通过一种更为轻松自由的笔记短札形式,即《随思随笔》来表达其对中国社会命运的关切。在对这一文体的关注与分析中,司马懿突出表达一个“文本处境神学”(textual context theology)的思想或概念。她认为,通过对徐氏的笔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的文本,不可能无上下文处境或者非处境。处境神学不能仅仅是关于社会经济的处境,也可以是文本的处境。文本本身必须在自身的处境中被理解,而不仅仅是在作者的文化或社会政治处境中被理解。但在阅读和理解中国基督徒的写作过程中,文本的形式一直未能被重视。因为一旦排除文学的视阈,写作与特别文学形式间相互依赖或紧密的联系并不明显。当我们阅读中国神学,仅限于像阅读西方神学那样的系统文本时,实际上就陷入了中国基督徒如何表达和理解上帝的一个基本误区。将中国神学的讨论与交流,限定于传统的文本形式,实际上是限定了神学本身,也阻碍了与现代中国神学家的交流。
总之,司马懿从文本和文学的路径出发研究近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及其神学思想,她的研究与以往学者不同。可以说,她的方法超越了前贤,开辟一个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
问:可否谈谈您对汉学研究的看法,以及您对汉语神学研究未来的展望。
答:对于汉学,很多人认为外国人做的是汉学,中国人做的是国学,而我并不这样认为。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不愿意区分外国人做的汉学还是中国人做的国学。我认为归类是荒谬的,我不喜欢将东方和西方分割开来的做法,也不太喜欢汉学与国学之分。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一定有区别,如胡小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这本书,所有的西方人写文本的转变,我没有研究这本书的社会与群体生态层面。当我看完这本书,我很关注版本的层面。比如,我读了很多版本的《花月痕》,从1880年至1990年之间的版本,我研究同一本书跨越一百年间的不同版本。所以我的书里面研究文本的出版、文本的对比(comparetext)和文本的变换。
我认为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在历史和哲学领域,中国基督教研究都受了很多限制,但现在那么多人做各种不同的研究。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做了很多有意思的研究。因此我对中国青年一代学人的发展非常乐观。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限制,有青年学者研究圣经,语言是最大的障碍,所以需要更好的训练。像丁光训主教那个时代的牧者、包括现在的牧师王艾明他们都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对于中国教会而言,面临的问题是,现在的基督徒知识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牧者也需要提升自己的素养。乡村里的牧师亟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然文盲的牧者如何能牧养他们的信徒?城市里面的牧者更是如此,不仅需要有正直的人格、属灵的生命,同时还要有较高水平的学识。如果城市里普通信徒的教育水平比牧师还要高,那就会出现问题,因为牧师需要向信徒解释圣经。因此,中国的神学院需要培养高水平的学生,金陵神学院的责任尤其重大,正如金陵一直在做的那样。中国近代的很多牧师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对于研究神学的学者而言,尤其需要具备国际视野,所做的研究也一定要和西方对话。我想刚才说的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解决的事情,教育是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但是现在需要开始。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你会发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那样的年代已经达到了现在看来是很高的水平,我觉得那是一段非常值得去重新思考的历史。最后,我想表达的是,我非常乐观,对汉语神学研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司马懿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其中中文书更是占据了其中一整个书架,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世情小说史》等。访谈期间,她也向笔者介绍了一些西方其他的研究成果,如叶凯蒂(Catherine Yeh)的《上海之爱:1850—1910年间的妓女、文人与娱乐文化》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Entertainment Culture,1850-1910)等研究中国晚清文学的作品。在结束访谈前,她还特别拿出一本《汉英四书》,称这本书对于她有特别的意义:
还记得1992年至1993年我在贵州大学花溪校区学习,当时在贵大有6到8个外国人,都是来学中文的。按照规定我们不能参加本科生的学习,但贵大有非常好的老师,他们到我们的宿舍来一对一地教我们。我现在还珍藏了一本理雅各的《汉英四书》,是贵州大学一位老师送给我的,在书的扉页上,他用遒劲的钢笔字专门写了一段话:“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我头也不回,汗也不擦,拼命地爬上山去。半山了,努力!努力往上跑!录胡适博士《上山》诗中句赠司马懿同学。中国贵州大学徐明德1992年。”
司马懿是一位胸怀远见、充满睿智的青年汉学家。她为人处世真诚热情,对每个人都有细微之处的关怀。她热爱学术研究,并全情投入于她所钟爱的研究领域。她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精通中、法、俄三语,并能熟练阅读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可以说,她所受的学术训练和具备的语言能力,加上她敏捷独到的思维和跨越中西的国际视阈,已令她成为海外汉学研究中的佼佼者。希望她永远不要停下来,在学术的道路上,一直努力往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