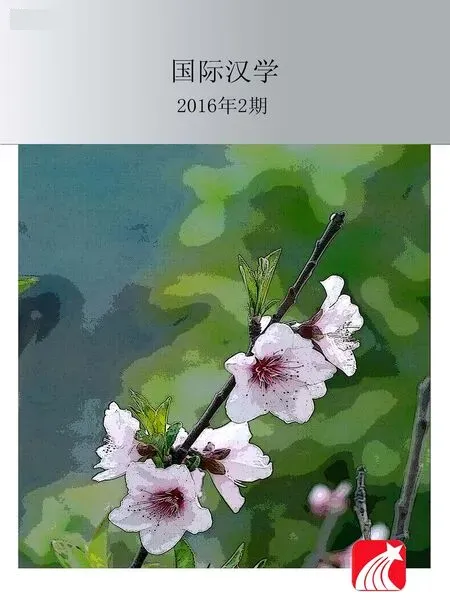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季进教授访谈录
访谈者:邓 楚、许 路
访谈按语:2012年12月15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研究—以20世纪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举办。借苏州大学季进教授来北外主持讨论之机,笔者对季进教授就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访谈。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和钱锺书研究。
访谈者:季老师,您好!您这次来北京是为了参加北外举办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及影响研究—以20世纪为中心”研讨会,此次会议对翻译、现当代文学等议题也有所涉及。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概况?有哪些领域值得关注?
季进:这是一个很大的论题,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经过了近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蔚为可观的规模,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也有着各自的特色,很难做简单的概括,我还是说说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情况吧,这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成果最丰富,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中国文学翻译来看,重要作品、论著的英译本不断问世,其中既包括对较少受关注的作品的引进,也有对经典译本的翻新。最有影响的译介成果是各种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如孙康宜、苏源熙(Haun Saussy)合编的《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2000),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刘绍铭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007)等,为普通读者接受中国文学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在编写文学史方面,总体观照和分时代、文类概论的著作都不少,尤其是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2)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0)集中了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流学者,无论以质还是以量来衡量都是当之无愧的皇皇巨著。
而在专精性的学术研究领域,除了已为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文学研究名家外,学术新秀也不断涌现。这些学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积极回应时代与社会的要求,或积极寻觅崭新的研究领域、或强调新理论或跨学科的方法,使美国汉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形态。比如魏爱莲(Ellen Widmer)的《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06), 高 彦 颐(Dorothy Ko)的《闺阁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1995)等女性主义理论立场的彰显,王斑的《历史的崇高形象》(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97)、刘 康的《美学与马克思主义》(Aesthetics and Marxism:Chinese Aesthetic Marxists and Their Western Contemporaries,2000)等对美学意识形态的观照,杜润德(Stephen W. Durrant)的《模糊的镜子—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1995)、裴碧兰(Deborah Lynn Porter)的《从大洪水到著述:神话、历史与中国小说的诞生》(From Deluge to Discourse: Myth, Histor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Fiction,1996)、何复平(Mark Halperin)的《走出回廊—宋代中国对佛教的文人透视》(Out of the Cloister: 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 960-1279,2006)等对文学与历史与宗教的跨学科阐释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汉学学者在视觉文化领域的研究,它可算是1990年以来海外汉学研究中最受瞩目的一支力量。海外汉学视野下的视觉文化研究一方面尝试着跨越原有的“艺术史研究”学科边界,另一方面也在尝试走向跨文化的对话;它一方面企图超越视觉感官、将研究置于更深更广的领域,另一方面也通过线条、色彩、布局等“表面文章”挖掘特定历史中的意识形态。视觉文本已然成为融文化、政治、经济、历史、科技等领域于一体的开放性批评范畴,很值得关注。
访谈者: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译介与研究如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成果?
季进: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关注起步较晚,最近几年发展较快。197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整理出版了《外国研究中国》《国外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情况》等,编著了《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等工具书,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成果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海外重要学术成果陆续翻译出版。就专著而言,近年来海外学者的研究著作已逐步成为出版热点。除了宇文所安、李欧梵、王德威等著名学者的著述得到全面译介之外,在海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者的代表作也纷纷出版,如孙康宜的《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Six Dynasties Poetry,1986)、高友工和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2005)、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1993)、梅维恒的《唐代变文》(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1989)等;就选集而言,有乐黛云、陈珏编选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Jr.)编选的《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浦安迪(Andrew H. Plaks)的《浦安迪自选集》、莫砺锋编的《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等。就译丛而言,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着眼点较广,所出书籍兼顾文学、历史、社会文化多个方面;我和王尧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上海三联书店)比较系统地呈现了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与面向;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则侧重于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些是国内学者负责编选的系列丛书。而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引进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主编、收录不少汉学名家成名作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已有数本中译版面世,我认为是相当值得关注的。
其次是国内学者开始了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其中又可大略分成几类:一是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丛书,比如傅璇琮和周发祥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花城出版社),此外张西平主编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大象出版社),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学苑出版社)等也涉及不少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著作;二是概论性或专题性的研究专著,前者有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葛桂录的《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王晓路主编《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等等,后者有江岚的《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徐志啸的《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顾钧的《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姜智芹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等等;三是出现了一批专业工具书,如中国社科院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胡志挥编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索引手册》、安平秋和安乐哲(Roger T. Ames)编的《北美汉学家辞典》,最新的有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出版的系列工具书,如汪次昕编《英译中文诗词曲索引:五代至清末》、倪豪士编《唐代文学西文论著选目》、汪次昕和邱冬银编《英译中文新诗索引,1917—1995》以及雷金庆(Kam Louie)和李栏(Louise Edwards)编写、1993年出版的Bibliography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Critiqu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1945—1992;四是大批相关学术期刊的创办与研究论文的发表,《世界汉学》《国际汉学》《汉学研究》《清华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读书》《汉学研究通讯》等刊物,都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海外中国文学传播的研究论文。2000年以来,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有明显增多的趋势。
访谈者: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认识与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
季进:海外汉学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而我们对海外学者成果的研究才不过数十年,盲点和误区是必然存在的。我认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对于海外汉学没有全方位的认识与介绍。大量的海外研究成果尚未译介,目前得到引进的只占很小的比例。不进行必要的了解,研究与评论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一是我们对一些汉学家的思想及论著缺乏系统性的译介,缺乏对海外学者的知识谱系、思想变化的动态考察,更没有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衡量其地位和价值,因此我们时常以偏概全地把单部作品甚至论述的断片当成一个研究者全部的理论思想,或者因陷入“我执”境地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周蕾(Rey Chow)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周蕾是探讨性别问题、香港形象、视觉文化的先驱学者,她不仅出版了多部专著,而且在多份理论批评与研究刊物上频频发表文章,和宇文所安、张隆溪等学者之间也有过理论的交锋和论辩。作为一个生于香港、活跃于美国学界的女性,她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边缘者的立场上,从个人经历出发,综合运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武器,着力于揭示并批判西方社会和主流文化对“中国”单一、稳定的身份认识,恢复中国文学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然而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华裔学者的著述,仅有一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1991)2008年在大陆出版。国内学界对周蕾的兴趣也主要集中于一些颇具争议性的章节,比如《原初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1995)中对鲁迅笔下“幻灯片放映”事件的探讨,不仅没能理解其独创性论点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反而连续出现了好几篇批评性的文章。周蕾的理论当然有其不足,完全可以商榷与批评,但是比起匆忙地为她打上“阐释过度”的标签,深入地介绍周蕾的研究立场和体系显然更为重要,也更为有益。
二是在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认知上存在盲区。以地理盲区为例,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荷兰、瑞典、捷克等国的汉学研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独有的特色。由于20世纪以来英语文化圈的空前扩大,以及“典范转移”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风向标,国内学界对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对非英语国家地区的研究成果关注不足,翻译出版的成果也是相当有限。比如荷兰莱顿大学早在1875年就创设了汉学讲席,执教于莱顿的佛克马(Douwe W. Fokkema,1931—2011)也是一位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汉学家,而我们对莱顿这个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显然缺乏更多认识。在法国,讨论中国文学的有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等本土学者,也有如程抱一这些来自中国的研究力量,但目前国内全面展现法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情况的成果相对较少,只有钱林森主编的三卷本《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等少量的著作。再比如捷克的汉学研究在欧洲一直颇有影响,我们只知道普实克(Jaruslav Průšek,1906—1980)及其“布拉格学派”,但对捷克的中国文学研究、对“布拉格学派”的形成、演变其实不甚了然。2012年5月,我请布拉格查理大学的汉学中心主任罗然(Olga Lomová)教授来做了一次讲座,主题为《鲁道夫·德沃夏克(Rudolf Dvrák,1820—1860):查理大学与中国最早的学术相遇》—如果没有罗然的讲座,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普实克之前还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捷克汉学家。
这其中当然有语言层面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视野的局限。我们国内的学者习惯于关注热点现象、知名人物,习惯于关注一个固定的语言文化圈,但是缺少将各国各地区的成果作为一个统一有机体进行考量的自觉意识,也不会主动地同海外学者对话,形成良性互动。国内到现在都没有一份较为全面的海外中国文学翻译作品与研究著作的目录,对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的发展脉络、基本特点、总体成就与经验不足等,还缺少深入的分析评述,更未能从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高度,对此展开总体研究与深入反思。所以我们在加大译介力度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论述,力争从跨文化研究视野考察与评估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特殊作用,并阐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对国内学界的借鉴意义。
访谈者:在国内学界,不仅有盛赞海外汉学的声音,也有着对它的批评和质疑。比如有些评论者认为,一些海外学者完全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脱离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而国内的研究者亦对其盲目推崇,结果形成了一种褊狭的“汉学主义”倾向。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季进:我想,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海外汉学成果的重视和引进并不代表它们就比国内学者的作品要来得“优秀”,我们也不必将海外学者的立场或方法标榜为唯一“正确”的研究之道。但我也不赞同将海外汉学与“汉学主义”简单等同,“汉学主义”概念的理论推演似乎要远大于海外汉学的研究实际。
单纯从学理上来看,当某种思潮或倾向包含一套独立的解释概念和批评方法并构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时,我们为之冠名以“主义”是比较合适的。而目前被称作“汉学主义”的学界现象似乎并不总是符合以上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回答:到底什么是“汉学主义”?这种所谓的“汉学主义”潮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会在何时逆转、缘何而逆转?它的背后潜藏了怎样的权力话语和知识取向?当然,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是,我们站在何种立场上提出这种批评,是基于不同学术话语的对谈、不同文化语境的协商、还是不同地缘之间的跨国流通?或者换一种更为直接的说法: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术范围内谈论中西差异呢,还是在不同的文化间讨论同一个学术?这个基础预设,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学术的立场和界限到底在哪里,其发展和新变的依据又是什么,以及支持这种学术的动力机制和意识结构是什么。我们与其急着用“汉学主义”指责海外汉学,不如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我觉得,与其纠缠于“汉学主义”的争论,不如将海外汉学与本土研究都视为某种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它是指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传统与资源被广泛分享,人们在深入地理解、探讨和展示其中某些方面时所形成的一种学术联结。它取代了那种实存的人际关系和学术网络,转而强调虚拟的同一性的时空构造。“想象”是其中的关键词,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学术共同体”的理念。我们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反思,也就是试图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性描述和现象铺陈,力图将海外与国内的研究状况、特点、历史都视为统一的整体进行比较性的深挖,以一种“共同体”的学术理念,来看待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所引起的全球性文学与文化反思和学术生态的发展。
访谈者: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它?对于海外汉学,您是如何理解的?
季进:所谓海外汉学,指的是“中国”地理国界与学术体系之外的中国想象与研究,这种研究以及我们对其进行的再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实践,也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20世纪以来全世界的社会历史语境变得空前复杂多变,使得在中西文化与学术彼此紧密联系又相互激烈碰撞中产生的海外汉学研究,就像王德威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多重话语冲突、对话、融合、共生的场所,是历史、虚构、民族、国家、性别、主体、情感、日常生活、离散、族裔、主权、霸权互动的空间,是学科对话、理论旅行,展示“再现”和“代表”的政治的理想对象。
海外学者的学术方法、思维模式、言说理论以及其中体现出来的复杂的“话语权力”,本身即是对中西文学交流的复杂面向的一种说明。这些研究不免会出现“六经注我”的过度解读倾向,也有可能导向牺牲文本的原有特性、以“文化研究”大包大揽,也许还会脱离中国现实语境和史料基础,把中国文学文本变成西方理论预设的某种“佐证”。但是,正是由于海外汉学在学术视野、对象选取、方法抉择、理论取向等方面,与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异其趣,才呈现出它独特的学术魅力。因此,我们如何坚持自己的主体性,对海外汉学展开扎实而深入的再研究,才是我们所面临的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对于海外汉学,我认为不仅要将其视为一个研究对象,更要将其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富于启示性的“方法”与“机制”。我们应当超越对海外汉学成果简单的价值评述,要发现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把它变成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媒介和通道:既关心“海外汉学”探讨了什么、阐述了什么,更要阐明其挑动了什么、质疑了什么,又释放了什么;特别是这些成果在反馈到国内时,对国内的研究格局和书写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刺激和影响,在何种意义上推动了文学研究的跨文化对话进程。我们也应当将海外汉学理解为一种机制。这个理念在于阐明海外汉学研究不单具备丰厚的学术价值,也拥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效应。借着海外学术界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历史,我们得以反思和正视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向海外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优缺利弊,换言之,它变身为一种指导机制和测试体系,能够帮助我们不断修缮、完备本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达到文化交流的和谐有序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要把全世界范围的(当然也要把我们本国学术界包括在内)相关研究视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讨论海外汉学界如何与中国学术界展开互动,如何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证、互补、互识的双边对等关系,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建立完善的认识论主体,充分论证文化传播对促成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融合、对话的价值、意义,也考察其可能潜藏的意识形态运作和霸权干预,真正地实现中国人文学术的范式转型。
访谈者:您是研究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在您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目前在海外的接受情况是怎样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到底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季进:这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崛起,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也从单一的政治、经济与外交领域转向文学文化领域,同时中国政府也为塑造正面文学与文化形象而实施了文化走出去战略,加之当代作品不断获得国际奖项,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影响与地位显然有所改善,中外文学的交流也日益成熟。但中外文学交流依然很明显地存在不平等的现状。我们对西方文学的关注与熟悉程度,永远与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相距甚远。西方出版社每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远远无法和我们每年引进、出版的西方文学作品相比肩。透过这一现象,我们看到的是历经世代累积所造成的中西经济、政治、文化实力的悬殊差距。
其次,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大,但其实还是属于绝对的边缘化、小众化,很难成为大众畅销读物。这种情况可能欧洲比美国要好一些、诗歌的命运也比小说要好一些。王德威曾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学翻译系列”,囊括了《私人生活》《我爱美元》《马桥词典》《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长恨歌》等拥有一定影响力的当代文学作品,译作也皆是出自名家高手,但是总体而言销量极为有限,更多的是进入大学图书馆作为专业研究者的阅读材料。所幸王德威未必看重眼下的市场收益,而更多地从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这些译本的文学史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才会逐渐彰显出来。
西方的读者在何种层面上接受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接受了哪些现当代文学作品?这虽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分析的课题,但我们很轻易就能发现,在热闹的文学输出的背后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我们对现在媒体过于乐观的宣传,也要保持冷静审慎的态度。
访谈者:莫言小说的英文译者葛浩文是英语世界最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之一,莫言的创作能得到国际认可,葛浩文绝对是功不可没的。您认为从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谁来“操刀”更为合适?
季进:如果是为了更广泛地获取海外读者的认同,我认为也许由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来完成翻译工作比较合适。这并不是在怀疑国内众多翻译家的素养和能力,我也没有资格否认他们的专业功底,但是文学作品的翻译绝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符码间的精准转换,更何况植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间本身就不可能有绝对的意义对等。钱锺书谈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进入“化境”,就是说在深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将原来的作品的情感意旨自然而然地与新的语言文化融合在一起。葛浩文的母语是英语,他一定比我们更了解鲜活泼辣的、“活着的”本土英语,而且他也一定比我们更清楚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欣赏什么、排斥什么。他可以挑选最符合英语读者理解习惯的词汇与表达方式,而且他也能依据读者的需要调整小说内容—事实上,葛浩文对莫言的小说也确实有所删改,也许有批评者认为作为翻译者葛浩文不够“忠实”,但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英美当代文学的外衣,我想这恐怕是葛浩文译本受到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国内的译者很难与之比肩的巨大优势。
在时下的中国,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似乎成为了一种潮流。翻译实践不仅仅是为了“出口”本国文学,但无论如何,没有读者的翻译是无效的交流。对于国家斥巨资组织各种典籍或经典作品的外译“工程”,我们一方面乐观其成,一方面也应当对其效果持保留态度。以前中国政府也推出过“熊猫丛书”,翻译介绍了从古至今的数百部中国文学作品,从整体质量上来讲还是不错的。可是这套丛书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出版之后悄无声息,有的永远躺在驻外使馆的地下室蒙上尘埃蛛网、遭受湿气或者蠹虫的侵袭,极少数命运稍好的译本进入大学图书馆,被相关研究者翻阅,但总体来讲对于西方大众读者并没造成多大的触动。当代文学的翻译,更为有效的方式可能还是得靠以西方语言为母语的国外专业翻译家或汉学家,由他们自主选择、自主翻译的作品,可能更容易获得西方读者的青睐,争取更多的普通读者。
访谈者: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文的数量其实并不少,但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却不多,您所说的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真正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呢?
季进: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海外影响力不尽如人意,我想最大的原因应该还是语言文化的天然隔阂。我们看来十分优美动人的篇章,也许在外国读者眼中就会变成连篇累牍、不知所云的“天书”。就像我在上一个问题中所回答的那样,译者也许可以费尽心思越过语言的关卡,但再优秀的译者也不一定就能跨过文化的鸿沟。西方国家有着发达而自足的文学传统,有着自己的阅读趣味与评判标准,再加上一些复杂的现实原因,导致国外读者对外来的文学有一定的排斥,这是第二个原因。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发展得也不充分,在整体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上确实难以与西方抗衡,这是第三个原因。除此以外,西方读者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对中国的固有偏见,在“东方主义”式的凝视中,中国文学不可避免地变成被想象、被审视、被阅读的对象,甚至被认为是与西方决然不同的存在。西方读者未必对当下中国人的真实经验与需求感兴趣,而中国文学本身的巨大变化,有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与想象的范围。
如何真正有效地让我们的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被西方读者接受,我想这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使命。虽然文学文化的交流途径并不仅限一种,但文本的翻译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所以我们需要重视翻译工作,如果有可能,最好能够与国外的翻译者进行合作。在其他技术层面我们也可以去创造交流的可能,比如组织文学交流活动,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展会,使文学作品更频繁地参与到世界性的文学生产、流通与阅读中去。这项工作不是只靠若干高校、个人或组织就能完成的,国家的支持、社会力量的参与十分必要,而且争取海外出版商、高校、相关组织机构甚至是公司财团的帮助,对于扩大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抱着特别功利性的目的,也不应奢求我们的努力在短时间内就能立竿见影,更不必为了迎合国外的某种趣味而刻意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边缘化地位的确立,历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要让西方读者认识中国文学、消除之前的偏见,也同样需要经过慢慢的积累才可能逐步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所展现的独特的认识与情感,以及它立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现实所发生的变化,这本身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独特定位。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个性、成为西方所熟悉所想象的“中国文学”,那又会被西方无情抛弃。倒是你长期坚守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和价值,也许某一天终将为西方读者所认可。
访谈者:我们经常谈论中外文学关系,谈论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其实从比较文学的立场来看,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您能不能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季进: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有学者在提及“世界文学”时遗漏中国文学的存在,只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学到底要以何种面貌居于“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我认为,在强调全球化、强调资本与商品的跨国流通、强调普世价值的今天,更应当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最起码的中国立场。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那就很容易走向浅薄的全球普世主义,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削足适履地置于“与全球化接轨”的想象之中。但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文化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你想方设法和别人保持一致,这也许会比较容易获得接纳,但没有差别意味着你不能做出独到的贡献,而且和他人一样的特征仅仅是模仿得来,没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所以你也不大可能超越别人。时间一长这种行为就会变成慢性自杀,没有个性的文学也就没有活力,终将被历史淡忘。我们并不是要故步自封、和全球化的潮流相抗衡,而是希望承认“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生态系统的内在多样性。
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写了一本《何谓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3),从全球化的角度将“世界文学”理解为世界范围内文学的生产、流通和翻译的过程。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与其他各民族、各语际的文学一起,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学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整个世界文学应该是一种不断交流与联系的状态,哪怕是一种想象性的联系。每个国别文学都只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即使我们总是讨论国别文学,将其与其他文学相区别,但仍然无法回避它与世界文学的联系。我在跟宇文所安做访谈时,他也曾经提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应该成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宝贵遗产。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强调中国文学是中国独有的东西,而是应该把《红楼梦》与《堂吉诃德》都视为同等伟大的小说,使中国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我个人对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是比较赞同的。中国文学本身就代表了世界文学的一个面向,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面向。中国作家用独特的语言文字和表达方式,写下自己对国家民族、对这个世界、还有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独特感受,以自己个体化的经验去丰富全体人类的经验,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去为世界文学共同体增添色彩,这样的意义与价值,不需要借助“被译成几国文字”“在海外销量如何”或是“获得哪些国际奖项”就可以肯定—有人曾问,莫言获奖可否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成功?这个问题也许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中国现当代文学本来就被包含在世界之内,哪里来的“里外”之分,又怎么会需要“走出去”呢?
其实,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文学、文化研究及其相应的理论和学术规范,也是作为一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与渗透。我们如何重返中国文学的传统,丰富自身的文学实践,以独特的实践参与到世界文学的进程之中,既不要遗失中国文化的固有血脉,又不会脱离世界文学的谱系,从而催生中国文学的内爆,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我觉得这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访谈者:最后能不能介绍一下您主持的“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还有您最近在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呢?
季进:“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是2005年成立的,它的创立与发展离不开李欧梵教授的关心与支持。2004年我应李欧梵教授之邀在哈佛大学交流访学,正好李欧梵教授从哈佛荣休,他就将自己的藏书、手稿及一些影像录音资料全部慷慨地赠给了我们,以此为契机,我们成立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并邀请他担任名誉主任,此后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出版与交流活动,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心是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这正好跟北外、华师大等海外汉学研究重镇的研究重心形成了互补。这些年来,我们举办了数十场学术讲座,邀请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来苏州讲学交流,宇文所安、艾朗诺(Ronald Egan)、高利克(Marián Gálik)、罗然、顾彬(Wolfgang Kubin)、伊维德(Wilt Idema)、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田晓菲、瓦格纳(Rudolf G. Wagner)、李欧梵、王德威、张隆溪、奚密、叶凯蒂、王斑、张英进、黄心村等都来讲过,影响不小。我们还出了一本《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
在海内外学者的支持下,我们还策划出版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试图较全面地呈现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及趋向。现在正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和英文版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系列文选。此外,我们还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先后举办了 “中世文学的世界:汉魏六朝唐宋研究的新视域与新路径”国际学术论坛和“学术共同体中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学术会议。此外,我们还有一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zwwhgx.com),除了介绍我们自己的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与最新消息外,也致力于整合汉学研究网络资源,发布相关领域的最新消息。可惜现在精力不够,网站建设受到影响。
至于我本人,近些年主要的研究领域还是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今年会完成相关的国家社科和教育部课题。去年我们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我主要承担“英语卷子课题”的任务。此外,我想和同事、朋友合作编写一本关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经典的导读教材,希望以此普及一些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础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