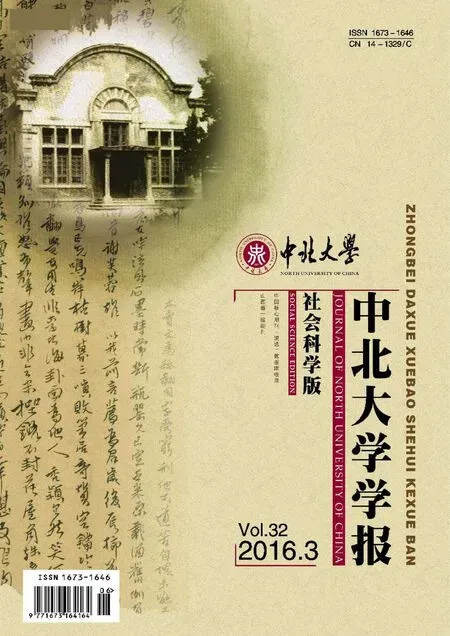从边缘人到“经济精英”的转型
——对浙东GM村乡村混混生存机制的考察
顾豪迈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5)
从边缘人到“经济精英”的转型
——对浙东GM村乡村混混生存机制的考察
顾豪迈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乡村灰色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以乡村混混为主体的“乡村灰色化”现象十分严重。 乡村混混群体运用灰色手段攫取大量国家建设性资源, 迅速完成从村庄边缘人物到村庄经济精英的转变。 乡村混混“精英化”的转变, 给村庄的道德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如何遏制“农村灰色化”、 防止国家建设性资源流失、 推进新农村建设、 重建乡村秩序, 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关键词:渐东GM村; 乡村混混; 生存机制; 生命史; 互动模式; 乡村秩序变迁
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国家层面来看, 这一战略有利于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从农民个体层面来看, 这一战略有利于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从而使9亿农民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但是, 正如任何事物的成长发展都非一帆风顺一样, 新农村建设的开展, 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由于片面强调基础设施建设、 村容村貌整治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农村缺少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建设, “乡村灰色化”现象十分严重。
“乡村灰色化”是指乡村社会受到灰社会力量的影响不断增强, 以至于影响到一般农民群众生产与生活秩序的社会过程。 灰社会力量指的是乡村混混群体。 乡村混混群体, 指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运用各种灰色手段攫取了大量国家建设性资源, 迅速完成了从村庄边缘人物到村庄经济精英的转变。 这一转变表面上是乡村混混通过努力争取生存空间与获得意义存在的结果, 实质上是转型期乡村秩序畸变的表现。 如何遏制“乡村灰色化”、 推进新农村建设、 重建乡村秩序, 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GM村为调研地点, 就乡村混混由村庄边缘人物到村庄精英的生命史进行考察, 并对乡村混混在村庄生活中与乡村基层组织、 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互动模式进行分析, 从而对以GM 村为代表的工业化农村地区的混混的生存机制有所界定, 同时透视转型期工业化农村秩序的变迁, 并尝试为遏制“乡村灰色化”提出解决的路径。
1何谓乡村混混
乡村混混是指既不按正常的社会方式谋生,也不像黑社会那样公然通过严密的组织危害社会,而是用灰色的手段谋取灰色利益,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乡村各种社会关系, 支配乡村社会秩序, 并因此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一种基础的群体。
20世纪80年代, 我国人民公社体制逐步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 由此, 农民的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完全束缚于土地的时代一去不返, 他们获得了一些自由。 农民的时间不再被国家制度强制规定, 可以自由支配, 这导致他们开始了身体流动。 与此同时, 革命理想主义在乡村也开始退潮, 农民个人与村庄集体之间原有的紧密关系也逐渐松弛, 村庄集体对农民事无巨细的控制力随之下降。 可见, 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 为乡村混混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在农村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混混的生命史有着显著的不同,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具有沿海地理优势和良好乡村工业基础的浙东GM村, 大部分村民的生活是忙碌的,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人的行为模式显得有些另类。 他们喜欢像没有具体目的的野马一样在村庄里东游西荡。 他们聚在一起, 有自己独特的“玩耍”方式, 或躲在草垛后面打牌娱乐, 或在晒谷场上打弹珠, 或切磋“武功秘笈”。 他们的生存之道也往往伴随一些“流浪”的行为。 他们没有正式的工作, 对生活也没有长远的打算, 在游荡玩耍之余通过偷窃、 敲诈等手段谋生。 随着1983年 “严打”的开始, 乡村混混才逐渐被压制下去。
20世纪90 年代, GM村的混混对于“严打”仍心有余悸, 担心自己逞一时之勇而引来牢狱之灾, 不敢过于猖狂。 再加上, 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争勇斗狠、 偷鸡摸狗并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只会拉开与其他勤劳智慧的村民之间的差距。 所以, 大部分混混纷纷在1980年退出江湖, 开始走上了勤劳致富、 合法经营的道路。 由此, GM村的乡村江湖暂时衰落。
进入21世纪之后, 特别是2004年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后, 乡村混混的生命轨迹又发生了一些转变。 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后, 他们或是运用暴力和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行承包工程项目, 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或是与乡村基层组织结成利益联盟, 协助解决拆迁钉子户等棘手问题, 换取现实利益的回报。 通过各种灰色手段隐秘蚕食了国家输送到农村的大量资源和利益后, GM村的混混迅速完成了从村庄边缘人物到村庄经济精英的转变。 村民对乡村混混的道德评价由此开始模糊, 甚至反转。 在话语表征体系中, 乡村混混实现了实质性的转变。 最初, 在村民们看来, 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地痞”“流氓”, 他们在道义上被贴上了不光彩的标签。 如今, 村民开始将他们唤作“有本事的人”, 并开始慢慢接受他们, 甚至主动在生活中巴结他们。 乡村混混成为了村庄中“有面子”的人。
2乡村混混的生活世界
生活是生命的展开形式和存续形式,是一种活动过程,是一系列历经时间与空间的流动。 一旦这种流动停止, 生活便告结束。 而生活世界就是由生活过程及其结果所构成的物理空间(外在-生成世界)和起于心意以内的由己性的意义世界(内在-原生形态世界)。[1]人要想实现意义世界的现实化, 则需基于在现实社会中与他人的互动。 在互动的过程中, 人们实现着各自的意义世界, 同时又重新构造了其中的价值要素。 通过与乡村基层组织、 村民和外来务工者的互动, 乡村混混确立了自己的村庄精英地位。 通过窥探乡村混混的生活世界, 我们可以发现转型期以GM村为代表的工业化农村地区的道德话语变迁、 乡村秩序变迁以及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
2.1乡村混混与乡村基层组织
据调查可知, 当地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等乡村基层组织与混混之间的互动模式基本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
由于税费改革, 基层组织的财政收入大减, 治理能力随之降低。 再加上基层组织不断精简机构、 撤乡并镇, 对乡村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不断下降, 呈现出相对“悬浮”的状态。 而基层组织面临的处理钉子户、 维稳等行政压力却有增无减。
在新农村拆迁改造过程中, 钉子户是基层组织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对象。 概括来说, 钉子户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维权户”, 他们以法律和政策为依据, 声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因此拒不拆迁; 另一种是“无理户”, 他们的诉求并无道理, 仅仅试图通过与政府不合作来谋取更多的利益。[2]如若不对这些人进行适当性处理, 政府的社会建设和财政收入将无法实现, 村干部的政绩考核势必也要受到影响。 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 就意味着要加大对村民的经济补偿, 这无疑将压缩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收入。 所以, 在当前合理合法的治理手段缺失、 治理能力弱化以及维权话语笼罩的情况下, 基层组织也就被迫和混混结成利益的同盟。
由于基层组织依赖乡村混混进行乡村治理,因而不得不对他们保持“战略性的容忍”,并给予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回报。乡镇政府为了收买一个叫金国(化名)的乡村混混,就将MZ大道的建设项目承包给他。但是完工不到半年,路面就出现了严重的破损情况。道路周边的村民都在背后议论纷纷,认为金国一定在修路过程中偷工减料,捞了不少好处。
此外混混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 通常不会明目张胆地实施犯罪行为, 而只是小错不断, 这也使得基层组织无法对乡村混混进行有效的打击和压制。
在传统中国, 国家权力止于县, 县以下的乡村日常秩序主要依赖士绅阶层进行管理。 华裔美籍学者费正清指出, 在过去的一千年间, 士绅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活, 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并履行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责。[3]20-24而当下, 正如罗兴佐在《第三种力量》一文中所说, 介入了乡村治理的却是乡村混混。 乡村混混已经成为了转型期乡村治理的隐性基础[4]、 乡村治理的非正式人员。 乡村混混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 乡村秩序陷入混乱, 基层治理“内卷化”进一步加重。 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在后文中将予以详细阐述。
2.2乡村混混与村民
生活于乡村的乡村混混, 其朝夕相处的对象是本地的村民。 从与村民的互动中, 很能显示他们的生存状态。 一般来说, 只要不涉及利益上的冲突, 混混和村民还是能和睦相处的。 他们在日常交往中对村民比较随和客气, 也不占什么小便宜, 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出面帮忙。
实际上, 这种表面上遵守村庄人际交往原则的做法正是乡村混混的聪明之处。 如果为了一点日常小利益, 就动辄暴力相向, 迟早会因下手过重而出事;过于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 也容易触犯国家治安的底线, 招来基层组织的毁灭性打击。[5]但是, 这种客气只是表面上的。 一旦村民涉及“涉及他们”及其近亲属的利益, 或者是妨碍了混混“事业”发展的核心利益, 他们往往就不再客气。
村民在与乡村混混的互动中对他们则是又羡慕又害怕。 虽然村民们对他们致富的方式口头上表示厌恶, 称其为 “拿不上台面的勾当”, 但是在心里却羡慕他们是“有本事、 有能力的能人”。 当遇到和他们发生利益冲突时, 除了特别犟的村民, 一般村民出于人身安全考虑, 都会主动让步。 一个叫桂芬(化名)的村民在拆迁过程中就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老房子根本就没赔足钱, 但乡村混混把她家的水电都掐掉了, 她只好搬了出来。 因为她考虑到他们人长得高大、 交往圈子又复杂, 只好抱着吃亏换平安的态度任由混混们胡作非为。
由此可见, 在村民眼里, 乡村混混终究不可能是“好人”, 而属于“坏人”之列;他们是“有面子”的人, 但不是有威望的人。
2.3乡村混混与外来务工人员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 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涌入GM村, 使该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 全村共有农户1 067户, 村民2 557人, 登记在册的进城务工人员4 000多人。 村民对于外事务工人员这一隐性暴力团伙的惧怕原因在于: 首先, 村庄的道德约束对他们毫无效力, 使得他们做起事来毫无忌惮, 下手较狠;其次, 他们大都居无定所, 村民若在冲突中遭到伤害, 很难找到当事人算账; 最后, 老乡之间互帮互助的意识较强, 往往一个人出了事, 一群人会出来打击报复。 相反, 本村村民受损后同乡却鲜有人支援。 这些都给当地村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乡村混混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们无牵挂、 下手狠、 跑得快的特点, 所以时不时地施以小恩小惠来拉拢他们, 从而为自己积蓄暴力资源, 以备不时之需。 而外来务工人员也愿意与他们“交朋友”。 这其中除了出于经济收益的考虑之外, 外事务工人员也希望以此得到乡村混混的帮助, 如介绍工作、 租房子、 孩子上学等。 高强度的流动使得外来务工人员难以建立稳定的社会网络联系, 他们需要依靠乡村混混这棵大树, 借助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打开局面。
外来务工人员成为乡村混混的可支配暴力资源, 使得乡村混混可以不用直接以赤裸裸的暴力姿态展现在村民面前, 而是以隐退和操控的方式牟取不法利益。 这无疑增强了乡村混混精英地位的正当性。
3乡村混混走向“精英化”的后果
新农村建设开始之后, 乡村混混通过攫取国家惠农福利和村庄集体资源, 从村庄边缘人物转变成了村庄经济精英。 这一转变不仅对乡村混混个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对乡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和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严重的损害。
3.1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在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之后, 大量支农资金以项目的形式进入农村, 主要用于完善村庄公共用品、 发展村庄经济、 改善村民生活。 但由于乡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混混结成了利益同盟, 乡村基层组织援引乡村混混介入村庄治理, 需要给予他们一定利益的回报, 因此部分本该村庄和村民享受的福利被乡村混混等非体制性力量截留, 村庄和村民并没有享受到政府惠农政策的好处。
此外, 乡村混混介入村庄治理, 成为隐蔽的治理力量, 但是他们无视地方性规范和国家法律, 只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治理手段。 村民在治理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正气和正义, 而是乡村混混的无理和强势, 这让基层组织的合法性面临严重的挑战。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听到村民讲“中央的政策是好的, 是乡镇和村里的干部没有落实好政策”这样的话, 实际上, 新农村建设及一系列涉农、 惠农政策的出台, 本来是为了提升农民对基层政府的认同感的。 但援引乡村混混参与基层治理, 处理拆迁、 维稳等事务, 却让基层政权的权威和合法性遭到损害, 基层治理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 最早提出“内卷化”这一概念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戈登维泽, 他以此来描述“投入增长, 但发展停滞不前”的状态。 杜赞奇将“内卷化”作为概念工具引入到政治学, 提出的“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论断是指: 国家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带来效益的提高。 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 都伴随着非正式结构收入的增加, 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 从而出现“税收增加而效益递减”的严重后果。[6]66-68根据之前的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下的基层治理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 大量资源下乡, 并没有带来村民对于基层政权认同感的增加, 反而是基层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3.2乡村社会秩序的畸变
乡村混混通过灰色手段攫取了大量的国家建设性资源, 迅速完成了从村庄边缘人物到村庄经济精英的阶层再造。 这对村民的劳动与财富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由此也重塑了村民的价值观和村庄的道德秩序。
在传统农村, “勤劳致富”“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是农民坚定不移的信条。 但在目睹乡村混混不劳动却迅速致富的现实之后, 村民的劳动与财富观逐渐发生变化。 勤劳致富和劳动光荣的伦理观念不再受到推崇。 只要你有钱有消费能力, 人们不会在意钱是怎么来的。 村民一改之前疏离的态度, 反而羡慕和赞赏靠狠气和暴力谋取利益的乡村混混群体, 甚至开始几近病态地讨好他们。
由此可见, 由厌恶、 谴责到认同、 巴结的村庄话语体系的畸形转变, 折射出GM村村民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遭到利益至上原则的浸润, 开始呈现“无伦理”或市场伦理的特征。
4“乡村灰色化”困境的解决思路
GM村乡村混混从边缘人物到经济精英的“华丽转身”, 从微观层面来看, 是乡村混混的利益诉求与乡村基层组织、 村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诉求耦合的结果, 但从中观层面来看, 实质上却是工业化农村地区的乡村治理困境使然。
4.1增强村民的合作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与城市社区不同, 村庄的秩序诸如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等不是由国家,而是由村庄自己提供的,村民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为获得村庄秩序而努力。因此,村庄内生治理能力对于有效解决“乡村灰色化”问题尤为重要。而村庄内生治理能力则需从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和村庄舆论约束力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既有研究表明, 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 村民一致行动能力强, 容易达成对内合作和对外抵御;而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 内生治理能力的基础容易丧失, 村庄难以对内合作、 对外抗御。[7]如今, GM村村民之间传统的社会关系已经解体。 曾经血浓于水的亲情在经济理性面前慢慢变淡。 虽然邻居之间可能还会互相串门聊天, 但是却也不像以前那么无拘无束。 虽然只是一墙之隔, 但是谁也不再奢望对方能够在自己危难的时刻帮自己一把, 而只求对方不要在背后插自己一刀就好。 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代表的传统联系的衰落, 使得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逐渐削弱, 因此无法从村庄内部生发出对抗混混的力量, 也无法有效监督村干部的工作和对抗外来的务工人员。
另外, 从农业型农村地区转变为工业化农村地区, 市场经济不仅打破了村庄的边界, 还重塑了村民的价值观念, 从而使村庄的舆论导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从另一方面降低了村庄的内生治理能力。 如今村民日渐把追求货币以及具备这种成功追求货币的能力作为衡量其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 他们普遍认为, 谁会赚钱, 谁就了不起, 且令人钦佩。 村庄文化也不再如过去那样重视道德的成分。 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引下, 村民开始几近病态地巴结村庄中的一切经济能人, 包括曾经厌恶的“乡村混混”。 这使得乡村混混群体不但没有被消解, 而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因此, 若要解决“乡村灰色化”问题, 我们还应从增强村民间的社会纽带入手, 提升村民的合作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秦晖认为, 农民合作应是农民主动的合作, 而不能是被动的合作, 如不能由基层组织来负责组织农民合作。 贺雪峰则认为, 可以通过对当前农村基层村社组织稍加改造, 来解决农民的合作问题。[8]从GM村的实际情况来看, 上述两种论断并不矛盾。 因土地征用赔偿问题, 原GM村第一村民小组组长召集了所有组员前往村办公室讨说法。 村干部迫于压力, 下令停止了在第一村民小组土地上进行的绿化带施工。 据村民介绍, 光2014年上半年, 村民组长就因土地、 集体仓库等问题组织了三次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谈判。 在农业型农村到工业化农村转变的过程中, 重视和发挥村民小组在促进村民主动合作中的作用, 将是正途, 也是捷径。
4.2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
当前, 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呈现出两种面向。 一方面, 通过统一的法律规则和现代观念, 国家权力深深地“嵌入”了乡村社会。 得益于通讯与信息储存手段的高度发展, 以及交通手段的日益提高, 国家的技术控制能力在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 基层政府不断精简机构、 撤乡并镇, 对乡村社会呈现出相对“悬浮”的状态, 基层政府的“身体载体”在地理上远离了村庄, 控制能力也随之下降。 这样, 基层政府就呈现出“技术治理能力”提高, 而“身体治理能力”下降的现象。[9]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变化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使其在治理灰色势力上能力不足。 与身体在场相比, 技术治理能力给乡村混混的心理震慑力并不大, 且难以完全有效地应对社会流动所带来的问题。 乡村混混总处于流动状态,“身体不在场”的基层政府要约束他们,需要支付的成本非常高,这就降低了乡村灰色势力的风险成本。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变化还为灰色势力的生长和泛滥创造了可能性。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断弱化, 但是维稳等治理任务仍然繁重, 在这种背景下, 援引乡村混混介入村庄治理就有了可能。
因此, 若要解决“乡村灰色化”问题, 我国还应从增强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入手。 根据之前的分析,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的症结在于处于“悬浮”状态的基层政府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了解和控制。 要改变这一不利的局面, 大力发展“线人”制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灰色势力”藏身在群众中间, 政府看不见其活动, 群众却能看到, 但群众敢怒不敢言。 因此, 多发展有正义感的群众作为“线人”, 有助于基层政府加强对乡村混混的控制与打击, 从而遏制“乡村灰色化”的蔓延。
参考文献
[1]晏辉. 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6(3): 1-7.
[2]李祖佩. 混混、 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J]. 青年研究, 2011(3): 55-67.
[3][美]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M]. 张理京,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4]罗兴佐. 第三种力量[J]. 浙江学刊, 2002(1): 58-59.
[5]陈柏峰. 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 33-42.
[6][美]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7]贺雪峰, 仝志辉. 论村庄社会关联[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 124-134.
[8]贺雪峰. 中国农民合作的正途与捷径[J]. 探索与争鸣, 2010(2): 55-58.
[9]董磊明, 陈柏峰. 乡村治理的软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9(4): 142-146.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rginalized Men to “The Economic Elites”——An Investigation of the Village Hooligans’ Living Strategies in an Eastern Zhejiang
GU Haomai
(College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Graying” of rural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ry areas. As the main body of a “gray society”, village hooligans illegally occupy large amounts of national resources, and swiftly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marginalized people to wealthy men due to the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hooligans significantly crashes the traditional moral system and leads to the “Involution” of country society. Hence,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gray society” issue,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s and rebuild the order of rural areas at present.
Key words:Eastern Zhejiang Village; Village Hunhun; survival strategies; life history; interactive model; the change of country order
文章编号:1673-1646(2016)03-0035-05
*收稿日期:2015-12-06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乡村混混的行动逻辑——基于对渐东GM村拆迁改造的调查研究(201210027168)
作者简介:顾豪迈(1991-),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6.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