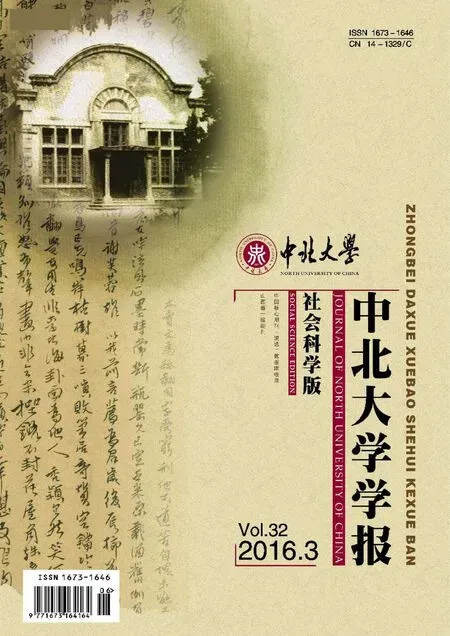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重新厘定
——基于一起离婚案件的分析
刘慧兰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法律系, 山西 太原 030031)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重新厘定
——基于一起离婚案件的分析
刘慧兰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法律系, 山西 太原 030031)
摘要:《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赠与法律关系中赠与人和受赠人的利益, 也缓和了赠与关系中义务的片面性, 尤其是对保护赠与人而言, 该制度的设立功不可没。 然而, 实践中一起离婚案件却折射出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立法的瑕疵以及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彩礼返回问题规制的漏洞, 应着重完善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约束机制和对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机制, 从而保护受赠人, 尤其是在彩礼赠与中受赠人的利益。
关键词:赠与合同; 任意撤销权; 彩礼返还
罗马法在法律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为民法的精髓和渊源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因为它孕育了私法的三大原则——所有权绝对尊重、 契约自由、 过失责任。[1]这种思想和精神最终被欧洲近代民法所创立, 最终形成了民法的三大支柱。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3条确立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4条“三位一体”平等保护理念的确立, 即“国家、 集体、 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私有财产的保护最终深入人心, 并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而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民法的专利。 本文通过对一起实务案例的探析, 重新审视了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制度, 以期为该制度在我国新形势下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1从一起离婚案看赠与合同撤销权的适用
1.1案情介绍与评析
张某(女方)与王某(男方)于2010年4月14日登记结婚, 在婚前(2010年4月8日), 王某承诺给张某家四万元彩礼, 由于当时王某手头紧俏, 便给女方写下一纸承诺: “我答应给张某家的四万彩礼, 现因为坝陵桥的平房还没有过户成我的名字, 无法卖掉, 先把婚礼举行, 等房子过户成我的名字, 我马上卖掉, 一定把四万彩礼给齐, 绝不食言。” 按照王某的这一承诺, 以及基于张某对其的信任, 双方在登记结婚后的2010年5月1日如期举行了婚礼, 而属于王某的房产(王某继承其父的遗产, 王某之母、 之妹通过公证放弃继承, 现房产权属于王某一人)也于2010年11月过户在其名下, 但王某一直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 而此事也成为双方日后感情破裂的一个导火索, 再加之双方经常因为一些琐碎小事而吵闹, 最终导致感情破裂。 张某于2014年6月向当地法院起诉离婚。 在诉讼请求中, 张某要求王某给付婚前所承诺的四万元彩礼。 这项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需要在法律上梳理如下问题:
1.1.1现行法律关于彩礼给付的法律定性及相关规定
从古代的“三书六礼”到现代的婚姻, 彩礼的给付似乎已经成为婚嫁的一道必经程序, 不论这种给付是否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愿, 但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视为是在婚姻中对女方家的尊重和缔结婚姻诚意的体现, 即彩礼的给付与买卖婚姻是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 尽管如此, 在法律当中对给付彩礼的定性仍然存在争议, 存在普通赠与说、 附条件赠与说、 附义务赠与说、 目的性赠与说、 婚约定金说等观点。 笔者认为, 将彩礼的给付定性为目的赠与、 附解除条件之赠与较为妥当。 也就是说, 在目的已成就或解除条件(离婚)成就前, 彩礼的所有权属于女方, 但如果目的未成就或解除条件(离婚)已成就, 由于彩礼存在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女方应当返还彩礼。
1.1.2个案的剖析折射出的法律盲点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为实践中解决彩礼返还纠纷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 但就本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这条规定似乎显得捉襟见肘。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适用的前提是在缔结婚姻过程中, 依照习俗, 男方已将彩礼给付女方, 如果双方未登记结婚或在离婚时, 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三种情形, 女方是应该返还的, 至于是全部返还还是部分返还, 得依个案而定, 用证据说明。 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 就是为了将借婚姻敛财的风险降到最低。 但该案中男方在婚前并没有给付女方彩礼, 其原因是当时给付彩礼的标的物的所有权还不属于男方, 但男方为此专门写下保证, 承诺标的物一旦过户到其名下, 立即兑现彩礼, 而女方基于婚姻中对男方最基本的信任, 和男方如期办理结婚登记并举行婚礼, 婚后共同生活且育有一子, 在离婚时, 女方主张婚前的彩礼, 可否?现行的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该情形下的彩礼返还(给付)。 据此, 结论如下: 婚前男方给付女方彩礼了, 女方如符合法定的三种情形, 就应返还男方彩礼, 反之, 婚前男方承诺给付女方彩礼, 并且“白纸黑字”写明, 女方和男方踏踏实实过日子, 离婚时, 索要这部分彩礼的法律依据却“无影无踪”, 这样的规定明显有违民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在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找不到本案的法律依据, 那民法的其他部门分支会有相关规定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离不开对彩礼给付的定性, 彩礼属于目的赠与、 附解除条件的赠与, 现在本案的关键是男方在婚前并未给付女方, 而双方结婚之目的又已实现, 这明显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在逻辑上相矛盾。 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明在解除条件成就前法律行为已生效, 当条件成就了, 法律行为归于无效, 而本案恰恰由于男方婚前并未给付, 也就是这个赠与并未生效, 自然谈不上女方的返还问题。
综上分析, 将彩礼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在逻辑和体系上能够自足, 但在本案的解决上似乎走进了盲区, 最终无奈的选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 男方似乎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支持自己的“出尔反尔”, 而女方的索要恰恰与法无据。
1.2关于本案的建议
从理论上来讲, 本案中女方的诉求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理由如下: 第一, 保护女方期待利益说。 婚姻的缔结是以双方的自愿为前提, 这种身份性质的法律行为显然与等价有偿原则下交易的自愿不能一概而论, 婚姻中的“自愿”更应靠双方的忠诚、 诚信去维系, 在此案件中, 女方之所以暂缓男方的彩礼给付, 正是对男方、 更是对婚姻信任的一种体现, 这种信赖利益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否则, 无异于鼓励人们的不诚信。 第二, 共同财产利益减少说。 关于彩礼的性质, 主流观点依然是把其定性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2], 即在条件成就前, 赠与行为是生效的。 也就是说, 如果男方在婚前信守承诺给付了女方彩礼, 按照习俗, 该彩礼似乎应成为双方婚后的共同财产, 正是由于男方的毁约, 导致女方婚后可得的共同财产相应减少, 那此部分(至少彩礼数额的一半)也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第三, 单方允诺债务形成说。 目前, 我国学者起草的三部民法典草案都明确将单方允诺行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加以规制, 王利明教授在比较单方允诺和契约合意后, 进一步得出单方允诺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结论。[3]可见, 单方允诺的效力正当性已得到学者的认同, 问题的关键是在实践中, 哪些单方允诺可以被强制执行的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笔者认为, 婚姻的缔结乃双方之自愿, 但作为社会最小细胞的家庭, 它的稳定、 和谐与否直接关乎社会的稳定、 和谐, 而婚姻的维系又需要彼此的忠诚, 所以, 这种婚前的单方允诺承载的是一种社会公众的期待, 它应当被强制执行, 从某种意义上也能让当事人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从而降低离婚率。
2赠与合同撤销权视角下的法理分析
2.1不同性质的赠与与撤销权的关系
2.1.1一般赠与与撤销权的适用
所谓一般赠与, 即仅仅是为了增进情感, 加深情谊而为的给与, 这种赠与不同于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或经过公证的赠与, 后者的目的性、 针对性更强, 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利益或赠与人的意志, 所以针对一般性的赠与, 《合同法》第186条赋予了赠与人在履行赠与合同前的任意撤销权, 给其在没有充分考虑下而为的赠与一个补救的机会。 本案中, 男方婚前承诺给付女方的彩礼, 不应该仅仅视为一个普通的赠与, 因为这种赠与是以和对方缔结婚姻为前提的, 况且在女方已和对方完婚的情形下, 如果允许男方援引186条的规定, 对女方而言是有失公平的。 这种婚前彩礼的赠与更应定性为“赠与约定”而非“赠与原因”。 所谓赠与约定是指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要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一方违约, 将要承担违约责任, 而赠与原因强调的是为已经发生的财产变动提供正当性, 该赠与意思单方、 双方均可, 但都不产生赠与人的给付义务。[4]
2.1.2附义务赠与与撤销权的适用
所谓附义务赠与, 即在赠与法律关系中, 赠与人对其赠与附加一定的义务, 作为受赠人取得赠与物的前提, 当受赠人不履行该义务时, 赠与人是可以请求受赠人履行的。 如果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 赠与人同样可以撤销赠与合同, 只不过此撤销是法定撤销。 如果用此理论来分析该案, 那么, 以下问题值得商榷, 即能否将彩礼的给付定性为附义务的赠与?答案是否定的。 理由如下: 第一, 如果将结婚作为彩礼给付所附的义务, 极易导致买卖婚姻现象的出现, 这与婚姻法倡导的婚姻自由原则是相违背的。 第二, 在附义务赠与中, 如果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 赠与人是可以要求其履行的, 而婚姻如果作为彩礼给付所附的义务, 由于其具有的人身性, 导致其不可以被请求执行。 在这个意义上, 彩礼的给付可理解为目的赠与。 在目的赠与中, 赠与人是无权要求受赠人必须实现当初赠与之目的的, 而只能于目的不被实现时, 依不当得利要求受赠人予以返还, 这与将彩礼给付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行为, 在理论内涵上能够保持一致。 第三, 附义务的赠与, 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而附条件的赠与, 当条件成就或不成就时, 法律行为的效力是自始的、 当然的、 确定的, 无需行使撤销权。
2.2类推、 对赠、 撤销权在该案适用中的质疑
所谓类推适用又名类比推理, 它是指在法律就某种情形的立法适用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 在司法实践中, 可以比照相近的法律规定加以处理的规则。 这充分说明, 当法无明文规定的时候, 个案的处理不会陷入一种僵局, 反而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 因为相类似规定的法律条文所蕴含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精髓在解决该案的过程中同样适用, 同样可以被彰显。 这种类推规则的适用, 是以一定的公理、 政策和需要为基础的, 它更是法律正义价值的要求, 而在现代社会, 类推适用只具有私法价值而不具公法价值。[5]但需要说明的是, 类推的适用止步于民事领域。 因为在刑法和行政法等公法领域内, 要严格执行罪行法定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 类推的适用在实践中比较难以把握。 故按照类推的原理,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法律规定了女方应当返还彩礼的三种法定情形, 这样的立法大大保护了婚姻中男方的权益, 按照孟德斯鸠“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 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平等保护自是民法应有的基本原则, 那么从保护女方角度而言, 女方在与对方办理了结婚登记, 并且也已共同生活, 由于特殊原因婚前男方没有给付彩礼, 但其书面承诺彩礼会于婚后兑现, 于此情形下, 若允许男方以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来撤销该赠与的话, 那女方的权益又何以保护?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以单方意志而撤销赠与, 即法律是在变相承认赠与人的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 那么,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的道德理念岂不在法律中如同一纸空文?况且,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凌驾于受赠人意志之上而行使的, 全然不顾受赠人的感受, 这岂不又是公然挑战社会的公平、 正义理念吗?所以, 基于彩礼给付行为法律性质的特殊性, 僵化适用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势必会以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牺牲来保全法律在个案中的适用, 这也绝不是立法者的初衷。
3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内涵
3.1任意撤销权的法理基础
3.1.1赠与合同的单务性、 无偿性、 诺成性使然
赠与合同的单务性、 无偿性和诺成性决定了在该法律关系中, 赠与人只负义务, 而且该义务没有对价权利, 一经承诺即发生法律效力, 这样的法律规则从权利义务对等关系来看, 对赠与人似乎是不公平的, 而作为追求公平、 正义的法律在此刻便赋予了赠与人一个任意撤销的权利, 即在履行赠与合同前, 赠与人原则上是可以随意撤销赠与合同的, 以此达到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 这也符合利益衡量的价值追求。
3.1.2利益衡量下的价值选择
一个法律制度的出台是否能产生积极的法律效应, 取决于该制度的理论生命力是否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而这一考验标准就在于该制度是否达到了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由于赠与合同的特殊性质使得各国在规范该制度时无一例外地赋予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这项特别优遇赠与人的制度[6], 这与赠与合同的性质定性密不可分。
3.2任意撤销权之“任意”的内涵分析
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的前提是因为赠与合同的性质使然, 是保护赠与人的一种价值选择, 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 《合同法》第188条规定: “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 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可以看出, 此类合同是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行使的例外。 也就是说, 任意撤销权之“任意”是相对的, 这种相对性也体现出法的包容性。
3.3任意撤销权之行使与民事责任之承担
赠与人在行使任意撤销权后, 对受赠人来说, 无疑是一种无形信誉的损失, 这种心里期待利益的损失, 也势必会造成彼此信任的游离, 对整个社会诚信秩序的构建形成一种威胁。 那么, 在任意撤销权被行使后, 对赠与人造成的损失也应该由一种责任机制来约束, 这就是责任的承担, 唯有如此, 双方利益才能达到一种平衡。
4任意撤销权的立法不足
4.1缺乏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约束机制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一原则体现在合同法领域中便是契约自由, 法无明文规定皆自由便是对其最好的诠释。 那么, 在赠与合同中, 赠与人自愿以其不利益, 而让受赠人获益, 无可厚非, 或许此行为乃一时冲动之举, 为了平衡双方之权益, 法律赋予了赠与人在实施赠与行为之前的反悔权——任意撤销权。 但《合同法》第186的规定未免有些简单, 它只规定了在财产转移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 这样的规定极易产生权利被滥用的风险, 而纵观民法中的其他“撤销权”类型, 均对权利行使的条件和时间做出了明确规定。
4.2缺乏对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机制
从人的有限理性角度来看, 任意撤销权的存在似乎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不强调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原因是该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憾, 极易导致赠与人滥用该权利, 从而损害受赠人的信赖利益。 而撤销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在形成权中, 权利人为相对人设定义务, 相对人在被动接受义务的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为避免相对人在法律上受到差别对待, 法律为形成权的行使规定了一系列限制, 如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行使、 权利人终止合同需要说明理由、 权利人存在主观过错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等。[7]而我国正是由于缺少权利行使的约束机制, 那么, 对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必然会显得捉襟见肘。 我国在缔约过失责任的构建中, 就是充分考虑了合同一方因信赖对方的未来诚信履行而遭致对方不诚信的, 法律即赋予了该方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 这种立法模式, 同样可以在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行使中为保护受赠人的信赖利益而充分借鉴。
5完善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措施
从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本身来看, 立法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该制度达到对法律关系当事人利益均衡保护的目的。 因为赠与法律行为的特殊性, 可能使得立法中难免对其适当倾斜, 但纵观整个民法理论, 赠与是双方法律行为, 双方当事人应处于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 可现行法律规定似乎有“顾此失彼”之嫌疑, 在保护赠与人利益的同时, 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赠人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怀。 所以, 加大对受赠人利益的保护, 方能真正平衡双方的地位。 笔者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5.1确立任意撤销权行使的约束机制
5.1.1确立任意撤销权行使的期限, 明确规定除斥期间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在内容上虽然不是绝对“任意”的, 诸如具有救灾、 扶贫等社会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是不得被任意撤销的, 但除此以外的赠与合同, 赠与人在行使撤销权时似乎又是绝对的“任意”, 因为赠与人“一不高兴”就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而使赠与合同归于无效, 受赠人在赠与合同中的命运听命于赠与人的意志, 这样的立法缺憾无疑使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过于膨胀, 这与民法中的撤销权理念也是相违背的。
纵观民法, 我国目前的撤销权制度主要集中在以下立法规范中: 一是一般撤销权制度, 主要在民法总则中予以规定, 如《民法通则》第59条; 二是破产法中的撤销权, 如《破产法》第31条的规定; 三是在债的关系中, 债权人的撤销权, 如《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四是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 如《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 前三类撤销权的行使条件相对比较严格, 要受除斥期间的限制,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 撤销权一般属于形成权, 而形成权最明显的特征即是通过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决定法律关系的命运, 相对方对于法律关系的变动是一种“被”接受, 正是基于这一点, 所以, 从平衡双方利益角度而言, 应该明确规定任意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 以降低该项制度在实践中被滥用的风险。 至于除斥期间的计算, 可从合同成立之初算起, 且不存在中止、 中断、 延长的情形, 这样更有利于在平衡双方权益的基础上维护交易安全, 构建和谐秩序。
5.1.2确立任意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从《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可知, 法律对任意撤销权如何行使并未明确写明, 而法律行为有要式和不要式之分, 如果允许撤销权以非要式(口头)方式行使, 则会产生两种不利后果: 一是法律的严肃性、 谨慎性易遭破坏, 二是纠纷产生后, 不利于证据的收集。 为此, 笔者认为, 任意撤销权应以要式(书面)形式来行使。
5.1.3扩大不可撤销的范围
1) 效仿日本民法, 以书面形式达成的赠与不得撤销。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制度始创于日本。 《日本民法典》第550条规定: “非依书面的赠与, 各当事人可以撤回, 但已履行完毕的部分, 不在此限。 ”该条充分说明, 以书面形式订立的赠与合同, 由于其形式上的要式性, 足以表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严谨性, 这种“严谨”在法律上是当事人三思而后行下的意思自治的充分体现。 而在道德层面, 这也体现了“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的诚信, 无论与法与理, 作为帝王条款的诚信原则应该是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秉承的思想准则和行为指引。 所以, 一旦当事人以书面形式固定赠与的意思表示, 这种表意是不允许当事人以行使任意撤销权为由而加以撤销的。[8]
2) 明确约定放弃任意撤销权的赠与不得撤销。 从权利性质或功能角度来看, 它属于形成权。 所谓形式权, 即单方意思表示就可决定法律关系的命运。 如此一来, 在赠与合同从成立到履行的这一阶段, 受赠人时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法律关系状态中, 因为只要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 双方的法律关系也就此终结, 这对尤其是为履行赠与合同而做了一定准备工作的受赠人来说, 无疑是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打击, 从而也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 有序发展, 因为没有一个理性主体愿承受不稳定之法律关系。 所以, 如果赠与人在订立合同之初已明确放弃任意撤销权的, 事后不允许反悔。
3) 所附义务大于赠与物价值的赠与不得撤销。 撤销权究其实质, 其实是法律赋予赠与人在其真正履行赠与前的一次反悔的权利, 这种权利就像一把双刃剑, 它在保护、 平衡赠与人利益方面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但如果被不当运用, 则有可能扼杀受赠人的期待利益、 信赖利益, 成为了用表面的公正掩盖法律关系内在的不公正的“恶法”, 这绝不是立法者的初衷。 对撤销权予以必要的限制, 符合权利不得滥用的立法原则, 是对权利自由绝对化的矫正。 《合同法》第190条规定, 赠与是可以附义务的, 这条规定并不是赠与合同单务性、 无偿性的否认, 而是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更大的自主空间, 而且通常所附的义务也不是赠与物的对价。 同时第192条又规定, 当受赠人不履行赠与所附义务的, 赠与人是可以撤销赠与合同的, 此撤销权是赠与法定撤销权的内容之一, 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 是平衡当事人利益后的选择, 义务的履行是赠与合同生效的条件, 当前提不存在时, 合同自无生效之必要, 赠与人即可行使法定的撤销权, 这样的规定不无道理。 但是, 该规定在与任意撤销权在衔接时会出现一种矛盾, 如当赠与所附义务高于或大于赠与物价值时, 受赠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而履行了该义务, 依照任意撤销权理论, 赠与人同样是可以行使撤销权的, 这对已履行赠与义务的受赠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反而容易成为赠与人“戏谑”受赠人的工具, 违反了法的公平、 正义。 所以, 法律有必要明确规定, 在受赠人已履行义务的范围内, 赠与人是不可以撤销赠与的。[9]
5.2确立受赠人的信赖利益保护机制
5.2.1引入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法律对于合同中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制度主要体现在缔约过失责任的构建上。 该责任产生于合同缔结过程中, 即双方处于接触、 磋商阶段, 基于诚信原则而负的先合同义务的违法致相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而负的赔偿责任。 同理, 在赠与合同中, 如果赠与人欲行使任意撤销权, 极有可能导致为接受赠与而事先已做履行准备的受赠人的利益, 但由于此时双方的赠与法律关系已成立, 而非处于缔约阶段, 所以, 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追究赠与人的赔偿责任并不妥当, 只能依照受赠人的损失, 并基于公平原则来进行赔偿, 从而约束赠与人滥用任意撤销权, 此法理基础乃为民法之诚信原则。 然而, 诚信原则并不是一个具有必须予以核对的具体要件的法律规则, 而是可以被称为一个“开放性”的规范。 它的内容不能通过抽象方式来确定, 而只能通过其被适用的方式得以具体化。[10]
5.2.2增加恶意赠与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所谓恶意赠与, 即赠与人在没有赠与真实意图的前提下, 而对受赠人所为的虚假赠与的意思表示。 按照法律行为效力理论, 不具备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是不生效的, 而这种不生效是赠与人的主观原因所致, 为了惩戒不诚信行为, 笔者建议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 即赠与人除了赔偿受赠人因信赖赠与而所受的损失, 还应给予不超过赠与物价值一倍的赔偿。
综上所述, 笔者建议,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关于返还彩礼的三种情形之上, 增加一条规定, 即“婚前男方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给付女方彩礼的, 而婚后未予兑现的, 离婚时, 女方可要求男方返还, 法院应予以支持”。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彰显民法以人为本的关怀理念。
参考文献
[1]刘艺工、 刘志敏, 试论罗马法复兴运动[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5(1): 56-61.
[2]潘君, 彩礼返还法律问题研究[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14.
[3]徐涤宇、 黄美玲, 单方允诺的效力根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4): 141-160.
[4]刘家安, 赠与的法律范畴[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4(5): 57-63.
[5]屈茂辉, 类推适用的私法价值与司法适用[J]. 法学研究, 2005(1): 3-19.
[6]李辉, 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研究[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12.
[7][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 邵建东,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8]高爱霞, 论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3.
[9]楼淑馨, 赠与合同撤销权限制行使探析[J]. 科协论坛(下半月), 2010(9): 119-120.
[10][德]莱茵哈德.齐默曼, [英]西蒙.惠特克. 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M]. 丁广余, 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Arbitrary Avoidance of Gift Contract——An Analysis Based on a Divorce Case
LIU Huilan
(Dept. of Law, Business College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1, China)
Abstract:Provisions in relation to arbitrary avoidance of gift contract in the Contract Law of China, to some extent, have not only balanced interests of the donor and the recipient of a legal relationship but also reduced the overemphasis of the duties in a legal relationship. In particular, this system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dono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case, a number of legislation problems of arbitrary avoidance of gift contract in the Contract Law and legal flaws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turn of betrothal gifts in current marriage laws are investigated and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donee in a marriage gift deal,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to restrict the rights of the donor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donee.
Key words:contract of gift; arbitrary avoidance; return of betrothal gifts
文章编号:1673-1646(2016)03-0045-06
*收稿日期:2015-12-11
作者简介:刘慧兰(1981-), 女, 讲师, 硕士, 从事专业: 民法。
中图分类号:D91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6.0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