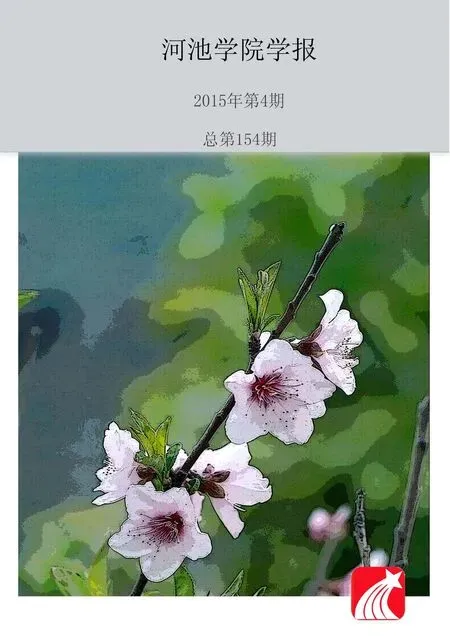禘祭祭礼与《周颂·雝》诗考辨
水 汶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554300)
禘祭祭礼与《周颂·雝》诗考辨
水 汶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554300)
《雝》是《诗经·周颂》中的一首祭祖诗歌。关于其诗主旨,《毛诗序》认为是禘祭太祖之诗。结合历史文献,参证甲骨卜辞及金文考察禘祭祭礼,详细解读《雝》诗诗歌内容,《雝》诗或难与禘祭联系起来。综合诗歌文本及禘祭礼仪考察,《诗经·周颂·雝》当是周武王祭祀考母的诗歌。
《诗经·周颂·雝》;禘祭;《雝》诗主旨
关于《诗经·周颂·雝》诗的主旨,《毛诗序》认为是禘祭太祖之诗*参见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595页。。结合历史文献,参证甲骨卜辞及金文考察禘祭祭礼,“禘”主要是祭祀近祖的祭礼,在周穆王之前,一般以男性为祭祀对象;解读《雝》诗诗歌内容,《雝》当是周武王祭祀考母的诗歌,而不是禘祭太祖之诗。
一、关于禘祭
“禘”为国之大祭,甚至被认为是治国之本。《礼记·祭统》言:“禘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1]1488然关于禘祭祭礼,历来却是争议颇大。首先分别看一下文献及甲骨卜辞、金文中反映的禘祭祭礼:
(一)文献中的禘礼
文献中出现的禘礼,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
1.“禘祖配祖”和“禘天配祖”说。这种说法出自《礼记·丧服小记》。其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1]1628,郑玄认为,“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1587页。表明了禘、郊、祖、宗这四种祭礼的含义都是祭祀并配食。其中禘的对象是昊天,祭祀的地点是圆丘。;孔颖达引王肃《圣证论》说法,认为禘祭是禘祭始祖而以其祖配祭*孔颖达指出禘在经传中含义各殊,他引用王肃《圣证论》的说法:“案《圣证论》以此禘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颖达表达了王肃的意思是,所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以有虞氏禘黄帝为例),就是禘黄帝而以颛顼配祭。那么禘祭的含义就是禘祭始祖而以其祖配祭。。
郑玄的“禘”为“祭昊天于圆丘说”和王肃的“禘祭始祖”说可谓“禘”礼争议的一大悬案。两者都有一大批的支持者,千古之下,争讼不已。从表面上看,王肃“禘祖配祖”的说法比较合理。但是,“以祖配祖”的祭礼在经传中未见有过记载。“禘天配祖”说虽使人怀疑,但祭天配祖的祭礼却确实存在。《诗经·大雅·文王》有文王配天的记载:“文王陟降,在帝左右[2]504……永言配命,自求多福”[2]505;《周颂·思文》一诗据《毛诗序》所说为“后稷配天也”[2]590。因此,从实际情况看,“禘天配祖”的说法或有一定渊源。
2.“‘大祭祀’统称”说。《周礼·春官·大司乐》“凡乐”至“则人鬼可得而礼矣”,郑玄注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则主北辰,地祗则主崐崘,人鬼则主后稷”[3]790。这种说法将“禘”解释为祭天、地、人鬼皆可称之的大祭祀。以王肃为代表反对郑玄“禘为圆丘祭天说”的一派意见,似未直接反对这种说法。
3.“四时祭之一”说。四时祭又被称为时祭或时享,是春夏秋冬四季向祖先献祭的祭祖礼。某些文献将“禘”列为四时祭之一,如《礼记·祭统》:“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1]1606;再如《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1]1335。按照这样的说法,则禘是四时祭之一。但四时之祭尚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758页;《周礼·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尝,冬烝”,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773;《白虎通》:“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汉班固《白虎通》,丛书集成初编本(0238-0239),北京:中华书局,1985;《尔雅·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阮元校刻《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2609页;《春秋繁露》“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丛刊初编本(10),上海:上海书店,1989,卷15,第3页,“禴”与“礿”,“烝”与“蒸”在表示祭名时相通,大部分文献所记载的四时祭名其实是“祠禴(礿)尝烝(蒸)”。。许子滨《<春秋><左传>礼制研究》列举了《春秋》《左传》记录的春秋时期禘祭实例,其中明确指出禘祭的祭礼中,举行的时间有“夏五月”(《春秋·闵公二年》 )“秋七月”(《春秋·僖公八年》*原文为:“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见于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799页。)“冬十月”(《左传·定公八年》*原文为:“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见于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第2143页。)。可见,“禘可能是不受季节限制”[4]216的祭礼。
4.“吉禘”说。所谓“吉禘”,就是在祖先三年之丧后行禘祭,变凶礼(丧礼)为吉礼(祭礼),故称“吉”。在春秋文献中,有“吉禘”的记录。《春秋经·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5]1787。《左传》的记事原则是“常祀不书”。对于记录上面所说“吉禘于庄公”的原因,《公羊传》作出了解释。《公羊传·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为谓之未三年?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其言于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曷为未可以称宫庙?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6]2244。在这段文字中,很清楚地表明了史家记载此次吉禘的原因:吉禘是三年丧毕之禘,而这次吉禘未到庄公三年丧毕之时,所以史家记录了这次吉禘。许子滨《<春秋>、<左传>礼制研究》认为:“三年吉禘之说有理有据,可以无疑。”[4]212
5.殷祭说。《公羊传·文公二年》“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殷,盛也,谓三年祫五年禘。”[6]2267从而指出,“殷祭”是“三年祫五年禘”。其所说的与“祫”礼相联系的“禘”,指的是五年一次在宗庙举行的大祭,属于殷祭。禘、祫都属殷祭,三年祫五年禘。
从文献的记录来看,“禘”的含义不止一种。从举行禘祭的实例来说,“吉禘”说可得到《左传》的印证;而禘为“四时祭之一”说似乎不妥。“祭天配祖”的仪式在《诗经》中出现过,但是否为禘祭尚难定论;至于禘是否为“‘大祭祀’统称”,是否存在“三年祫五年禘”的“殷祭”,尚难以遽下定论。
(二)与卜辞、金文相参证的禘礼
考古文献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料。文献资料参证甲骨卜辞、金文中的材料或许更客观一些。


剌鼎:“唯五月,王在衣(殷),辰在丁卯,王啻(禘)。用牡于大室,啻(禘)卲(昭)王,剌御,王賜剌貝卅朋……”[11]2776
小盂鼎:“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明,王各周廟……用牲,啻(禘)周王、武王、成王……”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4,第2839页。“各”,即“在”。据考证,此器作于康王二十五年。禘祭的对象是周王、武王、成王,周王当指文王。
关于“禘”的对象,剌鼎、鲜簋之禘为祭卲王,即昭王;而小盂鼎之禘为祭文王、武王、成王;大簋之禘为祭其考,祭祀对象均为祖考。这表明了西周禘礼有专祭、合祭,都为祭其近祖。
关于“禘天配祖”说和“三禘”说,卜辞中有祭天,祭祀对象也比较多。而在金文中,刘雨先生说,“金文禘祭全是以祖考为对象,不见禘天,也不见禘地”[12]497。可见,从殷到周,禘祭的含义是在演变中的。
关于“禘祭始祖”,刘雨先生认为,“禘祭始祖在西周金文中没有发现。相反,在西周金文中禘祭的对象都是近祖。记录禘礼的铜器除小盂鼎是康王禘祭其三代先王之外,鲜簋、剌鼎为穆王禘祭其考昭王,大簋、繁卣也是作器者禘祭其考大仲和辛公”[12]497。
至于禘祭时间,殷商和西周无规律性。因此,时禘说看来并不可靠。由前文看出,剌鼎、鲜簋铭记载穆王五月禘昭王,大簋铭记载行禘在六月,小盂鼎铭记载康王八月禘文王、武王、成王,繁卣记载九月禘其考辛公。禘祭的时间从五月至九月,很难以某个季度来概括。因此,禘不是四时祭名之一。
综合历史文献、甲骨卜辞及金文资料来看,禘祭是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祭礼。“禘”在殷代曾是表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的祭礼,后来禘祭先公先王。而到了周代,“禘”主要是祭祀祖先的祭礼。从甲骨卜辞、金文及文献的实录来看,“祭天配祖”祭礼似可得到《诗经》相关诗歌佐证,但是否为“禘”祭难以定论;禘祭的目的有“终丧之禘”,也就是“吉禘”,可得到《左传》印证;禘祭的对象主要是近祖,有独祭,有合祭;禘祭的时间不受季节限制。“禘”是否为“‘大祭祀’统称”,是否进行“三年祫五年禘”的所谓“殷祭”,难以遽下定论。
二、《雝》诗内容分析
《雝》诗原文如下:
有来雝雝,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於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④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595-596页;本标题下所引用《雝》诗原文及《传》《笺》《疏》皆引自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关于此诗的主旨,《诗序》认为是“禘大祖”。*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595页;“大”古常通作“太”,下同。《正义》进一步解释:“《雝》者,禘大祖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禘祭大祖之庙,诗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为此歌焉”。朱熹、姚际恒等不同意以上说法。朱熹《诗集传》以为:“此武王祭文王之诗”[13]230。姚际恒《诗经通论》:“《小序》谓‘禘大祖’,谬。周之大祖,后稷也。据《礼》,‘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后稷所自出为喾,诗无及于喾、稷,前人已辨之。今按篇末曰‘烈考、文母’,于禘义尤万里。此武王祭文王徹时之乐歌”[14]340-341。考察诗意内容,本诗是否反映“禘”祭的内容及“禘”祭的对象是否为“大祖”,确实有待探讨。而要弄清楚此诗到底表达了何种内容,关键在于弄清楚本诗的祭祀对象。
关于祭祀对象,《序》以为是“大祖”。关于太祖所指的具体人物,《笺》以为“大祖”即文王。姚际恒、孙诒让等人认为太祖为后稷。姚际恒《诗经通论》云:“周之大祖,后稷也”[14]340。此说有理。《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郑注:“大祖,后稷”[1]1335。可见,周制王室太祖为后稷。《汉书·韦玄成传》虽说:“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15]3118。并且汉制确实是以“受命之王”为太祖,《通典》记载汉代:“以高皇帝为太祖”[16]267。但周制不尽相同,太祖为后稷。周之历史,后稷始封,文武受命,按照韦玄成之意皆可称为太祖。而作为诸侯的后稷始封在先,文王、武王受命在后。以此论之,太祖当指作为始封之君的后稷。所以孙诒让《周礼正义·守祧》解释说,“案:周虽文武受命;而先为诸侯,后稷实始受封,故文王不为太祖,而后稷为太祖也。”[17]1676
《白虎通义》云:“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也。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庙,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18]3,这里所谓“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之“太祖”,毫无疑问当指后稷。其后面却说,“文王为太祖”,若是这样,则岂不是应该合食于文王庙了?我们清楚地知道,周制合食于大祖后稷之庙。看来,这里所谓“太祖”或泛指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并非周王祫祭时合食于太祖之太祖。因此,孙诒让《周礼正义》说:“彼以礼,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谓文王为太祖耳,非祫祭群祖合食之太祖……成王时,文王尚在四亲庙,则不得以为太祖明矣”[17]1676-1677。
在周代,“太祖”一词倾向于指其始祖,或者说“始封之君”。《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1335页;以下对于此段文字的注疏亦皆出自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此段文字出现三次“大祖”,对于周天子来说,太祖为始祖,即后稷。郑注“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大祖,后稷”;对于诸侯来说,太祖指始封为诸侯者。郑注“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云:“大祖,始封之君。”这里所说的始封之君,是指始封为诸侯之君。对于大夫来说,他们的大祖是指始有封邑者。“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郑注:“太祖,别子始爵者”。别子,在这里指的是诸侯之庶子有了封邑,从而成为一个宗族或家族的始祖。因此,周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庙制所谓的太祖,分别指其始封之君。
当然,文王也曾被作为太祖享受祭祀。周公被封为鲁,其子伯禽为鲁国之君,成王特赐鲁国可以以文王为太祖,进行祭祀。故傅亚庶说“周公既帮助武王灭殷,又有辅助成王之大功,故天子特赐鲁国可以立文王为大祖”[19]136。但是,文王是被作为诸侯国的太祖,并非周王室的太祖。郑玄所谓文王为太祖的说法,或搀杂了后世的制度。《雝》诗所写为周天子之礼,故“大祖”当指后稷。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亦说,“周王室以后稷为大祖”[19]136。然考察诗意内容,诗中所祭祀的对象与后稷无涉。
诗中可作为判断祭祀对象依据的诗句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假哉皇考
文武维后
诗的最后一句“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很清楚地指明了祭祀对象。文母指的是文王之妃太姒,古今学者皆无疑义。那么,烈考与文母对举,烈考自然当指文王。正如马瑞辰所说,“诗以烈考与文母并举,文母为大姒,则烈考为文王无疑”[20]1084。曹兆兰对殷周金文材料进行研究后亦说:“合祭中的享祭者为异性时,均以夫妻联袂的形式出现”[21]80。可见,祭祀对象当为文王与文母无疑。毛《传》以为“烈考,武王也”[2]596,不当。
从“假哉皇考”句看,皇考亦当指文王。皇:君;考,成德之名,父祖都可称。《释诂》云:“皇,君也”[22]2568。孔疏:“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虽说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参见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1589页。。但实际上,在《闵予小子》“於乎,皇考”句中,“皇考”即指其父武王*参见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第598页。。此句与《闵予小子》一样,虽然非其曾祖亦称皇考,以其散文取尊君之义,所以父祖皆可称之。故朱子《集传》谓“烈考,犹皇考也”[13]230。烈考,前已说明为文王,此处亦指文王。
关于“文武维后”一句,或以为“文武”乃文王、武王,但这种说法脱离了诗的上下文意。“文武维后”前一句是“宣哲维人”,即“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宣哲”,犹“明哲”;人,指人臣;后指君,在句式上正是“宣哲”与“文武”(即文德武功),“后”与“君”相对举。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宣哲’与‘文武’对举,二字平列……宣之言显;显,明也。宣哲犹言明哲也……‘人’对‘后’言,当训为臣”*参见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1083页。。所以,此处文武不指文王、武王,而是指文王的文德武功。其实,《诗经》中亦有赞美文王武功之例,如《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2]526,意思是文王受天之命,有此赫赫武功。即是指文王有文德武功,文武兼备。所以“文武维后”将“文武”并举,是赞美文王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文武兼备。
三、《雝》诗主旨
因此,此诗内容是祭祀文王与文母,主祭者当为武王。在殷周时代,作为祭祀对象,女性是可以和男性一起接受享祀的。曹兆兰《金文中的女性享祭者及其社会地位》记录了“享祭者为父母”[21]81的祭祀事例。因此,武王祭祀父母也是符合历史现实的。
《序》言此诗为“禘大祖也”,如前所述,周王室太祖是后稷,而此诗祭祀文王和文母,故祭祀对象所言不确。关于此诗反映的祭礼,《序》以为是“禘”祭。但从祭祀对象分析,此诗不能判断为描写“禘”祭。考察诗意,诗歌祭祀的对象为文王和文母,那么主祭者当为武王,属西周早期诗歌。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载:“目前所见到的材料多集中于西周中期偏早(穆王)之前,可知禘发生于祭祀男性祖先的仪式之中”[8]71。《雝》诗反映的正是穆王之前的祭礼,而这一时期的“禘”祭,其祭祀对象为男性祖先,都是近世祖考,而不及女性。另外,从文献反映的材料来看,“禘”祭的对象亦为男性,故《诗经原始》说:“文母之祭亦与谛义无涉”[23]608。何休注《公羊传·文二年》有言,禘祭“功臣皆祭也”[6]2267,可见,功臣可以作为配祭的对象,但亦不见女性可以作为“禘”祭或配祭的对象。
《左传》里有一条禘祭女性的材料,但这条材料本身就有一些问题,不足为禘祭女性的证据。《左传·僖公八年》记载:“禘于大庙,用致夫人”[5]1799。此处夫人指哀姜。哀姜是庄公的夫人,庄公死后,齐人立哀姜之娣叔姜的儿子即后来的闵公为君。哀姜与共仲私通,参与杀死闵公,欲立共仲为君。事情败露后,她死于非命。《左传》记载此事,“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齐人取而杀之于夷”[5]1787。所以,史家记载此次祭祀有讥讽之意。《左传》杜预注对于此禘祭的动机便提出了怀疑,并解释说,哀姜“淫而与杀,不薨于寝,于礼不应致,故僖公疑其礼,历三禘,今果行之。嫌异常,故书之”[5]1799。
综上,禘祭在周代初年主要指的是祭祀近祖的祭礼,一般的祭祀对象为男性,禘祭的时间没有规律。《周颂·雝》被《毛诗序》认为是禘祭太祖的诗歌,然周太祖一般指始祖后稷。考查《雝》诗内容“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等,《雝》诗当为祭祀近祖而非远祖的诗歌,祭祀对象既有男性又有女性,亦难与周初禘祭联系起来。因而,其反映的祭礼当是周武王祭祀考母的内容。
[1]阮元校刻.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2]阮元校刻.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3]阮元校刻.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4]许子滨.春秋左传礼制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6]阮元校刻.春秋公羊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7]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8]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董莲池.殷周禘祭探真[J].人文杂志,1994:(5):75-78.
[10]容庚.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4.
[12]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J].考古学报,1989:(4):495-522.
[13]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4]姚际恒.顾颉刚,标点.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汉班固.(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孙诒让.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6)
[18](汉)班固.白虎通[Z]//丛书集成初编(0238-0239).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0]马瑞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曹兆兰.金文中的女性享祭者及其社会地位[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79-86.
[22]阮元校刻.尔雅注疏[M].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
[23]方玉润.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 韦杨波]
The Rite of Di and the PoemZhousong·Yongin the Book of Songs
SHUI W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YongisapoemoftheBookofSongs for ancestor worship. About the subject of poem, Mao Shi Xu considers it as the Rite of Di. By referr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oracle inscriptions and rite of Di on ancient bronze, and by detailed reading ofYong, it’s found thatYongmay not be related to the Rite of Di.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Yongand the Rite of Di, the author thinks thatZhousong.Yongmust be a poem which describes the Rite of the King Wu of the Zhou Dynasty worshiping his mother and father.
zhousong.Yong; the Rite of Di; the purpose of Yong
水汶(1978-),女,山东济南人,铜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I206.2
A
1672-9021(2015)04-0053-06
2015-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