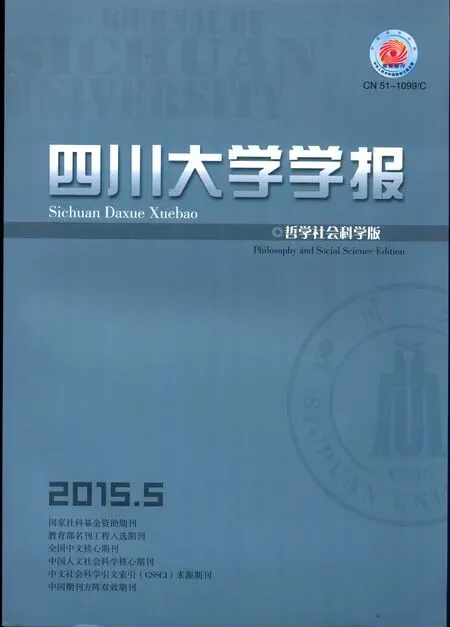早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论”文艺思想
朱 研,普 慧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①《论语·雍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00页。孔子把“文质彬彬”作为衡量君子人格的基本判准,其“文质论”主要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讲的。到了经学发达的汉代,儒家文质相副的理论则被进一步赋予社会政治和形而上学的意义。
西汉初期流行的“文质论”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尚书大传》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礼三正记》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也。”②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68、360页。将质、文与三代历史及礼制相关联,通过质、文的逻辑关系来理解和诠释夏、商、周时代的礼制变迁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方法和观念。自董仲舒提出“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起,③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04页。文质论更是与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结合在一起,构成基本的治道理论。其后,扬雄“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斑斑,万物粲然”,④司马光:《太玄集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7页。“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等说法,⑤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三、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7、60页。还是继承原始儒家的文质论调,从君子修身、立德角度来谈文质问题,看重的依旧是文质范畴的道德评价功能,而不是审美意识自觉后所形成的文学批评原则,其直接影响似乎更体现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方面。⑥《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仲尼之后,……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颜师古注:“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质。”(中华书局,1962年,第3582页)这条注释颇能说明扬雄所谓的“文质”仍在乎品人而非品文。到了东汉,班彪称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⑦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其子班固亦言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⑧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可以说,班氏父子是最早将“文质论”真正运用于文艺批评实践的,但是在文质世运说占主导地位的汉代,他们的批评似乎只是父子间的响应,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
曹魏时期,阮瑀与应玚著名的“文质之争”,其实也都不能算作是自觉的文质论文艺思想。阮瑀所谓“盖闻日月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着地,可见而易制。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进而得察,质之用也”,应玚所言“日月运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丽于土,芳华茂于春。是与圣人合德天地,禀气淳灵,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①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二引二人所作《文质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11-412页。事实上关注的是宇宙论框架下文与质的关系,并不是针对审美意义上的文质关系而言。延至南朝,“文质论”才成为评论作家作品、指导创作实践的普遍话语。沈约就曾在其《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称道建安文学“以文被质”;②《文选》卷五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18页。刘勰的《文心雕龙》围绕文质问题,展开了大量论述;钟嵘在《诗品》中称赞曹植诗“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批评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王粲“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③周振甫:《诗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7、16、39页。其他如萧统、萧纲、萧绎等也将文质概念运用到了他们的文学批评当中。
考察文献,梳理“文质论”思想的渊源流变,可以发现在汉代除了班氏父子的点滴论述之外,文质思想主要存在于人格修养与社会政治领域,其何以在南朝骤然于文学领域发展繁荣起来,这是本文着力思考的问题。实际上,作为纯粹意义上的文艺思想,“文质论”在南朝以后的文学批评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典翻译过程中的“文质之争”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魏晋时期的佛典译家已经开始关注译文的文质问题,这在大量的译经序文和僧人传记中都可以发现。而现存最古的佛经目录《众经别录》④自19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发现伯3747号即为亡佚已久的《众经别录》(一般认为撰于刘宋之时)残卷起,这部在唐智昇撰写《开元释教录》时已经“寻本未获”的经录,又重新进入了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更是在概括诸经宗旨之外,对所录佛经译本皆有诸如“文”“质”“文多质少”“多质”“不文不质”“文质均”的直接品评,表现出对文质问题的特别关注。这场在佛典翻译过程中生成的文质辩争,转借了儒家起初只有人格品评和社会政治内涵的“文质”概念,将其运用于译文批评。当时的译家们从“内容与形式”、语言风格两个层面对“文质”进行的辨析,以及在实践中对译文“质文允正”的共同美学追求,标志着“文质论”开始落实为一种产生广泛影响的文艺思想。这一文艺思想对南朝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特别的贡献值得我们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
一、作为“内容与形式”的文质论
佛典汉译之发端,学界对此有不同认识。但东汉桓帝、灵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和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来华入洛京译经,则已为学界认同。自是,不断有佛教典籍传译入华。初期的佛典译师大多来自西域诸国,一方面他们谙熟梵文或西域文字,不娴汉语,导致他们一味强调原文,不加文饰;另一方面,在佛典初译阶段,尊重原本要义和风格,不敢擅自修饰,是译师们恪守的一个原则。如苻秦道安曾评价安世高的译本“贵本不饰”,支谶“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实尚中,不存文饰”。⑤道安:《大十二门经序》《合首楞严经记》,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54、270页。对准确传达原始经义的过分强调使得初期的佛典译文往往缺乏文辞感染力,为救质言之穷,一些译家开始强调文饰,译坛出现“文质之争”。作于黄武三年 (224)的《法句经序》最早记载了佛典翻译文质问题的论争:
始者维祗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①《法句经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第273页。
这篇未注明作者的序文批评竺将炎译文“其辞不雅”,维祗难则借佛言以说明佛经的翻译宗旨在于“当令易晓,勿失厥义”。这里问题的焦点似乎在于语言风格的“雅”或“不雅”,因此以往的论者往往将“文质”仅仅视为修辞层面的问题。但实质上,这场文质论争的根源在于对佛典义理与译文语言关系的思考,因此从根本上讲,是“内容与形式”层面的探讨。上述所谓“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贵本不饰”“贵实尚中,不存文饰”,以及《道行经序》中“因本顺旨,转音如己,敬顺圣言,了不加饰”、《首楞严经后记》中“辞旨如本,不加文饰”,②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第264、271页。《高僧传》中“弃文存质,深得经意”③慧皎:《高僧传》卷一《支楼迦谶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等等,大量类似这样的表述,虽然常常并不是直接将“质”“文”二字对举,但体现的正是作为“内容与形式”的文质内涵。
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文”字的甲骨文及金文的字形各不相同,原意尚未确知。《说文解字》释“文,错画也,象交文”;“质,以物相赘也”。④许慎:《说文解字》卷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85、130页。关于“文”,《易·系辞下》言“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谓“五色成文而不乱”,⑤《十三经注疏》卷八、卷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0、1536页。则“文”即具“彩色交错”这一含义。由此引申出外在文饰之意,与“内质”相对。而“质”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与本质、实质的义项相差甚远。其演变、引申的过程也没有定论。从字形上讲,“質”从两斤,从贝,会意。斤斤,显明的样子。其本义或为:买卖或财物交换时,比对财物或物品之间的价值,使其相当。由财物的价格和其价值相符、不乱要价,或可引申到对事物本身的描述不浮夸,实事求是,得“本质”“实质”之意,与“文”(事物的外表和形式)相对。孔子首开先河将“文质”作为一对概念提出,认为外在礼仪和内在品质相伴适中才能成就君子人格。后来这一概念又推演出社会礼制方面的含义。 《礼记·表记》云:“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⑥《十三经注疏》卷五十四,第1642页。儒家圣贤认为,夏朝尊天命重人道,宽于外在的礼制刑罚,周朝则礼乐刑赏,周密详备,无以复加,这两种治世典范如果走向极端,前者可能会使人民愚朴粗鄙,后者则会因虚文缛节招致怨怼,因此,内在的道德人伦与外在的礼节刑赏都不可偏废。汉代董仲舒等人更是将此观念发展为“文质互救”的政治实践指导思想。但是,无论是就修身之道还是治世之道而言,这对概念的发展始终具有内在与外在、品质与礼仪这样的内涵。由此,在佛典汉译活动中把“文质”引申到“形式与内容”的探讨是很自然的。
虽然学界常常把前秦的道安和后秦的鸠摩罗什分别看作“质”派与“文”派的代表,但实际上在这场译界的论争中并不存在绝对对立的两派。无论是支谦、鸠摩罗什,还是道安以及协同道安译经的赵政,在翻译实践中他们对于以文害质与重质伤文的倾向都是努力规避的。例如,对于同样是“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光赞般若经》之汉译,道安就认为,“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辞质胜文也”,并且指出:“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及腾 (按,或为“反腾”之误),每大简焉。”⑦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第266、265页。在道安看来,一味强调传译佛经义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往往会忽略其表达形式的语言美感;而删削重复,形式简约,固然有“易观”的好处,但删繁就简难免会伤及内容的完整性。对于如何处理好佛经翻译过程中“事”(内容)和“饰”(形式)的关系,道安始终认为这是一个译事上的难题。
经过长时间的译经实践与思考,道安与赵政悟出“经之巧质有自来矣”,①道安:《鞞婆沙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82页。即经文的“巧”或“质”,乃是由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一定的内容对于形式是有选择性的,恰当的形式对于内容的彰显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二者的统一不是简单的不能分割,缺一不可,而是一种更复杂的配合关系。吕澂说:“大乘经可以‘文’一些,而戒律则非‘质’不可。毗昙有一定格式,也不能够删略。……般若一类的思想是很阔大的,但思想总要通过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因此,‘逐事而明之’,就是它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比方说,他们讲般若是因,而其结果则为‘一切智’。‘一切智’,就是什么都知道,非列举诸事不可。过去的翻译,把‘一切智’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删掉了,因而使人很难理解般若是什么。”②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页。例如,《放光般若经》和《光赞般若经》③《放光般若经》,无叉罗、竺叔兰译,《大正藏》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5年,第1-146页;《光赞般若经》,竺法护译,《大正藏》第8册,第147-216页。是同本异译的“般若经”。在《光赞般若经·分别空品》中,佛祖为须菩提说法,然后向须菩提提问,看他是否理解。反复问难,有数十问答,颇为重复铺排。与之相应的《放光般若经·行品》则将问答的重复部分完全删略。对此,道安评价说:“叉罗、支越,斲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④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0页。在道安看来,般若类经典繁复质朴的形式特点正是由其阔大的思想内容决定的,轻易删削,只会“惧窍成而混沌终”。也就是说,应该遵循特定内容对其最佳表现形式的选择性。
赵政与道安的主张超越了孔子“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简单的二元对立思想影响下的文质论文艺批评,使得这一理论不致流于肤浅,对今天的文论研究仍具参考价值。有学者认为,“文与质作为两种基础审美风格,实质上是因形式与内容二要素在审美对象中量的比重关系而形成的两种对象结构类型,是在审美对象结构类型基础上产生的审美风格”。⑤薛富兴:《文与质:一对具普遍意义的美学范畴》,《学术研究》2012年第7期。佛典翻译的实践与理论探讨说明,形式可能具有某种含义,而内容也会依本身选择形式,二者很难完全割裂,更无法用科学主义的天平称出一个孰重孰轻的比重关系。
后秦鸠摩罗什的译经,也往往依据经义,灵活处理译文,实现汉译佛典中文质关系的调和。兹以鸠摩罗什所译《大庄严经论》为例:
汝若欲知可炙处者,汝但炙汝瞋忿之心,若能炙心,是名真炙,如牛驾车,车若不行,乃须策牛,不须打车,身犹如车,心如彼牛,以是义故,汝应炙心,云何暴身,又复身者,如材如墙,虽复烧炙,将何所补。⑥马鸣:《大庄严经论》卷二,《大正藏》第4册,第266页上。
这段话是一位比丘尼所言。比丘尼见一位婆罗门不追求心灵觉悟,一味苦行伤身,就想要启发他,“汝可炙者而不炙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却反而激起婆罗门恼怒,于是再申劝解。陈寅恪曾据梵文本加以比对,发现此节原本为偈体,汉译则为朴素平易的散文体。面对婆罗门的急躁、恼怒,直接解说清楚道理应比唱偈更合常理。鸠摩罗什不拘泥原文体式,选择用质直的散文体表现比丘尼用打比方来讲道理,更能显明经义,感染读者。这样理解鸠摩罗什对佛典原文的变易,方能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知哲匠之用心,见译者之能事”。⑦参见陈寅恪:《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27年第2期。陈寅恪认为,汉译《大庄严经论》与梵文残本《童受喻鬘论》“内容又无不符合,则今所谓马鸣之《大庄严经论》,本即童受之《喻鬘论》,殆无可疑”。
当然,在不影响经义的情况下,鸠摩罗什对文辞典雅的追求更常常为人所称道。《高僧传·释僧叡传》载:“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其领悟标出,皆类也。”①慧皎:《高僧传》卷六《释僧叡传》,第245页。鸠摩罗什译本的辞美义足使其达到早期汉传佛教译经的巅峰。僧肇评价什译“考校正本,陶练复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宗致划尔,无间然矣”,②僧肇:《百论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第403页。此说可谓精到。鸠摩罗什译本的流行使得早期片面强调论旨甚至不惜弃文以存质的倾向得到扭转。辅助鸠摩罗什译经的诸位高僧受其影响,也都重视译本的文采, “时有生、融、影、叡、严、观、恒、肇,皆领悟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旨,任在伊人,故长安所译,郁为称首”。③慧皎:《高僧传》卷三《僧伽婆罗传》,第142页。
南朝的佛典译文虽然更注重语言的文丽简约,但是强调原本经义的“尚质”传统依然或隐或显地约束着译师们。《高僧传》曾记载这样一则译事:“《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严乃梦见一人,形状极伟,厉声谓严曰:‘涅槃尊经,何以轻加斟酌。’严觉已惕然,乃更集僧,欲收前本。时识者咸云:‘此盖欲诫厉后人耳,若必不应者,何容即时方梦。’严以为然。顷之,又梦神人告曰:‘君以弘经之力,必当见佛也。’”④慧皎:《高僧传》卷七《释慧严传》,第262-263页。《大般涅槃经》原有北凉昙无谶的译本四十卷,世称北本,经慧严、谢灵运、慧观等治改后成三十六卷,世称南本。虽然品目有所变化,但文字上不过稍有差别。汤用彤曾比对过这两个译本:“至若文字上之改治,则常因原文之过质。如北本曰:‘犹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丧亡,送其尸骸,置于冢间,归还怅恨,愁忧苦恼。’南本改曰:‘犹如慈父,唯有一子,卒病命终,殡送归还,极大忧恼。’”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6页。虽然文字上的改动极小,但是慧严仍然内心惶恐,怕失去原典风貌,以致梦见神人警告。可见早期佛典汉译“文质之争”带给译师们的心理影响之大。也正是因为佛典翻译过程中对义理的忠实与对译文文丽雅致的追求往往难以平衡,文本“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在早期佛典译家们的辩难中逐渐显露,从中孕育出文学实用理论、接受理论、文学审美理论的种子。
通过传译异质文化背景中的宗教经典,使其宗教信仰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彰显和光大,赢得信徒并进而取得相应的文化地位,达到经教流传的目的,是所有宗教经典翻译的共同旨趣。佛典汉译亦是如此。在汉语文化传统中,儒家对于文学伦理性的认知,导致了实用性理论的形成,强调文学的政治、道德功能,而不是其审美作用。佛典汉译中对文字“易晓”“易观”的追求,主要着眼于宣教目的,实际上是将文艺的实用功能从政治、道德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了宗教领域。无论是《诗大序》中所讲“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⑥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3页。还是王充主张的“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⑦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69页。儒家早期的文学实用理论关注的焦点过多地集中于文学对读者的道德、政治影响,对影响如何发生,以及文学传播中作者与读者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则鲜有关注。而佛典译家则既要尽可能地保证译本“不失本旨”,还要考虑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较之儒家的文学观念,这种双重意识,凸显了难得的读者意识,表现出文学观念的一种进步。
二、作为两种语言风格的文质论
魏晋南北朝佛典翻译活动中的“文质”论争虽然在根本上讲是对译文“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的探讨,但它往往首先由文丽与质朴这两种语言风格的竞逐引发。诸如《法句经序》作者对竺将炎译文语言“质直”“不雅”的批评,支敏度对支谦译经“颇从文丽”⑧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第270页。的称赞,类似的修辞角度的译经评论在当时的佛教文献中不胜枚举。南朝梁僧祐总结自汉至梁的佛典汉译业绩时就曾评价:
昔安息世高聪哲不群,所出众经,质文允正。安玄、严调,既亹亹以条理;支越、竺兰,亦彬彬而雅畅。凡斯数贤,并见美前代。及护公专精,兼习华梵,译文传经,不愆于旧。逮乎罗什法师,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机水镜,故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至昙谶之传《涅槃》,跋陀之出《华严》,辞理辨畅,明逾日月,观其为美,继轨什公矣。至于杂类细经,多出《四含》,或以汉来,或自晋出,译人无名,莫能详究。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故知明允之匠,难可世遇矣。①僧祐:《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出三藏记集》卷一,第14页。
“文丽与质朴”这对“文质”义项和其“内容与形式”义项有着无法割裂的逻辑关联:一味强调义理的信实而忽视表达的形式,可能导致文辞粗俗;努力追求辞采文丽的表达形式,却也可能牺牲部分原典的意旨。正如僧祐在这里所指出的,译经时如果把握不好这两种语言风格的尺度,会失之于浮艳或粗鄙,影响经义的传达。修辞适中,不伤于野艳,才能既不失美感,又能显明经义,成就优秀的译本。
可以说,“佛经翻译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文’和‘质’变成了修辞风格的术语,这是文体讨论的参加者们所没有想到的”。②李永红、金瑾英:《佛经翻译的“文”“质”概念与〈文心雕龙〉之“文质论”》,见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续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9页。南朝萧统、萧绎都曾从文章修辞风格角度讨论“文”与“质”。如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亦言及“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而有质”。这与前述僧祐“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的表述极其相似。而从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对裴子野诗“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的批评,③以上三文参见严可均:《全梁文》卷二十、卷十七、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16、195、115页。也可看出“文质之争”的影子。“三萧”之父梁武帝萧衍崇信佛教,在位期间大力推动译经事业,积极参与注经弘法,他即曾在《注解大品序》中言及“广其所见,使质而不简,文而不繁,庶令学者有过半之思”。④萧衍:《注解大品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6页。受乃父影响,萧氏兄弟深通佛典,常与当时名僧学法讲经,并写作了许多有关佛教的诗、文,《广弘明集》中就收录了萧纲此类诗、文31篇 (首),萧绎5篇 (首),萧统11篇 (首)。⑤另参见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第三、四章,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谭洁:《南朝佛学与文学:以竟陵“八友”为中心》第五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萧绎《金楼子·著书》更在四部之外,列出其所著《内典博要》。佛教译经借儒家的“文质”话语来讨论译文,对于“三萧”这样既有深厚儒家修养,又崇信佛教的文人来说,接受佛教翻译的“文质论”影响也并非不可能。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佛典翻译既要顾及目的语语言风格和文化审美取向,还要忠实于原典语体风格,这样的两难处境是产生修辞层面“文质之争”的一个深层原因。道安等被视为崇尚质朴风格的译家并非缺乏传统的文学修养,只是他们认为朴素、质直、繁重是所据佛典固有的语体风格,在翻译中应尽量保持。道安曾提出:“译胡为秦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⑥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0页。这里道安所提出的“五失本”主要是针对以中亚语言⑦古代中亚语言又被汉人称为胡语,主要有吐火罗语、塞语、粟特语、犍陀罗语等。或混合梵语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为载体的早期佛典而言的,它们比起后起的较为纯净的梵语文本来说,则质朴、繁复得多。故道安所说的“胡经尚质”“委悉”“反腾”等,正是对“胡语”质朴、繁复语言风格的总结。同时,他又充分认识到汉语典籍文丽、简约的特点,因而对译经语言风格迎合汉语文化以致“失本”也颇感无奈。
李炜曾将汉译《撰集百缘经》与梵文原本进行对比:“在对照表中的梵文文本里:当众佛、众世尊露出微笑的时候,同时从口中放出蓝色、黄色、红色和白色的光,这些光照向下方,照到八个热地狱和八个寒地狱,那里人的痛苦被解除……;光照向上方,照到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 (共二十二个神界);又照到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世尊有愿望去解释过去的业,这些光在世尊的后面消失;如果他有愿望去解释将来的业,这些光在世尊前面消失;…… (光在佛身体的十二个部位消失)。现存几种梵文文本中均有的这样长的一段描述在汉语译文里只有一句话‘出五色光,遍照世界’。”①李炜:《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与翻译方法初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0页。即便用汉译佛典的不同版本来对读,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裁斥”“刈除”的现象在当时的翻译实践中并不少见。僧叡《大智释论序》及作者不详的《大智论记》就指出,鸠摩罗什所译百卷本《大智度论》也不是完整翻译。而由于百卷本也过于庞大,如庐山慧远《大智论抄序》中所言,“文藻之士犹以为繁,咸累于博,罕既其实”,②以上三文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87、388、391页。为此慧远还制作了二十卷的《大智论抄》。
在考察印度佛教文献的传播时,往往可以发现简洁与冗长的文本同时存在。正如慧远《大智论抄序》中所说“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在传播教义时,可能采取两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即采用最小众的精英化语言进行简洁宣讲,或与之完全相反,极其详尽地全面论述教义。但是,正如日本学者船山徹文所指出的,“与印度相比,中国方面具有明显的节略经典、制作摘要版的倾向”。③船山徹文:《六朝佛典的翻译和编辑中存在的中国化问题》,《法音》2014年第2期。即以《大智度论》为例,虽然罗什翻译的梵本是“全本”或是“略本”至今仍无定论,但诸说皆承认罗什译本为略译本。如慧远《大智论抄序》就认为,“童寿以此论深广,难卒精究,因方言易省,故约本以为百卷,计所遗落,殆过叁倍”;僧睿《大智释论序》说过,“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繁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论》之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胡文委屈,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大智论记》也指出,“论初品三十四卷,解释一品,是全论具本。二品以下,法师略之,取其要。足以开释文意而已,不复被其广释。若尽出之,将十倍于此”。④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91、387、388页。
相较印度,佛典初入中国时这种更显著的节略经典的倾向可以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加以解释。文化呈现出强语境 (high context)和弱语境 (low context)两种态势。在强语境传播或信息传递中,多数信息不是处于物理语境之中,就是已内化于人自身,很少进入被编码的、明晰的传播过程。而在弱语境传播中,情况却相反,大部分信息都被赋予明晰的编码之中。⑤爱德华·T·霍尔:《语境和意义》,见《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7页。在佛典汉译过程中,无论梵语还是其他中亚语文化都是处于弱语境态势,需要“不嫌其烦”地把所有信息都表明在文本中,而汉语文化相对处于强语境态势,很多语境中所包含的,或是人们信息系统中储备的信息就不会再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在弱语境向强语境的文化传播中,具有两种不同语言风格的文化碰撞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另一方面,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比较开放,允许信徒们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宣传教义。⑥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57年第1期。听闻说教的众生根机利钝不同,对于普通信众就需要运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尽量朴素、详尽地说明。尽管学界对早期汉译佛典所据原典的语言问题至今仍无定论,⑦法国学者西尔万·列维 (Sylvain Lévi)和我国学者季羡林认为早期汉译佛典是从吐火罗语翻译而来,英国学者贝利 (H.W.Bailey)和布劳 (John Brough)则认为早期汉译佛典译自犍陀罗语,李炜的最新研究认为早期的汉译佛典来源于带有中古印度方言特点即早期各地普拉克利塔方言特点的佛教混合梵文。参见李炜:《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与翻译方法初探》,第174-178页。但是诸家皆不反对早期汉译佛典所据原典的语体带有俗语、方言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其语体风格的质朴、繁复。因此,早期译家们注意到所据佛典不同于汉语典籍的语体风格是很自然的。中国早期佛典翻译中两种语体风格的竞逐,还使得二者所伴随的语言表达方式,即俗语与文言在书面使用中的冲突开始凸显出来。“尽管中国权威顽固地抵制把自己的俗语当作国语——也许是由于文言过高的威望与力量——佛教徒却在自己的书面语中不受限制地使用俗语”。①梅维恒 (Victor H.Mair):《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99页。在汉语语境中,口语和书面语的明显对立,导致了精英文化的书面语权威的确立,尤其在知识精英层面,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几乎一统天下,引领着读书人向着唯美化的方向迅猛行进。而佛典的翻译活动,“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②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这种文学新体,半文半白,夹杂大量口语、方言,运用了不少俗字,与正统的骈俪化文学,显得格格不入,必然会引起一些有着极高文学修养的汉僧的强烈非议。但是,在实际翻译中,道安、赵政等译家仍然尽最大努力避免失去佛典原文的语体风格,他们认为:
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③道安:《鞞婆沙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82页。
道安等人的文质思想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前文已经述及的作为“形式与内容”的文质问题,即“经之巧质”与所传之“事”的关系问题;二即“胡言”和“秦语”的语体风格问题。这些“尚质”译家的坚持,一方面保留住了很多弱语境的信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本土文学审美取向的多元化:即追求唯美的骈俪文学不再是唯一的审美诉求。即使鸠摩罗什这样比较重视辞采,讲究简约的译家,其译著依然能体现出所据佛典质朴、繁重的语言特点,被赞宁称为“有天然西域之语趣”。④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满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页。梁启超谓此评价,“洵乃精评。自罗什诸经论出,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⑤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05页。相对而言,无论在书面语还是口语中,含蓄、简约之美一直都为汉语文化所崇尚,尤其是在书面语中,“精约”更是文言的内在要求。但是在接受了佛典跨文化的传播之后,人们也可以欣赏那些“辞直义畅,切理厌心”的“语趣”了。在将俗语、口语纳入书面语的历史进程中,佛典汉译所起的重要作用显然是不容置疑的。
三、刘勰“文质论”文艺思想与佛教“文质译论”
佛典翻译活动中关于“文质”关系的探讨对当时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就可见一斑。如,《征圣》中言“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指出文采与质实兼善才是文之典范;《辨骚》中告诫诗人学习借鉴《诗经》《楚辞》,要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强调不能仅仅欣赏经典的辞采而忽视其主旨;《序志》中云“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则是直接批评其时藻饰过度而内容空洞的文风。这些论述和大量佛典译文批评一样,虽然没有直接用到“文”“质”二字,但实际上讨论的正是文质关系问题。而《情采》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更是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质论”文艺思想。他的论述已经超越了儒家的人格论与治道说文质范畴,是在文学意义上自觉地探讨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此外,在《才略》中刘勰评价荀子之文说:“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①以上引文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6、48、726、537、698页。他称赞荀子状物成赋,文辞和内容相称,表达出大儒的情思。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提出了文章风格与时俱变的观点。如他在《通变》中先总结了从黄尧到魏晋九代的文风演变,接着指出:“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变通矣。”在他看来,只有博观精研古今作品,既不盲从新奇讹浅的时流,也不陷入因袭守旧的圈套,独立地在文质之间斟酌尽善,在雅俗之间安排妥帖,才能会通变革,日新其业。在《时序》中,他不仅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质文沿时,崇替在选”,而且还进一步说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②以上引文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520、671、675页。认为政教、学风、时俗等因素都会对文风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虽然自董仲舒提出“王者以治,一商一夏,一质一文”起,“质文代变”“文质再复”的观念就颇为流行,但这还完全是一种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刘勰将此观念运用在文学领域的风格演变,毋宁说更接近道安、赵政“文质是时,幸勿易之”③道安:《鞞婆沙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82页。的文质发展观。就是说,一般的“文”与“质”风格标准,往往会易世而变:古人不以为“质”的,于今可能被目之为“质”甚至“野”;现今不以为“质”的,将来亦或被目以为“质”,因此不能随意以今俗妄断古经。刘勰主张考察世情、时序以鉴赏历代文章的思想与之完全契合。此外,在《书记》中刘勰讲状、列、辞、谚的写作时说:“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460页。他认为文质之用,各有体宜,必须随着内容确立体制。这种“随事立体”的思想与前述道安、赵政对佛典内容与形式的选择、配合关系之探讨,也不无暗合。
沈约、钟嵘、“三萧”等重要批评家都曾以文质观念批评作品,但是真正系统地以文质论文是《文心雕龙》,所以考辨刘勰“文质论”与早期佛典汉译过程中的“文质译论”之关系,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据《梁书》记载,在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之前,刘勰一直依附于定林寺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⑤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刘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0页。《高僧传》亦载僧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⑥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僧祐传》,第440页。因此,在僧祐“造立经藏,搜校卷轴”的过程中,如《梁书》本传所言,刘勰协助僧祐抄写、整理甚至可能撰写了其中一些记序。关于刘勰的“录而序之”,后人也有论及。如明代徐惟起《文心雕龙跋》曰:“曹能始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手笔。’今观其《法集总目录序》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之论,不诬矣。”对此,杨明照也认为:“僧祐使人抄撰诸书,由今存者文笔验之,恐多为舍人捉刀。”⑦参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49、393页。而范文澜在《序志》篇注中早已指出:“僧祐宣扬大教,未必能潜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彦和手也。”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30-731页。饶宗颐亦怀疑《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是刘勰的代师之作。⑨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日本学者兴膳宏更是从思想内容、遣词用字等多方面论证《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之关系,认为刘勰《练字》《灭惑论》与僧祐《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存在着“亲缘性”,《出三藏记集》当有多篇文章出自刘勰之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僧祐自己在此书中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用他自己名字发表的著述不一定由他本人执笔。例如卷十二《经序》部末尾有‘僧祐编’《法集杂记铭》七卷,列记了序和篇目,其中除僧祐自己的著述外还有刘勰撰《钟山定林寺上寺碑铭》一卷、《僧柔法师砷铭》一卷及沈约撰《献统上碑铭》一卷。僧祐在序中说:‘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造自鄙衷。’”[10]兴膳宏:《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彭恩华译,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20-21页。
《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中总结了自汉至梁各位译师的文质风格,特别强调译笔文质对经义传达的作用:“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于执笔。”①僧祐:《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出三藏记集》卷一,第14页。该文既有对译文内容与形式关系之探讨,又有从文章修辞角度对各位译师译文文质风格的品评,其对译文“质文允正”的追求也与刘勰论文“文质相称”的思想一致。即使此篇确实是僧祐授意,而刘勰仅仅走笔成文,其师的译经文质论思想也应为刘勰所接受。因此,正如潘重规在分析《文心雕龙》中的文质论思想时所指出的:“僧祐留意译经,彦和编校佛藏,故论译述与创作文质之宜,其言密合如此。”②潘重规:《敦煌写本〈众经别录〉之发现》,《敦煌学》第4辑,1979年。除了《出三藏记集》中的一些篇目,白化文还怀疑前文曾经提及的《众经别录》亦为刘勰所作。③白化文:《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虽然对于刘勰是否为译经撰写过记序,《出三藏记集》哪些记序是其所撰,《众经别录》是否也出自其手等问题,尚无确凿论据证实,但他曾协助僧祐进行校录工作,了解僧祐的翻译思想,能接触到定林寺在当时规模最大的馆藏佛教译经,熟稔《出三藏记集》所载诸译序中的文质译论是完全具备条件的。因此,刘勰继承乃师译论中的文质观,接受在译经文质之争中已成为译文品评术语的文质概念也应是水到渠成之事。特别是在儒家文质人格论与文质世运说仍然颇为盛行的当时,他从独立的文学角度对创作的文质之宜进行系统论述,这很难说没有受到佛典翻译过程中对译文文质大规模探讨的影响。
四、结 论
“内容与形式”是典型的西方文论话语,西方注重修辞的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的传统认为,形式所指的是语言构成的诸因素——节奏、音律、词汇、形象,而内容所指的是主旨或教训。对于内容与形式的严格的区分,在马克思主义批评派那里得到了延续。但是这种割裂已经被20世纪的批评家克罗齐、俄国形式主义派、美国新批评等所摒弃。形式与内容相互作用并且浑一的观点,在现代文艺批评领域中已经被牢固地树立起来了。韦勒克曾在《二十世纪文艺批评关于形式与结构的概念》一文中不惜笔墨,详细地梳理了西方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传统和现代观点,指出:“我们看到‘形式’事实上以某种方式囊括和渗入到主旨中去,构成了更深刻、更实在的含义,超乎抽象的主旨或外在的装饰之上。”④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37页。从赵政、道安、刘勰对于文质的思考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西方文论在这一点上的冥契。虽然中西方文论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对传统文论资源的整理与归纳中寻绎出颇具现代性意义的价值取向。
作为儒家人格论与治道学说的“文质论”在南朝时期骤然繁荣于文学领域,无疑是与魏晋以来佛典翻译过程中对译文文质问题的长期探讨分不开的。佛典译家们接过儒家的“文质论”话语来进行翻译批评,他们对于佛典“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对后来文学实用理论、接受理论、文学审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对佛典译文语言风格的论争也促进了文学审美风格的多元化,使得质朴、繁复成为汉语精约、含蓄的审美风格之外可欣赏的一种“语趣”,在俗语书面语产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道安、赵政等人的“文质”发展观和对“质”与“文”之间选择性关系的主张更具启发意义。佛典翻译过程中不断深化的“文质论”终于在刘勰集南朝文艺理论之大成的《文心雕龙》中发展成为成熟、系统的文艺思想。不过,唐代以后,随着儒学的进一步强盛,“质”的内涵基本上被狭义化为儒家之“道”,“文”与“道”成为并立的范畴。随着古文运动的推进,“文道论”逐渐取代“文质论”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主导话语。宋代以后,文以载道、重道轻文的“文道论”更被推向极致。“文质论”只是作为汉代发展起来的治道学说延续下来,直到明清之际,王夫之等学者才重新关注作为文艺思想的“文质论”,但是也很少有超出前人的创见。“以道衡文”仍然是当时理学语境中学者文人无法摆脱的主流思想。⑤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文质论》,《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在佛典翻译方面,由于“隋唐时代,国家组织的译场人员齐备,水平极高。有精通梵汉两种文字的译主,有缀文、证义、参译、刊定、润文等反复校量译文‘文质’务使其‘均’的众多助手,有更多的参听讲说者参加讨论提意见。译文水平有了保证,这就使文质之评成为多余的事。即使有点小问题,对皇帝亲开的大译场的工作成果,敕定颁布的经文,也没有人敢去下鉴定”。①白化文:《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因此,佛典翻译过程中的文质批评也由此渐衰。《大唐西域记》书末所附辩机撰写的《记赞》中记载了一位“搢绅先生”的进言:“传经深旨,务从易晓。苟不违本,斯则为善。文过则艳,质甚则野。谠而不文,辩而不质,则可无大过矣,始可与言译也。”这可以说大体上反映了玄奘的翻译思想,基本沿袭了僧祐《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中的文质观,仍然追求“质文允正”。但由《记赞》中所载僧众将玄奘译经的地位类比于孔子删定《春秋》,认为玄奘译经“非如童寿逍遥之集文,任生、肇、融、叡之笔削。况乎园方为圆之世,斲雕从朴之时,其可增损圣旨,绮藻经文者欤”,②引文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46、1047页。可知,玄奘在译经过程中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且他并不轻易删削经文、藻饰文字。相较什译“任生、肇、融、叡之笔削”,玄奘对经文原典的透彻理解和母语的绝高造诣,使其对译本文质的处理,赢得了僧众的绝对信任,对文质问题的直接讨论也就比较少见了。
作为中国文学奠基理论,除了南朝文学批评家的文质批评,魏晋南北朝大量针对佛典译经的文质批评,也是我们研究这一文艺思想亟待挖掘的资料。类似“文质”这样源自儒家正统学说,而后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艺思想内涵的概念还有不少,这也是今后研究应该着重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