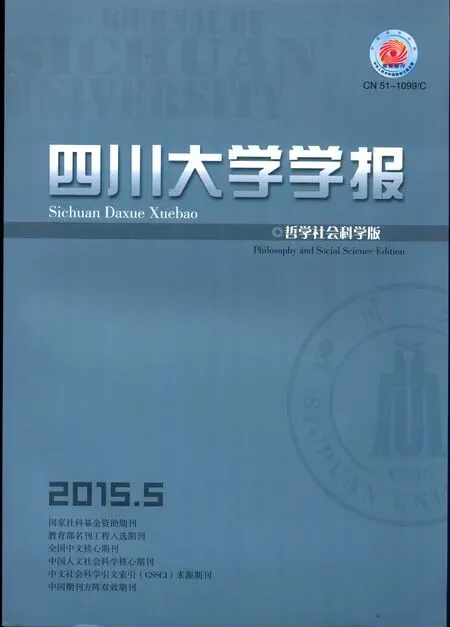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依托的内外资源探析
田庆立
战后日本素以“和平国家”与“民主国家”自居,然而,在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后,无论是其对内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还是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并通过安保相关法案,甚或大肆宣扬“积极和平主义”,实质上都在从根基上侵蚀和瓦解着“和平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基础。“历史修正主义”和“防卫修正主义”思潮及举动肆意蔓延,不免使人们对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产生了诸多疑问。由此,亟须对形塑战后日本国家认同①国家认同的概念十分宽泛而富含多样性,其内涵主要关涉国家的独特性,即“我们”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譬如,既可能是由族群或语言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独特性,也可能是由社会意识形态与制度构成的独特性。当某种独特性被大多数国民所认同,就构成了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本文所阐述的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建构,主要是基于建构主义的“自我—他者”的认知模式分析框架,侧重从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角度,集中考察作为形塑日本国家认同的主体——政治家、知识精英及普通国民——如何为突出和强化自我民族特性而付诸努力,又是如何依凭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外来资源为其建构国家认同服务。无疑,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形塑国家认同的思想资源多种多样,既包括本土资源,也包括外来资源。就战后日本而言,本文仅择取作为本土资源的天皇制展开论述,但并不意味着否认甚或忽视其他传统文化在形塑国家认同中所起的应有作用。同理,作为日本确立“自我”参照物的“他者”也有很多种,既包括文中提及的美国、中国,当然也包括德国、法国、苏联 (俄罗斯)、韩国等其他国家。限于篇幅,且笔者认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他者”在建构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过程中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所以才试图从微观视角进行论述和解读,以期达到管中窥豹的目的。的国内外资源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学理性探讨,才能深刻地认识到右翼保守主义思潮依然泛滥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即是天皇制的存在。同时,日本政治家和知识精英还通过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外来资源进行有目的的“整合”和“解读”,从不同侧面塑造了迥然有异的美国和中国的“他者”形象,旨在不断增强国家的内聚力。若从思想观念和行为认知层面厘清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可以深化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和社会总体保守化形成的思想根源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会对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日本缘何依然奉行“亲美抑中”战略作出合理的解答。显然,若希冀对当前的中美日三边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从思想认知层面解读和梳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建构轨迹,对于研判今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和未来走向,无疑会大有助益。
一、“自我—他者”认知模式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
所谓“自我-他者”的认知模式,是指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不仅包括对共同体“自我”①“自我”的概念最初源于法国医生拉康的“镜像理论”,其后被移植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之中。本文运用的“自我”与“他者”概念主要遵循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民族国家行为体的人性化指涉。具体而言,所谓“自我”即指日本民族国家本身,“他者”主要指作为日本确立“自我”主体性参照物的美国和中国等国家行为体。相关概念可参阅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本身共性的尊崇及体认,还包括对异域和“他者”的认知和想象。国家认同不仅根据本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国民特性从内部加以界定,同时也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对,在不断寻求差异性的互动中建构起来,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国家认同具有双重特性和功能:一方面是要求共同体成员“向内看”,产生一种共同体的自我意识,界定谁是共同体的成员;另一方面是“向外看”,识别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不同,界定谁不属于本民族 (国家)。因此“他者”的观念内在地存在于民族主义信条之中,对于大多数民族 (国家)共同体来说,都曾经存在而且可能仍然存在与本民族 (国家)共同体相区别的“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②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他者”是表现“我们”的同一性或身份归属的前提。就人类集团的同一性而言,“我们”的同一性是通过相对于“他们”的差异性而被类型化的。同一性始终以“与他者的差异意识”为前提,蕴含着排斥和压迫他者的逻辑冲动。“自我”在确定自己特定身份的同时,也确定了“他者”相应的反角色,这种反角色使得“自我”的身份具有了意义。③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2页。
建构国家认同首先是从“自我”的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并结合现代性语境予以重构。同时,必然伴随着建构“他者”,认同大都是“想异”而“构同”,想象出对立面的“敌人”即“他者”,才能建构出“自我”的认同。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动力机制体现为,一方面热衷于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旨在突出和强化“自我”;另一方面则注重与外在的“他者”进行比对、互动及博弈,以期形塑富有自身特色的身份认同。
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资源主要涵盖三个层面的内容 (参见图1),作为本土资源的象征天皇制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外来资源,它们自内而外地界定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向度。从“自我—他者”的认知模式来看,建构国家认同包含着“求同”与“斥异”的二重向度。“求同”意味着从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中谋求同一性,就日本而言,战后的象征天皇制④有关日美两国在象征天皇制形成过程中的互动博弈可参阅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53-319页;田庆立:《象征天皇制与日本民主主义的融合与冲突》,《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即是通过对“自我”既有的本土资源——天皇制进行重新整合,使其发挥强化身份认同和加强国民统合的机能,具有“同一性”与“整合性”的特征,是形塑国家认同的核心精神资源,也是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国家自豪感和实现“自我”确证的重要手段。

图1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本土资源及外来资源
“斥异”所蕴涵的内在逻辑则相对较为复杂,一方面,“自我”通过与先进的“他者”进行比对后,认为自身与其存在差异,进而通过习得的方式向先进的“他者”学习,力图消除两者之间的水平差距。日本社会心理学家井上忠司认为:“在我国,人们自古以来一直采取完全根据外集团的价值基准来观察内集团中的自我这样一种行为方式。”①井上忠司:『「世間体」の構造』,東京:NHKブックス,1977年,第80页。显然,美国这一先进的“他者”在建构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即充当了价值标准的角色,通过对美国的全方位追随以及对美式民主主义理念的引入,“亲美”思潮成为审视和观察日本形塑自我身份的“风向标”,体现出“依存性”的特质。同时,为谋求国家的“自立性”和“自主性”,“反美”情绪及斗争也一直或明或暗地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斥异”还体现为想象和寻求对立的“他者”,通过确立本民族国家的对立面和假想敌的方式,有意识地利用和倚重民族主义的能量从外部强化和促进国家认同的凝聚。冷战时期,中国这一“他者”更多地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日本通过与中国的横向比较,突出和强化自身在亚洲具有不可撼动的“优越性”地位。后冷战时代,随着中国崛起,日本逐步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对华“警戒性”的一面日益凸显。
二、象征天皇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国民统合
天皇制起源于日本古代社会,至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大体经历了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象征天皇制三种发展样态。古代天皇制主要以儒家思想、佛教和神道教为精神支柱;近代天皇制融合了传统儒学的“忠孝”观念、国家神道的神统思想及西方的立宪主义,通过《明治宪法》赋予了天皇集神政、家长式权威及立宪主义三重特性于一身的无上权力;象征天皇制的法理依据主要来源于1946年11月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其中第1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②渡边洋三:《日本国宪法的精神》,魏晓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与战前的近代天皇制相比,象征天皇制中的天皇不再拥有政治权力,仅保留在礼仪性事务中对国民具有的权威。天皇制在形塑日本的民族特性与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维系和支撑日本民族精神内核的就是绵延不绝的天皇制。在建构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象征天皇制作为日本政治家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重塑,主要发挥强化身份认同、凝聚国民统合的“自我”确证效能。
(一)富有国民统合机能的天皇制
天皇制在日本拥有悠久的历史,战后日本的象征天皇制作为形塑国家认同的核心精神资源,成为统合国民的象征符号。有日本学者认为:“我国上承万世一系之皇统,举国国民对皇室常怀万国无与伦比的尊崇忠诚之念,实乃我国国民团结之中枢,系为我国国家最为强大之处。”③美濃部達吉:「民主主義と我が議会制度」,『世界』1946年1月号。美国学者约翰·道尔也指出:“日本现代经验的短暂周期,几乎与裕仁天皇的统治时期完全一致。天皇是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试金石,是从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了无痕迹地过渡到帝制民主的象征。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对那些希望强调种族和文化的‘国民统合’者而言,天皇都是最显而易见的图腾号召。”④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547页。
天皇制的政治机能主要体现在国民统合的意蕴上,旨在巩固和树立“自我”的自信心,“国民统合”实际上是表达旧有“家国”思想的新形式。和谐与等级被认为在价值上高于竞争和个性,新的天皇象征仍然体现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发明的“大和民族”的特性,从而排斥朝鲜人、台湾(地区)人、中国人、高加索人等一切外来人种成为“日本人”。抛开宗教和国家的正式分别不谈,天皇仍然是日本本土神道教的大祭司,在皇宫中举行深奥的仪式,并前往伊势神宫向他的神的祖先禀告。所有这一切仍然让他成为种族隔离和血统民族主义的最高偶像,体现着想象中的、使日本人有别于并优越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所谓永恒本质。⑤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254页。
在美国主导下,盟军并未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也不再是“现人神”,在“人间宣言”中作为神的天皇信仰也随之消失。然而,这些举措并未改变日本人崇拜天皇的意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拥护天皇的社会心理基础。加上战后裕仁天皇在日本国内各地“巡幸”,以及媒体对“民主化天皇”的大肆宣传,间接强化了美国占领政策中拥戴象征天皇的国民意识。①南博:《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邱琡雯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与《日本国宪法》同时公布的新宪法义解对天皇与国民之间的关系作了如下解释:“我国的基本特色是以深藏于国民心中的对天皇的倾心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国家是以向往天皇为核心的全体国民的结合。即国民以天皇为向往之核心,因此,仰视天皇时,便能看到日本的国姿,而且也能看到国民自身结合之姿态。本条乃是立足于我国的这一基本特色之上,用‘象征’之词来表达天皇所具有的本质。”②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4页。
象征天皇制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发挥着凝聚国民共识、增强国民整合性与同一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行发挥着“稳定器”的效能。“战后日本的新价值体系,虽然从主张国民主权的原则出发,但仍保持天皇为日本国的精神象征,对缺乏‘独立自主’经验的日本国民来说,如果失去任何精神依托及信仰的表象,恐怕就会产生不安的感觉吧。因此天皇的地位,从神权性绝对性的主权者,转化为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象征天皇制’已失去政治机能,但又产生安定体制的另一政治机能”。③许介鳞:《谁最了解日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二)日本政府着力强化国民对天皇制的认同
政治价值系统是一整套逻辑上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提供一套认知系统 (cognitive system)以及象征符号体系,从而唤起民众“对统治者合法性的信仰”。④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9页。天皇制在日本政治体制中发挥的主要效用即为培养国民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心理。曾任自民党宪法调查会会长的保冈兴治在宪法修订案中强调,应该突出“我国的独特特征”,“简言之,就是国家认同。比如,天皇是日本历史传统的集中表现。我们的文化被世人视为优秀的文化,天皇制是国民情感表达所系,是国民可敬的献身精神之象征与指引,这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⑤保岡興治:「憲法激論 (2)自民党」,『週刊金曜日』2004年6月25日。2012年2月,自民党制定宪法修正案,主张通过修改宪法,从而确立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通过赋予天皇以新的地位和精神权威,以期达到凝聚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目的。
和辻哲郎认为,战后的天皇制是日本“文化共同体”的象征。《日本国宪法》只不过改变了明治时代发展而来的“政体”,作为日本人本质性特征的天皇崇拜却并未发生变化而一直持续着。⑥和辻哲郎:『国民統合の象徴』,東京:勁草書房,1948年,第100页。1960年代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宪法中象征天皇制的支持意见已经从战后的五成大幅度提升至八成左右。⑦寺沢正晴:『日本人の精神構造——伝統と現在』,京都:晃洋書房,2002年,第211页。象征天皇制之所以能成为“国民整体的象征”,是由于“国民”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国民是指具有同一语言、风俗习惯、信仰等的文化共同体,与国家同时存在。它表现为集团性,这种集团意识在日本的最好体现就是天皇。保留了天皇就无需在战后日本创造出一个能体现国民意志的另类存在。所以,象征天皇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将国民全体性与文化共同体等同起来的连接物。⑧崔世广主编:《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吉田茂内阁时期,日本极力将“皇室在政治、宗教及文化等社会层面确立为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中心”,通过强化皇室仪式作为国民庆典等活动,力争将天皇和皇室打造为“国民精神统合的核心”。旨在构筑以天皇为中心而将民众囊括其中的秩序框架,进而使天皇精神上的影响力和天皇权威充分发挥出来。吉田茂认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传统上,皇室与民众都是“一体不可分的”,正是基于此种关系才成为“国家秩序的根源”。吉田内阁的文部大臣天野贞祐认为,日本国内共产党势力之所以不断扩大,原因即在于缺乏爱国心,因此应该复活“日之丸”和“君之代”,同时主张应加强道德教育,并发言声称“国家的道德中心属于天皇”,为把爱国心教育的中心集中于天皇身上,他还草拟并发表了《国民实践纲要》。①河西秀哉:『「象徴天皇」の戦後史』,東京:講談社,2010年,第95-96页。战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一直在历史认识、战争责任等问题上态度暧昧,与中、韩等亚洲邻国龃龉不断,其深层原因即在于天皇制的存在。若对这一系列问题予以深究的话,已故的裕仁天皇自然难辞其咎,因此导致战后日本国内有关天皇的话题成为禁忌,对其战争责任等竭力予以粉饰和掩盖。从这一角度而言,天皇制在形塑日本国家认同时具有不容否认的消极作用,也成为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乃至社会总体保守化的内在思想根源之一。
象征天皇制在凝聚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政治家往往有意识地利用天皇制作为传统的“本土文化资源”,竭力将其打造为强化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和“团结”国民的有效手段。对于日本国民而言,其中不免蕴含着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权力话语支配”的意蕴。同时,日本政治家和知识精英通过不同方式对象征天皇制及与之相关的本土资源进行挖掘与重构,旨在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使日本人在精神上凝聚起来,重新发现、整理和熔铸体现日本特色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质”,从而凸显出与外国人 (欧洲人、美国人及中国人等)在行为取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并对之加以体系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而划分出“我们”与“他们”的象征性界线,以期强化和重塑战后日本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
三、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亲美”与“反美”思潮
在战后国家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日本始终将来自美国的思想观念视为其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外来资源之一,由此形成“亲美”与“反美”思潮的持续斗争,在复杂、纠结的矛盾状态下不断与“美国”进行着“自我”确证与互动。
(一)“亲美”思潮形成的主要原因
来自美国的资源在构筑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对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推崇和认同,对美式民主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美国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吸收和迷恋,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战后日本人所拥有的浓烈的“亲美”情结。
1.美式民主主义价值观具有的吸引力。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占领本身往往伴随着心理上的纠葛、挫折、失落感和劣等感。尽管如此,美国的占领政策还是得以顺利推进,对于其中缘由,曾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担任陆军飞行员的美国史专家猿谷要进行了分析:“无论是农地改革,还是解散财阀、赋予女性参政权、制定和平宪法,任何一项举措单靠日本人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作为占领军进入日本的美国人当中,似乎存在着具有将在本国国内无法实现的理想方案力图在日本付诸实践志向的自由主义人士。如果不产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日本人也不会那么喜欢美国。日本人出现这种重大变化大概也与原来热衷于美国的大众文化不无关系。这种情感尽管曾被在战争期间提出的‘鬼畜美英’的口号所压制,但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暗流涌动的状态持续着。正因如此,随着战争结束的解禁,暗流遂立即喷涌而出,并以瞬间之势遮蔽日本。”②猿谷要:『アメリカよ、美しく年をとれ』,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2-23页。
战后日本人的价值观主要是以《日本国宪法》为中心构筑而成的,可以将其命名为“和平与民主主义”价值观,主要以和平主义、主权者意识及人权思想为核心,其间涵盖着尊重生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及平等主义等观念,对外意识中的主流是亲美思想和国际协调主义。③寺沢正晴:『日本人の精神構造——伝統と現在』,第230-231页。战后的日本人具有强烈的亲美意识,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2002年,喜欢美国的人口比例,韩国为53%,日本则高达72%。④「日韓中米四国世論調査」,『朝日新聞』2003年1月15日。2006年春,美国舆论调查机构在世界14个国家进行了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抱有好感的比例,英国为56%,法国为39%,德国为37%,土耳其为12%,日本则高达63%,这一比例是所有调查对象当中最高的。①「世界十四カ国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06年6月15日。由此可见,美式民主主义价值观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颇具民意基础的大众“亲美”思潮。
2.裕仁天皇与政治家奉行“英美协调主义”。在明治宪法体制下,裕仁天皇作为“统治权总揽者”始终保持着参与国政的热情,因此可以率性地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基于自身信念开展行动。在战后的象征天皇制下,裕仁仍然保持这一政策惯性,为实现自身理念,对于强加在其身上的“象征”框架感到形同桎梏,因而试图予以突破。裕仁天皇在内政外交上的理念具体体现为:第一,对英美奉行协调主义,同时推行反苏、反共主义;第二,日本的国家安全通过依存美国并与之协调加以保障。第一条中的对英美协调主义,主要是考虑到在战后美苏对抗的冷战背景下,英美协调主义与反苏反共主义乃是一体的;第二点是基于与英美战争战败后的痛切“反省”,而将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通过依附美国的方式来实现,从中充分体现了天皇在筹划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走向方面的构想。这两大理念具体反映了天皇的国际形势观,并将其作为日本对外政策中应该追求的目标。②渡辺治:『戦後政治史の中の天皇制』,東京:青木書店,1990年,第152-153页。可见,从国家层面而言,天皇内心深处的对美友好认知,很大程度上在幕后主导和界定了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亲美主义”决策取向。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尔斯也分析指出,面对冷战加剧的态势,“裕仁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因为没有宪法上的权力,天皇只得在幕后操作,他鼓励美国保留冲绳作为军事基地,尔后又为巩固日美军事同盟发挥了作用。对他来说,反对苏联和与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种回归,由于他前期背离了这个政策才导致了日本的灾难。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③赫伯特·比尔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孙盛萍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87页。另据重光葵回忆,“天皇强调日美协力与反共的必要性。故而认为驻日美军不应撤出”。④伊藤隆編:『続重光葵手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年,第732页。战后裕仁天皇奉行与英美协调亲善的合作之举,主要是基于追求本国利益的“现实主义”谋算,认为从属于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会为自身的经济增长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面对战败的惨淡景象,日本人充分地认识到,战前的国家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作用,必须寻求新的国家发展模式。确实,当时很多人认为日本不可能再恢复到战前的状况,加之国民能引以为豪的东西也不存在了,面对整个国家个人主义横溢和道德观沦丧的痛心情景,这些人就呼吁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向西方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答案。⑤小熊英二:《近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林振江主编:《解读日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17页。在某种意义上,战后日本“脱亚入美”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选择即是处于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思维模式的惯性和延长线上。同时,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阵营虽然具有接受战败事实的非主观性,但慑于美国在二战中蓄积的超强国力,以吉田茂为首的政治家在总结战前的经验教训时,认为与英美为敌不符合日本国家的长远利益。日本既然不具备挑战欧美的实力,莫不如躬下身来虚心学习借鉴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由此可见,美国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取向在形塑日本的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亲美”情结中的实用主义取向。战败初期,皇太子明仁在日记中写道:“单个比较起来,日本人要优于美国人,但在团体较量上,美国人占优势。因而未来的关键在于发展科学,以及学习像美国人那样整个国家融洽合作。”⑥木下道雄:『側近日誌』,東京:文藝春秋,1990年,第48-49页。战后日本“亲美”情结的形成也与日本民族性格中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紧密关联,正如吉田茂所言:“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不仅应该从历史必然性上进行理解,而且应该从日本经济的基本性质上进行理解。日本是一个岛国,一个海洋国家。用世界的标准衡量,日本领土范围较小,人口密度却很大。为了养活这些人口,绝对需要促进国际贸易。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必然要从先进国家引入资本和技术。无论从国际贸易还是引入资本上看,日本都应该与世界上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结合在一起。主义和意识形态都不是问题,用最省力的方式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才是问题之所在。从这一方面看,世界上最值得日本尊敬的国家就是美国和英国。”⑦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从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轨迹来看,“亲美”思潮无疑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化的“日本”如何区隔日本之“自我”与已内在化于己身的美国这一“他者”,这成为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甚感困惑的“两难命题”。日本学者渡边治认为:“如果说战前日本统治构造的轴心是天皇制的话,那么支撑现代日本社会与国家统治构造的两大支柱就是企业异常而强有力的对劳动者的控制,以及对美从属的所谓国际性框架。”①渡辺治:『戦後政治史の中の天皇制』,第416页。
(二)“反美”情绪蕴含的矛盾纠结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中形成的“亲美”情结自有其内在的脉络和机理。同时,在面对美国这一“巨大的他者”的情形下,不断寻求从这一阴影中摆脱出来,谋求自主性和独立性,也成为战后日本化解国家认同危机所不得不予以克服的一大难题,而在日本各界不时爆发的“反美”民族主义斗争即是其重要表征。“亲美”与“反美”的情感错综交织,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折射出日本人复杂而矛盾的对美认知。
1.普通国民的反美情绪及斗争。战后美国的影响已经波及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已经内在化的他者“美国”,包含着内在暴力化的内涵,这个“美国”是以显而易见的美军基地的形式存在的。占领军继承了以往日军在亚洲各地建设和使用的军事设施,同时基地周边还存在着卖春问题。在“潘潘”(卖春妇)的衣着及举止上体现出来的美国的新潮性,对于多数日本男性而言,不免产生“日本被侵犯”的厌恶情感,而且类似的言论被刻意地加工、生产和消费,从而为构筑战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基础。②吉見俊哉:『親米と反米——戦後日本の政治的無意識』,東京:岩波書店,2009年,第227-228页。这一问题所折射出的意蕴表现为,日本之于美国,是作为“女性”遭致了侵犯,日本的“贞操”受到破坏,其中隐喻着美国支配日本的殖民主义逻辑,国民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也因之受挫,由此不免在日本国民内心中埋下了“反美”的种子。
1950年代,日本国内持续的大众性反美运动,以“反基地”为口号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这一时期的“反美”与其他时代相比更为激烈,显示出其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当时,《旧金山媾和条约》生效后仍然保留了大规模的美军基地,由此引发日本各界的普遍不满和深刻质疑。正因为这种不满广泛流布于大众之间,才使得1950年代的反基地斗争超越了党派斗争的框架,而拥有大众性和持续性的特征。颇为吊诡的是,“反美”情绪爆发的内在驱动力恰恰是来源于美国的追求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理念,“在日本政治、思想及其他诸多方面曾经一度产生高涨的反美情绪,从其典型事例反对美军基地斗争上看,其‘理论武装’却是来自美国宪法思想的法律观”。③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26-127页。
从占领期到1950年代,日本国民面对美国表现为“亲美”和“反美”的两种态度,而且日益呈现尖锐对立的态势。一方面,占领期的日本大众从电影、音乐乃至美食、家具、居所等方面,对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寄予了憧憬。美国成为富足的象征,所谓战后的“民主化”,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更富有吸引力的是如何过上像美国一样富裕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在面对蔓延全国的反基地斗争的现实问题时,对于作为“暴力”而侵入日常生活中的“美国”,对抗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随之被调动起来。④吉見俊哉:『親米と反米——戦後日本の政治的無意識』,第231页。
日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学生认为,推翻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是太平洋战争的唯一成果,因此他们对再军备和大企业的垄断极为敏感,并强烈反对。他们尤其猛烈地抨击美国对日政策的180度大转弯,谴责当初就是美国强迫日本非军事化,而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又立即摇身一变,命令建立警察预备队(实质上的军队),再度复兴军需生产,把日本变成美军的军事供应基地。美军刚到日本的一段时间,日本国民甚至包括共产党人大都把美军看成是解放者而感激他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日本人对美军开始感到失望。到了1950年代中期,一部分知识精英、学生和工人团体的反美情绪更是一触即发。当1960年岸信介内阁批准《新日美安全条约》时,日本民众的反美情绪达到了顶峰。⑤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战后日本“反美”斗争的主体主要包括日本共产党、在日朝鲜人和基地周边的农民等,这些人强烈地主张应该对美国在亚洲实施的统治进行抵抗。战后来自日本右翼势力方面的“反美”举动之所以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主要是由于天皇与麦克阿瑟业已达成妥协。即便战后崇尚天皇制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反美”,但从逻辑上看,也不免陷入在尊崇天皇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责难的自我矛盾的困境。甚或为了遮蔽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们也不得不推行自我欺瞒式的韬光养晦战略。①吉見俊哉:『親米と反米——戦後日本の政治的無意識』,第208页。这显然是一部分右翼势力别无选择的道路,至少在1980年代以前,他们完全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具体反映右翼势力在面对美国时的矛盾心态的一则轶事是,日本社会学者见田宗介在1980年代曾听过右翼运动家赤尾敏的街头演说。赤尾说:“(演说的声音突然压低)其实说实话,我是十分讨厌美国的。(声音又被抬高)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呢?日本对苏联和中共的……”②小熊英二:《全球化与日本的民族主义》,第26页。这反映出在右翼分子心灵深处蕴藏着厌恶美国的情感,但为了对抗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不得不依靠美国。
2.政治家的“反美”诉求及悲情。1952年,随着盟军占领的结束,日本国内的政治权力斗争也呈现白热化状态,大体上形成以吉田茂等为首的“主流派”和以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为中心重新集结起来的“非主流派”。吉田等“主流派”承袭占领时期的路线,在媾和以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主张继续推行对美依存政策。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军事政策方面,他们依然原封不动地保持对美从属地位,遵循宪法第九条,并且采取逐步使之扩大化的路线。③渡辺治:『日本国憲法「改正」史』,東京:日本評論社,1987年,第117-118页。媾和以后重新崛起的“非主流派”则立场鲜明地提出所谓“反占领及独立”的民族主义口号,不过他们也认同日本在总体框架下作为反共及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在反共这一点上也丝毫不逊色于吉田派。但是,在外交政策上,他们认为应该从历来由吉田主导的对美依存路线中解脱出来,主张向更为自主的方向发展。为此,他们特别强调通过“自主防卫”修订屈辱的安保条约,在安保方面以平等的同盟条约的形式实现日美地位的对等。而为了消除“自主防卫”的障碍,他们主张修改确定非武装化的宪法。对他们而言,宪法是美国占领支配日本的屈辱性象征,只有对其进行修改,才是日本独立及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出发点。同时,为了集结在战败和被占领过程中民众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诉求,修改宪法成为他们的中心口号。④渡辺治:『戦後政治史の中の天皇制』,第172页。实际上,目前安倍晋三内阁倡导的修宪主张,即是承袭战后以来“非主流派”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谋求国家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未尽夙愿。
中曾根康弘认为:“日本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制定国策时大国依赖性和功利性强。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续这种状况,国家战略的脆弱性丝毫没有改变。……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⑤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联慧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页。前原诚司也曾强烈主张日本不能事事听命于美国。1999年3月,前原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地说:“我不能不从心底对美国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⑥前原誠司、中村慶一郎:「政界直撃対談「周辺有事」より 「日本有事」が先決」,『財界にっぽん』1999年5月号。前原还主张“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来保卫,自主防卫是日本应循的道路。但是,考虑到日本把日美安保完全纳入了美国防卫政策这一现实,心中充满挫折感、压抑感也是没有办法的”。⑦转引自孟晓旭:《“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学报》2011年第4期。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后旋即得到了日本国内“新自主派”的回应。这一派学者主张,日本政府应在军事上独立自主,修正宪法第九条对自卫队的约束,透过军事力量,走向真正独立自主之路。“新自主派”认为“文明冲突论”对于沉醉于和平主义、执着于不修宪的日本国人不啻为一记棒喝,并提醒应该恢复日本在战后被美国抹除的传统与主体性。⑧Richard Samuel,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9-132.
时至今日,对于日本而言,“美国”这一外来资源既是其谋求“自我”主体性和确立国家认同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也是其终究难以从自身彻底剥离的内在化的“他者”。日本的困惑与迷惘深刻地体现在江藤淳的论述中:“为了实现自我恢复就必须谋求‘美国’的后退;而要为了安全保障则必须谋求美国的继续存在。”①江藤淳:『一九四六年憲法――その拘束』,東京:文藝春秋,1980年,第130页。日本人的“美国观”充满了矛盾和纠结,正如八木秀次在对小林善纪的反美主义进行批判时所指出的:“我认为思想、政治或外交应该分开考虑。在思想上,有时我也有大喊反美的冲动。但在政治上,反美则不会成为一个选择项。”②米原谦:《日本民族主义中的“美国身影”》,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八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考虑到如果由于日本方面的反美行动而使美国对日本不理不睬,那么日本的安全保障就将陷入危机之中。这种思想信念与行动选择之间暗含的无法克服的矛盾,也深刻地体现在日本政治家的对美认知及态度中,从安倍晋三等政治家的政治信念来看,一方面他们的内心里始终无法摆脱“反美自立”的情结,积极主张修改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和平宪法即是其中显著一例;另一方面,面对美国依然在国际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现实,加之日美安保体制的束缚,以及尚有应对邻国中国崛起的现实诉求,日本又无法彻底摆脱美国的利用与掌控。因此,从建构国家认同的努力来看,美国对于日本而言,是一个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交织的对象。诚如米原谦所云:“对20世纪日本的民族主义而言,美国始终是其‘最重要的他者’。美国是依存和反抗的对象,是憧憬与敌意交织于其中的‘父亲’。日本人对没有从这位‘父亲’那里得到适合自己的‘认可’(recognition)始终抱有不满。”③米原谦:《日本民族主义中的“美国身影”》,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2》,第181页。
在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日本面对来自美国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取向呈现出一种“既迎又拒”的矛盾心态,在民主理念及价值观等认知层面,积极借鉴和吸收来自美国的思想资源,是实现日本近代以来树立的现代化目标的“不二法门”;在政治体制及防务安全等实务层面,依托日美同盟体制确保日本的国家安全也是战后以来一直维系的政策惯性。因此,“亲美”思潮的蔓延既具备广泛的民众心理基础,也不乏政治家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实用主义谋算,旨在通过倚重美国的政治和军事资源为其自身国家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过多地追随和依附美国,对于美国各方面的诉求予以照单全收式地呼应和接受,既有损于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国格”,也会悄然侵蚀日本国家本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何摆脱这一“两难困境”,是战后日本在形塑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在面对“美国”这一他者时短时期内所无法轻易破解的“难题”。
四、作为“反命题”而存在的“他者”中国
中国这一“他者”之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有效性体现为,将“中国”描绘成可怕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和“竞争对手”,与积极倡导“中日友好”④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维持了两国关系史上罕有的倡导“中日友好”的“蜜月时代”,彼时中国这一“他者”在日本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日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对中国进行援助和帮扶,既可以凸显日本融入西方的“先进性”,也可通过对中国施以援手的方式对比出中国作为东方代表的“落后性”,从而有效地呈现自身在亚洲区域的主体性和自豪感。同时,日本之所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援助,一方面蕴含着自古以来日本对中华文化的迷恋与倾慕;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以来日本“古典的亚细亚主义”理念一脉相承,旨在通过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方式,增强与中国的“连带感”和一体化意识,将自身在亚洲区域的引领角色和主导作用凸显出来。有关战后日本与亚洲融合的论述可参阅原洋之介:『新東亜論』,東京:NTT出版株式会社,2002年,第24-33页;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60-369页。此外,由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日本对中国的这一大义之举深表赞赏,且对中国怀有“歉疚感”和“同情心”,这一心理层面的积极对华友好认知,成为这一时期推动日本各界人士加强对华援助与友好合作的深层思想动因。有关日本对华援助的原因分析可参阅田庆立:《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4期。总之,日本视域中的中国这一“他者”,绝非仅仅是“对立”与“竞争”的客体,也包含着“友好”与“合作”的侧面,而这也与建构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议题息息相关,限于篇幅,有关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只能另文专述了。相比,可以更为立竿见影且有效地达到动员民族主义情绪的目的,进而增强国家的内聚力。至于这种有意识的主观想象和恶意误读是否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态,可能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形塑者主体——政治家们所关注的重点。譬如,即便安倍晋三内心深处也可能认为中国并不一定会真正成为日本的“威胁”,但为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势必要对近邻中国的军事能力进行渲染和夸大,从而引起国民恐慌,为其修宪和增加防卫预算制造依据。无疑,有关日本人的中国观这一课题,涉及诸多群体的不同侧面,既存在着对中国的负面和消极认识,也包含着冷静而客观的对华认知。仅就本文的视角而言,日本人的中国认知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现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凸显了日本自身的特性,特别是日本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
中国作为“他者”,是战后日本确立“自我”主体性及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参照物之一,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日本的“反命题”而存在的。基于国内外主客观条件的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中国”这一他者的界定不断发生变化,或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又或视为“竞争对手”,不断通过与“中国”的互动,以期将之形塑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
(一)作为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他者”中国
战后日本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中国则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此,中日双方更多地依据意识形态划线审视和观察对方,从而形成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对峙状态。①有关意识形态因素与日本的中国认识之间的关系,可参见田庆立:《试论“他者”认识与日本中国认识形成的内在机理》,《日本学刊》2011年第6期。对于日本而言,基于意识形态因素考量而将中国推向对立面,在形塑国家认同上发挥的效用体现为,一方面通过积极表现出“亲美反共”的姿态,以期赢得美国认可,为其加入西方阵营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依循“西方”代表“先进”,“东方”代表“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竭力将自身打造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同时通过突出和强化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及价值观念上不同于西方的异质性,将中国纳入到代表“落后”的“东方”的范畴,从而彰显日本在亚洲的优越地位和先进性,由此获得自信心和自豪感。
吉田茂等保守派政治家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并对苏联及中国等国家怀有深深的恐惧感。日本领导层对二战后的形势判断是:“远东形势孕育着极大的危机。现在千岛、库页岛、中国大陆和朝鲜的一半已纳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共产主义国家以日本为进攻目标的意图已十分明朗,在近几年内很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日本正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②王少普、吴寄南:《战后日本防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页。1954年11月,吉田茂在国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今天一切自由国家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共政策。现在,这些自由国家似乎对我国也抛弃了过去的敌对感情,为了把我国引进自由国家阵营之中,希望同我国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国家把渗透的目标指向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各国。”③吉田茂:《十年回忆》(第四卷),韩润棠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95页。1957年6月,岸信介在访美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宣扬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说,他公然宣称共产主义的威胁来自中国,“新独立的亚洲各国正在急于摆脱不安定和贫困,于是共产主义,特别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便宣称说,只有他们的道路才是走向进步的途径”。④尹协华:《日本的秘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第349页。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在冷战结构中,随着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中恢复了自信,对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反共意识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又再一次与战前蔑视中国的感情结合起来。”⑤沟口雄三:《历史认识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页。沟口还尖锐地提醒道:“在日本国民中间缺乏一种能够切实地接受邻国这一警告的感觉上的参照系。在日本,存在一种与追随欧美互为表里的歧视亚洲、自恃日本优越的意识结构。这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情感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它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积弊,犹如麻醉药麻醉着全身,扭曲或阻碍着对亚洲现实的认识能力的发展。”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64页。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依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审视和观察中国,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旨在围堵和遏制中国。2006年,安倍晋三指出:“中国是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事实,其军费连续18年以两位数增长。中国与日本不能共享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①「日本対中出口と投資両国互恵」,『日本経済新聞』2006年4月4日。2007年1月,安倍在施政演说中重申,要与和日本拥有同样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构筑开放和民主的亚洲,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并再次强调进一步深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合作,扩大首脑交流。安倍建立价值观同盟的构想甫一出台,便遭致国内外的广泛质疑,被认为是以倡导“共同价值观”之名,而行建立“对华包围圈”之实。日本学者对此批评道:“当今世纪,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在国际关系被民族、宗教等多种复杂因素驱动的今天,仍以价值观为基础描绘出的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只能是一种虚幻。”②寺島実郎:「米中接近に直視する」,『文藝春秋』2007年8月号。2007年8月,安倍访问印度并发表讲话称:“日印伙伴关系是一种结合,即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尊重基本人权以及战略利益。”通过将这种伙伴关系定义为民主国家之间的结合,巧妙地将中国排除在圈子之外。因此,安倍的讲话实质上含有潜在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③高兰:《冷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思想与实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二)作为“竞争对手”的“他者”中国
日本拥有通过找寻“他者”的方式进而突出和强化自我认同的民族偏好,历史上日本通常会借助“外部刺激”推动自身进步,或者通过抵御排斥“外部刺激”以形成自身的或与传统、或与现实相结合的“反应”,无论选择什么,其最终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内与外的紧张关系之下谋求自身的本真性。④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曾经是一个巨大的他者存在,现在依然如此。为了日本及其文化作为自立的东西得以存在确立起来,或者为了有可能去主张这种自立的存在,日本也需要将自己与中国及其文化差异化。只有把与自己的异质性强加给中国及其文化,也就是强有力地将中国他者化,才可能以此主张日本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⑤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8页。中国这一邻近的“他者”在形塑日本国家认同过程中即充当了“外部刺激”的角色,正因如此,“中国崛起”的事实被广泛宣扬为中国正在实质性地“威胁”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成为日本凝聚社会共识、打击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和调动各种政治力量突破和平宪法体制约束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⑥朱锋:《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美国学者艾伦·杰罗认为:“日本没有强大的国家认同,而国际舞台用霍布斯的话来说是个凶险的、野蛮的场所。根据这种情形来看,日本由于没有强大的自我,它面对着别的国家咄咄逼人的冲击浪潮,有可能会被巨浪淹没;只有建立坚强的国家意识,以之作为进入国际舞台的前提,才能保证日本在将来不至于淹没。”⑦艾伦·杰罗:《消费亚洲、消费日本:日本新民族主义者的新修正主义》,劳拉·赫茵等编:《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聂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5页。面对中国崛起而引发的恐惧心理,直接导致日本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其不惜竭尽全力地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围堵和遏制,实际上正是在应对中国时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并呈现出一种近乎歇斯底里式的狂躁状态。日本评论家西尾干二在分析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国内背景时指出:“日本经济长期陷于不景气而开始丧失了自信,一国处于衰退时必然兴起的现象就是对自我认识危机的强烈呼唤,即日本究竟是什么,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在哪里,日本这个国家究竟应如何认识等,产生重新认识历史的欲求。”⑧西尾幹二:「強く信じるからこそ強く疑える」,『正論』2001年2月号。
后冷战时代,中国崛起的态势成为引发日本国家认同危机的“触媒点”,以往日本以中国为参照系而拥有的优越感与蔑视感被恐惧感和排斥感所代替,沟口雄三将这种状态称之为“中国的冲击”。“脱亚”的日本似乎一直统领着“亚洲”,然而曾被视为尾随着自己的“亚洲”,如今却不知不觉地开始引导日本了。日本人关于“脱亚”的认识与现实的“亚洲”之间出现了微妙的错位,并且几乎没有日本人意识到这种现实中的错位;于是,出现了现实与认识上的双重错位。⑨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第5-6页。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即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各界的甚嚣尘上,对中国的警惕性认识超过了以往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优越性认识,日本“自我”身份确立的主体性发生动摇。西尾干二在分析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时指出,其中就有因“中国强大,变成威胁”的因素。“中国是弱小国时,日本人有敬爱其悠久历史的民族性,但一旦中国强大变成威胁时,则日本人就保持距离,有从中国脱离的倾向,实古已有之”。①西尾幹二:「強く信じるからこそ強く疑える」,『正論』2001年2月号。山室信一也认为:“只要断定中国蕴藏着比日本更快地同化于西方文明并实现军事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持续地感受到中国凌驾于日本之上的强烈威胁。”②山室信一:《面向未来的回忆——他者认识和价值创建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实际上,日本处心积虑地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其真实意图在于,一方面,安倍等右翼保守势力无论是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还是不断推动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升级,都迫切地需要寻找“假想敌”,并且这一“敌人”还须易于引起日本国民感情上的共鸣,而肆意夸大来自近邻中国的威胁,即会达到煽动民意以期为自身的合法性制造依据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普通国民珍爱和平的心理,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目标“超出实际防卫需要”,暗示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将会给日本带来威胁,导致日本国民形成警惕和防范中国的戒备心理,进而利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装置,将国民对国内现实的不满情绪转嫁到中国身上,从而达到凝聚和整合国家认同的目的。
后冷战时代,面对东西方阵营对峙格局的解体,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业已实现,但却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之中,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和航向突然消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而此时正在崛起的中国进入了日本视野。 “日本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却并不适合于担任一个世界的‘领跑者’。在一度作为世界的领跑者而失去了发展目标与前进动力、逐渐陷入‘主体性迷失’的背景之下,‘中国’再度成为一个关注对象。由此可见,作为‘方法’的中国,实质上是为日本谋求一个新的判断视角,是为日本提供的一个‘非西方化’的选择而已”。③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第172页。
日本心理学家南博认为,“日本人的自我结构中,最明显的特质之一是缺乏主体性的‘自我不确定感’”。④南博:《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第218页。美籍日裔学者玉元胜曾撰文指出:“日本对于中国主导亚洲事务充满了担忧,‘中国是个威胁,因为它是中国’,这似乎是日本国家安全圈子里盛行的潜在论断;日本对华关系一波三折的根源在于它自古以来不能容忍与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平起平坐;日本之所以对中国充满疑心,其背后根源在于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日本社会对于自己没有信心;日本谋求‘正常国家’的地位与追求民族主义复兴的背后,‘中国经济威胁论’喧嚣而起,乃是源于自身的难以启齿、却最终不得不承认的相对衰弱的事实;历史问题的纠葛与激活,将带有了后现代特征的日本推回了现代状态,使日本不得不适应亚洲的作风,从而产生了与中国发生摩擦与纠纷的根源。”⑤转引自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第26-27页。
日本学者小岛朋之的观点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日本人在审视和观察中国时的矛盾心理,既不希望一个“虚弱的中国”出现,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诞生。原因在于,“经济破产和对政治不满严重化”的“虚弱的中国”将成为亚洲区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至于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为背景,忽视他国意愿,强硬推行以中国为主体、建立新秩序”的“强大的中国”,将给亚洲带来威胁。⑥「強大的中国の独走」,『読売新聞』2000年11月7日。显然,当前中国的发展态势已经夺去日本曾在亚洲所拥有的“一枝独秀”的光芒,如果说一个积贫积弱甚或落后的中国尚能容忍的话,面对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无疑会引起日本的高度警惕和关注。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日本若依然秉持冷战思维,为凝聚国家认同画地为牢,一味寻求排斥性的他者,显然无益于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构。中日两国积极挖掘东亚文化传统中的“和”的思想资源,增进相互理解,强化互信共赢理念,才是两国最终达成历史性“和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正途”。
五、结 语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呈现为消解与重构、削弱与强化并行的特征。①王卓君、何华玲:《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全球化失去方向感的后果很可能促使人们在更为本土化或民族性的事务上寻求慰藉和生存意义,不论它是同一种语言还是一段共同的历史。②Gideon Rachman,“The Strange Revival of Nationalism in Global Politics,”Financial Times,Sept.22,2014.从战后建构国家认同的历程来看,日本既有意识地从本民族国家中挖掘本土的天皇制精神资源,以期达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合国民的目的,也积极地吸纳和整合来自美国方面的思想资源,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阵营,并以“和平国家”和“民主国家”自居,期望在世界范围内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彰显国家软实力。通过日美结盟的方式推行日美基轴外交,一方面使日本能够集中精力专注于经济大国的建设;另一方面也付出了与美国亦步亦趋缺乏外交自主性的代价。在冷战体制下,“他者”中国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更多地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由于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分歧和结构性矛盾,因而导致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出一系列负面形象。在日本确立经济大国地位之后,通过与中国的对比往往展现出自明治时代以来的优越感。然而,在中国崛起之后,由于中日两国呈现“两强并立”的态势,日本审视和观察中国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卑感和警惕感潜滋暗长,两千年来处于强大中国笼罩之下的历史意识与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日本各界甚嚣尘上。
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由于一方面面对美国这一他者而时时存在着自卑感,另一方面又不甘于本土思想文化资源的完全“美国化”,于是,不断试图通过捍卫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以抵消来自于西方及美国的思想资源对其本体的“侵蚀”。由此出现所谓后发展型国家的两种自我疏离 (selfalienation)现象:一种是完全西化,企图使自己完全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另一种是退回传统文化。后发展型国家往往在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时,或以传统文化、或强调西化作为策略,但是又必须克服上述自我疏离的难题。③Arif Dirlik,“Culture against History?The Politics of the East Asian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Society,Vol.28,No.2,1999,p.169.对于日本而言,今后如何有效地维系和整合本土文化资源,消解来自全球化的压力对其构筑国家认同的侵蚀;如何处理谋求自立性与自主性而又不至于破坏日美同盟关系,在“亲美”与“反美”之间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如何克服将面对美国时所蓄积的不满和精神压力发泄给亚洲邻国的“痼疾”,探寻确立一种理性而健康的形塑国家认同的路径,无疑将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考验着日本政治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