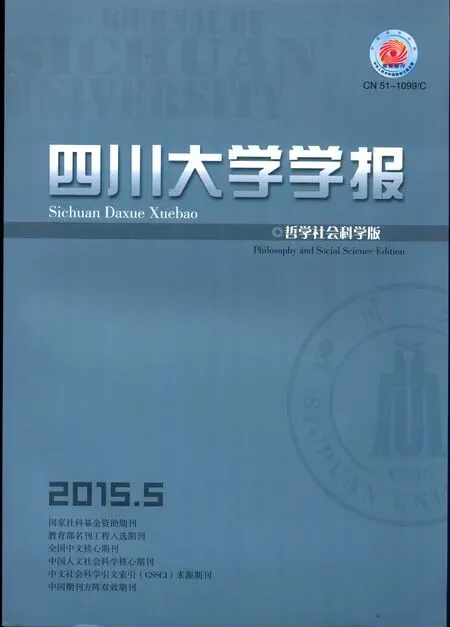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书写——以江淹为考察中心
何剑平
南朝士大夫与佛教关系密切,并且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学书写,就此而言,江淹颇具代表性。江淹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以文章诗赋见重于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与佛教相关。尽管前辈学者在考证江淹作品的写作年代、生平事迹以及创作活动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①江淹集的注本主要有:1.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此书以明万历梅鼎祚刻本为基础,校以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刻本,并加注释。2.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江淹年谱主要有:1.吴丕绩:《江淹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2.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俞绍初:《江淹年谱》,《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4.丁福林:《江淹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极珍贵的资料和线索,但于江淹此类作品则较少措意,致使这些作品的意义仍晦暗不明。事实上,正如汤用彤所指出的:“南朝文人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者,自谢、颜以下,几不可胜述。……至若虽未出家而奉法虔敬,如周颙、王筠、江淹等各有文载《广弘明集》中,则实代表士大夫之风尚,非三数人所独有之信仰也。”②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484页。因此,以江淹为中心,考察其与释教相关的作品,③据笔者考察,江淹与佛教相关的作品有《遂古篇》《与交友论隐书》《伤爱子赋》《水上神女赋》《丹砂可学赋并序》《莲华赋并序》《青苔赋并序》《哀千里赋》《吴中礼石佛》《构象台》(《杂三言》五首之一)、《无为论 (并序)》《铜剑赞》《自序》等13篇。其中:《遂古篇》《莲华赋并序》只是摘引佛学事典用作诗文的材料;《丹砂可学赋并序》《青苔赋并序》《哀千里赋》则表现于某些概念语词与佛教的相通;《与交友论隐书》《伤爱子赋》是表现作者敬信佛教因缘果报主题的作品,前人所论已多,此不赘述;至于《铜剑赞》,钱钟书先生已指出其故事即《大唐西域记》卷六《拘尸那揭罗国》“大邑聚及罗怙罗神迹传说”,乃“荣古虐今”之例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8页);《水上神女赋》需另文探讨。对于了解当时士大夫的文化风尚以及佛教信仰对其创作的具体影响都是颇有帮助的。本文拟以江淹的《吴中礼石佛》《无为论(并序)》《构象台》等诗文为重点考察对象,对其所呈现的佛教思想及其生存背景作具体探究。
一、江淹的佛教观与南朝流行之佛典
江淹博通世典,兼习佛理,是南朝士大夫中崇信佛教的文人之一。他的佛教观与当时流行之经典与学说有不解之因缘,这可以从《吴中礼石佛》诗中看出。其诗云:
幻生太浮诡,长思多沉疑。疑思不惭炤,诡生宁尽时!敬承积劫下,金光铄海湄。火宅敛焚炭,药草匝惠滋。常愿乐此道,诵经空山坻。禅心暮不杂,寂行好无私。轩骑久已诀,亲爱不留迟。忧伤漫漫情,灵意终不缁。誓寻青莲果,永入梵庭期。①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卷三,第114页。
此诗作于宋顺帝升明元年 (477),②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68页;丁福林:《江淹年谱》,第114页。题名中的石佛,即吴县 (今苏州)通玄寺的石佛像,该石佛像于西晋愍帝建兴元年 (313)在吴松江沪渎口被渔人发现,后被吴县奉佛居士朱应及东云寺帛尼等安置于通玄寺 (该寺原为孙权为乳母陈氏所立)中。③此事见载于慧皎:《高僧传》卷一三《竺慧达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78页;简文帝:《吴郡石像铭》,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七《内典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318页。石佛的来临以及吴郡僧俗至诚感神的事迹,使通玄寺自东晋至南朝陈即成为一个多显灵瑞的所在,被当时许多文献记录和传抄,④如:释僧顺在《答道士假称张融三破论十九条》中曰:“浮图者,圣瑞灵图浮海而至,故云浮图也。吴中石佛泛海鯈来,即其事矣。”《高明二法师答李交州淼难佛不见形事 (并李书)》中载:“吴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师,人从百数。符章鼓舞,一不能动。黑衣五六,朱张数四,薄尔奉接,遂相胜举。即今见在吴郡北寺。淳诚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张连世奉佛,由睹验。”(分别见《弘明集》卷八、卷十一,《大正藏》第52册,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1934年,第52页上、71页下)《续高僧传》卷一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君页传》记载通玄寺的传说云:“东晋之日,吴有白尼,至诚感神,无远弗届。天竺石像,双济沧波。照烛神光,融曜沪渎。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晋距陈,多显灵瑞。”(《大正藏》第52册,第535页中)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五《佛德篇第三之二》列塔像神瑞迹中亦有吴中石佛:“吴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躯,昔西晋建兴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应,接而出之,举高七尺。于通玄寺视背有铭,一名惟卫,二名迦叶。”(《大正藏》第52册,第202页中)此条亦见于《高丽大藏经》第33册,首尔:东国大学校译经院出版部,1975年,第441页。并吸引了大量信众前去礼拜。据记载,江淹早年的荐举人隐士何点也因在此通玄寺 (石佛寺)讲说佛经获佑而袪除渴痢之患。⑤据《梁书》卷五一《何点传》记载:“点少时尝患渴痢,积岁不愈,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于讲所昼寝,梦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梦中服之,自此而差,时人以为淳德所感。”(中华书局,1973年,第733页)诗中“敬承积劫下,金光铄海湄”句正是对石像浮江而至、吴中士庶往接恭迎这一灵异事件的描写。而慧君页传中所云“天竺石像,双济沧波。照烛神光,融曜沪渎”诸句正可为此作注脚。
石佛的来临犹如药草滋繁,给吴郡士庶带了无量饶益,⑥“药草匝惠滋”,如释慧君页传中记载慧君页为沙门道愿、法济等讲解佛理事,云:“有余杭沙门道愿、法济等,先禀成论,义同门户。不远千里,请道金陵。乃欝相然诺。既而敷畅至理,药木滋繁。”惠施众生,拔济愚迷于三界火宅,即江淹所谓:“火宅敛焚炭,药草匝惠滋。”“药草”典出《妙法莲华经》卷三《药草喻品》,是法华七喻之一。竺道生对以药草为品题的旨意,作如此解说:“药草者,明其昔日曾受持于圣教,圣教沾神,则烦恼病愈。故寄药草,以目品焉。”⑦竺道生:《妙法莲华经疏》卷下,《卍续藏经》第1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77年,第818页。可见,在《妙法莲华经》中,药草能治愈人之烦恼病。南北朝诸多文献中也常提及药草的此层含义。如梁武帝萧衍开说《三慧经》的洪恩即言“俾兹含生随药木而增长”;萧纲在《大法颂并序》说“慧流总被,药木开芒”;⑧分见《广弘明集》卷一九、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234、241页下。慧君页传中所谓“敷畅至理,药木滋繁”等皆是。江淹诗中的“药草”与萧纲等文中的“药木”应属同源。以药草为喻,展示了他与《法华经》的密切关联。而江淹佛教观念中的法华元素,在其《无为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⑨《无为论 (并序)》见载《广弘明集》卷二九,《大正藏》第52册,第342页下。研究者多举《吴中礼石佛》为证,然于江淹《无为论》与《法华经》的紧密联系却颇为忽略,现并作讨论,以求方家。
《无为论 (并序)》的写作时间,《自序》一文中已有所示:“在邑三载,朱方竟败焉。复还京师,值世道已昏,守志闲居,不交当轴之士。”[10]江淹:《自序》,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卷十,第380页。可见,江淹回京口后有一闲居不仕之阶段。“世道已昏”盖谓后废帝时朝政混乱。又据《无为论》中所言:“吾曾回向正觉,归依福田。友人劝吾仕,吾志不改。”可知,此文应是江淹由吴兴返故乡不久,萧道成尚未提拔他为官时所作。[11]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系此篇于升明元年 (477)至齐高帝建元元年 (479)之间(《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68页),丁福林《江淹年谱》亦系此于宋顺帝升明元年 (第113-114页)。甚是。在《无为论》中,江淹以弈叶公子与无为先生对论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出处穷通的看法。其中写到无为先生“无学不窥”的知识修养—— “至如释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书,宣尼六艺之文,百氏兼该之术,靡不详其津要”等——乃作者自喻,文中所述无疑都是江淹的自我写照。文章后半借无为先生之口叙述了对“忧喜不移其情”的“大人”境界的尊尚,其基本观点,令人注意:
吾闻大人降迹,广树慈悲,破生死之樊笼,登涅槃之彼岸。阐三乘以诱物,去一相以归真。有智者不见其去来,有心者莫知其终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绝殊途。无变无迁,长祛百虑,恬然养神,以安志为业。欲使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舒卷随取,进退自然,遁逸无闷,幽居永贞,亦何荣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尘内方外,于是乎着。
这段话从佛教的角度阐述了对仕隐进退的看法,是关系到江淹信仰特质的一段重要言论。这些言论大多从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经论中化出,就思想来源来看,最明显的有以下四处:
(一)大人观念。“大人”语出儒家经典,①《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2页)这段话被后儒视为儒家境界哲学的代表。但在此文中江淹所提及的“大人”却是佛教视界中的大人观念。关于“大人”,《大智度论》中多有所载,如卷二《释初品中婆伽婆》中“问曰:有一切智人,何等人是?答曰:是第一大人,三界尊,名曰佛”;卷一三《释初品中戒相义》中“复次,行者当学大人法,一切大人中,佛为最大”;卷七七《释同学品》中“又复大人菩萨无所求欲,能以头、目等施与众生,所得果报,亦以施与”。此外,《坐禅三昧经》卷下:“复次以佛道乐涅槃之乐,与一切人,是名大慈。行者思惟:现在未来大人行慈,利益一切。我亦被蒙,是我良佑。”《十二门论·观因缘门》:“摩诃衍者,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诸佛大人乘是乘故,故名为大。”②《大智度论》卷二、卷一三、卷七七,《大正藏》第25册,第75、155、606页;《坐禅三昧经》卷下,《大正藏》第15册,第282页上;《十二门论》,《大正藏》第30册,第159页下。这里的“大人”明显皆指称佛或菩萨。江淹诵读的《妙法莲华经》卷七《妙音菩萨品》亦说:“尔时,释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放眉间白毫相光,遍照东方百八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世界。”③《妙法妙莲华经》卷七,《大正藏》第9册,第55页上。显然,江淹忠实于大乘佛教经论,在此把“大人”视作“广树慈悲” “湛然常住”、超越生死的“佛”。
(二)三乘归一观念。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乃佛说法的三个次第,最终三乘同归一佛乘。通过区别小乘以显示大乘是《法华经》的重要思想。如《妙法妙莲华经》卷一《方便品》中,佛告舍利弗说“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乘,唯一佛乘”。对于佛开三乘的根本原因,竺道生解释说:“圣人非自欲设三教,但众生秽浊,难以一悟,故为说三乘。出不获已,岂欲尔乎?……于一佛乘,分别说三。佛以浊世人无大志,而所以佛理幽远,不能信之,抑使近人,作三乘教耳。虽曰说三,恒是说一。”又,“三乘之化,本为浊世,其土既净,不容有三。而言三者,欲明三即是一,更无别三”。④《妙法妙莲华经》卷一,《大正藏》第9册,第7页;竺道生:《妙法莲华经疏》卷上《方便品》《譬喻品》,《卍续藏经》第150册,第808、809页。其意盖谓,如来出世之始,本欲为说大乘经,但于时众生无有堪受大乘之根机,用大乘化众之法既然不能通行,而又不可令此众生永沦长苦,是故如来用三乘教化取众生,即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待后大乘机发时,方说大乘经。江淹所说的“阐三乘以诱物”含义与此完全一致,采用了时人习知的法华教理;而“去一相以归真”乃谓佛之说法虽随众生根机之差别而有二乘、三乘之分,但这只是方便权教 (权者,是权假暂时之谓,非是久长之义),在实质上为同一相、同一味,故《妙法莲华经》卷三《药草喻品》说:“如来说法,一相一味,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至于一切种智。”此也由“三乘方便”凸显“一乘真实”之意。所谓一相指无差别之相,即无相,一切法空即是无相。⑤《妙法妙莲华经》卷三,《大正藏》第9册,第19页中;《大智度论》卷七○《释问相品》:“‘空相’者,内外空等诸空。若诸法空者,即是无有男女、长短、好丑等相,是名‘无相相’。”(《大正藏》第25册,第548页中)然而,欲求解脱之众生根有利钝,利根者闻空,即得无相;钝根者能观一切法空,却又往往执着于空相,生种种烦恼,不知此空相不可得。因是佛陀教化众生令得空相已,又说无相。无相之相名为实相,此乃毕竟空,离分别之境。江淹在此文中持义近于梁武帝对《法华经》教理的认识。梁武帝《注解大品序》说:“《法华》会三以归一,则三遣而一存,一存未免乎相,故以万善为乘体。”①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94页。则江淹对《法华经》大乘无相之解,与萧衍持论若一贯,其命意同以“知取相为过,舍相是道理,归一实”为务,②《大般涅槃经集解》卷五二引宝亮语:“实谓大乘无相之解。菩萨知取相为过,舍相是道理,归一实,更无异途也。”(《大正藏》第37册,第535页中)其渊源宜有自也。
(三)佛身常住观念。佛经对涅槃境界的描述往往会关涉到佛身同常人的区别,提出“佛身是常”的观念。《妙法莲华经》属初期大乘佛经,在其卷五《从地踊出品》《如来寿量品》亦假长寿以彰显释迦成佛常住不灭之旨。③如《如来寿量品》引佛语:“我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大正藏》第9册,第42页下)生活于公元3-4世纪的龙树菩萨,在其所著《大智度论》中将“佛身是常”这一观念条理化,提出佛有两种身之说,④详见《大智度论》卷九《释初品中现普身》、卷三○《释初品中善根供养义》、卷三三《释初品中到彼岸义》、卷八八《释四摄品》、卷九九《释昙无竭品》,《大正藏》第25册,第121、278、303、683、747页。如他在《释初品中现普身》中所言:一者法性身,二者父母生身。法性身又作佛法身,此身“常出种种身、种种名号、种种生处、种种方便度众生,常度一切,无须臾息时”,“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无来无去);父母生身即佛随世间身,亦名色身,乃“在人中生,人父母,受人身力”,但与常人不同的是,经由父母生身的佛不受罪报,不为寒热、饥渴、睡眠、诽谤、老、病、死等诸患之所困,因为世谛之故现受人法。于佛二身中,法身为大。龙树之后出现的《涅槃经》继承其说。例如,在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中,卷三四《迦叶菩萨品》:“法身即是常乐我净,永离一切生老病死,非白非黑非长非短,非此非彼,非学非无学,若佛出世及不出世,常住不动,无有变易”;卷三《金刚身品》引世尊告迦叶语:“如来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坏身,金刚之身,非杂食身,即是法身。……是身不生不灭、不习不修,无量无边,无有足迹,无有去来而亦去来,不破不坏,不断不绝,不出不灭。”《大般涅槃经》以“常住不动,无有变易”以及“永离一切生老病死”来解说佛身的特质。江淹《无为论》中“破生死之樊笼”“不见其去来”“湛然常住”诸语也被用来说明“大人”出现于世 (降迹)诱物行化的特性,其间源流关系昭然若揭。江淹所说的大人“无变无迁,长祛百虑”,喻指佛身的湛然常住,非如凡身剎那迁变,其涵义也来源于《大般涅槃经》卷五《如来性品》所记佛对迦叶菩萨广说大涅槃行解脱之义:“真解脱者,名曰远离一切系缚。……真解脱者不生不灭,是故解脱即是如来。如来亦尔。不生不灭、不老不死、不破不坏、非有为法。以是义故,名曰如来入大涅槃。不老不死,有何等义?老者,名为迁变,发白面皱;死者,身坏命终。如是等法,解脱中无。以无是事,故名解脱。如来亦无发白面皱有为之法,是故如来无有老也。无有老故,则无有死。又解脱者,名曰无病。所谓病者,四百四病,及余外来侵损身者,是处无故,故名解脱。无病疾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如来无病。是故法身,亦无有病,如是无病,即是如来。”⑤《大般涅槃经》卷三四、卷三、卷五,《大正藏》第12册,第567、382、392页。可以说,佛之“常住”“不变异”“无为”这三方面内容渗入到《无为论》中,形成了江淹“大人”(佛法身)“无变无迁,长祛百虑”的观念,并用以表达其心目中圣者(“大人”)修行的最高境界。江淹以“无为”命题,也暗合了解脱之意。
(四)不着的观念。所谓“着”,即隋慧远《大乘义章》卷二《三有为义两门分别》所说:“缠爱不舍名着。”⑥《大乘义章》卷二,《大正藏》第44册,第492页。盖谓人之心执着于某事理而不能舍离。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三《相行品》,此种执着包括对无明、邪见等的执着贪爱和对善法 (佛道)的执着贪爱两种,二者皆为致病之本,以如此专求欲得的执着之心去处理事物,是不能得到智慧的。有鉴于此,大乘般若学说主张以去执着为能事,圣人之教“于一切法中无所住”,此即所谓“不住般若”的观念。①《大智度论》卷五四《释天王品》记须菩提语舍利弗:“诸佛心于一切法中无所住,所谓色乃至一切种智。”(《大正藏》第25册,第447页中)有关“着”之释义,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三《相行品》以及《大智度论》卷四三《释行相品》、卷四六《释摩诃衍品》等中皆有表述。即便是对利益佛道之善法的爱,亦不可着,着亦成过患。欲使行者忘彼我、遗所寄,泛若不系之舟,无所倚薄,则与佛理相契。江淹所说的“尘内方外,于是乎着”的“着”字,即指人若对方内、方外有忆想分别,就会产生执着。很明显,江淹在这里采用般若玄理对庄子思想作了提升和发挥。②“尘内方外”,原本于《庄子·大宗师》引孔子告子贡语:“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三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67页)所谓“方”,《文选》卷二六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卷四七夏侯孝若《东方朔画赞》皆引司马彪注说:“方,常也。言彼游心于常教之外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8页上、668页下)在此,孔子盛称方外之士孟子反、子琴张二人能齐一生死、不为教迹所拘,游心寰宇之外。而自己与子贡身为儒者,则和光接物,为方内之俗礼所桎梏。《庄子》原话有强调内外道殊,推重方外高人之意,如郭象注所云“以方内为桎梏,明所贵在方外”。③《文选》,第378页上。又见《庄子集释》卷三上,第271页。然在江淹看来,贵重方外而轻贱方内 (区域),或者贵重方内而轻贱方外皆有内外、胜劣之分,皆是着心取相,理应袪除。江淹撷取般若学“于一切法无所住”的观念对《庄子》如何达致“游外而共内”(“游外者依内”)的方略作了推衍和引申。此外,受“般若法门”影响的《法华经》卷一《方便品》中也说佛“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着”。④关于《法华经》与《般若经》思想源流的讨论,可参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四,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047页;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09、1090页;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3页。对此,诵读过《法华经》的江淹当不陌生。总之,《无为论》对“着”的书写,与《般若经》《法华经》等所举“离着”之说,旨义相符。《无为论》“不着”观念的建立,明显借助了当时盛行的大乘佛典中的“不住”思想。
以上所述法华三乘归一、涅槃常住不灭、般若离着去执等佛教观念,不仅影响着江淹的诗文创作,也指导着他处理仕隐、进退、荣鄙、得失等关系问题。事实上,《法华经》《涅槃经》《大智度论》等大乘经论自传入中土后就一直是当时知识阶层关注的圣典,试举三则材料为证:《南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行状》:“自方等来仪,变胡为汉。鸿才巨学,连轴比肩。《法华》《维摩》之家,往往间出。《涅槃》《成实》之唱,处处聚徒。”周颙《抄成实论序》:“顷《泥洹》《法华》虽或时讲,《维摩》《胜鬘》颇参余席。”《续高僧传》卷七《陈杨都大彭城寺释宝琼传》:“梁祖年暮,惟事熏修。臣下偃风,情言扇俗。搢绅学者必兼文义,所以屡开理教。《维摩》《涅槃》道被下筵,憓飞上席。”⑤《广弘明集》卷二三,《大正藏》第52册,第268页下。《出三藏记集》卷一一,第406页。《大正藏》第50册,第478页下。这些记载展现了《法华经》《涅槃经》等在南朝宋、齐、梁以来广为流传的事实。其中,周颙《抄成实论序》作于永明八年 (490),⑥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之下编《永明文学系年》对此有考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251页。《南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行状》(阙撰人,一作“裴子野”)则作于南齐永元三年 (501)以后。要言之:在江淹生活的时代——刘宋、南齐,续讲众经盛于京邑,对《法华经》《涅槃经》的讲唱及研究从未间断。刘宋大明年间,江淹的荐举人隐士何点就曾招僧大集,请“学涉众典,而偏以《法华》著名”的释僧印为法匠,听者七百余人;⑦《高僧传》卷八《齐京师中兴寺释僧印传》,第330页。萧道成称帝以前即建立招提,傍求义学沙门,⑧《高僧传》卷八《齐上定林寺释僧柔传》记释僧柔学通经论:“齐太祖创业之始,及世祖袭图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义士。以柔耆素有闻,故征书岁及。”(第322页)尝于刘宋升明元年造《妙法莲华经普门品》。⑨敦煌遗书中较为可靠的早期题记为伯422号、伯2522号、伯2836号,略谓:“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衮北徐衮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郡开国公萧道成,普为一切,敬造供养。”该卷系刘宋升明元年萧道成所造。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91页。齐永明五年,竟陵王萧子良“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招致名僧,讲论佛法”,[10]萧绎:《金楼子》卷三《说蕃》,许逸民:《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43页。江淹当时也是竟陵门下喜好文学的士林之杰,尝参与西邸盛会。据《南齐书·庾杲之传》载,齐武帝萧赜“敕杲之与济阳江淹,五日一诣诸王,使申游好”,①《南齐书》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15页。此明江淹于永明中与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等皆有往来。而竟陵王所敬礼之僧尼最有名者有注《法华经》的慧基,“敬集名僧,夤敷奥籍”②沈约:《竟陵王解讲疏》其二,《广弘明集》卷一九,《大正藏》第52册,第232页下。成为时尚,江淹无疑会受到这一盛弘讲说风尚的影响。当时诗坛胜流多通过阅读内典、座下听经等途径接受佛教的熏习浸染,其中的“三乘归一”“法身常住”诸义是《法华经》《涅槃经》一贯的思想,皆为当时文化中心区的知识精英所熟悉,其余芬泽及当时不为外物所动的隐逸之士和排斥佛法的布衣之士。如南齐时荆州隐士刘虬精于释理,善于论议,述佛理,莫能屈,所注及所讲佛典皆当时流行者;③萧子良《与荆州隐士刘虬书》载其“注《法华》等经,讲《涅槃》 《大小品》等”,见《广弘明集》卷一九,《大正藏》第52册,第233页上。世居江左且与梁武帝有布衣交的才士荀济见萧衍信重释门,寺像崇盛,便上书讥佛法,言营费太甚,其表引《涅槃经》“阇王害父耆婆叙状”,斥天子注经,讥臣下逆乱。④《广弘明集》卷七《辩惑篇第二之三·叙列代王臣滞惑解下》,《大正藏》第52册,第130页中。在此种崇重讲论的环境中,江淹也概莫能外,其《无为论》中所表现的佛教思想无疑同当时流行的《法华经》《涅槃经》《大智度论》等佛教经典的讲说有直接联系。我们只有从宋、齐、梁所流行的佛典与学说来理解江淹等南朝士大夫们的相关作品,才能深入了解其意义。
二、江淹的佛教信仰与荆州的禅法
《吴中礼石佛》一诗写到了江淹的“禅心”。其中“常愿乐此道,诵经空山坻”句展现了江淹对佛教经卷讽诵功德的信受。⑤《妙法莲华经》卷六《法师功德品》赞扬诵经的功德,认为诵经是五种法师功德之一,可得六根清净果报。而“禅心暮不杂,寂行好无私”句则写出诗人对习禅的一种体验。“不杂”乃专心修定、不杂余想 (不杂爱见、慢等烦恼)⑥《大智度论》卷二四《释初品十力》:“禅波罗蜜即是诸解脱。禅、定、三昧、解脱,皆名为定,定名为心不散乱。‘垢’名爱见、慢等诸烦恼; ‘净’名真禅定,不杂爱见、慢等烦恼,如真金。”又,卷八八《释四摄品》:“四禅、四无色定、灭受想,名‘九次第’;灭受定,但圣人能得。四禅、四无色定——从初禅起更不杂余心而入二禅;从二禅乃至灭受定,念念中受,不杂余心,名为‘次第’。”(《大正藏》第25册,第238页下、682页下)之谓。“暮”字当作“晚”解,非指称年龄(江淹时年三十四),盖指夜晚宜于静心习禅。这在佛教经论中多有表述,如《摩诃僧祇律》卷一《明四波罗夷法之一》记舍卫城难提长老于开眼林中作草庵舍,“于其中初、中、后夜修行自业 (禅定)”;《大智度论》卷六《释初品中十喻》说“苦行头陀,初、中、后夜,勤心坐禅,观苦而得道”;《大方等大集经》卷三四《日藏分护持正法品》说持法比丘“初、中、后夜减省睡眠,精进诵经、坐禅修道”。⑦《摩诃僧祇律》卷一,《大正藏》第22册,第232页上。《大智度论》卷六,《大正藏》第25册,第107页上。《大方等大集经》卷三四,《大正藏》第34册,第236页下。皎然《答俞校书冬夜》诗所谓“夜闲禅用精,空界亦清迥”⑧皎然:《昼上人集》卷一,四部丛刊本,第5页。当承用其意。据此可知,“禅心暮不杂”一语乃对修禅深有体悟者方能道出,江淹当对修禅有所了解,或者说,他已有禅修的习惯。“忧伤漫漫情,灵意终不缁。誓寻青莲果,永入梵庭期”四句表达了诗人尊崇佛教的誓约。“灵”字在时人及江淹自己的作品中亦习见,且多与神灵或佛教相关涉,⑨如刘勰《灭惑论》:“夫塔寺之兴,阐扬灵教。功立一时,而道被千载。”释僧敏《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夫佛者,是正灵之别号。……杳然之灵者,常乐永净也。”(分见《弘明集》卷八、卷七,《大正藏》第52册,第50页上、47页上)简文帝《吴郡石像碑》所谓“道由慈善,应起灵觉”“灵相峩峩,渐来就浦”“况远追应身,近规灵迹”“宝兹灵像”等(《吴郡志》卷三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8页),其“灵”字皆与佛有关。此处当指诗人对佛教的信仰,江淹在借以喻指自己对佛教的崇信终究不会因世俗之“忧伤漫漫情”而受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江淹的《杂三言》五首之一《构象台》诗也提及修禅,且该作早于《吴中礼石佛》。[10]丁福林《江淹年谱》(第99页)系此于宋元徽四年 (476),谓此诗是江淹在闽 (建安吴兴)第三年作。《杂三言》五首亦属骚体,诗序中所说“予上国不才,黜为中山长史,待罪三载,究识烟霞之状”,与《自序》中“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着文章自娱”诸语相合。①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卷五、卷十,第177、379页。下引《构象台》诗,见《江文通集汇注》,第178页。所谓“待罪三载”,即指被黜为吴兴令的三年。五首分别以“构象台” “访道经”“镜论语”“悦曲池”“爱远山”为题,可谓作者吴兴生活之具体反映。《构象台》诗云:“余汩阻兮至南国,迹已徂兮心未扃。立孤台兮山岫,架半室兮江汀。……伊日月之寂寂,无人音与马迹。耽禅情于云径,守息心于端石。永结意于鹫山,长憔悴而不惜。”所谓象台者,当有或塑或铸的佛像。从诗的内容来看,江淹立象台,盖为禅修观想之用(“取佛形相,系想思察”②慧远:《佛说无量寿佛经义疏》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178页。)。这也再次表明,江淹不仅了解禅修,且已经有禅修的习惯。那么,江淹的禅修始于何时且得之于何处?要回答这一问题,须将江淹仕宦荆州的经历及其与南朝宋、齐诸王的交游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因为南朝诸王子颇信佛,并多与文人交游,诸王、文士与佛教之关系成为一种引人注意的现象。而江淹尝历仕宋、齐诸王,其中的巴陵王刘休若、建平王刘景素及豫章王萧嶷,皆与荆州地区的禅法有关联,且江淹曾侍从他们出镇荆州。
巴陵王刘休若是宋文帝刘义隆第十九子,《宋书》卷七二、《南史》卷一四有传。江淹《自序》云:“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右常侍。”据《宋书·明帝纪》所载,刘休若于泰始五年 (469)闰十一月为征西将军、荆州刺史,七年二月为建平王所代,则江淹赴荆州就任巴陵王右常侍当在泰始六年。③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卷十,第379页。《宋书》卷八《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5页。刘休若为荆州刺史时,常与江陵释僧隐交游。《宋江陵释僧隐传》载:“释僧隐,……常游心律苑,妙通《十诵》,诵《法华》《维摩》,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笈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顷之东下,止江陵琵琶寺,……禅慧之风,被于荆楚。……后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税驾禅房,屈膝恭礼。”④《高僧传》卷一一,第432页。这条文献有三处值得注意:第一,僧隐是《法华经》的诵读者;第二,僧隐为玄高弟子,禅律兼善,对荆州禅法之流布贡献至大;第三,巴陵王刘休若及建平王刘景素在任荆州刺史期间与之交往密切。江淹就任巴陵王右常侍时,当有机会接触这种源自北方的禅法。
建平王刘景素,父刘宏,为宋文帝第七子。南朝王子尊崇释教,刘景素可为代表。据史书记载,刘景素好文章书籍,喜招集才义之士,以收名誉。⑤《宋书》卷七二,第1861页。《南史》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1页。《隋书·经籍志四》集部“别集”类,著录宋《建平王景素集》十卷。刘景素与佛教之关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于佛教义学颇有造诣,有相关专著。《南齐书·王智深传》载:“宋建平王景素为南徐州,作《观法篇》,智深和之,见赏,辟为西曹书佐。”⑥《南齐书》卷五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96页。此《观法篇》作于宋元徽四年 (476)。二是与名僧交游密切。据《宋京师庄严寺释昙斌传》记载,释昙斌初止新安寺,讲《小品》《十地》,申顿悟惭悟之旨,建平王刘景素“谘其戒范”。又据《南史》建平王本传、《齐上定林寺释僧远传》记载,栖玄寺在鸡笼山东北,宋文帝为建平王刘宏立第于此,后舍为寺。刘景素“谓栖玄寺是先王经始”,欲请隐迹于上定林山禅室的释僧远驻锡,僧远未允。⑦《高僧传》卷七,第291页。《南史》卷一四《宋宗室及诸王下》,第400页。《高僧传》卷八,第319页。泰始七年二月,刘景素取代刘休若为荆州刺史,至泰豫元年 (472)四月宋明帝卒,改征为太常。⑧参见《宋书》卷七二《建平宣简王宏传附子景素传》、卷八《明帝纪》,第1865、169页。刘景素赴荆州任的这一年间,江淹随之。《梁书》江淹本传载:“景素为荆州,淹从之镇。”江淹《望荆山》李善注引沈约《宋书》曰:“建平王景素,为右将军、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经。”⑨《梁书》卷一四,第249页;《文选》卷二七,第385页下。由此可以推知,江淹先后随从巴陵、建平二王镇守荆州,当亦曾随二王拜谒江陵释僧隐,并藉此获得对僧隐禅法的了解。
豫章王萧嶷,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次子。据《南齐书》其本传记载,萧嶷虔敬佛教,临终时尚不忘嘱咐二子“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云云。又据《梁上定林寺释法通传》载,萧嶷尝拜谒定林上寺释法通,而法通“专精方等,《大品》《法华》尤所研审”。①《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第417页。《高僧传》卷八,第339页。可见萧嶷笃信释教,并重义理。江淹《自序》、刘璠《梁典》《梁书》江淹本传都言及江淹在南齐建国之初,尝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参军一职。②江淹《自序》云:“受禅之后,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参军,镇东武令,参掌诏册,并典国史。”《文选》卷一六江文通《恨赋》引刘璠《梁典》:“齐兴,为豫章王记室。”(第235页)《梁书》江淹本传:“建元初,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参掌诏册,并典国史。寻迁中书侍郎。”《南史》江淹本传中“骠骑豫章王”下有“嶷”字。(第1450页)《南齐书·高帝纪下》载,建元元年 (479)夏四月戊戌,萧嶷以荆州刺史除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六月甲申,被立为豫章王;九月乙巳,又以新除尚书令、骠骑将军、豫章王身份为荆、湘二州刺史。江淹于是年四月任骠骑府记室参军,据《南齐书·檀超传》所载“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与骠骑记室江淹掌史职”,则至少在建元二年,江淹尚在萧嶷府中任职。③参见《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卷五二《檀超传》,第35、891页。建元元年九月,萧嶷为荆、湘二州刺史时,江淹当随嶷之荆州。是年,萧嶷与从蜀下荆州传播禅法的玄畅禅师相遇。据《齐蜀齐后山释玄畅传》记载,玄高弟子释玄畅自宋元嘉三十年 (453)后,“迁憩荆州,止长沙寺。时沙门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经》等,畅刊正文字,辞旨婉切”。④《高僧传》卷八,第314-315页。盖在刘宋末年,玄畅西适成都行化,至建元元年九月,萧嶷为荆、湘二州刺史,出镇荆、陕,又遣使征请玄畅重返江陵。⑤宝唱:《比丘尼传》卷三《集善寺慧绪尼传》:“齐太尉大司马豫章王萧嶷,以宋升明末出镇荆、陕,知其有道行,迎请入内,备尽四事。时有玄畅禅师,从蜀下荆,绪就受禅法,究极精妙。畅每称其宿习不浅。绪既善解禅行,兼菜蔬励节。豫章王妃及内眷属,敬信甚深,从受禅法。……萧王要共还都,为起精舍,在第东田之东,名曰福田寺,常入第行道。”(《大正藏》第50册,第943页下)《齐蜀齐后山释玄畅传》:“齐骠骑豫章王嶷作镇荆、峡,遣使征请。”(第316页)萧嶷及其眷属与玄畅交往密切,江淹随从萧嶷,当亦对玄畅禅法有所了解。
总之,江淹此三段侍从诸王之荆州的经历为他接受禅法提供了机缘,其中前两次经历都发生在江淹被贬建安吴令前,即《吴中礼石佛》《构象台》二诗的写作之前。荆州特殊的地域性,为江淹接触禅法提供了便利。荆州,东晋定治江陵,至南朝一直为长江中游重镇。刘宋初年,荆州已成为当时经济极发达繁荣之大都市,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⑥《宋书》卷五四末引史臣语,第1540页。宋武帝诸子如彭城王义康、江夏王义恭、临川王义庆、衡阳王义季、南郡王义宣等皆尝次第为荆州刺史。⑦《宋书》卷六八《南郡王义宣传》记载:“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谢晦平后,以授彭城王义康。义康入相,次江夏王义恭。又以临川王义庆宗室令望,且临川武烈王有大功于社稷,义庆又居之。其后宜在义宣。上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阳王义季代义庆,而以义宣代义季为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军事、征北将军,持节如故。……二十一年,乃以义宣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义宣至镇,……多畜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第1798-1799页)诸王赴荆州之任,对当地文学及佛事活动皆有推动。如,元嘉二十九年正月三日,天竺国大乘比丘释求那跋陀罗于荆州城内译出《八吉祥经》,义宣即为檀越。⑧《八吉祥经后记》,《出三藏记集》卷九,第352页。刘义庆“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晩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⑨《宋书》卷五一《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子刘义庆传》,第1477页。汤用彤已指出:“宋初禅法流行之域,为蜀、为荆州,为建业。蜀与荆州接近北方,故禅定甚盛。……宋以后二地 (蜀与荆州)禅师,较江南为多。”[1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773页。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僧隐、玄畅以外,在刘宋前后还有诸多禅师尝驻锡荆州,如:佛驮跋陀罗,传罽宾佛大先新禅法,在庐山受慧远之请,出禅数诸经,“停止岁许,复西适江陵”;①《高僧传》卷二《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传》,第72页。《出三藏记集》卷一四《佛驮跋陀传》作“以义煕八年,遂适荆州”。(第542页)昙摩耶舍,罽宾人,刘宋初年,“南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其有味靖之宾,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②《高僧传》卷一《晋江陵辛寺昙摩耶舍传》,第42页。昙摩密多,罽宾人,特深禅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阁”;③《高僧传》卷三《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传》,第121页。《出三藏记集》卷一四《昙摩蜜多传》中记载昙摩密多特深禅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停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馆”。(第546页)宝亮:《名僧传抄》第十九中记载昙摩密多 (梁言法友)“偏好禅那,兼修定品”,“志愿游方,弘通禅悦,于是泛泊来东,以宋永初三年,始至江陵,住长沙寺”。(《卍续藏经》第134册,第18页)畺良耶舍,西域人,以禅门专业,“后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后还卒于江陵”;④《高僧传》卷三《畺良耶舍传》,第128页。释法期,乃玄畅弟子中特有禅分者,“及畅下江陵,期亦随从”,后卒于长沙寺;⑤《高僧传》卷一一《宋荆州长沙寺释法期传》,第419页。释僧印,玄高弟子,“修大乘观,所得境界,为禅学之宗”, “尝在江陵教一比丘受禅,颇有所得”;⑥宝亮:《名僧传抄》第二○,《卍续藏经》第134册,第20页。僧景法师,前往庐山求佛道,“于时江陵僧徒多有行业,或告法师曰荆州法事大盛”,乃因此东枻,“遇僧净道人深解禅定,乃曰:‘真吾师也。’遂落发从之,住竹林禅房”。⑦虞羲:《庐山香炉峰寺景法师行状》,《广弘明集》卷二三,《大正藏》52册,第269页下。
自东晋义煕八年 (412)至南齐建元年间,荆州地区禅法颇盛。尤其在刘宋元嘉元年,其禅法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从师承看,荆州禅法主要来自公元4、5世纪盛行于罽宾的禅法。如昙摩耶舍传罽宾弗若多罗禅系;浮驮跋陀罗弘传达磨多罗与佛大先禅系,凉州释玄高从之受禅法,⑧《高僧传》卷一一《宋伪魏平城释玄高传》,第409页。而僧隐、玄畅又皆玄高弟子。由于罽宾禅风在荆州的行化,至唐代,荆州青溪山寺禅众天下称最。⑨《续高僧传》卷一九《唐雍州津梁寺释法喜传》,《大正藏》第50册,第587页上。总之,江淹尝随行诸王就任的荆州地区,自东晋以来就是一个禅法流行的区域。由于巴陵王刘休若、建平王刘景素及豫章王萧嶷,皆崇信释教,且皆与荆州地区的禅法有关联,故江淹当无法疏离于这种习禅的佛教文化背景之外,这就可以解释他的诗中为何屡屡提到“耽禅”“禅心”此类与禅修有关的语汇。
此外还有一条较少有人解读的资料,可以说明江淹与禅法的关系,这就是“江淹才尽”的传说: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10]《南史》卷五九《江淹传》,第1451页。并见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34页。
这里提到江淹罢任宣城太守后,尝“泊禅灵寺渚”。禅灵寺,齐永明七年武皇帝萧赜所造,由谢蘥撰写碑文。[11]《南齐书》卷四三《谢蘥传》,第764页。《南朝佛寺志》卷下云:“其地当秦淮运渎之交,有渚 (即今之范家塘)有桥 (即今之斗门桥)。”[12]陈作霖编:《南朝佛寺志》,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246页。南朝帝王中,齐武帝乃佛事活动的参预、信仰较著者,[13]《出三藏记集》卷一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之“杂图像集上卷第八”载《齐武皇帝造释迦瑞像记》,“经藏正斋集卷第十”载《齐武皇帝供圣僧灵瑞记》,“止恶兴善集卷第十二”载《齐高武二皇帝敕六斋断杀记》《齐武皇帝敕断钟山玄武湖渔猎记》《齐武皇帝敕罢射雉断卖鸟雀记》,第487-490页。为造禅灵寺,尝施舍倾赀,[14]《南齐书》卷四○《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永明末,上将射雉,萧子良谏表中有“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倾金宝于禅灵”之语。(第699页)故其于禅灵寺甚珍爱[15]《南齐书》卷五六《吕文度传》,第978页。。至于起禅灵寺之最初动机,《南齐书·祥瑞志》载:“(永明)七年,越州献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长三寸。上起禅灵寺,置刹下。”《大智度论》卷一七《释初品中禅波罗蜜》曰:“禅,此言思惟修,言禅波罗蜜一切皆摄。”《一切经音义》卷二一《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卷一四“净行品音义”释“禅那”曰:“此云静虑,谓静心思虑也。旧翻为思惟修者,略也。”①《南齐书》卷一八《祥瑞志》,第366页。《大正藏》第25册,第185页中。《大正藏》第54册,第439页中。可见,禅灵寺最初的命名即与禅修佛像的灵瑞传说有关。禅灵寺建成后成为信众巡礼、修禅及举行斋仪的所在,②《出三藏记集》卷一二《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著录竟陵王萧子良《八日禅灵寺斋并颂》一卷。(第452页)《金楼子》卷一《箴戒》:“齐武帝时,内人出家为异衣,住禅灵寺者,犹爱带之如初。”(《金楼子校笺》,第339页)而自齐建武三年 (496)至齐东昏侯永元元年江淹出为宣城太守,③参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60-461页;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54-455页;俞绍初:《江淹年谱》,第438页;丁福林:《江淹年谱》,第185页。期间禅灵寺成为他经常巡礼的地方。对此,唐人常咏及,如皎然《七言酬秦山人赠别二首》之一:“我有主人江太守,如何相伴住禅灵。”自注:“江淹为宣城守,常会禅灵寺。”贯休《避地毗陵寒月上孙徽使君兼寄东阳王使君三首》之三:“唯有孤高江太守,不忘病客在禅灵。”徐铉《送德迈道人之豫章》:“禅灵桥畔落残花,桥上离情对日斜。……莫道空谈便无事,碧云诗思更无涯。”④皎然:《昼上人集》卷一,第12页。胡大浚:《贯休歌诗系年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960页。《全唐诗》卷七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83页。唐人的这种认识当承自南朝。
三、结 语
江淹涉佛诗文的生成与南朝佛教讲说之风及流行情况有极密切的关系,作为当时士大夫的代表,他的个案实际上反映了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书写状况。纵观其佛教世界,江淹诗文中所表现的佛教思想至少有三方面的来源:
一是佛教的三世果报观。此在其《伤爱子赋》得到反映:“伤弱子之冥冥,独幽泉兮而永秘。余无愆于苍祇,亦何怨于厚地。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愿同升于净刹,与尘习兮永弃。”⑤《广弘明集》卷二九,《大正藏》第52册,第342页中。“三世之远致”即佛教三世果报之说,亦即所谓“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⑥《大般涅槃经后分》卷上《遗教品第一》,《大正藏》第12册,第900页下。之意。此说自晋宋以还一直是士大夫谈论之题旨,江淹贬谪之前因世事无常、家庭变故导致其对佛教三世说的崇信,这与《无为论 (并序)》中所云“吾曾回向正觉,归依福田”,及《自序》中所云“又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偏好老氏清净之术”的观念相符。
二是当时文化精英群中盛行的大乘佛教思想,诸如法华三乘、涅槃常住等观念。佛教传入中土,自东晋以还,所出佛经多是大乘佛典,文化中心地区也以讲说大乘经典为时尚,⑦《出三藏记集》卷一载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序》:“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已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第2页)“名师法匠,职竞玄义”,“讲匠英德,锐精于玄义”,⑧《出三藏记集》卷一二载释僧祐《世界记目录序》《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第464、476页。精研大乘佛理成为这一时期知识精英们的共同追求。江淹生活的时代,正是大乘佛教在中土强势发展的荣茂时期,当朝诸王不但奉法虔敬,且精于玄理,常招致名僧讲说佛法,这对当时士大夫接受佛教以及佛学经典的传播具有推动作用,大乘佛教之圣典如《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涅槃经》《大智度论》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案头读物,其中有关般若有无、法华三乘、涅槃常住等玄理备受青睐,成为他们辩析论难时重要的哲学命题,亦成为他们诗文命意遣辞的主要资粮。江淹在诗文也常表现这些观念,比如《水上神女赋》中所表现的“有无”观念:“悦有无于俄顷,验变化于咫尺。视空同而失貌,察倏忽而亡迹。野田田而虚翠,水湛湛而空碧。……退以为妙声无形,奇色非质。”以及诸多诗文中所展现的“空”的观念:《丽色赋》“嗟楚王之心悦,怨汉女之情空”;《青苔赋并序》“必居闲而就寂,以幽意之深伤。……昼遥遥而不暮,夜永永以空长”;《哀千里赋》“惜重华之已没,念芳草之坐空”。而《丹砂可学赋并序》记修道者“抱魄寂处,凝神空居,……辍阴阳于形有,传变化于心识”,更是由“空”而体认到“心识”的相续以及生灭变动。①参见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第27、75、18-20、17、47页。“有无”“空”“寂”“心识”等佛教名相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江淹诗文的玄理及厚度;同时,这些颇具开释深义、解散疑结之效的大乘教理,也给江淹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指导,像他在《无为论》中所建构的“大人”境界,即是其解决出处进退的良方。
三是禅观修习。以江淹为代表的南朝士人爱乐佛法,不仅表现在玄理层面,亦在宗教实践方面,如坐禅、诵经。江淹所接触到的荆州一带的禅观佛教,有别于建康城内偏尚玄义的义学佛教,②《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解篇论》:“当斯时也,天下无事,家国会昌。……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谘质文理,往往而繁。时有三大法师云、旻、藏者,方驾当途,复称僧杰。挹酌成论,齐骛先驱。”(《大正藏》第50册,第548页上)使他的日常生活中有了禅修实践,这在《构象台》《吴中礼石佛》中都有反映,并且这种禅修一直持续到江淹出任宣城太守之时。要言之,禅观的修行方式被江淹奉为秘要,最终成为其在贬谪生活中息心和对治烦恼的药草,使之在患难中做到“忧喜不移其情”,守静味禅,“逍遥经纪”,以适性为乐。在老氏知足为怀和佛教离着说的双重映照下,原本无心著书的江淹在齐永明初年以后便不再“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③江淹:《自序》,《江文通集汇注》卷十,第381页。在诗文创作上也不再汲汲于进取,由此“江郎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