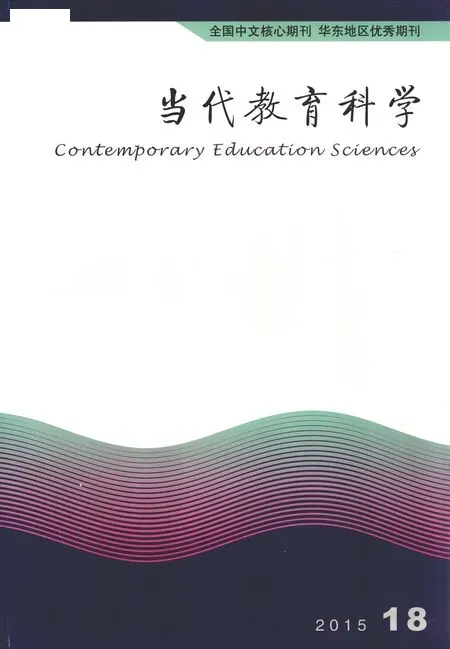教师犬儒化的反思与超越*
●郑立群
教师犬儒化的反思与超越*
●郑立群
现代犬儒主义成为现代社会不可规避的话题,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受此文化形态的影响,而教师被犬儒化后,教育价值追求幻灭,理想虚无;在教育实践中显得既无生命力,又无深度。教师身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的时代特征使整个教育陷入危机,教师应意识到并努力寻找超越犬儒主义的出路,努力实现自身“沉思生活”和“行动生活”的统一。
教师;现代犬儒化;批判与反思;超越
现代语境中,犬儒主义背叛了古典犬儒主义的崇高价值,陷入了精神危机,对信仰嗤之以鼻。如果说古典犬儒主义是行动居住在随遇而安的“大瓮”里,现代犬儒主义则是思想意识蜷缩在自己构建的“围墙”里。“平庸的邪恶”成为现代犬儒主义的主要特征:生活中玩世不恭随波逐流,自诩为“难得糊涂”又对一切抱着不相信的态度。这种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还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1]部分教师受其影响,逐渐丧失了教育价值追求,在教育实践中表现为懒惰平庸。教师身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的普遍生存状态将使整个教育陷入危机。教师应意识到自身问题,寻求超越现代犬儒主义的出路,唤醒自身公共理性精神,投身公共生活的构建,积极实现自身“沉思生活”和“行动生活”的统一。
一、教师犬儒化产生的社会背景
现代犬儒文化产生的背景可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对理性生活的允诺无法兑现,导致人们对未来理想的幻灭;此外,工业革命的兴起发展促使了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在物的包围中,人成为消费社会的奴隶。
(一)后现代主义的物化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商品极大丰富、信息爆炸式增长、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2]这种消费社会的兴盛,使抽象的历史进程被物化和欲望化。文化形态相应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也进入了大变革时期。“1964年以来,时代精神的巨变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识,左派和右派的整体意识形态再也于事无补了。”[3]中国80年代经历了西方思潮文化的全面冲击,随着后来这股势头的瓦解,脆弱敏感的理想主义者逐渐依附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商品化生活,这正是现代犬儒主义产生的土壤:丰盛与全套的商品让人们沉浸于物质生活中不可自拔,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们眼花缭乱,无暇顾及、无暇思考存在的意义,在“物的包围”中,沉溺于感官的享受,这种感觉将人的精神活动引入懒惰无为的状态,人彻底沦为消费社会的奴隶。现代犬儒主义表现出极端功利主义的特征: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对我有利”成为“怎样活着”的唯一标准,其他一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二)传统道德理想的瓦解
启蒙运动为民众绘制了一幅不可实现的理想蓝图:一个合理自由的世界,一个整体和谐的主体,一种结束社会不平等的希望。[4]所有允诺随着启蒙运动的失败而泯灭,斯洛特蒂克将其定义为“启蒙的虚假意识”,这滋生了人们的悲观情绪,对自身的生存状态亦产生怀疑,甚至演变为一种用不相信来理解自身的存在。现代“犬儒主义”的产生,正源于启蒙运动的失败,它成为启蒙运动失败的缓冲物,理想破灭,民众失去理想的指引,一切都化为虚无。它打破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选择关系,泯灭了“可能之事”和“对不可能之事的追求”之间的差别。既然理想在现实中屡屡碰壁、无法依靠,不如抛弃理想,随遇而安,过好现在的生活,只有日子每天都在继续是最可靠的。如果说现代犬儒主义在美国的症状是“没有深度的能量”,在欧洲的症状是“没有能量的深度”,[5]那么在中国的症状就是“既没有能量也没有深度”。中国现代犬儒主义将功利视为唯一的价值取向,排斥其他真善美的精神价值,为了谋求生存利益最大化,不顾及社会的道德底线,甚至以更糟糕的弄虚作假来面对公民道德。教师作为个体在社会关系中也很容易被现代犬儒主义所异化。传统中国教育的“百年树人”深受现代消费社会的冲击,教育成为了“生产力”,教育被“产业化”,而传统中国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延伸到了经济领域,教师成为“老板”、“商人”。教育成为一种非物质的商品,一种文化消费。
(三)社会转型期的精神困境
中国正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急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在严重分化,心理结构也在发生严重变化。在中国当代社会,经历了“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学潮”等洗礼,知识分子变得噤若寒蝉,不敢再争取所谓的话语权,不愿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起来具有争议性,失去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勇气和动力。既然理想是靠不住的,那就泯灭理想;既然信仰是无法实现的,那就不再信仰;既然崇高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躲避崇高”。所以,一切都不要多想。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大欺骗,何必要去辨别真伪,“难得糊涂”才是其精神的归宿。在现代犬儒主义这里,人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不再重要,“人活着”战胜了“人应该怎样活着”的命题。此外,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失去理性思考,变成“有知识的人”,实际是后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在后现代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的主观性逐渐被异化,个人变得既没意愿,也没激情,对政治表现出一种无奈和冷漠。因为“一切都已经问题重重,所以一切也都似乎毫无差别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现实无力感后,对什么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处事态度,这实际是精神削弱后的颓废,是通往真理之路上对阻力的妥协,是人性的衰退。这种人性的衰退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绪和对未来毫无希望的状态。
二、教师犬儒化的表征
教师被犬儒化后,教育理想和教育实践都显出一种“没有能量和没有深度”,在教育理想上顺从胆怯、没有信仰,没有教育目的,没有对教育价值的追求,走向极端虚无主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变得懒惰无为,没有利益就没有动力,走向极端功利主义。
(一)教育信仰缺失,理性精神走向虚无
教师犬儒化后,“没有能量和没有深度”的一种明显表征是对教育没有信仰,没有教育理想,甚至嘲讽他人的理想。“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6]如果教育只剩下冷冰冰的技术手段,教师对学生缺乏“爱心”,就会从心底拒绝理解学生、接纳学生,无视学生的内心和情感需要,表现在言语上不关心学生的内在性,可以在课堂上,公然“教育”学生:“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分数才是真的。”语言是思想的外在形式,教师这种“没有能量和没有深度”的信仰正是教师丧失理想追求的显现。教师信仰的缺失,将会造成从事教育工作的驱动力丧失,陷入对“教育意义”无力感的漩涡,消解“教育意义”,不愿意肩负起“教育意义”的重担,教师这种颓废的人生态度会慢慢腐蚀学生的价值观,这种没有信仰追求的教育,实际抽离了教育的灵魂,只将教育当作单纯的技术手段,关注学生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忽视学生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主体性价值。甚至嘲讽学生的理想,“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空谈。”对他人的教育理想也是一种怀疑态度,“别假惺惺了,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啊”。如果教师身上缺少了“为国家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和使命,缺少了对于未来的希望,言传给学生的也将是没有人生理想追求的极端虚无,还极有可能导致所教育的学生精神颓废。
教师如果被犬儒化将导致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匮乏,瓦解身为人师的传统道德理想,这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国教师群体的特殊身份,从自由知识分子,传统社会的“士”到现代社会的“体制内人”。教师作为“体制内人”,服从“体制”比反思“体制”重要,若有不同观念、鲜明个性,稍不留神就会失去已拥有的一切。那就“让怎么干就怎么干,想那么多干嘛”,对待学生提出的质疑,甚至会说“想那么多干嘛?考试就把这个标准答案记住就行”……教师的思考高度将直接影响学生的思考能力,慢慢地,教师陷入对自身奴隶状态的不觉悟,对自身异化处境的不自知。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荡然无存,处于盲目和茫然状态,不知道自身存在的目的何在,长此以往,教师思想被引向了理想的极端虚无主义。
(二)教育目标短浅,教育价值趋向媚俗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7]教育如此,教师亦如此。教师犬儒化后,教育价值理性缺位,在教育中处于“无思”状态。因为丧失教育理想,也就不敢怀疑教育目标,无暇深思教育目的,教师缺乏教育热情,片面追求教的工具理性。现代社会,“在消费的普遍化过程中,再也没有灵魂、影子、复制品、镜像……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的:标志着各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育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8]教师只追求教育的工具理性,将直接导致教师在教育中拒绝思考、拒绝独立,这种对教育事业“思考”能力的缺席,导致教师在教育理念中盲目顺从,将教育目标当成教育目的。所以,教师即使知道有些教育目标违背教育目的,也会随波逐流,甘愿被大众同化,迎合大众的附庸风雅需求,这种迎合往往是对教育问题的不敢批判、媚俗盲从。教师媚俗还表现在沉浸于消费社会的商品化欲望,教育行政化的追逐名利;为了迎合大众品味,放弃自己的学术品味,走向低级趣味;为博得眼球,不惜为社会的某种病态教育现象辩护,甚至为那些失去教师道德良知、失去社会责任感的“范跑跑”之流辩护。
媚俗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一大特征,大众传媒的发达,娱乐至死的文化消费惹人关注,消解着文化的意义,为了适应新环境的文化,教育也在适应这种新环境文化,教师也在传播这种物质的文化需求,教师对大众文化的依附成为其文化媚俗的一个重要表现。教师的追求趋向于短期目标、临时目标,教育价值追求不敢偏离大众轨道,不敢坚持教育的本质需求,导致所从事的教育工作越来越媚俗化。
(三)生活中平庸无为,教育实践迈向功利
教师犬儒化后,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表现为职业倦态,对教育现状的各种“无奈感”和“乏力感”。具体为,教师对待学生没有热情,对待所从事的职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单纯将其当作谋生的工具。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不敢公开表示质疑,虽然头脑中的知识明知都是假的,行动上却义无反顾、争先恐后,对现实有诸多不满,但是“无力改变”成为生存状态最深处的写照。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依附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通过搞突击、弄虚作假“争荣誉”,应付所谓的“教育评估”。在对待教育指标问题上,教师彼此心照不宣、上下皆然,造成学校内部师生之间都熟练操作两套话语系统。比如在评优晋级、三好优干等问题上,虽然表面上都合情合理合程序,而实际运作却是按需分配,在公正的名义下执行另外一套规则,人们也逐渐变得见惯不惊甚至默而从之。这种教育体系内的“身教”严重损害了受教育者的是非观,对教育道德品质的破坏非常严重。
教师犬儒化后,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还表现为急功近利、专注“量化”形式。现代社会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消解了教师应该遵从的价值规范和良心,仅仅以功利的心态去对待一切超验价值,教师日常的行事逻辑热衷于分数,惟考试成绩马首是瞻,为了提高教学成绩、为了提高升学率,也可谓煞费苦心:有的苦口婆心地教诲学生,殚尽竭虑地给学生补课,甚至采用辱骂、威胁、体罚等手段逼迫学生学习;有的为了不让学生拖延班级成绩后腿,不惜采用欺骗手段,让成绩落后学生装病缺考;在老师之间互相保密,隐瞒自己复习的真实情况,不敢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如果说教师功利主义是为了学生“追求最大幸福”从而获得教师“最大的幸福”,那么犬儒化的教师在急功近利地追求“量化”和分数后却失去了作为教师的幸福。教师虽明知理念与现实之间有差距,仍然会以“不得不为”的心态安慰自己,使利益追求成为常态,虚假成为常态,道德沦丧成为常态,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实践活动将教师的精神处于矛盾和分裂状态之中,从而使教师变为利益和权力的依恋者。
三、教师犬儒化的超越
我们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征途中,遭受着现代社会既定的制度和个人内心良知的双重考验。教师犬儒化将导致教师在教育生活中对学生缺乏热情、对教育思想、教学方法除了怀疑就是否定,除了不相信就是无所谓。教育犬儒化的最大问题在于,教育不再是参与公共生活、建构公共秩序的积极力量,这种教育反而带来了当代政治文化的冷漠与幻灭。[9]教师要在这种现代化语境中保持清醒就要努力实现对犬儒化的超越。
(一)教师“沉思生活”的永恒追寻
“沉思生活”意在对人类存在境界的本质追求,是一种高尚的人类机能。教师“沉思生活”首先包括教师对教育理想的追寻,坚持信仰爱的教育。教育理想的信仰不仅包括教师对自己人生追求的信仰,还包括教师对教育信念的信仰。教师对教育理想的信仰是教师最重要的内在精神动力,“我们认为人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10]启发着教师理想追求的方向,为教师提供强大的信仰力量,从而使教师具备成长为理想教师的信仰。教育信念的信仰主要指“爱教育”的信仰,“爱的本质是要为某种东西付出‘劳动’,以及‘使某种东西成长’。”[11]爱的教育,在原始生命力中,在创造和付出中成为可能。教师只有爱教育,才会用心从事每天的教育活动。教师犬儒化,往往造成不相信教育,甚至拒绝正视道德良心的审判。教师将这种非道德和非良心解释为对自我生存的无奈和自己身为弱者的保护伞,进行自我蒙蔽。教师可以从古典犬儒主义那里寻求精神的救赎。古典犬儒主义把挽救道德败坏看作自己的职责,奉行“德”,注重内在的修养,追求精神信仰。
其次,这种“沉思生活”还包括教师对自身职业伦理精神的追寻。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教师除了关注学生的工具价值,重视学生对学校各门课程的学习,还要关注学生灵魂的成长,人的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教师的职业伦理精神还包括教师的职业伦理道德。亚里士多德早就看到了:道德随着践行道德的能动者而发生变化,教师的道德不同于商人的道德,承担的义务也不同于商人的义务。所以教师不仅要为人师表,还要对个人德性走向进行反省与自明,不仅规范学生的日常学校生活,还要关怀学生的内心情感。
(二)教师“行动生活”的积极实践
“无论一个思想家多么关注永恒,当他一坐下来写他的思想的时刻,他就首先考虑的不是永恒,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怎么样留下一些永恒的印迹。”[12]这里“留下痕迹”的过程就是“行动生活”。“行动”是阿伦特笔下的积极活动,是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之一,这种行动不需要中介,而是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并伴随着言说进行,是行动者在言行中的彰显。“行动”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教师的生活正是这样一种“行动生活”,通过教师与学生直接进行交流、互动,去改造学生,启发学生的心智。
教师犬儒化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教育工作冷漠,对任何事情都持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要超越这种生活,需要教师积极进行教育实践活动,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努力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首先,教师要积极参与教育活动。教师对教育的参与,源于教师独立人格和独立理性的需求,而非教师作为“体制人”的不得不为的教育职业需求。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要充分引导师生间的互动,与学生进行思想情感交流,以此引导学生追求较高的思想境界。此外,教师的劳动对象是正在成长的个体,这种个体带有开创性,对学生的教育不仅仅是商品的复制,还需要教师用自己的思想、常识和言行直接影响劳动对象。
(三)教师“公共生活”的主动介入
“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自愿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13]教师要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就必须自觉进入“公共生活”。此外,教师还是一种社会角色,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这种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教师“行动生活”的基本保障。教师犬儒化,则意味着一种公众生活规范的危机。破除危机,则要教师实现公共生活的主动自觉。这种公众生活的自觉涉及到公共领域的环境、制度和秩序。阿伦特认为,公共生活具有相当的公开性和共同性,与政治关系重大;哈贝马斯更明确指出,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利领域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这正是中国目前亟需规范的空间,公民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才能实现完整意义上人的生活。
教师犬儒化的超越要依赖这种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首先,树立自觉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教师不是上完课就与课堂没有关系,每个教师都要有主动参与班级管理、学校管理、社团活动的意识,在这个场所里,自觉遵循一定的活动规范,共同维护学校的公共环境;其次,保证参与公共生活的时间。学校公共生活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一个文件一阵风式的,它应该成为教师常态化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跟风性的参与,而是教师权利和义务的一部分;最后,理性参与公共生活。教师区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需要依赖公共理性。康德认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是唯一可以带来人类启蒙的途径。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还会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14]罗尔斯在此基础上重新明确了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15]所以,教师在公共领域对公共理性的运用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教师运用公共理性的能力也是启蒙学生的必备能力。
[1]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221.
[2][8][美]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97-198.
[3]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意识形态的暗淡”(“Ideological Blurring”),见《瞭望》(Prospect),1996年6月.
[4][5][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7,174.
[6][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4.
[7][捷]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易伟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75.
[9]高伟.现代犬儒主义教育哲学批判[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2).
[10][美]赫舍尔.人是谁[M].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7.
[11][德]艾·弗罗姆.爱的艺术[M].李建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23.
[12][1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0,24.
[1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25.
[15][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25.
(责任编辑:刘君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3JJD880004
郑立群/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