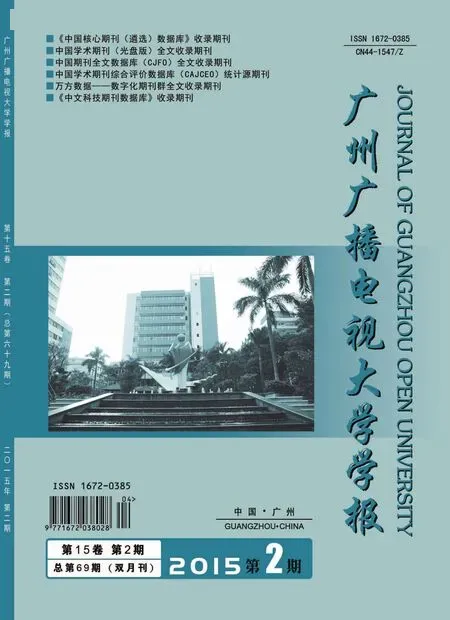悲剧:从消亡到重生——浅析尼采“悲剧消亡”思想的美学意义
摘 要:“悲剧消亡”思想是尼采悲剧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尼采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尼采认为,真正的希腊悲剧精神是一种可以净化人生的审美存在,而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文化,则彻底地把悲剧葬送了,悲剧的消亡到重生就是“从事辩证法的苏格拉底”到“从事音乐的苏格拉底”的一个历史性的历程。通过希腊悲剧精神的回归,尼采的悲剧美学思想蕴含着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收稿日期:2015-03-01
作者简介:卢赛男,女,助理讲师,研究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尼采是一个具有否定精神的哲学家和美学家。海德格尔在谈到尼采对传统哲学思想的批判时指出:“‘否定’是他所热衷的,他喜欢有一个勇敢好战的灵魂。否定的思想方式,使尼采不会告诉你在你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有价值,但会告诉你只有你的生命才能衡量价值。” [1]尼采哲学的美学意义不仅仅是否定前人的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在提出否定性观念的同时,也已经在自己的哲学和美学活动中形成了鲜明的价值指向。他把自己比作是可以否定那些已经形成稳定价值观念的“炸药”,自称:“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2],并强调“否定和毁灭乃是肯定的条件” [3]。本文将试从悲剧的起源和古希腊悲剧的诞生、古希腊悲剧的消亡和古希腊悲剧重生的可能性三个方面阐释尼采“悲剧消亡”思想的美学意义。
一、悲剧的起源和古希腊悲剧的诞生
1869年5月,尼采开始写作《悲剧的诞生》。这本著作是尼采早期的重要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他哲学和美学的理论基础。在《看呢这人:尼采自述》中,尼采谈到了他的《悲剧的诞生》,他这样说道:“这本书有两项带根本性的革新,一、对希腊人的狄俄倪索斯现象的认识——这是对这一现象的首次心理学分析,这本书把这一现象看成整个希腊艺术的根据之一。二、对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首次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用‘理性’对抗本能。坚决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 [4]尼采认为,真正的希腊悲剧精神是一种可以净化人生的实质性悲剧,是一种可以将人生以一种审美化的状态呈现出来的审美存在,而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文化,则彻底地把悲剧葬送了。尼采据此对悲剧的起源和本质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悲剧是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相互斗争的结果,是日神艺术和酒神艺术相互渗透的产物。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互为斗争的,日神和酒神“这酷似生育有依赖于性的二元性,其中有着连续不断的斗争和只是间发性的和解。” [5]日神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倾向于外在表现型的造型艺术,体现的是理想和希望的阿波罗精神;酒神精神是以醉为本质的,体现的是人的最本质的追求享乐和放纵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在日神艺术和酒神艺术这一对概念中,尼采提出,一方面,日神艺术是一种肯定性的冲动,是一种肯定形式的存在,但是日神艺术所创造的个体存在是有限的,而且也都不可避免地在走向消亡,因此,日神艺术是一种包含否定性的肯定性存在;另一方面,酒神艺术是一种否定性的冲动,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但是酒神艺术的否定和毁灭不单纯地是为了否定个体存在,而是为了在否定的基础上进行更好地肯定和创造,因此酒神艺术是一种包含肯定性的否定性存在。这两种精神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希腊悲剧,即是尼采自己所说的:“悲剧神话只能理解为酒神智慧借日神艺术手段而达到的形象化。” [6]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肯定的是:狄奥尼索斯精神,即意志生命力体现;生命必然的悲剧性质和生命一定要有对抗痛苦的欢乐;意识不是创造者,本能是旺盛的生命力;理性使悲死亡。” [7]所以在悲剧的起源问题上,尼采认为悲剧的本质就是悲剧性,就如同人生的悲剧的本质就是人生的悲剧性一样。人是作为一个注定要消亡的个体而存在的,这就是人生悲剧的根源,也是人生悲剧性的实质。
那么,如何消解这一层次的悲剧呢?古希腊人把希望寄托于由日神艺术和酒神艺术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悲剧神话,他们的这一行为得到了尼采的肯定。受叔本华悲观意志论哲学影响,尼采认为,人生确实就是悲惨的,也是充满悲剧性的,要想消解人生的这种悲剧性,就必须把人生和世界当作一种审美现象,以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来看待人生,他说:“现在,我们在这里必须勇往直前地跃入艺术形而上学中去,为此我要重复早先提出的这个命题:只有作为一种审美,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 [8]
二、古希腊悲剧的消亡
尼采认为,源自于苏格拉底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在希腊文化中产生的对悲剧具有毁灭性的东西。受科学精神的影响,人们开始认为知识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这种科学精神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贪得无厌的求知欲,正是这种贪得无厌的求知欲让希腊人心中对悲剧艺术的渴望之情日渐熄灭,希腊人心中的酒神被扼杀了。尼采之前的哲学史认为,希腊哲学的兴盛时期是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但是尼采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希腊哲学的高峰期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时期,他认为真正的哲学精神应该是健康灵魂的一种发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赫拉克利特就是能表现真正哲学精神的代表。苏格拉底精神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就是希腊悲剧精神消亡的根本因素。正如尼采所说:“欧里庇得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具,借他之口说话的神祗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一个崭新的灵物,名叫苏格拉底。这是新的对立,酒神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的对立,而希腊悲剧的艺术作品就毁灭于苏格拉底精神。” [9]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用大量的篇幅来批判苏格拉底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其“面具”的欧里庇得斯。在尼采那里,苏格拉底在人类历史上成了一种既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的崭新的东西。尼采认为,逻辑和辩证法是苏格拉底所带来的一种追寻知识的手段和途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认为悲剧不属于对人生有实际功用的事物,而应该被列到谄媚艺术之中。在苏格拉底看来,悲剧艺术从来没有诉诸真理,甚至不能诉诸哲学家,这是他拒斥悲剧的双重理由。苏格拉底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只要条件允许都是可以被探知的。在尼采的眼中,苏格拉底这个用逻辑和辩证法来驱逐悲剧的不速之客,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他本人就是辩证法的代表,他本人就是辩证法的体现,或者更直接地说,苏格拉底本人就是辩证法。所以,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对悲剧真正的威胁不在于他所持用的逻辑精神和辩证法精神,而是苏格拉底这个个体存在背后所形成的“审美苏格拉底主义”和“逻辑苏格拉底主义”。“欧里庇得斯要把戏剧单独建立在日神基础之上是完全不成功的,他的非酒神倾向反而迷失不自然主义的非艺术的倾向,那么现在就可以迫近审美苏格拉底主义的实质了,其最高原则大致可以表述为‘理解然后美’,恰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彼此呼应。” [10]所谓的“逻辑苏格拉底主义”,也和“审美苏格拉底主义”一样,已经超越苏格拉底本人而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这种形而上的存在让苏格拉底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认为自己代表的是一种比同时代人更为先知性的存在,因此在他不被同时代人理解时,在他被审判时,在他被处以死刑时,他都显得大义凛然。“谁只要从柏拉图著作中稍稍领略过苏格拉底生活态度的神性的单纯和自信,他就能感觉到,逻辑苏格拉底主义的巨大齿轮仿佛在苏格拉底背后运行着,而这个齿轮又如何必能透过苏格拉底如同透过一个影子观察到。苏格拉底本人也预感到了这种关系,表现在无论何处,甚至在他的审判官司面前,他都大义凛然,有效地执行他的神圣使命。” [11]
苏格拉底不认可酒神精神所揭示的冷酷世界,不接受悲剧所揭示的世界的真相,他认为通过知识的获得可以克服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达到对人生有积极作用的乐观主义。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只是苏格拉底这个神祗的外面表现,苏格拉底借欧里庇得斯葬送了希腊悲剧精神,让人们陷入了理性和逻辑的漩涡中去。苏格拉底所代表的理性主义文化、科学主义文化以及功利主义文化都是对生命本能的一种扼杀,是对生命本能及人的创造力的一种敌视,是对艺术的一种毁灭。但不可否认的是,苏格拉底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正是这种深远和巨大的影响让尼采把苏格拉底当作人的生命本能的反抗者和扼杀者来批判。“苏格拉底的影响如何象暮色中愈来愈浓郁的阴影,笼罩着后世,直至今日乃至未来” [12]“我们只要看清楚,在苏格拉底这位科学秘教传播者之后,哲学派别如何一浪高一浪地相继而起,求知欲如何不可思议地泛滥于整个有教养阶层,科学被当作一切大智大能的真正使命汹涌高涨,从此不可逆转……那么,我们就不禁要把苏格拉底看作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旋涡了。” [13]应该说,悲剧是从酒神的音乐精神中诞生出来的,因此,它脱离了音乐精神就必然走向消亡。苏格拉底这个被雅典人放逐的手持辩证法的理性主义的先驱者,他最终借助于欧里庇得斯,在悲剧中渗入一种理性的、积极的乐观审美,从而把希腊悲剧精神葬送了。
三、古希腊悲剧重生的可能性
尼采认为,希腊悲剧必将重生。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在到了康德和叔本华阶段之后,支配柏拉图主义以及世界历史的苏格拉底精神是不是真的就要灭亡,酒神精神是不是必将回归?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认为,理性消灭了酒神精神,悲剧因此而消亡,但同时,尼采也乐观地认为,当代世界中的酒神精神正在苏醒,希腊悲剧正在适合它重生的土壤中回归。酒神的苏醒需要一个与酒神的消亡相反的过程,“公正地把酒神精神的消失,同希腊人最触目惊心的、但至今尚未阐明的转变和退化联系起来时,倘若最可靠的征兆向我们担保相反的过程,担保在我们当代世界中酒神精神正逐渐苏醒,我们心中将升起怎样的希望呵!” [14]尼采一度谈及德国的音乐,认为“德国音乐,我们主要是指它的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到瓦格纳这一光辉历程” [15]是与苏格拉底文化的原始前提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德国音乐既不能由苏格拉底文化说明,也不能由它辩护,但德国音乐的意义恰恰在于它是能使苏格拉底文化消亡的工具,是希腊悲剧回归的土壤。所以,在对瓦格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之后,在他的晚期哲学著作中,尼采仍然坚信悲剧这种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必定再生:“我预言,悲剧时代必将来临,因为,当人类经历了认为战争虽历尽千辛万苦、但又绝对必要这种意识之后,即不以为苦之后,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必将再生……” [16]
在尼采看来,悲剧的消亡到重生就是“从事辩证法的苏格拉底”到“从事音乐的苏格拉底”的一个历史性的历程。“从事辩证法的苏格拉底”在统治世界之后,又重新站到了狄奥尼索斯面前去悔过,就如同他临死前在狱中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经常在梦中梦到一个人向他说:苏格拉底,从事音乐吧!如此以来,“从事辩证法的苏格拉底”在经历了否定酒神,再否定自己这种否定之否定后,达到了“从事音乐的苏格拉底”这个层面,这一过程也不可否认的地成为一种尼采所扬弃的“辩证”的过程。而恰恰是在这种过程中,尼采看到了悲剧重生的希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乐观主义的尼采用乐观的态度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从这一点上来看,尼采的悲剧美学思想中无疑也蕴含着对人性及其人的审美化生存的巨大期许与精神慰藉,这也正是他的悲剧美学思想的价值所在。自从尼采在西方的思想界一跃而起的那一时刻开始,尼采的悲剧学说及其悲剧消亡观点曾一度被人误解,德国法西斯分子所掀起的“尼采热”更让尼采因此而背上了种种骂名。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再来回顾尼采的悲剧消亡思想,不仅会产生新的理论期望,而且它会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文化现实有积极的启发。在现代世界,对物质的贪婪和追求让人们的内心不断地感到空虚和无聊,这正如尼采笔下患“现代衰弱症”的人们一样,迷失在无意义的人生境况中。在尼采看来,人的出生就是最根本的悲剧,但人们只有拥有悲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生,尼采用大量篇幅来论述人生的悲剧及其消解的途径——艺术审美,正是为了向我们提出如何超越人生的悲剧的途径,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必须要肯定的是,尼采的悲剧消亡思想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悲剧消解的可能性,也蕴含着一种面对悲剧时必须具备的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因此,理解尼采悲剧消亡思想的美学内涵,对我们深化艺术审美与现实人生的关系,追求和谐的现实生存状态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