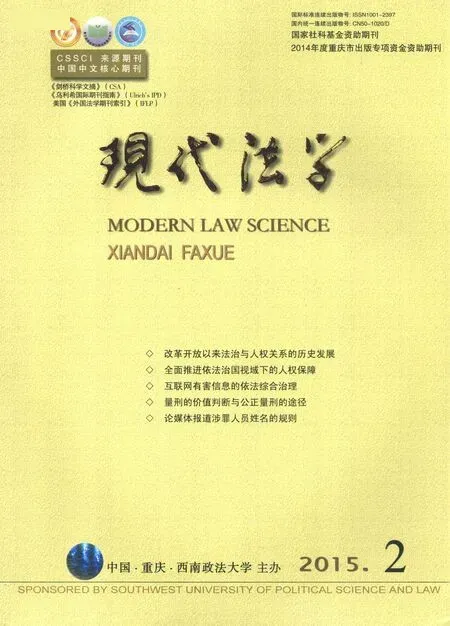论用工单位介入派遣劳动合同
论用工单位介入派遣劳动合同
涂永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真假劳务派遣或不当劳务派遣是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研究中的重要维度。劳务派遣作为一种特殊的用工方式,由派遣单位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谓之派遣类劳动合同。然而,如何订立派遣类劳动合同却在《劳动合同法》中少有提及。现实中普遍存在用工单位过度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过程的现象,在理论上也鲜有人讨论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过程的尺度。遵循劳动合同制度的一般原理,在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阶段引入实质雇主的判断标准,既要承认用工单位介入劳动合同订立过程的经济理性,又要限制用工单位的过度介入。在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阶段引入劳务派遣中的实质雇主标准,将是规范我国劳务派遣的一条重要路径。
关键词:派遣类劳动合同;用工单位介入;劳动合同;实质雇主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劳动合同法》专门规定了“劳务派遣”并自成一节,但对劳务派遣中的劳动合同并无特别的称谓,在实践中,劳务派遣中的劳动合同被称为“派遣类劳动合同”。与派遣类劳动合同同时存在的是劳务派遣协议,有时候甚至存在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用工合同”的现象。此三个合同存在关联性,在内容上又往往大同小异、互相连通。在一般情况下,签订派遣类劳动合同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用工单位的影响,而这也恰恰是被派遣劳动者感觉极为奇怪的事情:无论是去甲公司应聘却最终在乙公司工作,还是在乙公司应聘却最终与甲公司签约,均有些奇怪。从《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劳务派遣毕竟是一种非典型的、非主流的、灵活的就业方式,其合同形式理应简单明了,却在实践中成为比一般劳动合同更复杂的合同文本或文本群。倘若以合同理论的一般原理诸如缔约、成立、生效、相对性等来解释劳动合同、派遣协议、用工合同之并存,只怕极其困难,又鲜有论述。目前已有不少人对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结构进行了分析①探讨相关问题的文献较多,其中我国学者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既有研究,可参见:黄程贯.德国劳工派遣关系之法律结构[J].政大法学评论,1998,(6) : 271-302;周宝妹.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研究[J].法学杂志,2010,(3) :71-74.,而且劳务派遣之三角关系已经成为主流认识,有关劳务派遣法律管制的诸多问题均在此基础上展开。但是,关于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细致结构却又观点纷呈,如双重劳动关系说、双层运行说、共同雇主说、特殊劳动关系说等[1]125-137。故而在劳务派遣法规范分析方面有两种研究趋向:一种是细节的研究,如关于连带责任的研究[2];一种是整体的研究,如关于立法模糊与改进路径的研究[3]。本文拟沿着兼顾细节与立法改进的思路去研究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中用工单位介入问题。
2012年12月28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专门为劳务派遣作出了4处修改,其中在第63条关于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的规定中增加一款,即“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和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载明或者约定的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应当符合前款规定”,试图通过派遣类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一致性来解决同工同酬问题。然而,派遣类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内容方面的一致性必然会强化用工单位对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过程的影响。具言之,《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强制性要求用工单位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益,却忽视了劳动合同订立制度的一般原理,这种公法规范恣意干扰私法规范的立法模式可能会影响劳务派遣的法律结构,模糊劳务派遣法律关系应有的内容[4]。在此背景下,笔者试图建构劳务派遣中的劳动合同订立制度,而在立法、现实乃至学理均为用工单位介入敞开大门的时候,可能需要做的主要是拿捏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过程的尺度,因此,了解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现状显得极有必要。
二、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现状
被派遣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往往对派遣单位并不熟悉,却与用工单位熟悉。劳务派遣中的三个合同文本多由用工单位主导。①在个别情况下,如大型派遣公司也可能主导合同文本,但往往不能主导用人与否。随着劳务派遣概念的确立和相关法律的实施,劳务派遣的结构重心移向派遣单位,并有两个基本共识: (1)在劳务派遣中,由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劳务派遣是派遣单位招用劳动者后,将劳动者派到用工单位,由用工单位对劳动者进行指挥、管理。②《劳务派遣规定(草案)》中的概念可佐证这一共识:“本规定所称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招用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后,按照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将劳动者派到用工单位,由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指挥、监督和管理的一种用工形式。”于是,劳动者的就业过程与劳动合同的订立过程产生了远远大于劳动关系与劳动合同那样的裂隙,以致不再对应。奇怪的是,法律共识下的社会实践又颠倒了一次,即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是不争的事实。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之极端情形是用工单位将其已有员工转换为被派遣劳动者,这是典型的虚假派遣,在此不论。这里单论用工单位对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影响。
(一)用工单位在劳务派遣中的影响
用工单位在劳务派遣中的影响路线与我们定义劳务派遣的概念恰恰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定义劳务派遣的出发点是劳动合同,落脚点是用工单位的指挥、管理。用工单位影响劳务派遣的路线是自指挥、管理的考虑出发,落脚于劳动合同。这两个方向可以转化为派遣类劳动合同和劳动派遣协议孰先孰后。在理论上,派遣类劳动合同与劳动派遣协议的先后顺序无关紧要,既有派遣单位先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理由,也有要派单位先于派遣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理由[1]201。在现实中,极少出现派遣类劳动合同明显先于劳务派遣协议的情形,而从用工单位对派遣单位的介入基础来看,理应是劳务派遣协议先于派遣类劳动合同。
事实上,用工单位对劳务派遣的影响已经模糊了派遣类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的界限,使得两者往往成为一揽子协议。实践中出现的用工合同往往是该一揽子协议的产物。就用工单位之影响而言,派遣类劳动合同有如下特征:
1.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边缘化
劳动合同在劳务派遣中的地位因为用工单位的影响而被边缘化。在劳务派遣三方中,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以及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协商空间比较大,而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很少有直接的接触。劳动合同在此俨然成为劳务派遣协议和用工关系的衍生物。
2.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形骸化
派遣类劳动合同在形式上可能比一般的劳动合同还要复杂,因为它完全可以涉及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所有方面,但也可能没什么可约定的,因为劳动合同的内容在劳务派遣协议和用工关系中已有约定。派遣类劳动合同所承载之合同价值消散,其内容已经不为其所有,形式化的派遣类劳动合同往往仅具形骸。
3.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去合同化
派遣类劳动合同虽然具有合同的形式,诸如甲方乙方、权利义务等,却在制度设计上难以贯彻劳动合同的合同属性,并在用工单位的过度干预下成为用人单位与派遣单位、劳动者分别达成协议后的单方行为——用工单位的单方行为。本来劳务派遣作为一项特殊的劳动合同制度,被认为是以派遣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为基础的,而事实上却与劳动合同关系不大。我们把派遣类劳动合同所处的现实情形和制度境遇称为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去合同化”。①事实上,我们习惯于将劳务派遣作为一种用工方式,把派遣工、合同工并列起来,这必然会忽视其原本的合同属性。
(二)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情形
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情形大致有:
1.用工单位决定劳动合同的内容
对劳动者薪酬、休假、社保等涉及用人单位给付之事项并非派遣单位所关注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派遣单位关注派遣服务费,而用工单位却是劳动者薪酬、休假、社保等事项的最终义务主体,该事项理应由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共同决定。劳务派遣协议看似是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磋商的一个平台,劳动合同之内容也并非用工单位单方决定,却因为派遣单位利益激励的缺乏,成为用工单位单方决定之事项。在这个意义上,用工单位不只是影响劳动合同的内容,而且是决定劳动合同的内容。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派遣类劳动合同应当载明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而该等信息皆来自劳务派遣协议,可见用工单位影响乃至决定劳动合同的内容也是法律制度明确规定的。
2.用工单位直接决定劳动者的人选
用工单位决定劳动者的人选意味着用工单位介入派遣单位的招聘过程,不仅在招聘条件方面有决定权,而且对个别劳动者之选定拥有决定权。在一般情况下,用工单位并非概括地接受派遣单位所派遣之劳动者,而是对具体劳动者的情况进行了解,这也是确保指挥、管理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但是,用工单位直接逾越派遣单位决定劳动者之人选,则与劳务派遣的原理大相径庭。在现实中,用工单位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情形非常普遍,并且花样繁多,以致在企业力求规范化用工、典型用工的情况下,也借此触及劳务派遣。
(三)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之典型案例
用工单位往往全面决定派遣类劳动合同,包括派遣单位、劳动者等主体的选定,以及劳务派遣协议和劳动合同的起草与订立。以下是典型的案例:
甲公司经过公开招聘、面试等环节欲录用劳动者乙。劳动者乙上班伊始,多应当有实习期,但是却由甲公司安排乙同丙派遣公司签订派遣类劳动合同。之后,丙派遣公司为乙正常发放工资,履行用人单位的一应义务。时隔不久,甲公司与乙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在丙公司为乙支付三个月工资后,甲公司开始为乙支付工资。
在此案例中,用工单位将劳务派遣作为试用期的替代机制,已经超越了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边界,属于用工单位单方拟就之法律形式。但是,这一做法在法律上并无不妥,唯独酿成纠纷时,乙会面临纠纷主体上的混乱。在一般情况下,乙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其在甲公司的实际司龄①司龄,即在特定公司的工作年限。与法律上认定的司龄并不一致。
三、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的法律问题
(一)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的正当性分析
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情形多样,其正当性应当具体分析。一概否认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正当性,会让劳务派遣走向机械与空想,更不符合劳务派遣的实际。我们可以为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提供以下理由:
1.劳务派遣协议上的权利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其中,派遣岗位、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等属于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必备内容。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协议对派遣类劳动合同的介入是当然介入,有明确的法理依据,并体现为契约上的权利。假设派遣单位有足够多的劳动者,凡符合劳务派遣协议所约定之要求者,皆可派遣,并不影响派遣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派遣类劳动合同。
正是由于用工单位此种契约上权利的存在,用工单位对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之影响解释了两种不同的劳务派遣形态,此恰如日本之立法例。“派遣劳工与派遣公司雇主间,依派遣劳动雇佣实态,大约可以设定两种模式,一是派遣劳工常时与派遣公司雇主间有劳动契约关系存在,称之为‘常用雇佣型派遣劳工’(日本法中称之为‘特定劳工’)。二是派遣劳工并未常时与派遣公司雇主间有劳动契约关系存在,仅于派遣公司处登记,嗣派遣公司应要派公司之需求派遣劳工时,再与派遣公司订立定期劳动契约,此种形态之派遣劳工可称为‘登录型派遣劳工’(日本法中称之为‘一般劳工’)。”[5]125可见,在登录型劳务派遣中,劳动合同之订立应要派单位之需求而发生,属于典型的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之情形。在常用雇佣型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决定派遣类劳动合同之内容的痕迹并不明显。
我国《劳动合同法》限定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2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则意味着用工单位依据劳务派遣协议上的权利来决定派遣类劳动合同的依据并不充分。依照逻辑,用工单位可监督派遣单位与劳动者所签订劳动合同中相关内容的合法性,却并不可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工资磋商。然而,我国劳务派遣立法对劳务派遣协议和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有明示,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约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自然地反映到劳动合同当中,这已经不是劳务派遣协议上的权利,而是一种法定的介入。
2.管理方面的需要
用工单位实际使用劳动者,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管理、监督、指挥下进行劳动,这意味着用工单位必然关注劳动者的人选,也属合理。尽管在法理上,用工单位不应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之订立,不能事先拟定被派遣劳动者。“但要派公司于实际使派遣劳工服劳务之前,事先‘大体上’了解一下派遣公司所拟派之人选,应该也可容忍,是要派公司人力资源管理运用上之必要程序。”[6]但是,基于管理上的需要而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之订立需要一个度,即用工单位介入之理由不应当针对个别劳动者,而仅仅是出于管理上之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用工单位应当监督派遣单位所选定劳动者之资质,而不应直接选定劳动者。
(二)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的危害
派遣类劳动合同是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合同,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在法理、现实以及制度上均有障害。
1.违反意思自治等合同上的基本法理
“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一样,都存在合同订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商问题,彼此间自然会因协商与交涉而花费心力、财力,彼此间应当遵守类似民事合同要约与承诺理论一样的游戏规则。”[7]97双方当事人协商最重要的莫过于意思自治,意思自治是私法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应当遵循该原则。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剥夺了派遣单位和劳动者意思自治的空间,这是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最大的障碍。在此观念下,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协议来决定被派遣劳动者的岗位、期限、工资、社保等,违反了私法之基本观念。
2.助长了虚假派遣
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务派遣受到了诸多限制,一些劳务派遣开始改头换面,如存在“假外包,真派遣”的情况[8]。然而,此种能够轻易改头换面的劳务派遣往往属于用工单位能够过度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之情形。这些所谓的“真派遣”多是在派遣结构上而言的,未必经得起动态分析的检验。事实上,劳务派遣能够改头换面为“外包”的背后,是内部承包和临时用工①这里的临时用工是体制上的身份临时,非实际工作的临时。先改头换面为劳务派遣。为什么劳务派遣能够在用工方式中中途掺和,其根源在于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之法理欠缺。
在无限容忍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背景下,规制劳务派遣时对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考察是一种静态的考察,所规制的事项诸如同工同酬、团结权、三性岗位等皆与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无关。这些规制事项在用工单位看来又不尽合理,进而更助长了用工单位对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控制。在此意义上,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与虚假派遣之间是一个恶性循环。
3.抹杀了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制度空间
《劳动合同法》本当对派遣类劳动合同进行明确规定,却在立法趋向上更多关注劳务派遣业之立法,劳务派遣下之合同制度却有些混乱。在实务中,劳务派遣协议被定性为民事合同,且在理论上也有此主张,却又多考虑到劳务派遣协议对劳动者的影响。如学者认为,“劳务(该)协议虽然属于平等市场主体间的民事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应遵循私法自治的原则,由双方在合同中自行协商去确定,但由于协商涉及第三方——被派遣劳动者……”[9]37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虽然劳务派遣协议被定性为民事合同。但是作为民事合同不仅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涉及到了第三方,即被派遣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同时该协议中应当约定的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等内容都不仅涉及被派遣劳动者的权利义务,而且这种权利义务的约定增加了被派遣劳动者的负担。”[10]站在被派遣劳动者所处的派遣类劳动合同角度来看,劳务派遣协议分明剥夺了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完整权利。
被派遣劳动者被剥夺的权利转化成了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权利,并通过法律将这种介入固定下来。故可以说,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抹杀了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制度空间。
(三)用工单位拟就劳务派遣的法律效力
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来回避试用期,是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一个极端案例,在该类案例中,派遣类劳动合同是由用工单位拟就的,甚至整个劳务派遣的结构也是用工单位操持的,更无须区分用工单位介入的影响因素是合同内容的确定还是合同当事人的人选。那么,在这样的案例中,劳务派遣的效力如何?
1.劳务派遣的效力问题是否存在
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劳务派遣作为一个事实,故而有劳务派遣的真假之分,有时候把表面上的劳务派遣认定为用工单位直接雇佣,有时候把表面上的承揽认定为劳务派遣,但是,我们并不习惯于思考劳务派遣的效力问题。那么,劳务派遣的效力问题是否存在呢?
事实上,劳务派遣终究是个合同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劳务派遣协议,还是派遣类劳动合同,均是书面合同。劳务派遣中的基本法理终究应当回归到合同当中,而“真假派遣”更多是一种社会描述,会慢慢被《劳动合同法》淘汰。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法律问题终究会转化为派遣类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的效力问题。
2.用工单位拟就劳务派遣的法律效力
在实践层面上,用工单位拟就劳务派遣时只要不违反诸如逆派遣等强制性规定,劳务派遣中的两个合同是有效的。然而,在理论上,用工单位的此种做法却并不妥当。在我们看来,其中最缺失的应该是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制度。依劳动合同订立的一般法理,用工单位拟就劳务派遣时,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应属无效。
四、订立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与实质雇主之判断
(一)订立劳动合同的一般原理
《劳动合同法》第2章“劳动合同的订立”共22条,涉及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诸多制度。派遣类劳动合同属于特别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劳动合同订立的一般法理。对于派遣类劳动合同来说,订立劳动合同出现的以下趋向值得注意:
1.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剥离
在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关系的关系方面,出现过两种趋向:一是以书面劳动合同标志劳动法律关系的存在,无书面劳动合同则属于事实劳动关系;二是以用工标志劳动法律关系的建立,书面劳动合同为事后之法律上的形式。我们显然经历了从第一种趋势向第二种趋势的转化,书面劳动合同对于表征劳动法律关系的意义大大减弱。“劳动法对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应当是基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为证明劳动关系存在及合同具有真实内容的证据。”在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法律关系剥离之后,劳动合同理论与书面劳动合同产生了隔阂,其好处在于确认劳动关系变得容易,其弊端是忽略了劳动合同的缔约、成立以及生效等方面的理论探究。
2.订立劳动合同过程存在大量的强制性规范
订立劳动合同过程存在大量的强制性规范,而这些规范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单独规定用人单位的义务的,如用人单位不得扣押劳动者证件和要求提供担保、不得歧视劳动者、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种是混合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权利义务的强制性制度,如用人单位的告知义务和劳动者的说明义务、服务期制度、竞业限制制度等。
3.劳动合同内容的变动性
一般认为,劳动契约有两大特色:从属性、继续性[11]。其实,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往往能够呈现出此种特征。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个体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劳动合同诸多内容的协商过程并不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短暂的招聘与应聘中及时确定下来,恰恰是伴随着劳动给付与工资给付的互动,劳动合同的内容才逐渐稳定下来。当我们以劳动合同内容的变动性来思考劳动合同的订立时,劳动合同之成立制度是非常模糊的,而劳动合同之订立制度理当也会因此而越来越复杂。
(二)订立劳动合同的一般原理在派遣类劳动合同中的适用
1.订立派遣类劳动合同的特殊之处
订立派遣类劳动合同的特殊之处在于关涉劳动合同内容的订立制度多无法在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进行实质性协商,而是转移到劳务派遣协议和用工管理中。这在日本登录型劳务派遣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劳动者仅仅在派遣公司登记,在要派单位有用工之需求时,劳动者才与派遣单位订立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之内容更多受到要派单位的影响。因此,派遣类劳动合同更似一个格式化的书面劳动合同,它与劳动合同有很大隔阂,且与劳动关系有更大的隔阂。
2.订立劳动合同的一般原理很难在派遣类劳动合同中适用
首先,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法律关系剥离后,订立劳动合同的理论抛开了书面形式的限制,成为诸多具体的法律制度,而派遣类劳动合同则停留在书面劳动合同之形式上,其与劳动法律关系已无对应关系。事实上,劳务派遣作为一个完整的派遣过程,成立了劳务派遣下的劳动关系。现有立法将劳动关系拘泥于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而派遣单位又无用工之事实,劳动关系的建立必然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为依据。在这里,派遣类劳动合同作为一项制度已经形骸化,却又在制度上承载着劳动关系之存在。
其次,在订立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受到诸多限制。劳动法律强加给用人单位的义务很难由派遣单位去落实,而相关事项要么在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展开,要么在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之间展开。通过劳务派遣协议来确定工资给付的水平,已然是劳务派遣上的共识,而劳动者又往往不能介入该协议之订立。
最后,订立派遣类劳动合同无法体现劳动合同内容的变动性。从签订派遣类劳动合同之日起,涉及劳动合同内容的诸多事项已经明确下来。这意味着派遣类劳动合同中的劳动已经定量、定型,而这却不符合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工作的从属性和继续性。
3.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原理适用
然而,一旦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劳动合同的一般原理在派遣类劳动合同中的适用就完全不同了。倘若用工单位越过派遣单位与劳动者就劳动合同之事项达成协议,派遣类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用工管理等必然成为一揽子协议,整合三者恰恰是一个完整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合同只是在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被肢解了。在此意义上,完善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制度,对于规范劳务派遣具有长远意义。
(三)订立派遣类劳动合同中的实质雇主判断
订立派遣类劳动合同应当符合劳动合同订立的一般原理,此正如《劳动合同法》第58条所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无论是书面劳动合同,还是劳动法中的诸多强制性规范,均当然地在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适用。但是,考虑到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过程,劳动合同订立的一般规则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为了维护劳动合同的一般原理,明确用工单位介入的尺度,有必要建立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中的实质雇主判断规则——根据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的介入程度,判断名义上的派遣单位与名义上的用工单位谁才是实质上的用人单位。
实质雇主判断在实践中多被用于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根据现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是一个独立的案由。该类纠纷的实体法依据主要是原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在一般情况下,判断劳动关系的核心依据是该通知的如下规定:“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此即谓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然而,在劳务派遣用工背景下,该从属性在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亦表现得极为明显,这符合英美法中关于劳务派遣的共同雇主理论。然而,“共同雇主说超越了劳动关系个数的拘谨,直接进入到法律责任问题上,并把法律责任问题技术化。”[1]136倘若定要在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之间进行选择以确定法律关系成立之际真实用人单位判断的若干标准,则必然要否定共同雇主的思维,引入实质雇主的观念。同时,劳务派遣中的用人单位判断必然不同于确认一般劳动关系的要件理论,因此,应该在明确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制度的基础上,建构劳务派遣中的实质雇主理论。
五、实质雇主理论的价值与相关制度设计
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制度究竟包含哪些特殊内容,它与劳动合同订立的一般制度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分析用工单位介入与否所产生的不同情形时,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制度价值便会凸显出来的。
(一)实质雇主理论的价值
实质雇主理论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1.实质雇主判断是阻却用工单位介入的法律保障
对于当下用工单位主导的劳务派遣形成机制,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制度是一个致命性的制度否认。倘若用工单位既不介入劳动合同的内容,也不介入劳动合同的主体选定,用工单位就不会无限制地采用劳务派遣这一用工形式。从劳务派遣基本原理出发,用人单位也不宜过度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阻却用工单位的介入,是分流当下纷乱的劳务派遣的法律手段。
2.实质雇主理论是促使劳务派遣规范化的法律路径
劳务派遣不应该是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劳动者之间签订的一揽子协议,派遣类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用工管理均应当相对独立。其中,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制度应该是灵活就业的重要承载主体。目前,我国的劳务派遣立法只承认固定期限的派遣类劳动合同,这意味着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有一个独立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与用工单位无直接关系,如被派遣劳动者没有实际提供劳动,劳务派遣单位也应依法支付报酬。
(二)基于实质雇主的相关制度设计
在理想状态下,派遣类劳动合同应该是劳动者根据派遣单位所提供的不同条件而签订的没有实际劳动内容的劳动合同。根据该合同,派遣单位再根据用工单位所提供的不同条件选派劳动者。事实上,这样的先后次序并不现实,派遣类劳动合同与劳务派遣协议的同时并发才是常态。因此,既要适当容忍用工单位介入,又要确保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的真实性,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可考虑引入如下制度:
1.用工单位介入被派遣劳动者人选的派遣无效制度
用工单位介入被派遣劳动者的人选,意味着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合同的磋商过程,其最终形成的是用工单位的直接用人事实,故而,用工单位介入被派遣劳动者人选的派遣应该无效。然后,根据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的用工事实确认劳动关系,而劳动合同中的具体内容可参照派遣类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用工管理等从严认定,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2.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内容的责任强化制度
劳务派遣公司以经营人力为主业,理应为劳动者和用工单位量体裁衣,提供合适的合同范本和协议范本。但是,为避免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内容而使派遣单位成为单纯的食利者,应该在制度上确定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责任强化原则。一方面,禁止用工单位为特定的劳动者而与用工单位量体裁衣;另一方面,在此情况下,派遣单位的责任应该强化,如在劳动者无工作期间的工资支付应参照劳务派遣协议的标准。
3.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格式化
派遣类劳动合同并不指向具体的劳动,这意味派遣类劳动合同在内容上应当可以大大地简化。对于成熟的劳务派遣市场来说,派遣单位之间的竞争可以为劳动者提供多样化的合同范本。从用工单位远离派遣类劳动合同的订立出发,派遣类劳动合同应该走向格式化。在派遣类劳动合同格式化后,劳务派遣协议对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影响则会弱化。在我国不承认登录型劳务派遣的立法中,此种格式化思考对就业极其困难者应该是一个挑战,其与劳务派遣单位协商的结果,可能是最低标准的派遣类劳动合同;对于就业能力较强的劳动者而言,其与劳务派遣单位协商的结果,可能是较高标准的派遣类劳动合同。无论何种结局,派遣类劳动合同应该在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展开,不容用工单位浸染。
六、结论:在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阶段建构劳务派遣中的实质雇主理论
我国《劳动合同法》已经明确了劳务派遣的三角框架,而且明确规定派遣单位居于雇主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中流行的“劳务”派遣观念,即用工单位购买劳务。这意味着劳务派遣的理论建构以隔离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从属性、继续性为重要趋向。本文专注于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阶段的用工单位介入及其限制问题,并梳理了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制度的独立价值和应有内容。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阶段引入实质雇主判断规则,建构劳务派遣中的实质雇主理论。为此,提出以下见解:
第一,摒弃劳务派遣协议与派遣类劳动合同在性质上的对立观念,重构派遣类劳动合同的相对性观念。实质雇主判断应当以派遣类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协议明确的功能定位为前提,故有必要梳理劳务派遣协议与派遣类劳动合同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承认,劳务派遣三方之间的关联是一种法律事实。“在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被派遣劳动者共同参与的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中,一方面,三方主体之间各自有独立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不同主体之间,可以构成利益同盟,对抗另一方,而这种利益同盟又随时可以瓦解。”[10]其次,在制度上明确劳务派遣协议和派遣类劳动合同在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成立上均属于基础法律关系,具有互动性。最后,应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协议的用工单位具有适当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过程的权利,派遣类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具有适当介入劳务派遣协议订立过程的权利。
第二,明确用工单位正当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情形,保护用工单位介入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正当权益。何为正当介入?至少包括以下情形:其一,用工单位根据劳动法律中关于用人单位的强制性规范,要求派遣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符合法律的规定;其二,用工单位有权了解派遣类劳动合同的文本,掌握被派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相关的事项,但用工单位不能直接与劳动者磋商。
第三,在实践中引入实质雇主的判断标准,防止用工单位的不当介入。实质雇主标准在原理上可归于我国的确认劳动关系理论,但劳动关系理论主要是按照从属性来确认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区分。实质雇主是在派遣类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确定用人单位的选择性判断依据,即确立具体个案中派遣单位是雇主抑或用工单位是雇主的依据。在一般情形,派遣单位是实质雇主,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应该认定用工单位为实质雇主,如用工单位直接与劳动者进行磋商、用工单位派员参与招聘全过程等过度介入之情形。
参考文献:
[1]李海明.劳动派遣法原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25-137.
[2]侯玲玲.我国劳动派遣连带责任规定之法理分析——《劳动合同法》第92条规定[J].法学,2008,(5) : 54-62.
[3]谢德成.我国劳动派遣立法的模糊性及其改进路径[J].法学,2011,(8) :121-126.
[4]涂永前.劳务派遣制被滥用的缘由及法律规制[J].政法论坛,2013,(1) :177-183.
[5]邱骏彦.劳工派遣法制之研究——以日本劳工派遣法为例[G]/ /台湾劳动法学会.劳动派遣法制之研究.台北:台湾劳动法学会自版,2000:125.
[6]台湾劳动法学会.劳动基准法释义:施行二十年之回顾与展望[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196.
[7]郑尚元.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97.
[8]郑东亮.劳务派遣的发展与规制:来自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的调查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36.
[9]孙冰心.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37.
[10]周宝妹.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研究[J].法学杂志,2010,(3) :71-74.
[11]黄越钦.劳动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4-96.
[12]安玉萍.论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法律效力[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107-112.
[13]李海明.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J].清华法学,2011,(2) :115-129.
本文责任编辑:邵海
The Employer’s Intervention into the Labor Dispatch Contract
TU Yong-qian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Real and false labor dispatch or inappropriate labor dispatch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in the study of legal system regarding labor dispatch.Labor dispatch,as a special employment approach,is contracted between dispatching unit and laborer.However,it is rarely mentioned in the Labor Contract Law of PRC.In reality,it is common to see that the employer’s excessive intervention into the contracting process,and further in theory,there are few discussions focusing on the scale or degree of its intervention into the process.Follow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labor contract system,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authentic employer judgment standard into the labor dispatch contract,in which we should not only admit the employer’s involvement into the labor dispatch contracting process from the economic rationality,but also limit its excessive intervention of the concerning employer.In conclusion,the introduction of authentic employer standard into the process of labor dispatch contracting will be a significant approach in regulating labor dispatch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labor dispatch contract; employer’s intervention; employment contract; authentic employer
作者简介:涂永前(1974-),男,湖北武汉人,中国人民大学,。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谐劳动关系的工资权基础与法律机制研究”(12CFX088)
收稿日期:2014-09-18
文章编号:1001-2397(2015)02-0092-10
中图分类号:DF4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