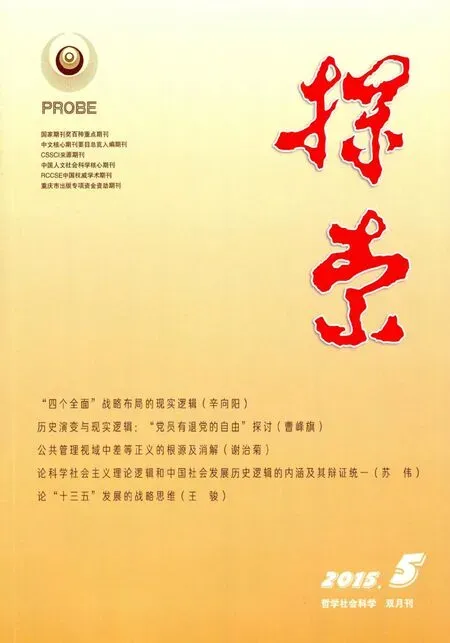生命价值的认知:从差等正义到追寻平等正义嬗变的逻辑及其进程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
人类社会关于生命价值的认知发生了从差等正义到追寻平等正义的嬗变。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差等”,反映的内在逻辑是工具理性对生命价值认知的影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使生命的工具性价值凌驾于生命的终极价值之上,从而导致不同社会成员生命价值实质上的不平等。当代社会以人为本和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要求社会管理者承认和尊重个体差异,构建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生命价值认知,从而推动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1 生命价值的内涵与生命价值观的演变
1.1 生命价值的内涵
价值泛指事物本身的有益性,在不同的领域中存在不同种类的价值,譬如政治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人的生命价值指向生命行为领域,即人的生命对于个人自身、他人以及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和效应。在一切人的价值中,人的生命价值无疑是最可贵和最复杂的价值。简言之,生命价值指生命的意义。
依据德沃金的观念,人的生命同时具备工具价值、主观价值与内在价值。其中,生命的工具价值以人的生命能为他人提供多少利益作为衡量标准;生命的主观价值(或生命的个人价值)以人的生命对促进个人活跃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生命的内在价值指任何人类有机体无论是否具有工具价值或个人价值,人都具有的内在价值。德沃金认为当政府肯定并主张人们具有生存权,并且认为人们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时,政府所致力保护的是人的生命的主观价值[1]90-91。德沃金所界定的生命的工具价值与生命的主观价值同属一种类型,均以人的生命能够为客体(他人或者自身)提供的利益作为评判标准,强调生命价值的工具理性维度。他所诠释的生命的内在价值,则强调生命价值的价值理性维度,指向生命的至高无上的终极价值。
从宏观上来看,人的生命价值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生命的工具性价值即考量个体生命的作用与功效,或者说个体的生命能够为自身、他人与社会提供的利益。生命的工具性价值包括正向的积极价值与负向的消极价值。第二类:生命的终极价值,指排除了人的阶层、种族、地位与权势等一切外在因素与外在条件之后,人依然保留的内在的生命价值。生命的终极价值一般意义上指的是正向的积极价值。无论个体对自己、他人与社会的作用与功效大小,每个个体都具有内在性的生命价值,生命的终极价值不因外在条件而消减或消逝。
1.2 生命价值观的演变
生命价值观指人们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认知、理解、判断及抉择,以及对于实现人的生命价值的方式与选择的认知。具体包括认知人的生命价值、理解人的生命具有何种价值、判断人的生命是否具有价值、选择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以及辨析人的生命内在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优先程度等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纵观人类整体进化过程和分析人的宏观生命活动过程可知,人的生命行为具有特别的复杂性。人的生命系统与生命机理极为复杂,即便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取得较大进展的今天,人类社会仍不敢断言已经完全认知人的生命系统与生命机理。历经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与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度或地域,人类社会形成了多样的生命价值观。生命价值观形塑的总体趋势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类社会对生命现象的认知由蒙昧走向清晰,人的生命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关于生命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这一趋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成员对人的生命现象的认知由神圣走向世俗。在古代社会,由于人类掌握的技术尤其是医疗技术极其有限,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对自身生命的维持大体上依赖于简单、自然的工具,有时人们借助巫术、神术、宗教等前现代“生命技术”,试图沟通神秘力量来寻求对人的生命的庇佑。在最初,囿于技术、能力以及可利用资源的极其有限性,人类社会无法客观认知人的生命现象,由于对未知的困惑和恐惧产生了生命崇拜。早期人类社会将生育、性行为等生命现象神化,寄希望于“神”或者其他超自然力量对生命现象的解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人的生命特征、生命阶段和生命节律等的客观认知不断深化,人们逐渐发现生命并不是神的恩赐,也并非超自然力量的赐予。随着知识的传播与发展,人类社会对生命行为的认知更加理性、系统与科学,人们认识到生命行为是世俗性的行为,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由神圣化向世俗化过渡。
第二,社会成员对人的生命行为的界定由义务转为权利。人类这一物种出现后的数百万年间,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处于无规范无控制的状态,人的生命行为既非权利亦非义务,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带有浓烈生物色彩的活动过程。而后,农业经济推动了世界上最早的复杂社会的发展,在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非洲的埃及、努比亚,南亚的印度等国家纷纷确立复杂社会[2]34。在前工业社会中,人们承认个人的生命具有某种社会价值,但这一生命价值完全属于社会(国家或者宗族)。人的生命行为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宗族利益等而必须履行的义务。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以及个体差别的不断扩大,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获得了某种使他凌驾于自身和社会之上的尊严。人类社会逐渐接近这样的时刻:同一个人类群体的所有成员再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他们都是“人”这一共同点之外。集体情感不得不依附于它所剩下的唯一对象,并且由此赋予这个对象——“人”——一种无与伦比的价值[3]361-364。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建立将人的生命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确立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拥有选择生命行为方式的权利和自由,对生命行为的界定由义务转向权利。
第三,社会成员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确认由差等正义趋向平等正义。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人们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知不断发展与深化。在前工业社会,等级制度和差等正义使得统治者的生命价值得到确认,被统治者的生命价值被视为工具性的,统治者承认被统治者的有用价值而忽视其生命价值。在工业社会,得益于人权与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认知的发展,生命价值观念得以进步,但这种进步是扭曲的,在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下,包括人的生命行为在内的一切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均以效率、利益为导向,人被普遍物化,虚拟需求取代了真实需求,导致一定程度上人的有用价值凌驾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认识到只有承认平等的生命价值,才不会出现一种社会阶层的生命价值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的社会现象,人们开始追寻与践行实质平等的生命价值。
2 人类社会关于生命价值的认知的嬗变
在人类社会演进的不同模式下,人的生命价值呈现多样态势。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以及其后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医疗技术水平与自然环境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为了氏族的延续,身体强健因而有利于生命族群延续的青壮年被视为氏族或者部落的支撑力量,尽管此时的原始人类还未树立客观的生命价值观,但已在实际操作中重视青壮年的生命价值,漠视老者、病患等的生命价值。自阶级社会诞生起,在前工业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人的生命价值呈现为差等正义的价值。工业革命后,随着现代国家制度对人的自然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确立,人的生命价值呈现为趋向平等的价值。然而工业社会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使生命的工具性价值一度凌驾于生命的终极价值之上,出现趋向异化的危象。
2.1 前工业社会:呈现差等正义的生命价值
在漫长的前工业社会中,差等正义论得以产生且备受推崇,是因为它能有效地服务于专制统治者,为其宣示权利与社会地位差异的合理性,为维护其所需要的等级秩序与特权利益提供理论支撑[4]。早期人类社会大致存在三类共有的阶层:统治阶层、自由人和奴隶。在呈现差等秩序的前工业社会中,统治阶层凌驾于自由人和奴隶之上,统治阶级以单向度的极端方式干预自由人和奴隶的生命及生活。
统治者依据社会成员的不同等级,将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同样区分为不同的层次。统治者享有对被统治者生命(主要通过生命的载体即身体来实现)的支配特权,被统治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呈现差等正义的生命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阶层间的差等生命价值;第二,不同性别间的差等生命价值。
不同阶层之间的差等生命价值,是依据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阶层所决定的。例如在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美索不达米亚人大致分为五种社会阶层,即统治阶层(国王和贵族)、祭司、普通的自由人、依附农和奴隶。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哈拉巴社会,雅利安人分为祭祀(婆罗门)、战士和贵族(刹帝利)、农耕者工匠和商人(吠舍)、没有土地的农民和奴隶(首陀罗)四种瓦尔那(瓦尔那为梵文词汇,指颜色)。据此,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得以支配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
不同性别间的差等生命价值主要体现为男性的生命价值绝对优于女性的生命价值,甚至于男性能够支配女性的生命行为。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均由成年男性主导,法律认可男性作为家庭的管理者。父权社会的权威持续加强对女性的社会行为和性行为的控制,这种做法迅速在西南亚和地中海世界传播开来,并进一步巩固了父权社会的结构[2]45-46。父权社会的权威一直延续,在前工业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人类社会将男性的生命价值置于至高地位,漠视女性的生命价值,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庸和工具。
2.2 工业社会及其后:呈现异化趋势的生命价值
现代性的精神实质就是肯定并且认可人的至高价值。现代文明赋予人类“万物之灵长”的至高地位,人的自由与人的权利被视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其中生命权不仅作为人权的子项,而且更被视为“第一人权”。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推动个体的生命权意识觉醒,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和接受。现代国家制度对人的自然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确立,促成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以人的生命为中心的生命价值观,在应然层面,人的生命价值是人人平等的。
工业社会公开呼吁保护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成为工业社会运行的主导价值。工业文明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强调,使得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生命价值被机器、时间所估量、分割,生命的内在价值为生命的工具价值所僭越。人们认识到在应然状态中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是平等的,但在实然状态中对工具(形式)理性的过度强调,使人普遍被物化,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人的生命价值出现异化的趋势或状态。
工业社会呈现异化趋势的生命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命的工具性价值凌驾于生命的终极价值之上。生命的工具性价值理应为生命的终极价值服务,但在实践中出现生命的工具性价值对生命的终极价值的僭越。第二,人的生命价值在形式上平等,但在实质上却不平等:阶层、种族、社会地位决定人的生命价值。人的出身、地位、身份、权势、财富等外在因素不同,这些外在性的条件使人的生命价值在实质上仍然呈现差等正义。
2.3 后工业社会:追寻实质平等的生命价值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们认识到只有承认平等的生命价值,才不会出现一种社会阶层的生命价值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的生命价值差等的社会现象,才能尊重每个人不同的生命行为选择,进而尊重社会中多样性、多元化的生命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新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新的家庭形式等社会因素也在客观上丰富了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后工业社会重新张扬人的价值理性,主张重新寻找人的主体性地位,此时诉求的是平等正义的生命价值。
3 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差等表现
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人的生命价值在实质上均是不平等的。古代社会的差等秩序决定了人的生命价值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不平等。近现代社会中,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颠覆了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的合法性,现代文明社会将尊重人权及弘扬人的生命价值视为要旨。此后人的生命价值在形式上大致表现为平等,但在实然状态中还存在许多不平等,诸如种族歧视、文化歧视、性别歧视、财产和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歧视仍在影响人们对自身或者他人生命价值的认知和判断。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本质而言,生命价值指向个体生命的内在性价值,人的生命价值本无高低贵贱之分,无论阶层、种族、地位与权势,每个人的生命都应当同等受益。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出现异化的趋势或状态,生命价值中的差等正义与当代服务导向型公共治理模式所诉求的公平正义理念背道而驰。社会成员生命价值的差等主要表现为个体生命价值实质上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管理者对不同个体生命权诉求的回应程度不同。
第一,个体生命价值实质上的不平等。人的出身、地位、身份、权势、财富等外在性的条件使人的生命价值在实质上仍然呈现差等状态。譬如我国,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人的生命价值“同命不同价”的差等现象仍然存在。个体生命价值实质上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以金钱来估量人的生命价值,甚至用金钱与人的生命价值来“交易”。典型的案例是人体交易。在印度等国家,受到个体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种族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人体交易只可能是穷人卖给富人,而不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2008年密里曼(Milliman)公司精算师曾计算出各类器官移植所需的费用,肾脏移植、肝脏移植、胰腺移植、肠移植费用分别为25.9万美元、52.34万美元、27.5万美元和120万美元。昂贵的价格在客观上决定了人体交易的“准入资格”,只有富人或享有政府超级保单的人才能考虑进行器官移植[5]72-73。个体拥有财富的多少客观上“决定”个体生命价值的高低,富人的生命行为选择权限往往比穷人大得多。
由于支付能力的差异,人体交易往往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公民购买(人体组织或器官),而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公民出售(人体组织或器官),或者同一国家与地区中富人购买、穷人出售。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制定相应政策规定社会成员在本国内的人体交易非法,但却没有规定本国公民在国外的人体交易非法。当社会成员无法在本国内获得人体组织或器官时,他们往往选择在没有法律限制并且价格低廉的其他国家进行人体交易行为。类似的生命行为管理政策造成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贬值,还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公民的生命价值的差等。
第二,社会管理者对不同个体生命权诉求的回应程度不同。社会管理者针对不同个体的出身、地位、身份、权势、财富等外在因素,有选择地以不同方式回应个体的生命诉求。譬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了公民的生育限额,针对公民超生收取一定数额的社会抚养费。若明星名流、富豪等社会地位较高或者财富较多的个体超生,他们可以选择缴纳社会抚养费,实际上是以权势或者金钱购买超生指标。若家庭贫困者超生,无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时,他们就有可能面临强制引产或者面临超生子女无法上户口等惩罚手段。尽管政府制定的管理措施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同样有效,但由于个体的外在条件不同,在实际上个体的生命权诉求不能得到公正、平等的回应与满足。
4 生命价值认知呈现差等正义的内在逻辑
生命的工具性价值与生命的终极价值存在辩证关系。在应然状态下,生命的终极价值优于生命的工具性价值,获取生命的工具性价值不得以贬低生命的终极价值为前提,当生命的终极价值与生命的工具性价值发生矛盾与冲突时,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主体应优先考虑生命的终极价值而不是生命的工具性价值。当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认知呈现差等正义,表现为受到个体的阶层、种族、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的影响,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仅在形式上平等,而没有实现实质上平等。生命价值认知呈现差等正义的内在逻辑在于因为工具理性压抑价值理性导致的生命的工具性价值对生命的终极价值的僭越。
在人们认知进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的理性逻辑与理性选择表现出两个维度:第一种维度是考量为实现人的某种目标需要选择的手段以及这一手段可能导致的后果,为达成人的目的而追求人类行为的效用最大化;第二种维度是将人本身作为目的,相信人类行为中蕴含着无条件的终极价值,不论手段与后果如何都要完成这一行为。理性的两个维度分别代表理性的不同偏向。马克斯·韦伯针对理性的不同特征,将第一种维度的理性归纳为工具理性,将第二种维度的理性归纳为价值理性。在应然状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两个侧面,不可分割,人的实践活动应当兼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但在实然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出现“失调”,工具理性不断彰显而价值理性逐渐衰落,人的理性偏向丧失合理的尺度。
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凸显甚至压倒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逐渐走向分离,甚至出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导致诸多社会病态现象的发生,使现代社会产生现代性危机。工具理性应当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价值理性则回答“做什么”的问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体视工具理性为圭臬。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现代性的信条与现代人的信仰。现代社会将工具理性视为信仰,将科学技术、法律制度、市场机制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随着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法律、市场、技术等工具出现“目标替代”或者说“目标置换”,由人类解放的工具异化为统治人类的工具。
在当代服务导向型公共治理模式下,实现实质平等的生命价值正在成为时代的主流。然而,由于工业社会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张扬以及对价值理性的忽视,社会管理者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知出现偏差,导致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或在具体领域中只弘扬生命的工具性价值而贬低特定个体或者特定群体的生命的终极价值。
生命的工具性价值与终极价值本末倒置,其根源在于部分社会治理主体还未正视特定个体或者特定群体的生命权诉求,他们没有认知到人的生命行为是权利而非义务,也没有意识到公民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并存才构成人类生命的共同体。人的生物差异性决定了其生命行为的个体性和复杂性。生命的特别的复杂性和生命行为的差异性,使公众诉求尊重个体差异的实质上平等的生命价值,要求治理主体树立更多元、更包容与更尊重个体意愿的生命价值观。
5 余论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随着知识的传播与发展、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知更加科学化和系统化,人的生命行为选择与人的生命行为表现方式呈现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趋势。在一些国家或地域,特定个体进行堕胎、代孕、人体器官移植、安乐死等已经具备合法律性,一些对当代医学与人工智能技术持乐观态度的社会成员甚至预期在未来社会中出现3D打印人体组织、定制婴儿、人的克隆等新型生命行为。
当人们回顾20世纪初期至中叶欧美等国家的所谓优生运动时仍不禁有许多感慨。按照今天人类社会对基因的认知,人体内并不存在所谓的“优等”基因与“劣等”基因,当时纳粹政权施行的基因清洗政策根本没有科学依据。然而将人的基因划分等级这一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匪夷所思的观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中,竟然能够得到许多自诩“正常人”或者“优等人”的社会成员的认同与支持。这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与社会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的生命价值认知不同。总体而言,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的传播与发展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嬗变,社会成员的生命价值认知在不断更新与进步。
无论古代社会的差等生命价值,还是现代社会倡导平等却趋向异化的生命价值,都没有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实质上平等,因而,导致社会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漠视特定个体或特定群体的生命权诉求,无视生命的复杂性和社会成员的差异性,压抑人们的生命行为选择自由,这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侵害。鉴往知来,在如今生物多样性、价值多样性的多元社会中,人类社会应当以更加包容和宽容的态度认知人的生命价值,尊重社会成员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承认社会成员实现其生命价值的方式是多样的。在承认和包容差异性的导向下,消除当下社会中潜在的人的生命价值的不平等。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德沃金.生命的自主权——堕胎、安乐死和个人自由的辩论[M].郭贞伶,陈雅汝,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2]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M].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黄健荣.当下中国公共政策差等正义批判[J].社会科学,2013(3).
[5]斯科特·卡尼.人体交易[M].姚怡平,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