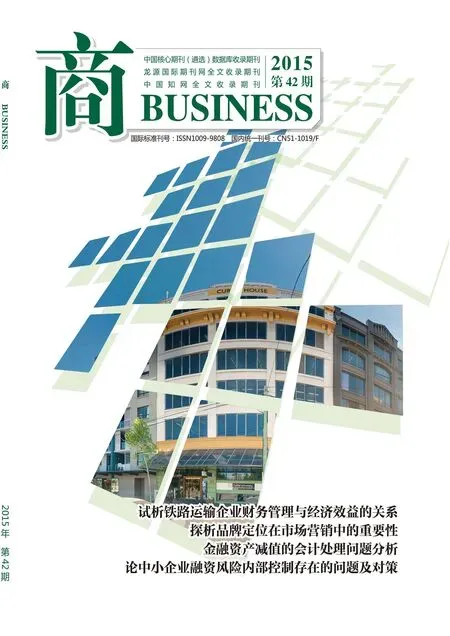文明的暗影
莫丽娟
摘 要:《蝇王》关于人性恶的揭示是深刻的,但是关于人性的讨论是否可以单纯的只从生物性的角度入手,而不考虑历史、社会和文明对人性形成发展的影响?本文从社会固有的权力制度出发,试图从成人世界固有制度对儿童的影响入手,分析人性恶真正的成因。
关键词:人性;社会制度;权力
小说《蝇王》雖以拉尔夫的获救作结,但面对如此的结尾却让任何人轻松不起来。戛然而止的结尾留给读者的是咀嚼不尽的反思,究竟是什么让美丽的小岛变为人间地狱?一曲人类毁灭的警世悲歌,是作者戈尔丁留给后人的“戈耳迪之结”。
戈尔丁曾说:“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1]戈尔丁所谓的那些岁月,是指作者年轻时参与二战时那段特别的经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同类互相厮杀的残酷,不仅仅在戈尔丁的心中,应该说,在所有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人心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蝇王》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觉察出这一点,中外学者在对《蝇王》进行解读时大都延续了作者的这一观点,将《蝇王》定义为一部关于人性恶的黑暗史。但事实果真如戈尔丁“性本恶”所说的这么简单、这么黑白分明吗?人性是否真就像基督教教义中那样的原罪?答案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西方的性恶论比性善论总是要深刻许多,但深刻并不意味着全面、客观。《蝇王》关于人性的剖析可谓煞费苦心,特意安排一群不谙世事小孩儿,逐步验证性本恶。但如果不顾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忽视客观历史的作用,将人性架空于社会之上来讨论,似乎有失偏颇。我国学者陈焜在《蝇王》刚刚流传到国内时就认为“戈尔丁抽象掉人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恶看成先验和超历史的东西,和我们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2]但陈焜也同时指出“戈尔丁对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他的绝望,虽然不十分阴沉,但是有一种深远的忧思。”[3]戈尔丁关于人性,关于人类未来的末世情调虽不免有些绝望,但就像加缪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说的那样,那些经历过世界大战、希特勒政权、集中营的人,那些今天不得不继续生活在原子弹威胁下的人,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是温情主义的。
但人们不经要问,戈尔丁笔下的“恶”究竟是什么?在过去的研究中,人性的“恶”总是与小说中儿童所表现出的残忍嗜血和互相杀戮相关,“恶”是从一系列人的行为中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行为本身是中性的,无关乎善恶,如《蝇王》和《珊瑚岛》中同样有猎杀野猪的情节,何以本质相同的情节在前者就是“恶”,是人类嗜血的表现,而在后者则是智慧和勇气的彰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对《蝇王》“社会群体”这一特点的把握。
《蝇王》历来被当做是英国荒岛小说特殊的一支,戈尔丁自己也承认作品是建构在对巴兰坦《珊瑚岛》戏谑的模仿上。戈尔丁对《珊瑚岛》热情洋溢、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情调不能苟同,遂在自己的作品中叙写了一篇完全相反的小岛历险经历。但在与过去包括《鲁滨逊漂流记》、《星银岛》、《珊瑚岛》等作品的比较上我们可以发现,《蝇王》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将过去人性善简单地置换到人性恶上来,而是在于戈尔丁由过去的个人历险转变到群体历险上来,这一转变极其重要,可以当做是解读作者人性恶观点的关键钥匙。
早期的荒岛小说一般都是关于主人翁一个人的历险,身兼人类各种优良品质,带着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优越感与自信,陶醉在文明感化的自豪之中。但随着西方工业社会发展而来的是各式各样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不禁对文明产生怀疑,以文明自居的人类似乎并不那么“文明”。戈尔丁将一群小孩儿放到一个优越而封闭的环境中,却走上了一条与成人世界一模一样的不归路,关于人性探索的问题也不言自明了。但作者看似完美的论证至少忽略了两个关键的问题:首先,戈尔丁笔下所谓的儿童果真一尘不染吗?其次,作者设计的是一群小孩落难于岛上,这就涉及到一个群体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矛盾制约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与先前个人英雄主义版的荒岛历险完全不同了,无论是拉尔夫一方渴望重建民主共和的文明派,还是杰克一方崇拜专制集权的野蛮派,都是在一个社会群体的基础上活动,无论什么制度的建立都是在对成人固有社会制度的模仿上。因此,关于文明的崩塌以及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上就不能再单纯从生物性的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上升到文明制度与人性二者相互作用的层面上来讨论。
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阿德勒在对人性的研究中将人性分为温顺的和专横的两种类型。在他看来命令式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儿童起了权力的示范作用,而且向他们显示了各种与享受权力有关的快乐。杰克就是小说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他的出现立刻让人感觉到他与周围人的不同。杰克带领他的唱诗班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那种森然有序、整齐划一的纪律性与四周乱哄哄的孩子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纪律所带来的优越感让原本正在登记姓名的猪崽子不敢轻易过问他们的名字。杰克对纪律的重视自一开始就达到一种扭曲的地步,即使在闷热的海岛上,他依然要求唱诗班的孩子们保持队列,不许随意脱掉制服。在杰克内心深处,早已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那就是严明的纪律高于一切,而纪律的维护则需要一个能力超群的领袖。
杰克对自己的能力无疑是满意的。虽然他也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儿童,这种“有能力就是王”的基本逻辑在他童年时期即已产生,并且深深植根于他的内心,这种思维模式影响了他之后一系列行为,包括与拉尔夫争夺权力,以及在最后哪怕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任然将拉尔夫视为最大的隐患而坚决要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另一方面,唱诗班的纪律制度对杰克手下的那群小孩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则体现出一种服从权威和服从有力量的人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唱诗班的孩子无论是一开始受过去文明制度纪律化的影响,还是后来在杰克的调教下成为了凶残的猎人,他们总是习惯性地听命于杰克。当拉尔夫试图建立一种更文明更民主的制度,并被大家选作新的头领时,他们也曾动摇过,也曾一度为拉尔夫的当选而欢呼。但当他们发现拉尔夫无力为大家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而杰克却能为大家提供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保障的时候,不仅是唱诗班的孩子们,包括其他一些更小的小孩儿则更愿意依附在有能力的人身边,这会让他们想依仗有能力的领袖来间接获取领袖那巨大的权力,他们会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这种类似成人世界强者为王的思维定势如此强大,甚至让拉尔夫都一度抵挡不住杰克能力的诱惑,萌生过放弃领导权,加入杰克一伙儿的念头。
结尾处,拉尔夫面对烧毁的岛屿,为童心泯灭和人性黑暗而悲泣。但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只是制度对人异化的一个最终结果,就像那个赶来营救他们的海军军官,他和他身后的那艘漂亮的军舰不也是掌权者手中的一枚棋子吗?在战争中又有多少人性恶的行为是由制度与纪律造成人的不思考而产生的?总之,如果剥离社会文化而但就动物性来研究人性是有失偏颇的,像格尔丁那样笼统地将社会文明毁灭的原因归罪于人性固有的恶,最终也是无法找到拉尔夫哭泣的真正原因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 格尔丁 《蝇王》 龚志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
[2] [3]陈焜 《人性恶的忧虑 谈谈威廉戈尔丁的蝇之王》 《读书》1981年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