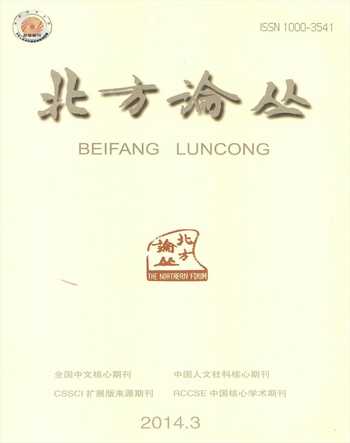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摘要]东汉迎来我国古代民间士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数量大增。他们长期活跃于乡里,凭借博厚的学识与道德,树立一定的私人威望,在地方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间士人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文化发展,与官方“道洽政治”的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另一方面,士人们努力保持人格与道义上的独立,或拒召不仕,或抗衡长吏,与官方“野无遗贤”的主导意识相冲突,客观上不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的有序运行过程中,民间士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东汉;民间士人;地方政治;社会权威
[中图分类号]K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3-0075-04
两汉时期,民间士人(既包括史书上所载的隐士、逸民等,亦包括处于未仕状态下的贤士,包括致仕、暂时赋闲在家者)的数量由少渐多,至东汉尤盛。以典型的民间士人——隐士为例,据相关统计,西汉211年,总得隐者22人,而东汉存在的171年间,隐逸之士多至百余人[1](p.189),故东汉被学者视为“中国古代隐士出现的第一个高潮”[2]。隐士数量的增多,使其势力由弱瑧强,壮大了民间士人的力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前,学界对东汉民间士人特别是隐士的关注较多,亦有涉及其与时政关系者,但鲜有集中论述民间士人群体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者。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正史《后汉书》中的隐士资料为主,考察活跃于当时的民间士人在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和拒召不仕、抗衡长吏等方面的表现。从中可见东汉民间士人掌握、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知识、道义和声望资源,与官方意志相一致或相抗衡,隐然成为一种社会权威,对地方社会政治施以各种影响。
一、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东汉民间士人以其道德、学识树立个人威望,凝聚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敦励风俗、道德教化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官方“道洽政治”的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平息乡讼
在古代乡里争讼中,民间调停是重要裁决方式之一。东汉时期,很多民间士人居于某地,充当了争讼调停、平息者的角色,发挥了较大作用。如《后汉书》载,司马均“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3](p1240),王烈“少师事陈寔,以义行称……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3](p.2696),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 [3](p.1260);陈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3](p.2066);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3](p.2208);高凤“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凤(高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謝罪” [3](p.2769),等等。
从上举数例可见以下两点:第一,在民间士人的道德感化(如前三例)和合理调解(如后二例)下,民间社区出现闾里“不争讼”、“争者怀感,投兵谢罪”、“不直者终无敢言”和“退无怨者”、“无怨”的局面。尽管平息解决争讼是地方政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为政无讼、无为而治是古代治政者的最高理想。东汉民间士人利用个人的道德与声望将可能诉诸官方的争讼通过协调解决,使社会争端减少,客观上节省了地方行政成本,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第二,民众有各种纠纷者,多选择请民间士人去调停,比较信赖和依靠这种民间力量的德行感化,且效果颇佳,出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民间士人调解民间争讼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当然,在民间事务的解决中,如果民间力量暂时阙如或不能奏效时,民众才诉诸官方,请求公法断决。在汉代之后,这种民间事务解决途径及先后顺序亦与此相仿,庶几成为一种模式。
2.感化民众
(1)感化凡庸。民间士人常以高尚之德感化凡庸平民,和美当地风俗。史书中类似的例子较多。如马瑶,“隐于汧山,以菟罝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3](p.2772);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3](p.2554);王扶,“少修节行,客居琅邪不其县,所止聚落化其德”[3](p.1298);孔嵩,“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3](p.2679),等等(其他例子还有李弘、徐稺、冯良、周党等人,俱见《后汉书》本传)。这些民间士人每到一地,则使“所居俗化”、“里落化其仁让”、“所止聚落化其德”、“子弟服其训化”,不分老少,皆被德化,其在局部地区的教化作用之大和有利稳定政局的客观之效,由此可见。
(2)感化坏恶。民间士人感化顽劣、导其向善。例如,周燮“居家清处,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宾,乡曲不善者皆从其教”[3](p.1742);又如,一代名士郭林宗,对“性轻悍,与人报仇,为郡县所疾”的宋果,“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敕”[3](p.2229);再如,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3](p.1301)。在最后一例,淳于恭帮助盗果者收采或伏草免惊偷禾者,多有夸张之处,但民间士人以高德自居,借此来感化不善,应实有其事。这在其他例子中亦不鲜见(如郭太、包咸、姜肱、陈寔、王丹、王烈、徐稺等人,各见其《后汉书》本传)。后来的正史中也有类似例子,如《宋书·隐逸传》载,沈道虔“有人窃其园莱者,还见之,乃自逃隐,待窃者取足去后乃出。人拔其屋后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乃令人买大笋送与之。盗者惭不取,道虔使置其门内而还”[4](p.2291);再如,《梁书·处士传》载,范元琰“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菜,元琰遽退走……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5](p.746),皆此之类。从中可见东汉民间士人高行之影子,或可视为受其影响所为而致。当然,如理解为历代民间士人特别是真正的道隐之士“性分所至”[3](p.2755),亦无不可。
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活跃在乡里的汉代民间士人劝导良善、感化坏恶,收到了“不善者皆从其教也”、“改节自敕”、“里落化之”等效果,承担着重要的教化民众功用。这种教化虽然独立于国家权力控制下的政治教化之外,但客观上有利于地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而追溯这些民间士人的高尚德行之来源,或许与其崇奉儒家“修己以安人”[6](p.159)、“在下位则美俗”[7](p.120)的淑世情怀有关,亦有受道家崇尚厚道、玄德的影响在内。国外有学者将其称为“儒家典范性隐逸”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退隐的君子可以通过自身的高洁品行影响周围的人,移风易俗,而且这些典范性隐士们大多也正是努力去实践那些道德品行中本质的儒家理想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同时也从其他各家思想中得到启发”[8](p.163),洵然确论。
3.普及教育
除了以德能解决争讼、感化民众之外,民间士人还大力举办私学,普及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众多学子随其求学的现象。师徒关系的结合、扩充乃至壮大,使民间士人这一群体庶几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对时政的影响亦大。如史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3](p.2588)这种以学问相号召、有道义相结合、流动性极广的民间士人团体,于公权之外树立的威信,“分争王庭,树朋私里”,足以显示出其作为民间社会力量的强势一面。
私学始于春秋末,孔子发其嚆矢,至两汉空前发达,又以东汉为最。《后汉书卷五十二·崔骃传》记载:“方斯之际,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其数量之多可比“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艺拱把不为之数。”[3](p.1714)。 东汉民间私授、私学之盛,从以下数例亦可得详证。例如,杨厚,“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3](p.1050);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 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3](p.1243);丁恭,“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3](p.2578);公沙穆,“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3](p.2730);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3](p.1207)等(其他例子还有王良、刘昆、洼丹、任安、张兴、杨伦、郎顗、吴佑等,多见其《后汉书》本传)。
从上举例子中可见,民间士人在山林大泽或乡邑里巷传道授业,莘莘学子慕名而来,“弟子自远方至”或“远方至者常数百人”,人数庞大,动辄成百上千,私学盛况,可见一斑。兴盛的私学培养出了更多的知识分子,使民间士人也渐多起来。民间士人的增长,便于普通民众学习知识,可以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和开化程度,促进社会进步,提高文明觉悟。
从上所见,东汉民间士人解决民讼、化民向善、弟子成群,以德性、知识、声望为资本形成一种强大的民间力量。在传统地方社会和政治运作中除了官方正式的公共权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外,在民间还存着各种非正式的私人权威亦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士人、乡绅、游侠、族长等个体或群体以不同的优势(德学、财富、德力、血缘等)形成某种强力,影响着民间事务和地方时政。进而言之,在传统地方社会和政治运作中一种“公权一元,私威多元”的格局,而士人是私威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早在东汉时期,各级统治者都有意征辟举荐他们入仕,“通过扬褒隐士,宣扬道德修养,崇尚廉洁,从而有助于教化和澄清吏治”[9]。当然,有的民间士人心动而往,参与政事,与地方时政相谐而行[10](pp.85-87);但也有不少人拒绝征召,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相抗,对地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下文就此略加论述。
二、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政治的影响
儒家主张,士人应当拥有刚毅独立精神,所谓“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11](p.1582),“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11](p.1584),“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7](p.27),这一点被历代有志之士所继承,东汉民间士人亦然。他们通过博学高德形成一定的优势,以道统对抗政统,以私威抗衡公权,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对当地时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拒召不仕
此类事例在《后汉书》的《逸民列传》《独行列传》《儒林列传》里记载较为集中,例如,冯冑、庞公、台佟、高凤、孙期、丁恭、雷义、王烈等。见于其他籍记史载者亦不乏先例,例如,王扶,“国相张宗谒请,不应,欲强致之,遂杖策归乡里。连请,固病不起”[3](p.1298);廖扶,“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异,亦无所对……太守谒焕,先为诸生,从扶学,后临郡,未到,先遣吏修门人之礼,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3](pp.2719-2720);仲长统,“游学青、徐、并、冀之闲,与交友者多异之……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3](pp.1643-1644);张楷,“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3](p.1243);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3](p.1953),等等。
从上述诸例可见,民间士人甘于置身乡里甚至野林,不肯入仕,以私威对抗公权。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较复杂,有的纯粹是因个人性格爱好,或惧于政治斗争的险恶而拒绝仕宦,但更多的是介于隐仕之间,有志于淑世济生。对于后者而论,在出处默语的矛盾心理支配下,他们有令不遵地逃避和反抗时政,只是抗争无道当局,是不得已之举,内心深处则充满对有道将来、兼济天下的渴望与期待。在积累了更高的声望和资本,将来一有时机,就欣然入世。在古人“从道不从君”的入仕观点看来,一时拒召不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从政,即这部分民间士人“退隐的本身即是对‘无道社会的反抗,并非全然是消极避世,因而实际上也就参与了现实政治”[2]。
2.抗衡长吏
除了拒召不仕之外,民间士人还以其固有的知识和道德权威抗衡地方长吏,以道统对抗政统。以下有几则较为典型的例子,如杨后,“益州刺史焦参行部致谒,后(杨后)恶其苛暴,时耕于大泽,即委锄疾逝。参志恚之,收其妻子,录系,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12](p.8)。又如,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吏,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3](p.1695)。再如,逢萌“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答。太守怀恨而使捕之。吏叩头曰:‘子康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祇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3](p.2760)。
在这三例中,最明显者当属逢萌。他僻居劳山,太守召其出山被拒后,强行征捕之,却召到周围民众的武力捍卫,竟无果而终。从中得见民间士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傲视地方府吏之势,灼然可睹。而另两例,一者为杨后,他厌恶刺史苛暴之政,避而不受其谒见,即使妻子被录系,也不肯露面。姜岐亦宁愿受官场中桥玄等人趣嫁其母的羞辱,仍坚卧不起,不做府吏。另外,当太守桥玄与姜岐关系弄僵、骑虎难下之时,“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从中斡旋,桥玄方罢休,而郡内士大夫从中谏说、求请或施压,使执意让姜岐入仕的郡守最终改变初衷,示以妥协。此类士中亦不乏在野为民者,足见民间士人对地方行政所具的较大影响力。
以道德和学识对地方社会政治施以相当大影响,其之外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以崇高的德学声望确立一定的权威,为民理事、教化大众、举办私学、普及教育,有益于地方时政。
三、余论
综上可见,东汉民间士人依其知识和道德的优势教化民众,或以之来抗衡当局,彰显其人格道义上的独立性,客观上对官方的政治教化有益有损。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其一,从现有记载看,民间士人对于时政与社会的影响方面的史料,东汉多于西汉。这一点或许可以证明,东汉更多地依赖社会性力量如民间士人,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教化来维持民间社会本身和政治的运作,故留下的记载较多。这不同于西汉多为官方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如派遣循吏、大兴官学、诏令指示、派遣使者采风等)来治理民间社会。
其二,东汉民间士人作为当时较强的社会势力,对地方政治施以各种影响,与西汉时期社会权威多系于父老、豪杰或游侠的情况不尽相同。这既说明汉代各种民间力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情况各异,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力量知识化特别是儒学化的倾向。而这与武宣之后汉王朝奉行表章六艺、尊崇儒学的治世之策有关,自从那里起,汉朝开始从“霸王道杂之”向“纯任德教”[13](p.277)、“多行宽政”[3](p.1727)转变,直到东汉开国之主刘秀确定“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3](pp.68-69)的治国之策,皆为其征。当然最根本原因是民间士人特别是隐士,本身承载的学识道德具有独特的魅力,加之有政治力量的推崇,即“隐士是理想道德价值的表征符号,隐士建构身份的种种卓异行动,契合了社会心理对超越性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广泛的心理共鸣。这是社会接受隐士、尊仰隐士的心理基础。而政府搜求隐逸、擢拔贤良的政策,推动并强化了社会的尊隐风气。隐士作为一种身份类型,被置于伦理道德体系的顶峰,在社会声望评价方面处于常人不可企及的位置”[14](p.209)。
其三,东汉民间士人选择隐居于乡,不涉或少涉政治,并不影响实现其淑世从政的情怀。因为在儒家看来,为政以德,修身以德是从政的前提,治国平天下必须身修。个人一身正气、修己敬人即是从政,所谓“政者,正也” [6](p.129),“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6](p.138),以至他们认为,孝悌即是从政的王道,“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6](pp.20-21) ,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修齐治平”一体化的伦理政治是儒家泛政治论的核心,对后世士人的影响极大。东汉民间士人亦不例外,他们多以隐为仕,在自我修身与教化他人中实践这种泛化意义上的从政。
总之,从东汉民间士人的作为来看,他们掌握了相当的知识、道德和声望资源,形成一支较强的社会势力,与官方意志相谐或抗衡,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的有序运作过程中,以其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仁祥.先秦两汉的隐逸[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5.
[2]黄宛峰.论东汉的隐士[J].南都学坛,1989,(3).
[3]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4]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8][澳]文青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9]邹明军.东汉逸民的归隐及其与统治者的互动——读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1).
[10]巩宝平.汉代民间力量与地方政治关系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1]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李昉,等.太平御览(第5册)[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胡翼鹏.中国隐士身份建构与社会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晓校]